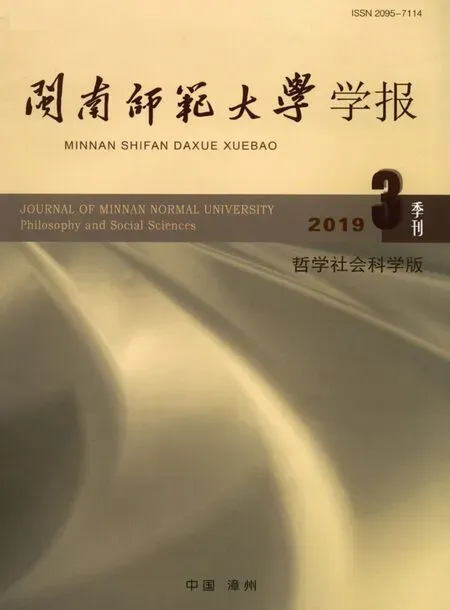情爱与政治
——历朝李杨故事叙事立场研究
柯佳玮
(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绍兴312000)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哲学史演讲录》中早已指出:“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 ”[1](P112)在具体史观的参与下,人们不仅会过滤那些自己不了解事物的存在,也会因习焉不察的固有成见而使熟悉的东西成为特定意识形态的注脚。 李隆基和杨玉环爱情故事的演化中唐以来便非罕调,在文人墨客的重塑下,故事逐渐“失真”。 从叙事立场的角度上看:经学家意在警世,道学家强调禁欲,才子歌咏佳人,流言家散布宫闱秘史。
在李杨故事的爱情美谈中,实际上是魅影幢幢,种种细节无法窥究,以此为土壤滋养出的民间传说与文人思考也因此不绝如缕。 在结合故事文本,梳理作者叙事立场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关于李杨爱情的评价,并没有形成泾渭自明的二元分殊,也没有一脉相承的统一观点,或是一方转向另一方的有迹可循的发展脉络,但总体论之,政治讽刺立场多于情爱歌颂立场,李杨故事中大多数,除了一般人所眩目如痴的宫闱爱情之外,更有士子对唐朝兴衰转捩的现实思考。
一、历朝李杨故事政治立场叙事研究
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勾连着安史之乱的时代背景,文人探讨亡国根源之时,天子万千宠爱与贵妃倾城美貌,与大唐由盛转衰的异变相绾合,便成了警戒后人的绝好载体。 历代作品中,所持政治批判立场的占大多数:以唐代为例,杜甫是最早察觉到这繁华幕后的危机,“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丽人行》)铺排出杨家兄妹的奢靡生活;中唐刘禹锡“军家诛戚族,天子舍妖姬”(《马嵬行》),言语中直斥杨玉环为妖姬;继而杜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以“妃子笑”暗对“百姓哭”,批判统治者纸醉金迷的自私作派。 以宋代为例,秦醇《骊山记》、《温泉记》则借杨玉环与安禄山的轶闻展开对“红颜祸水”的思考;苏轼吟咏的“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荔枝叹》)中,君王沉迷酒色、劳民伤财,依稀可辨。 以明代为例,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喻世明言》、詹詹外史的《情史》中,明言安禄山与杨贵妃私情,昭示后妃失德的乱象。 以清代为例,禇人获所作《隋唐演义》、孙郁的《天宝曲史》不约而同地暗示出后妃失德、权臣独大是唐朝由盛转捩的主要因素。
(一)中晚唐:盛世幻灭的追忆
安史之乱爆发后,曾涌现出一批以杜甫为代表的、批判李杨爱情的作品,这些人伤痛未愈,迫切需要一个为自己为民族不幸命运承担责任的肇事者。 在核心政坛之外,无法得知王朝弊病的情况下,联想起曾经的铺张奢华,君王荒淫、后妃乱政的评判,随之便一拍即合。
但文人叙述不是非黑即白,政治立场的角度也并不是一味地贬抑情爱,李杨故事在中晚唐文人心中,凝聚为李唐帝国繁盛的印记,此时诗歌中的批评色彩渐淡,更多的是对于盛世的憧憬与对于衰世的感慨。例如元稹《连昌宫词》中:“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阑干立”,表面上是以一位宫内老妪的眼光勾勒出李杨二人凭栏远眺、牵挂彼此的姿态,其后“舞榭欹倾基尚在,文窗窈窕纱犹绿”表露出物是人非的无奈感慨,并非是感官的行迹。 追忆开元光风霁月的时代氛围,是将当年盛世繁华与如今山河破败形成对比,锋芒所指不在美化歌颂前代功业,而在于为今日的困境找寻出路。 晚唐李商隐长叹:“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马嵬》),帝王妃子虽位尊人上、身世显赫,但也因此不得不始终如履薄冰,连平凡夫妇之间最基本的白头偕老都难以实现,哀叹李皇抛弃杨妃的爱情悲剧,意涵在于托出古往今来理想与现实相“对立”的人之共性。 于君王言,这种冲突体现在美人江山难以两全,于文士言,这种冲突压迫他们不断囿限在求仕与不得的囹圄中,借帝君的无情抒发士人渴望获得知遇、建功立业的志向。
(二)宋代:新叙事模式的批判
李杨故事在宋代的展演有如秦醇的《骊山记》和《温泉记》、苏轼的《荔枝叹》、真山民的《杨妃》、无名氏的《宣和遗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等,他们承袭了杜甫的政治批判立场,并展演出了新的叙事模式:将安禄山或梅妃嵌入李杨一对一式的爱情中。 北宋秦醇的《骊山记》中书生张俞游骊山“求古遗事”[1](P30),路逢田翁,通过田翁对其祖上的回忆叙写李杨爱情悲剧。 文章从骊宫说起,加入了安禄山抓伤杨贵妃乳房、贵妃出浴后唐明皇与安禄山作诗咏乳、野鹿衔出宫花暗指贵妃有私安禄山、安禄山因恋贵妃起兵渔阳等一系列安杨的香艳故事。 传奇叙事意在窥探宫闱秘事,但安禄山与杨贵妃之间暧昧的指向并非空穴来风,反应的是民间的共识。 文中对于安史战乱的起因直接由安禄山点明:“吾之此行,非敢觊觎大宝,但欲杀国忠及大臣数人,并见贵妃叙吾别后数年之离索,得回住三五日,便死亦快乐也”[2](P34)。 但杨国忠最后被安禄山所杀,原因并非“清君侧”,而是他私自扣下了安禄山赠予杨贵妃的私信和珍宝,阻碍了两人的私情。 安禄山的行径下总有杨玉环的影子,实际上是作者对女色祸国的暗示。
梅妃的形象最早见于佚名所著的《梅妃传》,据鲁迅、程毅中考证,此作创作于南渡前后,是梅妃形象的发端作品之一,并以传记的形式记录梅妃旧事。 从花的意象上看,梅清雅高洁的形象比起秾丽丰满的牡丹,更符合宋人崇尚内敛的心态。 文本中将梅妃塑造为一个优雅贤淑、纤瘦恭顺的有德妃子,与雍容华贵、端庄艳丽的杨贵妃相对比,除了有一定娱世悦人的目的,更多的现实诉求落脚于鉴戒。 在梅妃先入为主的情况下,杨玉环成为李隆基与梅妃之间从中作梗的第三人,梅妃的遭遇也就更容易受到大众的同情。 《梅妃传》中先讲明梅妃承欢圣意时“海内无事,上于兄弟间极友爱”[3](P90)、君臣和睦相亲的场面,进而与杨贵妃狐媚祸主、使得梅妃遭弃进行对比,甚至不惜在结尾直接批判道“(唐明皇)晚得杨氏变易三纲,浊乱四海,身废国辱”[3](P100)。
(三)元代:民族压迫的感伤
对李杨爱情的政治批判立场在元代展演出的命运兴亡之叹,更像是对中晚唐价值取向的延伸。 元代奉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导致汉人与南人的地位空前低下, 现实的隐痛使他们在回首大唐兴与衰的落差时,不由得产生人生如梦、世事无常的虚无感。 例如白朴的《梧桐雨》以唐明皇为主线,从政治的角度看,他自满骄纵、贪于淫乐;从情爱的角度看,他迷恋美色、深情贵妃;从命运的角度看,他无力回天、窜身失国。 从奢侈骄纵到孤独终老,从大权在握、美人在侧,到幽居宫殿、哭祭杨妃,在唐明皇形象的变迁中,但更多的是表现他在命运面前无可奈何的心境。 白朴借助李杨悲剧浇心中块垒,涉及到人的自身境遇以及对生命各种困难阻隔的反思,勾勒出的是那个时代汉人负重前行的切身隐痛,这是终身无法驱除的,如附骨之疽的悲哀。 元朝作品中,《梧桐雨》的政治感伤情绪并非罕调,同持此调的还有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关汉卿的《哭香囊》残篇。
(四)明代:八股盛行的批判
程朱理学在明代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对于李杨爱情的批判催生了诸如冯梦龙《警世通言》与《喻世明言》、吴世美的《惊鸿记》、詹詹外史的《情史》、钟惺的《混唐后传》等作品。 《惊鸿记》之名假托梅妃得宠时所创的惊鸿舞,在今非昔比中诉说梅妃的无奈与痛苦。 文章在野史轶闻中构建出的梅妃温婉淑贤的形象,对于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进行文学的重组与扩充,旨在揭示唐明皇肆无忌惮追求淫乐的恶果,传递的是荒淫奢靡导致国乱殃民的政治悲剧。 传奇第一出《本传提纲》便点明了文章主旨:“看往代荒淫败乱,今朝垂戒词场”[4](P68),从情爱角度上看,全剧对于梅、杨二人的争宠承袭贬杨褒梅的主张,体现在唐玄宗宠爱梅妃时歌舞升平的祥和氛围,宠爱而不专爱,故而社会安定、政局无端。 随后,杨玉环进入后宫,朝政便被唐玄宗所冷置,孰优孰劣,可见一斑。 从政治立场上看,第二十七出《马嵬杀妃》中借军士们之口托出作者对安史之乱成因的分析,认为导致国家危亡的原因有二,一是小人当权,二是君王失道,杨国忠前朝蝇营狗苟,杨贵妃后宫魅惑圣心,矛头直指杨家:“杨国忠苛刻聚敛,迎合君王,圣上因此宠他,骤迁相位,擅意诛杀军官,你道军官减下我们钱粮,也出无奈,要输到他相府去。君王朝欢暮乐,恋酒迷花,怎知有我们?如今又苦死用着我们也。 ”[4](P68)可见李扬爱情不再被视为大唐气象下的帝妃轶事,而是作为亡国之音备受谴责,文人的政治批判立场更为显著。
清代作品中李杨爱情多是论述朝代兴亡下的一个小章节,作者从宏大叙事的角度出发,例如《隋唐演义》、《儿女英雄传》、《女聊斋志异》等作品,其间的政治批判色彩多是通过杨玉环与安禄山私情的描写、突出杨玉环“悍妇”的形象得以呈现,作者的话外之响在于抒发朝代兴亡更迭的感概,更多的是娱乐市民的目的,而洪昇的《长生殿》属于情爱立场,后文会单独作述,故在此不多加展开。
二、历朝李杨故事情爱立场叙事研究
李隆基仪表俊丽、杨玉环国色天香,加上人们对红墙绿瓦背后宫闱深深的种种臆测与憧憬,使得这段结合演化为神圣庄严的爱情神话。 故而白居易提笔《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洪昇《长生殿》假托唐明皇唱道:“愿此生终老温柔,白云不羡仙乡”[5](P431)。 然而,墨子有云:“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本该是理想的爱情范式,却因马嵬驿的香消玉殒,带上悲剧的烙印,但这份绝情却远比有情更为动人,因而徐寅《开元即事》追怀道“未必蛾眉能破国,千秋休恨马嵬坡”,袁枚《明皇与贵妃》哀叹“到底君王负旧盟,江山情重美人轻”。 而正如牛郎织女由鹊桥相会,梁祝身后化蝶翩跹,在文人笔下,长生殿的相会是李杨爱情的延伸,成为悲剧的美好补充。
(一)唐代:情爱视域的初生
中唐白居易对李杨爱情持着较为复杂的态度,但其开启了肯定李杨爱情的先河,为此后历朝的情爱立场叙事奠定了基础。 七言歌行体的《长恨歌》所关切的更多在于李杨二人生死不离、超脱生死的爱恋,这是迥别于以社稷为先的全新概念。 故而后代读者在阅读接受《长恨歌》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作者不断规避着李杨在历史现实中的许多负面定位,将二者的关系纯粹化,归为风流君主与名门闺秀初恋式的结合。 开篇“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李隆基身为人父、强占儿媳的丑闻被抹去,变为真诚专一的情郎;而杨贵妃寄养叔家、嫁予寿王、敕命出家等复杂经历也一律归零,成为深闺丽人。 贵妃的自缢与缘由仅仅书道:“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不再钩沉“马嵬之变”的历史真相,而是侧重在塑造出一个无力的长情君王形象:“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龙御回宫时用“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与之呼应,让马嵬坡成为李杨爱情的物质载体与精神空间。 《长恨歌》中李隆基的相思占了大量的篇幅,天人相隔的相思驱遣于笔下,阴阳两界的间隔铸造李杨爱情的纯度,不仅推翻了前人对二人爱情的质疑,而且影响了后世美化李杨爱情的文学倾向。 正如王新霞说所:“人们像讲故事一样回忆着唐王朝历史上最兴盛的一页,对于有关李杨的传闻更是津津乐道、添枝加叶,使之愈来愈带有传奇色彩。 在中唐的各种传说中,开元时代是作为一个与现实对立的、美好的理想境界而加以描绘的。 ”[6]回归到作者身上,永贞革新的破产,“八司马”的斥逐,瞬息万变的朝政令其感受到中兴不易、世事变迁,更容易唤起他对开元盛世的维护之情。 无论是鸿都客的寻觅,亦或七夕月下盟誓,白居易执意于杨玉环香魂的背后,实际上是将李杨爱情上升为大唐帝国的繁盛象征,对杨贵妃的追忆即是对于开元盛世的追忆,于是不忍对于开元盛世的缔造者李隆基施以苛责,也不忍让李杨爱情因安史之乱而简单落幕。
(二)清代:至情论的展演
尽管外缘性因素形成了文本的架构和审美空间的某种创作风向,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作品产生仍是未知数,作家从环境中收集材料引发感思进而建构创作整体,因此活在同样时代背景下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叙事立场,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士人也可以持有相同的叙事立场,进而组织出相近的有机整体。 这种情爱立场的展演,在《长生殿》中也清晰可辨。 洪昇在《长生殿·例言》中写道:“予撰此剧,只按白居易《长恨歌》、陈泓《长恨歌传》为之。 ”[7](P1),但承接了白居易对于李杨爱情的认可,并非意味着全盘接受白居易的看法,《长生殿·自序》中提到“余览白乐天《长恨歌》及元人《秋雨梧桐》剧,辄作数日恶”[7](P1)“辄作数日恶”不意味着洪昇对于白居易和白朴作品的否定厌恶, 而是洪昇对于他们在文本中建构的李杨爱情悲剧的感触极深,不忍其草率收场。
洪昇透过《长生殿》表现出的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显示出了较强的个人主义与理想色彩。 戏曲中大量扩充了“情悔”的章节,虽然锦绣江山沦为欲望过度放纵下的牺牲品,但洪昇仍试图用李杨二人对过往穷欲的忏悔与反思来完成他对“人间至情”的拥护。 在后面七夕情誓、月宫重逢情节里面,流露出的是作者天地人相互交感有无的思想,在李杨的生死情爱面前,天地都为之感染,因此“情”成了人性之至,成为作者救治万民的良方。 虽然不排除洪昇写作有娱乐市民的立场,但他客观上完成了对封建伦理和两性色欲的超越,转向普世的情感需要,而这也成为了洪昇创作的动力来源。 但这终归是一个帝国由盛而衰的悲剧,因而在《长生殿》后半部玄沓飘渺的“情悔”场景里,总透着“情缘总归虚幻”的氛围,“大量笔墨着力描写李、杨之‘悔’,不仅与塑造人物形象,推动剧情发展有关,同时还意在表现当时的文人阶级,尤其是明朝遗民对晚明士人风习和生活态度的一种追思与忏悔”[8](P220)。
三、关于李杨故事的外缘因素分析
固然文本肌质与构架是作者基本追求目标与实践方向的表态,但这也会因为各代纷杂多元的现实传递相异的主题。因而时代背景的解读,有助于理解李杨爱情不同时代不同接受视域的形成原因。每一朝代的文化本身在它的内部基转中有不同的操作,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这个机制已经完成的时候,去考量它对文本建构与文人叙事立场的确立有哪些可能性的因素。
就唐代而言,文人对李杨爱情的态度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以杜甫为代表的诗人见证了裘马轻狂、青天揽月的盛唐大厦轰然崩塌时刻,于颠沛辛酸中目睹了国家破碎、百姓失所的局势,现实景象介入他们对于李杨爱情基本立场的审视,他们缅怀开元富庶而无暇对盛唐的残垣断壁进行更多本质性的分析,便匆忙投入了“女色惑主”与“荒淫误国”的思维模式之中。 时隔五十年,白居易的爱情解读突破了前人视野,在李杨爱情中熔铸了更宽广的情感表达,虽然这种情感表达仍未跳脱礼教范围,并有意回避了两人酿成的社会恶果,但就作者叙事立场而言,白居易为代表的中唐已与前人产生了分歧。 正如蹇长春所说:“面对苦难现实的中唐人民,特别是对时事敏感的文人世子,当他们渴望的‘中兴’终成梦幻,于是抚今追昔,借缅怀‘开元盛世’来寄托其盛世难再的叹恨与感伤,便成为一种时代思潮与风尚”[9](P497)。 溯其外缘,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等现象愈演愈烈,人们意识到开元盛况难以重演,李杨爱情便承担起盛唐时期逸兴遄飞美感的诗意化表现。
有宋一朝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局面,政治上的动荡不安造成了文人政治上的忧虑与困扰。 宋代“文人和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文人、官僚、政治家三位一体的现象较历代更为突出”[10](P4),他们从国家机器内部关注政局,对李杨爱情的态度有了新的解读,形成前所未有的“大否定”局面,更强调鉴戒的叙事立场下,情感立场的赞美成为绝唱。 而宋代经济繁荣,人口稠密,瓦舍勾栏应运而生,此时的文学创作是受到市民阶层审美风尚,世俗化的创作倾向更为明显,例如对男女艳情的大胆指向与描写,以及避开了唐人对李隆基与杨玉环之间一对一的情爱叙述,新晋梅妃或是安禄山组成三角关系;正如李军均所说:“(宋代传奇小说的)著述者的著述可以成为一种‘商品化’的流通物,从而具有‘商品性’,它必然要考虑到市场的阅读需求,也因而具有俗化特征。 这一俗化特征正是其编选的目的所在。 ”[11](P13)由此可见,宋人对小说娱乐功用的重视大大增强,小说的完成能否得到市民阶级的认可,已成为当时李杨情爱叙事的重要影响因子。
元代的统治集团由少数民族构成,民族制度上划分等级,在实际操作中将不同等级区别对待,《元史·百官志序》云:“官有长职,位有长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12](P72),元代文人的不幸催发了戏曲的繁盛,因而以叹世为主调,感慨消逝之物,以及对世界的变幻无常深感虚无悲哀的意绪,构成了时代精神特征在文学范畴中的投射。 在对人生苦短的感伤中延展出及时行乐的愿望,在历史兴亡的无奈里回避现实矛盾的思索,其背后,却是对自我价值悲剧性的体认。 《梧桐雨》中帝王的歌饮夜宴的追忆的现实意义更多在于与今日的苦寂清冷相对比,呈现出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乐极哀来的宿命观,并通过否定人生快乐的价值指向,在盛唐的兴衰与李杨爱情的流转变化中印证人生的无意义。
明清之际统治者权欲膨胀的高压政治,在思想领域内出现了不同的表征。 在明代,兴起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良心”说和以李贽为代表的“童心说”,形成高举自然本性旗帜的个性解放思潮。 而清初学者“虽然反对新学空言心性,甚至诋毁李卓吾,但实质上却接过李卓吾‘人必有私’的命题,肯定私欲的合理性,不同的是他们进而以此为基点将‘欲’、‘理’统一起来”[13](P201)。 儒学全面兴盛之下,文人对天理人欲的思考打破了全盘接受传统的思维模式。 而清代戏曲传奇的盛行除了市民阶级审美风尚的不自觉导向外,也与统治者严苛的思想恫慑有关。 “在统治者政治措施的严酷打击下,清前期的传奇作家既无法掩藏内心中的怨愤,又深深摄于统治者的淫威,他们往往‘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吴伟业《北词广正谱序》,李玉《一粒庵北词广正谱》卷首),形成前所未有的历史剧创作热潮。 ”[14](P315)在严苛的思想控制下,文学创作的历史意识大大增强,通过历史真实建构出的文学作品数量增加,清代文人更多深慨历史的兴衰之变,在寄托个人情愫的同时探索经世之道的途径。
由于各种因素,历朝历代文人对于李杨爱情的叙事立场没有呈现出由政治立场向情爱立场,或是由情爱立场向政治立场的单调转变,而是在各代文人的接受中显现出差异性。 但这种差异性绝不是没有前因后果酝酿的凭空出现,而是隐在历史的土壤里互相支援、联络,最后产生了化学反应,从而诞生了各朝李杨爱情叙事的独特性。 由于李杨爱情处于大唐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各朝代在阅读接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兼有对唐代社会剧变的反思,其中书写者多为科举士人,或是科举士人的周围文人,所反映的是士人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