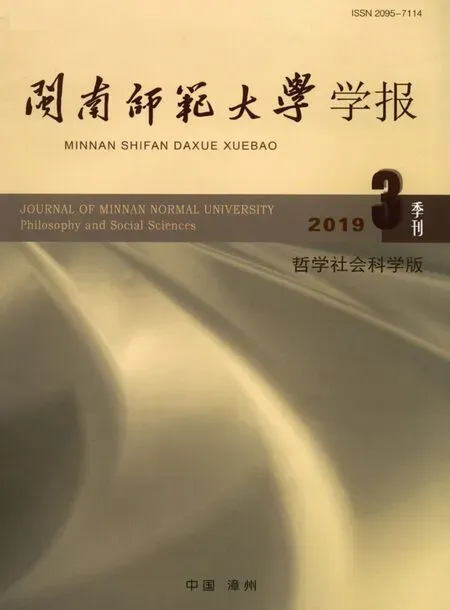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叙事与反思
——《老生》与《耶路撒冷》的比较浅论
黄 萍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学前教育系,福建 漳州363000)
贾平凹的《老生》与徐则臣的《耶路撒冷》这两部长篇小说都于2014 年推出,并且它们还同时获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举办的“当代·长篇小说年度论坛” 评选的“长篇小说(2014)年度五佳”。 这也是本文将其进行比较的主要缘由。《老生》以一个唱师的口吻,叙述了中国近100 年的历史发展进程;《耶路撒冷》则以四个出生于20 世纪70 年代中国小镇的年轻人为主线,通过他们“到世界去”,寻找心中的“精神寓所”——“一种让自己心安的生活方式”[1](P284)的过程,也讲述了中国这100 多年的历史变迁。 两部作品都试图通过对中国近百年社会发展的深切关注与呈现来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得与失,它们在创作中既有相似的一面,却也表现出诸多的不同。
一
贾平凹在《老生》的“后记”中谈到:“那我就是有责任心的人么。现在我是老了,人老多回忆往事,而往事如行车的路边树,树是闪过去了,但树还在,它需在烟的弥漫中才依稀可见呀”[2](P289),“时代风云激荡,社会几经转型,战争,动乱,灾荒,革命,运动,改革……太多的变数呵,沧海桑田,沉浮无定……到我年龄花甲了,却怎能不想不讲啊! ”[2](P291)因此,他的《老生》以四个相对独立又略有关联的故事,讲述了中国近100年的历史。 小说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革命战争写起,写到解放后的土地改革、文革中农业学大寨、1978 年改革开放直至21 世纪的经济建设,可谓具时代视野。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老生》主要是从农村的变迁来呈现中国近100 年的历史, 贾平凹力图通过陕西几个乡村的变化以及一些人物如老黑、 马生、老皮、墓生、老余、戏生等的生命历程来反思这一历史进程。
应该说,在《老生》这部小说中,贾平凹更主要的是去呈现与反思中国这近100 年的历史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比如他以马生等人来反映解放后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由于中国农民“他们最原始的愿望同一种狭隘、自私混杂在了一起”[3],这导致了土地改革政策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 而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急剧上升,但是因为市场经济监督管理机制还不够完善,市场经济伦理发展还不到位,于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暴露出了各种问题。 如在小说的第四个故事中就以当归村的农产品例, 典型地反映了这些年来国内在经济发展中尤其是食品生产领域所出现的突出问题。 小说写到,当归村种植的豆芽、西红柿、黄瓜、韭菜农残超标三十倍。
“有人正蹲在门口用旧牙刷在刷一堆长了绿毛的嫩核桃仁。 问:刷这干啥? 说:卖呀。 问:颜色都这样了还能卖?说:用福尔马林一泡就白了。”[2](P239-240)小说还通过戏生谎称拍到老虎的情节来影射2007 年的周正龙假老虎事件。 毋庸置疑,我们国家在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老生》这部小说除了反映这些历史成就外,之所以聚焦于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与问题,是基于中国知识分子一向就肩负着的爱国心与社会责任感:他们希望通过深刻的反思,纠正时弊。
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以花街四个年轻人为主人公,在对他们故事的叙述之中带入中国当下社会现实并往前追述了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 小说尤其关注国内近二十年来城市的发展与城镇的衰退,一开始就借着归来者初平阳的目光批评中国城镇的发展。他写运河两岸的芦苇、菖蒲和野草都消失了,河岸变成石头与水泥的堤坝,房屋则不仅越盖越高,隔三岔五还有高楼大厦在不断地拔地而起。中国富有特色的城镇如今跟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什么两样了。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及快速城镇化却导致了乡村惊人的衰退,甚至是农村空心化:“现在满村找不到三头牛,牲口都不喂了,耕种收全是机器,再过两年,干活的人也没了,都出去挣钱了”, “若从生活质量论,现在的乡村绝不是一片乐土”[1](P176)。 “城市像恶性瘟疫一样迅速蔓延,运河以南的地皮一天能涨两次价。 ”[1](P487)
而除了呈现与批评近二十年来城市与乡镇发展的问题,国内在这一阶段所发生的历史大事件与社会现象,如2008 年汶川大地震、2003 年非典、1997 年香港回归、大城市板房、社会消费化等也一一出现在了小说中。
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徐则臣还十分巧妙地借小说中的一些人物来勾连追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更遥远的历史。 比如,他借塞缪尔教授回溯三四十年代那段现在很多人都已遗忘的上海收容犹太人的历史,借初平阳的导师顾念章、杨杰母亲李老师、景侉子、秦环、易培卿等人的故事陆陆续续讲述了解放前、解放初与“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 同贾平凹一样,徐则臣在小说当中亦表现出了对中国近100 年社会发展进程的强烈关注,他试图为此描摹出一幅完整而连续的图景,并通过对这些图景的阐释来探寻未来之路。 小说篇名《耶路撒冷》指的不是寻求某种宗教的寄托,而是在思考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路径与中国人的精神安放问题。
二
当然,《老生》与《耶路撒冷》这两部叙述与反思中国近百年历史发展进程的长篇小说在创作上亦凸显了诸多差异。 这既有因作家个体固有的差异而产生的不同,但也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不同代作家创作视角及创作手法的差别。
(一)乡村与城市
虽然同样力图表现与反思中国百年历史进程,但两位作家选择的题材却大不相同。 《老生》完全聚集于乡村与农民。 解放初的土地改革与农业学大寨自不必说,发生的地点都在乡村,但就是到了改革开放甚至是21 世纪之后,贾平凹的笔墨也几乎全部集中在农村与农民身上。 事实上,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农民工大量涌进城市,很多农民的故事演绎场所已转换到了城市;另外,离开农村的农民到了城市中,其思想也会因为环境的变化与眼界的不同而改变。 但是《老生》这部小说即使在讲述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发展的第四个故事当中,也仍然将叙述重点放在农村。 戏生进城只是他农村生涯的一个小插曲,贾平凹以极短的篇幅简要地叙述了他失败的进城打工经历,而后返回农村展开乡村叙事。
《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曾在评价《耶路撒冷》时谈到,这部小说让他“既吃惊又满意”[4],他认为徐则臣为了展现现实的多重矛盾与冲突,将国际国内、城市乡村、外省首都、文化界商界等多个方面并置起来书写。 由梁鸿鹰的这个评价我们已可以看出徐则臣《耶路撒冷》视野的开阔与选题的沉重。 《耶路撒冷》故事主要发生地都在城镇与城市。 一方面,初平阳、杨杰、秦福小、易长安四人均出身于小城镇——花街。 中国的城镇既有别于城市但也不是农村,或者说它正是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徐则臣通过对城镇的描写与叙述把城市与乡村联结起来。 另一方面,由于初平阳、杨杰、秦福小、易长安长大后都到城市中谋生,因此,关于他们长大后的故事便主要在城市中展开。 当然,小说中徐则臣也借由初平阳写的一些故事带入农村的叙述,但如同贾平凹书写城市一样,徐则臣对农村的完全着墨在整部小说的篇幅中可以说是极为微小的。更值得关注的是,即使写的是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徐则臣选取的也依然是城市。
《老生》与《耶路撒冷》这两部小说对乡村与城市题材的不同选择除了作家个人创作的差异外,可能也有中国当代作家代际之间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创作视角转换的原因。 关于这一现象的讨论最突出的莫过于孟繁华。
孟繁华在2012 年提出中国当代作家代际间创作题材不同与创作视角的转换问题。 他认为,目前“50后”作家虽仍占据中国文坛主流[5],但随着“中国的现代性——乡村文明的溃败和新文明的迅速崛起带来”,使这一百年来一直是中国文学主流的乡村书写遭遇到了不曾有过的挑战。 而在这样的挑战中,一大部分以农村生活为创作对象的“50 后”作家基本还固守着过去乡村文明的经验。针对此种现象,他作出“乡村文明的溃败与‘50 后’作家的终结”同时发生的判断。 同时,他也褒扬“70 后”作家对中国新文明即城市文化的书写以及为中国文坛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并呈现了“文学的新变”[6]。
“50 后”作家,除了王安忆始终孜孜不倦地书写大城市上海外,其他作家的目光还是更多地对准农村,比如莫言的《生死疲劳》、贾平凹的《古炉》《带灯》、刘醒龙的《天行者》等,都还是将农村作为他们书写中国社会的重点。 而“70 后”作家,如徐则臣、田耳、冯唐、张悦然等,一开始就是以城市为主题。 徐则臣的《跑步进入中关村》《啊,北京》、田耳的《天体悬浮》、张悦然的《水仙已乘鲤鱼去》、冯唐的“北京三部曲” 等都是书写城市的佳作。 以孟繁华的观点视之,《老生》与《耶路撒冷》呈现了“50 后”作家与“70”后作家创作题材上的差异。
事实上,由于近些年“70 后”作家的异军突起,他们亦得到中国当代文坛的广泛关注[7]并被寄予厚望。张丽军就认为,由于“70 后”作家有幸亲眼见证了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亲身经历了愈来愈快的城市化进程,亲身体验到传统与现代、历史和现实、物质同精神相互分离割裂的痛楚、挣扎与悲哀。 因此,“70 后”作家有责任也有使命深入广阔的民间与繁复的历史去呈现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喜怒哀乐,去建立起专属于他们的打通过去和未来的经典文学[8]。
(二)线性结构与网状结构
虽然《老生》的主体故事采用倒叙的叙述顺序,但这“倒叙”只是引子而已,之后对中国近100 年的历史讲述完全是按时间的顺序进行。 因此,小说的叙述结构是线性结构。
而《耶路撒冷》的开头跟《老生》一样都是从后面的时间切入,但这一切入并不像《老生》那样是一次性的技巧而已。 《耶路撒冷》主体情节——初平阳返乡处理祖屋大和堂到处理完毕过程,其叙述看似按时间顺序,但这主体情节在小说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徐则臣通过各个角色回溯花街与中国百年历史。 回溯时,徐则臣并不采用线性结构的方式,而是随着人物随着情节不断地回到过去又不断地切回小说的主体情节时间。 事实上,《耶路撒冷》各章的题名已暗示我们这不是一部线性时间的小说。 《耶路撒冷》共11 章,每一章都以人物的姓名来命名,中间章是花街四个朋友挥之不去的内疚“景天赐”,其余各章分别是上半部下半部各出现一次但排列次序相反的“初平阳”“舒袖”“易长安”“秦福小”“杨杰”。 这种叙述结构可以称之为“网状结构”。 如果用“图例”来表示这两部小说对历史的叙述,那么《老生》是一条平滑的直线,《耶路撒冷》则充满了无序且长短不一的线段。
《老生》与《耶路撒冷》对线性结构和网状结构的应用,我以为这也体现了不同代作家之间历史观的差异。 大部分“50 后”作家对采用线性结构来描述历史有一种偏爱,似乎不用线性结构就无法呈现中国这百年的历史巨变、中国民众在其中所承受的苦难以及坚忍的品质。 如莫言的《丰乳肥臀》以时间为序塑造了历经中国百年历史、饱尝苦痛但始终坚强的中国母亲形象,余华的《活着》也是以时间为序讲述了饱经百年沧桑与磨难的福贵的故事。 他们是认同“大历史”的,认为历史远比个人重要也更有力,人物在历史的洪流中只能随波而行。而“70 后”作家虽然也受过“大历史”的教育,但他们更关注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正如徐则臣在小说中所说的:“中国的年轻人如今像中子一样,在全世界无规则地快速运动”[1](P33),历史有其洪流,但个人却并不一定都被洪流冲走或在洪流中完全无法抵抗。 时间在流动,但并不那么有序或有力,于是,便有了《耶路撒冷》的网状结构,也有了小说最后初平阳等人改变时间与命运的可能。
线性结构与网状结构本身并没有优劣,关键是叙述效果。 就这两部小说而言,《老生》采用线性结构却没有丰厚的叙述,只是用了22 万字的篇幅,百年时间的各个时段都极为快速地滑过,轻快而流畅。 而《耶路撒冷》除了在篇幅是《老生》的一倍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的网状结构在不断地插叙、补叙人物的过去甚至于插入其他人物的故事,不停地拆解时间,拉开时间的宽度,因此显得较为饱满与厚重。
(三)人物主体性的有与无
这里借用哲学的主体性概念来讨论两部小说中人物的主体性。 《老生》中故事的讲述者是一位唱师,身在阴阳两界、活了百十来年、在葬礼上唱阴歌。 唱师虽然也为故事中的人物如老黑、墓生、戏生等唱阴歌,但这个角色是超脱于故事之上的;他看历史,但他不进入历史;他描述历史,但不评价历史。 因此,他是置身于故事/历史之外的。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无论是早期的老黑、四凤、白土、马生,还是后来的老皮、老余、戏生、荞麦等人,也都只是随着历史的波涛沉浮,对于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几乎没有思考、判断与选择的能力,可以说他们的主体性是缺失的。 除了主体故事之外,小说还把一位老师教习放羊的孩子《山海经》的情节串连在主体故事的四个小故事之中。 这位老师通过对《山海经》的教习谈到:“人是产生一切灾难苦厄的根源”,“当人主宰了这个世界,大多数的兽在灭绝和正在灭绝,有的则转化成了人”[2](P108),“现在的人太有应当的想法了,而一切的应当却使得我们人类的头脑越来越病态”[2](P250-251)这样的观点。 这些类似于哲学或历史的反思,但既超拔于故事之外,也似是而非,因此,“老师”这一人物的主体性也不确定。 刘大先曾严厉地批评《老生》中人物主体性的缺失。 他认为,《老生》中所写的人物除了李得胜与老黑少数几个,其余人物都缺少对生活的渴望与对未来的想象,表现得冷漠无知、愚昧无为且自私自利,只是被动地承受时代的挤压。 而戏生虽然有所行动,但几乎纯是欲望驱使,其渴望与本能也是浮表化的。他批评贾平凹在小说中表现出真正的冷漠和超然,只是将所写的那些农民作为对象,而没有与他们同情共感,这样一来:“不是历史在拨弄人物,而是人物自己在历史中内耗,人物从来对于历史没有自觉,更遑论他们永远不会成为历史的主体。 ”[9]
《耶路撒冷》则不同,小说中的人物角色虽然不是徐则臣自述的“边缘人”,但也不是能够掌握历史乾坤之人,他们只是中国千千万万普通的民众之一。 事实上,小说借《我看见的脸》《你不是你》等几篇初平阳写的文章刻意写了许多没有名字的人,这即是以他们来代表中国民众的整体。 值得注意的是徐则臣的写法,他赋予了小说中所有人物以强烈的主体性。 初平阳、秦福小、易长安、杨杰等人自不必说,小说写的就是他们的精神历程。 此精神历程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他们对景天赐自杀事件的内疚持续与不断回顾;其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不断地观看并思考中国这百年来的历史尤其是近二十年的社会发展。 就是初平阳文章中写到的各式有名无名的人物也都陷入无尽的社会思考与精神追求之中。
小说最后的“心安”不仅是初平阳等四人对景天赐事件的释怀,更是他们找到了解决中国社会症结的方法。他们在游走“世界”、在苦苦思索之后,终于发现,返乡重建是最好的道路: 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1](P609)。 乡村应是安放乡魂的领地,《耶路撒冷》中的人物——这些普通的中国民众始终在参与历史,也回应历史,他们也相信历史可以自他们的手中改写。
(四)时间的静止与流动
比较两部小说的结局是颇让人寻味的:《老生》结束于老唱师的死亡,那学习了《山海经》的放羊孩子在唱师死亡的现场,但他并没有因为学习显示出对未来的思考与把握,而是一如既往的懵懂。 就如以上所讨论的,这个孩子也是缺失主体性的,所以,他并不代表任何意义,我们也无法通过他在《老生》中看到未来。 而《耶路撒冷》中,秦福小是花街四个好朋友中最早找到解决社会症结方法的女子:她出走“世界”十年,最后返乡,“香甜,宁和,笃定,有种沧桑阅尽的美”[1](P313),因为“她用人生几近半数的时间才弄明白,从哪里来必须回到哪里去”[1](P400)。 天送是秦福小的养子,我们当然可以期望,由这样的女性养育出来的孩子将是全新的一代,他既不同于初平阳、杨杰这一代,更不同于易培卿、景侉子的上一代。 天送象征着中国的未来与希望,不仅秦福小他们要把掉在地上的捡起来,天送这一代更会接着秦福小们未能捡完的继续下去。
不同的结局呈现出小说家对时间不同的态度。 《老生》中的人物在代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中的时间是静止的。 尽管小说中出现了许多年轻人,像老黑、白土、马生、戏生、墓生等,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年轻人优于老一辈的特质。 虽然贾平凹说过,小说篇名为“老生”指的是唱师与每一个故事中“总有一个名字里有老字,总有一个名字里有生字”[2](P294),但我以为这“老生”更恰切的理解应该是指小说中这些虽然年轻但与老人无异的年轻人。 《老生》中有朝气的年轻人是缺席的,《耶路撒冷》则十分鲜明地表现出时间的流动,虽然它的叙述结构是网状式的。 初平阳一代当然有别于甚至是超越了初医生一代,而易长安与易培卿父子则更明显地体现这一点。 同时,小说也暗示了天送这代表未来的一代还会更胜于初平阳这一代。
李敬泽认为,《耶路撒冷》是一部正面强攻我们时代的作品,它表现了“一代人的复杂经验”[4],并且还赞赏它为陷入僵局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范本。 的确,徐则臣很好地回应了人们对“70 后”作家的期盼:他们已能够建立起“属于这一代人打通过去和未来的经典文学”[8]的责任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