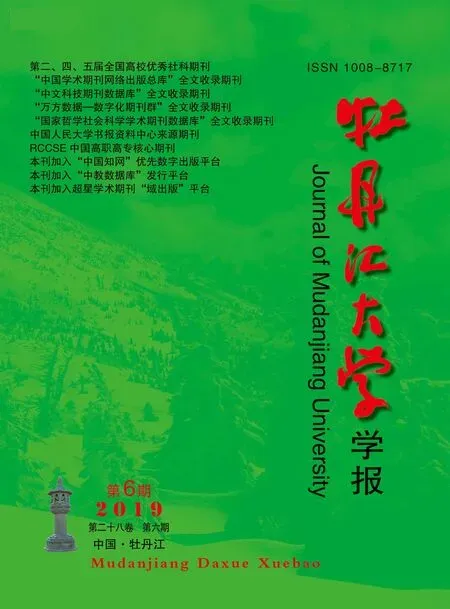阳明心学与明代性灵说研究
李 益 王军涛
(西藏大学 文学院,西藏 拉萨 850000)
明代文学突转是“心学”大兴,打破了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使人们开始探索理学衰落原因及文学归途等。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同属中华文化范畴,是先秦心性论的延续与发展,更是中华文化心法之所在。
一、阳明心学与先秦心性论
“心学”缘起先秦。《尚书·大禹谟》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阐明维护“道心”的重要性和具体方法,孔子扩展为“正心”“诚意”等。“心学”经历漫长的沉寂期至陆九渊、王阳明才逐步完善。明代中期,明前期的励精图治已经消耗殆尽,代之而起的是皇帝的荒诞不经、官宦的专权暴政与朝臣的阿谀奉承。思想领域,极度的高压政策和暗杀活动频仍,严格的八股取士制度,宋明理学的桎梏等,使文士们惶惶不安,不得已转而求佛、求道,以致明代道观众多,狂禅之风盛行。在与佛道对抗交融中,儒学发生变革,心学与理学分庭抗礼,成为主导社会各方面的思潮之一。
(一)阳明心学内蕴
1.“心即理”的心学观
王阳明言心即理,强调万物之源在“心”,故心之外无他物、无他理。在其思想体系中,“心”居于中心,由心得理。当心与万物契合之时,理心一体。如观花,当主体未看花时,花与主体“同归于寂”。王阳明以“此花与汝同归于寂”说明“心即理”,揭示自我之心的自由,即花之美在于人的观赏,尤其是人心的体察。
2.“致良知”的良知说
王阳明视良知为“心之本体”,总言之为“性”。先秦文献常有“心性”一词,如孟子指出良知是人“所不虑而知者”,也即先天具足,而非后天所得。王阳明进一步发展为“心自然会知”,言孝悌恻隐皆源己心,因为心中存有,故自然而然表现出来,并不由外而求。“良知”归于人心之本,即“本然之良知”,通过自知和外化,最终达到知行合一。内修于心,自然外化于行,这既是君子之行,也是儒家内外兼修之法的发展和延伸,更是帮助人们排除内心杂念,修养身心,从而唤起内心深处最纯正思想——“良知”。
3.“知行合一”的实践论
知行关系问题,从先秦到宋明皆有论述。“知之匪艰,行之惟艰”(《尚书·说命》),强调知易行难。孔子言“学而时习之”,又说“不知而作之者,吾无是也”,强调知为前提,但需要行来巩固,因为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佛家天台宗强调定慧均等和止观双修,实际也要将知行结合起来,达到双修目的。北宋四明知礼强调“智为行本则行借智生,行能成智则智借行成”,暗含知行结合思想。朱熹指出“知行长相须”,认为知行并列,则“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综合前学,王阳明反对朱熹的“真知必能行”,强调真知即是行。“真知即是行”是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基本观点之一,从知识层面来讲,“知行合一”中的“知”即对事物的深入了解后形成的知识和道理,主要通过实践获得,并最终体现在自己日常生活中。在此过程中,由知到行,再由行到知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其中知是行的起点,行是知的完成,二者构成“知行合一”说的基本理论。此外,“知”即良知,包含自知与外化。王阳明强调“圣人之道吾心具足”,至于如何成为圣人,王阳明指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推动知行合一。
(二)先秦儒学心性论
1.“性本善也”的天赋之性
“人之初,性本善”,言其对人“本然”状态的认知,认为“善”乃天赋之性,人皆有之。这基本是从先秦孟子那里承继来的。首先,孟子强调人人之不忍。因为不忍,所以有恻隐;因为有恻隐,所以有善行。孟子举例说,当妇人去井边打水,忽然看见小孩掉进井里,她的第一反应是赶紧救孩子。因为“不忍”的天性,所以自然做出救孩子的义举。孟子认为性善源于人心本能,是出于人的天性,故称之为“良知”“良能”。其次,孟子强调人之天性即善,由此生发出“四端之心”,这些善性都是自我本身天赋之性。再次,孟子强调“尽心知性”的天道论,认为“尽心”“知性”以致“知天”,是“性本善”的最终归宿。最后,“性善”最终目的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重建礼乐文明。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不断扩充自己的善性,由己及他,共建“协和万邦”的社会至境和“世界大同”的国家至境。
2.“内外兼修”的养性之法
儒家强调“内外兼修”,内修即修心,外修即修行,修心与修行并重。孟子“穷善其身,达济天下”观念,几乎成了中国文士的人生信条,与“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仁义观一起塑造了中国独特的文人政治,同时也展现“政坛不幸文坛幸”的文人典型。仁、义构成先秦两个重要命题。“仁”即内化道德品性,“义”即外在相宜行为,仁义并行,即内修于心和外化于行的统一。告子曰:“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在先秦时期,“仁义”已渐融合,形成人们固有的思想理念,当人心之道德与相宜之行为有效结合起来,表里如一,心性自明。
3.“扩及他人”的存世之法
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第六》)这包含“换位思考”和“扩及他人”两个思想理念,前者强调站在对方立场上想问题,既不要把自我意志强加他人,也不要因为某种原因丧失自我本性为他人所驱使;后者强调要扩充善性,修养道德,只有自己先理解,才能要求别人来理解。二者共同之处,即在于拥有高尚品德,通过潜移默化的力量传递给他人,使他人不经意间向有美好德行操守之人看齐,最终促使社会文明发展,这正是儒家教化的功效。中国儒家“神道设教”思想,以圣贤教化民众,由己而扩及他人乃至天下。
4.“齐家治平”的养心之法
《大学》开篇指明人生宗旨,即儒家修养“四纲”。在四纲总领下,儒家又提出“八目”。“四纲八目”是儒家提出的养心之法,先圣指出为人应做君子儒,勿做小人儒,要急他人之所急,想他人之所想,能够做到“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张载),修身养性,齐家治平。
(三)心学与心性的契合
“心性”是我国古典哲学思想之一,源于孟子尽心知性说。魏晋南北朝时佛学大兴,谈玄之风盛行。葛洪《抱朴子·交际》提出“心性”一说:“今先生所交必清澄其行业,所厚必沙汰其心性。”佛学心性思想融入,推动了时人对先秦心性论重新思考。程颐、朱熹视“性”为天理,强调“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陆九渊、王阳明主张“心即理”,二者并无差别。清代王夫之、戴震等人对心性的阐述更加理性,认为“心性不异,即心即性”(《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在中国思想史上,多以“心性之学”称宋明理学,但心性之学囊括儒道佛等,二者并不完全等同。
“心学”从北宋程颢发端,陆九渊最早提倡,经王阳明完善,成为天下显学之一。其后,文学家广泛关注这一理论,推动明中后期主情论的丰富和发展。“心学”继承先秦心性论而不断完善,二者存在契合:(1)同属中国哲学范畴,都是对人本身内在精神的探索及对外在事物的观照;(2)都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心性”在前,“心学”在后,形成继承和发展的哲学关系;(3)都以人本身为研究对象,强调内外兼顾。二者的合流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在儒学渐趋衰落并落入窠臼时,心学渐兴且与理学抗衡,推动中国文学理论蓬勃发展。
二、明代性灵说与心学的发展
明代性灵说的代表公安三袁,尤以袁宏道为最。“性灵”一词,并非袁宏道初次提出,在他之前,先秦儒家以“性情”阐释相关理论;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开始频繁使用“性灵”一词;隋唐以后,渐少使用,偶或使用,但也影响甚微。直到袁宏道将其作为写诗主张大力宣扬后才被关注,成为中国文学理论中一个重要观点。
(一)性灵说的思想渊源
“心学”发展推动明代文学归宿的探寻,自由思想的融入使文人从明前期政治宦海生活转入自我日常生活写作中来,文学之风也由沉闷枯燥的八股写作转换为清新自然的散文创作,主“情”思潮成为文坛主流。对此,袁宏道探索“性灵”缘由及内涵。中晚年他由于为官清正与上级多有不和、挚友兼长兄的袁宗道逝世等,亦官亦隐。在道佛感悟中,他从儒学性理悟入,以道佛之虚充实儒学之实,如其《广庄》《金屑》《西方合论》《德山塵谈》等文。
明中叶后,封建专制日益强化,“心学”影响下的自由思想萌发,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思想领域展开了对理学的批判和修正。李贽倡言童心说,要求以“真”来对抗儒学尤其理学的“假”,以真人真言真事真文来反对假人假言假事假文。他说:“童心者,心之初也。”指出文学要写“童心”,也即人之“真”与“本”,实质借助文学平台表现自我之“真情”,反对儒家礼教下的“伪情”。作为李贽门生,袁宏道法“童心”以引“性灵”,并深入阐述其内在意蕴。
(二)性灵说的内在意蕴
1.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袁宏道在《小修诗序》中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其核心是写作要展现自我个性,直抒胸臆,表现真情实感不作伪。在这里,袁宏道认为“真”构成了“性灵说”的主体,认为创作本身就是要表达“真”的情感与心志,展现出人对于世间万物“真”的看法,以求创作出最“真”的文章来。他强调好诗句应该“情真而语直”(《陶孝若枕中呓引》),且“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2.性情至上,行藏在我
袁宏道堪为性情中人,信奉“性情至上,行藏在我”。他“笃于天伦,入孝出悌”,与庶祖母詹大姑感情笃厚,祖母病重,他辞官归家悉心照料;因孝养父亲,多次弃隐做官;朋友兼长兄的袁宗道逝世,他辞官归隐达七年之久;待穷困故交,他始终如一,从不相弃;对已故亲人朋友,一往情深,时时怀念,这都是他“精诚所至之真情”。同时,他主张自然随性不作伪。《识张幼于箴铭后》说:“(放达者与慎密者)两者不相笑也,各任其性耳。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为,是谓真人。”相比慎密者,他更欣赏疏狂奇士,因他好山水,尤喜新奇险怪的山水之风,又有“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的不羁和张扬,喜欢陶潜醉心山野的诗意人生,以“归去来兮”的随性之愿,实践了苏轼“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沁园春》)的洒脱与自然。
3.辞贵自然,独出机杼
袁宏道强调“真性灵”之诗以“真”为核,以“趣”“淡”为翼,冲淡而有余味。在行文中,他认为辞贵自然,故倡言质朴。他为人随性自然,在语言表达上主张独出机杼,体现自然洒脱、不事雕琢的特点。同时,又强调要“信心而言,寄口于腕”(《叙梅子马王程稿》),接近口语为好。倘以古语说出,自然之味已然全无,与其情性之说极不相符,故以自然口语表达为好。
4.隐逸山林,关心世道
袁宏道虽倡性灵,主张随性自然,热衷隐逸,但却始终关心世道,关注国家兴衰。鲁迅先生赞他“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的人”。无论在朝还是归隐,他都时刻关注朝廷大事。明中后期国家内“宦官横行,朝臣聚党互攻,外患潜伏,国事方隐忧未已”,他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借人才与气运关系大胆评说国家命运:“常闻天下有道,则人才易主,亦易成就,而国家享黄发之赐。气运将塞,则人才先受其祸。……若但以堂上之孤独,血胤之鲜少,同乡同举之情,则其哀亦仅仅而已,不至若永叔之所云也。”他关注国家兴衰,忧国忧民之心极为恳切,故虽无意功名,却怀揣着“一副忧世心肠,何等紧切”,将浓厚的爱国情怀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展现得淋漓尽致。
三、性灵说与明代文学创作
阳明心学产生之后,文统开始回归,并与明初道统抗衡。明初道统的束缚,文学危机四伏。台阁体的发展与消亡,促使文人反思。前、后七子试图以秦汉文学来抵消道统对文学的驾驭,最终回归文学本身,但过于强调模仿,难脱古人旧习,在创作上难与道统相抗而渐趋衰落。唐宋派散文的出现,便是道统派以创作实际回击复古派并获得成功的例证。归有光文以情取胜,如《项脊轩志》《思子亭记》等清新自然,情意真切,与袁宏道“辞贵自然”有同工之妙。在心学影响下,汤显祖综合儒释道及王学左派思想,兼容李贽童心说、袁宏道性灵说及达观和尚心性思想等提出至情论,突出强调“情”反对“理”,认为有情则无理,有理必无情,以“至情”直击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紫钗记》《牡丹亭还魂记》《南柯梦记》《邯郸梦记》,几乎无一不是其“至情”思想的产物:前两部以宣扬男女至情爱恋,对抗封建礼教并最终取得胜利,表现“真情”之动人;后两部借仕宦沉浮,告诫世人超越“矫情”,回归自然本性。汤氏之至情实则从性灵角度倡导思想解放,把文章视为“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新元长嘘云轩文字序》)。同时,小品文盛行。张岱《自为墓志铭》大胆抛出自我年轻时“极爱繁华”生活,揭露自然真我;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阐述“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的道理,表露自我自在逍遥、率心而行的真实心态。这些都推动了明中后期主情文学的发展与繁荣。
综上所论,从先秦儒学心性论到阳明心学,再到性灵说,进一步到明代主情文学写作,这是一个继承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明代知识分子以极大的热情展现了其精神状态及理想信念,挑战封建权威以求跳脱理学窠臼,最终回归文学本质,体现出文人对于社会人生的理解与认同,展示出明中后期文学主情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