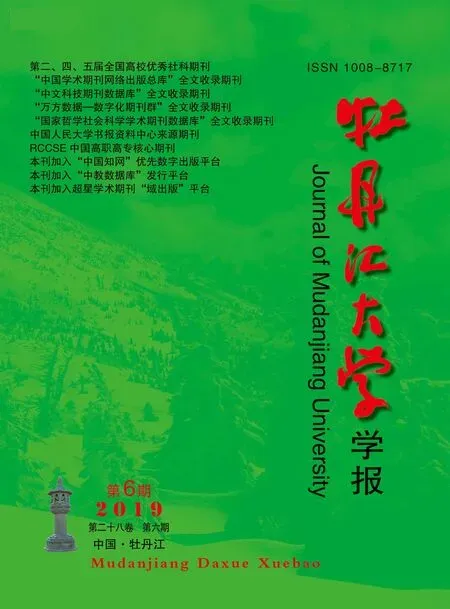格雷厄姆·格林的倦怠与悲悯
张 莉 郭君臣
(1.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2.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在晚年的回忆录《逃避之路》中,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把写作视为一种治疗的方式,“有时我感到奇怪,那些不写书、不作曲也不绘画的人,怎么居然能逃脱掉人生固有的疯狂、悲愁和惊惶恐惧呢”。[1]155-156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常会主动现身于世界各地的革命、战争或危机之中,信仰和情感生活也有大波动,写作是他生活中沉思的部分,一段奔波劳碌之后,他会坐下来,每天安排一段时间回忆和反思自己的所闻所历,力图从中咂么出一点温暖、踏实的东西来。格林尝试过诗歌、戏剧、小说等多种写作样式,最能代表他成就的是长篇小说,本文也主要讨论他的长篇小说。
一、格林对人世的体察及倦怠
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格林就充分体味到人生的“疯狂、悲愁和惊慌恐惧” 。在中学里他是校长的儿子,完全应付不了其他同学的怀疑和敌意,觉得自己生活在家庭与学校的边界上,“烦躁不安,许多爱和恨的纽带牵动着你的心(《不法之路(The Lawless Road)》)”。[2]146长时间的折磨差点让他崩溃,几次试图自杀,父母不得不把他送到伦敦进行半年的精神分析治疗,少年时代心灵的创伤使得格林对现实世界的各种缺陷特别敏感。1932年出版的小说《伊斯坦布尔列车》(Stamboul Train)第一次完整地展现了格林心中的世界,那辆载着革命家、犹太商人、穷歌女、杀人犯等各色人等的列车就是这个混乱世界的缩影:人们被欲望驱驰着,极轻易地失去人格和尊严,虚妄、做作、心怀恶意。革命家津纳满怀共产主义热情,被秘密处死之前,还想以自己的慷慨赴死唤起些微弱的反抗意识,但一切毫无意义,“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清醒的理智告诉他,他的死亡产生影响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3]189之后的几十年,格林迹遍全球,见多识广,也把世界的阴沉可怖描述得更加真切和多样。1948年出版的《问题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中,英属西非警察局“后面狭窄、阴暗的过道里,在审讯室和牢房里,斯考比总是觉察到人类的粗俗和不公正,就是那里有一种动物园散发出的气味,锯末、粪便、阿摩尼亚的气味,而且缺乏自由”。[4]101955年出版的《沉静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中,越南北方发艳的运河里尽是死尸,“重重叠叠:有一个人头,已变成乌黑色了,像个剃光了头发的无名无姓的罪犯,冒出水面,像一个港口里常见的浮标”。[5]51-52格林反对评论家把自己的这些描述视为他想象力的创造物,“我不仅是个小说家,也是一个新闻记者。我向你们保证,水沟里躺着的那个死孩子就是那种姿势。发艳的运河里就是漂浮着许多尸体……”。[1]167
这些体验使得格林满是对世界的厌倦,为了逃避,他寻求变动或激烈的生活,有时会轻率地投身于危机中,并暗暗期待着死亡。死亡并没有来,格林在各种各样的旅行中“感知到的是居住着古怪人们的世界,奇异的行当,以及让人难以置信的蠢行,同时为了平衡它们,你也有了惊人的忍耐力。”[6]格林作品中弥漫着倦怠的气息,主人公不论年龄大小,大都多历磨难,心事重重,深切地领略了环绕着生命的阴暗区域,不再有轻快简单的希望。《布莱顿硬糖》(Brighton Rock)中十七八岁的黑帮头目平基已经对生活颇有感慨,“人自出生之后,就只能苟延残喘,慢慢死去”。[7]251生活需要无限的忍耐,领略其中意味的人们颓唐而沮丧,消极又沉郁,《权力与荣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中的神父又一次偏离逃往路线,去面对一个快死的女人,“好像不很情愿去参加一次他无法逃避的庆典。他悲哀地说:‘好像总是要发生一点事儿。像这次一样’”。[8]18倦怠侵蚀着热情、希望和日常的生活,《问题的核心》是格林基调最为低沉的小说,警官斯考比被疲乏、阴郁、罪恶、隔膜的气氛笼罩着,“他本来认为爱、同情、相互理解是有关系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知道没有谁能够了解另外一个人。爱本是一种想了解别人的愿望,只是因为不断失败,这种愿望很快就死亡了,爱或者也随着死去,或者变成了痛苦的情谊,变成忠贞、怜悯……”。[4]325
二、天主教式的挣扎与救赎
格林多情善感,智力超群,不能认同这个混乱的世界,他一直在摸索能够赋予生命以活力和意义的力量。大学毕业后他爱上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姑娘,这段感情和接下来二人的婚姻促使他改信天主教,整个过程有点突然,“我只记得在1926年1月,我开始相信确实可能有某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天主的存在”。这不是一次随随便便的皈依,“我非常清楚地记得离开教堂时我感受到的情绪的本质:根本没有什么喜乐的成分,只有一种阴沉沉的忧虑”,[9]6它起因于格林心中的困惑,也极大地影响着格林的生活。接下来十多年,格林忙忙碌碌,也在尽力做一个合格的天主教徒,“我没有感情上的激动,只有理性的信服。我养成了参加宗教仪式的习惯,一个月做一次告解等等。在闲暇的时间里我读了很多神学书,有时读得入迷,有时非常反感,但总是怀着极大的兴趣”。[1]164格林不停地与上帝、耶稣基督和现实进行种种对话,寻求心灵上的慰藉,试图接近天主教信仰的核心。但这段时期,天主教还只是格林个人寻求救赎的路途,“我的职业生活和我的信仰一直分储在两个格子里,我始终没有雄心壮志把他们糅合起来”。[1]165
1937年格林的信仰开始渗入其创作中,在本想写成简单侦探小说的《布赖顿硬糖》中,他不自觉地“讨论起善与恶,是与非和‘上帝令人惊骇的奇异的仁慈’”来。[1]166十多年的信仰和反省让格林熟悉了天主教徒的精神状态,当时西班牙和墨西哥对天主教徒的迫害又唤起了他的宗教热情和同情心,他“开始深入地探讨信仰对行动所起的作用”,[1]165先后出版了四部作品:《布赖顿硬糖》(1938)、《权力与荣耀》(1940)、《问题的核心》(1948)、《恋情的终结 (The End of the Affair)》(1951)。四部小说中,上帝或耶稣都是主人公应对或超越现实世界的支撑。少年黑帮头目平基只有地狱般生活的狭隘经历,粗鲁残忍、冷酷无情,坚信自己也只能到地狱里去。他一意孤行,拼命抵抗着更强大的暴力和妻子的温情,不时哼唱起赞美上帝的歌曲为自己打气:“上帝的羊羔替我们赎罪,给我们带来和平……”,[7]58他借上帝和地狱为自己的生活筑起一道屏障。《恋情的终结》里的萨拉也感知到上帝的存在,情人死里逃生,她视之为上帝的恩典,从此“染上了信仰,就像染上病一样。过去我从来没有像爱你一样地爱过,过去我也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地信仰过什么。我确信这一点。过去我从来没有确信过什么东西。当你带着满脸血迹从门口进来时,我变得确信了,爽快彻底地确信了”,[10]151爱情和由爱而生的信仰帮她摆脱了生活的沙漠,不过为了兑现给上帝的承诺,她不得不离开情人,开始了长久的爱情与信仰的拉锯战,格林当时也有这样的拉锯战,把这段内心挣扎写得凄婉而又热烈。《权力与荣耀》和《问题的核心》是格林更具雄心的杰作,书中的神父和警官斯考比都不是合格的信仰者,私通、酗酒,甚至自杀,他们为此痛苦不已,却又想着能有所担当。神父疲于逃命,却念念不忘自己的职责,最终为救赎一个将死的犯人而重回死路。斯考比则被过度的怜悯压跨,不想抛弃妻子或者情人,只好抛弃了自己的生命。这两部作品融进了格林更多的激情和阅历,展现的是人接近上帝和基督的艰难努力,救赎和悲悯的调子时隐时现:在监狱的黑夜里,神父想起以往遇到的很多张脸,满怀柔情,“如果你恨谁,那是因为你缺乏想象力”,“仔细地揣摩一下一个人的脸相,不管是男是女,你都会可怜起他来,因为每个人的面目都有着基督的形象”。[8]185
《布赖顿棒糖》为格林赢得了天主教作家的声誉,接下来的《权力与荣耀》与《问题的核心》则引起了天主教评论界的非议,他们认为小说中神父和斯考比的信仰以及行为很成问题。对此格林强调自己小说家的身份,坚持文学研究人性弱点的权力。不过这些争议与《问题的核心》出版后那些宗教受难者的纠缠,使得格林开始重新思考信仰问题,“过去我总把信仰视为风平浪静的海样,现在这一幻觉一去不复返了;信仰更像海洋上的一阵大风暴,幸运者一下子被卷进去,立刻沉默,不幸的人却残存下来,遍体鳞伤地被投掷到海岸上。”[1]1841960年出版的《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A Burn-Out Case)是格林最后一部探讨天主教信仰的小说,主人公奎里就是一个遍体鳞伤的信仰者,生活所历让他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他不再相信那些历史的、哲学的、逻辑的和辞源学印论证了”。[11]195生活失去根基,奎里厌倦了事业和情人,自我流放到非洲丛林中,在当地坚持疗救麻风病人的神父和医生身上,他看到平实、坚韧的力量,又有了生活下去的理由。医生是无神论者,却坚信爱会存在于人的脑海中,“我怀着一个微小的希望,一个非常渺茫的希望,但愿那个被大家叫做基督的人实际是一粒肥硕的种子,正在寻找一个强缝生根发芽”。[11]153院长神父则更愿意把这种爱拉近信仰,“人只要开始寻找上帝,就已经找到上帝了。爱也是这样”。[11]253小说写完之后不久,格林给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写信,说医生是“稳定、安适的无神论”代表,而院长神父则代表着“稳定、安适的信仰”。[1]186经过漫长的摸索信仰的旅途,格林觉得自己终于来到了“希望寄居的地区,上演悲喜剧的拉曼却平原(堂吉诃德的故乡)”。[1]190从此之后,格林的信仰就在院长神父和医生之间徘徊,有时称自己为“天主教不可知论者”或“天主教无神论者”,他会怀疑上帝是否存在,却从未放弃过对耶稣基督的认同。在他晚期的重要作品《名誉领事》(The Honorary Consul)中,劫匪利瓦斯神父断定人类的邪恶来自于上帝的阴暗面,却看重忍辱负重的基督,“我相信十字架和基督对人类的救赎。那既是对人类的救赎,也是对上帝的救赎”,[12]262小说中神父的话语也就是格林本人的信念。
三、“人性的因素”的救赎力量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格林将自己的小说分为两种:小说和消遣读物。两者界限非常清晰,《布赖顿棒糖》等探讨人与上帝关系的小说多有内心挣扎,力图进入人生命体验的深处;消遣读物大多为侦探故事,背景也是阴郁可怖的种种世界,主人公也不乏倦怠,疲惫地寻找或显示着动人的情谊,不过格林在这里展现的主要是编织惊悚情节的高超天分,写得也更快一些,代表性作品有以下几部:《一杆出售的枪》(A Gun for Sale,1936)、《秘使》(The Confidential Agent,1939)、《恐怖部》(The Ministry of Fear,1943)、《第三者》(The Third Man,1949)。五十年代以后,两者之间的界限消失了,格林将激动人心的情节和灵魂的挣扎糅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创作模式。此时格林的天主教信仰已经开始动摇,这种模式的小说更接近他的“消遣读物”,是没“受过洗礼的”,[13]149-150主人公大都不再是天主教徒,没有那种天主教徒才有的挣扎——犯有罪孽,却又热切地想亲近上帝。这类小说创作从《文静的美国人》(1955)开始,一直延续到格林的最后时期,比较重要的有《名誉领事》(1973)、《人性的因素》(The Human Factor,1978)、《第十人》(The Tenth Man,1985)等。
五十年代格林作为一名记者报道过肯尼亚和越南、马来亚等地的紧张局势,六十年代之后他版税丰厚,又是世界知名作家,在全球各地来去更加自由,拉美地区因为频发革命或政治危机最受他的注意。这些旅行消除着他的厌烦,也帮他积累起各种素材,他开始描述多种政治冲突中个人的徘徊与选择。《文静的美国人》中,天真的美国人派尔不满法国人与越盟僵持不下的战争,想通过扶持第三方势力实现越南的民主与自由,不惜让许多平民丧命。对此老练的福勒不得不作出选择,派尔也因此死于非命。《名誉领事》是一个劫错人质的故事,医生普拉尔行走于行政机构和劫匪之间,力图在国家的冷漠和革命的暴力之间找到一点空隙,救福特那姆一命,最后自己却命丧枪下。《人性的因素》则塑造了几个英国特工,他们身上人性的因素使其在英苏间谍战中备受打击:一个被杀,一个辞职,一个逃往苏联后发现自己不过是个棋子。格林说,从1933年起政治在他的书里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政治事件往往后果惨烈,更集中地显现出人的邪恶和苦难,他愿意在这样背景之上展开自己的故事,“你如果首先激动观众的心弦,就可以使他们接受你所要描述的恐怖、苦难和真理”。[14]2
格林常有对现实的不满,也怀疑任何一种政治势力或思想所宣扬的美好图景。《权力与荣耀》中神父质疑中尉的共产主义倾向,以为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什么,“你们党里的人不都是好人。于是过去那些坏事就要重新出现,有人挨饿,有人挨打,也有人发财,等等”。[8]273《文静的美国人》里,福勒嘲笑派尔要给越南人带来自由、民主的信念,“他们要够吃的大米,他们不要去塞炮眼。他们希望有那么一天跟别人平等。他们不要我们这些白皮肤的人待在这儿,告诉他们什么是他们所需要的。”[5]103格林不相信政治手段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问题,权力很容易同暴力、邪恶连接起来,只有悲悯和同情、爱和对具体生命珍视才能给这个阴暗的世界带来些许光明。五十年代格林的天主教信仰淡去之后,他的书中开始肯定温暖的“人性的因素”。《名誉领事》中的劫持事件里的曲折让普拉尔和福特那姆都感受到了爱的存在,最后福特那姆原谅了还对普拉尔心怀眷恋的妻子,“他意识到,克莱拉以前从没有跟他像现在这样靠得这么近”。[12]312《人性的因素》中,双重间谍卡斯尔不认为通敌就是背叛,他觉得存在着由依恋、同情构成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国家。
这大体上也是格林现实世界里的立场,他激烈地反对美国的政治干预,为卡斯特罗和叛国间谍菲尔比辩护,批评苏联政府对作家的迫害。他常常喜欢与主流的意识唱反调,强调“不忠诚的重要性和美德”,因为忠诚“毒化人们心灵上的泉源,限制人类的同情心,鼓励人们发出嘘声”,会导致国家“永恒地混淆公正与报应界限”的危险,[15]47而“作家应随时做好改变立场的准备。他为弱者说话,而弱势群体是在变化的”。[16]
20世纪人类的罪恶和苦难在格林作品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迹,格林步履沉重,延续《圣经》的传统,讲述着人类苦难和救赎的故事。他喜欢引证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布娄格拉姆主教》中的几行诗,并愿意用这几句诗总结自己的所有创作:
我们的兴趣在事物危险的一端,
诚实的盗贼,软心肠的杀人犯,
迷信、偏执的无神论者……[17]10
格林洞悉人性的弱点,知道爱与行善的艰难,“我是一个极其相信炼狱的人,炼狱在我看来,具有意义……你会有一种活动的感觉。我无法相信一个只是消极被动的幸福的天堂。”[18]2通过作品中弥漫着的倦怠和悲悯,格林告诉我们:没有轻易的救赎,人只能经历磨难才能认识自己,才能与他人、乃至与基督和上帝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