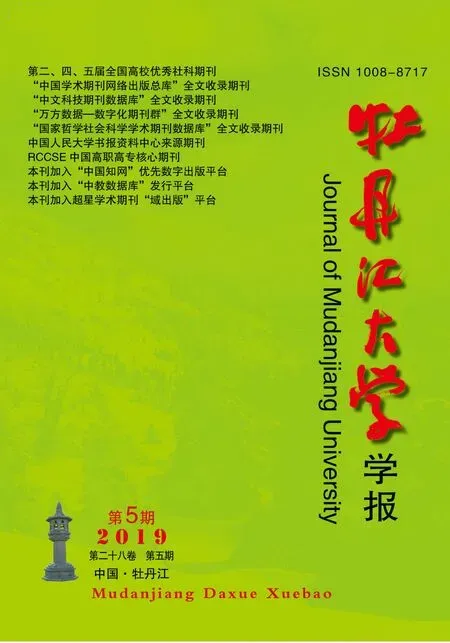论叶梅小说的民俗书写
姚 瑶
(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宁夏 银川 750001)
在当今多元文化的背景下,立足于本土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其民族元素更多成为标榜民族作家身份和吸引读者目光的噱头。聚焦于传统/现代的经典二元对立,少数民族作家在书写乡土,关注底层、边缘经验等方面不自觉地将目光转向民族传统文化,在拒绝将民族文化过于符号化和场面性的呈现于文本创作中,更多的是力图通过本土写作反思民族的历史和记忆与现代文明和全球化进程的碰撞和冲突。
叶梅的小说再现鄂西神秘而独特的峡江生活和一方土家人的浮沉历史,土家民俗在作家笔下艺术化,紧密联系着民族意识和家园想象进入文本整体,对神奇的地域风光和独特的民族文化真挚的赞美与讴歌,暗含了作者对于整个民族的深切关怀。在她的创作中对民族历史、神话传说和民俗文化的书写,使作品在整体上具有多重象征意蕴,作家叶梅有着少数民族、女性、现代知识分子等多重身份,自觉感知到本民族传统文化在生存空间上的困境,构成一种深层“无意识”隐藏在文本创作之下,通过小说表达着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反思和批判。
本文以民俗书写为切入点,从细致的文本分析入手,探析土家族的民俗元素在叶梅小说中的整体表现特征,结合土家族的具体民俗探究小说创作中体现的深层意蕴,着眼于作家的多重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写作背景分析叶梅的小说创作与民俗书写的相互关系和价值意义。
一、土家民俗文化进入文本书写的整体性表现
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中国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将土家文化的民俗元素置于文本中分析,民俗书写不应是简单的场面化呈现,叶梅的创作暗含着在多元语境下,将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与民俗书写形成有力的结合,更为深入到整个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剖析,“叶梅为民族文化的表现,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提供了另一种方式:温柔的反抗,这种反抗又主要通过极力展现民族文化本身的美感而得以实现。”
土家人日常生产生活离不开民歌,重大的节日庆典、祭祖活动等更是离不开各种歌谣的吟唱。号子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创作演唱的,是直接伴随体力劳动,并和劳动节奏密切配合的民歌”,是劳动中最简单、有节奏的呼号。《撒忧的龙船河》中龙船寨的桡夫子覃老大和覃老二常年往来于峡谷险滩之间,两兄弟一人掌舵一人扳浆,空寥的峡谷河流之中,挥汗如雨的汉子们响起有力的号子声:“拖,拖拖——!拖,拖拖——!”简单有力的民歌号子不仅体现出桡夫子的健壮体魄,更是将鄂西山川险阻的峡江地形侧面烘托出来,展现一幅质朴豪迈的土家人行走于大江峡谷险滩之间的生动画卷。当莲玉初见覃老大健壮雄悍的身体时,少数民族原始气息的男性伟力以强势攻势将女性充满生命力的自然欲望完全释放:“桡夫子覃老大于岩壁上拖着纤绳,全身却是一丝不挂,那古铜色肉体在夕阳余晖映照的青翠之中格外突兀,厚实的脊梁、硕圆的扭动的屁股和粗壮的双腿在小城女子莲玉眼前烧成一蓬大火。”充满原欲和自然人性的裸露下,覃老大作为土家族力与美的文化象征体与代表汉文化身份的莲玉,显然是隐喻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冲突,莲玉对覃老大的主动迎合的姿态,不自觉地摒弃儒教传统、三纲五常的思想束缚,充分表现作者对有着鲜活的生命力和自然、原始气息的土家文化的赞扬态度,“可以将这些对于少数族群文化的呈现,看作主流或中心文化的自我形象的投射。”
舍巴日是土家族集祭祖、祈福和庆祝丰收功能等为一体的古老节庆活动,舍巴,意为“摆手”,舍巴舞就是“摆手舞”。土家族人的狂欢心理,都在这重大的节日民俗活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特别是众人齐跳舍巴舞的环节,这是整个活动的最高潮,族人们以虔诚敬祖之情在返璞归真的舞蹈动作中得到尽情的宣泄:“一年之中最要紧的祭祀舍巴日又来到了。……鼓声如雷滚过舍巴堂,那祭祀的黄牛又牵上场来。三通鼓过,牛在寨民们震耳呐喊声中射出一道红光,场上跳起了舍巴舞。先有一群象征先人的“茅谷斯”扫堂,人们全身赤裸返璞归真,只用兜布围了羞处,夹一把竹扫把扫进扫出。扫天瘟地瘟,牛瘟马瘟,收风调雨顺太太平平。”古老而健康的风俗在淳朴的土家人传承延续,激情的舞蹈和奔放的人们一起痛快的燃烧。这样极具民族特色的民俗场面,不只是单纯宣扬自由奔放、健康人性的民族性格,更是将狂欢的节庆盛典与人物的悲剧命运相照应。
《最后的土司》中哑巴伍娘以热情奔放的舍巴舞亮相,先天性的失语不能阻止她以舍巴舞来表现对生命的渴望,对情感的诉求。尽情的舞蹈将姣好的面容,窈窕的身材展露无遗,充满着鲜活的生命力,她因舞蹈而生。就是这样一个善良与美丽的女子,在面对土司覃尧和李安的三角情感纠葛中,以母性的宽容和牺牲面对命运的不公,终究在失去爱情和孩子的双重打击下,她没有指责任何人,更没有选择报仇,以忘情的舍巴舞绝望地结束自己生命的燃烧,通过舞蹈以无声的控诉,忘却悲伤,她因舞而死。舍巴舞对于伍娘而言已不止是身体的解脱,在疯狂的动作中绽放着自己,在忘我的舞蹈中释放自己的精神与灵魂。
“在文本中,民间仪俗是双重的象征符号:作为文化的象征符号和作为作品意蕴的象征符号。”民俗元素进入小说文本后,并不是单一的民俗风景化呈现,而是紧贴人物描写的辅助作用:山高水急的峡谷之间,覃家兄弟的形象因劳动号子而更具有力与美的民族文化象征体;狂欢的节日场面与伍娘凄凉的落幕形成巨大反差,民俗元素更是作为环境烘托,蕴含着人物悲惨的命运结局。
二、梯玛信仰与巫文化崇拜:土家民俗之精髓
南方少数民族都盛行巫鬼迷信,土家人生活在山川险阻之中,与世隔绝,这里的百姓自觉遵守着古老而传统的生活方式,从原始先民传承下来的对自然的敬畏、对一切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虔诚信仰。
“民俗一旦形成,就会成为集体的行为习惯,并在广泛的时空范围内流动。”②土家族的各种民俗事象蕴含着巫文化崇拜和迷信观念,体现在土家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日常生活到生产劳动皆被民间信仰“隐形”控制,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民俗心理:“反馈于人类自身而形成的具有群体历史精神内涵。”③诸如《撒忧的龙船河》中巴茶就将丈夫心有他人的行为,认定自己的男人是“丢失了魂魄”,为了挽回丈夫的心而实施“喊魂”的巫术:“就去镇上买回来香油灯烛,到晚间将四对香烛点燃在神龛上,将青青茅草掐一段压在炉脚,又掐一段点火烧去,然后沿着河岸用嘶哑和凄凉召唤老大:更尼啊——泥猪替得他的真魂,蚂蚁替得他的真命。乾塔地界上,拿了他的真魂,探了他的真命。魂来归家哎——魄来安身——”。“喊魂”仪式后确实让丈夫回到龙船寨,却“喊”不回丈夫倾心于外乡女子的心。巴茶的行为揭示了土家族妇女面临婚姻危机时,无力解决夫妻关系中的被动姿态,妄图通过迷信的行为改变自己的婚姻状态,始终在父权社会的阴影下被遮蔽而无力反抗。民间信仰在乡土社会中很容易产生负面、迷信的影响。叶梅的民俗书写也不再是一味的风俗画卷的展示,而是对“喊魂”封建巫术和愚昧的民众持批判的态度,同时暗含着无奈和同情的目光看向土家妇女的生存困境。
“从事祭神驱鬼巫术的人常是老土司,土家语称他叫‘梯玛’。”“梯玛”一是指一种古老的宗教仪式,二是指负责人神之间沟通的梯玛仪式的巫师。作为梯玛,身负着主持祭祀、婚嫁丧葬、祈福求神、卜卦预言和救人等重要职责。信仰巫术和梯玛的神力能带给族人安定生活的信心,求得祖先神灵的庇佑。梯玛对于土家族传统文化不仅是传承者,更是传播者,是神秘的巫文化重要的一部分,而梯玛信仰更是土家文化的信仰核心。
叶梅的多部小说中梯玛信仰都作为文本之下隐藏的核心线索,引导着人物各自的命运结局。龙船寨的土家人与梯玛信仰已然融为一体,引导和约束他们生活行为的各个方面。“凡嫁到龙船河的女子,初夜都是奉给神的。”《最后的土司》中三个主人公的情感纠葛皆因这句话而起,当李安在未举办婚礼的情况下想和伍娘行周公之礼时,伍娘拒绝了按捺不住的李安,拒接婚前失身,只因伍娘有着虔诚的梯玛信仰:初夜权必须献给神以求获得神灵的保佑和祝福。覃尧明白初夜权只是对神的敬献仪式,身为土司他必须充当神的象征体,对每一位龙船寨少女行使初夜之俗也是有名无实。但是在伍娘出嫁的过程中他却发现自己已然深深爱上了伍娘,决定在利用初夜权占有伍娘。李安作为外乡人,无意间闯入龙船寨代表着异质文化——外来文化与土家文化的直接碰撞和冲突,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观念注定让他无法理解土家人的梯玛信仰和精神文化,注定了他对伍娘的不贞而报复,对整个龙船寨的痛恨。梯玛信仰在三人之间呈现出三重冲突:伍娘作为土家精神中纯洁“天使”的化身;覃尧是身为土司,代表土家文化的捍卫者;李安是代表异质文化的外乡人,注定他们三人的悲剧命运因土家人的梯玛信仰而各走一方。叶梅聚焦于民族文化发展的思考中揭示深刻的矛盾与冲突,本土文化能否对现代文明进行抵抗或者对话,民俗书写将文本引入深层次的批判与反思,凸显很大的张力。
三、创作主体的多重身份和文化认同的民俗书写
叶梅作为一位土家族作家,其民族身份和女性作家是很多研究学者的关注点,作为当代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女作家,她的创作也并不局限于民族题材,更多的是在时代变革下具备现代知识分子的敏锐和理智,立足于本土、本民族的创作姿态。就叶梅的多重身份来说,除去族别、性别身份,对她创作影响起到原动力的知识分子身份不容忽略。可以说作为现代知识分子,让她带有不自觉的对现代文明和全球化进程后果的警惕和焦虑感,叶梅也深刻意识到,力图构建诗意般的民族历史家园的可能性在无孔不入的现代化影响下希望渺茫,那种理想化、浪漫化的诗意追寻必然找不到出路,所以立足于本土书写的坚守姿态必然带有现实主义倾向,具有批判和辩证思维以创作乡土文化寻根。
“民俗事象因其丰富性、直观性、原生态性、生活化、可操作性和巨大的文化张力等特点,经过交糅组合,能够比较容易将构想的意念转化为审美的物化形态,传达出作家的深度思考。”鄂西峡江一带的秀美风光和浓郁的民俗文化积淀通过女性作家细腻、敏锐的体察,叶梅很自然地运用本民族的民俗元素题材进行文本创作,再者民俗文化广泛植根于中国乡土传统之中,民俗书写有助于深入土家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挖掘。
“文艺创作中艺术思维虽然如潮水般流动,但思维的民俗心理结构,却是潜藏着的看不见的河床,规范着它的流向。”叶梅的民俗书写将视角始终深情望向生活在鄂西乡土之中的土家人,对土家文化的热爱和作为言说主体的本土文化认同,性别身份和民族身份依然凸显叶梅小说的整体风貌。关注女性生命经验的创作更是让多重身份的作家在多元文化语境下显示出多重话语冲突和反抗,更是带有现代知识女性对于时代女性的命运和情感困境的思考。“哭嫁”是土家族人婚礼的序曲,真诚直白的唱词,用情至深的眼泪是待嫁少女倾诉心中的情感特有哭嫁方式,“以表感激父母养育之恩和亲友难舍难分之情”。“夜晚,火塘里烧起疙瘩柴,火苗子扑扑地闪,一溜姑娘家围着火塘坐定,轮次地唱。……后生们拥挤在吊脚楼下如痴如醉,听得皓月当空,听得五更鸡叫。”待嫁闺中的少女经由哭嫁仪式后进入婚姻的殿堂完成了女性身份的转换。《花树花树》中瑛女和昭女两姐妹在现实境遇下遭遇着同样的情感不幸和悲剧宿命,她们有着土家人美丽和刚烈的特质,各自的不幸也呈现出爱情在性别秩序上女性的被动和失语:昭女和瑛女在面对现代知识的索取下,昭女刻苦读书只是希望有份立身的工作,而瑛女早就放弃读书只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花布店。为什么面对现代文明的积极或疏离的态度依然会让两姐妹在爱情更或是人生有着同样的悲剧:身体已然被男性欲望而占有,精神上也无力挣脱。女性的解决途径只能是出走或者结束生命:昭女对这个麻木愚昧的乡村绝望而出走,瑛女选择自焚而亡,以放弃生命的代价拒绝畸形的乡土世界。小说的尾声响起那为女子的不幸而唱哭嫁歌:“娘啊,我是一口生水锅啊,不会伸来不会缩啊,要伸要缩除非破啊。娘啊,我是一根青枫炭啊,来到这世上不会弯啊,那要扭弯除非得断啊……”人喜则笑,遇悲乃哭。哭嫁也分真哭和假哭,在瑛女生命结束时响起的哭嫁歌,当然不是一个待嫁女子“假哭”要嫁给心爱的男子的心境,此刻的哭嫁歌是真切的悲悯瑛女可怜的命运,女子个人遭遇的哭诉,真真切切,让人叹息。这样的民俗仪式加上坎坷不幸的人物命运不再是民俗魅力和地域色彩的表现,动人的唱词使整篇故事充满了峡江女子对于爱情的向往,对个人命运多舛的无奈,就像那山高水长的路途一样虽坎坷艰难,却又必须面对走下去的悲凉命运。
叶梅的小说展示了一幅幅土家儿女鲜活生命力的风俗画卷,当中不乏有田园牧歌式的家园想象,更重要的是她的作品中体现出自觉寻根本民族文化,特别是在现代文明进程与民族传统文化生存空间的冲突与碰撞,坚持本土书写的坚守姿态进行反思和质疑。
作为当代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女作家,叶梅在很多作品中都是以鄂西峡江生活的普通民众的情感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内蕴和独特的审美价值。作品中大量有代表性的土家族民俗书写与小说文本叙事融为一体,构成了小说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鲜活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淳朴的民风以及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情。在此要强调的是,民俗书写并不能成为解读叶梅小说的多重内蕴和价值意义的唯一途径,民俗书写表现在作家的多重身份和文化认同的观照下,蕴含着浓郁的土家文化与全球化现代文明进程的反思,更为丰富作家的创作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