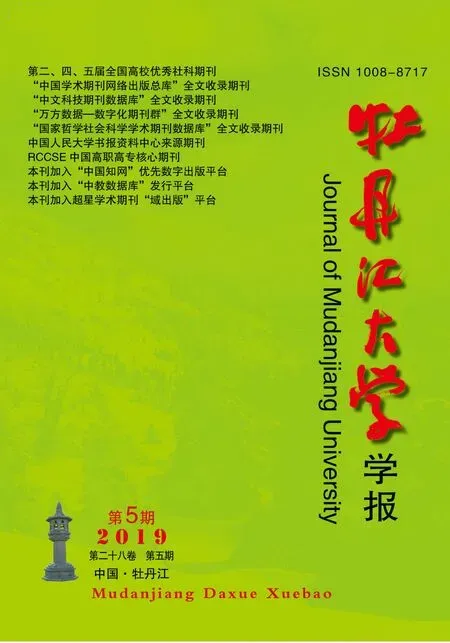身体·暴力·审美
——余华《一九八六年》的身体叙事探论
张 不 凡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余华是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浪潮中备受关注的当代作家。无论是早期的先锋创作还是风格转向后的写实创作,我们在余华小说中都得以窥见他将人物身体的感受置于中心地带,并将身体与政治、身体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深刻思考,身体现象成为余华小说里的“典型风景”。《一九八六年》中的身体被呈现为书写的对象、叙事的对象,也是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作用对象。但是,学界对余华作品的研究主要侧重在主题特征、语言风格、暴力书写、死亡意象和零度叙事上,始终没有把承受这种暴力和死亡折磨的身体作为探讨的核心。鉴于此,从身体叙事的角度解读余华的小说《一九八六年》,追朔其中的内涵是很有必要的。
一、《一九八六年》中身体的隐喻内涵
身体是我们得以生存和感知世界的载体,关于身体的讨论,西方经历了从传统的身体之沉重到现代的身体之觉醒再到后现代的身体之“逆袭”的三个转变,即从柏拉图的扬心抑身到尼采的“一切从身体出发”再到福柯的权力视角下的身体。可见,西方从关注理性转向关注感性,身体自然成为研究热点,学界将“身体”与各个学科联系起来形成了对身体的多视角研究。譬如:理查德·舒斯特曼将身体与美学联系起来,并且开创了身体美学这一学科的先河。他在《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一书中还指出,“身体是我们身份认同的重要而根本的维度。身体形成了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最初视角,或者说,它形成了我们与这个世界融合的模式。”[1]13“身体”代表着感性,它作为与理性相抗衡的重要对象在西方受到更多关注与探讨。除了西方,中国文化中亦有许多对“身体”的探讨。“如果说传统西方哲学是一种以意识为其根本的哲学,是一种意识本体论的哲学的话,那么与之迥异,中国古代哲学则为一种以身体为其根本的哲学,是一种身体本体论的哲学。”[2]28中国哲学家关注的不是意识而是身体,他们始终将“身体”置于核心位置。譬如《淮南子》谓“圣人以身体之”(《淮南子·论训》);庄子谓“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庄子·德充符》);王夫子谓“即身而道在”(《尚书引义四》),如此等等无一不是其强有力的印证。
由上可知,中西方关于身体的讨论,由来已久且涉及到各个学科领域,这为身体叙事的出现和存在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身体叙事起初是带有性别意味的概念,也就是将身体叙事与女权主义紧密联系,让身体成为女权主义者言说和捍卫的对象。到了20世纪末期,一些学者试图将身体与叙事学结合起来,构建起身体叙事理论。虽然身体叙事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我们认为身体叙事就是以身体本身作为叙事的对象,围绕身体展开叙事策略,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在80年代中期的“先锋小说”中,对死亡和暴力的研究无疑是“先锋小说”的优长,因而对身体进行阐释就成了一种必然。作为先锋作家的余华,他的作品中自然存在身体叙事这一创作迹象。余华试图在许多作品里都引入了身体维度,不是间接地表达,而是直接加以明示。在《现实一种》《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等作品中余华直接将身体的各种痛苦呈现出来,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又一个“身体奇观”。《一九八六年》是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的一部中篇小说,它与侧重于描写特殊时期人们不幸的“伤痕文学”的作品不同,《一九八六年》没有侧重描写历史事件,而是将其作为故事的一个背景,表现文革后主体的精神创伤与肉体挣扎。在《一九八六年》中,中学历史老师的疯癫与自戕揭示出文革对历史老师身心的双重伤害。余华通过中学历史老师的疯癫行为诉说历史,反映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身体与历史同构了。这种将身体历史化的叙事方式颠覆了以往作家对历史叙述的传统方式。从某种意义说,疯子的一次次令人战栗的自我残害向读者展示了那段历史对身体的规训与惩罚。余华将历史老师的身体作为一种隐喻来揭示那曾压在疯子身上的令人压抑的历史,批判文革对人身心的毒害,批判文革遗留下来的精神浩劫和潜藏的影响。正如高宣扬所言:“人的身体作为象征性的结构也是一种文本,它是文化符号和象征性语言的浓缩,是各种历史事件的见证。在人的身体及其各个部分中,呈现了人类的所有喜怒哀乐的经历和体验。身体及其各个部分的审美意义,是身体伴随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的记录和见证。”[3]475总之,历史老师的身体作为苦难记忆下的一种书写,它不仅推动着故事的发展,还在叙事中逐渐被符号化、历史化、象征化。
二、身体叙事的另类景观:暴力叙述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暴力叙述在中国文坛成为一种显要书写,先锋派作家热衷于通过展现暴力去探讨历史与政治,发掘出暴力书写背后的深刻意味与美学追求。余华作品中呈现出的暴力是不容忽视的主题,作为暴力的承受对象即身体更是他苦心经营的叙事焦点。余华的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从历史的高度剖析酷刑文化,表现出他对暴力背后人类身体意识、生存境况的强烈关注;此外,他从视觉文化的“看”与“被看”中批判了看客文化以及人们邪恶的审美趣味。
(一)显性的暴力:身体的酷刑体验
“暴力总是针对身体的,没有身体就没有暴力,即使是思想文化、语言符号、意识形态的暴力,也总是落实在身体或作用于身体。因而书写暴力是书写身体的一种方式。”[4]31《一九八六年》描写了一位经历了“文革”的中学历史老师突然失踪,多年后他成为疯子重返故乡,他在街头上当众自戕以展示“文革”暴力,并以自己分裂的双重人格进行残忍的“报复”。他的“报复”是通过极其残酷的刑罚来实施的,即墨、劓、剕、宫和凌迟。这些残酷的惩罚方式是非人性化的,是一种加之于肉体之上的显性的暴力,它代表着权力对身体的压迫、制裁和摧毁,身体只能去承受这种压迫、制裁和摧毁。余华将这种权力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了循规蹈矩的中学历史教师的身上,他将“报复”之刃指向自己,将这满腔无处发泄的痛苦转化为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自虐。历史老师在承受这种显性的暴力时呈现出双重身份,他既是施虐者,也是受虐者。起初疯子幻想着对来来往往的人们施以酷刑,他在这种想象性的疯癫状态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和快感,即便如此他依然觉得不够痛快淋漓,于是他开始对自己的肉体实施酷刑。
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于是黑乎乎的嘴唇开始红润了。不一会钢锯锯在了鼻骨上,发出沙沙的轻微摩擦声……鲜血此刻畅流而下,不一会工夫整个嘴唇和下巴都染得通红,胸膛上出现了无数歪曲交叉的血流,有几道流到了头发上,顺着发丝爬行而下,然后滴在水泥地上 ,像溅开来的火星……接着伸出长得出奇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入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里闪烁着红光……接着就将钢锯取了出来,再用手去摇摇鼻子,于是那鼻子秋千般地在脸上荡了起来。[5]134
这段“劓”刑过程的精细描绘让读者毛骨悚然、颤栗不安。疯子对自己的身体施行了五种惨不忍睹的刑罚,当他作为施虐者即暴力主体而居时,他的肉体充当了受虐的对象。因此,疯子的暴力指向仍是他自己。但是不论疯子充当施虐者还是受虐者的角色,两方面都真实反映了疯子才是历史暴力下真正的受害者,他在历史暴力下变得疯癫,这种疯癫让他做出残害自己身体的行为。余华没有刻意强调暴力背后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因素,而是将暴力事件或暴力行为集中表现为疯子极端化的“狂欢”。不可否认,这是一场盛大而残酷的刑罚“表演”,人从刑罚产生之日起,它就作用于人的身体,身体是主体言论、行动的承载者。在历史老师的身上,刑罚权赤裸裸地实施在肉体上,撕裂它,摧毁它。透过残酷刑罚下身体的书写,突出了刑罚的狰狞可怖,揭示出文革历史对人们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摧残,表明身体是政治与权力所施加的对象。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指出:“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符号。”[6]27在福柯的权力与规训的视角下,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权力运作的中心始终是身体,肉体的惩罚只是一种手段,它是为了对社会民众的精神进行规制。
(二)隐性的暴力:看客的目光
看与被看在鲁迅的小说中或隐或显地出现,成为鲁迅小说的一大景观。在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塑造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看客群像,覆盖了社会底层的各种人,这组群像有着共同的特点:愚昧落后、狭隘自私、百无聊赖、麻木冷漠。他们无论男女老幼,都没有姓名,没有具体的相貌,只有一个动作——“看”。鲁迅认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7]170在这些“群众”的眼中,别人的事情是“一出戏”,他们作为看客只需旁观。鲁迅在他的小说里不留余力地批判这类麻木不仁、愚昧无知的看客,继而站在启蒙立场严厉地批判国民性和人性。在鲁迅的影响下,看客文化进入了文学的视野,作家们紧跟鲁迅的步伐,深入剖析、批评看客文化。于是小说中出现了许多看客群体或个体形象,如莫言的《檀香刑》中就不乏看客的存在,他们以观看行刑为乐趣。妓女被凌迟的时候,刑场上围满了观众,“六君子”被行刑的时候,看客更是成千上万地涌上去。在《一九八六年》中,余华也将笔触对准了“看”与“被看”。当疯子开始忘乎所以地自残时,周围的行人冷漠地观看着,“那个疯子用自己的肉,让他们一次次重复着惊讶不已,然后是哈哈大笑。于是他们又说起了早些日子的疯子,疯子用钢锯锯自己的鼻子,锯自己的腿,他们又反复惊讶起来,还叹息起来。叹息里没有半点怜悯之意,叹息里包含着的还是惊讶。他们就这样谈着疯子,他们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恐惧。他们觉得这种事是多么有趣,而有趣的事小镇里时常出现,他们便时常谈论。”[5]148看客以观看疯子的戕害为乐,他们没有意识到疯子疯掉的原因与自残的真相,更不会意识到他们也活在历史的压迫之中,他们选择的是继续麻木地过自己的生活。在这里,看客们冷漠的目光足以将疯子判以死刑,这象征着一种隐性的暴力,它虽然不像历史暴力那样显而易见,但是它却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无处不在,几近于“杀人的帮凶”。
三、荒诞化的审美向度:身体的暴力美学
“暴力美学”起源于美国,在香港电影界发展成熟,是一种“艺术趣味和形式探索”。随着“暴力美学”的不断发展,它不仅局限于影视之中,还渗透到文学、电子游戏、动画、漫画、平面设计等多个领域。《一九八六年》中的暴力是与伤害、自残、死亡挂钩的,而美则是与真善挂钩,所谓真与善的和谐统一带给人愉悦的生活形象,称之为美。换句话说,美既然服务于善,更多的就与“生”相关联。而暴力直接与“死”相关联。两个如此相悖的词联系在一起,何以产生美感呢?我们认为这种暴力让人内心获得某种满足感是产生美感的一个原因。在暴力中获得满足或想象会在暴力中获得满足的人,一般都会认为暴力是美的。表现在电影中,战争片就是最好的例证。战争片如果不是从研究人性和反思历史出发,仅仅只是某个党派展示战争结果的政治宣传工具,那么都会有一种美化暴力的意味,即己方的暴力是美丽的,民众很自然地就会将己方暴力与宏大、庄严、崇高、正义等词联姻,于是观众能从电影预设的暴力中获得一种审美的愉悦感。表现在小说《一九八六年》中,也是同理。小说里的历史老师自残时的暴力性、血腥性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作为置身事外的民众在观看时,虽然会表示出不适的反应,但他们依然围上去观看,满足了好奇心之后他们愉快地散开了,全身心的满足感或愉悦感似乎要从胸膛里暴溢出来。这种暴力叙述演化为一种新的美学风格,一种荒诞化的审美即“暴力美学”,它通过暴力叙述和身体书写颠覆传统美学,是对传统美学规范的突破与反叛。传统美学崇尚真善美,然而“暴力美学”以刺激感官为主,以审丑的审美趣味站在传统美学的对立面,颠覆了传统美学,亦在陪衬下或对比中凸显真正的美的存在。朱立元在其《美学》一书中提到的:“在有些情况下,真正的美学是以反美学或非美学的面目出现的。”[8]18余华的“暴力美学”正是用“反美学或非美学的面目出现的”,他通过对暴力荒诞化的审美处理,用暴力的形式深度反讽历史暴力的真相与不堪,使其存在能够提醒人们认识到现实世界的残酷与丑恶,并认识到历史暴力对人的戕害。余华透过暴力之美深刻地透露出他对人们适应新文明的担忧,揭示出人的生存困境,反思暴力之恶带给人类的惩罚与痛苦。
四、结语
在《一九八六年》中,余华以身体、暴力、审美这三个方面的叙述展示了他对暴力、历史、人的生存困境等的全面思考。他用直接呈现身体的感知和书写生命体验的方式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模式,将身体维度引入叙事之中,这就为身体叙事提供了新的视角,对当下的身体写作仍有可供开掘的借鉴意义。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身体写作开始偏向商业化和庸俗化,出现了一些“宝贝”作家,以棉棉和卫慧、木子美等为代表。她们为了迎合市场与大众,她们笔下的身体写作主要是性的书写,然而性并不是身体书写的唯一方面。余华的身体叙事不是一种简单的身体描写,而是感官的写作,意味着各种感官都是在场的,如听觉、视觉、嗅觉、触觉的在场。余华的身体书写连接着对意义的质问和对价值的追寻,这为消费文化下的身体写作提供了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