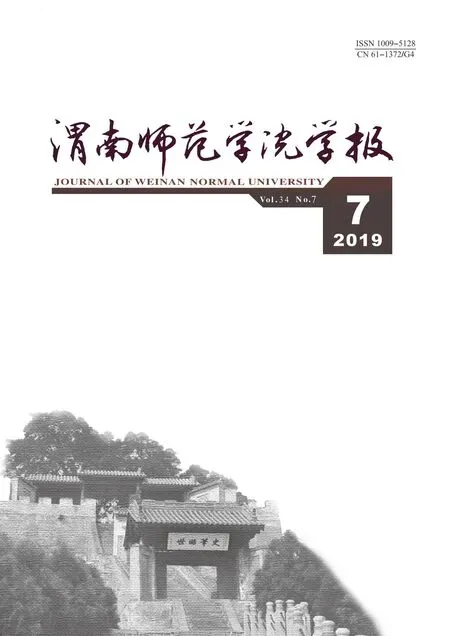楚汉战争中的“五诸侯”再讨论
崔 建 华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119)
秦朝灭亡后,项羽主持分封,“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1]317。而齐地豪强田荣因“不肯出兵助楚、赵攻秦,故不得王”,遂“怨项王”,“乃自立为齐王,尽并三齐之地”,“项王闻之,大怒,乃北伐齐”[1]2645。正是在项氏无暇他顾的形势下,发生了刘邦统领“五诸侯”直捣彭城的战事。对于此事,《史记》《汉书》皆有记载。然而古今学人对所谓“五诸侯”究竟何所指,分歧甚大。笔者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申说己意,愿就教于方家。
一、“五诸侯”相关史料及新说平议
与彭城之战有关的“五诸侯”概念,《史记》可见如下两条记载:《史记·项羽本纪》:“(汉二年)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1]321《史记·高祖本纪》:“项羽虽闻汉东,既已连齐兵,欲遂破之而击汉。汉王以故得劫五诸侯兵,遂入彭城。”[1]371在这两条之外,叔孙通的传记当中亦可见“五诸侯”称谓。《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叔孙通降汉王。”《汉书·叔孙通传》:“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通降汉王。”通过比较可见,《史记》“叔孙通”在《汉书》中只是简作“通”而已,丝毫不影响对文意的理解。虽然叔孙通传记中说“从五诸侯”,与《史记·项羽本纪》的“部五诸侯”,以及《高祖本纪》当中的“劫五诸侯”在用字上有异,但“从五诸侯”本身即是一个中性化的描述,不牵涉刘邦与五诸侯的实际关系。并且“从”与“部”“劫”混淆的可能性极小。因此,本文在论述中并未将叔孙通传记中的“从五诸侯”纳入考量。
项羽、高祖《本纪》的记载亦见于《汉书》的相应纪传,只是文字表述或有些许差异,为便于比较,亦录于下:《汉书·项籍传》:“汉王劫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2]1812《汉书·高帝纪》:“羽虽闻汉东,既击齐,欲遂破之而后击汉,汉王以故得劫五诸侯兵,东伐楚。”[2]35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汉王部五诸侯兵”,在《汉书·项籍传》里写作“汉王劫五诸侯兵”。“部”与“劫”的文字差异,《史记》注家早已注意到。如针对《史记·项羽本纪》所见“部”字,《集解》引徐广曰:“一作‘劫’。”《索隐》也说:“按,《汉书》见作‘劫’字。”[1]322但二注家仅是指出差异,皆未对“部”或“劫”有所评骘。而清人王念孙认为:“作‘劫’者是也。《高祖纪》及《汉书·高祖纪》《项籍传》并作‘劫’。《陆贾传》亦曰:‘汉王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隶书‘劫’‘部’形相近,故‘劫’误为‘部’。”[3]202如果仅从文献校勘的角度而言,“汉王劫五诸侯兵”未必是《史记》原本的表述,毕竟南朝《集解》及唐代《索隐》所见的“汉王劫五诸侯兵”,也只是来自于《汉书·项籍传》而已,至于注家是否有多种本子的《史记·项羽本纪》及《汉书·项籍传》作为校勘的文本证据,则并没有明确的说法。而班固(或其父班彪)在从《史记》中抄录相关传记以编撰《汉书·项籍传》时,在文字上或有未审,最终将“部”改为“劫”,也是有可能的。
不过,王念孙“‘劫’误为‘部’”的说法仍然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毕竟他在《汉书·项籍传》以外,又援引了《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及《陆贾传》的相关表述作为旁证,然后据以认定《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汉王部五诸侯兵”,属于“汉王劫五诸侯兵”的误写,这是合乎论证逻辑的。此外,司马迁、班固均为汉朝当代人,依照常理,他们应当为尊者讳,对开国皇帝的行为予以美化。由于所谓“劫五诸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负面道德评价,这样的表述自不当出现。但事实上,不仅司马迁在多处记载刘邦“劫五诸侯”,并且班固还照录不改。显然,他们这么做绝非为了污蔑汉高祖,合理的解释是,“劫五诸侯”是一种实录,它符合历史真相。
因此,在对“五诸侯”问题进行探讨时,“劫五诸侯”是一种比较值得信赖的文本样貌。“劫五诸侯”则明确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形,即刘邦与五诸侯之间在表面的从属关系之下,还存在着一个被迫服属的实态,而这个实态,“部五诸侯”的表述是无法传达出来的。明了这一点,便会意识到,“部五诸侯”抑或“劫五诸侯”,势必影响到确定五诸侯时所应遵循的相关原则。
关于“五诸侯”的具体所指,辛德勇先生以表格的形式列出了十二种说法[4]113-114,但实际上仍有补充的余地。[注]清人沈家本也曾详细梳理过关于五诸侯的种种论说,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指出“五诸侯共有十二说”,分别是“汉唐旧说”五种,“宋人之说”两种,“今人之说”(亦曰“国朝说”)五种。但实际上,由于司马贞与如淳的结论相同,周寿昌秉持“阙疑之意”,未下结论。(沈氏前后有不照应之处。在介绍如淳说时,沈氏曾指出洪颐煊同意如说,而“周寿昌以洪说为是”。显然,周寿昌是有自己的确切论断的,并非“阙疑”。但无论阙疑还是同意如淳之说,周氏对五诸侯均未做出新的认定,不能算作一说。)而王先谦只是对全祖望的说法表示赞同,因此,沈氏所谓十二说,实际应为九说。〔沈家本《汉书琐言》,收入徐蜀编《两汉书订补文献汇编》(第二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76-78页〕比较而言,辛先生在九说之外,新增了赵翼、汪中、吴汝纶三说。比如梁玉绳认为:“各家所数,祗韩、魏、赵、齐为可信,盖魏、赵从军皆见于其传,韩王之从军见于《月表》,合齐击楚见于《淮阴传》,是得四诸侯兵,而其一必衡山也。衡山王吴芮之将梅鋗,自高祖入武关时即以兵从,故《令甲》称芮至忠,封长沙王,则彭城之役有不属在行间者乎?”[5]206梁氏判定五诸侯分别指韩、魏、赵、齐、衡山,这个说法与辛先生所列十二说均不相同,似应列为第十三说。
另外,辛先生表列十二说中的第十说即董教增之说,似乎另当别论,置于十二说之中,或有未允。董氏之说见于王先谦所引,原文如下:
颜氏牵引诸王,以足五数,于义亦非。盖此处“五诸侯”有河南、韩、魏、殷等,而《项籍传赞》云“遂将五诸侯灭秦”,又系何人?寻其条贯,当据故七国,以其地言,不以其王言也。汉定三秦,即秦故地;项羽王楚,即故楚地。其余韩、赵、魏、齐、燕为五诸侯。“劫五诸侯兵”犹后言“引天下兵”耳。故汉伐楚可言“五诸侯”,楚灭秦亦可言“五诸侯”也。[6]43
此说实受裴骃《集解》之启发。《史记·项羽本纪》“太史公曰”:
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1]338
引文中所谓“五诸侯”,《集解》:“此时山东六国,而齐、赵、韩、魏、燕五国并起,从伐秦,故云五诸侯。”[1]339泷川资言认为:“董氏依《羽纪》论赞《集解》,其说最稳。”[7]452但王先谦指出:“董以‘五诸侯’为天下兵,古籍既无是义,此与《项籍传》‘五诸侯’亦不同。”[6]43也就是说,董教增表面上是在解释刘邦“劫五诸侯”,然而实际上谈论的却是项羽“将五诸侯”,以史实而论,前者目的在于伐项羽,后者旨在“灭秦”,两件史事中的“五诸侯”根本不是同一个概念。因此,将董说表列于刘邦“劫五诸侯”的种种论说中,有失之于表面化之嫌。
二、河南王申阳参与彭城之战的可能性
当然,瑕不掩瑜,辛先生鉴于诸说“彼此参差,出入很大”,并且“诸家各执一词,自以为是,然而却大多出自臆度,缺乏有力的证据。因此,不论其正确与否,都令人难以信从”。他提出了确定“五诸侯”的新思路:“其实所谓‘五诸侯兵’问题本来并不复杂,只要弄清到底有哪些诸侯王直接随从刘邦参与了这场战役,就可以顺利地解决这一问题。”循着这个思路,辛先生最后确认:“塞、翟、殷、魏、韩五个诸侯王随同刘邦征伐彭城具有确实可信的记载。”[4]114“所谓汉王劫五诸侯兵,指的就是这五个诸侯。”[4]117
笔者认为,辛先生所提出的确定“五诸侯”的新思维确为卓识。只是,辛先生认为韩王信是五诸侯之一,笔者对此尚有疑问。按照辛先生提出的标准,确定五诸侯的关键环节是“哪些诸侯王直接随从刘邦参与了”彭城之战,以这个标准而言,河南王申阳是不能被断然排除在五诸侯之外的。在辛先生的文章中,他做了非常仔细的考证。比如,《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记载:
汉二年,韩信略定韩十余城。汉王至河南,韩信急击韩王昌阳城。昌降,汉王乃立韩信为韩王,常将韩兵从。[1]2632
这段史料,朱希祖也曾经注意到。朱氏认为“常将韩兵从”即“指从伐楚彭城也”,由此确认韩王信是五诸侯之一。[8]辛先生对朱氏的史料解读提出批评:“今按‘常将韩兵从’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是‘常常率领韩兵随从刘邦征战’,韩信随从刘邦参与的这些战役,可能有彭城之战,也可能不包括彭城之战,从这句话本身得不出其确指‘从伐彭城’的结论。”因此,尽管辛先生与朱氏都认为韩王信是从伐彭城的,但辛先生认为朱氏的论证“并不足以取信于人”。他特地指出:“其实韩信从击彭城,在《史记》《汉书》当中别有清楚的记载,朱希祖用不着强据本传立论。《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及《汉书》卷一三《异姓诸侯王表》,均记载韩信在彭城之战发生的同一月内‘从汉伐楚’,这是韩信参与彭城之战的确证。”[4]115-116
辛先生断定韩王信参与了彭城之战。然而,对于河南王申阳是否参与彭城之战,辛先生却没有如此深入的考证,只是说河南王派兵参战是“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说明”的,前人认为河南王居五诸侯之列的看法“出自臆度,故无须多事辩驳”[4]120。笔者以为,辛先生这个说法并不十分周全。从逻辑上讲,河南王派兵参与彭城之战一事,即便“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说明”,那也不能必然地得出河南王不曾参与彭城之战的结论。仅就可能性而言,有的诸侯王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其一定参加了彭城之役,但不宜由此全然否定其参与此役的可能性,河南王申阳即属于这种情况。
判断诸侯是否参与了彭城之战,史书对彭城战败后诸侯下落的记载也是一种有益线索。比如,根据《史记·淮阴侯列传》:“汉之败却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汉降楚……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国,即绝河关反汉。”可知,塞、翟、魏三王参与了彭城之战。根据《汉书·高帝纪》:“诸侯见汉败,皆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2]36又可知殷王司马卬也参与了彭城之战。至于河南王申阳的下落,史籍虽未有明确记载,但《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南安侯”条记载:“以河南将军汉王三年降晋阳,以亚将破臧荼,侯,九百户。”[1]910此处所谓“河南将军”值得推敲。
秦汉之际很少见到将地名冠于“将军”之前的正式官号,“河南将军”究竟是什么身份?我们注意到,史家对当时职官的记载常呈现职位前冠以国名的形式。如“彭越为魏相国”[1]2592,高祖功臣冯解敢“以代太尉汉王三年降”[注]《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945页。“代太尉”,《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写作“代大与”,见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92页。似应以“代太尉”为是。,又如韩王信,“汉王还定三秦,乃许信为韩王,先拜信为韩太尉”[1]2632。肥如侯蔡寅“以魏太仆三年初从”[1]911,义陵侯吴程“以长沙柱国侯”[1]950。至于将军称号,检索《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所见将军,最常见的是裸称者,如平阳侯曹参“以将军入汉”[1]881,清阳侯王吸、广平侯薛欧“以将军击项羽”[1]883,886。通常是指刘邦阵营的将军。有以兵种为称者,如颍阴侯灌婴“以车骑将军属淮阴”[1]895,任侯张越亦“为车骑将军”[1]919。有以作战方式为称者,如阳夏侯陈豨“以游击将军别定代”[1]902。还有不少以国为称者,如栒侯温疥“以燕将军汉王四年从曹咎军”[1]937,武原侯卫胠“以梁将军初从击韩信、陈豨、黥布”[1]937。“河南将军”显然并非属汉的将军,亦非以兵种或作战方式为称,只能理解为当时常见的以国为称的将军。河南将军应视为从属于河南王的将军,而楚汉之际的河南王无他,唯申阳一人而已。如果这个认识能够成立,那么,号称“河南将军”者站在刘邦对立面的由来大致可推测如下:申阳与魏王、翟王等一同参与了彭城之役,彭城败绩之后,河南王如其他诸侯一样,见风使舵,选择背弃刘邦,而其部将大概是受此影响,亦随主复叛。[注]《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汉二年冬十月,“河南王申阳降”。杨树达按:“据《项籍传》,阳本张耳嬖臣,此盖因耳已降汉,故亦降也。他日三秦王复叛,阳始终助汉,盖亦以此。”(杨树达《汉书窥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杨先生所谓“阳始终助汉”,不知何据。
以上推论虽然还不能确切证明河南王申阳参加了彭城之役,但他参与其中的可能性不容忽略。除此之外,以情理而论,河南王也有必要参与彭城之战。《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记载,高皇帝二年“春,定塞、翟、魏、河南、韩、殷国”[1]1119。同书《淮阴侯列传》:“汉二年,出关,收魏、河南、韩、殷王皆降。”[1]2613其中都说到,刘邦出关中不久,河南王即已同魏、殷、韩陆续归汉。若如辛先生之说,关东地区的殷、魏、韩诸王皆附从刘邦伐楚,其中并无河南王。那也就意味着,关东的归降诸王之中,唯独河南王不参与此事,这是令人费解的。因为,河南王申阳是向刘邦投降的,他并没有被处死,在这种情形下,他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不参与彭城之战。反过来想,其他降者皆参与其事,如果只有他一家置身事外,对于一个降者而言,结局会怎样?这并不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综合来看,笔者认为,河南王申阳应当也参与了彭城之战。在此认识基础上,河南王申阳也应当是五诸侯的候选人之一。
三、政治道义与河南王、韩王的取舍
由于韩王信、河南王申阳皆参与了彭城之战,如果仅仅依照辛先生的标准,那么,“五诸侯”将成为“六诸侯”,扞格难通之处显而易见。当然,这并不是说辛先生的标准不合理,只是不够充分而已,需要在原有的标准之上再引入其他的参考项,方能将“六诸侯”还原为“五诸侯”。
前已言及,《史记·高祖本纪》在叙述彭城之战时,用了一个感情色彩极为鲜明的说法,叫作“劫五诸侯”。“劫”,《说文》曰:“人欲去,以力胁止曰‘劫’。”[9]701既然五诸侯是被劫的,那些自愿跟随刘邦的诸侯就不能算在五诸侯之列。根据这一标准,洪颐煊指出:“韩本属汉,不得云‘劫’。”[10]68此说甚是。
跟随刘邦直捣彭城的韩王信,原本并非韩王。《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项籍之封诸王皆就国,韩王成以不从无功,不遣就国,更以为列侯。及闻汉遣韩信略韩地,乃令故项籍游吴时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汉二年,韩信略定韩十余城。汉王乃至河南,韩信急击韩王昌阳城。昌降,汉王乃立韩信为韩王,常将韩兵从。[1]2632
梳理这段记载,可以知道,很短的时间内,韩王换了三任。这里特别提请注意的是,韩王信堪称刘邦的盟友,并且立他为王的正是刘邦。在这种情况下,韩王信跟随刘邦攻打彭城,当然是自愿前往,不存在被“劫”的问题。
以上是从特定语境来判定韩国不当列入五诸侯。另外,洪颐煊还通过史籍所用的特定地域称谓,断定河南王应在五诸侯之列。刘邦在东进彭城之前,曾为义帝发丧,并派出使者告诸侯曰:
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1]370
其中所谓“关内”“三河”,洪氏曰:“‘关中’(即关内)谓塞、翟,‘三河’谓魏、殷、河南,此所谓‘五诸侯’也。”[10]67-68汉代的“三河”是指河东、河内、河南,被项羽封在河东的是魏王魏豹,封在河内的是殷王司马卬,二诸侯之兵既为刘邦所收,那就不能独缺河南王申阳的兵力,否则就是“二河士”,而不能称之为“三河士”。
洪颐煊认为“三河士”必然包括河南王的兵力,这大体上是可信的。不过,他的看法也不是毫无瑕疵。毕竟,关内、三河作为地域称谓,其地理疆界并不是像行政区划那样明确的。具体就“河南”称谓而言,战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广狭程度不等的多种用法,广义上的“河南”是可以将韩地(约略相当于后来的颍川郡)包括在内的。[11]28-39因此,“收三河士”的说法,虽然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河南王申阳也参与了彭城之战,但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将韩王信排除在外。尽管如此,洪氏弃韩,而将河南王申阳列为五诸侯之一,这个看法仍然是正确的。只不过,他在做出选择时,弃与择各有其解说,未能按照同一个标准做出比较,这是洪说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注]周寿昌曰“洪说是也”,但未作具体申述。〔周寿昌《汉书注校补》,收入徐蜀编《两汉书订补文献汇编》(第一册),第569页〕王荣商曰:“洪说得之。时雍王被围,常山无兵,韩王信本属汉,不得云‘劫’。齐方与楚相拒荥阳(按,《史记·项羽本纪》:田氏‘反城阳。项羽因留,连战未能下’。‘荥阳’似为‘城阳’之误),燕及衡山从军,不见纪传。赵虽以兵从,其王歇亦未至彭城。诸家之说皆未允也。”〔王荣商《汉书补注》,收入徐蜀编《两汉书订补文献汇编》(第一册),第996页。〕王氏运用排除法,来确定五诸侯,固然可行,然而,这个思路的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对某种政治势力何以被列入五诸侯的正面论述。李慈铭曰:“折衷而言,洪说为近。既贯上文,又符‘劫’义也。”(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68页。)所谓“贯上文”,指洪氏据“三河”称谓而断定五诸侯有河南王。所谓“符‘劫’义”,指洪氏根据“劫”字的意涵而将韩王信排除在五诸侯之外。这便是笔者此处所言的在做出判断时缺乏同一标准,“弃与择各有其解说”。
司马迁、班固在记录彭城之战时,都突出一个“劫”字。刘邦为何要“劫”五诸侯?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好回答,无非是为了充实兵力,壮大实力。然而,从更深层次来讲,诸侯实际不愿前往,而刘邦偏要胁迫他们附从伐楚,此举显然是为了营造己方得道多助的正义形象。这一点,结合刘邦伐楚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可以获得更真切的认识。《汉书·高帝纪》记载,当刘邦还定三秦东抵洛阳后,老者董公遮说汉王曰:
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之诸侯,为此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2]34
老者一席话,令刘邦茅塞顿开。随后,为义帝发丧,“发使者告诸侯”等一系列举措相继展开。由此可见,在彭城之战前,刘邦为了使自己师出有名,在政治宣传方面做足了功夫。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考量,所谓“劫五诸侯”,实际上也是树立政治道义的一个步骤。表面上看,史家用一个“劫”字,将刘邦此举在道德上的负面色彩揭示了出来,如果站在刘邦的立场上来看问题,那么,他胁迫五诸侯附从伐楚,而不是简单地将五诸侯悉数消灭,其塑造得道多助政治形象的强烈期许便不难理解。也就是说,刘邦事实上是以一种不道德的手段来增进自身伐楚行为在政治道德方面的合理性。明确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只需比较一番,看一看韩王信与河南王申阳,究竟哪个更有助于提升刘邦的政治道义。这个问题清楚了,二者之中哪一个应该列入五诸侯,也便迎刃而解。
说到政治道义的提升,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谈论政治宣传的有效性问题。对于刘邦而言,诸侯权力是来自于刘邦自己,抑或来自于项羽,这是他在选择五诸侯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如果是他自己所封,虽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营造己方的正义性,但与那些由项羽所封的诸侯相较,毫无疑问,后者来归的有效度更高。
前面已经指出,韩国国王原本是项羽所封的郑昌,郑昌被击败后,刘邦“乃立韩信为韩王”,说明韩王信的权力源自刘邦。而河南王申阳的来历,据《史记·项羽本纪》:“瑕丘申阳者,张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故立申阳为河南王,都雒阳。”[1]316可见,河南王申阳的权力来自于项羽。两者相较,河南王申阳作为一个由项羽所封的诸侯,最后却顺从了刘邦,显然比刘邦自己所封的韩王信更有利于营造刘氏伐楚的正当性。因此,附从刘邦的五诸侯,应当列入河南王申阳,韩王信不当列入。
单就政治宣传的效力而言,韩王郑昌既然是项羽所封,当他被韩王信击降后,刘邦将其列入五诸侯,也是符合条件的。但是,据《史记》卷九三《韩信卢绾列传》的说法,郑昌是因受到韩王信“急击”,方才归降。比较而言,塞、翟、魏、殷、河南五王投降时,均未见类似于“急击”的记载,望风而降的可能性很大。望风而降与战败而降,前者显然更便利于用来进行政治道义的宣传。因此,韩王郑昌不应当列入五诸侯。
唐人司马贞亦不同意将韩王郑昌列入五诸侯,但他的理由是:“韩王郑昌拒汉,汉使韩信击破之,则是韩兵不下而已破散也”。[1]322意谓郑昌无兵,不可能参与彭城之战,自然也就不能居于五诸侯之列。笔者认为,有兵无兵以及兵多兵少,并不是判断是否五诸侯的关键因素。项羽所封诸侯即便被剥夺了兵权,只要他望风而降,并亲身跟随刘邦前往彭城,在政治道义的宣传上即可达成功效,将之列于五诸侯便无大碍。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判断哪些政治势力居于五诸侯之列,应当坚持两个层次的标准:第一个层次如辛德勇先生所言,要看诸侯是否参与了彭城之战,通过排除法,将塞、翟、魏、殷、韩、河南作为五诸侯的候选项。第二个层次则是要看诸侯的权力来源,由于塞、翟、魏、殷、河南皆为项羽所封,能够更有效地提升刘邦伐楚的政治道义,因此应当被确定为五诸侯。而韩王信是刘邦所封,政治宣传的有效度较低,故而应摒弃于五诸侯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