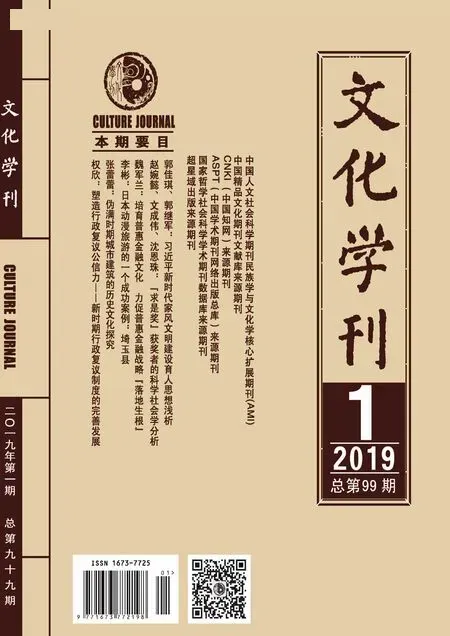中国古代之社与日本神社的原初形态和功能相似性
——以韩国济州岛的堂为媒介
刘 燕
“社”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核心概念,日本的神社虽然与中国的“社”字相通,但目前并无证据证明两者早期存在必然关联,况且神社的称呼也仅仅是明治时代统一的结果,明治以来日本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也使得一部分神社承载了更多的政治功能,部分脱离了其原初形态和功能。但“社”字在八世纪成书的和歌集《万叶集》及《日本书纪》等书中已经用来指代祭祀场所,日本自古以来的祭祀场所很多都称作“社”,这说明两者间至少有一定的相似性才会产生文字上的附会。已有日本学者指出神社的原初形态与日本本土以外的文化具有类同性,如鸟越宪三郎认为韩国济州岛的堂与日本古代的信仰是相同的。[1]冈谷公二遍访济州诸岛,并对日本本土内的诸多大陆系和半岛系神社进行了实地考察,进一步推进了堂与神社两者的关系。中国古籍中记载的有关社的形态和功能的描述与两位学者考察的堂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如果以堂为媒介,原始神社当与社有共通性。本文试图探讨这种共通性,并以历史和地理资料为脉络梳理社与神社之间产生关联性的可能。
一、堂﹑原始神社和中国古代社的形态
所谓“堂”,是普遍存在于济州岛各村落的圣地,供奉的一般是一村一地的保护神。根据冈谷公二的调查[2],济州岛的堂主要具有以下形态:位于树林的空地中;基本没有堂舍;受祭祀的往往是一棵大树,海边则以巨大的岩石或立状的岩石作为祭祀对象。
日本现在的神社境内一般都具有本殿、拜殿﹑鸟居﹑狛犬及位于拜殿外的赛钱口等人工标志。本殿是神明所在的殿,但并没有用以祭拜的神像,这是因为神道认为神本身就在神社,因此本殿中只安放神明的宿体——御神体,可以是剑﹑镜等物品,也可以是山﹑树木﹑岩石等自然物质。自然,后者的情况无法建造社殿,原始的神社并不具有社殿。据鎌田純一的《神道概说》,在有社殿的神社出现之前,有「カンナビ(神奈備)」「神籬」「磐境」「磐座」等古代祭祀场所。「カンナビ」是“神隐﹑神在之神圣之所”之意,「神籬」被认为是神灵降临时的以及包括树的整个祭祀场所,而「磐境」「磐座」则指以岩石环绕或以自然岩石为祭祀场所的圣域。[3]据《万叶神事语辞典》,在八世纪成书的诗集《万叶集》中指代“神之居所”及“祭神场所”的“社”及“杜”字,读音为“森(もり)”,《万叶集》中的“社”字也读作「やしろ」,从语源考虑即“屋代”,这时的祭祀场所可能出现了临时建筑。[4]神社中出现社殿等建筑物一般认为是佛教传入后的公元六七世纪以后。《日本书纪》中记载天武十年(681)国家发布了社殿营造令,但事实上,包括春日大社这样的数一数二的大社,在八世纪中期还是仅仅“被树林包围的方形神地”。[5]即使在现在的日本,很多神社的本殿都很小,参拜者也很少能够目睹。不设社殿的神社至今也有很多,最著名的是祭祀曾出现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神话中三轮明神的大神神社,以奈良的三轮山的整个山体作为神体,被认为是古代神道的残留,此神社的山顶有被巨石环绕称为奥津磐座的圣境,在其最深处有被视为神座的巨石。祭祀日本最高神也是皇祖神天照大御神和农耕神丰受大神的伊势神宫,每二十年会把神宫拆毁重建,称为“式年迁宫”,“式年迁宫”的新殿址处会立一根称为“心之御柱”的木柱,正殿建于其上,下次迁宫时,柱上的建筑被拆除,但御柱仍会得以保留。从这一传统可以看出,社殿在以前并非是常设的建筑。此外,由于御柱并不和其上的建筑有接合处,因此可以认为其存在并非出于建筑上的考量,而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在玉石铺地的广场上树立柱子就是神宫的古时形态”。日本的神一般用“柱”这个数量单位来计数,“从这个习惯来考虑,树立柱子来祭神应该在古代广泛进行”。[6]位于日本长野的諏访大社上社四周也有四根与建筑无关的木柱,称为“御柱”,而諏访大社作为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之一,至今没有本殿存在。
丁山指出,“社”之字形“在商代作土,在宗周时作杜,战国以后乃有(左示右上木下土),至秦乃省而为社。史记以社主与杜主互见。”[7]这说明远古社与土、树木的关系向来密切。早在20世纪初,法国汉学家沙畹就根据古籍记载撰文指出社具有社坛(土冢﹑土封)﹑树(树丛﹑圣林)﹑石(社主)等要素,且具有露天的特点。[8]关于社与土,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指出殷卜辞中的“土”即为“社”,“假土为社,疑诸土皆社之假借字”。[9]《诗·大雅·绵》中提到周人“迺立冢土,戎丑攸行”,毛传注:“冢土,大社也”。关于社与树木的记载较多,如《墨子·明鬼下篇》中言:“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丛位。”《吕氏春秋·怀宠篇》言:“问其丛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废者而复兴之,曲加其祀礼。”也有以石为社的记载,《淮南子·齐就俗训》言:“殷人之礼,其社用石。”《吕氏春秋·贵直篇》也提到:“城濮之战,五败荆人,围卫,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此外,《周礼·封人》言:“设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五经通义》提到:“社皆有垣无屋,树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万物,万物莫善于木,故树木也。”据上可知,社有矮墙,却无房屋之类建筑。《礼记·郊特牲》中记载:“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是故丧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也。薄社北牖,使阴明也。”社中的土丘﹑树木﹑石头所起的是沟通天地的作用,只有亡国之社需要加盖房屋遮掩,使其绝通天地之气。
综上所述,堂﹑原始神社以及中国古籍中记载的社具有形态上的类同性,当然这种类同性也许是早期社会发展阶段中具有的比较普遍的宗教信仰的共有形态及残留。那么,这几者之间是否在祭神等方面具有更多的关联性呢?
二、堂﹑原始神社和古代社的祭神
(一)堂与原始神社的祭神
济州岛的堂神可以大致分为四种:山神﹑农耕神﹑海神﹑其他神灵。[10]其中,山神(男)和农耕神(女)一般以夫妇神的形式作为守护本乡的堂神受到祭拜。此外,比较多的是主管治愈儿童病和皮肤病及生育的七日堂神,被认为是农耕神的派生。鸟越宪三郎的考察中则提到济州岛村落共同信仰的堂神是以蛇神为象征的农耕神,在每年播种祈祷丰收时及秋收后表示感谢时祭祀[11],这与中国社祀的春祈秋报是完全一样的。蛇神不但是镇守村落的堂神,在济州岛的各家各户还同样作为农耕神——谷神及财神受到二重祭祀,称为七星堂神。济州岛多蛇,蛇生殖能力极强,蛇会蜕皮,使人们相信它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应该说济州岛的以蛇为象征的农耕神信仰是也是基于生殖崇拜的。冈谷公二所提到的本乡堂的农耕神是女性的人格神,这显然也是基于将农业生产与生育相关联的思想。
关于日本原始神社的祭神,岛根的出云大社11月举行的神在祭只在迎神时才建立临时的建筑,祭祀过程中有迎神和送神的环节,结束后建筑即被拆除,而地主神的圣域则不会拆除,民俗学者谷川健一据此认为圣域最早祭祀的当为地主神,神在祭的送神是为了不让原本存在的地主之神生气而进行报复。[12]日本也同济州岛一样,有蛇神崇拜,以整座山为神殿的奈良的三轮山大神神社所祭之神大物主大神的本体就是蛇神。据《日本书记》(720)记载,大物主大神与妻子倭迹迹日百袭姬命每日夜里相会,妻子要求看他面容,他告知白天会躲在她放梳子的箱子里,天亮后妻子打开箱子一看竟然是条美丽的蛇,因而受到惊吓,大物主大神则化作人形飞回山中。大神神社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之一,大物主大神是稻作丰产﹑酿酒﹑除疫病之神。以蛇为本体﹑男女夜间相会﹑怀孕等神话,说明其农神的性格和生殖观念是相连的。由于日本有文字记载的文献出现较晚(八世纪),因此神社何时产生目前并无定论,但一般认为神社的产生与稻作文化及铁器的传来相关,这个时间大致可以定位在绳文时代的晚期及弥生时代(公元前4—3世纪)。日本现在的一些神社的农耕祭礼仍然保留着生殖崇拜的要素,位于爱知县小牧市的田县神社及犬山市的大县神社都是日本相当古老的神社之一,据社传,大县神社在公元前3年就已由别处移至现处。[13]田县神社供奉着众多的木质男根,在每年3月15日为祈祷五谷丰登和子孙繁荣而举行的“丰年祭”上,男人们扛着装着巨大男根的神轿,巫女们则抱着小些的男根沿街行走。[14]大县神社供奉和在丰年祭上展示的则是女阴。中国学者胡稹也曾指出日本奈良县飞鸟神社的“田植祭”﹑六县神社的“分娩祭”﹑茨城县的“御舟祭”等与农耕相关的祭祀礼仪分别有模仿男女交媾、模仿女性怀孕生产、吊挂稻草制成的男女性器官的环节,认为这些祭礼“反映出与中国‘社’相似的发展历程:先是人自身的生殖崇拜,随着农业的出现,生殖崇拜逐渐与期盼丰收有机联系起来,直至后来发展到直接为农事服务。”[15]
(二)中国古代社的祭神和演变
根据考古资料的显示,距今4000~5 000年前的良渚文化遗址的祭坛和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的东山嘴遗址都具有后世文献记载的社的形态,陈剩勇认为良渚文化祭坛立于山顶,封三色土为祭坛,祭坛露天,四周为树林及面向稻田、田野等特点与三代之“社”关系密切,与先民的土地崇拜有关,是三代之社“封土为社”的社祀礼典的前身。[16]东山嘴祭坛北侧有方坛﹑南侧有圆坛,方坛内立有数个石柱,有矮石垣,圆坛附近有鼓腹丰臀的裸体女像等,田广林认为该祭坛与商周时的社形态相似,反映了天圆地方的观念,是后世北郊祭天、南郊祭地的源头。方坛内的石头表示地神的社主,坐于圆坛上的女偶则代表了天神和祖神的合体。[17]《论语·八佾》中虽有“夏后氏以松”为社,但关于夏社的记载却很少。至殷商时期,甲骨卜辞有“贞,又燎于毫土”(《佚存》)的记载,毫为殷商之称,土如王国维所言是社的假借字,“天神在上,非燔柴不足以达之”(《礼记·郊特牲》),“贞,勿求年于邦土”(《前编》)等表述说明商社既祭祀天神,也祭祀地神。[18]关于周社的记载较多,从前文所引“冢土”等记载来看,周社的确与土地的崇拜密不可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农业的发展和土地面积的开发,社与稷开始合并祭祀,并且开始出现民间社祀——以先秦最基本的行政单位为基础的里社。[19]秦汉时期,社祀日益大众化、世俗化,“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谷丰熟;秋祭社以百谷丰稔,所以报功”(《周礼·地官·州长》),社神是春祈秋报对象的土地神和农耕神,此外,为了消灾病、男女相爱、子孙繁衍,人们都会求于社神。[20]
《国语·鲁语上·展禽论祀爰居》中言:“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甲骨文和金文的“后”字象征母亲生子,由此,丁山认为地神为后土“当然是从生殖神话演来,其原始的神性都应属于妇女。”[21]何新认为甲骨文的土字如同乳房之形,而古代汉语中“土”与“母”同音同义,与“高禖神”的“禖”也同音,因此,土神就是地母神和高禖神。他还据《周礼·地官》中“媒氏……以仲春之月,会合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等记载,认为古时春社就是男女一时的交合场所,社中石或土代表女性,而树木则代表男根。[22]大地的生产如同人类的繁殖一样,多产即意味着繁盛,对于古代人类而言,两者都具有神圣性,因此,社同时具有土地崇拜、地母神崇拜﹑生殖崇拜的功能并不奇怪。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社﹑济州岛的堂和原始神社似乎在功能上都具有祭祀土地神和由土地神派生的农耕神,而这种祭祀往往与生殖崇拜密切相关,显示了农耕文化的特色。
三、社与神社在历史与地理方面发生关联的可能性
成书于西汉初年的《尚书大传》中记载了商人后代箕子建立箕子朝鲜的事迹:“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描述了战国末年进入朝鲜的移民,“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西汉初年,燕人卫满消灭了箕子王朝,建立了卫满朝鲜。汉武帝时期,中国征服了以平壤为中心的卫氏朝鲜国,设立了乐浪郡等四郡,当时大陆移民和文化的流入可想而知。
济州岛位于朝鲜半岛以南,在古代朝鲜半岛中南部地区,有古辰国。据《三国志·东夷传》记载:“韩在带方之南,东西以海为限,南与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辰韩者,古之辰国也。”而据《后汉书·东夷列传》:“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辰。马韩在西,有五十四国,其北与乐浪,南与倭接,辰韩在东,十有二国,其北与濊貊接。弁辰在辰韩之南,亦十有二国,其南亦与倭接。凡七十八国……皆古之辰国也。”从以上表述来看,三韩似乎是由古辰国分化而来,三韩在不但地理上与倭非常接近,与中国的关系也很密切。从《三国志·魏书》和《后汉书·东夷列传》的记载:“辰韩者,古之辰国也,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郡,弓为弧、贼为寇,有似秦语,故或名之秦韩”可以得知,辰韩本就是秦人建立的国家,辰韩还善于制造铁器,“国出铁,濊、倭、马韩并从市之。凡诸贸易,皆以铁为货”。三韩在西汉及之后也与中国关系密切,《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曾提到:“桓、灵之末,韩濊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可以说,从战国末年到秦汉之际,中日韩之间以朝鲜半岛为中介有着频繁的移民和文化贸易交流。这一时期基本上相当于日本的绳文时代晚期和弥生时代,在这一时期日本列岛出现了以稻作和铁器为特征的﹑完全不同于之前的绳文文化的农耕文化,有理由表明,弥生文化是由携带稻作文化和铁器文化的外部移民在进入日本列岛后产生的。
鸟越宪三郎走遍中国西南腹地和东南亚进行实地调查,划出一条倭人分布图。他指出携带稻作文化进入日本的弥生人就是倭人,倭人和稻作文化源于中国云南省,以高床式建筑(床指地板,地板高出地面许多,用梯子上下出入)﹑断发﹑文身﹑穿贯头衣等习俗为标志。古时倭人的一部分沿长江东下,在长江中下游定居。后来,吴国被越国打败,很多倭人及其子孙为了逃避战乱,经山东半岛和东北地区进入朝鲜半岛,然后又有一部分进入日本列岛。[23]倭人的习俗及自长江下游地区的来历在古籍中也可窥得一斑。记载日本最早的文献是陈寿所著《魏志·倭人传》,其中记载魏时日本列岛上的倭人,男子“悉鲸面文身”,女子穿“贯头衣”,“自谓太伯之后,又言上古使诣中国,皆自称大夫。昔夏少康之子封于会稽,继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人好沈没取鱼,亦文身以厌水禽”。而《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言吴国的建国者是周太王的儿子太伯,因为继承问题与弟弟避至荆蛮之地,并随俗“文身断发”。而《后汉书》中提到马韩“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弁韩“其国近倭,故颇有文身者”。
以上记载和习俗的相似都表明倭人与中国和朝鲜半岛尤其是南部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社与产生于弥生时代的神社在文化的源流上具有相通性的可能性很高。当然,这一结论还需要更多的实地调查及结合考古资料进行进一步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