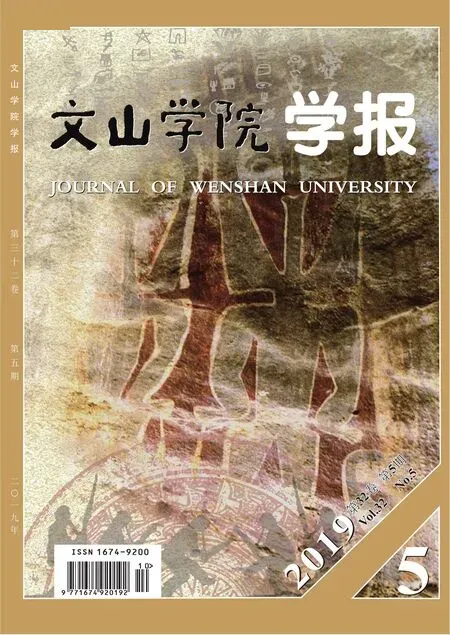从“大一统”到“正统”:《史记》《汉书》民族传比较视野中“华夷观”的历史衍变与嬗代整合
杨泽宇,成海燕
(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史记》和《汉书》的比较探讨一直是学界老生常谈的话题,目前以民族列传为参考文本的对照研究,在文学和史学领域均有所涉猎,且成果显著。刘泽群的《〈史记〉〈汉书〉民族传记文学探究》[1]一文,从民族传的内涵、文艺形象和文学价值三个方面作出文学角度的解析;而在史学上亦有从史料学、思想史等方面着手的著述,如:王鹏《〈史记〉〈汉书〉民族史料比较研究》[2]总结出《汉书》在承继《史记》相关史料的基础上亦有所补足、修正和完善;朱凤相《〈史记〉〈汉书〉景帝至武帝间年表中民族史料考异与订误》[3]则发现《史记》和《汉书》民族传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存有部分舛互之处,并进行了史料考索;郎华芳《〈史记〉〈汉书〉民族史的撰述及意义》[4]认为两书民族列传为后世研究汉代边境的少数民族历史提供了权威资料;夏民程《新中国〈史记〉〈汉书〉民族思想比较研究综述》[5]总结了新中国以来白寿彝、张大可等在史汉比较研究中所做的贡献,并从民族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对前辈学者民族思想加以分类介绍与诠释;王静《司马迁与班固民族思想比较研究》[6]以儒家思想作为史家民族观形成的共同理论基础,并以此述明班固、司马迁民族思想对后世统治者制定治边政策的影响。从上述的研究来看,《史记》与《汉书》民族列传比较研究涉及视野虽广,但从个人际遇所形成的治学倾向与研究侧重探究两部史学巨著在“华夷观”上的差异,并通过嬗代之际“大一统”到“正统”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型中,廓清从《史记》“同源共祖”到《汉书》“种别域殊”的逻辑联系却略显单薄。笔者浅见,对《史记》《汉书》汉民族列传作进一步的比较研究似乎很有必要,从“华夷观”衍变之中解读史家秉持史观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基础或意涵,于西汉民族史研究而言,不仅可以尽力摆脱历史事实探寻中“历史”①无奈且尴尬的困顿,亦是一种有益于复原历史语境甚至重返历史现场的探索与尝试。
一、“同源共祖”:“大一统”趋势中《史记》的华夷共处观
《史记》拓创新域,首创包括《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在内的民族传,将汉王朝周边的少数民族纳入中原王朝历史书写的体系之中,成为研究先秦至秦汉民族历史最基础的文献。从诸民族列传的字里行间不难发现,司马迁秉持的“华夷观”是在武帝时期“大一统”模式下被儒家知识分子所广泛接纳的诸民族“同源共祖”的调和共处和相对平等意识,一定程度上挣脱了先秦以来视别族为异类的“外夷狄”视野,为从史学眼光诠释汉王朝天下一统的政治格局奠定了思想基础,成为当时思想界的共识。
(一)相对的“平等”:从“外夷狄”到“大一统”
司马迁所生活的年代,西汉王朝刚走出“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步入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司马迁看来,不仅要思想统一,更要实际上的“大一统”。
《史记》的“大一统”首先是文化上的“大一统”,司马迁继承董仲舒的“一统观”,认为只有在文化上趋于融洽,才能在和平的前提下达到政权的一统。如在《匈奴列传》中涉及匈奴习俗、文化时,司马迁便认为不同民族生活习性的差异有其形成的深层次根源,无论进步与否,都不应该轻视,其他民族也不应该将自己的习惯、思维强加于他族。“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7]3483
但是《史记》民族传中的“大一统”并不是当前意义上的民族平等,而是一种简单、机械的以汉民族为主导的民族罗列和相对平等主义。司马迁认为,周边少数民族与汉族统一要采取向汉族臣服的方式,就如同儒家的核心礼法等级观念一样,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如庶子与嫡子之别,尊卑高下远近亲疏是要有明确区分的,司马迁的这种相对平等的“华夷观”,于当时时代发展而言,无疑是很必要的,但用今天的批判思维来看,这也使得西汉王朝及之后的政权自始至终都将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摆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不能用平等的观念来看待,自然而然在后来边疆民族治理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二)四海如一家:从“华夷有别”到“同源共祖”
《史记》在承认汉室正统和“大一统”的前提下,认为每个民族都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在华夏中心论的视野中,民族叙述应该强调以统一王朝为主线,将各民族统一纳入以华夏族为主的中原王朝中加以考察,而这种研究方式首先要处理的就是“华”与“夷”的起源关系。
在《史记》中,司马迁清晰表达了华夏民族与少数民族均是炎黄子孙的观点。《五帝本纪》言明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之间的传承关系,认为后四帝与黄帝血统一致,为之后代。在夏商周本纪中列举了创夏者禹、建商者契、周始祖后稷均为五帝后人,如《夏本纪》说“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7]63;《殷本纪》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7]119。在记载公卿王侯的诸世家和民族传中,也论及西周分封制下诸侯王以及周边诸民族也都是黄帝后辈所建。
如《越王勾践世家》记“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7]2087。《楚世家》中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7]2027。《吴太伯世家》中说“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7]1773。可见南方诸蛮中的吴、越、楚在创建之始均与黄帝为首的华夏部落颇有渊源。
《匈奴列传》中就记载匈奴是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匈奴,其先祖夏后世之苗裔也,曰淳维”[7]3461,而夏后帝是少康庶子,这也就向大家表明,匈奴与汉族的关系是同宗同源。《朝鲜列传》也载“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7]3593;《南越列传》记“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7]3569也都力图阐明“夷”出自于“华”、“华”为“夷”祖和四海一家的民族起源观。
司马迁作为历史上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的人物,其所用的资料多取自民间传说和先秦典籍,一定程度上讲,不如后世史书所参考的史料丰富,准确度和真实性也有值得推敲之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司马迁这种华夷同源、共处的观点,在多民族“大一统”的西汉王朝是值得肯定的,这为其后民族融合和国家“大一统”都提供了思想上的根据。
二、“种别域殊”:“正统”论中《汉书》的治夷、变夷观
《汉书》中的民族列传虽在《史记》史料和体例的基础上继往开来,但班固的“华夷观”却在继承司马迁“华夷共处”模式中发生着向以“扬汉”为目的“治夷、贬夷和变夷”的嬗变,以汉为天下之主,四方民族为汉朝之附庸、臣服于汉的民族认识较之《史记》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显得更为极端。而这种过度美誉中原汉室王朝的思想不仅来自班氏家族因世受皇恩而唯汉命事从的心态,更多的则是源于两汉嬗代之际“正统论”逐渐成为当时读书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以及“正统”政治语境下儒学“华夷观念”由“大一统”向“尊汉抑夷”的蜕变。
(一)“文野”与“纯杂”:“域殊”、“文殊”即“种别”
“种别域殊”语出《汉书·叙传》“西南外夷,种别域殊”[8]3085。字面理解“域殊”即是地域不同,但班固借此一词,不仅强调不同民族在地缘上的远近差异,文化上亦有文野之分,血缘上更有纯杂之别。
如《匈奴传》中将匈奴与汉族的生活习俗、生产模式加以比较,认为匈奴文化落后、习性野蛮,称之为“禽兽”,可见大汉族主义史观下的民族歧视和种族差别。
“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8]2752
《西域传》同样带有鄙薄之意,刻意夸大西域民族与汉族的文化差距。
“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旎,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唯其小邑鄯善、车师,界迫匈奴,尚为所拘。而其大国莎车、于阗之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
(二)“治夷”与“变夷”:王制之下的差序格局和怀柔政策
“差序格局”源自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以亲疏、远近为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本土化特点,并强调以“己”为中心的社会学概念,而在古代中国传统王朝政治体系下中原对边疆民族的认识、管辖和治理也存在根据“血缘、地缘、经济水平、政治地位和知识文化水平”来划分亲疏关系的“差序”模式,在这种人际格局,或者说是民族关系之中,中原政权一切价值都以“华夏”作为中心而自我标榜和他者贬抑,尤其在人治色彩较浓的汉代社会,维持所谓华夷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并非法律,更多的是自先秦肇始“驱夷”的历史传统和秦汉以降传统社会中以“羁縻”“怀柔”和“教化”为民族关系模式的制度安排和权利运作。笔者认为差序格局可以使用于对传统社会中治夷、变夷政策的观察,是因为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族群关系,或是民族关系,无外乎都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差异亦有,相似亦有,共通之处就在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带有流动性的人际交往,以及以集体意识为基础凝聚而成的族群认同,而对于修史者来说,更多的是个人根据时代意识的评判标准书写被时代所需、被统治者所用的“历史”。《汉书》民族列传即是在两汉嬗代之际儒家由“大一统”衍变而来的“正统”意识形态中根据血缘、地缘、经济水平、政治地位和知识文化水平区别出“亲夏”与“疏狄”的差序格局的,从前文叙述班固在民族传中对一些少数民族轻视言辞即可显露出其“以夏为峰,傲视诸夷”的以“己”为中心的睥睨姿态。
所以在班固看来,汉族对周边少数民族当采取“招携以礼,怀远以德”的怀柔态度,在文化上用“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儒家思想教化之;在政治上用“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8]2752的羁縻政策管辖,而这种区别于司马迁“四海一家”的狭隘民族观,多半源自班固在大一统管理下对国家的信任以及因汉族的经济优势衍生出极度的文化自信。
《汉书》详细记述了少数民族生产与生活方式及其统一于汉朝中央的过程,经历文景之治、武帝大一统、昭宣中兴近百年繁荣强盛的西汉王朝,汉族人民有了不同于以往强烈的民族自信意识和华夏一统观念,西汉一朝,不仅在史实上给了班固很大的发挥空间,更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就班固个人来讲,班固一家,世世代代都是汉朝大臣,他自己从幼年起就读儒家经典,尊信儒学,这样班固自然就将“华夷之别”更加放大了,司马迁的华夷观念是潜意识里的,只可意会而不言传,而到了班固这里,就毫不掩饰的去表达对少数民族的轻蔑。
当然,我们从班固的身世、历史阶级和时代局限性来说,这倒也无可厚非。《汉书》曾对匈奴人的饮食、语言、生活习俗进行了描述,就把匈奴人比作“兽”,毫不掩饰民族轻视,在《汉书·西域传》里,班固就曾说“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8]2825。
三、从“大一统”到“正统”:多维视角中《史记》《汉书》“华夷观”的比较研究
在从“大一统”到“正统”的政治语境嬗变中解释《史记》《汉书》在易代之际“华夷观”的衍变规律与逻辑联系,目前学界虽有研究但未成定论。在笔者看来,《史记》之“华夷共处观”虽难舍大汉族主义色彩,但主要以适应大一统环境的民族调和为基调,显得朴素真实;《汉书》民族列传虽涵纳史料较《史记》丰富,但其以“治夷、变夷”为手段的华夷关系模式,却过于宣扬汉室国威,贬低周边民族,其取悦汉室的撰写心态和虚美尊汉、以彰汉德的观念也是班固撰史常被后世诟病之处。现从编撰体例、战和态度和民族地位三方面进行解读,以求阐明两汉历经百年辗转中两位杰出史家“华夷观”的历史衍变与嬗代整合。
(一)从“独立”到“从属”:以编撰体例为参考的布局侧重
在编排方式上,《史记》把与少数民族相关联的人和事联系起来,将各民族传穿插安排在与之相关的名臣将相列传之间。这种编撰体例的安排,一方面可以在史料并不充裕的情况下,集中将与某一民族相关的人、事、物并列作为参考依据,看似混乱重复,却能有效的把该民族信息进行传达,读者阅读时对一族历史之疑问亦可参顾他篇,以便加深理解与认知。另一方面,从司马迁的“华夷观”解阅,笔者认为这是在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相对平等理解基础上的一种有意安排。如:《匈奴列传》在《史记》中编排为一百一十卷,前篇一百零九卷为记载抗匈名将李广的《李将军列传》,后篇一百一十一为记录骠骑将军卫青远征匈奴的《卫将军骠骑列传》。再如第一百一十六卷《西南夷列传》,其后便是出使西南夷的司马相如之传。这种安排不仅没有把少数民族看成是与汉王室对峙的异族,同时看重民族间融合、和谐的关系,有益于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
而在《汉书》中班固将民族传集中安排全书最后,从格式上来说,在末端专讲民族,体例布局和目录编篡会显得整齐;但从“华夷”视角分析,班固刻意将匈奴、西域、西南夷等少数民族的历史书写区别于汉族对待,其实质是一种“华夷有别”狭隘民族意识和“内夏外夷、尊汉贬夷”民族对峙思想的文本体现。相比于《史记》的编排体例,《汉书》第九十四卷是《匈奴传》,与匈奴相关的汉室臣将李广、卫青、霍去病传则分别安排在第五十四卷《李广苏建传》、第五十五卷《卫青霍去病传》;再如第九十五卷是《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而《司马相如传》则安排在第五十七卷。这种排序虽未明言歧视,但似乎有种把少数民族当作汉族附庸、将汉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对立开来的感觉。
(二)“以和为贵”与“一战永逸”:以和亲政策为中心的战和衡量
西汉王朝作为汉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时期,无论是汉族疆域的扩张还是中原文化的辐射,在与周边少数民族接触、混合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摩擦,这种摩擦即是从中原到边疆,汉王朝扩展疆域、传播文化的需要,也是从边疆到中原,少数民族对汉族先进文化、优厚物质环境的渴望。因此当汉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需求在一定平衡区间内,边境局势就相对和平;而当双方的这种需求不断扩大以至于打破平衡之时,民族间的战火便会燃起,双方又要重新寻找新的空间来调适彼此的需求才能恢复和谐。而就当时的民族关系来看,无论汉、胡政权哪一方得势,新的调整空间也多数以汉嫁公主的和亲形式为考量。基于此,我们不妨从和亲的视野分析班固、司马迁的民族战和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高度赞扬和亲政策。对司马迁而言,虽身处西汉鼎盛之世,但汉初凋敝的社会经济情况尚距离不远。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7]1703,国家无力承担大规模的兵事征伐,高祖被困平城便是在脱离社会人力、物力的情况下仓促用兵的结果。所以高祖平城解围后,惠帝、吕后、文帝、景帝至武帝初年对北方匈奴的基本政策均为和亲,对南方的两越和西南夷也不采用武力征服,多是以“安抚”“怀柔”的政策与之交好。在这种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中,汉与少数民族间的矛盾得以缓和,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促进了中原与边疆民族的交流,所以他在《吕太后本纪》中评论和亲政策时说道:“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7]515
而当汉室强起,武帝南征北伐之际,心怀安定、赞同和平的司马迁则给出了不满之音。《匈奴列传》在评到伐匈奴时:
“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7]3504
由此可看出,他觉得与匈奴主要应该是以防御为主,结使交好,选择人才将相以保证边陲太平。在《大宛列传》中因汉朝欺凌大宛而引起的矛盾,他也客观作评:“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多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转相奉伐宛,凡五十余校尉”[7]3826,以掩盖汉朝贸然挑起战端和失败的事实。由此可见,司马迁更倾向于民族和平交流,强调和平时代下国富民强、各民族的协同发展。
班固虽也主张民族相安无事,但他却认为和亲不但无用,还是一种委屈求全下的一时之策。他在《匈奴传》中论及和亲时说:
“若不置质,空约和亲,是袭孝文既往之悔,而长匈奴无已之诈也。夫边城不选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备塞之具,厉长戟劲弩之械,恃吾所以待边寇。而务赋敛于民,远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仇。信甘言,守空约,而几胡马之不窥,不已过乎。”[7]2751
在他看来,和亲是“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8]2749背景下“约结和亲,贿遗单于”[8]2749的无奈之举。班固“华夷观”的初衷更多的是通过汉族的教化使少数民族臣服和归附,最终达到同化异族的目的。而当他在随军北伐匈奴胜利时,则更倾向于通过战争“一劳尔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9]815,使四海皆服于汉。
(三)“褒汉”必“抑夷”?以华夷地位为视角的叙事姿态
“华夷关系”在中国古代一直是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探讨如何处理与周边民族问题的热点议题,对华夷关系不同解读,不仅是秉持观点者学术渊源、人生阅历的经验反映,同时也是一个时代、一个王朝气度和胸襟的政治呈现。可以说,班固、司马迁民族史观中的华夷概念即是当时环境孕育产物,反过来也催生了那个历史时代下“华夷观”的思考与转型。
司马迁“汉夷共述”的华夷观。首先,他认为“夏”和“夷”之间最大的区别在文化层面,但是他又提出每个民族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中原文化的强势扩张使其在各民族文化交融中保有优势地位,但强迫他族接受本族文化是不应该的。所以,他的观点是民族文化无论进步与落后,都不能成为评判一个民族的唯一标准,尊重文化的多样与独特,顺应文化糅合的自然趋势,这种民族文化观体现出司马迁豁达、包容的民族心态。其次,司马迁虽未能彻底摆脱传统的华夏贵贱尊卑的观点,但从《史记》的目录编排而言,民族传列之于汉族官家臣僚之间,仰夏贬夷的思想较之于先秦有了很大的改观,他的诸族同源说虽未能阐明政治上的民族平等,但是华夷交替叙述的模式却体现了司马迁在学术上对少数民族地位的认可。
相比之下,班固在论述华夷关系时就显得过于“褒华贬夷”。首先是“褒华”,班固始终怀揣维护大汉国威、宣扬汉帝功劳、粉饰汉室恢宏的心态,在撰史上也使他与司马迁相比,多了一份虚美汉室的羁绊、少了一份客观述史的从容。如:《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和《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在记载苏建出战匈奴,兵败归营为免罚而所做解释中,前文道:“力战一日餘,士尽,不敢有二心,自归”[7]3522;后文说:“力战一日余,士皆不敢有二心”[8]1742;前者可以表露苏建一人的赤诚之心,后文便所有士卒的报国之情溢于言表,略动几字,一人之忠变为众人之忠,大汉将士之威和忠贞为国之心更加凸显。同时是《卫将军骠骑列传》和《卫青霍去病传》中记录卫青三伐匈奴之历程,前者道:“遗居延,遂过小月氏,攻祁连山”[7]3526,如实的反映了卫青率军远伐跋山涉水之险阻和艰辛,后篇在记载行军进程之后多补一句“扬武乎鱳得?”[8]1745赞颂大汉军威,彰显伐匈汉军的英勇气势。不难发现在《汉书》对《史记》的一些增补中,通过几字几词的变动,所述意义虽未发生大的变化,但感情色彩已大有不同,述史中若过于夹杂执笔者个人的情感态度,史书的客观性和严谨性便会大大降低。其次是“贬夷”,《汉书》中直接贬低少数民族的言语较多,不仅主观上将少数民族置于中原王朝之下,谩骂、污诋之声也使得少数民族在《汉书》中以罪恶奸邪的形式歪曲存在。如:记载匈奴冒顿单于时期,南征北战,匈奴最为强盛兴起时,《史记》道:“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7]3473《汉书》中称:“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诸夏为敌国,其世姓官号可得而记云”。[8]2687
从“中国”到“诸夏”的文字差别体现了班固“华夷之别”的观念,反映了他并不承认匈奴作为中国一独立政权存在,而是排除在诸夏之外的夷邦,臣服于汉治下的外民,如其在《自序》中道:“百蛮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亦迪斯文,宪章六学,统一圣真”[8]3061,“百蛮是攘”“武功既抗”明显体现出“尊汉攘夷”的民族态度,“统一圣真”“亦迪斯文”则说明班固认为汉文化作为当时最先进的文明,应该担负“以华变夏”,教化蛮夷的民族文化心理。上述可知在班固的华夷视野中,少数民族既无独立于汉族之外的政治地位也无脱离于汉文明的文化地位。
比较《史记》与《汉书》的“华夷观”,不难发现《史记》侧重于民族间的调适和平衡,不赞成用暴力解决民族间存在的矛盾,认同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民族纠纷,但必要时刻也不排除武力解决的可能,而《汉书》更侧重于扬汉族、蔑他族,饰汉室、贬夷狄,一方面强调汉王室在少数民族政权众星捧月的高等地位,一方面通过对《史记》原文的改字、替用和补句达到吹捧汉室、污蔑少数民族的目的。
四、结论与思考
从史学史的角度溯源,以民族列传为范式的少数民族历史叙述模式,首创于《史记》,《汉书》继往开来,整齐体例,为后世正史所沿用,对民族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整理与研究既有拓创新域之功,亦有启蒙后世之效。而从对待所谓“夷族”之态度上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史记》秉持的“华夷观”在西汉“大一统”意识格局之中被当时儒学界共识的诸族“同源共祖”观念基础上融入司马迁的调和与相对平等意识而形成的“华夷共处观”;《汉书》“华夷观”继承《史记》但发生着政治、思想嬗代过程中的衍变与整合,是在美誉中原汉室王朝的东汉“正统”政治语境下以维护大汉国威、宣扬汉帝功劳、粉饰汉室恢宏为目的、“治夷变夷”为手段、“褒汉贬夷”为叙事姿态的“华优、夷劣”观。在经过编撰体例、战和态度和民族地位三方面的详细讨论后,我们明显看到,同是“华夷观”,《史记》和《汉书》不同之处,不仅是史家个人际遇、知识经验形成的治学倾向与研究侧重所致,更重要的是一个时代、一个王朝和一个政权呈现在对待“他、异”概念时呈现的意识、气度、姿态和政治胸襟。
时至今日,我们仍不能凭一家之言将《史记》《汉书》“华夷观”作一致性、一体化的评述,就像当今治民族史的学者也不能以己所需而完全无视时代意识一样。“历史事实”的探求,表现在与社会科学结合的史学研究上,而社会科学既然是强调“社会”,更不能将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置之不理。《史记》和《汉书》民族书写在各自时代意识的立场上让后世了解到先秦两汉时期各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化、饮食诸多细节,其价值异乎寻常,而当今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代中国民族史研究更是应该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环境,通过民族共识和文化自信维系各民族多元统一的格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巩固与铸牢奉献学术上的理论尝试和实践探索。
注释:
① 此处加上引号的“历史”引于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一书,他认为“历史”指人们对历史的记忆与语言、文字表述,是历史事实造成的“现在”,更是历史事实造成部分人掌握社会权力及历史记忆,并以此区别于真实的历史事实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