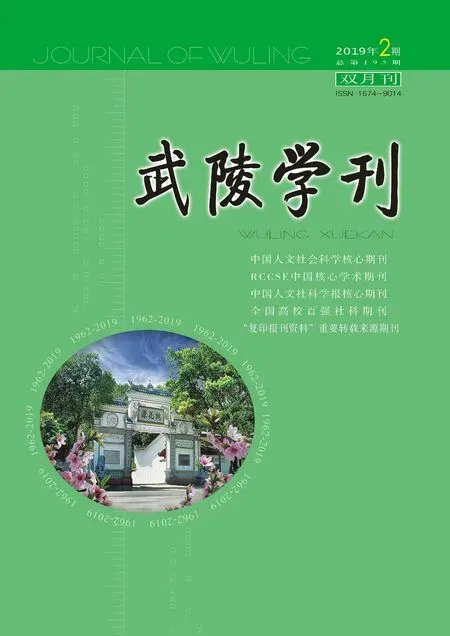异地唱和:群体的认同与巩固
——浅论北宋超然台唱和的群体意义
田 甘,刘向宏
(1.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2.沈阳师范大学 期刊中心,辽宁 沈阳 110034)
从兰亭雅集到西昆酬唱,诗酒唱和、奇文共赏一直是历代文人心仪的风雅乐事,同时也是他们交流切磋、增进感情、巩固群体的一种方式。然而到了北宋中后期,外放贬谪频繁,昔日的群体成员如今天各一方,已不具备同席宴饮的空间可能,那么他们是靠何种方式来维系这个群体的呢?幸而北宋的驿寄制度已经颇为完善,故异地唱和就成为了他们的不二之选。北宋异地唱和次数颇多,像颜乐亭、“千秋岁”这样知名的也不在少数,本文仅选取发生在新旧党争初期的超然台唱和为例,探讨异地唱和的群体意义。
一、群体的表态与认同
熙宁八年(1075),苏轼于密州(今山东诸城)任上修葺所居园北旧台,并以此为契机发起了这次异地唱和。现存作品共有苏轼自作记一篇;苏辙、文同、李清臣、张耒和鲜于侁赋各一篇;文彦博、司马光寄题诗各一首;苏轼次韵文彦博诗一首;题跋苏辙、文同、李清臣赋各一篇。此次唱和虽然同以超然台为题,然却为异地唱和,据朱刚等考证,除苏轼本人和李清臣外,其余六人并未亲临超然台[1],故此次唱和主题并不在台本身,而在对台名“超然”的理解与阐发上,那么台缘何得名将是探究唱和主题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台由苏辙命名,苏辙在《超然台赋》的序中详细记述了建台经过和命名缘由:苏轼初至密州时,蝗虫肆虐,狱讼充斥,人们食不果腹,经过一年治理后社会才得以安定,遂建台以与僚属登览为乐,并请苏辙命名。苏辙认为:
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渔者知泽,安于其所而已。其乐不相及也,而台则尽之。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故邪?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尝试以超然命之,可乎?[2]331-332
由此可知,超然台之命名有两层涵义:一是表达对苏轼使耕者、渔者都“安于其所”的政绩和修台为乐行为的肯定,二是表达对依旧“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的人的悲哀。苏轼不为困境所苦,超脱得以为乐,是一“超然”也;而与沉浮宦海之人相比,苏轼游于其外,则是“超然”的另一义。
细读其他几人作品,发现主题也大致不出此两端。文彦博在诗中说:“名教有静乐,纷华不动心。……民被袴襦惠,境绝枹鼓音。”[3]即是对苏轼不慕世俗之乐以及施政惠民的赞扬。司马光《超然台寄子瞻学士》言:“使君仁智心,济以忠义胆。……用此始优游,当官免阿谄。向时守高密,民安吏手敛。……比之在陋巷,为乐亦何歉。”[4]也肯定了苏轼的超脱优游和政绩,并且还以颜回比之。张耒则将苏轼与奔走名利之人的对比阐述得更加直露:“予视世之贱丈夫方奔走劳役,守尘壤,握垢秽,嗜之而不知厌。而超然者方远引绝去,芥视万物,视世之所乐,不动其心,则可不谓贤邪?”[5]15从而加深了对苏轼的认同。苏轼本人在《和潞公超然台次韵》中也表达了对文彦博的赞同:“我公厌富贵,常苦勋业寻。相期赤松子,永望白云岑。清风出谈笑,万窍为号吟。吟成超然诗,洗我蓬之心。”[6]将潞公引为同道中人。
对以上作品分析发现,诸公在表达对苏轼本人的肯定时,除了认同其为人和政绩之外,通常都是通过否定其对立面,即沉浮宦海为名利汲汲奔走的人而完成的。然若真的达到超然,万物皆不足以挂怀,又何必设置对立面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还在苏轼的《超然台记》中。苏轼在记中自言:“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7]351若不将诸公之作结合来看,孤立视之,还以为苏轼仅仅是为了说明自己超越了这些困苦而最终获得超然呢。然若结合来看,苏轼初至密州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与那些奔走名利之人有何关系呢?苏轼最终在御史台的监狱中吐露了实情,据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记载:
轼又作《超然台记》云:“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意言连年蝗虫盗贼狱讼之多,非讽朝廷,政事阙失,并新法不便所致。及云“斋厨所然,日食杞菊”以非讽朝廷,新法削减公使钱太甚。[8]
原来苏轼之言乃有所指,那么诸公在肯定苏轼时,否定的对立面就应与苏轼所指相同,即因颁行新法而得贵的众人。故苏轼邀请诸公同赋超然台,诸公随即纷纷应和,这既是表态支持苏轼,同时也是在向新党表态,他们欲以超然之态度傲视新党。此处需要说明的是,李清臣属新党,支持变法,他所以参与此次唱和,当与他任职京东路行狱有关[9],密州正为他的辖区,并且他还曾亲临超然台,故苏轼邀请他参与此次唱和也在情理之中。
此外,除了诸公对“超然”主体的阐述可以表明他们对新党的态度,他们唱和所选用的文体也是别有深意的。自古以来文人多以诗歌唱答,因其短小,易于操作,同时还因孔子先圣早有“诗可以群”的倡导,似乎早早就为后世文人交流唱和选定了文体。而至中唐,尤其是北宋,又多了与诗扯不清关系的词,词便于抒情,同样适合作酬唱之用。当然,文人交流,尺牍书信亦不可少,但无论如何,都不至于用赋体来酬唱。然而苏轼作为发起人,却刻意选择了赋这一文体,张耒在《超然台赋》的序中言明:“苏子瞻守密,作台于囿,名以超然,命诸公赋之。”[5]15可知赋体确为苏轼所指定。苏轼为何选择如此具有难度的一种文体呢?是因为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推行新法,罢诗赋,专以策论取士。苏轼当即表示不满,作《议学校贡举状》,认为朝廷能否得人,在于知人、责实,不在于以何科目取士,并且以杨亿、石介分别为正反例论述了文华不碍为臣之道:“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通经学古者,莫如孙复、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又可施之于政事之间乎?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7]724苏轼以文名家,并且对取士之道一向持比较开通的态度,故苏轼反对废除辞赋也是应有之义。因此苏轼发起此次唱和,刻意选择赋这一文体,一是为了表明对新法改革科举考试、废除辞赋的反对,同时,作为一个以文自任的人,欧阳修所选定的文坛盟主接班人,苏轼也有责任保护赋这一文体不要因新法的冲击而衰落。实际上,不唯此次,在元祐旧党执政后,刘挚等人便上书要求科考恢复旧制,兼试诗赋与策论,苏轼又作《复改科赋》,云:“新天子兮,继体承乾。老相国兮,更张孰先?悯科场之积弊,复诗赋以求贤。探经义之渊源,是非纷若;考辞章之声律,去取昭然。”[7]29又一次以实际创作表达了对诗赋的支持和对新法的反对。苏轼发起于前,而诸公纷纷响应于后(除了文彦博和司马光,苏轼或不敢“命其赋之”),以赋作答,即表明对苏轼的支持,对新法的反对。所以此次唱和,无论在主题的表达还是在文体的选用上都是有意为之,他们以群体形式表达了对新法的反对和对同属反对新法这一群体成员间的彼此认同。
二、群体成员间的相互慰藉
承前所言,此时正值旧党与新党斗争失利之际,他们心理上的压抑和苦闷是可以想见的,正如苏辙在赋中所说:
嗟人生之飘摇兮,寄流枿于海壖。苟所遇而皆得兮,遑退择而后安。彼世俗之私己兮,每自予于曲全。中变溃而失故兮,有惊悼而汍澜。诚达观之无不可兮,又何有于忧患。顾游宦之迫隘兮,常勤苦以终年。盍求乐于一醉兮,灭膏火之焚煎。[2]332
虽然苏辙以“超然”二字名台,但从赋中可知,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是飘摇坎坷、辛苦终年,还常常要屈己求全,不免心若油烹,故在苏辙看来,“超然”实为他们不得已的一种选择,万般无奈下的一条出路。苏辙于唱和之中,率先作赋,实道出所有旧党人的心声,这既是他对同道中人的倾诉,也是对他们的理解,其他人既是倾听者,同时也是被理解者。大家同在、彼此交流、相互理解,这对于同处其中的人来说,不能不算是一种安慰,故这是此次唱和带给群体成员心理慰藉的第一层,也是“超然”雄篇的前奏。“超然”的最后唱响和更进一层的心理慰藉还要靠苏轼来完成。
《超然台记》虽为记体散文,然苏轼开篇立论“凡物皆有可观”[7]351,既然“皆有可观”,那势必会“无往而不乐”,而人们为何会忧处其间,不能自拔呢?苏轼接下来分析了原因:
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7]351
细绎之,原因不外有二:一为人之欲无穷,而物有尽,物注定不能满足人欲,是以人们不能常乐。二为人们身处其间,为物所役,故当局者迷,不能感受到乐之所在。厘清不乐之原因后,苏轼便为人们提出了可以无往而不乐的方法,即“超然”,即“游于物外”。何谓“游于物外”,即是心中无物,充分享受外物带给他的乐趣,却不为物所累,以一种优游的态度处之。苏轼这种游于物外、超然豁达的人生哲学,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其后“超越意识”的萌芽。所谓“超越意识”,尚永亮先生是这样界定的:“乃指主体在历经磨难后承受忧患、理解忧患并最终超越忧患以获取自由人格的一种努力,也就是说,贬谪士人虽身处逆境,却能不为所累,超然物外,与世无争,在精神上达到一种无所挂碍的境界。”[10]苏轼此后历黄、惠、儋三贬,每次都能很快从困境中超脱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他的超越意识在起作用。于苏轼本人而言,外任密州仿佛是此后三贬的昭示,而超然雄篇也为此后的超越夯实了思想基础,正如林纾先生所言:“惟东坡有超然台之作,则后此惠州、滕迈、儋耳之行,皆无关紧要矣。”[11]
而对于此次唱和的群体而言,这篇力作无疑传达了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周辉《清波杂志》有言:“放臣逐客,一旦弃置远外,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什,特为酸楚,极有不能自遣者。”[12]可见文人志士一旦被外任、贬谪,作戚戚之文乃是常情、常态,故韩愈也不能免俗。于群体士气低落之际,苏轼发起唱和,除了传递一种群体犹在、屹立不倒的信息外,更传递了一种傲视困难、自信健拔的精神力量。然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心理上的慰藉和鼓励,苏轼更传授给其他群体成员一种超越困难的方法,即“游于物外”。苏轼深究物理,每有所得便乐于与众分享,以期对方得以自释。他曾致书滕达道教其如何“省事”:“近得筠州舍弟书,教以省事,若能省之又省,使终日无一语一事,则其中自有至乐,殆不可名。此法奇秘,惟不肖与公共之。”[7]1482他还曾教张耒怎样断肉:“天下之难事也,殆似断肉。今使人一生食菜,必不肯。且断肉百日,似易听也。百日之后,复展百日,以及期年,几忘肉矣。但且立期展限,决有成也。已验之方,思以奉传,想识此意也。”[7]1538缘何要“省事”“断肉”?无非是时事艰难,要于其中获得心理上的自释。苏轼历三贬,年纪愈大,贬谪愈远,境遇也愈艰难,然他仍不忘致书亲友,教他们如何超越困难,获得心理上的自释与自乐。这也许正是苏轼的凝聚力所在。他能引诸多门人朋友舍身追随,不完全是因为他的才华无人匹敌,还因为他能经常传递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给对方,并且将众人系于心上,每有所得便欲推广,以惠及他人,维系群体,使其生生不息,就如程磊先生所言:“领袖人物以气质感召的辐射影响,与自我人格修养融合起来,这是一种以情感交流和心理慰勉为基础的双向互动,从而培育出并立相砥的士人群体精神,在愈加酷烈的党争中,此种群体凝聚的人文精神一直爝火不息,维系着士人阶层的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使其能胸次振拔、以道抗势,从容面对甚至慷慨承当贬谪中的种种困苦磨难。”[13]而苏轼于政治斗争失利之际发起唱和,正起到了振奋群体精神、鼓舞群体士气的作用,是此次唱和带给众人的第二重心理慰藉。
三、主盟的尝试与群体的巩固
虽然此次唱和包含一定的政治因素,但不能忽视的是,它仍是一次文学唱和,其中包含的政治因素也是以文学形式表现出来的。苏轼主动发出邀请,诸公立即纷纷响应,故我们可以将之视为苏轼主盟文坛的一次尝试和准备。
主观上讲,苏轼具备主盟的意愿和提携后辈的雅量。据李廌《师友谈记》载,苏轼曾自言:“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14]苏轼在《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中亦深情回忆欧公生前对他的嘱托:“我老将休,付子斯文。”[15]由此可见,欧公生前已有将文坛盟主之位传于苏轼的意愿,而苏轼在那时便已做了有朝一日会成为接班人的心理准备。并且苏轼爱才之心与欧公无异,但凡有机会,便会提携奖掖后学。据《宋史·晁补之传》载:“十七岁从父官杭州,稡钱塘山川风物之丽,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苏轼。轼先欲有所赋,读之叹曰:‘吾可以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16]而晁咏之却受到了更好的礼遇:“时苏轼守扬州,补之倅州事,以其诗文献轼,轼曰:‘有才如此,独不令我一识面邪?’乃具参军礼入谒,轼下堂挽而上,顾坐客曰:‘奇才也!’复举进士,又举宏词,一时传诵其文。”[17]可见,苏轼奖掖后辈,甚至不惜屈己以抬高其声名,确实雅量非常。
客观上讲,苏轼主盟文坛的时机已然成熟。苏轼的恩师欧阳修已于熙宁五年(1072)辞世,执掌文坛的重任便落在苏轼肩上。而此时,“苏门四学士”已有三人拜入其门下,最早的便是张耒。据《宋史·张耒传》云:“十七时作《函关赋》,已传人口。游学于陈,学官苏辙爱之,因得从轼游,轼亦深知之,称其文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声。”[18]时在熙宁三年(1070)。继之为晁补之,熙宁六年(1073),晁补之与苏轼见于新城[19]。再次是秦观,苏轼与之神交于来密州上任的路上,据惠洪《冷斋夜话》载:“东坡初未识秦少游,少游知其将复过维扬,作坡笔语题壁于一山中寺。东坡果不能辨,大惊。及见孙莘老,出少游词数百篇,读之乃叹曰:‘向书寺壁者岂此郎邪?’”[20]虽不曾谋面,但此次神交就是秦观为拜入苏轼门下而精心设计的。故在熙宁八年(1075),苏轼发起超然台唱和之际,后来的“苏门”已初具规模,所以称此次唱和为苏轼主盟的尝试应不过分。
另外,从实际操作上看,此次唱和已具有一种大规模文学活动的流程。首先是苏轼修台,继而请苏辙命名并作赋,之后自作记,并邀请其他人作赋。张耒序中言:“予在东海,子瞻令贡父来命。”[5]15可见苏轼主持此次唱和是不计路途远近的。他人寄来文稿之后,苏轼还一一予以题跋、点评。如评价苏辙之文:“子由之文,词理精确,有不及吾,而体气高妙,吾所不及。虽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资所短,终莫能脱。至于此文,则精确、高妙,殆两得之,尤为可贵也。”[7]2059这一著名论断便出自此时。并且从他《书李邦直超然台赋后》中言“邦直之言,可谓善自持矣,故刻石以自儆云”[7]2060可知,苏轼还将所得之文刻石为记。此外,他还向文与可乞诗:“向有书,乞《超然台》诗,仍乞草书,得为摹石台上,切望!切望!”[7]2441今不见文与可之诗,但从信中我们可以探知,苏轼对此次唱和是极为用心的,甚至连刻石之书体都做了统一规定,其文坛盟主之风采由此可见一斑。
若从文学角度考察,本次唱和收获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苏轼的《超然台记》犹为其中的压卷之作。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群体的努力,使赋这一饱受新法冲击、濒于没落的文体再次为世人瞩目。而从群体角度考察,此次文学唱和可以算作一次群体交流活动,群体活动越多,成员之间联系越是密切,群体则越为稳固。并且,此次唱和中,更有人借机表达了欲从苏轼游的愿望,如文与可在赋中说:“余将从之兮遥相望……下超然兮拜其旁,愿有问兮遇非常。”[21]而鲜于侁也表示:“天之西兮海之东,不惮远兮欲从其游。”[22]由此可知,此次唱和活动进一步巩固了这一群体,使群体成员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
王水照先生曾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宋文学结盟思潮是政治上‘朋党论’的文学版,文学结盟是政治结盟的逻辑延伸。”[23]此次超然台唱和亦然。因政治倾向相同而组织了文学唱和,以文学唱和为契机,又表达了相同的政治倾向;因政治立场相同而结成文学同盟,而文学同盟的成立又巩固了政治同盟。由此次超然台唱和可以看出,以苏轼为中心的群体具备政治与文学的双重属性,而一个群体所具备的共同属性越多,它就越稳固。故这一群体一直自强不息、屹立不倒,以铮铮之铁骨和傲岸的气节随党争相沉浮,一直持续到其间成员相继辞世。同时,此次唱和也使“诗可以群”这一命题有了更为深广丰富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