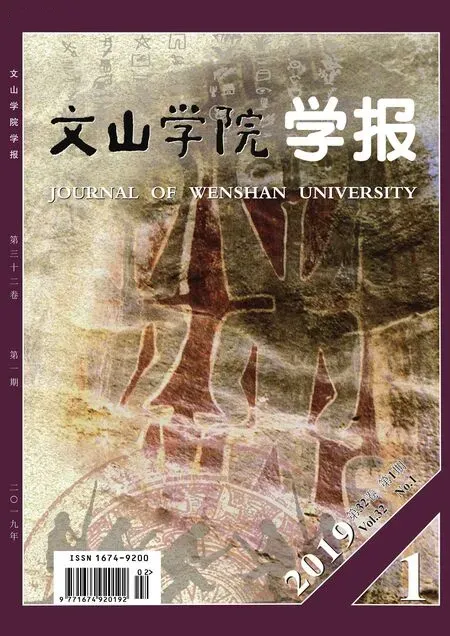论《牡丹亭》的梦境构建及其文化意蕴
刘 燕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牡丹亭》作为“临川四梦”的翘楚之作,一经面世便引起了文坛的极大震动,以至于“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1]女主人公杜丽娘“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生死死为情多”的旷世爱情传奇使得杜丽娘成为“至情”的化身。而这种超越生死的“至情”依托于“梦”来构建,正如汤显祖自己为“四梦”所作的理论总结:“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复甘义麓》)[2]1367。“梦”是联结“情”和“戏”的桥梁,“梦”是“情”的一种外化,赋予了“情”以象征的意义,同时“梦”构成“戏”的一种最显著的艺术特征,即富有梦幻色彩。“人世之事,非人世所能尽”(《牡丹亭记题词》)[2]1093,汤显祖认为,拘泥于生活现实,反而无法道尽生活本来的复杂性,而通过梦境的构建,倒更能说尽“人世之事”,从而反映出比现实更深广的人生世相和更真切的情感意蕴。
《牡丹亭》中杜丽娘的至情至幻之梦既是汤显祖通过虚幻的梦境以反衬女性现实生活的黑暗,在对女性源于内心最本质最真切的情欲进行大胆的肯定和体认中,彰显了汤显祖对女性生命意义的一种人道主义关怀。同时在杜丽娘至情之梦的表征下,倾注了作者的政治失意、壮志未酬和年华易逝的苦闷和悲愤,寄托了经过宦海浮沉的汤显祖对人生、人性、社会政治、世道民生等多方面的体察和思考。这种香草美人式的政治寄托无疑是对中国源远流长的诗骚传统的一种有意继承和发挥。
一、至情之梦:对女性生命意义的人文关怀
早在创作《牡丹亭》之前,汤显祖就在《赴帅生梦作有序》中提出了“梦生于情,情生于适”的戏剧理念,明确指出“梦”源于“情”,而“情”则是来自于梦者和所梦对象的情投意合,即“适”,标示了“梦”的原动力是源于梦者最真切的“情”,“情”则基于自我体认的本质之“真”。这种戏剧观念无疑在其后创作的《牡丹亭》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说:“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2]1093在汤氏看来,梦是由人的真实情感引发的,能反映人物灵魂深处最隐秘最真实的情感诉求,因而在“梦”这一虚幻的外壳中包含着人世间最真最至的“情”。
《牡丹亭》的意义在于作者汤显祖通过“梦”这一艺术化、理想化的形式,将隐藏在杜丽娘内心深处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和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追求进行尽情地释放,从而将现实中被理学压抑的人性之美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杜丽娘本能的从宣扬“后妃之德”的《诗经·关雎》中发现了被遮蔽的自我真实的存在,在《诗经》昭示的人性之真与苦闷现实的比照中,杜丽娘觉出自我生命价值的失落,不由发出“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的沉痛感叹。清醒的意识到自己生存状态的不合理后,杜丽娘想要挣脱被强大的封建意识形态所笼罩的封闭生活,所以她勇敢的走出了反抗的第一步——将自己的活动范围由闺阁延伸到了后花园。步入“姹紫嫣红开遍”的满园春色,触发了杜丽娘对自我生命的惊异。在对满园春色和自我青春生命的同构对比中,杜丽娘产生了“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的惆怅和感伤,这意味着杜丽娘自我意识觉醒的开始。
“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在“超我”所属的快乐原则战胜“自我”所属的道德原则的束缚下,杜丽娘终于迎来了一场至真至美的“情欲之梦”。在梦中,杜丽娘冲破禁锢人性的枷锁,大胆的与自己心爱的人相会,并享受“云雨之欢”。就这样,杜丽娘在现实中“剪不断、理还乱”的无法排遣的愁闷的春情,在梦中却能“密约偷期,皆得成秦晋”;现实中“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的生命孤独感和焦灼感,在梦中却能得到梦中情人“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爱怜和顾盼。这预示着杜丽娘完成了对自我的突破和飞越,真正成为自我的开始。“梦”作为一个有别于现实的虚幻存在,在杜丽娘的心理认知中却是“情与梦同,梦与真同”(三妇本《婚走》批语),也即是说梦即现实,现实等同于梦,“梦境”在杜丽娘志诚的坚信中成了“真境”。《惊梦》之后的杜丽娘“从此无时不在梦中矣”(三妇本《惊梦》批语)。
梦醒之后的杜丽娘“行坐不宁,自觉如有所失”,再也无法平静的回归到令人窒息的往日生活了,带着对爱情的渴望继而去“寻梦”,企图回到梦中的生活空间。如果说,“惊梦”触发了杜丽娘青春意识的觉醒,那么,“寻梦”便是杜丽娘对自我生命价值的主动追寻。而最终寻梦无着,杜丽娘只能以终结生命这一沉重的代价来换取梦境中理想生活的继续——杜丽娘在阴间(梦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寻找到梦中情人后大胆的“自荐枕席”,这是杜丽娘寻找一种现实情欲得不到满足的替代性的补偿,更是杜丽娘在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中获得外部世界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认同和肯定。
梦境中的至情王国使杜丽娘对现实生活发出“理应当如此”的呼唤,然而这种理想王国终究只存在于杜丽娘的梦境中,一旦由阴返阳(梦的对立一方),杜丽娘再次被令人窒息的封建礼教这一无形的力量所包围。生身父亲杜宝面对重生的杜丽娘,“愿吾皇向金阶一打,立见妖魔”(第五十五出《圆驾》),宁愿要死去的贞节的杜丽娘,也不愿接受曾经苟合过的活生生的杜丽娘,昭示了“有情人”杜丽娘与“无情”的封建礼教的尖锐对立。而最终皇帝裁决、全家团圆的大团圆结局并没有消解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封建压抑人性的客观环境的深刻矛盾,只是汤显祖在梦醒后无路可走的现实中所作的一个理想幻境的设计。
杜丽娘死于对爱情的徒然渴望,梦中情人柳梦梅是杜丽娘封闭生活里自我幻想的产物,揭示了中国封建女性生命的悲哀。至此我们看到,无论是杜丽娘至情至真之梦的构建,还是历经阴阳轮回最终取得最高权威认可的情节设计,都是基于汤显祖运用梦境观照现实、反衬现实的创作心理——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就在梦境中获得替代性的补偿,这其中融入了汤显祖对千千万万个像杜丽娘一样的女性生命意义的关怀,“梦”也就成了广大女性个体生命深受理学摧残的一味心灵安慰剂,汤显祖运用“梦”这一艺术形式,不仅加大了《牡丹亭》的悲剧深度,而且使这个“梦”具有了深广的时代意义和丰富的人文内涵,“拨开了正统理学的迷雾,在受迫害最深的女性胸间吹拂起阵阵和煦清新的春风。”[3]
汤显祖通过梦境的抒写与构建,以表达对女性自我生命价值的人文关怀,这与明代特定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明初是程朱理学盛行一时的时代,它以“穷理尽性”为核心,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人们必须绝对服从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为准则的封建纲常伦理,理性凌驾于个体意识、情感意欲之上,人成了一个抽象化的封建纲常伦理的载体,从而出现理学和人的两极对立。处于封建社会两性关系劣势地位的女性更是饱受封建礼教的摧残,很多女性不幸沦为封建礼教的殉葬品。据《明史·列女传》记载:“明兴,著为规条,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4]直到陆王心学的创立和异端思想的兴起,才透露出个性解放的灵光。王阳明的“心学”重新高扬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精神,这为晚明士人摆脱封建理学的束缚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被视为异端之尤的李贽对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更是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他大声疾呼,为妇女鸣不平,一时间社会上兴起了一股高扬个体主体精神和独立自由人格的自我实现的进步思潮。汤显祖的《牡丹亭》正是在时代精神的脉动中应运而生,他将笔触指向了杜丽娘式的广大女性个体生命遭逢的不幸和苦难上,关注女性个体的生存状态,在对女性生命价值的关照中揭露理学世界的虚伪和残酷,肯定了人的自然生命欲望包括生理需求在内的人生欲求,在戏剧领域呼应了时代关注妇女解放的思想潮流。
汤显祖这种对女性自我生命价值的人文关怀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自于汤显祖一生所秉持的“至情观”和“贵生”思想。汤显祖提出“世总为情”[2]1050“人生而有情”[2]1127的“至情观”,并认为他创作戏剧的原动力来自于“情”的驱使:“吾犹在此为情所使,劬于伎剧”(《续栖贤莲社求友文》)[2]1161,确立了“情”在戏剧中的崇高地位。这种重情的思想来源于恩师罗汝芳、亦师亦友的名僧达观和具有异端思想的李贽。罗汝芳是泰州学派王艮的三传弟子,他标举个体要回归到自然本真状态的“赤子之心”,认为顺从本心即合天理,肯定人的自然情性。李贽所极力主张的“童心说”则更强调本真自我的完整显现,将王艮以来泰州学派张扬个体意识的理论倾向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达观禅师提出“无情则同木石,有情则不异于众生”的命题,这些对自然人性的张扬使汤显祖对“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汤显祖意欲通过“至情”的宣扬建立“有情之天下”(《青莲阁记》)。另外,受罗汝芳宇宙万物皆“生生不已”观念的影响,汤显祖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贵生书院说》)的“贵生”思想,而“贵生”的前提是“知生”,即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自觉自明,“知生则知自贵,又知天下之生皆当贵重也”,彰显了汤显祖对自然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视和关怀。
“重情”和“贵生”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思想倾向在汤显祖创作的《牡丹亭》中得到了完美地体现。汤氏认为,无情不足以生梦,无梦则不足以见真情,醒觉之情伪,梦幻之情真。杜丽娘因情成梦,在梦中自我的自然天性得到尽情地释放,自我的生命价值得以实现和彰显,梦中的王国是“有情之天下”。最终杜丽娘一梦而亡,为了追寻梦中理想的爱情伴侣而付出生命的惨痛代价,则是汤显祖对“有法之天下”天理扼杀人性的强烈控诉。这种强调人的自然情欲的合理性、张扬个体生命价值实现、关怀女性现实人生的人道主义情怀正是基于汤显祖“贵生”哲学观和“至情”文艺观在戏剧领域的具体实践。
《牡丹亭》因融入了汤显祖对女性生命价值的深刻思考以及对女性现实命运的深切关怀,故而打动了后世无数个幽禁深闺的闺阁女子的心,“入人最深,遂令后世之听者泪,读者颦,无情者心动,有情者肠裂”(《焚香记总评》)。因此,明清闺阁女子将汤显祖视为“闺阁知音”,正如清代顾娰所说:“百余年来,诵此书者如俞娘、小青,闺阁中多有解人”[5]。她们忘我式的沉浸在《牡丹亭》的阅读里,融入了自己深刻的情感体验和生命体验,在对杜丽娘生存状态的观照和审视中,发现了自我,在汤显祖所构建的梦境中获得了一种现实生活无法实现的想象性、替代性的满足,以寻找情感和心灵的慰藉。如扬州才女冯小青因读《牡丹亭》抑郁而终,临终前留下了一段灵魂告白:“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读《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又有娄江女子俞二娘为一曲牡丹断肠而死;广陵金凤钿未及见玉茗抑郁而终;余杭女伶商小玲一曲牡丹痛绝于红氍毹;而颦儿为一曲牡丹,“不觉点头自叹……心动神摇……如痴如醉,站立不住……心痛神驰,眼中落泪”[6]……这些或现实中或小说中的闺阁女子之所以因阅读《牡丹亭》或落泪或夭折,就在于《牡丹亭》真切的反映了明清女子压抑苦闷的生存境遇和悲剧的生命体验,从而产生了极大的情感共鸣,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牡丹亭》所包含的深厚的情感内涵和人文意蕴。
二、政治之梦:香草美人式的政治寄托
李卓吾评《西厢记》时说:“余览斯记,想见其为人,当其时必有大不得意于君臣朋友之间者,故借夫妇离合姻缘以发其端。”李卓吾这段对《西厢记》写夫妇以喻君臣的经典评价同样也可以用于《牡丹亭》。《牡丹亭》在杜、柳爱情故事的背后,隐藏着汤显祖一生内心萦绕不去的儒家政治情怀,正如他在《答牛春宇中丞》里所说:“天下忘吾属易,吾属忘天下难也”[2]1393,自屈原《离骚》开创的香草美人式的政治寄托传统在《牡丹亭》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清陆次云《北墅绪言》早就注意到了这点,指出:“《还魂》如莺惜春残,雁哀月冷,《离骚》之遗绪也。”[7]
出身于书香世家的汤显祖从小就被父亲寄托厚望,正如其名“显祖”所显示的,希望汤显祖走“学而优则仕”的儒家知识分子人生道路,从而光宗耀祖。汤显祖也不负父望,积极投身举业,十四岁就中了秀才,二十一岁时又中江西乡试第八名举人。处于人生上升期的汤显祖踌躇满志,“志意激昂,风骨遒紧。扼腕希风,视天下事数着可了”(《汤遂昌显祖传》),然而刚正不阿、不事权贵的秉性让他的入仕之路异常艰辛。面对执政首辅张居正的拉拢,汤显祖秉持人格的纯净,“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汤显祖《秀才说》),从而导致四次会试都名落孙山,直到张居正死后的第二年才登进士及第。此时的他已经三十四岁,“数不第,展转顿挫,气力已减”(沈际飞《玉茗堂文集题词》),青年时期的书生刚毅之气,在辗转举业十余年后已经大大消减。
万历十九年,一封震惊朝野的《论辅臣科臣书》触犯皇威,汤显祖被贬到雷州半岛的徐闻县任小吏典史。直到万历二十一年,汤显祖才量移遂昌县知县。此时的他虽历经仕途坎坷,然而执着于政治理想实现的他意欲把处于百废待兴的山区小县遂昌打造成他的理想政治王国。五年任职期间,他体恤民情、抑制豪绅、扶持农桑、兴办教育,“一时循吏声,为两浙冠”[8],却始终得不到升迁。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挂冠求去、归隐田园,潜心于戏曲诗文创作中,“掩门自贞”,并抱着一朝起用的最后一丝幻想。然而万历二十九年,吏部以“浮躁”的罪名罢了他的职,至此,汤显祖一生的政治仕途就宣告终结。
怅然退隐的汤显祖“胸中魁垒,陶写未尽,则发而为词曲”。汤显祖曾自言“经济自常体,著作乃余事”,可见,汤显祖“平生以天下为己任”[9],志在实现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当政治理想受挫时,汤显祖遂退而著述,将自己的一腔政治热情借助戏剧的形式予以倾吐和宣泄。可以说,创作“临川四梦”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其政治理想的进一步延伸。
《牡丹亭》中,汤显祖将自己政治怀抱不得舒展的苦闷和压抑的思绪投射到了女主人公杜丽娘的身上。首先,杜丽娘以貌自怜为表征的自恋与汤显祖以才自侍为表征的自恋心理同构。《惊梦》一出,杜丽娘感叹自己“颜色如花”“如花美眷”却“三春好处无人见”;《写真》一出,杜丽娘对镜流连顾盼,“三分春色描来易,一段伤心画出难”,感叹自己“二八春容”“人如花貌”,流露出深深的自怜自赏的自恋情结。正如三妇本所评:“游园时,好处恨无人见;写真时,美貌恐有谁知:一种深情”。杜丽娘这种基于对自己外貌强烈的认同意识,实则是汤显祖以才自骄的一种心理投影。无论是“某颇有区区之略,可以变化天下”(《答余中宇先生》)的自诩,还是“童子诸生中,俊气万人一。弱冠精华开,上路风云出”“历落在世事,慷慨趋王术。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三十七》)的自视甚高,体现的都是汤显祖对自己政治才华的体认和自赏。
其次,杜丽娘这种由自己的美貌“无人见”而生发的伤春伤怀的“幽闺自怜”与汤显祖因自己的政治才华不被君王赏识的苦闷心理同构。杜丽娘游园所引发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光阴”“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的美人迟暮之感隐喻汤显祖政治才华得不到施展、青春年华虚掷的政治苦闷。“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杜丽娘对如意郎君的深切呼唤和渴望,实则是怅然退隐的汤显祖对皇上一朝“起报知遇”之恩的期待和憧憬。然而朝廷却以“浮躁”之名断了汤显祖最后的一点政治幻想,治世之梦的幻灭让汤显祖不由发出“伤心拍遍无人会”(《七夕醉答君东》)的呼喊。这种郁郁不得志的政治感伤隐藏在杜丽娘“因春感情,遇秋成恨”的怅惘中,隐藏在为杜丽娘寻梦不得而亡的“卧薪痛哭”(焦循《剧说》卷五)中。中国古典诗词中的伤春意识常常联结着个体生命价值得不到实现的愤懑和不满,从屈原的“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南”,到杜甫、陆游和辛弃疾等人的诗词,无不具有这种强烈的伤怀忧世意识。汤显祖继承历来古诗词的伤春传统,借杜丽娘的伤春以抒发他的忧世意识和个人政治才能得不到施展的苦闷情绪。
再次,杜丽娘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寻找到自己理想的爱人,只能在一场美丽的梦境中获得情欲的满足。现代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愿望的满足”[10]。这个梦境是杜丽娘内心情欲焦灼的大胆释放,也是汤显祖自身政治上无路可走所产生的焦灼心理的一种宣泄,从而获得一种替代性的心理补偿。杜丽娘最终因寻梦不着而郁郁而死,后又还魂归来和梦中情人柳梦梅结为伉俪,这种为了理想爱情“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执着追求精神无疑也是汤显祖为了实现其治世之梦而执着追求的生动写照。需要说明的是,《牡丹亭》最后这种圆梦结局的设计不是汤显祖对才子佳人“有情人终成眷属”俗套的格格相因,而是借圆梦的艺术设计抚慰自己受挫郁积的儒家政治情怀。故而汤显祖感叹“人知其乐,不知其悲”(《答李乃始》),喜剧表壳的背后,隐藏着更深的悲。这不仅是以杜丽娘为代表的广大女性的悲,更是作者隐写的政治悲剧,倾注了作者的政治失意、壮志未酬和年华易逝的悲愤。
如果说创作于青年时期的“四梦”之一《紫箫记》还存有对“元和皇帝”的溢美倾向,那么在经历过人生政治道路上的起起伏伏后,汤显祖早期的愚忠思想也在慢慢的瓦解,使得汤显祖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济世理想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于是以笔代剑,完成了“后二梦”——《南柯记》《邯郸记》的创作。相对于“前二梦”表现出对参与政治的心理认同和执着追求,“后二梦”则表现出愈演愈烈的政治批判和一种理想幻灭的虚无。正如其《梦亭》诗曰:“知向梦中来,好向梦中去。来去梦亭中,知醒在何处?”表现了汤显祖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彷徨和苦闷。从青年时期的认同到中年时期的追求再到晚年时期的最终幻灭,汤显祖将自己一生的政治情怀贯穿在了“四梦”的梦境构建中,从而在梦境中开拓自己的治世之梦。
创作于汤显祖罢官归田当年的《牡丹亭》处于汤显祖人生和政治思想的过渡时期,此时的他既有积极入世的执着追求,又迫于“世路良难,吏道殊迫”(《答山阴王遂车》)的无奈政治现实,再加上“家君恒督我以检儒,大父辄要我以仙游”(《和大父游城西魏夫人坛故址诗》),汤显祖始终徘徊在“出世”和“入世”的矛盾和困扰中,进退两难。这种政治的矛盾态度反映在《牡丹亭》中,便体现出杜丽娘在梦境和现实、“本我”和“超我”的两难境地里挣扎、苦闷和幽怨。梦境中的杜丽娘自荐枕席以求美好姻缘,宣泄内心深处最原始最本质最隐秘的情感欲望,以打破现实的束缚和桎梏,然而梦醒后,又不得不遵从封建纲常伦理对人的压制与摧残。汤显祖在杜丽娘的心理轨迹中投射了自我政治态度的挣扎和转变,故而抒写杜丽娘的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汤显祖一种香草美人式的政治寄托。
可以说,杜丽娘的身上承载着汤显祖大半生所走过的政治道路上的憧憬、执着、彷徨、苦闷、困惑等等复杂情绪,而这一切都是通过《牡丹亭》所构建的梦境来呈现的,无“梦”就不足以成就《牡丹亭》,无“梦”就不足以宣泄萦绕在汤显祖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入世情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牡丹亭》里“梦”的抒写和构建,富有多元化的文化意蕴。对杜丽娘“至情之梦”的抒写,既是基于对女性生命意义的一种人道主义关怀,同时也融入了作者对社会人生、自然人性、政治道路等多方面的思考和观照,从而使《牡丹亭》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爱情戏剧,在对人生哲理、生命意义的叩问和追寻中获得了永恒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