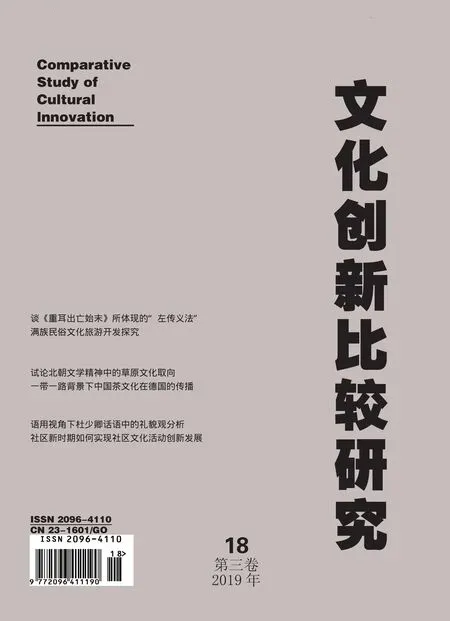屈赋黄色意象的文化阐释
李梦欣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湖南湘潭 411201)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热衷于意象的构造,在屈赋意象群中黄色意象独特而耀眼,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是屈原对其所处时代的无声诉说。与其它颜色意象相比较,黄色意象的使用频率不算高,但黄色意象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却是不容忽视的,是屈赋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1 高洁坚贞的自我表达
从绚丽多姿的色彩体系中挑选合适的颜色,不仅与颜色本身有关,也与抒情主人公的情感有着莫大干系,是主观与客观相契合的产物。屈原在创作屈赋时,根据自身情感的变化选择不同的颜色意象,而黄色意象的运用是屈原高洁坚贞的自我表达。
作为纯色的“黄”,自古以来便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少文人都曾对此作出阐释。比如许慎在《说文·黄部》中论述:“黄,地之色也。从田从苂,苂亦声。臧苂,古文光。”[1]可见“黄”指的是大地之色,这与五行中“土”的颜色有关联,《周礼·考工记》中记载:“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2]古人将五行、五方与五色结合起来,认为东方为木,南方为火,北方为水,西方为金,中央为土,这样“黄”即中原黄土地带的大地色。黄河流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它处中央地带,黄河的水色是黄色,地色也是黄色,黄色自然成了人们崇拜的颜色。郭沫若追溯“黄”之起源,他发现:“黄即佩玉……复假为黄白字,卒至假借义行而本义废,乃造珩若璜以代之,或更假用衡字。”(《金文丛考》)“黄”的本义为“佩玉”,而我们现在所说的“黄色”乃假借义,由于某些原因导致“假借义行而本义废”。若从这个角度考量,发现屈原喜用黄色意象与其偏爱玉佩有关,是其品格高洁的一种象征。屈原的高洁坚贞借助一系列黄色意象巧妙地表达出来,屈赋中“黄”、“秋菊”、“黄鹄”这些黄色意象也因屈原高尚的人格而更具象征意义。
“青黄杂糅,文章烂兮。”(《九章·橘颂》)“青”指的是没成熟的橘子,“黄”指的是成熟的橘子,青涩的和成熟的橘子错杂相间,色彩纷呈灿烂鲜艳,悬挂于枝头,令人垂涎欲滴。以青色和黄色这两种色差较大的颜色混杂在一起,形成视觉上的落差,更突显出橘树生长之茂盛,生命之活跃。“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章·橘颂》)橘树长得繁盛且修饰得当,美丽得异乎寻常,有着特立独行不随波逐流的品行。屈原从对橘的喜爱与赞颂过渡到对自己崇高志向的抒发,既是对橘的赞美,也是对理想人物的称颂与呼唤。
秋菊,又称菊花、黄花、九华等。秋菊性耐寒,当众芳凋零之际,唯它依然傲立于枝头之上,历来被认为是名士高洁品行与卓尔不群风范的代表。朱淑贞《菊花》曾云:“宁可抱香枝头死,不随黄叶舞秋风。”赞美了菊花宁死也不愿随波逐流的高尚节操,菊花也成了坚贞的象征。“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这是屈原对自己饮食的描述,他早晨喝春兰滴下的露水,傍晚吃秋菊掉下的花朵,饮食芳洁,已超越世俗所追崇的酒肉之欲,宛若飞登仙位的上神,饮食不为裹腹,而源于一种高洁的情趣。“春兰兮秋菊,长与绝兮终古。”(《九歌·礼魂》)每年春兰、秋菊开花的季节,就是人们祭祀的时候,祭祀活动如春兰、秋菊每年必定开花那样会薪火相传,直到终古之际,表现了人们对神明的虔诚与对幸福生活的期望。屈原以春兰、秋菊并举,表明它们是春与秋的象征,是高洁与坚贞的阐释。
“在上古,‘鹤’与‘鹄’音近,‘黄鹤’是由‘黄鹄’通变而来。”[3]王玉仁认为“黄鹤”就是“黄鹄”,由于某次讹传,把“黄鹄”传成“黄鹤”,恰好人们认同这种讹误,后世使用“黄鹤”的频率高于“黄鹄”。“宁与黄鹄比翼乎?宁与鸡鹜争食乎?”(《卜居》)“卜居”指的是屈原占卜自己该以何种态度处世,其实屈原对于自己何去何从是明确的,不过是假借占卜来抒发积压已久的愤懑,彰显自己高洁坚贞的志向,屈原的明君贤臣理想可与“黄鹄”比翼,岂会与小人争食?“黄鹄”是屈原对理想人物的美称或是自喻,“鸡鹜”是指君王身边的奸佞小人,屈原不屑与之为伍。“黄鹄”是世人熟知的天鹅,它能展翅高飞,被认为有远大的志向,《史记·陈涉世家》曾记载:“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鸿鹄”即“黄鹄”的别称,“鸿鹄之志”成了高远抱负的代名词。
“黄”因其独特的涵义而获得人们的青睐,由对黄河的崇拜引发先民对“黄色”的喜爱与崇拜。耐寒的“秋菊”于枝头之上笑看人世的沧海桑田,不为世俗所改变,坚持内心的高洁与坚贞。有着高远理想的“黄鹄”是屈原自身的写照,渴望像“黄鹄”那样挣脱世事的羁绊,在高空中一展身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2 神话色彩的丰富意蕴
“神话”是先民留下的宝贵财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还原当时的社会环境。矛盾曾说“就文学的立点而言,神话实实在在是原始人民的文学,迨及渐进于文明,一民族的神话即成为一民族文学的根源。”[4]屈赋神话色彩浓厚,作为屈赋代表作的《离骚》开篇就言:“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屈原自称为太阳神颛顼的后代,他“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吃穿用度都与世人大相径庭,这皆源于他对自己身份的认同。
知人论世,屈原特殊的身份导致屈赋充满神话色彩,焕发出神之光芒。屈赋黄色意象中的“黄熊”、“阳离”、“黄棘”等,这些意象富含想象与夸张,淋漓尽致地将黄色与神话传说融为一体,黄色意象自然被赋予神话意蕴。
“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天问》)“黄熊”是传说中的兽名,体型像熊,但有三只脚。究竟是“鲧化黄熊”还是“羿化黄熊”?古今学者大多认同前一说法,但从行文顺序上来考察,文本自“帝降夷羿”至“岩何越焉”的所有提问都是针对羿事而发,接下来并未更换主语,因此在这里的“黄熊”应是指羿。叶舒宪认为:“羿的变形情节正是人类学上所说的‘仪式性改变身份’的象征表现,其实质是让来自尘世的、犯有罪过的即污秽不洁的羿‘象征性’地死去,而由主持这仪式的神巫所‘复活’了的则是焕然一新的、洁净的羿。”[5]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天问》)天帝将夷羿派至人间,为的是解决夏民的忧患。羿的血统是神族,为东夷之神,人类学家利普斯认为:“太阳神可以一个神,一个英雄,可以仅是一个人,或者可以是一根燃烧的柱子。太阳光芒是太阳神射向地球的箭……”[6]按照这种思维我们不妨将羿设想为太阳神,“黄熊”即夷羿,夷羿即太阳神。屈原自称是太阳神的后裔,太阳光是明黄的,故屈原多偏爱黄色,屈赋中也多处涉及黄色意象。屈赋塑造了一系列太阳神形象,“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天问》)羲和是太阳的驾驶者。“天式从横,阳离爰死。”(《天问》)“离”即“黄鹂”,被古人视为凤凰类神鸟,“阳离”指的是太阳鸟黄鹂,太阳鸟黄鹂悲伤地死去,这是黄色意象的间接使用。太阳神家族的塑造是屈赋的一大成功,给中国古代神话添上了光辉的一笔。
“借光景以往来兮,施黄棘之枉策。”(《九章·悲回风》)屈原借光影在天地间来往,用黄棘做的马鞭很弯,《九章·悲回风》是屈原沉江前一年秋冬所作,抒发了缠绵悱恻、痛苦忧伤的悲秋情感。“黄棘”是一种树木名,《山海经·中山经》记载:“又东二十里,曰苦山……其上有木焉,名曰黄棘,黄华而员叶,其实如兰,服之不字。”[7]黄棘树开的花具有使人不孕的功效。但洪兴祖认为此处的“黄棘”是地名,“言己所以假延日月,往来天地之间,无以自处者,以其君施黄棘之枉策故也。”[8]怀王二十五年,与秦昭王在黄棘立下盟约,后被秦王骗,最终客死于秦。现在的楚倾襄王近小人远君子,是再次“施黄棘之枉策”,如再不改变楚国将面临灭国亡君的困境。
《山海经》与《楚辞》同为中国古代神话的源头,是一座富饶的宝库,保留了丰富的神话材料,是研究先秦神话的重要书籍。屈赋作为《楚辞》的重要组成部分,神话色彩更为浓厚,其中黄色意象所指代的文化内涵意蕴丰富,具有宝贵的研究价值。
3 楚地文化的深刻阐释
具有“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特点的楚辞是楚地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楚文化之大成,楚文化通过屈赋多方面展示出来。屈赋黄色意象中的“黄昏”、“纁黄”、“黄钟”形象地揭示了楚地所蕴含的文化因子。
人类学家利普斯认为:“太阳乘舟旅行于天空的海洋,是地球上许多民族所熟知的。但既然天和地在地平线上似乎是长在一起的,故人经常相信每天两者之间在西方要分合一次,而每天黄昏太阳必须从两者之间,小裂缝中通过。”[9]这一通道为“蒙谷”。黄昏是介于白天与黑夜之间的一段时期,人们经过一天的农忙之后在黄昏时分得以短暂的歇息,也是在这个时间段进行有限的文化活动。
“黄昏”的“昏”与“婚”通,由这层关系可以联想到“娶妇以昏时”的风俗习惯,《易经·屯》中记载:“乘马班如,匪寇,婚媾。”[10]反映的是原始社会中存在的抢婚现象,“匪”通“非”说明这不是抢婚,而是假抢真婚,在原始社会,女子常被当作私有财产,自然成了男子争夺的对象,抢婚这种不光彩的行为只有在半明半暗的黄昏下才方便进行,于黄昏时分成亲便成了传统世代沿袭下来。
屈原好以男女关系喻君臣关系,将楚王比作郎君,“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离骚》)、“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九章·抽思》)、“指嶓冢之西隈兮,与纁黄以为期。”(《九章·思美人》)以黄昏作为两人的约会时间,“人约黄昏后”,可屈原等风来,等雨来,就是等不来楚王,他不明白此前两人的关系亲密无间为何此时却生分了,指出楚王的反复无常。以黄昏作为约会、结婚的时间是楚文化的一大特色,这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文明背景分不开,白天辛苦劳作后,乘着天色昏暗暗的,男女双方相约于黄昏后,共述衷情,谱下一曲恋爱之歌。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越人歌》)黄昏时分荡舟于河面之上,今日何其有幸能和王子同舟共济,心中暗恋君子可君子不知。经楚翻译的《越人歌》是我国最早的翻译作品,体现了楚文化对越文化的包容与吸收,是楚越文化交融的结晶与见证。从民族关系颂歌演变为大众所熟知的男女恋歌,是一曲女子向男子表达爱意的情歌。
“楚人在楚辞创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除了作媒介物和催化剂之外,主要不在体裁方面,而在精神方面。”[11]楚人富有浪漫主义精神,以浪漫的眼光去看待身边的人事物,楚人的浪漫精神影响了楚文化,楚文化的浪漫精神与屈原自身的浪漫情怀相契合,碰撞出激情的火花,结出繁盛的文学之果。
《卜居》中还有另一个黄色意象,那便是“黄钟”。“黄钟”本为音乐上的名词,是十二律之首,“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卜居》)“黄钟”与“瓦釜”是一组对比,这里的“黄钟”借用为合乎黄钟律的钟,是编钟里音响最宏大深沉的一枚,为高雅之乐,“瓦釜”原指陶制的锅,这里代表鄙俗之乐,发音洪亮的黄钟被毁坏抛弃,粗鄙的瓦釜之声却被说成雷鸣,简直是非不分。“黄钟”比喻有才德之人,“瓦釜”比喻无才德的平庸之辈,有才之人弃之不用反而重用无才之人,这和楚国当时的现实十分吻合,屈原自比为黄钟,在乱世中被楚王抛弃,使屈原对楚国失去了信心,不知“居世何所宜行”,借占卜来决定自己何去何从。
“人约黄昏后”及抢婚的古老习俗都在黄昏时分进行,楚文化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在接纳周边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从黄昏时分与音乐等各个不同的角度揭示出楚地文化的多层性与丰富性,足以让世人惊叹。
翻开屈赋,屈原笔下的意象如同跳跃的精灵蹦跶在眼前,用意象说话,远胜于枯燥的说教,令人神之往之。黄色,不仅是自然颜色的呈现,更是精神文化的承载。黄色意象的独特文化意蕴,体现在屈原高洁坚贞的品格、耐人寻味的神话色彩以及对楚地文化的深刻阐释中,为屈原意象体系添上厚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