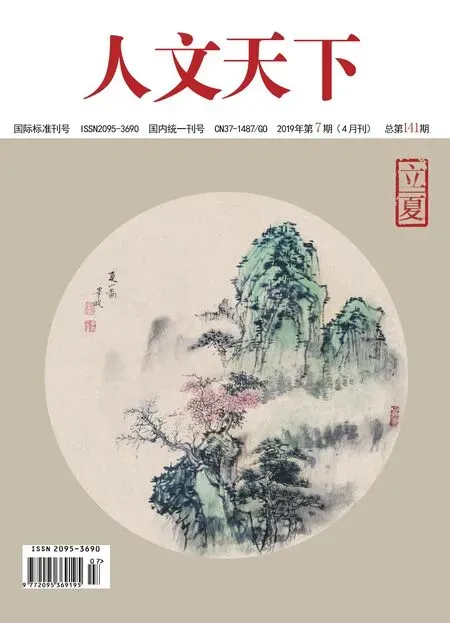中国古代蒙学概说
宋志霞
蒙学,通俗地讲就是儿童教育。蒙学是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四库全书》等大规模的丛书中都有单独的“蒙学”类目。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一书中曾说过:“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同样可以看出古人对蒙学的重视。
一、蒙学的含义
蒙学,又称开蒙、启蒙、发蒙、训蒙,相当于现代的幼儿园至小学阶段。《周易·蒙卦·彖辞》曰:“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郑玄注曰:“屯在十二月丑,故为‘物之始生’,蒙在正月寅,故为‘物之长穉。’施之于人,则幼穉为‘童蒙’也。”郭齐家《文明薪火赖传承: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教育》指出:古人将儿童称为童蒙,童蒙就是不懂事的孩子。《易经》有蒙卦,其实就是讲对儿童的启蒙教育。蒙卦是上“艮”下“坎”,“艮”为山,“坎”为水,意为山下有泉。就是说,童蒙好像安静的青山下一个清澈的源泉。山静、泉清,象征着儿童未被开发的天然善性。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说:“蒙,谓暗昧也,幼童于事多暗昧,是以谓之童蒙焉。”蒙学就是在童稚之时开发心志的之义。“蒙学”这个概念何时开始使用已无从可知。《周易·蒙卦·彖辞》说:“蒙以养正,圣功也。”这就是说启蒙的目的是希望蒙童“正”,这种“正”表现为思想纯正合乎道德要求。
蒙学一方面是教授蒙童识字、读书和作文,另一方面则是以传统的伦理道德来训导蒙童。蒙学是一个体系,不仅包括蒙学文献这个主体,还包括与之相关的教学对象、教学场所、教学方法、教育思想等。
二、蒙学的对象
蒙学教育的对象是儿童。古代儿童入学的年龄,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可能有所差异。
《汉书·食货志》说:“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岁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大戴礼记·保傅》说:“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八岁至十五岁,这是一个大致的年龄范围。除了正式入学受蒙之外,儿童在家庭中接受的启蒙教育也是蒙学教育的一部分,施教者一般是家长或由家长聘任的家庭教师。
三、蒙学的场所
蒙童接受训蒙必然要在一定的场所内,这种场所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形式上也有所不同。蒙学的场所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私人场所,即家庭或家塾;一种是公共场所,如村塾、社学、义学等。
《学记》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这些都是蒙学场所的雏形。汉代的蒙学场所一般是由个人、家族或地方乡绅筹建的。汉代的授蒙场所称“书馆”或“蒙馆”。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记载:“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苍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除此之外,还有在京师中专为贵族子弟开设的蒙学,如明帝为外戚子弟办四姓小侯学,邓太后开邸第延师教授诸王子和外戚子孙,这些场所均具有蒙学性质。宋元时代,既有民间办的私学,又有政府办的官学。由政府办的官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设在京城宫廷内的贵胄小学。据《宋史·选举志》记载,“凡诸王属尊者,立小学于其宫,其子孙,自八岁至十四岁皆入学,日诵二十字”。另一种则是设在地方上的庶民小学。元朝在立国之初,也曾下令在路学和县学内附设小学,《元史·选举志》记载,至元二十八年,“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
总体而言,公共教育在蒙学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其社会影响远远超过家庭教育。下面来看几种蒙学中的公共教育。
(一)社学
自唐代开始,民间办学就开始补充官方办学。《唐会要》记载,开元二十六年唐玄宗敕:“古者乡有序,党有塾,将以宏长儒教,诱进学徒,化民成俗,率由于是。其天下州县,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出于“化民成俗”的目的,从元代开始出现社学。《新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三年,“诸县所属村疃,五十家为一社,择年高晓农事者立为社长……每社立学校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师,农隙使子弟入学。如学文有成者,申请官司照验”。明代非常重视社学的建立。朱元璋曾经下旨命令各地建立社学。《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八年春正月丁亥,命天下立社学。上谓中书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序,故民无不知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学,适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也。’”清代对社学的建立更为积极。《清史稿·选举志》记载,康熙九年下令各直省设置社学、社师,规定凡府、州、县每乡各置社学,“择文行优者充社师,免其差徭,量给廪饩”。
元明清三代的社学多具有官方性质,具体筹办者是地方各级官员。许多官员不仅积极建立社学,有的还亲自授课。如明正统间吴郡知府朱胜在吴邑和长洲的交会处设立社学一所,“聚百童而教焉”。
(二)义学
义学亦称义塾,是我国古代社会靠官款、地方公款或地租以及个人捐赠而设立的一种蒙学。义学早在宋代就已出现过,但它只是以宗族为单位设立的,限于教授本族子弟的学校。与族塾相比,其特点是专为民间贫寒子弟所设,一般不收学费,有的还发放生活用品。明清时期,义学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清代有了政府的提倡,义学开始广为设置,从而使得义学分化为官立、民办两种形式。官立义学是由政府投资兴办的,学校经费从国库中开支。民办义学是由“民”通过捐钱、捐田、捐房设立的,包括公办(学校经费由公款或公田地租支付)和私办(私人捐资兴办)两种形式。
(三)冬学
冬学原本是私人或宗族设立的一种学校,开办于农闲的冬季,起源较早。南宋陆游曾赋诗描绘过冬学的情形。明太祖倡办社学,但地方官吏多以办社学之名进行敲诈勒索,为此,洪武十三年曾一度废止社学,只设冬学。《皇明制书》记载:“今后民间子弟,许令有德之人,不拘所在,又不拘弟子名数,每年十月初开学,至腊月终罢。”冬学曾作为一种适应农时变化的灵活办学形式长期存在,成为正规蒙学教育的一种补充。
四、蒙学的师资
蒙师在蒙学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由当时的知识分子担任。蒙师的身份具有多样性,包括官员、学者、隐士、乡间知识分子。普通蒙师的身份是十分低微的。韩愈在《师说》中曾说:“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可见蒙师历来不受人重视。再者,蒙师的收入极少,大多生活贫寒。很多蒙师是当地的穷秀才,“潦倒青衫”是他们的真实写照,他们窘迫的生活境况在清代诗歌中多有记载。
郑板桥早年家贫也当过蒙师,曾作诗自嘲:“教馆原来是下流,傍人门户过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而今幸作青云客,遮却当年一半羞。”《都门竹枝词》描述蒙师的贫寒生活:“三两言明按月支,支来两月便迟迟。束脩漂了随君便,再请旁人做老师。”光绪年间李森庐教读谋生,某年逼岁除,不能归,寄其妻诗曰:“我命从来实可怜,一双赤手砚为田。今年恰似逢干旱,只半收成莫怨天。”蒙师生活之困穷可见一斑。
五、蒙学教材
蒙学教材是蒙学训导蒙童所使用的文本。《汉书·艺文志》记载:“《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从这里可以看出,《史籀篇》是周时太史用来教授蒙童的教材,也是我国最早见于著录的字书。我国蒙学的经典教材主要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声律启蒙》等。
一般认为,《三字经》的作者是宋代末年的王应麟。王氏一生关注蒙学教育,除了《三字经》之外,还著有《蒙训》《小学绀珠》《小学封咏》《姓氏急就篇》等。该书篇幅不长,共1200个字,但内容丰富,用三言短句的形式向童蒙讲述天文、地理、时节、方位、植物、动物、伦理、典籍、历史,甚至还包括一些重视学习的历史人物的故事,充分反映了作者注重教育的思想。书中对训蒙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凡训蒙,须讲究。祥训诂,明句读。”
《百家姓》产生于宋代。该书四字一句,共472个字,有408个单姓,30个复姓。因为只是收录姓氏,内容上没有什么深奥之处,读起来郎朗上口,此外,《百家姓》很方便蒙童识字,故而一直流传不衰。
《梁书·周兴嗣传》记载:“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这就是《千字文》的来历。该书每四字一句,全书共二百五十句,一千字。《千字文》是我国经典蒙学读物“三、百、千”中出现最早的一部。
《弟子规》是清代秀才李毓秀所作,是他根据自己的实际教学经验,吸取了《论语》《礼记》《仪礼》等书的内容编纂而成。此书原名《训蒙篇》,后经贾有仁修改之后,改名为《弟子规》。全书以《论语·学而》第六条:“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总纲目,具体列举了为人处事、待人接物、修身养性以及学习读书等各方面的要求。全书内容就如题目“弟子规”所揭示的一样,是童蒙弟子的行为规范。该书三字一句,每句押韵,共360句,1080句。因其通俗流畅,编成以来广为流传,影响颇大。即使是在今日,很多幼儿园、小学也将之运用到儿童的教育中。
《声律启蒙》,又称《声律启蒙撮要》,作者是清代康熙年间进士车万育。此书是学习声韵和对仗的蒙学读物。全书按韵部排列,内容包罗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方面的虚实应对。“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蒙童能从中得到音韵、词汇、修辞等方面的训练。
总体而言,我们古代的蒙学教材涵盖了天文、地理知识、历史、社会等不同方面的知识。蒙学教材的编排必须要符合蒙童的需要,因此蒙学教材不仅具有时代性,还存在一定的历史传承性。
此外,家训和杂字作为蒙学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值得学者的重视。
家训,又称家规、家范、诫子书、家诫、庭诰、庭戒等。从汉代开始就有明确的“家训”著作,如东方朔的《诫子书》、班昭的《女诫》等。历史上,最早把“家训”二字作为一个名词使用的是蔡邕。《后汉书·边让传》记载,蔡邕在向何进推荐贤士边让时,说他“髫龇夙孤,不尽家训”。这里的家训偏重于行为戒律。已知最早使用“家训”一词命名的文献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有文可据的第一部家训总集是北宋孙颀编纂的《古今家诫》。此书虽已亡佚,但其内容可以从苏辙为此书作的序中大致了解:“太长少卿长沙孙公景修,少孤而教于母。母贤,能就其业。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为《贤母录》,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诫》,得四十九人,以示辄曰:‘古有为是书者,以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为此,合众父母之心,以遗天下之人,庶几有益乎?’”到了南宋年间,刘清之编纂了规模更大的家训总集《戒子通录》,后来被收录到《四库全书》之中。今人选编合集较多,有周秀才《中国历代家训大观》、包东波《中国历代名人家训精萃》、王玉波《中国古代家训》、李茂序《中国传世家训》等,对此类文献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家训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家规式。此类家训或是作者总结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诫子孙,或是总结本族内历代圣贤事迹,加上先圣贤语以此来记录本家的辉煌和训诫子孙。如颜之推《颜氏家训》、柳玼《柳玼家训》、黄庭坚《家诫》、陆游《放翁家训》、袁衷《庭帷杂录》、袁黄《了凡四训》、朱柏庐《朱子治家格言》等。另外一种是家书式。此类家训大多是针对特定的人或者是特定的事而作,言辞真切。如东方朔《诫子书》、诸葛亮《诫子书》、羊祜《诫子书》、李世民《帝范》、范质《诫从子诗》、陈栎《与子勋书》、周怡《示儿书》、张履祥《张杨园训子语》等等。
从文体上看,家训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散文,行文灵活,少者有几百字,多者上万字。内容繁多者,大多分条目来编排,如袁黄《了凡四训》分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二是诗歌,如元稹为《白氏长庆集》作的序文中说:“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三是格言,句式整齐押韵,读起来琅琅上口,如朱柏庐《朱子治家格言》等。
杂字,是一种字书。《隋书·经籍志》中就著录有多种杂字,如魏掖庭右丞周氏的《杂字解诂》四卷,后汉太子中庶郭显卿的《杂字指》一卷,密州行参军李少通的《杂字要》三卷等,但皆已亡佚。杂字从宋代开始兴盛,但大多未知何人所作。陆游《秋日郊居》诗云:“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作者在自注中说:“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目前所说的杂字,是一种汇集某类文字,编排成形式整齐,有些还押韵的一种字书。
杂字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蒙学读物,对蒙童的识字教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当时的那些“下层人民”的子弟来说。黄震在《黄氏日抄》中记述了当时流行的杂字书:“往岁尝过村学堂,见为之师者授村童,书名《小杂字》,句必四句,皆器物名,而字多隐僻,义理无关,余窃鄙之,然本其所由作,特以识器物之名,于世尚为用。”
除了少数比较特殊的杂字书之外,大多数杂字书没有编者姓名,不知编撰年代,历代书目也很少收录。张志公《语文教育初探》把杂字分成了四类。一是分类词汇。此类书按类编排,以词为主,并不连属成文,也不编成韵语,如《俗务要名林》。二是分类韵语。大多按类编排,但大都是四言或六言韵语,如《鳌头备用杂字元龟》。三是分类杂言。此类书也是按类编排,但是二言、三言、四言、六言交错运用,也不是全都押韵,如《群珠杂字》。四是杂字韵文。此类书往往具有针对性,全书一贯,连属成文,收字不多,不分类,都是用四言、五言、六言的韵语,如《山东庄农日用杂字》。徐梓在《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中把杂字分成了三类:一是各言杂字,从2字到10字几乎各言杂字都有,如《三言杂字》《四言杂字》《五言杂字》《七言杂字》《十字各言杂字》等。二是各类杂字,如《益幼杂字》《必须杂字》《庄农杂字》等等。三是各地杂字,这一类有着强烈的地域色彩,如《山东庄农日用杂字》等。
著名学者吴伯萧在记起儿时读过的《日用杂字》时,给予了高度评价:“这里边有不少耕作技术方面的经验,这些经验显然是老农经过多年积累得来的。这些地方不仅教人识字,也教人学做农活,《杂字》成为教科书了。以后写间苗,写养蚕,写麦收,写打场。一桩一桩都写得很真实,没有渲染,没有夸张,读了使人感到一个字像一钉一铆,结结实实,很有用处。”
结语
蒙学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着“蒙以养正”或“养正于蒙”的理念,蒙学旨在开发蒙童的智慧和修养,使其符合时代的要求。我国古代长期的蒙学发展留下了丰富的基础教育的方法、理念和资料文献,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