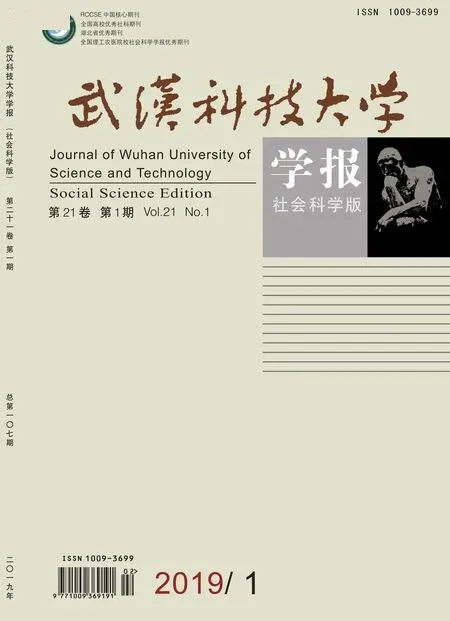戈夫曼、全控机构与自我分析
——兼论精神病人的调适与抗争
王 晴 锋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以拟剧、框架和博弈等不同视角分析面对面人际互动,自我是贯穿于戈夫曼社会学的重要主题,它从未被放弃或忽视,即使在探讨公共场所的行为时,戈夫曼也关注不同的“自我圈”或“自我的领地”[1]242。在戈夫曼那里,社会性的自我既在情境中呈现,亦在情境中形成并被形塑。在《收容所:论精神病人与其他被收容者的社会情境》(Asylums:EssaysontheSocialSituationofMentalPatientsandotherInmates,下文简称《收容所》)一书中,戈夫曼探讨了精神病人如何体验制度化的生活世界,他对精神病人世界的分析包含了关于自我的重要思想。确切地说,《收容所》的主要内涵是以精神病院为例阐释全控机构的观念并论述自我的结构,尤其是通过自我遭羞辱的过程阐述自我依存的社会条件,而在常态的公民社会里则很难观察到这些条件。戈夫曼以“制度性的方法研究自我”[2]127,在《收容所》的导言中,他明确指出其意图是“提出一种关于自我结构的社会学阐释”[2]xiii。戈夫曼不仅聚焦于全控机构中的自我体验,而且也强调个体的能动性,他之所以关注全控机构中的自我,是因为他试图探讨互动秩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供抵制与反抗[3]。《收容所》一书的出版对美国的公共政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推动了20世纪70、80年代美国乃至西方社会对精神病治疗的去机构化改革浪潮。本文主要论述戈夫曼如何在全控机构的思想框架下对自我进行情境社会学的剖析。
一、全控机构与自我的情境分析
1955年,戈夫曼受命于美国的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对精神病人进行观察和研究,搬入位于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附近的公寓,考虑到戈夫曼的研究计划,医院的管理层赋予他担任康复部主任助理的角色,使他有充分的权限观察病人的日常生活。戈夫曼对精神病人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参与式观察,搜集了大量的生活资料。戈夫曼认为,自我是情境的产物,只有将它置于与之相关的社会情境才能充分理解,同时,自我又是神圣的客体,互动参与者运用规避仪式与他人保持仪式性距离,避免情境失当或隐私的话题,并且不侵犯围绕在个体周围如齐美尔所说的“理想领域”[4]62。戈夫曼关于自我的领地的阐述,可以被视为他分析全控机构中自我的理论基础,他主要关注情境性的领地和自我中心主义的领地。包围在个体四周的空间是个人空间,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他人进入该空间会令个体产生被侵犯感,他可能会表现出不悦甚至导致情境撤离。个体可以通过保持距离感,以远离被他人污染的情境。个人空间的合法性宣称会根据情境属性产生变化,诸如人群密度、靠近者的意图、固定的坐席设备和社交场合特征等,并且在同一情境中,合法性宣称也会持续发生变化。因此,个人空间并不是永久恒定的宣称,它是一种暂时的、情境性的保留区或禁区。通过分析自我的情境性和自我中心的禁区,戈夫曼进而探讨个体积极认同的、关于自我特性的主观感受。在戈夫曼看来,实质性的问题并不是个体的禁区是否得到维持、共享抑或放弃,而是个体在其宣称的特性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尤其是保持个体自决的能动性。
全控机构是指这样一种场域:“它是一个居住和工作之地,里面有大量遭遇类似情境的个体,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外部社会切断关系,共同过着一种封闭的、被形式化管理的生活。”[2]xiii根据与外部世界之间不同的封闭性程度,全控机构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封闭、强制性的全控机构,包括监狱、精神病院等,它们设有不可逾越的物理障碍,诸如铁丝网、高墙等,机构内部的阶序等级是固化的,通常不存在晋升的渠道,社会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被收容者和管理者之间的身份判然分明,且不可逾越;第二类是相对开放性的全控机构,包括基布兹(kibbutz,以色列的集体农场)、伐木场、商船队以及宗教性机构等,在此类机构中,个体可以相对自由、随意地进入和离开,他们的社会地位虽然具有阶序性,但存在流动的可能性;第三类是处于开放性和封闭性全控机构之间的类别,包括军队、寺院、修道院、寄宿学校等。不同全控机构的开放性或封闭性特征之间构成一个连续统。全控机构对外公开宣称的目的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以机构本身为目的,起着社会隔离和控制的作用;第二,实用主义目的,主要是经济或军事意图;第三,改造和教育[5]。不少全控机构的目标是混合式的,并且随着时间而改变。由于不同的标准会产生不同的分类,因此也可以根据全控机构的开放或封闭程度和公开宣称的官方目标将全控机构进行交互分类。全控机构的“全控”或“总体性”涵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
第一,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同样的地方和同一个权威下进行。第二,成员日常活动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在大量他人的密切陪伴下开展的,这些人都以同样的方式被对待,并被要求共同做相同的事情。第三,日常活动的所有阶段都被紧凑地安排,在预先规定好的某个时间,一项活动将引向下一项活动,全部活动序列由来自上级的系统设定,该系统具有明确、正式的支配系统以及行政官僚体系。第四,各种强制执行的活动被整合到统一的理性规划之中,以有计划地实现机构的正式目标。[2]6
大体而言,戈夫曼从两条路径来分析全控机构。第一条路径是从社会组织研究的视角切入,主要关注全控机构独特的组织特性。戈夫曼认为,社会组织的核心要素是“声索”或“宣称”,也就是拥有、控制、使用或者处置所欲求的对象或状态的权利[6]。全控机构作为“一种社会混杂物,部分是居住共同体,部分是正式组织”[2]12,因此,它蕴含着特殊的社会学涵义,这是戈夫曼关注全控机构的重要原因。第二条路径是以情境性的视角分析自我。戈夫曼一直关注着个体的自我问题,在他看来,改造个体的强制性社会设置是对自我施行各种自然试验的场域,这是戈夫曼关注全控机构的另一个缘由。确切地说,戈夫曼是从情境社会学的视角分析机构化的自我:
戈夫曼的互动主义立场是对被收容者自我的制度设置进行社会学评估,而不是对被收容者本人对当下环境的感知进行的调查。……对自我的羞辱并不总是与被收容者真实经历的窘迫、沮丧和痛苦等感受相一致。换句话说,戈夫曼呈现的并非关于被收容者经历的现象学,而是通过面对面行为表现出来的制度安排描绘被收容者的观点,并进行社会学转译。戈夫曼试图描述的不是病人的经验,而是他们所处的情境。[7]
从表面上看,戈夫曼是以“被收容者的世界”“机构人员的世界”这样二元对立的范畴进行分析,但实质上,其内在的分析脉络是通过组织与自我这两条线索展开的。戈夫曼的全控机构模型是以圣伊丽莎白医院为原型的。作为权威系统,精神病院迫使病人承认自己患有精神疾病并接受严格的治疗与规训,它侵入并摧毁个体原有的自我,形塑个体的思维方式与言行举止。被收容者的基本生活和需要都是被事先计划好的,对工作的激励也缺乏外部世界具有的那种结构性意义。他们被分配的工作大多是非技术性的、低效率的和令人厌烦的,机构可能象征性地提供定量的烟草或其他小礼物作为报酬。当需要极其繁重的劳动时,机构不是施以报酬,而是以体罚作为威胁。全控机构还会出现某种奴役现象,使被收容者的自我感和人格占有状态完全疏离于他的能力,他们变得意志消沉、士气低落。在这种压迫性和高度制度化的情境里,病人的自我以及他对自我和他人的评判都将发生序列性变化。与全控机构的制度化世界相对应的是家庭生活或公民社会,也就是说,全控机构与外部社会的基本设置,尤其是家庭制度,是冰火难容的。家庭生活不同于隐居和遁世,它又与机构化的“批量生活”(batch living)形成鲜明对照,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全控机构内的被收容者无法维持家庭式生活方式,而机构人员由于维持着公民社会的家庭关系,他们能够逃离全控机构而与外部的共同体整合在一起。
通过研究精神病人的生活世界,戈夫曼质疑精神病学方法和实践的科学有效性,认为精神病学家关于精神病行为的诊断并不是基于神经病学、生物学或生理学等科学解释,他们缺乏坚实的事实根据,唯一凭借的是对个体的外在行为进行观察。在戈夫曼看来,精神病学对精神错乱的诊断显得非常主观和含糊,其治疗是自欺欺人的,与其说是对疾病的治疗不如说是对人身的监控。正因如此,戈夫曼称精神病医生为“拙劣的修补匠”,精神病学则是“瞎忙的行业”[2]321。戈夫曼关于全控机构的阐述实质上是对制度结构、社会控制和自我之间关系的探讨。
二、自我的机构化:漂白、剥夺与改造
“强制性幼稚症”(infantilism)是被迫进入全控机构的人们遭遇的集体命运。一旦进入全控机构,个体就被迫开始羞辱的历程,他遭受“一系列对自我的贬抑、降级、侮辱和亵渎”[2]14。全控机构对个体的公民自我进行强制剥离,切断与外部世界的经验联系和支持,尤其是剥夺家庭生活提供的各种稳定的社会设置。
被收容者与外部世界的隔离是削弱自我的第一步,原先的角色安排被完全瓦解,个体处于角色剥离的状态,这种剥离事实上宣判了公民身份的死亡[2]16。机构的准入程序可以被概括为“脱下”、“裸露”和“再穿上”三个步骤,具体包括填写履历、照相、称重、指纹识别、分配编号、搜身、列出个人物品清单进行储存、脱衣、淋浴、消毒、剪发、分发制服、规则训示和房间分配等。编码化的命名与称呼系统意味着匿名化、均质化和无隐私,它类似于格式化之后重新程序化,个体被塑造和编码成能被送入规训机构的客体,能够通过例行的操作对其实现有序的管理。除了官方的准入程序与顺从测试之外,新成员还会经历其他“欢迎仪式”,这是一种非人化的剥离过程,经由这种“通过仪式”,新来者认识到他在这个附属性群体里的社会位置。
所有物的剥夺是自我机构化的重要步骤,因为个体在其所有物中投射和赋予了自我的感受。个人所有物(包括私人空间)是自我及其自主性的延伸,它与自我之间存在特殊的联系,个体需要通过这些具有个性的支持物来支持和整饰自我。例如,个体在进行面子管理时需要一种“身份套装”(identity kit)[2]20,它们是自我的重要构成。在通常情况下,日常生活的社会设置必须保证必要的自我支持物,诸如自主性、隐私、职业身份和资源控制等。但是这些身份的装备(如衣物、化妆品、梳洗沐浴用具等)与外表整饰的服务(如美容、理发等)在全控机构中是完全缺失的,个体无法在他人面前呈现出惯常的、完整的形象。通过各种安排与设置,机构使个体最大程度地忽略和缩减原先的自我认同。所有与个人身份有关的事物都被清除、遗忘,原先的名字也被废除,取而代之以编号。在精神病院里,连用剩的铅笔都要归还之后才能换取新的,甚至房间也会定期更换。对个体而言,被迫使用的机构所有物是陌生的、疏离的和异质的,他们无法在这些不断更新的事物上投射自我、也无法赋予其心理上的依附感,即使个体投射了依恋之情,它们也会马上被置换。而且,机构分发的物品通常粗制滥造、质量低劣且不合身,最主要的是它们无法体现个体性差异:所有人都使用一模一样的标准物品。同时,由于无法保存属于自己的所有物,并且一个人使用的物品同时也被他人使用,因而它无法确保避免遭受他人的社会性污染。总之,在全控机构里,个体的所有物被彻底剥夺,从而断绝心理上的依恋、认同和移情的可能性,它使自我变得孤苦伶仃、无所依靠。全控机构里呈现的是赤裸裸的、被剥离得一丝不挂的自我,它被抛置于荒蛮之地。
全控机构以上帝、国家、正义、治疗以及社会关怀的名义剥夺了个体赖以支持自我的一切物理性和社会性要素,自我遭受贬黜、降格、羞辱、亵渎与玷污。全控机构还采取物理性的强迫手段,诸如殴打、休克疗法、对精神病人施行外科手术以及各种永久性的身体烙印作为污名标记等,各种类型的损容、毁形措施使被收容者处于无法保证身体整全的环境。各种形式的损形、污辱等使被收容者无法确证即时在场或情境中的事物之象征性意义,无法巩固和支撑其原先的自我观念,从而实现机构对个体自我进行原始而直接的攻击[2]35。在精神病院里,蔑视与违抗还被视为精神病的症状而严加惩治。全控机构无视仪式性自我的需要,强制开启对自我的改造历程,自我的建立或摧毁成为一场无耻的游戏。
对自我进行的间接羞辱则是破坏个体行动者与其行为之间的正常关系。对这种关系的第一种攻击类型是“链环效应”,即施行者激发被收容者的防御性反应,并将这种反应作为下一次攻击的目标[2]36。而个体对攻击自我的防御性反应被瓦解在情境之中,他无法通过保持与羞辱性情境之间的距离来保护自己。通过链环化过程,被收容者的情境反应消解于情境本身,个体的顺从模式是这种链环效应之明证。在公民社会里,当个体面对冒犯和有辱其自我的情境时,他会为顾全脸面而产生应对性的表达方式,如愠怒、违抗、低声嘀咕、蔑视、讽刺和嘲笑等。但在全控机构里,对羞辱性要求作出自我保护式表达将遭致惩罚。“去区隔化”是链环效应的另一个例子。在公民社会里,由于受众和角色扮演的多样性,个体在某个活动的物理场景中作出的关于自我的公开宣称和潜在主张通常无法验证他在其他场景中的行为。而全控机构的生活领域是去区隔化的,被收容者在某个活动场景中的行为能够评价和检验他在另一种情境里的行为。对被收容者作为行动者身份的第二种攻击类型是“严密管控”和“极权统治”。个体的活动轨迹受到机构人员的管控与评判,他的生活受到各种渗透和约束,每一项具体规定都剥夺了个体在需求与目标之间有效达成平衡的机会。这种严格组织化的社会控制吞噬了个体行动的自主性。全控机构剥夺了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执行能力,某些原本可以自主进行的微不足道的活动,如吸烟、上厕所、打电话、寄钱、写信等,个体也必须提出请求才能被许可。这种约束不仅使个体处于服从的、哀求的卑微角色,还使机构人员能“截取”其行动路线。机构对自我的贬抑使个体不得不调适关于外表、行为和情境的独特表达性习语。在戈夫曼看来,全控机构“就像精修学校,但它徒有‘教养’却毫不‘优雅’”[2]41-42。
不同类型的全控机构对自我的攻击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诸如宗教机构对自我的环境安排是得到认可的,苦修者更多的是自我禁欲、克制;集中营或监狱运用强制性的羞辱手段,囚犯通常不会接受或参与对自我施加的毁灭;其他全控机构通过各种理由使约束和苦行合理化,诸如卫生、生命责任、安全等。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全控机构里,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自我的缩减或剥夺现象,全控机构对被收容者的自我改造是决定性的,被收容者明显感到个体的失能以及自我旨趣与机构目标之间的冲突。在精神病院的管理人员看来,精神病人无法充分控制自我,他们是有缺陷的人,而一系列制度化实践则确保这些精神病人确实是病态的,需要加以治疗和规训。与此同时,医护人员和精神病学家扮演着充满内在矛盾的角色,它们亦处于执行规章制度和履行行政长官命令的紧张关系之中。为此,他们区分了“以人为对象的工作”和“以物为对象的工作”。前者以人性的标准对待精神病人,帮助其进行康复治疗;后者将精神病人视为如同流水生产线上的产品,它以组织效率为首要考量。结果,他们往往有意混淆对精神病人的监控与治疗,比如将单独监禁称为“建设性的沉思冥想”[2]82。
三、精神病人的道德历程
戈夫曼认为,“道德历程”是个体的自我以及用以评判自身和他人所必须的框架,“历程”这个概念可以相对客观地考察相对主观的议题。精神病人经历了从家庭世界到精神病院然后再回到公民社会的过程,亦即精神病人的治疗历程可以分为住院前病人、住院病人和出院病人三个阶段。这种分类方式类似于阿诺德·范·杰内普(Arnold Van Gennep)将通过仪式分成“隔离-过渡-重融”,但对戈夫曼而言,两者的理想效果不可同日而语。戈夫曼在《收容所》里重点探讨前两个阶段,而他的《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则可被视为对出院后阶段的进一步论述,其阐述对象是包括精神病人在内的所有污名携带者。
在入院之前,精神病人就已经开启其道德历程。在重要他人(important others)的怀疑下,个体遭遇一种“离间联盟”,他经历了对自我的“分裂性重估”,出现自言自语、幻听、习得性无力感等症状,并感觉被最亲近的人背叛、欺骗,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会转而寻求与“行业代理人”(如精神病学家、社工、律师、警察等)进行接触,后者的判断与共谋直接影响他是否进入精神病院接受机构化治疗。对住院前病人而言,进入精神病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自我压力,因为精神病院对个体的期待和要求相对较少。在这种意义上,全控机构也具有支持性和保护性的一面。然而,自愿进入精神病院与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之间的界限往往很模糊,病人在几乎被剥夺了一切之后,他们最终以冰冷的精神病房为归宿。精神病人的机构化和再社会化表明,自我“并非一座防卫森严的堡垒要塞”,而是很容易被攻占和侵入的“开放小城”[2]165。因此,自我虽然存在于社会系统为其成员确立的各种安排之中,但是“这种特殊类型的制度设置对它所构成的自我并没有提供太多的支持”[2]168。
被全控机构捕获之后,个体的道德生涯经历了急剧转变。个体由于长期被收容而弱化了与机构外部之间的联系,他不仅丧失了公民社会中自我认同的各种表意性手段,而且还被迫认同那些在公民社会里可能会竭力与之保持距离的人。受到强迫性关系的污损,被收容者也无法抵制机构人员察看或探悉他们的底细。全控机构采取各种措施维持机构内部的秩序,它不仅采取精神性的管控,也采取物理惩戒与威慑,以增强机构对身体的支配权力。诸如,咬人者可能被拔光牙齿,乱交的女性可能被切除子宫,习惯好斗的人则被施行脑叶切断术[2]79。全控机构无限制地扩张并侵占个人的领地,改变个体自我管控的内在倾向,不断蚕食个人自我信息保护的权利。在戈夫曼看来,全控机构重塑的自我完全不同于公民社会的自我,因此,它并非为了使个体今后能更好地适应社会、重新过上市民生活。
与精神病人的自我之沉浮相关的还包括病人对亲密关系者忠诚度的感知和在他人面前呈现自我的防护或撤离策略。由于意识到自己生活在无法控制的各种暴露和变化不定的条件下,包括自我之构成性装备和地位的转变以及风险的不断变化,这种道德经历使个体无法继续维持固定和完整的自我观。但是,个体一旦适应和接受精神病院的制度化设置,他会配合医院的矫治措施,并且发现道德地位和自我状态的萎缩并没有想象的那样严重,因为毕竟不会遭致法律的制裁或进一步降低身份,也不会将他驱逐出病人共同体,他也没有更多的声誉和权利可供剥夺。在这种情况下,自我的降级、贬抑和重构不再被赋予过多的重要性。自我成为一种外在性,它能够被给予和剥夺,被建构、丧失和重建。精神病人认识到自己被社会和机构定义为缺乏切实可行的独立自我,在这种道德冷漠的境遇里,自我的型塑过程如同游戏一般,这进一步导致去道德化的结果,产生道德的松弛和疲乏。在戈夫曼看来,精神病人的这种道德历程具有独特的作用:
它能够表明一种可能性,即当脱去旧有自我的衣物时——或者撕裂这层伪装时——个体不必寻找新的衣袍或者在新的观众面前畏葸退缩。相反,他可以学习,至少暂时地,如何当着所有群体的面践行毫无廉耻之心的非道德艺术。[2]169
四、次级调适与自我抗争
戈夫曼论述了个体对全控机构的自我剥离进行的抵制与反抗。精神病人并非绝望无助地在全控机构中苟延残喘,或完全被动地任由操控。当他们为了得到信件或香烟而表现得恭谨温驯时,他们无法从这种不对等的权力结构中获得或维持自尊,因此,他们经常通过各种手段绕过机构人员获取他们想要的事物。病人对机构性羞辱的应对策略是采取各种形式的次级调适,它们构成了全控机构的“隐秘生活”(underlife)。次级调适是个体设法应付机构对个体行为施加的各种压制与限制,它包括各种权宜之计、废物利用、动用外部联系、“自由之地”的活动等。次级调适使被收容者获得违禁的满足,或通过违禁的手段获得特许,但它不会对机构人员直接构成挑战。次级调适向被收容者表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能够自己做主、掌控环境,而不完全是附属物或傀儡。次级调适有时可以成为自我的贮存和寄宿之地,它是灵魂得以驻留于其中的护身符与神圣物[2]55。被收容者除了以一套“机构性隐语”描述他们独特世界里的重要事件之外,还存在各种形式的“捣乱”[2]53,诸如打架、斗殴、酗酒、自杀、赌博、违抗、同性性行为、集体骚乱、逃脱等,这些禁止性活动一旦败露将遭致严惩。机构人员与被收容者之间可能会达成默契,允许被收容者某种形式的捣乱,以发泄对不公正的情境之愤恨与不满。对全控机构而言,捣乱具有重要的安全阀功能,它们赋予刚性、严苛的制度结构以某种柔韧性。同时,它使被收容者群体内部打破原有的身份等级进行接触,促进特权系统内的信息流通。
也就是说,全控机构内部的个体并非完全处于崩溃、失能的存在状态,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试图恢复整合性,创造有限的私人空间,联合抵制不公正待遇。这类似于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cott)所说的“弱者的武器”和“不被统治的艺术”,被收容者以各种细微的方式寻找自主性、反抗权威压制并保存自我。对精神病人而言,他们通过这些姿态拒绝承认机构的理性与功效,反对精神病院对他们作出的心智不健全的判定[1]224。在这种情境中,受害者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他们集体建构一种避免被支配性阶级完全控制的生活和文化,从而撕掉奉承巴结的面具。在这些相对安全的行动空间里,居于支配地位的不再是统治阶级强加的定义和表演[8]。从属群体不仅在行动上进行另一种形式的反抗,如讽刺嘲笑、流言蜚语、偷懒怠工、装糊涂、搞破坏、偷盗和开小差等,也可以在意识形态上进行颠覆与否定。每一种社会机构对其参与者的肉体和灵魂都有一整套不同程度的期待和规范,而参与者会采取各种次级调适拒绝和抵制机构的制度化设置、意识形态及其隐含的为其参与者设计和安排的自我观和生活世界,正是这种隐秘生活使参与者在制度化的机构里获得一定的自由度。隐秘生活表明了,当个体的生存需要被降到最低限度时,他们会如何使生活充实并具体化,藏匿处、输送方式、自由场所、领地、经济与社会交换等都是建构这种生活的基本要求。总之,正式组织存在诸多难以防守的脆弱场域,正是在这些角落里滋生和蔓延着大量次级调适。
被收容者在其道德生涯的不同阶段会运用不同的适应策略。在受辱性制度环境的压力下,被收容者为了保全自我通常采取四种调适手段[2]61-65。第一,情境性撤离。被收容者撤回对周围事物的关注,使互动卷入程度急剧缩减。在精神病学中,这种心理防御机制被称为“退行机制”;在集中营中,它甚至表现为人格解组。情境性撤离通过白日梦、幻想等方式将自身脱离于全控机构。第二,不妥协的底线。被收容者公然拒绝与机构人员合作,故意挑战制度。当对自我身份的攻击和羞辱超出能够容忍的最低限度时,个体会产生不遵从、反击甚至报复。不妥协需要坚定的意志和勇气,它通常是暂时的和初始的反应阶段,并可能转向情境性撤离或其他适应策略。第三,殖民化。被收容者将机构提供的外部世界视为整体,从而建立起稳固的、相对满足的实在。外部世界的经历被用作参照点,以表明机构内生活的适宜性,从而缓解两个世界之间的张力。被收容者理想化地比较全控机构内的生活与外部世界的生活,甚至规划着释放、回归社会之后如何重新得到社会认可。殖民化的被收容者会尽可能地利用有限的设施创造一个自由的共同体。第四,皈依。被收容者从官方或机构人员的立场看待自己,并付诸于实际行动以展现合格的形象。他至少在表面上接受、承认上级的权威,表示洗心革面、悔过自新。皈依者比殖民化者采取更为规训化、道德主义和单向度的策略,其对制度和机构的热情通常受管理人员支配。
上述每一种适应策略都象征着处理家庭世界与制度化世界之间紧张关系的方式。在大多数全控机构里,被收容者通常采取“冷处理”的行动策略,它包含次级调适、皈依、殖民化以及对被收容者群体的忠诚等,这些行动策略使被收容者最大程度地挣脱生理和心理上的伤害。
然而,戈夫曼并没有将精神病人的生活世界浪漫化,他们的隐秘生活也存在敲诈勒索等阴暗面。而且对精神病学家而言,病人的次级调适是不存在的,它们往往被视为潜在的疾病之表征或是康复的迹象。也就是说,这些被收容者采取保全自我的理性行为却被精神病院的管理者理解为精神疾病的症状,而精神病医院治疗和纠正的正是这些由于全控机构对病人自我的攻击而导致的行为症状。被收容者的任何保全自我和身份的理性企图都进一步肯定了精神病院对被收容者的最初诊断。全控机构试图破坏或侵蚀的行动正是那些在公民社会中起着确证行动者掌控自我之作用的行为,它们原本能够表明个体是自决、自主和自由的行动者。
戈夫曼的研究表明,即使全控机构也存在着自主性的领域,尽管支配不可避免,但权威仍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挑战。他试图从广义上探讨社会联结的本质,个体通过次级调适在自身和机构/他人假定的身份之间保持距离,因此,自我也会对互动的形态产生制约。安妮·罗尔斯(Anne Rawls)认为,自我从全控机构中获得的特许并非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社会的构成》(TheConstitutionofSociety,1984)中对戈夫曼的解读那样是有能力的行动者通过日常生活的抵制而抵消严酷的纪律。在戈夫曼关于全控机构的论述中,纪律、规则和惯例并非是首要的,全控机构的日常活动违反了互动的基本准则,并进而破坏意图性行动和社会性自我,而这一切通过隐秘生活得到平衡。它并非取决于“有能力的行动者”抵抗制度性约束,而是互动秩序凭借自身的力量和方式进行抵制[3]。
五、结语
全控机构是戈夫曼对自我进行情境分析的重要场域,他描述了全控机构中生活世界的过程和结构,探讨了精神病人的日常体验、住院治疗的主体经历以及机构化自我。对戈夫曼而言,全控机构是一种理想类型,其重要特征是对自我实施机构化的重塑。通过与外部世界之间不可渗透的边界,全控机构消解了日常生活中原本分离的不同领域,剥离了个体在外部世界享有的各种身份属性,使行动者无法向他人和自身表明充分的能动性,从而威胁整个互动领域的实践形式。这是全控机构的压制性本质,它只剩下孤零、赤裸、无依无靠的自我在那里瑟瑟发抖;而在公民社会里,自我“能够在自由意志的选择下进行重新创造”[4]237。从整体上而言,戈夫曼对精神病人的同情和对精神病学的愤怒源自他对自我的捍卫[9]。在戈夫曼看来,精神病院的首要功能并非是治疗性的,而是管控性的。戈夫曼关于遵从和越轨行为的研究表明,症状本身并不是真正能够反映精神疾病的指标。“病态行为”并非精神疾病之产物,而是个体与即时性情境之间的社会距离造成的。精神病院制度化的意外后果是产生各种形式的次级调适,它也是关于社会控制与集体抵抗的阐述。精神病人的道德历程和次级调适表明,个体的自我形象与社会结构之间是相互形塑的。
全控机构是改造个体的强制性场所,戈夫曼对精神病人的机构性体验和对自我羞辱过程的分析表明机构能强迫性地改变自我,同时,倘若个体想保持作为公民的自我,他必须得到基本社会设置的保障。在公民社会的某些场域,也可以观察到全控机构的某些特征,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全控机构带来的压制具有普遍性,它并非仅局限于全控机构的物理场域之内。正因如此,戈夫曼的《收容所》不仅是关于场所(美国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的民族志,也是关于“全控机构”这一概念的民族志[10],这也体现了戈夫曼从经验到理论、从具体到普遍的学术旨趣。本文最后强调两点:第一,戈夫曼是站在病人的立场来描述精神病院的生活,因此他的视角可能“呈现偏向性的观点”[2]x;第二,诚如戈夫曼指出的,这种探讨自我之命运的符号-互动框架与以压力为核心的传统生理-心理框架之间存在区别[2]47。自我的贬抑或缩减包含着个体强烈的心理压力,但是对于厌世或罪孽感深重的个体而言,自我的羞辱和贬抑反而可能带来心理上的愉悦与解脱。
——以离婚纠纷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