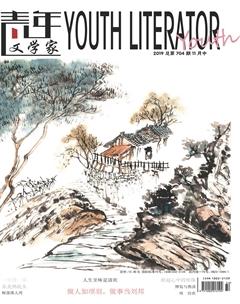《霸王别姬》:病与因
王依澜
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我们真的了解程蝶衣的心理吗?
我们只看到他的扭曲和病态,也许还嗤笑他对段小楼的迷恋,但是他病态人格的形成在前半部电影中大有伏笔。
程蝶衣的灵魂残缺不全,甚至是畸形的,但是能说这不美吗?很美,病态的东西总有一种邪美。正是因为它本身的不合常理和亚健康,我们才会有被深深吸引的情感。
程蝶衣,太苦了。身体上的创伤无疑加剧了精神上的创伤。
幼时被年轻的母亲送入梨园,那清秀的模样像水嫩嫩的芽尖。因为他的手长畸形,所以这是第一道精神创伤,由心爱的母亲亲自在脆弱的小心脏上划了一条泛着黑紫色脓血的伤--用肮脏的菜刀泛着无情的冷光。
我想这一定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痛的不只是流血的伤口,那双水汪汪的眼也蓄满了痛。这是把世界华美的袍翻过来时,看到背后密密麻麻且丑陋的虱子时的厌恶和无助。虱子爬满了他的一身,他之前穿的一直是一件单纯而华美的袍,后来虱子穿破薄如蝉翼的幻想来到他的身上,直透肌肤,最后叮咬他的心臟。
我在孩提时期也有过类似的感情。不,我没有被切断手指。但是那种细细的精神虐待,那种细若虫蝇的小伤口,我深有体会。所以每逢遇到类似的事,哪怕是电影中的事,也会在我心中引起共鸣,看一眼就知道。
程蝶衣是如此后知后觉,也许痛苦给他自己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帝国,一个用五彩斑斓的丝绒线编织的世界,每根线上有小铃铛,敏感的心灵会随着一点动静而满是银铃声。最后,这个华丽得像他自己的唱腔一样的世界,这个精美绝伦的世界,连他自己也找不到出口。他被自己的意念为逃避痛苦而制造缠绕的绒线绕晕。就再也走不出来了。
“我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是他的底线,也许折射了他灵魂的中流砥柱,是精神的芯柱。强行改变这句话,扭住他的舌头,将它绕成“我本是女娇娥”时的形状,相当于将他的底线连根拔起。他们自以为在教他唱戏,实际上是在割断他的心弦。从此之后他就不再是他自己了,他的灵魂开始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虞姬,另一部分才是本我。他不知道他像两片不对称的布片拼成的娃娃,这种娃娃连心的颜色都不一样。
后面的事,张公公完全的让他困在了那五彩的绒线的世界里。本来,如果世界对他友善一点,他是可以寻着友善的阳光找到出口的。但是,如果不封上出口的话,那太痛苦了,那太脏了,面对现实太艰难。于是他决定封上最后的一个出口,从此之后,他就彻底地成了那个浓妆艳抹,巧笑倩兮的虞姬。
一双手悄悄地伸到他的背后,又扯下了华美的袍,袍的背面——这次是硕大的毒虫。当初母亲切指时所见的虱,会使他痛痒。而这一次,只是疼痛蔓延至无边的深渊。疯和神志不清的表现未必要行为怪诞,言语痴傻;疯和神志不清也可以是心灵的核聚变,被肌肤裹住在体内爆炸,呛人的硝烟只是眼中的泪而已。最后在肌肤下的废墟是根本就看不到的,根本就看不到。
我们对别人的痛苦很难有想象能力。
我们对别人的痛苦时常呈嘲笑态度,对自己的痛苦却抱以十足的同情。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厚颜无耻。是否可以理解为自欺欺人。 是否可以理解为矫揉造作。我曾听过一个作家说:“我的心灵曾经历过原子弹爆炸。而在我心中的原子弹爆炸,血肉模糊的时候,却没人知道我在经历什么。”
行尸走肉一样。每天靠着小小的交际过活,偶尔快乐,偶尔受一下不良情绪的干扰。以思想简单为荣,以深入思考为耻。对周遭变化视若无睹,对伤感的他人视若不见。为自己的错误百口争辩,对他人得理不饶。
如果说什么是最低级的动物,莫不过人罢了。那些飘忽不定的眼神,阴阳怪气的腔调,为达目的所特地呈现的不自然的面部表情。那些莫名其妙的试探。
我们都应该更自然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