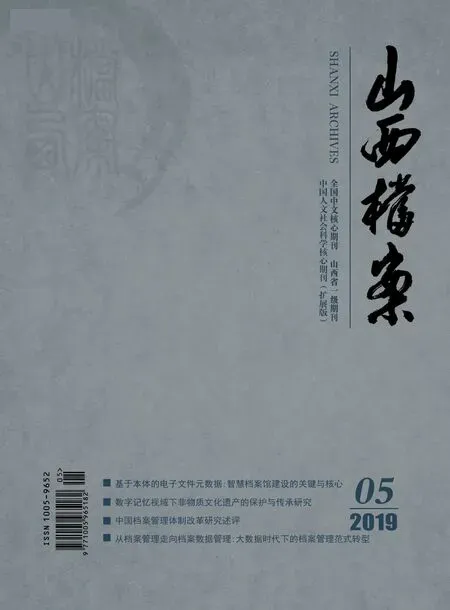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研究⋆
夏海超 何庄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2 )
曾国藩是晚清四大名臣之首,在治学从政治军生涯中,曾国藩花费大量精力致力于公文实践,留下了《讨粤匪檄》《应诏陈言疏》等公文范本名篇,并逐步形成了“义理、经济、考据、辞章”四位一体的理念框架。这八个字分别是对公文主旨、事功性、说理考证和文辞表达的要求。然而,当前研究涉及曾国藩公文的虽不在少数,但这些研究多是围绕公文具体内容分析特定历史事件,或将之作为研究曾国藩文学、理学思想等的底本,即史料学视角的研究,如《“杨萧三谕”与〈讨粤匪檄〉比较论》;少数相关性较高的研究也是集中在曾国藩公文风格上,如《曾国藩治牍批判之道与晚清公文文风革新》,而对于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的内涵是什么的问题尚未真正明确。作为特定社会阶段的产物,一种理念的形成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曾国藩“义理、经济、考据、辞章”四位一体公文写作理念的形成,同样有比较复杂的背景和比较长时间的演变过程。本文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对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从“形成背景”“形成过程”和“是什么”几个角度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
1 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形成背景
1.1 社会背景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交叠,社会矛盾尖锐,民族危机日渐深重。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的形成是这一特定社会背景的产物。一方面,为应对日益沉重的危机,部分有识之士开展了早期 “睁眼看世界”的探索活动,变革图强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曾国藩对晚清公文风气的流弊进行审视和突破,正顺应了这股潮流。另一方面,战争失利、人口激增、国库空虚、地方武装崛起等使得中央军权、财权不断旁落,清政府的控制力被不断削弱,原本铁桶一块的统治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裂痕,新尝试从此不再容易遭到扼杀,新思想的传播和交流也变得活跃。不得不说,曾国藩在公文写作理念上的革新,与这一变化有着密切联系。
1.2 学术思潮
在学术界,礼学兴盛、经世致用精神觉醒、汉宋兼容形成以及古文传统等,与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的形成关系更加直接。
首先,礼学兴盛对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的形成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有清一朝,礼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完成了社会学形态礼学对哲学形态理学的改造,更加注重礼学对具体国家政务和社会事务的阐释和规范,形成“以礼合理”的思维导向。这一转变使得义理的具体指向发生变化,对曾国藩乃至其公文写作理念的形成影响颇深。其次,经世致用精神的觉醒是影响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形成的又一大学术动态。晚清之际,经世致用理念已经较为广泛地觉醒,传统儒学的严格拘囿开始破裂,重道轻艺的理念也逐渐为经世致用、变法图强的理念取代。这一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包括公文在内的各项国家、社会事务。再次,汉宋兼容对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的影响既体现在宋学所暗含的经世致用精神上,又体现在其对汉学考据的关注和批判上。晚清时期,随着汉宋兼容终成定局,两家所秉持的理念——追求义理、注重经济、重视考据也相互融合,共同深刻地影响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的形成。最后,兼容骈散的古文传统也对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唐宋古文运动之后,所谓“古文”与先秦古文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它并不完全否定骈文,而是在自觉融合先秦两汉古文与六朝骈文的基础上,以散体为主,骈体为辅,形成了一种新型古文。这一新型古文不仅在实践上继续兼容骈散,而且在意识上也变得更加主动。从实际情况看,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无疑深受这一变化的影响。
1.3 个人经历
曾国藩“义理、经济、考据、辞章”公文写作理念的形成,还与其独特的人生轨迹紧密相关,其中师友交游和幕府幕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师友交游方面,家学启蒙、从游唐鉴、倭仁和私淑桐城,对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其中,家学启蒙奠定了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中“义理”的最初理念基础,而与唐鉴、倭仁交游,使得曾国藩开始转变理学作为考取功名工具的意识,使其真正用心于治理学,同时也夯实着其公文写作理念中“义理”的坚实基础。正是在唐鉴的引领、倭仁的扶掖下,曾国藩的为文之法乃至为学之术中最根本的“义理”得以奠基,而后通过私淑桐城和对桐城派姚鼐的 “义理、考据、辞章”理论的继承与改造,[1]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公文写作理念。开立幕府、广纳贤才之举对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的深化也具有一定影响。一方面,曾氏幕府幕僚文化程度极高,其中杰出者如李鸿章、吴汝纶、薛福成等,他们在接受曾国藩指导的同时,往往也以他们独具之才情给予曾国藩一定的启示;其二,曾氏幕府中幕僚多是经世之才,专业领域分布广泛,受经世致用思潮影响较深,这与曾国藩在挑选人才时“经济”的标准是分不开的。但这些幕僚往往又给予曾国藩反向激励,能够进一步深化其“经济”理念,并持续作用于包括公文在内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学等各个方面。
2 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的演变
曾国藩“义理、经济、考据、辞章”四位一体公文写作理念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不同时期四者比重具有较大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2.1 第一阶段:义理为核心
该阶段大致为道光中期至道光后期,其主要特征是“义理”占据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的核心位置,其余三者处于附属地位。这一时期,曾国藩公文如奏稿、批牍等几乎没有留存,难以直接从公文实体中探究曾国藩的公文写作理念,但根据《日记》《家书》等档案史料中曾国藩的一些言论,可以对其公文写作理念进行分析。
理学自始至终是曾国藩的立身处世之本,就公文来说,义理是重中之重,经济、考据、辞章则居于次要位置。在《日记》中,曾国藩曾记载了一段向唐鉴讨教“检身之要”的故事,唐鉴言:“学问三门:义理,考核,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蠢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诗文词曲皆可以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非所难。”[2]这是一种典型的重道轻文的观念,从曾国藩“昭然若发蒙”可以看出其颇为认同唐鉴这一理论。这表明此时包括公文写作在内的古文写作理念中,“义理”是曾国藩所要传达的第一要义,“经济”只是其组成部分,尚未独立;“辞章(文章)”是发挥义理的载体,也唯有精于义理方可至;对于“考据(考核)”,由于其多求粗遗精、管窥蠡测而被曾国藩“无取焉”。[3]
2.2 第二阶段:义理、考据、辞章并重
第二阶段,大致为道光后期至咸丰初年。这一阶段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中最显著的变化是把“考据”与“辞章”提升到与“义理”等同的位置,不过在序列上“义理”为先的地位仍不可动摇。
一方面,这一变化与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影响有着重大干系。例如,在道光二十三年《致刘蓉》信中,曾国藩谈及自己对“辞章”的新感悟,“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4]“明于文字”其实暗示曾国藩对“辞章”态度的转变。此外,曾国藩还继续指出:“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舍文字无以观圣人之道”,进而提出“坚车行远”的观点,对之前重义理、轻辞章的观点进行了修正。[5]这都表明曾国藩一如既往重视“义理”的同时,开始了对公文辞章的关注。另一方面, 曾国藩对“考据”的态度也有很大转变。如在《孙芝房侍讲刍论序》中,曾国藩曾以良知之学做类比,做出“近世汉学之说,诚非无弊;必谓其致粤贼之乱,则少过矣”的论断,[6]以此来澄清当世非议考据之学的观点,与前期对考据之学“无取焉”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可见,这一阶段,考据和辞章开始为曾国藩所重视。
2.3 第三阶段:四位一体理念框架最终形成
第三阶段,大致为咸丰后期至同治年间。这一阶段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中最显著的特征是文道关系的阶段性分离和“经济”的独立,从而使得“义理、经济、考据、辞章”真正由笼统走向分野。
曾国藩关于文道关系的分离集中体现在其关于“古文不宜说理”的论述。咸丰八年,曾国藩《致刘蓉》的信中谈及“道与文不能不离为二”的观点,并举方苞为例,认为方苞之所以不能“入古人之阃奥”的原因,正是由于用心不专、两下兼顾,[7]进而直言“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8]这与其前期“文道并重”的观点可谓格格不入。然而,同治九年,曾国藩的观念再次发生变化。同样是在给刘蓉的信中,曾国藩舍弃了“道与文不能不离为二”的论断,认为“道与文之轻重,纷纷无有定说久矣。”[9]由此可见,曾国藩这一时期公文写作理念中关于文道关系的认识具有一定反复性,但其最终向“无有定说”的转变,则仍然预示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中“义理”与“辞章”的关系回归到平等的位置。
食品生产过程中,微乳常暴露在不同pH环境下。因此,考察微乳的pH稳定性对于扩大其应用范围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分别考察丁香酚微乳和海藻酸钠修饰微乳的在pH 3.0~7.0稳定性。如图3所示,丁香酚微乳在pH 5.0~7.0时,呈现为乳白液状,粒径均小于200 nm;在pH 3.0~4.5时,丁香酚微乳出现了明显的沉淀与分层,可见在该pH条件下丁香微乳十分不稳定。结合表1可知,在pH 3.0~4.5范围下,丁香酚微乳的粒径及PDI明显增大。酪蛋白酸钠在等电点附近所带电荷量较少,静电斥力减弱,导致粒子发生聚集现象[23]。
在这一时期,“经济”也从“义理”中独立出来,成为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治八年七月,曾国藩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中,正式将为学之术总结为“义理、经济、考据、辞章”四义,这是曾国藩学术思想、文学思想的一个总领,同时也是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的精髓。与此同时,曾国藩进一步阐述了四者的相互关系,义理、经济、考据、辞章四义中,义理为最切要之事,重要性可达“切于身心而不可造次离”程度;经济次之,并能在义理通达之后而“该乎其中”;而后是考据,以使所见所闻,“证诸古制而不谬”;最后是辞章,使得所言之事“达诸笔札而不差。”[10]具体来说,辞章是具有输出性质的为文之法,而义理、经济、考据都是立文的基本要素:义理是立文的基础,经济是最终目的,二者“初无两术之可分……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11],而考据则是基本功力。自此,曾国藩“义理、经济、考据、辞章”四位一体的公文写作理念最终形成。下面,重点对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中“义理、经济、考据、辞章”的具体内涵进行分析。
3 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的内涵
3.1 义理
据曾国藩的论述,“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可见,对曾国藩而言,此处义理更偏向于宋明理学所宣扬的性理之学。曾国藩认为,由于人的才智、精力有限,君子当权衡取舍,而最为紧急切要之事,当“莫急于义理之学。”[12]对于公文,同样必须以义理为质,而后经济、考据、辞章乃有所归。[13]因而,在曾国藩的公文写作理念中,“义理”是公文的核心要义,陈义高远是写好公文的先决条件,只要义理之学功夫到家,公文便“根本固枝叶自茂”。[14]
义理既然对于公文如此重要,那么曾国藩所谓义理的具体指向便很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在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中,“义理”与“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二者,曾国藩将之总结为“理是礼之体,礼是理之用”,并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舍礼无所谓道德;……舍礼无所谓政事。”[15]这表明,曾国藩不仅将“礼”作为道德也即“义理”的承载,更将其作为修齐治平的根本途径。《清史稿》中也有记载:“(曾国藩)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惠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16]这就是说,在曾国藩的礼学理念中,当世的盐、钱、漕、河等具体事务都可以是礼的体现。由此可知,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中所强调的义理实质上既是一种注重内在修养、传统道德,进而维护纲常礼教的性命之理,同时也是一种内容庞杂具体、包含世事俗物的礼。
那么,曾国藩公文又是如何体现义理的呢?其一,立意上追求陈义高远。曾国藩十分推崇西汉公文的“陈义高远”与“不可磨灭之质干”,同样地,对于公文写作,陈义高远也为曾国藩所看重,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公文力求维护儒家道德礼法的核心地位,如《讨粤匪檄》几乎都在谈论维护名教尊卑、礼义人伦、诗书典则和忠信仁义,[17]表达了曾国藩维护纲常礼教的愿望;第二,公文力求达到“转移风俗”的目的。“转移风俗”,可以看成是对义理的一种间接追求,是实现义理的另一种形式。在公文中,转移风俗是曾国藩的不懈追求,许同莘在也称其公文为“以己之所向而转移风俗”[18],“得礼学精义”[19]。其二,内容上践行以礼为归的宗旨。事实上,曾国藩的多数公文,并不像《讨粤匪檄》有着明显直接的立意,而多为具体的政务军情,但这恰恰体现了曾国藩“礼为理之用”“不谈过高之理”的理念,更加注重现实操作性,注重以礼为归。其三,写作上注重议论说理。立意上陈义高远和内容上以礼为归是曾国藩公文中实现义理的主要方式,但“义理”要被透彻地阐明,还需要相应的写作与表达技巧,就曾国藩公文而言,即具有多叮咛告诫和善于平易处发绝大议论的特征。
3.2 经济
在传统语境中,经济可以理解为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等意思,具备很强的实学致用指向。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曾言:“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公文是实现“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曾国藩的公文写作理念中,“经济”同样是最基本要义之一,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公文必须要言之有“理”。这是因为“义理”之中本就包含了部分“经济”的特征。前文论及,在曾国藩的公文写作理念中,“义理”不仅关乎空谈心性的玄虚之理,而且涉及包括军事、政务、洋务等国计民生在内的一系列国家事务,即与“用”关系极为密切、具备实操性的“礼”。曾国藩的公文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和事务本身,致力于作为“用”的礼,不谈过高之“义理”,这就是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中“义理”所蕴含的“经济”特征。
再次,必须精简文风,提高效率。曾国藩倡导明白显豁、晓畅简明的文风,认为“(奏疏)总要以明显为要”,把“典、浅、显”作为评判奏疏的基本标准,并举出白居易之诗浅显为老妪所理解却又能打动人心这一实例,强调深入浅出、简明易懂的重要意义。[20]又,对于当世部分学者好以晦涩难懂字词来标榜古风的现象,曾国藩则解释古字现在虽晦涩难懂,但在当时“乃人人共称之名,人人惯用之字”[21],以此说明公文中借用晦涩难懂字词标榜古风这一做法的不合理性,提倡简明文风。
最后,分门别类,文有所专。在姚鼐对文章分类的基础上,曾国藩在《经史百家杂钞》中将文种重新调整为十一类,更换了部分选文,大量添加经、史、子三类文章,更加注重文章与政事的沟通。同时,在微观层面,曾国藩强调不同文体的功能差别,如“奏议类宜喷薄;诏令类、书牍类宜吞吐”,以文风来增强公文的“经济”功能。除此之外,文有所专也是增强公文“经济”功能的重要举措。曾国藩认为,流有主支之分、峰有主次之别,公文写作“主意亦不能两重”,唯有“专重一处”,公文才能“四体停匀,乃始成章。”[22]这就表明,公文必须一文一事,才能有效实现经世致用的目标。
3.3 考据
考据与汉学的兴盛紧密相关,是汉学家的主要治学方法。在公文写作中,曾国藩极为重视考据,当然,曾国藩对考据相关理念的运用吸收也是有所取舍的。
首先,对于考据“辩论动至数千言”的弊端,曾国藩在公文写作中坚定地予以摒弃,杜绝虚言浮文是其基本原则。曾国藩并不因为开始注重考据便在公文中大费周章专事考据,而是极力避免“枝之蒐而忘其本,流之逐而遗其源”[23]的现象,确保公文主旨的阐发。其次,曾国藩公文中考据的运用重在发挥义理和经世致用,有意识地淡化其过度侧重于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做法,更加注重将其运用于解析经典、发掘和阐释义理上,以确保在公文写作中的“义理正大”和质干不灭。最后,考据中训诂的方法为曾国藩公文所倚重。曾国藩认识到文字功底是公文的基础,文字功底及学养的积累需要精通训诂之学,只有在这方面具备一定造诣,才能于真正理解义理。
3.4 辞章
在义理、经济、考据、辞章中,辞章虽被曾国藩至于末位,但作为前三者赖以实践的载体,是公文顺利实现其目的的最后一公里,因而也是曾国藩持续用功所在。
首先,在气质上,追求“寓刚于柔”。在曾国藩看来,公文的风格可分为阳刚和阴柔两种,不同种类公文应当有适合的风格。但即便如此,曾国藩仍不改对阳刚雄奇之文的喜爱,正如其所言:“平生好雄直瑰伟之文”[24]“当以渴笔写吾雄直之气”[25]。然而,在阳刚与阴柔之外,曾国藩公文还有一个更极致的追求,即“寓刚于柔”。正如其在《日记》中所说:“若能合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26]由此可见,曾国藩关于公文风格的优劣一定的排序,即公文若能“合雄奇于淡远”则尤为可贵,阳刚次之,阴柔再次之。
其次,在章句上,主张不避骈文,兼容骈散。对于公文而言,曾国藩认为通达浅显固然有利于表达思想,但骈文并不影响精义的发挥以至于“芜累而伤气”,[27]反而会对提升气势大有裨益。更以陆宣公为例,称其虽然“无一句不对,无一字不协平仄,无一联不调马蹄”,但是无论是在义理还是气势上都比隆濂、洛、韩、苏,而陆宣公运用骈文剖析事理、陈情论事之“精当不移”却“非韩、苏所能及。”[28]事实上,曾国藩主张公文行文的兼容骈散有更深层次的哲学理论基础,他认为“天地之数,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奇一偶,互为其用,是以无息焉”,而“文字之道,何独不然?”[29]可见,在曾国藩看来,公文章句骈散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奇与偶辩证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唯有兼容骈散,文章方可经久不衰。
最后,在布局上,力主自然与剪裁相结合以达到“珠圆玉润”。曾国藩认为,古往今来,无论哪种文章,在构思行文上“总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30]那么,公文追求“珠圆玉润”也是应有之义。在某种程度上,公文追求自然与剪裁相结合与骈散兼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公文要经久不衰,需兼容骈散,而布局想达到“珠圆玉润”,则需要“自然”与“剪裁”结合。一方面,“自然”类似于“行散”,即顺应本来面目,不强取模拟,从而保持公文“自然”本真。另一方面,“自然”也是相对的,一篇公文要想顺利实现既定目标,必要的“剪裁”不可或缺。“剪裁”类似于“用骈”,一篇好的公文需要一定的雕琢,而这也正折射出了曾国藩对于“剪裁”的理解,即“位置之先后,剪裁之繁简,为文家第一要义也。”[31]
4 结语
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的形成,对重塑晚清公文风气、推动公文理论革新以及加速中国古代公文的近代化历程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在中国古代“泛文学”的观念下,公文写作与文学创作界限的模糊性,使得曾国藩的公文写作理念与其古文创作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最核心的义理、经济、考据、辞章四要义更是直接来源于其古文理论。不同的是,与一般的文学创作相比,曾国藩公文的写作更加注重实用性和事功性,因而突出“经济”、强调经世致用是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最重要的特征。但这只是相对于同一时代其他人而言的,并不意味着“经济”在曾国藩公文写作理念中处于最核心地位。相反,“义理”始终是曾国藩立论、宣扬和实践中最为看中的部分。就公文而言,曾国藩取得了比同时代几乎所有人都大的突破和影响,但从主观上说,其公文写作理念仍无法掩藏其对传统的认同与向先哲的回归。
——论《江格尔》重要问题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