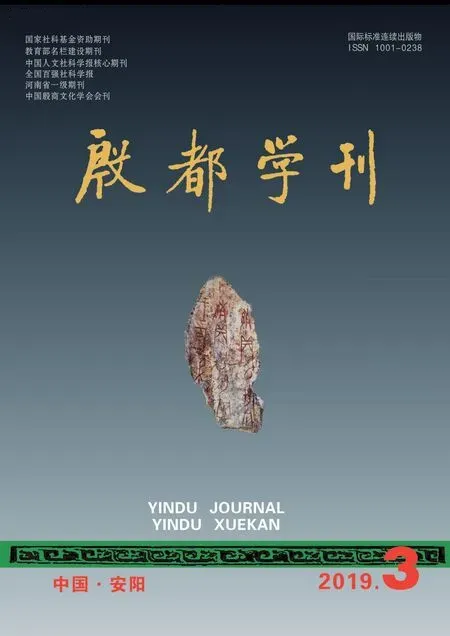《文心雕龙·程器》辨
高宏洲
(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 100705)
《程器》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九篇,关于它的主旨学界有“发愤而作说”、“文德论”、“论述士人的品德和才能”、“论从政与为文的关系”、“程文说”、“确立理想文士的标准”等多种观点。客观而言,这些观点都抓住了《程器》篇的某些内容,但是与《程器》的原意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本文在批判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详细梳理《程器》的语脉逻辑,澄清《程器》的主旨。
一、已有研究成果之检讨
目前,学界关于《文心雕龙·程器》篇的主旨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孙蓉蓉将其概括为“‘有激之谈’和‘发愤而著书’”“论述从政与为文的关系”“谈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三种,参见其《<文心雕龙·程器>辨析》,载《刘勰与<文心雕龙>考论》,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39-241页;张慧磊将其概括为“发愤著书说”“作家道德品行论”“学文本以达政旨”三种,参见其《<文心雕龙·程器>辨疑》,《语文学刊》2007年第11期。。
第一种是“发愤而作说”。清代纪昀较早提出这种观点。纪昀在《文心雕龙·程器》“文武之术,左右惟宜”部分眉批云:“观此一篇,彦和亦发愤而著书者。观《时序》篇,此书盖成于齐末。彦和入梁乃仕,故郁郁乃尔耶?”[1](P161)可见,纪昀的“发愤而著书”主要是针对刘勰仕途的蹇碍而言的。纪昀的这一观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研究者都将《程器》的主旨与刘勰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联系起来。刘永济将刘勰的不满概括为两个方面:“一者,叹息于无所凭藉者之易召讥谤;二者,讥讽位高任重者,怠其职责,而以文学邀誉。”[2](P169)王元化曾用《程器》篇的内容来证明刘勰的庶族身份,详细分析了《程器》“古之将相,疵疚实多”、“将相以位隆特达”、“士之登用,以成务为用”、“文武之术,左右惟宜”、“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等话语对社会现实的愤懑和不平[3](P12)。这种论调在郭晋稀的《文心雕龙注译》、祖保泉的《文心雕龙解说》、周振甫的《文心雕龙今译》等论著中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其实,这种论调属于过度阐释,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这种论调虽然注意到刘勰出身比较低微的社会现实,但是将这种现实无限放大,尤其是将刘勰代表的庶族与当时的士族尖锐地对立起来,夸大了刘勰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二是,这种论调没有顾及《程器》的文本语脉逻辑,采取“断章取义,余取所求”的方法,将其中的部分句子独立出来予以过度阐释。这集中体现在研究者们所列举的证据上,他们几乎都是用史书或文集中记载的文献材料来证明刘勰是针对现实而发的。这样的论证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所列举的证据并不有助于《程器》篇主旨的澄清。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看似真实的历史材料遮蔽了对《程器》篇主旨的探讨。
第二种是“文德论”,认为《程器》主要是论述作家的道德修养问题。陆侃如和牟世金的《文心雕龙译注》认为,《程器》主要是论述作家的道德品质问题,反对“有文无质”而主张德才兼备[4](P590)。刘铖也认为《程器》从品行方面评论作家,主要论述作家的道德品质问题,反对“有文无质”而主张德才兼备[5]。张利群认为“文德”是《程器》的重要内容,刘勰主要是从作者和作品两个角度来谈“文德”的[6]。周勋初的《文心雕龙解析》认为,刘勰在五十篇文章行将结束时,特设《程器》一篇讨论道德才能方面的问题,仍是在为贯彻儒家的宗旨而努力[7](P788)。张灯也认为《程器》实为评说文家品德操行的专论[8](P535)。周兴陆结合《文心雕龙》的全部内容,全面分析了刘勰“文德论”的独特内涵,认为刘勰的“文德论”包含“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达则奉时以骋绩,穷则独善以垂文;奉时骋绩时,应心怀忠信,具有切直謇谔之风;独善垂文时,能够道胜情泰,发愤以表志等内涵[9]。这一看法丰富了刘勰“文德论”的内涵,摆脱了将“文德论”视为简单的道德修养的传统窠臼。问题是,该文不是专门探讨《程器》篇的主旨,而是结合《文心雕龙》的全部材料论述刘勰的“文德”思想的独特内涵。离开《程器》的主旨而谈刘勰的“文德论”显然属于另一个问题了。“文德论”的局限在于无法获得《程器》文本的支持。正如巩本栋所言:“它不是一篇纯粹的作家道德品行论,也未涉及作家道德品行与创作的关系。”[10]况且,刘勰在《程器》的“赞”中明确使用过“文德”概念,但是并没有将此作为标题,这就间接告诉我们用“文德论”来概括《程器》的主旨是不贴切的。否则,严谨的刘勰一定会将其作为本篇的题目。
第三种是“论述士人的品德和才能”。这是主流的看法。比如,周振甫的《文心雕龙今译》云:“这篇讨论作家的品德才干问题,要求作家‘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认为光会写文章还不够,还要‘达于政事’,能文能武。”[11](P442)詹锳的《文心雕龙义证》云:“按‘器’是材器,这个材器和现在一般所说的文学创作才能不是一个意思,它指的是具有道德人品和识见的‘栋梁之材’。‘程器’就是衡量一个作家有没有这种包括道德品质、政治识见在内的全面的修养。”[12](P1867)王运熙、周锋的《文心雕龙译注》认为,《程器》是“论述士人的品德和才能问题……本篇上半篇着重谈文士的品行,谈‘名之扬抑’,批评文人无行论的片面性,显示出敢于向传统偏见挑战的勇气。下半篇着重谈士人的政治出路,谈‘位之通塞’,认为士人首先应当在政治军事上有所建树,并强调文学应为军国服务。”[13](P500)这一看法认识到了《程器》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内容之间的差异,但是没有很好地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仅仅将《程器》理解为讨论士人的品德和才能,那么是否存在《文心雕龙·总术》篇所谓的“一物携贰,莫不解体”的问题?《<文心雕龙>集校、集释、直译》就认为该篇虽然开头已明确表示要以“辞人文士应当兼重实与华、器用与文采为主要要旨,可是后半篇的论述重心却落在了力陈士人、君子应当兼通文武之术、‘弸中’而‘彪外’、‘纬军国’而‘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等等上面。启行之辞如彼,绝笔之言如此,一物携贰,首尾不一。”[14](P916)如果真是这样,《程器》的写作就是失败的。作者将这种失败归结于刘勰心中郁积已久的“有激”之言和为了理想抱负而不顾一切、急不择路的结果。我们认为这是研究者没有准确把握《程器》的主旨而进行的主观推断。况且,现代意义上的品德和才能与刘勰所谓的“名之抑扬”和“位之通塞”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第四种观点是“论从政与为文的关系”。王元化是这种观点的较早阐释者。《文心雕龙讲疏》云:“刘勰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文人的德行和器用,藉以阐明学文本以达政之旨。”[3](P12)讲得非常明确,认为论述文人的德行和器用的目的是为了阐明学文本以达政的宗旨。巩本栋是这种观点的积极阐发者,认为《程器》主要论述了从政与为文的关系,其主旨在力倡“贵器用”与尚“骋绩”[10]。张慧磊也认为“学文本以达政”更符合《程器》的原意[15]。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犯了以局部代整体的错误。刘勰在衡量文士的才能时提到了学文本以达政的思想,但这只是文士应该具备的一项品格,用它来概括《程器》的主旨是不妥当的。
第五种观点是“程文说”。这种观点是赵运通提出的。他说《程器》的实质是通过纠正时俗对文人的偏见,阐明“文采”对于全体社会成员“成务为用”的功能,也就是整体评价文的意义,并且认为只有这样引申才能辨明《程器》篇的“批评论”的性质[16]。《<文心雕龙>集校、集释、直译》也认为该篇中的“器”乃指“文”之器用、大用,而非指人的才器、器能、器用[14](P918)。指出《程器》具有纠正时俗对文人的偏见是合理的,但是将《程器》的主旨概括为评价文的意义则与事实严重不符。验诸文本,我们会发现《程器》主要讨论的是“文士”的器用和社会作用,而不是文,两者是不同的。
第六种观点是“程文士,即确立理想文士的标准”。这是刘方最近提出来的一种观点[17]。这种观点是在反思过去研究的不足的基础上提出的,其贡献是明确了《程器》篇“程文士”的特征,局限是将文中蕴含着的对理想文士的评价作为文章的主旨,同样犯了以局部代整体的错误。
二、《程器》的主旨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已有的研究的一个主要局限在于没有搞清楚《程器》篇的主旨与文中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因此,要准确理解《程器》的主旨必须搞清楚《程器》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在笔者看来,《程器》的主旨是衡量文士的器用和才能。但是刘勰不是面面俱到地谈论文士的器用和才能,而是主要从文士的声誉和仕途的通达与否两个方面来谈。《程器》对此作过交代,刘勰说:“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这句话是把握《程器》篇的语义逻辑的关键,但是却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这句话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意思是,《程器》的前半部分谈论的是文士的声誉升降的问题,后半部分谈论的是文士的仕途通达与否的问题。研究者们用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修养和政治才能代替刘勰的“名之抑扬”和“位之通塞”,显然是不准确的。鉴于此,本文结合刘勰的“名之抑扬”和“位之通塞”来还原《程器》的主旨。
(一)“名之抑扬”的问题
1.对“文人无行”的流俗之见的批评
《程器》既没有开门见山地谈论文士的器用和才能,也没有直接谈论道德修养与文学创作之间的紧密关系,而是从驳斥“文人无行”的雷同之见切入。刘勰先是引用《尚书·周书》论士的标准,“方之梓材,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这句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士人虽然以器用为贵,但同时也要兼具文采,器用和文采是士人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二是,器用和文采虽然是士人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但是相比较而言,器用是更根本的,只有在贵器用的前提下才能兼备文采。但是,由于近代辞人“务华弃实”,也就是“贵文采”而“弃器用”,引起魏文帝曹丕的批评,说“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之后,韦诞又对历代文人进行了诋毁。自此之后,人们对文人的看法几乎“混之一贯”,认为所有的文人都是无行的。从刘勰的叙述可以看出,他对曹丕和韦诞的批评基本是认可的,因为他们的批评建立在近代辞人“务华弃实”的事实之上。刘勰不满的是“后人雷同,混之一贯”,即人云亦云地认为所有的文人都是无行的。后人的这种雷同之见对整个文士阶层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所以刘勰要予以辩驳。
2.对文人的瑕疵是承认还是批评
在《程器》的第二段,刘勰比较详细地列举了文士的瑕疵,比如司马相如的“窃妻而受金”,扬雄的“嗜酒而少算”,冯衍之 “不循廉隅”,杜笃之“请求无厌”,班固谄媚窦宪作威作福,马融结党梁冀贪污财货,孔融傲慢放诞而招致诛杀,祢衡狂傲痴愚而遭到杀戮,王粲轻浮脆弱而急躁奔兢,陈琳奔走兢进而粗陋疏忽,丁仪心存贪念而乞求免死,路粹但求饮食而没有廉耻,潘岳诡草祷辞于愍怀太子,陆机倾身侧媚于贾谧、郭彰,傅玄刚强狭隘而大骂台阁,孙楚凶狠刚愎而聚讼官府,等等。大多数学者认为刘勰的这段话严厉地谴责了文士的不良德行。这种理解值得商榷。刘勰在列举完这些例子后说“诸如此类,并文士之瑕累”。从刘勰的叙述中,我们感觉到的只是他承认这些都是文士的瑕累,并没有予以严厉的谴责。相反,他还对文士的瑕累进行了一定的辩护。
3.对文士瑕累的辩护
刘勰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文士的瑕累进行辩护。首先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将相,疵疚实多”。比如管仲的盗窃,吴起的贪淫,陈平的污点,周勃、灌婴的谗佞嫉妒,等等。自此以下,数不胜数。其次是对文士的瑕疵进行了同情之理解。他说:“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磬悬,丁路之贫薄哉!”意思是,孔光身居要职还取媚讨好宠臣董贤,与此相比,职位卑微低下的班固、马融、潘岳谄媚窦宪、梁冀等权臣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吗?王戎享有开国功臣的厚禄,居然还卖官鬻爵,与此相比,贫困窘迫的司马相如、杜笃、丁路等贪污受贿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吗?再次是举出屈原、贾谊的忠贞,邹阳、枚乘的机警,黄香的至孝,徐干的沉静,证明并不是所有的文士都是有污点的。最后是从人的禀赋不同而会有所差异的角度,论述“自非上哲,难以求备”,不应该对文士求全责备,应该善于观其大端。
刘勰对文士的辩护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刘勰的辩护并不十分严密。不能因为自古武士和将相有瑕累就认为文士的瑕累是合理的,这就好比不能因为别人偷盗而证明自己的偷盗是合法的一样。纪昀的眉批“此亦有激之谈,不为典要”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1](P161)。但是,由于在中国古代武士将相和文士同属一个群体——士人群体,所以用武士将相的瑕累来为文士的瑕累辩护具有一定的意义,它有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文士的形象和社会地位。第二,刘勰并没有像后世的理学家那样对文士的瑕累责全求备,而是因每个人的禀赋不同,优劣长短各殊,主张不对每个士人作严苛的批评。第三,刘勰没有从道德律令的角度对文士和武士的瑕累进行严厉谴责,而是从实际的效果分析武士将相和文士的声誉的差异。刘勰说将相以“名崇而讥减”、“位隆而特达”,文士则“以职卑而多诮”。分析的结果不是这些行为符合不符合道德,而是职位的高低决定声誉的升降。“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刘勰的着眼点在于武士将相职位的崇高增加了其声誉的远扬,而文士职位的卑微增加了对其讥诮的分量。从道德律令的角度来看,刘勰的论述是不周延的。正如明代陈仁锡眉批所云:“位隆则不诮,非无疵也。”[1](P161)清代李安民旁批云:“大节既亏,安得从减?”[1](P161)一个强调的是“位隆”并不意味着没有瑕疵,一个关注的是大节既亏以后能否减少的问题。他们的着眼点与刘勰截然不同。由此可见,认为该篇属于“文德论”是站不住脚的。
(二)“位之通塞”的问题
刘勰对文士“位之通塞”的问题的讨论同样是根据文士的作用来衡量的。刘勰说:“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这与前面的“贵器用而兼文采”是一致的。刘勰进而用鲁国的妇人敬姜“推其机综,以方治国”的故事推论丈夫学文要达于政事。在这种观点的主导下,刘勰认为汉代扬雄和司马相如“终乎下位”的原因在于他们“有文无质”。刘勰举的一个成功典范是东晋的庾亮,他非常有才华,而且取得了伟大的功勋。在刘勰看来,正是伟大的功勋遮盖了庾亮的文艺才华;如果庾亮没有取得伟大的功勋,必将以文学才华扬名于后世。在刘勰看来,文士应该文武兼备,既好文又习武。刘勰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春秋时期的郤毂由于懂得诗书而被举荐为元帅,意在说明文士应该熟习军武;一个是孙武的《兵经》“辞如珠玉”,意在说明武士应该通晓文学。在此基础上,刘勰说,真正的文士应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要成就一番事业,就要有丰厚的蕴储蓄藏于内,鲜亮的光采显露于外,要具有楩木和楠木般的质地,枕树和樟树般的枝干,撰写的文章能够经邦纬国,负重的时候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穷困的时候独善其身以著述,发达的时候顺应时世建功立业。在刘勰看来,只有这样的文人才能达到《尚书·周书》中的“梓材”标准。
刘勰对文士“位之通塞”问题的讨论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他并没有将文士“终乎下位”的原因归结于统治者的昏庸或者政治体制的不公平,而这是近现代以来文学史和文论史上比较普遍的观点,而是从文士自身的角度思考问题。这可能与刘勰写作《文心雕龙》时的年龄有关。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时候刚过而立之年,还处在“君子藏器,待时而动”的时候,这样的年龄使他对未来的仕途抱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同时,由于没有接触社会的复杂性,容易将问题简单化,只从文学的角度思考文人的政治前途,而没有立体地、多角度地思考文人的创作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样的思考显然是不够成熟和深刻的,有主观浪漫主义的色彩。第二,刘勰是按照他的理想标准来衡量文士的,他对“文武之术,左右惟宜”、“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的论述,既有针对动荡的时代环境需要文士具备实际的政治才干的现实考虑,也与他在这方面的才能有关。纪昀说刘勰这些论述“纯是客气”[1](P161),魏伯河说刘勰的这些论述蕴含着强烈的干进意图[18],显然都是在没有搞清楚刘勰的论述旨趣的情况下进行的主观推测。事实证明,刘勰的这些论述绝不只是“客气”。《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19](P710)。从刘勰的入仕政绩和《文心雕龙》所取得的成就来看,刘勰是“文武之术,左右惟宜”的。刘勰虽然主张积极用世,但是他的出处是有原则的,是“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时候是“穷则独善以垂文”的时刻,他明确自己“傲岸泉石,咀嚼文义”(《序志》)的现实处境,追求的是“文果载心,余心有寄”的千古事业,怎么会在此表达干进之意呢?况且,刘勰具备“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杂文》)的文德思想,怎么会汲汲于仕进呢?一个真正有才华的人,一定是针对社会的现实问题而言的,不能因为刘勰在谈论文士的才华时结合了现实就认为他是在向统治者干进。
(三)“名之抑扬”与“位之通塞”的关系
已有研究成果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无法合理解释《程器》篇前半部分“名之抑扬”与后半部分“位之通塞”之间的关系。在笔者看来,“名之抑扬”与“位之通塞”是刘勰衡量文士的器用和才华的两个方面。刘勰的这一思想应该受到了王充《论衡》的影响。在《论衡·程材》篇,王充比较详细地衡量了儒生与文吏的优劣。在《论衡·量知》篇,王充明确说《程材》所论的是儒生与文吏的才能和行操[20](P546)。这一说明与大多数学者将《程器》的主旨概括为论述士人的品德和才华也是比较吻合的。但是仔细比对,在论述的角度上刘勰和王充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别。刘勰主要关注的是文士和武士的声誉的升降问题以及文士为什么“终乎下位”的问题,涉及面较小。除了《程材》篇,王充还在《量知》、《谢短》、《效力》等篇多角度地衡量了儒生与文吏的优劣。这种差别应当与刘勰那个时代文士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有关。在刘勰那个时代,一方面,社会上“文人无行”的雷同之见已经威胁到人们对文士的正确评价,所以必须予以辩驳;另一方面,文士“终乎下位”的社会现实也影响着人们对文士才能和社会作用的看法,所以必须给出合理解释。“名之抑扬”与“位之通塞”是当时影响文士社会地位的两个重要方面,而且前者已经对后者造成了一定的阻碍,所以必须予以辩驳。在这个意义上,《程器》具有为文士正名的意味。所以,刘勰才在《序志》篇说“耿介于《程器》”,就是对“文人无行”的流俗之见和文人“终乎下位”的社会现实耿耿于怀。
研究者由于没有搞清楚《程器》的主旨,而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文心雕龙>集校、集释、直译》认为该篇的写作存在文意游移、歧离,缺乏完整性和整一性[14](P911-913)。文意的游离和歧出主要指该篇首段明示辞人文士应当兼重实与华、器用与文采的意旨与第二段指出文人的瑕疵而又为之辩护、三四段力陈士人应当兼通文武之术、“弸中”而“彪外”、“纬军国”而“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不相一致。论述对象的游离和歧出主要指该篇前两段的论述对象是文人、辞人、群才、文士,而后两段的论述对象是士、君子。笔者认为这样的批评缺乏说服力。整体而言,《程器》的行文逻辑是比较连贯的,文章先提出真正的文士应该像梓材一样“贵器用而兼文采”,然后分析“文人无行”形成的原因,再辩驳“文人无行”的雷同之见的偏颇,最后分析文士仕途通达与否的问题,认为关键在于文士应具备“文武之术,左右惟宜”的才能。此外,《程器》开头提到的“《周书》论士,方之梓材”与结尾的“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也是前后呼应,首尾一贯的。前后两部分论述对象的差异并不是文章主旨的转变,而是体现了刘勰对文士身份的独特定位。在刘勰的心目中,文士不是只会进行文辞修饰的艺人,而是士人、君子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文人、辞人、文士在刘勰那里是与君子、士人高度重合的。这既与刘勰对文士的独特定位有关,也与《文心雕龙》既重文又重道的文学价值观完全一致。其中,“名之抑扬”与“位之通塞”是衡量文士器用的两个方面,不存在“一物携贰,莫不解体”的问题,它们共同在衡量文士的器用和社会价值的主旨统驭之下。
三、《程器》在《文心雕龙》中的位置
前人对《程器》在《文心雕龙》中的位置作过一些探讨。叶长青云:“兹篇为本书之终篇,四十八篇以上,文之体用具矣。殿以程器者,体用华也,程器实也。无器何有于用?孔门四科,首德行而末文学。故孔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又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盖德行为文之本,有德有文,相得益彰;无德有文,徒为文过济恶之资。宇宙间何贵有此文哉!然则以上四十八篇,与兹篇等量齐读可也。即先读兹篇,而后读四十八篇亦可也。又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器者所以求道,彦和首原道而终程器,示我周行矣。”[21](P115-116)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强调德行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二是从体用和道器的角度论述《程器》在《文心雕龙》中的位置,尤其是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传统思想解释《文心雕龙》的首《原道》而终《程器》的结构安排。祖保泉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如果我们把《文心》的首篇《原道》和结尾的《程器》联系起来看,似乎有体用结合的特点。《原道》论文之本质,《程器》论文之大用,这样首尾相应,显示了全书在结构上的严密性。”[22](P944-945)这些看法貌似有根有据,其实并不贴切。因为在交代《文心雕龙》结构的《序志》中,刘勰并没有说首《原道》终《程器》是按照“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哲学思想来安排的。况且,“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主要是解释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而《原道》强调的是文根源于道,《程器》讨论的是如何衡量文士的社会作用,两者并不是相互对应的关系。因此,不能按照“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思想来解释《文心雕龙》首《原道》终《程器》的结构。
其次,清代黄叔琳的眉批认为,《程器》是“于文外补修行立功,制作之体乃更完美”[1](P162)。如前所述,《程器》的主旨是衡量文士的器用和社会作用,而不是谈“文外修行立功”,尽管修行立功被刘勰认为是理想的文人应该具备的品格。张立斋的《文心雕龙注订》说:“《文心》一书首篇《原道》,论文人必守之则。此篇《程器》论文人当勉之行,两作相应,为本书之要,首尾应,用心远,立意深,不可不察也。”[23](P417)这也是不准确的。《原道》主要论述文本源于道,而不是论文人必守之则,尽管道对文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程器》是衡量文士的器用和社会作用,而不是论文人当勉之行,尽管具备实际的政治才干被刘勰认为是文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第三种观点认为《程器》属于《文心雕龙》的批评论或杂论,这是近代以来龙学界的主流观点。这种观点同样经不起推敲。首先,《文心雕龙》不是按照现代的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等来安排《文心雕龙》的结构的,而是根据上篇“纲领”和下篇“毛目”来安排的。其次,《文心雕龙》下篇的“毛目”并不是像现代人所理解的那样是将“剖情析采”概括为《神思》、《体性》等等,而是采用列举主要篇目的方法予以介绍。虽然刘勰的罗列具有一定的顺序,但是并没有严格按照现代人的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或杂论等逻辑,详细论述参见拙文《<文心雕龙>“剖情析采,笼圈条贯”辨》。
在笔者看来,衡量文士器用和社会地位的《程器》对《文心雕龙》是一个重要的补充。首先,当时有“文人无行”的雷同之见,不利于文人的社会地位。其次,整个《文心雕龙》还没有充分讨论文学的创作主体文士的器用和社会作用问题,而刘勰是具有明确的创作主体意识的,《征圣》就是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论述学习圣人为文的重要性。尽管如纪昀所言《征圣》“推到究极,仍是宗经”[1](P16),但是《征圣》和《宗经》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别的,《征圣》是强调学习圣人为文的原则和技巧,《宗经》是强调学习圣人创作的经典。《程器》则是刘勰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衡量文士的器用和社会作用的重要思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赋予文学非常崇高的地位,如果从事文学创作的文人是无行之徒,或者是无用之徒,那么谁会相信文学的魅力呢?所以,刘勰在《程器》篇衡量文人的器用和社会作用是非常有必要的,绝不是被动地接受王充《论衡·程器》篇的影响问题。《程器》是为了给文学创作的主体——文士正名,尽管刘勰所理解的文士具有独特的内涵。由于近现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很少探讨文学家的社会作用问题,所以导致学界不能准确地认识《程器》的价值;或者反过来说,由于没有充分认识《程器》的价值,所以我们的现当代文论对于文学家的社会作用和地位没有做出深入的研究。这是需要学界深长思之的一个学术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