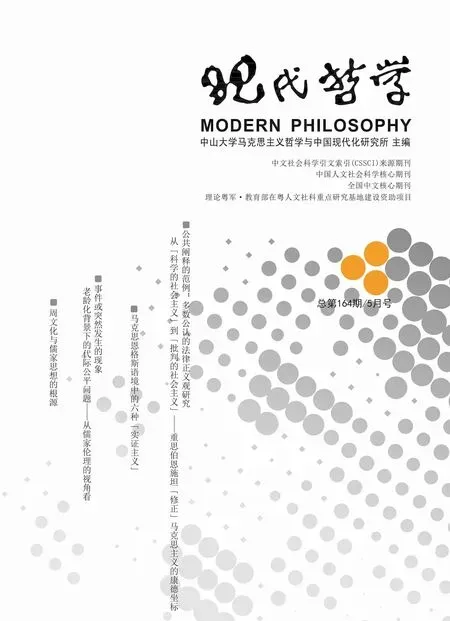作为一种存在论规定的人的本性概念
——马克思人的本性问题再考察*
[韩]梁承兑/著 金寿铁/译
一、马克思人的本性问题的论争史
在马克思思想研究中,对人的本性问题的讨论并不是很热门的研究对象[注]从B.耶索普编辑的四卷本《马克思政治-思想研究论文集》中,这点可见一斑,例如该论文集就没有收录相关论题的论文。。这不仅体现在第二国际实证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支配下的19世纪后半叶,也体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实践论复活的20世纪初叶,甚至在人们发现青年马克思著作的30年代以后也依然如故。换言之,无论是所谓法兰克福学派研究者基于黑格尔理解的马克思解释尝试,还是旨在重新解释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者研究,都处于两极偏激状态:要么片面地、断章取义地表达自身对马克思的人的本性的立场和见解;要么立足于人的本性的特定概念内容,牵强附会地重新解释马克思思想或者削足适履地将其应用于现实中。尽管存在多种多样的尝试和努力,但直到20世纪中叶,几乎没有这样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即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细致研究,从哲学、思想史视角探明马克思的人的本性概念自身。那么,其理由何在?
为了系统地、彻底地阐明这个问题,有必要探讨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西欧全部思想史的潮流,然而,这种作业已大大超出本文的考察范围。本文仅限于简要说明的是,在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之一是历史主义,而与历史主义一道兴起的 “无限可塑论”(the malleability/the plasticity principle)[注]人们通常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不过,如果在两者之间刻意做出某种区分的话,malleability要比plasticity更强调有意识的变化可能性层面。关于无限可塑性与历史主义关系的讨论,参见M.曼德尔鲍姆的思想史经典著作:《历史、人与理性》,巴尔的摩: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1971年。这一人的本性概念,恰恰与诸如此类的马克思研究动向有着极其深远的关联。
顾名思义,作为“无限可塑论”的人的本性概念意味着人可以以无限的方式发生变化。换言之,由于人可以被塑造为任何一种形态,所以并不存在决定论意义上的支配人的某种生物学本性或固定本质。限于题目,本文也无法具体探讨这种人的本性概念存在何种错误[注]实际上,要想详尽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考察与人的本质问题有关的全部西方哲学史,即从柏拉图的本质论到中世纪唯名论、近代经验哲学乃至德国人的哲学。不仅如此,还要考察伴随近代启蒙主义兴起的“无限可塑性”与自由主义及进化论之间的紧张、对峙和融合关系。可以说,K.勒维特的下述一段话简明扼要地表达了“无限可塑论”所包含的概念错误:“即使我们假定人的本质中的一种历史的转变,即假定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和转变,这种变化也只能发生在一个人基本上保持不变的时候。只是因为人的本质永久保持不变,这种本质才会发生变化。”(K.勒维特:《永恒与变化:历史哲学讲义》,马文·策特鲍姆,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247页。)。重要的是,“无限可塑性论”毕竟为批判地理解20世纪思想史主潮,即马克思研究论争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理论线索。
作为无限可塑论的人的本性概念是悖谬的,一方面,这一概念是对固定不变的人的本性的否定;另一方面,这一概念是对人的本性的另一种规定。也许,这种悖论恰恰说明了下述事实:自马克思逝世后,直到弗农·维纳布尔为止,为什么几乎还未曾有过专门研究马克思的人的本性概念本身的学者。究其原因,即无论是马克思研究者还是马克思思想的实践者都坚信,在马克思那里,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变革人及其本性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因而这种不言自明的真理不仅难以成为批判的对象,也不可能成为重新检讨的对象。此外,更具决定性的理由还见之于马克思的文献方面。
马克思明确探讨人的本性问题的作品当属他的早期著作,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作品迟至1930年才被发现,这恰恰说明了为什么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成为学者研究或讨论的对象。此外,另一个理由是,即使在其早期著作中,马克思也不是通过细致、系统的讨论展开人的本性问题,这点同样成为诱发学界所谓“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之争”的重要原因。换言之,这也是引发下述解释之争的一个重要原因:究竟马克思是由于学术上的未成熟性而暂时关注了人的本性问题,还是在其一生学术世界中都始终不渝、一以贯之地把人的本性视为核心主题?
围绕这些不同解释与论争史的脉络,本文将重新考察马克思的人的本性问题。此外,本文的主旨在于阐明在马克思思想中不仅存在“非无限可塑性”的人的本性概念,而且这种恒久不变的人的本性概念是马克思思想中的最根本、最牢固的存在论基础。在此,有必要批判性地整理、检讨与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两种相反立场,即维纳布尔[注]弗农·维纳布尔(Vernon Venable,1906-1996),美国社会学家和马克思学家,曾任瓦萨学院教授,主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和方法,代表作有《人的本性:马克思的观点》(1945)等。——中译注与杰拉斯[注]诺曼·杰拉斯(Norman Geras,1943-2013),英国政治理论家和马克思学家,曾任曼彻斯特大学名誉教授,代表作有《马克思人的本性》(1983)以及关于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论战文章。——中译注的讨论内容。
本文第二、三部分属于这一方面。这一检讨结果将表明,杰拉斯的解释比维纳布尔的解释更为妥当可靠。但是,杰拉斯的解释也具有根本局限性,那就是未能把握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的存在论意义。第四部分将阐明马克思的社会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必然要求关于人的形而上学的存在论,而这样的要求恰恰投射在马克思的“类的存在物”(Gattungswesen)概念之中。结语部分将提出笔者的下述结论: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依然停留在一种未完成的状态中,究其根本在于“类的存在”概念本身的未完成性,而作为对这种未完成性的解决方案,我们有必要从政治哲学史视角重新探索“类”概念,并以此为基础重新解释“类的存在”概念本身。
二、维纳布尔对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的解释
对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的最初研究当属维纳布尔的《人的本性:马克思的观点》(1945)[注]在本书《序言》中,维纳布尔宣称,他之所以撰写这部书,是因为直到那时“还全然没有说明马克思人的本性的著述”。V.维纳布尔:《人的本性:马克思的观点》,纽约:阿尔弗雷德·克诺夫,1945年,第ix页。——中译注。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一批学者[注]这批学者的代表性著作包括B.奥尔曼:《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概念》,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G.A.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8年;以及即将集中讨论的N.杰拉斯:《马克思与人的本性:一种传说的反驳》,伦敦:沃索出版社,1983年。提出新的批判以前,维纳布尔的研究一直被视为是对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的正统解释。这个正统的解释不是别的什么解释,而正是前述“无限可塑性”这一人的本性概念。
维纳布尔的著作一反传统研究模式,另辟蹊径,有关论述既没有参考也没有提及他所能接触到的那些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等。缺乏相关文献佐证,恰恰表现出他的研究基础的相对薄弱。另外,他对自然科学资料的把握也存在局限和偏颇。例如,他的议论乃至判断的基础知识主要依赖于霍尔姆霍兹(H.von.Helmholtz, 1821-1894)、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等19世纪科学史文献,而没有顾及20世纪突飞猛进的高新科学技术领域。换言之,在他的著作中,压根就没有理论联系实际,即结合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解释关于马克思的文献学、解释学、哲学史研究文献。后文将会提到,这恰恰凸显了他的研究的重大局限性。
尽管如此,维纳布尔的研究是建立在一种较高水平的学问素养、深刻的解释和明晰的分析基础之上的[注]无论对他的马克思解释赞成与否,我们都应客观理性地看待这本书。因此,下述这种态度显然有失公允,抹杀了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和贡献。例如, L.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伦敦:沃索出版社,1990年)一书中,只字不提维纳布尔的这本书,而B.奥尔曼在《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概念》(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一书中,则轻描淡写地掠过了这本书。。此外,与本书讨论内容有关且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研究马克思的人的本性的主旨在于奠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基础[注]V.维纳布尔:《人的本性:马克思的观点》,纽约:阿尔弗雷德·克诺弗出版社,1945年,第viii—ix章。。在此,笔者主要通过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具体考察维纳布尔关于马克思解释的主要论点。
在维纳布尔看来,马克思借以把握人的基本观点在于人与历史的统一性,即人是历史的另一侧面,反之,历史也不过是人的另一侧面而已[注]同上,第22页。。他把马克思心目中人的本来的特征叙述如下:“马克思全部社会概念中的核心部分无非是主张人改变历史,正因如此,人也改变自身,以及在此意义上,一切历史实际上都只不过是人的本性的不断变迁而已。”[注]同上,第33页。换言之,对维纳布尔来说,马克思人的本性观的核心内涵是否定人之中存在某种永恒的、固定不变的本性。此外,作为具体的解释根据,他试举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分析。与此相关,他澄清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并不是外附于人类历史的、单纯形式化的独断论过程,而是“无限可塑性”这一人的本性概念的另一侧面。鉴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业已众所周知,在此有必要重新检讨一下维纳布尔所整理的人的本性观点。
维纳布尔的出发点是把人的生存所必需的“人的需要”(human needs/menschliche Bedürfnisse)视为理解劳动概念的基本前提。虽然后来A.赫勒系统阐明了马克思“需要”概念的具体内涵,但是,维纳布尔也展示了这个概念的核心意义[注]有趣的是,像维纳布尔一样,赫勒也一边讨论“需要”概念,一边否认永恒的人的本性的存在。(参见A.赫勒:《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伦敦:阿里逊与布斯伯出版社,1976年,第2章。)。首先,维纳布尔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关于人类生存以及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一段话:“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注]V.维纳布尔:《人的本性:马克思的观点》,第28—29页。
可是,由于人的需要只能从自然中得到满足,所以必然发生“劳动”这一作为自然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而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详细说明了这种劳动概念。在此,我们暂且不谈论下述两个问题:第一,马克思的这种劳动概念是否能充分说明不同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根据?第二,在自身概念体系中,马克思的这种劳动概念是否完全统摄了劳动的社会性、历史性、阶级性及诉诸革命来克服阶级的可能性等问题。在此,与维纳布尔的解释有关,首先主要关注的是,基于无限可塑性的人的本性概念与基于劳动概念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是否能并立共存?[注]V.维纳布尔认为,这种并立共存是完全可行的。事实上,他的《人的本性:马克思的观点》就是按照这种并存模式,分两部分展开的:第一部分总体上展示人的无限可塑的可能性;第二部分别探讨劳动与生产、令人痛苦的阶级对立与分工体系、克服了这种痛苦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世界以及作为实现这种世界手段的阶级斗争等。
为了支撑对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的解释,维纳布尔展示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18世纪自由主义者所谓固定的、永恒的人的本性概念的批判。在此,马克思批判了他们所宣扬的人的永恒本性只不过是对市民社会关系的抽象化,指出所谓脱离社会关系的、抽象化的个人只不过是对市民自身世俗欲望的抽象化而已[注]V.维纳布尔:《人的本性:马克思的观点》,第52页。。因此,在维纳布尔看来,马克思主张的核心是,人的劳动能够改变人自身,由于劳动性质决定阶级结构,所以社会阶级结构历史地规定隶属于其中的人的性格,并且随之决定人的本性的发展方向。应当据此理解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所谓固定不变的社会法则的批判以及对市民自由的批判,即所谓自由主义的自由并非普遍自由,而是受到社会历史条件制约意义上的市民自由[注]同上,第101页。。
紧接着,维纳布尔这样解释作为无限可塑性的人的本性与马克思革命理论之间的关系[注]同上,第viii—ix章。:人自己有意识地根据社会劳动改变生产方式,而且,人自身改变了的那个生产方式重新改变着人。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正是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与只具有作为交换价值的劳动力的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对立产生了资本家与工人这一敌对阶级关系。换言之,由于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分工体系(manufactured division of labour)不是真正体现人的劳动的社会性的社会分工,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备感痛苦的人们重新变成阶级之人。此外,理所当然,如此变化了的阶级之人为摧毁压迫自身的社会结构而斗争。在人类历史上,这种斗争正是旨在终结阶级结构的历史进步的原动力。为了从迄今为止的阶级冲突的历史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有人情味的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变革并否定只不过是历史地局限于某一时代市民伦理的和平或非暴力的伦理[注]V.维纳布尔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础简要说明如下:“人必须斗争,没有斗争,人的自由就没有希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伦理学的核心要求……从理性角度说,这一事实对那个由伦理学家组成的自由意志学派是无法容忍的,至于那些受康德-基督教-资产阶级个性化平均主义影响而形成义务概念的人,他们对这一事实感到惊愕和厌恶。”。
虽然后面还会讨论这点,但与维纳布尔的这种解释相关,笔者有必要先行指出如下事实。卢卡奇曾经明确指出,即使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也存在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思想内容[注]G.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剑桥:米特出版社,1971年。。诚然,维纳布尔的研究重申马克思后期著作中所表现的人的本性概念,与以“类的存在”概念为中心的早期著作的内容本质上并无任何区别,但是,在此关键问题不在于他所援引的参考资料的范围,而在于他的解释本身妥当与否。尤其是维纳布尔为了导出作为无限可塑性这一马克思的人的本性概念,诉诸一系列作为解释根据的文章。那么,这些文章本身是否就自动支撑这种解释呢?
当然,如果不以人的变化可能性为前提条件,谈论社会结构的变革或历史进步是毫无意义的。马克思明确设想,历史的进步在于通过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因此,绝不能认为他否定了人的变化可能性。然而,人的可变化并不意味着这种变化是毫无目的或方向的、无分别的、无规定的连续冲动。马克思明确树立了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进程的终极目标,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侧面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在此情况下,其批判的终极标准只能是用人的劳动反对非人的劳动,用人的分工体系反对非人的分工体系。如果是这样,不以“真正人的东西”——换言之,什么是人之中原始的、本质的东西,什么是附带的、偶然的东西,即什么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即不以人的本性为前提,马克思的全部思想本质上就变成毫无意义的东西。
下文将重点讨论,维纳布尔为支撑自身的马克思解释而提出的那些马克思的陈述弄巧成拙,反倒成为自身解释的反面。就是说,维纳布尔引用的马克思的陈述本身反倒表明了马克思相信存在一种不变的、本原的人的本性。与这个问题相关,首先有必要检讨一下杰拉斯的相关研究[注]N.杰拉斯:《马克思与人的本性:一种传说的反驳》,伦敦:沃索出版社,1983年。。因为他的研究不仅是批判、反驳维纳布尔之解释的代表性研究,也是概括了迄今关于马克思人的本性研究结果的总结性研究。
三、杰拉斯对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的解释
杰拉斯的研究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解释相关的讨论。第二部分是正面阐述“永恒不变性”这一马克思的人的本性概念。维纳布尔将“无限可塑性”视为与历史唯物论并驾齐驱的人的本性概念,与此相对,在此杰拉斯论证了永恒不变的人的本性的存在与历史唯物论之间的可调和性和相容性。第三部分,杰拉斯澄清了对马克思人的本性的错误理解何以以讹传讹,以致成为一般化、模式化的刻板成见。就是说,他逐一审查马克思的陈述中可遭致这种误解的所有根据,并从结论性视角提出自身解释的妥当性以及这一方面马克思思想的普遍妥当性[注]杰拉斯将把这一讨论的核心内容概括为下述三句话:“[《提纲》]第三命题并不表明马克思拒斥人的本性理念;马克思并不拒斥某种人的本性理念。因为他恰恰承诺某种人的本性。”(同上,第166页。)。
总体上,杰拉斯的讨论慎重而系统地展现了与人的本性相关的马克思的陈述。在解释马克思文本时,许多马克思研究者要么囫囵吞枣、浮光掠影,要么盲人摸象、以偏概全。恰恰在这点上,杰拉斯超越了这些研究者。特别是,他对《提纲》的详细解剖可视为关于马克思文本研究的重要贡献。因为在一些马克思研究者那里,《提纲》标志着所谓“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决定性分野。按照这种观点,在《提纲》以后,马克思不再关注“普遍的人的本性”这一“形而上学”问题。按照这种观点,作为一个决定性证据,《提纲》支撑这样一种立场:“成熟的”老年马克思否定了一切本质论本性概念的“科学”妥当性,一劳永逸地转变成了经济决定论者或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注]杰拉斯指出,持这种观点的大有人在,除了V.维纳布尔之外,还有T.博托默尔、R-D.卡明、E.卡门卡、L.阿尔都塞、R.图克、S.胡克等大批著名马克思研究者。(同上,第50—55页。)。对此,杰拉斯回应说,《提纲》不仅不能成为支撑这种解释的决定性根据,反而可被解释为一种暗示,即马克思承认人的本性的存在。由此出发,他不厌其烦地论证他的这种解释与历史唯物论的体系化著作《资本论》等后期著作的许多陈述严格相符,毫无二致。
首先需要审视一下马克思所使用的“das menschliche Wesen”用语本身的意义问题。当然,这个用语英语可译作“human nature”或“the human essence”。杰拉斯借故“essence” 一词的形而上学表达而不使用该词,而是选用了彼此略有不同意义的“human nature”和“the nature of man”的译法。这两种表达的不同意义在于,前者强调“人的特性中的永恒不变要素”(a constant element in the character of human beings),而后者指称“人的全方位的特征”(the all-around character of men)。在杰拉斯看来,就引起争议的《提纲》的解释问题而言,无论从前一种意义上还是在后一种意义上接受das menschliche Wesen,《提纲》都不能被解释为必然否定人的本性的存在[注]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尤其引发争议的文本如下:“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以这种消极的论证为基础,杰拉斯在以《人的本性与历史唯物论》为题的下一章中提出这样一种积极改进的论点:人的本性概念不仅出现在《提纲》以前的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而且出现在大幅展开了历史唯物论的后期著作中。但是,杰拉斯对《提纲》的这种分析存在一个明显缺陷,那就是在充分理解《提纲》的过程中,这种分析并没有认识到蕴含在“抽象物”(Abstraktum)以及“在其现实性”(in seiner Wirklichkeit)中的马克思的“抽象性”(Abstraktit)“现实性”(Wirklichkeit)概念的本原重要性。换言之,他的研究倒置了分析对象的本末。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在后面结合马克思的辩证法作具体讨论。在此,首先检讨一下杰拉斯对das menschliche Wesen这一用语的意义区分是否妥当,是否能站得住脚?
严格检讨某一用语所包含的一切可能意义,这是所有这个概念解释者的当然义务。因此,杰拉斯式的意义区分本身是有意义的,那么他对das menschliche Wesen所提出的两种意义,即人的特性中的永恒不变要素(简称意义 A)与人的全方位的特征(简称意义B)之间的意义差别必须是界限分明的,不可含混不清。但是,如果“意义B”比“意义 A”更加包容宽泛,就应当说明在什么视角下如此,并且应当具体说明何以如此。然而,杰拉斯对此没有给出任何说明。当然,“human nature”与“the nature of man”所表达的一般语义自身也并非从一开始就使这种意义区分成为可能。此外,在他那里,“特征”(character)一词的意义也是模糊不清的。
“character”一词源于希腊语charakter,原意是雕刻之字,现用作表达某个人的总体心理特征,或者用作表达将某一人物或事物的许多特征结合在一起的一般素质。因此,杰拉斯应当明确阐明他所使用的“character”究竟属于上述两种意义中的哪一种。换言之,在规定“human nature”和“the nature of man”时,共同所使用的“character”用语是指心理素质还是指包括人乃至一切个体的存在论规定?在此,杰拉斯陷于两难境地。如果在马克思那里,人的本性属于心理学向度,那么他犯了这样一种错误,即把马克思拉回到他所正面否定和批判的斯密(Adam Smith)、边沁(Jeremy Bentham)等自由主义人性论的传统中。实际上,杰拉斯本人并没有这般从心理学向度接近马克思的人的本性概念。他只是执着于对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的文献阐明,以至于不仅没有从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的明晰规定出发展开讨论,而且没有对其概念的积极意义内容做出全面而系统的阐明。
这样,杰拉斯的唯一选择就是从存在论视角接近“character”的意义。杰拉斯的两难困境,换言之,他之所以无法从存在论视角积极地充分解释马克思的人的本性概念,在于对形而上学抱有的陈腐偏见。究其本质,人的本性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其根据将在下文予以详述。即使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带有非形而上学特征,在检讨他的概念前,就预先做出这种语义规定,可谓犯了一个基本逻辑错误,即错把证明的对象当成证明的前提。显然,单凭对“das menschliche Wesen”进行意义分析,并不能切入马克思关于人的本性问题的实质。关于人的本性,马克思除了使用“das menschliche Wesen”这一表达方式之外,还使用“das menschliche Natur”“der Mensch von Natur”“der Mensch ist”等,因此也有必要澄明这些表达方式所蕴含的意义。虽然根据上下语境,这些表达方式带有微妙的意义差别,但在马克思那里,这些都是与人的存在的本质问题相关的相同的表达方式。此外,在《资本论》中,特别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劳动和分工体系等的时候,马克思作为辩证分析方法使用了“本质-显现-假象”(Wesen-Erscheinung-Schein)这一二重反命题(Antithesis),与此相关,应追本溯源,回到马克思文本,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的涵义。
但是,饶有趣味的是,杰拉斯在《人的本性与历史唯物论》一章中试图论证马克思的人的本性概念,但到头来,只能从形而上学视角规定马克思的人的本性概念。杰拉斯的问题在于否定了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的形而上学内容。结果是,他的解释只限于侧重分析经验上可确证的概念内容的意义分析,而没有继续深入其本原意义——这一概念内容本身的根据,即对其形而上学或存在论意义的分析。因此,下文将以杰拉斯所整理的内容为基础,进一步阐明马克思的人的本性概念为何必然是存在论的规定。接着表明,马克思“类的存在”概念虽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概念,但它代表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论规定。与此相关,本文将进一步探究不仅维纳布尔、杰拉斯未能规定,而且迄今所有马克思研究也都未能规定的意义和原因所在。
四、马克思:“本质-显现-假象”
在分析马克思的《提纲》中,杰拉斯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命题决不能解释为对人的本性存在的否定。换言之,此命题应被解释为人的本性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conditioned)或为其“所显现”(manifested),而不应解释成前者为后者所决定(determined)或前者为后者所消解(dissolved)[注]N.杰拉斯:《马克思与人的本性:一种传说的反驳》,第45—46页。。此外,这一解释的正确性也从下述事实中得到证明:这一解释与老年马克思在历史唯物论思想的代表作《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等后期许多著作中所阐发的关于人的普遍规定,不仅在逻辑上一脉相通,内容上也完全吻合。正是这点构成了杰拉斯《人的本性与历史唯物论》一章讨论内容的核心。
杰拉斯的这一马克思研究充满了学术上的诚实和审慎态度,不过如前所述,这种表现倒置了分析对象的本末。首先,我们可根据“A = A”这一逻辑学的同一性原理,说明《提纲》的诸命题。如果“人的本性(A)= 社会关系的总和(B)”这一等式想要成为有意义的命题,那么它就应以“A不是B自身”或“B不是A自身”为前提。如果A是B自身,B就无需提示其他名称,应还原为A = A这一无意义的同语反复。因此,如果想使A = B这一同一性的命题变得有意义,其前提就是A和B应是不同的存在。这时A与B的同一性意味着所谓黑格尔意义上的非同一性的同一,即部分地共享同一性要素,同时持有各自不同的存在自身。所以,如果马克思否定了人的本性的存在自身,那他就应当明确提出“并不存在人的本性”或“所谓人的本性是无意义的概念”等陈述。然而,马克思一次也没有提出过这种陈述。尤其重要的是,在《提纲》的命题中,不是单纯提出了A与B的同一性,而是附加了“在其现实性上”(in der Wirklichkeit)这一限定语[注]与此同时,杰拉斯也明确表明,先于这一命题之前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这一命题也不可能成为对人的本性的否定。即“A is not B”形式的文章并不是对A与B的同一性的全部否定,而是对将A的同一性限定于B的否定,换言之,可以拥有“A is not only B”的意义。(同上,第31—32页。)。
德语“wirklich”“Wirklichkeit”是动词“wirken”的派生词,本来与“werken”是同义词,与英语“work”语源相同。当然,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实际发挥作用和效果的状态。黑格尔把这个词用作自身特有的哲学词汇。它引起一个人的现实存在内容与其本质的一致状态。换言之,它意味着某一事物完成其概念的状态[注]正因如此,他的《法哲学原理》《序言》的名句才得以成立:“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序言》第11页。)。因此,这个词与单纯具体地、经验地显现和作用意义上的德语“real”是有区别的。不过,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既没有把这个词用作独立的哲学用语,也没有从概念视角特别区分real与wirklich。他的前后期著作一以贯之的主线是对当时现实即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批判。不仅如此,他对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批判核心是,批判他们不是把资本主义现实接受为历史地决定了的东西,而是把它接受为绝对的现实自身。在马克思那里,这是理解“现实性”(Wirklichkeit)意义的关键。
对于马克思来说,现实性意味着具体地、经验地发挥作用,以及感性地被把握、被体验的世界。但是,这种意义并不是全部。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世界,例如资本主义“现实”的世界是畸形的、片面的、异化的世界,是应被批判、否定和克服的扭曲世界,即虚构的现象世界。于是,这样的现实批判不仅是以感性地、经验地显现的现象为前提,而且必然以与普遍理念和价值相一致的真正的现实存在为前提,而马克思理所当然地把这种现实概念化为共产主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的这种批判逻辑就形式化为“本质”(Wesen)“显现”(Erscheinung)以及“假象”(Schein)等的对立概念[注]此处之所以限定为“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地把这个对立概念展示为一个独立的方法论体系。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对这个问题作了经典研究。他的研究充分表明,马克思后期代表作《资本论》的整体结构是建立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的。(参见H.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伦敦:劳特利奇与克冈·保罗出版社,1973年。)。换言之,所谓“现实性”一方面意味着由于本质与外部现象一致而显现的(erscheinen)自身状态;另一方面意味着虽然显现为感性的、经验的世界,但本质没有得到实现的,进而与本质相游离的“虚构的状态”(Schein)。因此,马克思的人的本性即人的本质(Wesen)问题,也可以在这样的脉络中得到理解。与此相关,让我们重新返回到《提纲》。
如果应用上述概念图式,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解释马克思“人的本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命题的着重点。在此,他并不是否定人的本性本身,而是强调人的本性如何获得其实在性,即人的本性在一切社会关系中显现为外在现实。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现实性上决不是完备地体现了人的本性的状态,而是本质与显现(Erscheinung)相分离的虚构状态(Schein),即只不过是人的本性被异化的状态而已。马克思激烈批判亚当·斯密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及边沁等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其批判的核心在于,这些人仅仅把资本主义这一虚构现实把握为外在地显现的现象,而未能将这一现实把握为与其本质与显现的尖锐对立乃至冲突。
在《人的本性与历史唯物论》一章中,杰拉斯把这一点说明得很清楚。作为典据,他不仅明确提到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关于人的异化问题的各种陈述,也展示了明确展开历史唯物论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后期著作中关于人的本性的各种陈述。在他看来,这些陈述都有力地证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本身是建立在他的人的本性概念基础上的[注]与此相关,杰拉斯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中下述两段陈述。第一段,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一边批判边沁,一边指出“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Hundnatur)。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Nutzlichkeitsrinzip)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die menschliche Natur im allegemeinen),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4页。)第二段,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在比较必然王国与自由的王国时,这样写道:“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交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8—929页。)这些陈述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明确区分了被实现的人的本性的状态,即本质与现实相一致的状态与这两方面相分离的状态,并且以这种区分为根据批判了畸形的、片面的、异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恰恰在此暴露出杰拉斯解释的根本界限。如前所述,杰拉斯未能深入阐明人的本性概念所必然包含的本质论(essentialistic)的意义。为了具体阐明这个问题,首先应当调整研究维度,即不是阐明杰拉斯所展示的马克思思想中“人的本性”这一消极维度,而是深入底层,检讨他所展示的马克思思想中人的本性概念的积极内容。
杰拉斯从下述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展现了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的积极内容:第一,“人是凭借自身的生产活动实现创造潜力的存在”;第二,人是在社会关系中形成这种活动的“社会存在”(Gemeinwesen)。他以马克思后期著作为根据,尤其以《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die Grundrisse)、《剩余价值论》为根据说明了上述两个方面[注]N.杰拉斯:《马克思与人的本性:一种传说的反驳》,第80—86页。。借此,杰拉斯想强调,“人是社会存在”这一规定既不意味着否定普遍的人的本性的存在,也不意味着人的本性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相反,马克思追问,每个人的需求满足都产生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那么,为什么这种需求满足必然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关系?为此,他试图阐明这种自然的、因而符合人的本性的分工体系恰恰为资本主义分工体系所扭曲的过程。
不言而喻,杰拉斯的解释与上述“本质-显现-假象”的批判图式完全吻合。换言之,可从下述三种向度的关系概括关于马克思的讨论:人的本性中内在的社会性(Wesen)内容;与这种本质相一致的“自然的”社会分工体系(Erscheinung);虽具有分工体系的显现但不是人与人之间真正合作的分工,即剥削关系被伪装为分工的虚构的分工体系(Schein)。因此,就“das menschliche Wesen”而言,杰拉斯解释的界限在于,未能在马克思思想的整体向度中始终如一地说明Wesen的意义。但是,这种界限并不是内容上的缺陷,而是用语上缺陷,即缺乏术语的一贯性,因而可以说,这种界限无关宏旨,并无大碍。他的根本界限在于上述问题,即针对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的积极内容,他未能提出不言而喻的疑问并阐明其意义。其疑问和意义正是作为人的本质的创造性和社会性的问题。
作为人的本质的创造性和社会性概念由来已久,家喻户晓,以至于现在重新提起这个概念显得有点陈腐不堪。因此,当检讨人的本性概念的这一内容时,重要的不是单纯整理上下关联语句,而是仔细甄别是否存在概念内容上的特异性、独创性以及与思想体系整体的概念一致性、统一性等。虽然杰拉斯的相关论证未免过于单纯化,但他率先说明了人的创造性、社会性问题这一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根据,在某种程度上为阐明马克思政治思想的特异性、独创性做出学术贡献。但是,杰拉斯浅尝辄止,流于表面,并未深入阐明本原上人为何具有这种创造性和社会性,与这一疑问有关,他也没有进一步检讨马克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系统地、普遍地阐明了这个问题。此外,归根结底,这种阐明必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阐明,这点更深层次地显露了杰拉斯研究的限度。
毋庸置疑,虽然有关陈述缺乏完整性和体系性,但马克思确实讨论过自身人的本性概念的形而上学基础。与此相关,他的“类的存在”(Gattungwesen)概念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出现。不过,对这一概念的检审以及哲学的阐明牵涉另一项独立的工作。因此,笔者将在第五部分阐明有关这个概念的基本问题,并且展望今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主要争论点。
五、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的形而上学基础:“类的存在”
迄今已有许多学者通过“社会存在”探讨了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的主要内容,即“类的存在”概念[注]主要作者及代表作有:S.阿威纳日:《卡尔·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8年;B.奥尔曼:《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概念》,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P.桑蒂利:《马克思论类存在与社会本质》,载《苏维埃思想研究》第13卷,等等。。令人不解的是,杰拉斯全然没有提到最明确地说明了“类的存在”概念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此外,在《论犹太人问题》等著作中,马克思也明确使用过Gattung概念。但是,在检讨马克思陈述的其他研究论著时,杰拉斯也只限于整理有关词句的表面意义,而没有深入领悟马克思类的“概念存在”所固有的理论-实践意义。然而,恰恰通过“类的存在”概念,马克思试图说明人的社会性和创造性的根据,这最鲜明地体现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下述两段表述中:
人是类存在物(Gattung/specikes-being),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Gattung)——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universell)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
有意识的(bewusst)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
在上述两段话中,马克思想要传达的意思很明白:人是普遍的、自由的存在,这种自由和普遍性的根据不在于意识到自身、他人以及一切外部对象是单个的个别存在物,而在于意识到这些都是普遍的类的一个构成体,并且以这种普遍意识为基础,在普遍向度中对待一切个别对象。就像德语“Bewusstsein”一词已经包含存在性(Sein)一样,马克思所强调的是意识与行为的本原统一性以及这种意识自身的普遍存在性[注]在此,大体上,马克思也不是用“allgemein”一词而是用拉丁语词源“universell”标明了个别性与具体性的对立意义,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
当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其他早期著作中,马克思有关人的本性的这种陈述都显得是极其凝练和高度简化的。很清楚,马克思的有关陈述需要加以更具体的说明,特别是在他那里,Gattung概念的根据并没有得到充分展示,这应当说是他的学术不成熟性的一种表现。但是,充分地、完整地恢复这种说明的不充分性或概念的不完整性,正是当今研究者的一项不可推卸的任务。与此同时,应当更加系统地阐明马克思“类的存在”概念自身——它的具体内涵,可概括为“与其他人以及自然全体的统一性中,能够追求自由的、普遍的生活行为的存在”——所依据的更加本原的概念根据。如果不阐明何谓人的意识自身的存在论根据,即所谓形而上学问题,这个问题是绝对无法阐明的。
马克思从未明确探讨作为自身社会哲学、社会科学的终极基础一类的形而上学问题。因此,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他的思想并没有形成十分完整的体系。但是,如果从哲学史语境理解他的思想,我们就会发现借以克服其“非完整性”的可能线索。这个线索正是“类”(Gattung)概念自身。限于篇幅,在此笔者只能简要提示一下,为什么这个概念自身能够成为解答问题的决定性线索。
西方人性论传统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其源头远远超越苏格拉底,可上溯至犹太人的旧约圣经时代。从研究视角看,这种传统不是从个别的人的向度而是从普遍人,即借以统一个别人的人类(human species/die menschliche Gattung)向度理解人的问题。撇开近代相关哲学探求不谈,单是近代德国哲学中,特别是在康德哲学中,人的本性问题一直是哲学思维的中心问题。就是说,康德的全部哲学都可以归结为对人的理性的、道德本性的探求。只是康德没有在同自然秩序整体的连续中,系统讨论那种与事物有别的人的内容(what is specifically human)[注]值得注意的是,英语“species”一词衍生于像“specific”一类的拉丁词源spec(look)。而已。这在费希特、谢林那里也是相同的。在这些人的哲学中,人的问题都从正面得到了凸显,然而,他们都把人把握为自然这一秩序中的一个类,换言之,并没有从“客观向度”中把握人[注]参见J.L.纳维卡斯:《意识与现实》,海牙:尼霍夫出版社,1976年。。
黑格尔第一次从客观向度探讨了类的概念。在探究自然整体辩证发展过程的《自然哲学》(die Naturphilosophie)一书的末尾[注]G.W.F.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二部:自然哲学》,法兰克福/美因:苏尔卡姆普出版社,1970年,第367—370页。,他集中探讨了这个概念,而恰恰这一概念本身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黑格尔那里,《自然哲学》既是连结《逻辑学》和《精神哲学》的桥梁,也是表现精神在自我发展过程中的自为(Für-Sich-Sein)的环节(Moment)。正因如此,在黑格尔那里,类的概念恰恰表现从自在精神到自为环节的前进过程。换言之,这种过程就是通过与他者的结合,超越时间,维持自身的同一性(Identitaet),形成旨在克服作为生命体而势必感受到的实存(Dasein)的有死性[注]同上,第374页,附录。。因此,在黑格尔那里,类的属性基本上是色情的,最终在“性关系”(das Geschlechtsverhaltnis)中显露其具体面貌[注]同上,第369—370页。在这一语境中,黑格尔恰当地把德语的独特意义应用于自身的哲学“行为”中。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所使用的“Gattung”可译作多种英语,例如“genus”“species”“kind”乃至“the generic”等。实际上,由于德语Gattung一词本身意义多种多样,其内涵也很晦暗不明。“Gatte”一般指称配偶。格林兄弟《德语大词典》把这个词与拉丁语“socius”“consors”“conjux”,即同伴、同行人、配偶或新妇的意义联系起来。格林兄弟指出,Gattung的同义词是gatten,而“sici gatten”的意思是“结合”或“交接”。。换言之,精神上显现其具体面貌的那个永恒性以及与他者的辩证统一性乃是在“两性结合”这一类的必然过程中认识其开端的。
虽然黑格尔死后,将这一概念进一步大众化的是斯特劳斯[注]大卫·弗里德里希·斯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1874),德国新教哲学家、神学家和传记作者。他运用辩证哲学,通过反对力量的内在斗争强调社会进化,通过解释新约在神话中对基督的描述,在圣经解释中开辟了新天地。主要著作有《耶稣生平修订》(Das Leben Jesu kritisch bearbeitet, 2 vol., 1835-1836); 《新旧信仰》(Der alte und der neue Glaube, 1872)等。,但为了区别人与动物而特意利用这一概念的却是费尔巴哈[注]关于这种概念史的简要解说,参见D.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卡尔·马克思》,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1969年,第91页及以下。。此外,毫无疑问,在发展自身的社会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需要超越的主要对象之一正是费尔巴哈其人其说。
在此,笔者挂一漏万,极其扼要地介绍了与“类的存在”概念相关的哲学史进程。但是,即使是这种简要的说明也足以表明,作为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核心的“类的存在”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哲学、社会学意义。可以说,这种丰富的内涵远远超出了包括维纳布尔、杰拉斯在内的迄今所有马克思研究者们对这一概念的研究结果。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类概念被用以说明自然哲学到精神哲学的过渡,那么,基于对黑格尔类概念的正确理解,马克思是如何创造性地发展了自身“类”的存在概念呢?这不仅是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哲学史的关键问题,也是理解马克思思想之未完成性的核心问题。而且,唯有通过这种追本溯源、刨根究底的文本研究,才能避免肢解马克思理论——例如,东拉西扯,牵强附会,随意比附现实变化;盲目迎合马克思思想,偏执于马克思思想的纯粹性,如此等等——从而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探索新思路,开辟新途径,开创新局面。
(责任编辑 巳 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