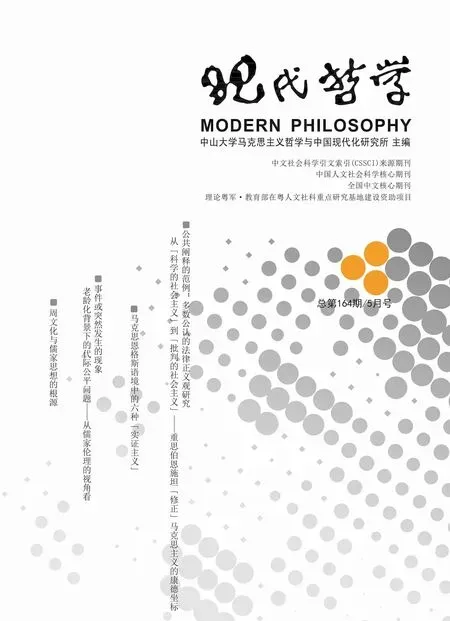罗明坚对《中庸》道德哲学概念的释译
王慧宇
16世纪来华耶稣会士拉开了东西文化交流的大幕。随着耶稣会士“文化适应”和“科学传教”策略的开展,大量欧洲神学、哲学、科学思想进入中国,开启了“西学东渐”的进程。同时,传教士亦开始中国典籍翻译工作,将中学经典传至欧洲,成为“中学西传”的先声。值得关注的是,在这场文化交流盛宴中,“道德”问题一直是双方关注的焦点。基于伦理道德和宗教的密切关系,传教士十分重视对西方伦理思想的传播,有大量著作问世,希望借由中国士大夫对伦理问题的关注来推动耶儒交流。在中学西传方面,传教士译介的重点“四书”“五经”也包含了大量中国道德智慧,正是这些西译经典,让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欧洲知识分子开始憧憬道德昌明、崇拜理性的中国。基于“四书”的重要性,明清之际有众多“四书”译本存世,而传教士译介“四书”的先驱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
“道德”在中国传统中的重要性无需赘言,特别是到了宋明儒学时期更是将道德、人格完善赋予了超越意义。“四书”作为儒家道德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自朱熹编定后,便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统治地位。道德哲学是《中庸》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中蕴含了道德本体、道德主体、道德伦理等方面内容,与西方哲学、神学有较大的公共讨论空间。本文将通过集中考察罗明坚的《中庸》译本情况,特别对其中儒家道德哲学“仁”“诚”“君子”等概念展开分析,以此讨论罗明坚等人对儒家道德哲学体系的理解。
一、罗明坚拉丁文“四书”手稿概况
罗明坚的拉丁文“四书”手稿藏于罗马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伊曼努尔二世馆(Biblioteca Nazionale V. Emanuele II di Roma),共344页,分五部分,含“四书”和《明心宝鉴》。据笔者考证,译本创作时间应为1591-1593年间[注]关于手稿写作时间及作者的争论问题,参见王慧宇:《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与翻译:以罗明坚〈中庸〉手稿为例》,《国际汉学》2016年第4期。。在拉丁文“四书”前罗明坚还完成过一部西班牙文“四书”手稿,其中包含《大学》《中庸》和《论语》的部分章节。西班牙文“四书”手稿是呈给西班牙国王阅示的清晰手抄本,拉丁文手稿字迹相对潦草、外加保存不善,研究整理存在一定的难度。两部手稿内容基本一致,是现存于世的最早“四书”欧洲语言译本,其译者是首位在华正式定居、开启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先河的耶稣会士罗明坚。
二、《中庸》译本中儒家道德哲学概念的释译
通过对全文的整体性考察,罗明坚的《中庸》译本是在朱熹的《中庸章句集注》基础上,理解文本内容,后翻译《中庸》原文而成[注]在《耶稣会士罗明坚〈中庸〉拉丁文译本手稿初探》一文中,罗莹对罗明坚《中庸》译本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底本进行了详细比对,笔者通过考察文本亦同意此观点。参见罗莹:《耶稣会士罗明坚〈中庸〉拉丁文译本手稿研究初探》,《基督教文化评论》2015年第1期。,而在概念的诠释译介上也有大量参考朱子注解的痕迹。
1.中庸
先看“中庸”。罗明坚用“semper in medio”(总是在中间)来译“中庸”,“中”为in medio,“庸”为副词semper。他虽将“中庸”合译,但也可拆分训解。其中,“中”为“in medio”(在中间),虽无错,但远未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也”[注][南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9页。的深度。“庸”的翻译则更值得关注。semper有“总是”“经常”“永远”之意,与程颐“不易之谓庸”“庸者,天下之定理”[注][美]杜维明:《中庸:论儒学的宗教性》,段德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1页。基本一致。朱子强调“庸”的平常义,除了照顾训诂的根据外,主要是认为平常的东西才是实践中能长久的,诡异高难的东西是无法长久的,强调道理不能离开人伦日用,隐含了对佛教离开人伦日用去求超越境界的批评。朱子说《中庸》是“实学”,强调中庸的道理不离事事物物[注]陈来:《朱熹〈中庸章句〉及其儒学思想》,《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夏之卷。。罗明坚并未理解到这一深度,遂也未将西学中的实学特质彰显。罗明坚认可“中庸”作为至德,指出“总是在中间就是此中间的最高完美”(Semper in medio hoc est ad summam perfectionem hujus medii),并强调通达这种至德的关键在于semper,即不断地保持。
2.诚
“诚”是《中庸》乃至宋明儒学核心概念,是将“命”“教”“性”“道”连接起来的纽带[注]王夫之说:“曰‘命’、曰‘性’、曰‘道’、曰‘教’,无不受统于此一‘诚’字。与此不察,其引人入迷津者不小。”([明]王夫之:《船山全书》第6册,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第996页。);它作为“一切道之道”“一切德之德”,又是连接人道与天道的枢纽[注]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9—40页。。若将《中庸》看作最具儒家心性和形而上学特性的著作,而其构建的重点就是“诚”推出的诚本论。
“诚”道德层面的本义是诚实不欺、真实无妄,扩展到“天道之诚”和“人道之诚”问题上,则增加了超越向度。宋明儒学各家依“诚”展开的思想体系错综复杂,初来中国的罗明坚很难对“诚”做全面深入的解读,辨析各家差异。他所能讨论的范围和关注点更多还是“诚”在人的终极道德完善方面如何展开。在儒学内,天道本就是真实的,不存在“不诚”,“诚者天之道”是在向人展现的层面来谈。人之“诚”正是对天道之诚的追求,实现道德完善的过程,“中庸”恰恰是君子修身、通达天之诚的方法之一。在儒家,“诚”的实现虽是个人修身范畴,但终不离终极的天道,其中正体现了儒家的超越关怀。
基于“诚”的复杂性,在译介时众多译本多是取“诚实”之意,如译成sincerity。但这种翻译将儒家以“诚”为中心的修身之学完全限制在日常实践范畴,彻底消解了其超越向度,无法翻译出宋明儒学的精髓。像陈荣捷虽用sincerity,但却会特别注意强调“诚”联结天人合一的性质,阐释“诚”必须既有心理学的、形上学的、也有宗教的含义,不只是心态,还是动力,无时无刻地在转化万物、完成万物,将天人联结到同一的文化之流中[注][美]陈荣捷编著:《中国哲学文献选编》,杨宾儒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06页。。杜维明则明确指出“诚”要兼具sincerity、truth or reality的含义,不仅是一个本体论概念,还显示人的实在性,更是道德哲学概念,显示人本真的存在,是一个贯穿儒家伦理、宗教和形而上学的中心概念,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概念[注]乔飞鸟:《〈中庸〉英译本比较研究:以理雅各、辜鸿铭、陈荣捷译本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2年,第101页。。
罗明坚也注意到“诚”的特点和复杂性,用rectus和veritas两个词互为补充来译介“诚”。这两个词本身含义非常丰富:rectus指形状直的,引申为适宜、正直;veritas则为真实、诚实,更指真理、实在。例如,对于“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他译为“与生俱来就正直的人是由至高天之光所允许的;但他不是生为正直,而是做到正直,那么,他要做自己的工作;他生而有正直,对任何事物达到目标,不需要考虑他获得事物本身,没有任何头脑的运转,他跟随理性的引导,这个人很显然是神圣的,但正直的人做事情时选择善,他较好地把握此善”(Qui cum hac rectitudine nascit à caelesti supra XX[注]此处手稿字迹模糊。lumine fastus e[st]; at qui non sic rectus nascitur, sed rectus faciendus est, sua ipsius opera faciendus e[st]; qui verò cum rectitudine natus est, nullo negocio scopum attingit, sinè ratiocinatione assequitur res ipsas, sinè ulla mensis agitatione rationem ducem sequitur, hic planè divinus e[st] vir, at qui rectus humana fit opera bonum eligit, ac fortiter tenet)。其中“诚者,天之道”朱子解为“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注][南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第32页。,罗明坚正是用rectus强调“天道之诚”的客观上的真实性。同时“faciendus”(做)也强调了“人道之诚”中的个人修炼。又如,在译“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时,罗明坚译为“由上天和神圣之光照亮并被赋予真理的人能知晓所有事情;并且这被称为上天的教导或者本性;达至人们对事物知识的人跟随真理之光,这被称为教导,被天赋予真理的人是智慧的,他所理解人的事物立即变成正直”(Qui à caelesti divinoque lumine veritatem dotatus e[st] nihil est quod non intelligat; et haec aucat caelestis disciplina, seu natura; qui humana opera ad res intelligendas pervenit veritatis lumen tandem consequetur, et haec doctrina nominatur, veritatem dotatus à caelo illico est sapiens, qui humana opera intelligit illico fit rectus)。陈来认为“朱子以德和明两者作为分析的基点,他认为圣人德无不实,这是诚;圣人明无不照,这是明。德是道德的德性,明是理性的能力”[注]陈来:《朱熹〈中庸章句〉及其儒学思想》,《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夏之卷。。而罗明坚则用“caelesti divinoque lumine”(上天和神圣之光)来阐释“明”的含义,彰显了儒家的宗教色彩,也为后续的儒耶调和打下基础。如果回归当时西方思想环境,此表述暗含了这种理性能力来自天主。但在西班牙文《中庸》译文中,罗明坚将“天”翻译为中性的“arriba”(向上)。罗明坚针对不同读者群体,在译介过程中采取不同的词汇。西班牙手稿因为是献给腓力二世的礼物,因此用arriba指自然之天。但是在拉丁文手稿中,更加体现了罗明坚对《中庸》概念的切实理解,保留了《中庸》文本本身的宗教性色彩。圣人能“率性为道”“自诚明”,其天然如此,因而罗明坚用“veritas”(真理)解其“天道之诚”。“贤人以下都是修道为教,由教而入,不是自然,而必须用各种功夫,先从学知明善入手,然后去实在地践行善,这是人道的特点”[注]陈来:《朱熹〈中庸章句〉及其儒学思想》,《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夏之卷。,因此罗明坚使用veritas和rectus交互解释“人道之诚”,突显人之修身践行的重要性。
罗明坚对《中庸》中“诚”这一概念与修身观念的把握,多是立足实践德道方面,适当兼顾超越和宗教因素。特别是他使用veritas和rectus交替释译“诚”,有意识地在翻译诠释中区别“天道之诚”和“人道之诚”,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诚”的超越意义,相较后世译本更体现了其思考的丰富。例如,《中国哲学家孔子》和《中华帝国六经》将“诚”仅译为“vera solidaque ratio,perfectus”(真实且坚定的理性、完美)以及“veritas(studio,arte acquisita)”(通过学习和技艺追求真实)等单纯的道德德性,完全消解“诚”的超越意义,相应地,儒家也仅仅是道德智慧,而不具备哲学、宗教的高度。
3.仁
“仁”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性不赘多言。《中庸》正是一个关于人性(“仁”)的整体论述,而不是格言集锦[注][美]杜维明:《中庸:论儒学的宗教性》,段德智译,第23页。。考察罗明坚如何理解并翻译“仁”,可见其对儒家德目的具体理解。
罗明坚在《中庸》译本中对“仁”的翻译用词也是极为丰富的,分别用了pietas、caritas和amor等词语。pietas和caritas多在互动中共同释“仁”。如“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译为“如果在美德之路上前行,他最大程度地完成了慈爱和仁爱这些美德。与仁爱连接的慈爱从人的本性出发”(Si per iter virtutis incedit; iter autem virtutis caritatem, maximè pietatem absoluit. Caritas cum pietate coniuncta homini insita est à natura)。其中,“修道以仁”之“仁”为caritas和pietas,“仁者,人也”之“仁”为pietas,而caritas则翻译“亲亲”。罗明坚十分明确地用pietas来指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之“仁”,而caritas主要释“亲亲”之爱,而在亲亲之“仁”时则为 caritas和pietas,用caritas对pietas解释补充。如“仁、智、勇”三达德中的“仁”则为pietas。caritas和amor则多在情的层面讲仁与爱。caritas有“爱”“博爱”之意,amor为“情爱”。不幸的是,译本中涉及amor处文献严重损毁已无法辨认,无法全面分析。
用caritas和amor解“仁”更为明确直接,后人用agape将天主教“爱人如己”之“神爱”赋予“仁”,或如英译中的humane、benevolence等译文亦可在含义中查到“仁”某一层面的含义。
以pietas译“仁”实为罗明坚之独创,相较后来者有其高明之处。在西方语境中,pietas是含义极为丰富的概念,其含义极为复杂,其内涵几经嬗变,值得思考。在古罗马时期,pietas有“忠诚”,即忠诚于君臣、父母之含义;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又扩展为人际关系层面的一种德性,包含忠诚、虔敬、仁慈、友善等多重含义,甚至还可表达“圣母对圣子耶稣的情感”[注]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米开朗基罗为教廷雕刻的圣母怜子雕像,名称即为“La Pietà”。。pietas也是英语词汇pity的词源,某种层面上又含有同情、怜悯、悲悯之意。但拉丁文在16世纪已开始衰落,其概念语词的意义能否继续发展确实有待商榷。如不回到当时具体文本考查pietas这一德目的含义,其他推断显然有失公允。与sapientia(智)、fortitudo(勇)、caritas、amor甚至是agape相比,pietas这一德目的外延更为丰富,相应内涵也更为模糊。罗明坚选择pietas这一当时已不常用的名词,很可能是在权衡“仁”作为至德、作为天道之人伦体现的意义后做出的深入思考。“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儒家传统中智者、勇者未必就是仁者,但仁者必须体现智勇。“仁”在儒家整个伦理体系中有着毋庸置疑的优先性和统摄性,“三达德”“四端”“五常”“九经”都是在“仁”的基础上展开的,并在不同层面丰富“仁”的内在资源[注][美]杜维明:《中庸:论儒学的宗教性》,段德智译,第70页。。pietas确实可涵盖sapientia、fortitudo、caritas的某些含义,因而可在“至德”和“统摄”意义上表述“仁”。借此可以发现,罗明坚对中学德目的概念辨析是深入的,对文本含义和概念在儒学伦理体系中的整体把握是有充分考虑的,其对于中学“德目”的表述翻译相较后世学者丝毫不显逊色。
4.君子、小人、圣人
在罗明坚拉丁文《中庸》译文中,将君子译为“vir bonus”(好人),小人译为“vir malus”(坏人),以善恶作为君子和小人的衡量标准。但在个别情况下,他也用“vir sapiens”(智慧的人)来指君子。翻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时,他指出“小人(坏人)对任何事物都不谨慎,对任何事物都不恐惧”(quia malus vir nihil cavet, neque reformidet)。君子在于能够“保持总是站立在中间”(Vir bonus semper in medio consistit),即“持中”;小人“总是在中间之外”(Vir malus semper extra medium e[st]),原因在于小人无所慎、无所惧怕。此处,罗明坚应是对朱子该处注解“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则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注][南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第21页。的直接翻译。在对儒家道德的最高典范“圣人”的翻译上,罗明坚将其译为“vir sapiens et sanctus”(神圣而智慧的人)或“divinus vir”(神圣的人)。这里的“圣人”“神圣”更多是指道德、哲学意义上的概念,并非特指天主教含义的“圣人”,而是强调人能通过德性完成自己,如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我们人最好的部分,即德性,是我们身上‘最神圣’(divine)的东西”[注]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05页。。站天主教传统的立场上,罗明坚将孔子列为“圣人”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在天主教文化下也并未称圣,其后利玛窦、柏应理等传教士皆沿袭了罗明坚对孔子的评价。但这也为日后的争端埋下伏笔,耶稣会之外的修会大部分认为不能称孔子为“圣人”。特别是在“礼仪之争”全面爆发后,罗马教会也正式否认孔子为“圣人”这一称谓[注]但中国奉教士大夫既不否定孔子为圣人,也没有违背教规称其为圣品,而是强调称孔子为圣人,“原只是造极之名,如孟子所谓‘美、大、圣、神’者,各有训解在,非泰西之所谓圣也,泰西特借用我国之字耳”。(参见林金水:《明清之际士大夫与中西礼仪之争》,《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三、结 论
罗明坚在其拉丁文“四书”,特别是《中庸》手稿中极力凸显伦理道德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他的拉丁文《中庸》一直将美德、美德的修炼贯穿整篇译稿,如将“道”译为“iter virtutis”(美德之路)以及“virtutis exercitatio”(美德的修炼)等。他也在译本中特别注重彰显儒家的理性因素,赋予儒家“礼”以“理性”“自然法”的含义。在罗明坚的《中庸》译本中,“礼”不仅有“ritus”(礼仪)、“ceremonia”(仪式)的意思,还有“lex”(法)的含义。例如,他将“斯礼者,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译为“Hoc e[st] ut etiam ipsi urbium praetores eadem legem luctus servandi tenerentur”(此城之官员应遵守关于哀悼的同样规定)。而“法”往往与“理性”交织在一起,如他对朱子注释的“达道者,循性之谓”解释为“perfectae rationis, et legum observatio”(完美的理性和对法律的顺从)。在罗明坚所处的西方思想环境中,“理性”与“法”是紧密联系的。在他的诠释下,“礼”与“法”借由“理性”交织在一起。
综上,罗明坚对儒学、对“中庸”道德哲学诸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在先秦儒学君子修身的范畴内,他并未像利玛窦一样对“古儒”与“今儒”有明确的取舍判断。但他对儒家经典的肯定、对儒家道德哲学的肯定,恰恰为其后百余年东西文化交流开拓了一条光明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