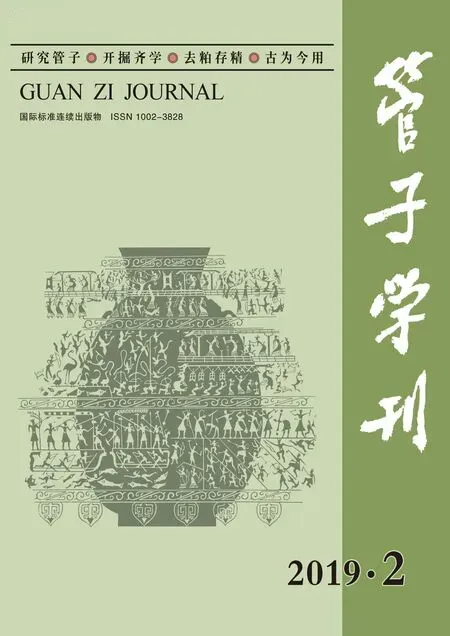《管子》四篇身心修养论相关命题探赜
陈志雄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100872;台州学院 和合文化研究院,浙江 台州 318000)
《管子》中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篇章我们通常将其视为是一个思想整体,称之为《管子》四篇(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它是形成于战国时期的黄老道家作品。其立足于气化宇宙生成论而展开的一套身心修养论,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所创造性提出的一系列新范畴、新命题极大地深化了黄老道家的思想境界。本文尝试从《管子》四篇的这些范畴与命题出发,重新探讨和评估其身心修养思想的价值和意义。
一、释“白心”
《白心》是《管子》四篇中的重要一篇,但对于这一篇名的来龙去脉历来争议较大。我们知道,郭店竹简《性自命出》是子思一派的著述,周凤五教授在《上海博物馆楚竹书〈彭祖〉重探》一文中指出,儒家文献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中“心欲柔齐而泊”就与“白心”的观念相关。而且,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彭祖》中有“远虑用素,心白身怿”的说法,也都出现了类似的《管子》用语注相关情况可参看《庆祝钱存训教授九五华诞学术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南山论学集:钱存训先生九五生日纪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11-15页。。此外,在《庄子·天地篇》,凿隧入井取水的丈人与子贡的对话中谈到:“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所谓“机心”正与“纯白”“白心”观念相对。《心术上》也说过:“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洁,神乃留处。”从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白心”的表述在子思与庄子那里也有类似的,因此它在《管子》四篇这里并不突兀,也就不能将其视为某一思想流派的专属特征。所以有的学者针对《庄子·天下篇》中出现的“以此白心”的字眼,将其作为认定《管子》四篇也是宋钘尹文的遗著的一个论据,显然是会站不稳脚跟的注更有学者经过详细考证,认为《国语·周语上》中“祓除其心,精也”也和“白心”概念相关。详见林志鹏著《宋钘学派遗著考论》,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354-356页。况且,《管子》这里也只是借用“白心”一词作为篇章之名,正文中并没有直接出现关于论述“白心”思想的内容。由此,我们可以推测,“白心”可能是一种当时人们所普遍共享的思想资源或既成的日常观念,因为它作为一种流行话语而被《管子》作者或整理《管子》的后人借用下来,使得自己的篇章标题更加醒目;而且《管子》四篇完全可以继续运用这种普遍观念来继续发挥,以凸显自己的思想特色。而当我们再仔细研究下四篇的其他篇名时就会发现,“心术”和“内业”同样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就目前所见,郭店楚墓儒简《性自命出》的第十四支简中有:“凡道,心术为主。”简五十四则有:“独处而乐,有内业者也。”[1]62-65在这一极小的文本范围内竟然都出现了《管子》中的篇名或用语,这不得不说这种流行话语的套用与互相借用现象在当时应该不是个别的或偶然的。
既然《管子》四篇这么推重“白心”这一流行话语,那么它一定有其深厚的思想渊源,这从《老子》[注]本文凡引《老子》原文皆依据王弼本,并随文只注篇章之名,如有不同理解则另出注说明。参看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中华书局,2011年。的一些思想中或许可以找到线索。《老子·四十一章》:“质真若渝,大白若辱。”[注]“大白若辱”一句原在“上德若谷”之后,陈鼓应依高亨、张松如之说,将其移置于“质真若渝”之后,今从之。见于陈鼓应著《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第227-231页。以及《老子·二十八章》:“知其白,守其黑。”在老子正言若反的思想表达方式中我们更能够了解到“白”的内涵。前一句中,所谓“辱”是指黑垢,是说质朴而纯真却好似浑浊的样子,最洁白的好似含垢了的样子,老子以此来描述“道”的冲虚、含藏,而“白”就应该是指一种素白、无染尘杂的状态,以及永葆素朴的质地。这一意思也就与《心术上》所要讲的“虚素”相合。其有言曰:“‘恬愉无为,去智与故’,言虚素也。”这都是说要排遣掉一些不必要之情欲的牵绊与智巧营为的干扰,而归之于冲泊质真的状态。所以,我们会发现《管子》四篇虽然借用了“白心”作为篇名,但在关于这一概念的思想性内涵上,它有了自己的创造性转化,从而树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虚素”。因此,对于这一篇名我们不必要拘泥考究太多,而应该把更多的目光聚焦到它背后所关联的思想内涵,并将其阐发出来。
“白心”思想对于《管子》四篇的重要性可以这么来看待:其一是突出了对“心”之作用的重视。“心”作为一种具有统合功能的器官,在人的生存活动中是具有主宰性地位的。如《心术上》说:“心之在体,君之在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心”管理着其他一些能够接触外物,获取知识、信息的感官,人当然就会在这种接触万物、获取外界信息的过程中产生一些心理上的变化,有的变化就会是消极的,以至于会出现有诸如“迫于恶”“怵于好”等惊慌、恐惧或苦闷情绪的困扰,这都是导致人产生疾病,减损寿命的原因所在。近来,就有学者结合现代生命科学学说对《管子》四篇中所体现出的“心法”做了很好的阐释,并认为包括《管子》四篇在内历代先哲们所倡导的“中华心法”是作为“复制子”载体的人类个体,在面对不可测的人生和不确定的世界,为了维护自身健康幸福的人生,所可以采取的真正彻底的有效途径。并相信,挖掘并弘扬《管子》四篇心法思想及其治心途径,当能为缓解人们的生活压力、调节心身健康提供有益的帮助,进而有效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注]相关研究成果可参看周昌乐:《宋钘“心法”思想及其科学阐释》,《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可见,《管子》四篇的养生原理,表现了一种“亦养生亦修养”的特色,它表明一个人的养生水平与其修养程度是高度相关的。按照这样来看,或许我们就可以说:修养越高的人,原则上应该是越养生的,寿命会是越长的。这种论断应该还是有立足于黄老道家的一些基本理念,而不是凭空的。比如说:人的修养就是要复归本真自然,不要矫揉造作。而这种本真状态被认为是最适合人的天性的发挥及其生存和发展的,人在这种状态下应该是最安适的。因此,修养不再仅仅是一种面向公共生活的道德伦理活动,也是一种关乎自身生命延长之切身利益的保生活动。在这里,身心修养对人来说更是不得不要被引起重视,它能够极大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一种成全他人与自己的双重任务。其二是它和《管子》四篇中的“虚欲”观念相一致。诚如陈鼓应教授所指出的,“白心”事实上就是《心术上》中所提到的“洁其宫”“虚其欲”的观念[2]162。这一论断确实是一针见血。而“虚欲”观念又直接将《管子》四篇的身心修养论与政治学说相沟通起来,依据这个枢纽点,几乎就覆盖了四篇近一大半的思想。接下来我们将对这一问题加以重点论述。
二、论“虚”的哲学
首先,《管子》四篇之所以倡导“虚”的价值理念仍然是依据于“道”之情。《内业》中就说到:“被道之情,恶音与声。修心静音,道乃可得。”“道”之原情是守虚静的,而厌恶杂音与语声,只有积极修养身心以守虚静,道才能不离于身。从这样的最高立场出发,倡导“虚”也就能被理解了。再者,对于“道不远而难极也,与人并处而难得也”一句,《心术上》是这样解释的:“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故曰‘不远而难极也’。虚之与人也无间,唯圣人得虚道,故曰‘并处而难得’。”我们认为,后半句应该这样断句,即“虚之,与人也无间,唯圣人得虚道,故曰‘并处而难得’”。“虚之”二字之所以应该单独成句,就在于它是说:一个人只要能够保持这种“虚”的境界或状态,则在与人共处中能够不起争端、不互相妨碍(“无间”),圣人正是把握到了这种与人相处的“虚道”。他们这样正是“道”之“并处而难得”特点的具体体现,“道”时时刻刻与人共处,但人却难以捉摸到它,天地间人与道处在一种和谐的律动中,无有互相窒碍,这其实和“不远而难极也”是一个意思,只不过前半句更多是就道本身来讲,而后半句则是专对人(甚至专对于“圣人”)来说。此外,既然因为“道”是广大无边的,它遍布在天地之间,作为有限性的单个人想要去把握它,并不是件如平常一般的事那么容易。“虚”之道则可以使个体实现以最大的阙无来去拥抱最大的实在之体。正因为能够“虚”,人才能最大限度地摆脱一切常规常理性的束缚,尽情的去感知这个“道”,使这个“道”能够淋漓尽致地绽露在自己的身心性命中。
“虚”字在《管子》四篇前后文中多次出现。“虚”有时候不仅是指涉一种人的心灵状态或某种精神性价值,也会作动词“放空”解。比如:“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洁,神乃留处。”(《心术上》)也就是说要放空、排遣掉那些过分的欲望,扫除纷杂,才能够安定神来入住。这里的“虚”字正和后文的“扫除”一词义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正所谓欲壑难填,人世间的许多纷争也都是因欲望的不满足而发,所以排遣那些过分的欲望是十分必要的。但不仅欲望要排遣,就连一些知虑也要加以摒弃。其有言曰:“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智乎,智乎,投之海外无自夺,求之者不及虚之者,夫圣人无求之也,故能虚无。”[注]此句原作“求之者不得处之者,夫正人无求之也,故能虚无”。唐人尹知章将其注解为“将欲求之智,终不知其处而得之也”,文意依然很不通畅。依郭沫若《管子集校》里的说法,“得处”二字系讹误,当改为“及虚”。此外,王念孙认为,“正”字是“圣”字声之误也,当改正。参看陈鼓应著《管子四篇诠释》,中华书局,2015年,第120页。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撰《管子集校》(下),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635页。(同上)这里再次出现了“虚之”一词,正和前文义同。此句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性:如果人人竞驰于智术与谋略,而道高一尺,魔高又是一丈的,相互之间比拼,则人与人永远是处在一个无底洞里打旋涡,最终损伤的是人自己的神智,搅扰的是人的心灵。圣人拥有最高的“智”,那就是无所求之于“智”,不以“智”为一种值得被欲求的价值存在,而是能够“虚无”。所以圣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是能够游刃有余的,既不受盘根错节的事务牵累,又能够随机应变。从这里可以看到,《管子》论述“去智”的问题还是离不开对“虚”这一核心范畴的把握,“虚”的精神实质和“去智”的主张实现了对接,并且它使得“去智”的主张具有了很高的现实针对性。“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同上),现实中人人都一心想获得更高的智慧,以期能够在人生剧场里获得更大的优势,获取更多的利益。但在四篇作者看来,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才是获得真正智慧的正确途径,最后反而是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无所适从了。
那么,当作为一种精神性价值,“虚”就是指一种出于理智性的退让,是一种暂时性的主体不在场,不主观保留,因而它可以是一种“无”。这种“无”当然不是永久性的回避与缺位,而是以这种暂时的不在场来实现一种更加理智、更加从容的回归,以一种更加稳健而巧妙的姿态来登场。这就是《管子》四篇中“虚”之哲学的独特魅力,它可以帮助人获得一种更加高超的精神智慧。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提及一下《管子》四篇与同样是黄老文献的《黄帝四经》在这方面的关联。许抗生教授认为,《黄帝四经》中的《经法》《称》《道原》三篇时间上应该早于《管子》四篇,后者可能是对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3]76-78。如果这一论断成立的话,《经法·名理》中所说的“道者,神明之原也”也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理解了。因为“道”如何能是人之精神智慧的源泉,《经法篇》并没有给出具体说明,只是留下了这么一个简白的开放式命题,给予后人很大的解释空间。而对《管子》四篇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了,因为既然道借助于精气而能充满天地之间,精气也就能够进入到人之中,构成事物的本原,那么它对人的精神智慧的作用自然也是不在话下。人只要能够“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枝坚固,可以为精舍”(《内业》)。以及“有神自在身,一往一来,莫之能思。失之必乱,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将自来。精想思之,宁念治之,严容畏敬,精将至定。得之而勿舍,耳目不淫,心无他图。正心在中,万物得度”(同上)。还有又说“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同上)。也就是说,当人做到了“定心在中”“敬除其舍”,则本处于游离弥漫状态的精气自然能被收纳于心,并在自己的精神生命里发挥作用。所以,人要获得高超的智慧还离不开对“精气”这一根本源头的积聚与酝蓄。
那么,具体该如何做到“虚”呢?这要分两边来看:在应物前,就是要保持虚静的状态,不躁动、不预设、无知无虑、不要有过多或不必要的期许,虚静以待之,静观其变。所谓“虚者,无藏也,故曰去知则奚率求矣?无藏则奚设矣?无求无设则无虑,无虑则反复虚矣”(《心术上》)。以及“‘君子之处也若无知’,言至虚也”(同上);而在应物时,“‘其应物也,若偶之’,言时适也,若影之象形,响之应声也。故物至则应,过则舍矣。舍矣者,言复所于虚也”(同上)。就是要能够随顺应变,不忤逆、与事态发展同行,时已过,则不挂念、不留恋,复归于应物前的本然状态。我们可以发现,道家或黄老道家每每在论述这种虚静或因循应物问题时,都常以“形影”“声响”的比喻来说明,这种类似比喻在《庄子》中也是不少见,如“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庄子·内篇·应帝王》)。所谓“块然”就是指如土块一样,在这里是形容人于任何事上都无所偏私,去琢复朴之后不知不识的样子。众所周知,诸如“土块”“形影”“声响”这类事物是没有生机和能动性的,因为“物”是无知之物,没有思虑,也没有先见,也恰恰因此它不会裹挟有一种主观偏私性,这正是为黄老道家所要提倡的。
要真正达到“虚”,还有一方面是需要“节欲”或“去欲”。“夫心有欲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心术上》)欲望在心中的存留和积渍,有时候会让人的五官都失去正常功能运转,使人心不在焉,如此则百事殆矣!
三、“节欲”与“去欲”之辨
“无欲”“去欲”“节欲”,三者都是针对欲望问题的一种伦理主张,它们所代表的价值观念之间显然是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但是却同时出现于《管子》四篇的不同篇章中,以至于经常会被人拿起来质疑四篇到底是不是成一思想体系的?[注]笔者另撰有一文对此问题有所探讨,具体可参看陈志雄:《〈管子〉四篇道气关系论辨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9年第1期。抑或是说这是《管子》四篇在理论建构上不够成熟的表现,以至于把一些具有细微差别的概念范畴给放在一起言说?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去欲”的出处是在《内业》中。其有言曰:“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忧乐喜怒欲利。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彼心之情,利安以宁,勿烦勿乱,和乃自成。”(《内业》)所谓“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事实上就是一种“去欲”的观念,其意思大概接近于“无欲”,认为“忧乐喜怒欲利”这些情绪的产生乃是导源于对外在欲望的追逐,因此主张要去除欲望。我们还要注意到《管子》四篇中有“无求”一类的说法。比如:“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智乎,智乎,投之海外无自夺,求之者不及虚之者,夫圣人无求之也,故能虚无。”(《心术上》)以及“故曰去知则奚率求矣,无藏则奚设矣。无求无设则无虑,无虑则反复虚矣”(同上)。很多学者都认为“无求”也就是一种“无欲”的表现,尤其是当和《势》中的“故贤者诚信以仁之,慈惠以爱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中静不留,裕德无求,形于女色。其所处者,柔安静乐,行德而不争,以待天下之濆作也”相参照时,这种意涵就更加明显了。
而同样也是在《内业》中,其后文却有“心能执静,道将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无败。节欲之道,万物不害”(《内业》)。这里直接提到了“节欲之道”,并且它们认为人人要是能够节制嗜欲,则万物之间并育而不相害。再者,又说“忿怒之失度,乃为之图。节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同上)。这是说对于由人体眼、耳、鼻、舌、心五种官能所产生的欲望要加以节制。以及说“食莫若无饱,思莫若勿致,节适之齐,彼将自至……凡食之道,大充,伤而形不臧;大摄,骨枯而血冱。充摄之间,此谓和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饥饱之失度,乃为之图。饱则疾动,饥则广思,老则长虑”(同上)。无论是饮食还是思虑用脑上都要调节适当,注重分寸,讲究节制不过度。其中,饮食的过度或过少都会直接导致伤形,而且这种伤形还是通过“血气”对人发生影响的。“大摄,骨枯而血冱”就是说过于饥饿会导致血消减而凝滞。尹知章也说:“饱而疾动,则食气销。”[4]947在《心术上》又说:“恶不失其理,欲不过其情,故曰‘君子’。”其中强调人的喜好之欲不要超过常情,显然也是一种在节欲层面上来展开讲的。可以说,《管子》四篇中已经有了比较成型的“节欲”观念,但行文中还是有诸如“去欲”或“无欲”的观念闪烁着。“去欲”和“无欲”这些概念在四篇里虽然没有直接出现,但是类似的表述却是广泛存在,这使得《管子》四篇在对待欲望问题上表现得有一些模棱两可之处,而往往让研究者百思不得其解。
当我们在单个思想流派内部苦苦找不到其自身思想逻辑一致性的原因时,这时就有必要把目光转移到宏大的思想史图景中,在那里有着同时代的思想参照系,或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同处于战国时期的孟子说过:“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孟子在论“养心”的问题上主张要“寡欲”,“寡欲”事实上也就是节欲。再朝前看,儒家系统里还有《论语》里所载的:“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论语·公冶长》)通常我们都把它理解为是孔子的无欲观。清人刘宝楠正义有载:“郑注云:‘刚谓强志不屈挠。’……志不屈挠,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能无欲也。”[5]180而在《论语·子路》中孔子也说“刚、毅、木、讷,近仁”。对此,王肃注云:“刚,无欲也。”[6]188至于此,一个摆在眼前的明显事实是:儒家内部也曾经历了从“无欲”到“节欲”的一个思想转变,与之相伴随的是历史已经是从春秋时期走向兼并混战的战国时代,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来说,春秋时期诸夏之间由于沾亲带故,其所发生的战争往往是一种带有礼仪性质的,主要以“争义”为主,开战前还要互相通报,很少是以掠夺财富、侵占领地为目的。而进入战国,这种宗法制度下的温情不复存在,代之以不择手段的阴谋权术,一些上层贵族野心勃勃,穷奢极欲,相互倾轧、吞并的现象层出不穷,社会政治形势变得十分残酷。所以,对处于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来说,以“无欲”的说辞,显然是收拾不住人心的,其理论主张会显得很苍白、很无力。相较而言,“节欲”会是一种比较好的共同倡议,也显得更具有现实说服力,有利于凝聚共识。因此,不论对于孟子还是《管子》四篇的作者,都需要努力做出这种思想调适,在这种调适过程中,出现新旧参半的思想两可性也是在所难免的了。所以,《管子》四篇在对待欲望问题上的两可表现,或许正是对战国中后期社会政治状况的一种因时制宜的反映。再者,如前所述,《管子》四篇脱胎于《黄帝四经》,因而还带有《黄帝四经》中关于“无欲”的思想成份也是有可能的。例如,《黄帝四经·道原篇》中就有:“无好无恶,上用□□而民不迷惑。上虚下静而道得其正。信能无欲,可为民命;上信无事,则万物周扁:分之以其分,而万民不争;授之以其名,而万物自定。”[7]409这里还特别针对在上者而言,认为他们苟能无欲、无事,则百姓自然能够得以立命而各安其性。在汲取了《黄帝四经》的思想要素后,《管子》四篇也慢慢实现了从《道原篇》的“无欲”到《内业》的“节欲”的一个转变[注]对这一见解的详细论述见于黄崇修:《〈黄帝四经〉阴阳观对〈管子〉“定静”工夫形成之影响》,《哲学与文化》,2015年第10期。。
当然,以上的论述也不妨碍我们做另外的一些推测与厘定。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状况,原因还有可能是,在稷下思想论辩中,《管子》四篇作者前后话语表达可能也会不断调整,以能够应对其他思想流派的挑战,而这些表述最后可能被编辑者都给汇编到《内业》中来了,形成了现在所见的文本状况。再者,也有可能这正是四篇在这一理论问题上不成熟的事实性表现,它没有达到足够的概念区分度,确立自己稳定的术语表达式。
四、关于“内静外敬”命题
“内静外敬”这一命题是在《内业》中被提出来的。其有言曰:“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从这段文本来看,“内静外敬”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心性修身问题,也是一个关于处世方法的问题。当对治自己的内在心灵世界时,要讲究“虚静”,保持自己内心世界的独立性;当面对外在纷繁复杂的世界时,最行之有效而可达之天下的方式是要依循以“敬”为核心精神的“礼义”规范[注]荀子说过:“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荀子·修身》)关于荀子“礼”的思想与《管子》四篇这里的“内静外敬”命题之间是否有关联性,我们需要另文加以深入探讨。。对于人世中出现的种种“不敬”之行为现象,《管子》四篇给予了最直接的贬斥。如《白心》中说:“满盛之国,不可以仕任;满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骄倨傲暴之人,不可与交。 ”生活穷奢极欲的满盛之家与生性“骄倨傲暴”的狂妄行为,都是一种不敬的表现,其危害性自然是很大的。进而又明确指出了由“不静”与“不敬”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四体既正,血气既静,一意抟心,耳目不淫,虽远若近。思索生知,慢易生忧,暴傲生怨,忧郁生疾,疾困乃死。思之而不舍,内困外薄,不早为图,生将巽舍。食莫若无饱,思莫若勿致,节适之齐,彼将自至。”(《内业》)所谓“不静”往往表现为人内心过多的思虑、忧郁、疾困;“不敬”则更多表现为外在行为举止上的慢易、暴傲等。其实,在人的实际生存境遇中,“内静”与“外敬”二者往往是交互影响,内外相互作用。比如说,就“慢易生忧,暴傲生怨”而言,当你“慢易”“暴傲”(不敬)时,就会产生“忧”“怨”“怒”等诸如此类的情绪来搅乱了自己的心境(不静);又如“不喜不怒,平正擅匈”“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当祛除了喜怒的变动搅扰,保持心境平和,人才能平正处事,因此处“静”是守“敬”的可靠途径。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该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对于人来说,“内静”与“外敬”两个方面会是相互作用的呢?窃以为,内外之所以会交互起作用,根柢还是在于人是“气化”的存在,这在《内业》的文本思想陈述上也得到了体现。在“内静外敬”这一命题提出的前文,正是讲到了:“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见,其征不丑。平正擅匈,论治在心。此以长寿。忿怒之失度,乃为之图。节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因为人是“精气”与“形气”和合而生的,气能流通于人的内外上下,所以“静”与“敬”的修养达成效果对人的影响作用是一贯的。这种作用机制就在“气”上,也就是说“气化”的思维是实现人的身心内外相贯通合一的前提条件。人的身心内外是合一的,尽管有时这种“合一”是在一种偏误意义上的相合,但内外皆偏误也足以证明人的身心内外是高度一致、连贯的。
当然,保持“静”和“敬”,实现了“内静外敬”,最终又能对这种精气的流行气化产生作用,使得精气安养在人的身体内,成为人生命创造之源泉。“形不正,德不来;中不静,心不治。正形摄德,天仁地义,则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极,照乎知万物。中义守不忒,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是谓中得。有神自在身,一往一来,莫之能思。失之必乱,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将自来。精想思之,宁念治之,严容畏敬,精将至定。得之而勿舍,耳目不淫。”(《内业》)这里还提到了“敬除其舍,精将自来”“严容畏敬,精将至定”,因此“敬”的内涵还包括有做事认真对待,以“敬”来克除散漫懈怠,保持外表仪态上的严整,容貌上的端庄。显然,《内业》把这种“敬”看做是采纳安养精气的必要路径。并且,在这段话中,作者更加突出了“敬”,而在之前的“守敬莫若静”中则更主要是强调“静”,二者对于《管子》四篇作者来说似乎都十分重要,才需要这样费口舌分别加以论述强调,与此同时二者发生的侧重点也得到了区分。
五、重视形身调养
四篇特别重视人肢体的强健,所谓的“筋肕而骨强”(《心术下》),而不是老子笔下的“骨弱筋柔”(《老子·五十五章》)或“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以及“专气致柔,能如婴儿”(《老子·十章》)。老子认为,通过集结精气以达致于如婴儿般的柔弱状态,而柔弱处下可以战胜刚强,使自己避免遭受一些戕害。但《管子》四篇却说:“抟气如神,万物备存。能抟乎?能一乎?……四体既正,血气既静,一意抟心,耳目不淫,虽远若近。”(《内业》)尹知章注曰:“抟,谓结聚也。结聚纯气,则无所不变化,故如神而物备存矣。”[4]943老子所谓的“专气”正是《管子》中的“抟气”。但《管子》所作的“抟气”工夫目的是要使自己的四体强壮、血气平和、精神饱满,因而和《老子》还是存在一些差异的。
《庄子·大宗师》中记载,当孔子问及什么是“坐忘”时,颜渊回答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而在外篇的《知北游》中更有:“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的主张。孟子也说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尽管庄子和孟子并不是直接有毁生灭性的主张,但他们的倾向让我们看到,战国时代思想界似乎存在着一股通过坏身以求精神超越的思想暗流,将肉体形身视作是人进行精神追求的累赘。基于此,我们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精神的超越与境界的提升一定是要通过减弱肉身肢体之娱逸的方式来实现吗?
《管子》四篇就不这么认为,他们主张心形双修、形德交养,并且形神是可以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谈在评点总结黄老学说时说到:“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8]759因此,没有形体的保全与康健,人的精神修炼从何谈起?四篇认为,只要按他们的要求真正做到了“虚”,注重“节欲”,那么形身的存在就不会如庄子所认为的是一种额外负担。况且,形身的坚固、体格的强壮是立足于精气的涵养或“抟气”来达成的,使精气能够充满于自己的形身之内,这当然也是“道”之生成活动的其中一环,“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藏以为泉原,浩然和平,以为气渊。渊之不涸,四体乃固;泉之不竭,九窍遂通。乃能穷天地,被四海,中无惑意,外无邪菑,心全于中,形全于外;不逢天菑,不遇人害,谓之圣人”(《内业》)。因而可以说形体的强健是值得被欲求的一件事。“抟气如神,万物备存。能抟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诸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四体既正,血气既静,一意抟心,耳目不淫,虽远若近。”(同上)在形体康健的基础上,人的精神灵明也变得饱满起来,形神真正实现了兼顾交养,人的生命就达致于“大清明”的状态。所以,归结起来看,《管子》四篇是把形神和合作为一种人的生命完美状态,形神不和,人的生命则不成。这是由于人在生命源头上就是天地之“精气”与“形气”相和合而生的:“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同上)
强烈的淑世情怀以及治事应务的思想取向,使得黄老都比较重视对形身的维护,因为现实中各种活动的开展根本上是要由一个健全的形身来支配,功业的创造离不开以健全的生命体为基础。就如《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在孝治思想引领下,爱身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所以对黄老学说也是如此,在追求治事应务与强调重视形身之间可能还存在着一些逻辑关联性。
——修身与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