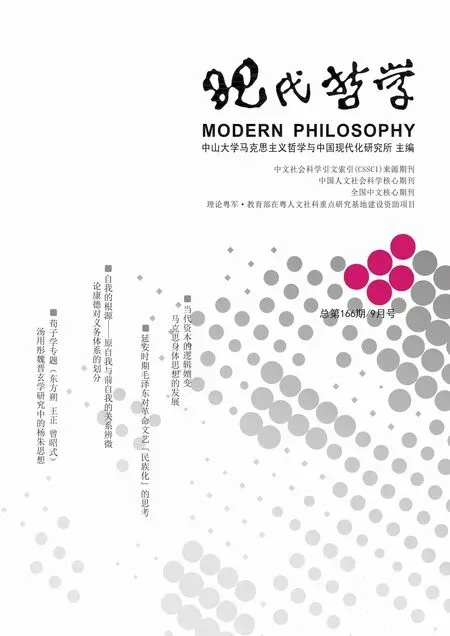自我的根源
——原自我与前自我的关系辨微
岳富林 王 恒
自我问题是胡塞尔现象学中的一项核心议题。在文本跨度上,自1898年《论感知》(1)Edmund Husserl, Ms. A VI 11 I, SS. 185-186, in Eduard Marbach, Das Problem des Ich in der Phänomenologie Husserls,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4, S. 6.文稿伊始,历经1901年《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1913年《纯粹现象学通论》(以下简称《观念I》),1929年《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直到1936年《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以下简称《危机》),可以说,胡塞尔整个哲学生涯都在思考自我问题。在现象学实事上,自我及其意识生活是对象显现以及对象认识的根据,整个超越论现象学的主题就是自我及其意识与世界之间的意向性关联,即世界在超越论自我及其意识之中的构造。超越论现象学的真正问题是构造问题,自我的“自身构造是所有那些所谓超越构造、世界对象性构造的基础”(2)[德]胡塞尔:《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张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24页。 引文在必要处有所改动,以下不再说明。,因此,探究自我自身构造之可能性和可理解性的本我学(Egologie)就是构造现象学的基础。下文第一部分将表明,自我自身构造的最终根源是原自我和前自我,它们不再诉诸某种更原初的自我概念。
关于原自我与前自我的关系,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提出了诸多不同的解读方案,具有代表性的是:李南麟(Nam-In Lee)的静态/发生式解读、田口茂(Shigeru Taguchi)的近距/远距式解读、倪梁康的形式/内容式解读、马迎辉的正史/前史式解读。这些方案具有交叉相似之处,也难掩其核心差异。遗憾的是,对于如此重要的问题,目前这些方案几乎都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相互之间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对话。有鉴于此,本文致力于厘清诸种解读之间的关系,分析它们对胡塞尔文本的忠实度,进而尝试提出既整合以上解读、又与之不同的解读方案。
一、作为根源的原自我与前自我
在正式进入原自我与前自我的关系之前,首先要对“自我的根源”这个表述正名,即,指出原自我、前自我对自我的最终奠基特性,对克劳斯·黑尔德(Klaus Held)、丹·扎哈维(Dan Zahavi)、艾杜德·马尔巴赫(Eduard Marbach)、艾尔玛·霍伦施泰因(Elmar Holenstein)将原自我、前自我的层级混淆于纯粹自我、人格自我的层级进行批判,对阿尔文·迪默(Alwin Diemer)将原自我这个根源混淆于前自我这个根源进行批判。
(一)超越论自我的被奠基特性
超越论自我是构造性的主体,经验自我是被构造的客体。在共属超越论态度的意义上,纯粹自我和人格自我都被称作超越论自我。纯粹自我是空洞的同一性极,人格自我是习性关联的统一体。对纯粹自我的讨论集中在《观念I》,对人格自我的讨论集中在《现象学的构成研究》(以下简称《观念II》)。而《观念I》《观念II》都局限在内在时间性领域,这个领域在意识流中具有其构造根源,相应地,纯粹自我和人格自我也应当在意识流中具有其构造根源。
在发现现象学还原并经过一段摇摆期(1907-1912)之后,胡塞尔在公开发表的《观念I》中果断承认纯粹自我在超越论领域中是绝对存在着的。但正如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所指出的,胡塞尔在《观念I》中涉及到两种绝对性的含义:一种是存在的必然性,与之相对的是存在的偶然性;另一种是存在的终极性,其存在不需要任何东西作为奠基,与之相对的则是被奠基之物(3)[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17页。。在前一个意义上,纯粹自我作为纯粹意识主体无疑是绝对被给予的;但在后一个意义上,纯粹自我这种“超越论‘绝对’实际上并非最终物;它是在某种深刻的和完全独特的意义上被构造的东西,而且它在一种最终和真正的绝对中有其根源”(4)同上,第204页。。具体而言,纯粹自我作为同一性极是意向体验之内在的超越,而“意向性……这个层级不下降到组成一切体验时间性的最终意识的晦暗深处,而是把体验看作内在反思中呈现的统一时间过程”(5)同上,第213—214页。。所谓“最终意识的晦暗深处”即构造起内在时间统一的意识流。
自我不仅是空洞的纯粹自我,还是具有其习性积淀的人格自我。一方面,人格自我作为具有稳定风格和固持习性的基底自我,具有从出生到成长、成熟直至衰老、死亡的发展过程,它与纯粹自我一样都是在内在时间中的绵延统一,因此人格自我也必定具有其在意识流中被奠基的特性。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承认他在《观念II》中的研究与《观念I》一样“完全保持在内在时间性内部”(6)[德]胡塞尔:《现象学的构成研究》,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6页。。另一方面,人格自我的习性不仅是主动行为之构造成就的积淀,而且一开始是由完全被动的本能所驱动的(7)同上,第213页。,因此,人格自我必定具有其习性动机关联的本能性“前人格”(Vorperson),正是后者使得我最终有可能将自身理解为“人格”(Person)。
(二)奠基性的原自我与前自我
自我的自身构造与内时间构造具有紧密的相关性,“构造现象学的基础也就在于,在内在时间性构造学说以及被归入它的内在体验构造的学说中创立一门本我学理论”(8)[德]胡塞尔:《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第24页。。关于时间构造,胡塞尔坚持区分意识流本身的流动与在其中被时间化了的河流,前者即活的当下的“原时间化”(Urzeitigung),后者即诸时间相位相互交织的自身延展。因而在自我的自身构造上,内在时间中的纯粹自我和人格自我应当具有其在原初流动中的“原存在”(Ursein)或“前存在”(Vorsein)(9)Edmund Husserl,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 1929-1935, hrsg von Iso Kern,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3, S. 584.。
通过对被奠基的纯粹自我及其生活加括号,胡塞尔最终还原到作为“原根基”(Urgrund)的原自我及其“原生活”(Urleben)(10)Edmund Husserl, Zur Phänomenologischen Reduktion,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26-1935), hrsg von Sebastian Luft,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 S. 300.。首先,原自我具有匿名性和唯一性。原自我是在活的当下中始终发挥着功能的原极,它不能被任何反思性直观所把捉到,更不是被回忆的对象自我,它是完全逃逸的、匿名的。同时,原自我具有独特的唯一性或“人称上的无变格性”(persönliche Undeklinierbarkeit)(11)[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33页。,它先于当下自我与过去自我之分,先于自我与他者之分。原自我既不是我也不是你/他/她,而是个体性之“人称”及其变格所构造的源泉。因为一切人称变格都是通过自身时间化构造起来的,而自身时间化又奠基于原自我的原时间化。其次,原自我与“原初非我”(urtümliches Nicht-Ich)不可分离地相统一。在活的当下中可以抽象地区分原自我以及作为其对立面的原初非我,原自我即在触发与行为相互唤起之前发挥着构造功能的原统觉,原初非我即“世间实在性之可被本己感知方面的现象学剩余项,即感觉质素,在其本己时间化中的原质素(Urhyle)”(12)Edmund Husserl, Späte Texte über Zeitkonstitution (1929-1934), Die C-Mnuskripte, hrsg von Dieter Lohmar, Dordrecht: Springer, 2006, S. 110.。原初非我为原自我而存在,前者在本质上是自我性的。作为一切存在者及其时间形式的原源泉,原自我与原初非我“这两个原根基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因此只能抽象地得到自为的考察”(13)Ibid., S. 199.,原时间化既是原自我的又是原初非我的原时间化。再次,原自我在原时间化中自身分异并自身融合。原自我生活在活的当下的原流动之中,它具有在原时间化中的存在。在原时间化中,存在着为分异奠基的“原分异”(Ursonderung),以及为统一奠基的“原融合”(Urverschmelzung),原自我在原分异中自身分异,在原融合中自身统一,它具有一种流动而持立的“二-一性”(Zwei-Einigkeit)(14)Ibid., S. 255, 76.。
不同于原自我,前自我是作为未被揭示本能之中心的前人格,它“固然是中心,但尚不是‘人格’,遑论在通常人类人格意义上的人格”(15)Ibid., S. 352.。在《逻辑研究》中,本能一方面被理解为非表象性的体验,另一方面被理解为不确定的表象体验(16)[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743页。。在后期研究中,胡塞尔将这两种理解分别对应于未被揭示的本能(本能,第一本能)和被揭示的本能(本欲,第二本能)(17)Edmund Husserl, Grenz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 Analysen des Unbewusstseins und der Instinkte, Metaphysik, Späte Ethik,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08-1937), hrsg von Rochus Sowa und Thomas Vongehr, Dordrecht: Springer, 2013, S. 124.:未被揭示的本能完全就不是表象活动,既非确定性表象又非不确定性表象,被揭示的本能则具有不确定的表象;未被揭示的本能是远距过去的天生本能,被揭示的本能则伴随着人格自我的全部发展过程。天生本能是“一种属于灵魂存在之原初本质结构的意向性”,即追求自身保存的总体本能,其中包含着诸多特殊的本能,每项本能的满足都具有“一个未被满足的空乏视域”,因而重复是天生本能的本质(18)Edmund Husserl, Späte Texte über Zeitkonstitution (1929-1934), S. 169, 257.。天生本能非表象性地追求作为感受性材料(质素流)的目标,不清醒地具有其非实显的世界,前自我与非自我的感受性内容不可分离地相互联结,本能意向性既分离又融合,因此前自我处在一种尚未分化的状态。处在这种状态中的“胎儿”(Urkind)之具体活的当下就是母体,“子宫中的婴儿已经具有动觉,并且动觉地、移动地具有其‘事物’——已经形成了原层级中的原真性”(19)Edmund Husserl,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 S. 604-605.。未被揭示的本能通过重复、满足、断裂、不满、替代生成为被揭示的本能,即有意识地、表象性地朝向某个对象的追求(20)Edmund Husserl, Späte Texte über Zeitkonstitution (1929-1934), S. 253; Edmund Husserl, Ms. C 13 III, S. 13, in Nam-In Lee, Edmund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er Instinkte,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3, SS. 177-178; Edmund Husserl, Ms. C 13 I, S. 8,引自[日]山口一郎:《发生现象学中作为原触发性被动综合的本欲意向性》,钟庸译,《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9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98页;Edmund Husserl, Ms. C 16 I, S. 14,引自[日]山口一郎:《发生现象学中作为原触发性被动综合的本欲意向性》,第201页。。因此,相对于胎儿,襁褓中的婴儿已经就是被奠基的,它具有来自胎儿的经验获得物。
(三)对混淆层级和混淆根源的批判
通过以上对原自我与前自我对超越论自我之奠基特性的说明,就可以对马尔巴赫、扎哈维、黑尔德、霍伦施泰因混淆构造层级以及迪默混淆构造根源进行批判。
在《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自我问题》第九章(“展望胡塞尔后期对自我问题的态度”)中,马尔巴赫宣称,胡塞尔在后期延续了早期关于自我问题的态度,仍将纯粹自我看作行为的射线中心。他认为,与《观念I》将实显性我思扩大到非实显性我思相应,胡塞尔在20世纪30年代将纯粹自我以及自我中心化扩大到原统觉和本能意向性的层面,只是此时触发物向自我“射入”而自我并不向触发物“射出”,这种自我状态相应于非实显性体验中的“行为引动”(Aktregung)(21)Eduard Marbach, Das Problem des Ich in der Phänomenologie Husserls, S. 296-297.。这种理解必然导致将前自我仅仅看作纯粹自我的被动状态,而行为的被动模态以得到凸显的触发物为前提,触发物恰恰要在未被揭示本能的重复、满足、断裂、不满、替代中才能得到构造。因此,马尔巴赫显然混淆了前自我与纯粹自我的不同构造层级。
扎哈维比马尔巴赫更敏锐地注意到原自我的唯一性、人称上无变格性与自我的复多性、人称变格性之间的矛盾。他提出如下两点来化解这个矛盾:1.原自我的唯一性表示自我只能对自身具有自身意识,而不能对他我具有自身意识,这种唯一性并不排除他我;2.抽象的自我极无需参照他我就能得到刻画,而具体的人格自我要在主体间性之中才能够得到构造。他还断言前自我不过是前反思的非对象性自我(22)Dan Zahavi, Husserl and Transcendental Intersubjectivity, translated by Elizabet A. Behnke,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82-83, 71.。扎哈维的错误在于将原自我、前自我、纯粹自我都规定为具有前反思自身意识的索引性第一人称视角,完全错失了内在时间性与意识流之间的层级区分,进而混淆了原自我和前自我与纯粹自我之不同的构造层级。
黑尔德比马尔巴赫和扎哈维更深刻,他区分了内在时间领域和意识流领域,正确地指出持恒自我极已然是被时间化了的内在时间对象,它必定具有相应的构造性意识,即活的当下。遗憾的是,黑尔德并没有相应地严格区分原自我和纯粹自我,以致于认为原自我的匿名性和唯一性不过是后来扎哈维所拥护的“第一人称”(23)Klaus Held, Lebendige Gegenwart: Die Frage nach der Seinsweise des transzendentalen Ich bei Edmund Husserl, entwickelt am Leitfaden der Zeitproblematik,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6, S. 161.,原自我具有与纯粹自我一样的前对象性反思的自身意识。黑尔德虽然比马尔巴赫和扎哈维都更接近实事本身,但对“第一人称”的无差别使用,阻碍了他发现比纯粹自我更深层的原自我。
与黑尔德区分内在时间性和意识流相平行,霍伦施泰因区分了自我性的联想进程与非自我性的联想进程,前者的载者是超越论自我,后者的载者是原流动生活,“自我是河流在其中得到中心化的极,是河流作为动机场域而对之发挥功能的主体”(24)Elmar Holenstein, Phänomenologie der Assoziation, Zur Struktur und Funktion eines Grundprinzips der passiven Genesis bei E. Husserl,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2, S. 213.。这种原流动生活并非完全的无自我性,而是具有某种自我关联,即与本能自我的关联。与马尔巴赫一样,霍伦施泰因援引《观念I》中我思从实显性体验向非实显性体验的拓展,认为本能自我与超越论自我的区分不过是被动性与主动性之间相对的程度性差异。因此,霍伦施泰因最终不仅错误地将前自我理解为自我极,而且还错误地将前自我理解为原自我(25)Ibid., S. 213, 218-221.。
如果说扎哈维和霍伦施泰因由于混淆了构造层级而混淆了原自我与前自我,那么迪默则是在区分不同构造层级的情况下混淆了两者。迪默承认,超越论自我的诸还原层级与时间构造的诸层级相平行。在深化的还原中,胡塞尔发现,“永恒当下(nunc stans)作为绝对的原自我存在于一切时间性之前,也存在于在其具体性中之自我的时间性之前”(26)Alwin Diemer, Edmund Husserl, Versuch einer systematischen Darstellung seiner Phänomenologie, Meisenheim am Glan, 1956, S. 43.。同时,具体的人格自我奠基于具有遗传之空乏视域的前自我,正是通过从原初本能中苏醒,自我才将自身构造为具有确定视域的、成熟的、理性的、正常的原真本我(27)Ibid., S. 276.。他还说:“‘趋向’已然在自我中被前给予和被前标识了,这种趋向作为‘本欲’和‘本能’在其自我性生活或‘前自我性’生活中被瞄向,即作为一种‘原自我’而被瞄向。”(28)Ibid., S.123-124.于是,迪默将前自我混淆为原自我。但正如上文所说的,原自我与前自我之间的区分是非常明显的,原自我是绝对持立在活的当下之中的原统觉,而前自我是远距过去的天生本能中心。
当然,不能将原自我与前自我的混淆完全归咎于扎哈维、霍伦施泰因或迪默,毕竟胡塞尔本人有时候就含混地使用着原自我与前自我这两个术语。例如,“每个经验自我都是作为原自我开始的……每一个自我在自我出生时完全如每一个其他自我一样是同一地同一个东西(作为自我)”(29)Edmund Husserl,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Erster Teil: 1905-1920, hrsg von Iso Kern,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3, S. 407.“原自我及其原形态与原内涵中的本欲系统在被动性和主动性之中发挥作用”(30)Edmund Husserl, Grenz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 S. 102.,这两个文本的原自我明显就是处在本能阶段的前自我;而“原初的时间化进程就是前自我的”(31)Edmund Husserl, Späte Texte über Zeitkonstitution (1929-1934), S. 309.等文本的前自我所指的则是活的当下中的原自我。
二、对原自我与前自我之关系的几种解读
通过阐明原自我与前自我在构造上为纯粹自我和人格自我提供最终奠基,原自我与前自我在内涵上相互区分,下面我们正式考察原自我与前自我的关系。首先,我们将介绍对原自我与前自我之关系的四种典型解读。进而,我们将根据胡塞尔文本对这些解读进行辨析,以期查明这些解读的有效性。
(一)四种解读
1.静态/发生式解读
迄今为止,学界对原自我与前自我之关系的最典型解读是李南麟在《埃德蒙德·胡塞尔的本能现象学》中提出的静态/发生式解读。这种解读是从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严格区分而来的。李南麟认为,静态现象学针对的是非时间性现象之较高统一与较低统一之间的本质关联,发生现象学则从时间性方面处理较高统一与较低统一之间的本质关联;前者关注效用奠基,后者关注发生奠基;前者是描述性现象学,后者是说明性现象学;前者是后者的方法性前提,后者是对前者的深化和完善(32)Nam-In Lee, Edmund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er Instinkte, S. 18-21.。具体而言,静态现象学包含了客体化意向性为非客体化意向性奠基,自我为他者奠基,主体为对象奠基,当下化为再当下化奠基,而这些奠基关系在发生现象学中都不再成立,甚至要被颠倒过来(33)Ibid., S. 26; [韩]李南麟:《主动发生与被动发生——发生现象学与先验主体性》,《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8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54页。。自我在静态现象学中被看作是一个点状的、逻辑性的自我极,在发生现象学中被看作具有其整个超越论生活;前者具有明确的自身意识,后者仅仅具有模糊的自身意识;前者必然导致唯我论,后者则一开始就具有主体间性经验(34)Nam-In Lee, Edmund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er Instinkte, S. 19, 27, 67.。相应地,原自我作为超越论主体性中心就是一切效用的根源,前自我作为原初时间河流的自我性要素和远距过去视域中的自我性要素就是一切发生的根源。最终,由于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是“两种独立的超越论现象学观念,它们不可能彼此还原”(35)[韩]李南麟:《主动发生与被动发生——发生现象学与先验主体性》,第21—22页。,所以原自我与前自我就被看作相互独立的。
2.近距/远距式解读
田口茂虽然继承了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区分,但着重强调的是原自我与前自我在其它方面的区分。在他看来,原自我是最终的效用根源,前自我是最终的发生根源。原自我悬搁了一切主体间性的效用,而前自我一开始就是主体间性的。这种描述似乎不过是李南麟之解读的翻版,但与李南麟的决定性不同在于,田口茂认为原自我由于面临本己自我与复多自我的疑难才成为主题,前自我是出于意识发生的前层级而成为主题。原自我具有本己自我的明见性,因而原自我对于从事现象学活动的自我来说是最切近的;而前自我对于从事现象学活动的自我而言则是我意识历史中之不可被回忆过去的远距自我(36)Shigeru Taguchi, Das Problem des,Ur-Ich‘ bei Edmund Husserl: Die Frage nach der selbstverständlichen, Nähe‘ des Selbst, Dordrecht: Springer, 2006, S. 119.。在发生次序上,前自我虽然可以被看作原自我的发生前史,但在明见性次序上,对远距自我的理解必须奠基于当下近距自我的存在,前者只有通过后者才能被重构出来,后者比前者更具明见性和原初性(37)Ibid., S. 120-121.。
3.形式/内容式解读
国内学界对原自我与前自我之关系的最具代表性解读由倪梁康提出。一方面,他在某种程度上接受李南麟的解读,认为前自我既是原初时间河流中的意识底层又是超越论自我出生的原开端(38)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496页。;另一方面,他提出了与李南麟、田口茂都不同的解读方案。首先,他并不在区分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意义上区分原自我与前自我,而是将原自我和前自我都看作发生现象学的课题(39)倪梁康:《“自我”发生的三个阶段——对胡塞尔1920年前后所撰三篇文字的重新解读》,《哲学研究》,2009年第11期,第55页。。其次,尽管原自我与前自我都具有自身觉察(Selbstinnerwerden),但原自我是“所有时间化统一的原极点”,前自我是“自我发生学中在原自我和自我之间的一个阶段”(40)同上,第55、52页。,因为前者是纯粹形式性的追求活动,后者则在形式之上还具有丰富的实事内容。虽然田口茂也暗中持有形式与内容之分,但这是在静态与发生这两个次序中进行的区分(41)Shigeru Taguchi, Das Problem des, Ur-Ich‘ bei Edmund Husserl, S. 121.,而在发生现象学内部进行的形式与内容之分以倪梁康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4.正史/前史式解读
不同于田口茂在近距与远距的区分基础上将原自我和前自我分别看作自我的正史和前史,马迎辉在活的当下与原感觉意识的区分基础上将原自我和前自我分别理解为正史和前史。与其独特的时间构造分级相平行,马迎辉对自我的自身构造进行相应分级。在最终的两个构造层级中,活的当下在原印象、原滞留和原前摄的原分异与原融合中流动而持立,生活于其中的自我是原自我。活的当下奠基于最终的构造层级——原感觉意识的同期(Zugleich),后者是活的当下的生成前史。前自我作为生活于原感觉意识同期中的自我尚不具有活的原视域,因此前自我是原自我的生成前史。原感觉意识的同期不能分离于活的当下,只能抽象性地得到考察,因此,前自我在本质上并不独立于原自我(42)马迎辉:《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时间性与本我论——一种建基关系的考察》,《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73—75、79页。。
以上四种解读虽然互有交叉的地方,但它们的核心主张是严格区分的。我们应该选择哪种解读方案?对此,需要进一步分析它们对胡塞尔文本的忠实度。
(二)辨析
1.静态与发生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李南麟的如下理解无疑是完全贴合胡塞尔本意的:静态现象学和发生现象学都是本质性的而非事实性的分析,都是超越论的分析而不是心理学的分析;静态现象学是描述性现象学,发生现象学是阐释性现象学(43)[德]胡塞尔:《被动综合分析》,李云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81页。。
至于胡塞尔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区分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李南麟就陷入混乱了。他在《埃德蒙德·胡塞尔的本能现象学》中认为是在1916/1917年,在《主动发生与被动发生》中却认为是在1920年以后(44)Nam-In Lee, Edmund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er Instinkte, S. 25;[韩]李南麟:《主动发生与被动发生——发生现象学与先验主体性》,第15页。。事实上,胡塞尔在1912年为《观念II》写的铅笔稿就区分了本体论和现象学,前者在同一性中静态地考察固定物,后者在流动统一中考察发生性进程(45)[德]胡塞尔:《现象学和科学基础》,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4页。。只是到1916/1917年,胡塞尔才明确使用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这两个术语,前者研究对象在显现统一之中的构造,后者研究意识的先天发生规律,即“一切当下经验动机都回溯到过去的意识”(46)Edmund Husserl,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Erster Teil, S. 357.。1921年,胡塞尔进一步规定了静态现象学和发生现象学的主题,意识与对象的相关性属于前者,内时间河流的构造、内在时间统一体的构造、自然的构造、动物的构造等属于后者,发生现象学所研究的发生规律既包含时间规律又包含联想和再生规律,静态现象学则是以静态对象为指导(Leitfaden)的“入门现象学”(die Phänomenologie der Leitfäden)(47)Edmund Husserl,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Zweiter Teil: 1921-1928, hrsg von Iso Kern,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3, S. 38-41.。胡塞尔在1925/1926年将活的当下纳入发生现象学的主题,“活的内在当下本身的确是最普遍的发生现象”(48)[德]胡塞尔:《被动综合分析》,第167页。。1930年的研究计划延续了前面的规定,即对意向对象、意向作用及其自我极的研究是静态的,而“作为唯我论抽象之本我的自体发生。被动发生理论,联想。前构造”(49)Edmund Husserl,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 S. XXXVI.属于发生现象学。从1912-1930年的规定看,原自我与前自我都应被纳入发生现象学的辖域,因为它们都不是意向体验的自我、而是前行为的自我,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同一性极、而是流动的统一。这导致以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来区分原自我与前自我这种解读方案的破产。
另外,李南麟所宣称的诸奠基关系从静态现象学到发生现象学的颠转,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原初意识流先于任何意向体验,天生本能先于任何本欲追求或主动追求,不能将行为层面的非客体化与客体化之分运用到前行为层面。其次,原质素与感受性材料不是对象,而且原自我与原初非我不可分离地相统一,前自我与感受性材料处在未分化状态,因而这里谈不上主体与对象间的奠基关系。再次,前自我确实一开始就具有原移情性经验,但原自我并非唯我论式的,否则就是无视《危机》§54 b)(我作为原自我构造我超越论他者的视域……)中通过视域意向性对他者问题的解决。最后,从前自我作为自我的发生根源不能得出再当下化为当下化奠基的结论,正如田口茂所指出的那样,对前自我的再当下化必须奠基于原自我的当下化。
2.近距与远距
田口茂认为原自我是受到本己自我与复多自我的区分疑难而成为主题的。根据马尔巴赫对胡塞尔承认纯粹自我的动机考察,一个重要的动机是为了区分本己意识流与复多意识流、自我与他我。但是,原自我不是纯粹自我,田口茂明显混淆了承认纯粹自我的动机与承认原自我的动机,胡塞尔承认原自我不是为了解决主体间疑难,而是为了对纯粹自我进行最终的奠基。进而,上文对李南麟之自我与他者奠基关系的批判同样适用于田口茂,后者错误地将原自我局限在唯我论领域内,忽视了原自我在《危机》中对解决主体间性问题的贡献。
田口茂将原自我规定为近距自我,他所谓的近距有两种不兼容的含义,一是当下的近距,一是与从事现象学活动之自我的近距。我们无条件认同前一种近距,因为原自我就是活的当下中保持为永恒当下的原统觉,它并不随时间相位的流逝而沉入过去,相应地,前自我则是不可能被带至当下的远距过去自我。与此同时,我们果断拒绝后一种近距。欧根·芬克(Eugen Fink)根据“观念”时期的现象学还原区分了三种自我:经验自我、超越论自我与现象学自我(50)Eugen Fink,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in der gegenwartigen Kritik”(1933), Studien zur Phänomenologie (1930-1939),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6, S. 355-356.。现象学自我只能表示本己自我,超越论自我表示包含自我与他我在内的一切构造性主体。这种区分并不适用于胡塞尔后期进一步现象学还原所发现的原自我,原自我既不是经验自我也不是超越论自我或现象学自我,后三种自我已然是被构造的内在时间统一体,而原自我是意识流的原功能者;后三种自我是个体性的,原自我是前个体性的。因此,原自我的近距不可能是对现象学自我而言的近距,前自我也不可能是对现象学自我而言的远距。
3.形式与内容
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形式与内容具有多种含义,形式可以表示时间形式、意向作用、形式范畴,内容可以表示时间内容、质素、区域范畴(51)Edmund Husserl, Späte Texte über Zeitkonstitution (1929-1934), S. 296;[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62、247页。。形式范畴与区域范畴只适用于意识对象,不能被用于作为原区域的纯粹意识。其它两种形式与内容也不能被用作区分原自我与前自我的依据,因为原自我(原统觉)作为意向作用(统觉)的奠基性要素与作为质素奠基性要素的原质素不可分离地相统一,前自我与感受性材料也尚未分化,它们既具有拟-时间形式又具有拟-时间内容。那么,还能够在什么意义上理解不具有内容的原自我呢?答案是抽象与具体。纯粹自我“除了其‘关系方式’或‘行为方式’以外……完全不具有……可说明的内容”(52)[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202页。,反之,每个人格自我都具有其独特的信念、风格及其周围世界。类似地,原自我“完全不具有确定的素质(Anlagen)……只有对于一切自我都同一的原-自我-结构或原-自我性本质”,前自我则具有其确定的素质,而且“每个自我都以一个不同的质素开端”(53)Edmund Husserl,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Erster Teil, S. 408.。在这个意义上,原自我是形式性的,前自我是内容性的。
如果说李南麟由于过分倚重前自我而模糊地将原自我理解为“反思的自我意识之中心的先验主体性”(54)[韩]李南麟:《主动发生与被动发生——发生现象学与先验主体性》,第54页。,甚至将原本属于原自我的原初时间意识流动中的自我性要素归给前自我,那么,倪梁康则由于侧重原自我而将前自我的纯粹本能理解为原自我的纯粹追求活动。适当地中和李南麟与倪梁康的理解,更加符合上文对原自我与前自我的规定,即原自我是在原初时间意识流动中的原统觉,前自我是纯粹本能的活动中心。
4.正史与前史
马迎辉正确地指出了共时性(Gleichzeitigkeit)与同期(Zugleich)的区分(55)马迎辉:《趋同与原意向》,《现代哲学》2010年第5期,第82页。。共时性只能表示复多时间对象在某个时间位置或时间段中的共时显现,并且在滞留的过程中保持着与当下的相同距离,同期则是原印象与原滞留之时间意识的融合,因此,“我们不能将这个或那个同期称之为一个共时。我们不能再去谈论一个最终构造着的意识的时间”(56)[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25页。。
马迎辉进一步区分活的当下与原感觉意识的理由是活的当下是具有现成时间相位或时间形式的时间意识,它必然导向更深层时间意识的构造,即原感觉意识的同期构造(57)马迎辉:《趋同与原意向》,第84页。。但是,首先,活的当下的原印象、原滞留、原前摄并不表示与内在时间相同的时间相位,毋宁说,活的当下是前时间的原时间化,正是活的当下这个最终时间意识构造了一切时间相位(58)Edmund Husserl, Späte Texte über Zeitkonstitution (1929-1934), S.117, 269; Edmund Husserl,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 S. 667.。其次,《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所谓原感觉意识的同期,无非就是《关于时间构造的晚期文本》(以下简称《C手稿》)中活的当下的“同时融合”(Simultanverschmelzung)。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原感觉意识的瞬间-同期(印象性的流淌之同期)和片段-同期(前-同期)分别表示“一个内在的现在的一个或一组原感觉”和“相位的连续统,这些相位与一个原感觉相衔接”,为了突出原感觉意识的抽象性,胡塞尔说“可惜我用瞬间-同期这个表达时处处都指的恰恰是片段-同期”(59)[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第125、126、484页。。在《C手稿》中,两种同期都被整合在活的当下的“同时融合”之中,“这种同时融合在形式上就是处在连续映射之中的原现在、滞留性过去与前摄性将来”,“作为当下,现在和曾在的连续性,以及保持的视域和将来的视域同期被意识到。这种‘同期’作为活的当下就是流动的同期”(60)Edmund Husserl, Späte Texte über Zeitkonstitution (1929-1934), S. 76; Gerd Brand, Welt, Ich und Zeit: Nach unveröffentlichten Manuskripten Edmund Husserls,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55, S. 78.。再次,即便承认活的当下与原感觉意识的构造性区分,我们也很难将前自我对应于原感觉意识,况且前自我是远距过去的自我,而非当下的原印象性自我。因此,在这里我们无法将原感觉意识看作为活的当下奠基,也无法将前自我看作原自我的生成前史。
综上所述可知,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不仅不能构成区分原自我与前自我的原则,而且必然会导致无法弥合两种原自我与前自我的关系,即在发生视角下前自我为原自我奠基,在静态视角下原自我为前自我奠基;可以在与当下、而不是与现象学自我的关系上,谈到原自我的近距与前自我的远距;除了抽象与具体,其它的形式与内容含义都不能被用于区分原自我与前自我;前自我并非原自我在时间意识构造上的前史。因此,静态/发生与正史/前史这两个选项就被排除了,但是将原自我与前自我的关系仅仅解读为近距/远距、形式/内容也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们既没有突出原自我与前自我在方法论上的差异,也没有回答原自我与前自我何以在结构上是类似的。因此,本文试图提出一种全新的解读方案。
三、建议性方案:发掘/重构式解读
胡塞尔在1923/1924年“第一哲学讲座”中提到现象学的考古学。这种“‘考古学’,应该系统地研究那种最终根源,以及在自身中包含着存在与真理的一切根源,并且进而应当向我们说明,一切认识何以能够出于一切意指和效用的这种源泉而获得最高的且最终的理性形式……”(61)[德]胡塞尔:《第一哲学(下卷)》,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2页。在1930年代,胡塞尔更加明确地规定了这门现象学考古学的方法:“对隐匿在其组元中的构造性建筑进行发掘……正如在通常的考古学中一样:重构,‘之字’地理解。”(62)Edmund Husserl, Späte Texte über Zeitkonstitution (1929-1934), S. 356-357.胡塞尔所提出现象学考古学包含了发掘与重构这两个步骤,“所有的原联想、原意向性首先都是通过拆解和重构而得到阐释的”(63)Ibid., S. 437.。发掘与重构考察的都是不可被反思性直观所直接把握的现象,但发掘所揭示的现象是原初地且绝然地被给予的,例如活的当下;而重构所揭示的现象则永远不可能被事实性地把握到,例如出生、死亡等界限现象。发掘性分析又被称作“回退现象学”(Regressive Phänomenologie),重构性分析又被称作“前进现象学”(Progressive Phänomenologie),前者是“对还原地被给予的、‘直观地’被证明的超越论主体性的构造性分析”,后者是对“所有被动机引发的、超出超越论生活之直观被给予性的建构整体”(64)Eugen Fink, Sixth Cartesian Meditation: The Idea of a Transcendental Theory of Method, with textual notations by Edmund Husserl, translated by Ronald Bruzina,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8; Edmund Husserl,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 S. XXXVIII-XXXIX.的分析。
在称号上,胡塞尔也许借用了康德的回溯法(分析法)和前进法(综合法)(65)[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3页。,或者借用了保罗·纳托尔普(Paul Natorp)在1880年代提出的建构法与重构法,但胡塞尔与他们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康德的回溯法以假定真理性的事实为前提,前进法首先要回答的是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因此前进法要优先于回溯法。胡塞尔的前进法则要以回溯法为前提,对不可被事实性经验现象的重构要以所发掘的隐匿组元和结构为前提。纳托尔普虽然试图根据本体论差异(对象或对象化主体与原初生活状态中的主体)区分建构法与重构法,但这两种方法实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在研究方向上存在着区分,建构法从对象到主体,重构法从主体到对象。这种方法一元论最终导致了本体一元论,即主体成为与客体不可分离的因果关联体。胡塞尔通过超越论还原“在方法论层面上准确地描述了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区别”(66)Sebastian Luft, “Reconstruction and Reduction: Nartop and Husserl on Method and the Question of Subjectivity”, Meta: research in hermeneutics, phenomenology, and practivcal philosophy, VIII (2), 2016, p. 345.,使得超越论主体完全摆脱了与自然客体的因果关联。此外,纳托尔普的建构与重构是静态的,胡塞尔的发掘与重构则是动态的。
发掘先行于重构,重构要以所发掘的最终根源为基础。发掘即“返问自然,并且从自然出发而作为现象学考古学的主导,发掘在其建造要素中隐匿的建造物,统觉性意义成就的建造物,这种意义成就已然为我们存在为了经验世界。对塑形着存在意义之个别成就的追溯和发掘,直到最终的‘本原’”(67)Edmund Hussel, Ms. C 16 VI, 1, in Nam-In Lee, Edmund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er Instinkte, S. 77.。发掘就是现象学还原的深化,具有系统性拆解、回溯性分析等表现方式。通过排除世界超越物、他者、一切再当下化,“最终的还原将关注的目光朝向绝对原初的生活,朝向原初的我-在,朝向流动,朝向原被动的流动,朝向我-做,自我-同一化,等等”(68)Edmund Husserl,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 S. 585.,因而最终我们发现了原自我及其原初流动的自我生活。但不同于李南麟、马迎辉(69)Nam-In Lee, Edmund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er Instinkte, S. 77; 马迎辉:《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时间性与本我论——一种建基关系的考察》,第79页。,我们将发掘方法仅仅用于原自我而不是前自我,因为前自我恰恰要以所发掘的原自我为基本图式才能得到重构。
“重构,即对并不直接被经验之物或不可被经验之物(但是是一种合乎本质的明见之物)的重构”(70)Edmund Husserl, Die Lebenswelt, Auslegungen der vorgegebenen Welt und ihrer Konstitution,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16-1937), hrsg von Rochus Sowa, Dordrecht: Springer, 2008, S. 480.,“对胎儿的灵魂生活就是如此。但是这个灵魂生活存在着,并且是可被明见地重构的(在一种仅仅‘模糊的’规定性之中),并且现实地具有重构为它所指派的存在意义”(71)Edmund Husserl,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 S. 608-609.。重构不是对可被现实经验到之发生过程的建构,而是对“那个或这个这样展开的关系之潜能”的揭示,现实自我的潜能首先发端于处在胎儿阶段的前自我(72)[德]汉斯·莱纳·塞普:《人格——戴着面具的自我》,江璐译,《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40页。。但是对成熟主体的结构研究要先于对胎儿或新生儿的研究(73)Ibid., S. 481.,正是根据成熟自我的原自我结构,前自我才被理解为“存在着的前存在者,即在方法上始终要被重构者和统一化者,在被统觉之前的‘曾在’者”(74)Edmund Husserl, Späte Texte über Zeitkonstitution (1929-1934), S. 223.。重构不是形而上学式的独断、假设、猜测或推论,而是植根于“迄今为止向‘原现象’之彻底还原的风格”(75)Klaus Held, Lebendige Gegenwart, S. 145.的经验。任何的重构都是以原初被给予之物为合理性基础而进行的,正是原自我的原原初明见性为前自我的重构提供了合法性。由于都是为自我进行最终奠基的构造性根源,都处在前行为、前触发、前时间的本己意识流层面,因而,原自我的结构——原自我与原初非我不可分离地统一,原自我具有原分异与原融合的原时间化——就可被转用(übertragen)于前自我:前自我与感受性材料尚未分化,前自我具有天生本能的空乏视域。正是这种结构相似性,使得胡塞尔偶尔含混地使用原自我与前自我这两个术语。但前自我不是原自我,也不是过去的原自我,因为原自我始终只能是原当下的自我,前自我始终是远距过去的自我。而且,原自我具有比前自我更加原初的被给予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赞同田口茂的断言,即前自我的明见性奠基于原自我的明见性。因此,虽然我们并不具有对不可被回忆之远距前自我的事实性经验,但在原自我的启发下,“我们建构了作为开端的仍然无世界的前场域(Vorfeld)和前自我”(76)Edmund Husserl, Späte Texte über Zeitkonstitution (1929-1934), S. 352.。
对原自我与前自我之关系的发掘/重构式解读,既整合了田口茂的近距/远距式解读和倪梁康的形式/内容式解读,又补充了原自我与前自我在方法论上的差异和在结构上的类似。发掘/重构式解读不仅具有胡塞尔文本为根本支撑,而且得到诸多现象学家的支持,其中不乏提出其它解读方案的现象学家。例如,马里亚·塞莱斯特·维奇诺(María Celeste Vecino)新近的观点即与我们所提出的解读方案相一致,他认为原自我作为当下的原真性是由向活的当下的现象学还原所发现的,前自我作为过去的原真性则只能通过重构才能通达;原自我具有比前自我更多的原初性,包括重构在内的任何现象学研究都预设了原自我的原当下存在(77)María Celeste Vecino, “Leib and Death: A Study on the Life of the Transcendental Ego in Husserl’s Late Penomenology”, https://www.academia.edu/34619560/Leib_and_death_a_study_on_the_life_of_the_ transcendental_Ego_in_Husserls_late_phenomenology_Workshop_internacional_Husserl_hermen%C3%A9utico_Heidegger_trascendental_Universidad_Diego_Portales_Junio_2017_.。另外,李南麟承认前自我是本我论反思的界限,它只能从沉淀化现象(这种沉淀化奠基于原自我的原时间化)出发通过相似结构的类比化才能够得到重构(78)Nam-In Lee, Edmund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er Instinkte, S. 65, 165.。田口茂也认为前自我只能被重构,而原自我在一切重构之先就已然存在着(79)Shigeru Taguchi, Das Problem des, Ur-Ich‘ bei Edmund Husserl, S. 119.。如果剔除在前面所指出的不足,李南麟和田口茂就理应被看作发掘/重构式解读的支持者。
——专栏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