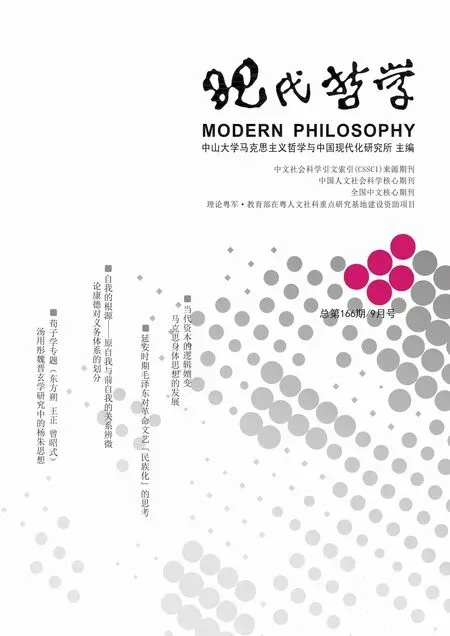论荀子的心学论证
——以《正名》为例
曾昭式
刘师培评儒家逻辑:“吾中国之儒,但有兴论理学之思想,未有用论理学之实际。观孔子言‘必也正名’,又言‘名不正,则言不顺’,盖知论理学之益矣。而董仲舒亦曰:‘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则亦知正名为要务矣。而《荀子·正名篇》,则又能解明论理学之用,及用论理学之规则。然中国上古之著,其能用论理学之规则者,有几人哉?”(1)刘师培:《国文杂记》,《左盦外集》卷十三,万仕国点校:《仪徵刘申叔遗书》第11册,扬州:广陵书社,2014年,第4959页。他把《荀子·正名》视为中国古代思想中少数能够用逻辑学规则论证思想的经典,认为中国有自己的逻辑,研究中国逻辑宜“循名责实”(“今欲正中国国文,宜先修中国固有之论理学,而以西国之论理学参益之,亦循名责实之一道也。”(2)同上。)和“解字析词”(“今欲诠明论理,其惟研覃小学,解字析词,以求古圣正名之旨,庶名理精谊,赖以维持。”(3)刘师培著、劳舒编、雪克校点:《刘师培学术论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页。)。但刘师培没有具体的中国逻辑研究,也没有指出“中国固有之论理学”是什么、“古圣正名之旨”为何。本文以《荀子·正名》为例,在总结百年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基础上,欲回答中国逻辑之类型和特征。
一、中国古代逻辑的称谓与“正名-用名”论证类型
刘师培称中国古代逻辑为“论理学”,也有学者称之为中国“名家”“名学”“辩学”“名辩学”“逻辑(学)”“符号学”“名学与辩学”“理则学”等。暂且不论这些称谓的成因,今举几例,目的是基于这些称谓而考察其内容所指。
1.“名家”为章太炎所提出。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讲学记录的《国学概论》涉及中国古代逻辑部分,他称之为“名家”。此“名家”指“名家是治‘正名定分之学’,就是现代的‘论理学’,可算是哲学的一部分。尹文子、公孙龙子和庄子所称述的惠子,都是治这种学问的。惠子和公孙龙子主用奇怪的论调,务使人为我所驳倒,就是希腊所谓‘诡辨学派’。《荀子·正名篇》研究‘名学’也很精当。墨子本为宗教家,但《经上》、《经下》二篇,是极好的名学。”(4)章太炎:《国学讲义》,北京:海潮出版社,2007年,第28页。此“名家”与“名学”义同,与“逻辑”义同。“正名定分之学”等同于“论理学”(即逻辑学)。
2.“名学”称谓的所指也没有离开演绎和归纳逻辑思想,如严复于1903年翻译的《穆勒名学》、杨荫杭1903年著的《名学教科书》、胡适1922年著的《先秦名学史》。虽然虞愚将中国名学分为“无名”“正名”“立名”“形名”四个学派,但其分类标准仍然是以西方逻辑为根本来确立中国古代逻辑的类型,如其言“而名学乃吾国先哲正名实之术”(5)虞愚著、刘培育主编:《虞愚文集》第1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5页。,“而《墨辩》对于推理、论证、判断、概念,均有详细之讨论”(6)同上,第447页。,中国名学“除讨论推论是非外,又注重实际人事……然其侧重伦常之道,谋人类切身之幸福,固为希印二土所不及”(7)同上,第541页。。此“吾国先哲正名实之术”既有推论的讨论,也“注重实际人事”。
3.“辩学”,如郭湛波在其著作《先秦辩学史》里说:“中国论理学有名学、形名学、辩学,等名词,我以为‘名学’二字太宽泛,‘形名学’太生涩,所以就用‘辩学’二字。”(8)郭湛波:《先秦辩学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自序”第5页。“形名学是讲思想的(Logic),正名学是讲伦理的(Ethic)。”(9)同上,第3页。
4.“名辩学”,如周云之言:“‘名辩学’的体系特点,一是正名学(概念论)和论辩学(推理论)的相对独立和有机结合,二是正名学和论辩学的体系应当是各以《正名》篇和《小取》篇的理论体系为基本依据。而如果仅仅是作为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概括与总结,那就只需要按照名(概念)、辞(命题)、说(推理)、辩(论证)的理论体系加以表述就完全可以了。”(10)周云之:《名辩学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年,第143页。刘培育认为,“‘名辩学’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建构的一门学问,主要研究正名、立辞、明说、辩当的方法、原则和规则。这门学问的核心是逻辑学,但也包括认识论和论辩术等内容,与政治和伦理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逻辑学是名辩学的核心,并非名辩学就是中国古代逻辑。名辩学在中国古代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而中国古代逻辑却没有得到很好发展,也没有形成完备的体系”(11)刘培育:《名辩学与中国古代逻辑》,《哲学研究》1998年增刊,第12—14页。。此“名辩学”是逻辑加认识论、论辩术。
5.“逻辑(逻辑学)”,如沈有鼎写作《墨经的逻辑学》,以概念论、判断论、演绎和类比推论、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等内容为线索,逐一比较《墨经》相关内容的异同。汪奠基对中国逻辑类型进行总结,大体上认为孔子等儒家逻辑的主流属于社会政治的逻辑,名家逻辑称为名辩逻辑,墨家逻辑归属于普通逻辑,老子的无名论逻辑归属于辩证逻辑,并写作了《老子朴素辩证的逻辑思想——无名论》《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第一辑)《中国逻辑思想史》等著作。温公颐在《〈先秦逻辑史〉编写中的几个问题》一文里讲:“先秦逻辑我把它分为两篇,第一篇写辩者的逻辑思想;第二篇写正名的逻辑思想。辩者的逻辑思想属于正宗的逻辑……比较倾向于纯逻辑的研究。至于正名的逻辑却是从政治伦理出发,可以称为政治伦理的逻辑。”(12)温公颐:《温公颐文集》,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第262页。
6.“符号学”,如李先焜以符号学理论写出《〈周易〉中的符号学思想》《先秦名家邓析、尹文、惠施的符号学思想》《公孙龙〈名实论〉中的符号学理论》《公孙龙〈指物论〉中的符号学思想》《公孙龙〈白马论〉中的符号学思想》《〈墨经〉中的符号学思想》《中国古代医学中的符号学》《中国古代的礼仪符号学》等论文。他认为中国古代逻辑是符号学,包括语用学、语义学和语形学,加上古汉语特点(13)参见李先焜:《语言、符号与逻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陈宗明、林铭钧、曾祥云等学者亦持此说,但思想有差异。
7.“名学与辩学”,是崔清田对“中国逻辑”的称谓,其中国古代逻辑观念可以参见《中国逻辑史研究“五范畴”:崔清田先生口述史片段》一文(14)曾昭式:《中国逻辑史研究“五范畴”:崔清田先生口述史片段》,《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这里的名学与辩学的关系尚有待研究的空间。
中国逻辑的称谓还有诸多种,这些称谓下的中国逻辑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以西方传统逻辑演绎、归纳理论框架提炼中国文本中的部分内容,剩余部分置之不顾;第二类,西方传统逻辑(含符号学)+中国的哲学、科学、伦理学等;第三类,中国逻辑是西方传统逻辑之名学+中国的政治伦理的名学;第四类,着力构建中国逻辑独立体系。其中,前两类显然是将中国逻辑置于西方传统逻辑里,第三类将中国名学割裂成西方逻辑+中国哲学,第四类需要进一步厘清中国哲学方法与中国逻辑、名学与辩学关系。
笔者认为,从称谓看,在当下学术史研究中国逻辑、印度逻辑等,既然将它们归于逻辑学科,统一用“逻辑”称谓,可以凸显逻辑史研究的明确性和学科归属,只是需要将逻辑学的内涵与外延确立为包含中、西、印等逻辑的内容与范围。从内容看,如果把逻辑学定义为关于论证结构与规则之学,则可称亚氏逻辑讨论的论证结构为三段论,佛教逻辑讨论的是三支论式,中国逻辑则为“正名-用名”论证类型,“正名”是确定名之所指,“用名”是在说、辩中正确使用已正之名,说、辩既呈现论证结构及规则,又涉及说辩者及说辩目的(15)参见曾昭式:《先秦逻辑新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从特征看,三段论讨论的是基于不同逻辑常项里的逻辑变项外延间关系,此真假概念纯为形式的;三支论式与“正名-用名”论证是一种带有信仰与价值的论式,自然引出论证者、论证目的的讨论,如三支论式的“极成”规则等。
二、《正名》之“正名-用名”理论:正心与圣人、君子之辨说
“正名”与“正心”。《荀子·正名》开篇讲君王如何制名,“刑名”“爵名”“文名”是不需要改变的(如《正名》讲“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只需要正“散名”,散名指万物之名,正散名的总原则是“从诸夏之成俗曲期”(同上)。荀子只选择万物中人之名来加以讨论,形成“正名-正散名-正人名-正心名-正道名”这样一个《正名》文本结构,其核心内容是从“正人名”到“正心名”。从文本看,“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16)“伪”即今“为”字。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12页。。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性伤谓之病。节遇谓之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后王之成名也”(同上)。引文中“人”之特性包括“性”“情”“虑”“为”“事”“行”“知”“智”“能”“病”“命”等。在这些“人”的特性里,可以分为人性本能和后天习得两类,只要是人,都具有人之性,包括五官和心的功能等,“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心有征知”(同上),此为本能之人性。后天习得之“人”的特性关键在“心”,所以文本接着讲,今乱世圣王不得不正名。荀子提出了“正名”原则,列举、分析了违反原则的“三惑”,提出去“三惑”的办法——“正心”,“正心”就是“正道”,今摘引《正名》文本内容,以佐证之:
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然则所为有名,与所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也。
“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也”,此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验之所为有名而观其孰行,则能禁之矣。“山渊平”“情欲寡”“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此惑于用实以乱名者也。验之所缘以同异而观其孰调,则能禁之矣。“非而谒楹有牛,马非马也”,此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验之名约,以其所受,悖其所辞,则能禁之矣。
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请而喻。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
荀子在讨论人之“心”时,包括本能之心和后天习得之心,“正名”重在“正心”,就是正后天习得之心,让心符合荀子之道,因为心左右“情”“虑”“为”“事”“行”“知”“智”等方面,只有“正心”,方能“语治”,方能治“欲”,文本自“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正名》)以后便是讨论这一论题,如所谓“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节求也”“道者,古今之正权也”“以己为物役”“重己役物”(同上)。可见,《正名》篇的主题还是通过“正名”来正人心的,所以《解蔽》篇之后便有《正名》篇。《解蔽》是要去蔽,是要去心之弊而求道,故说“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未得道而求道者,谓之虚壹而静”“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正名》与此一脉相承。如果说《解蔽》重在批评思想上的“弊”,《正名》则在于“语治”,通过“正心”,在“正名”和“说”“辨”中避免以名乱名、用实乱名、以名乱实之“三惑”情况。
再看“用名”与圣人、君子之辨说。在《正名》里,荀子的“用名”理论表现于其对“说”“辨”的研究。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荀子关于“说”“辨”“辩”的理解,从先秦逻辑视角看,考察《荀子》诸篇,只有《正名》有“说”“辨”研究,其它篇用“辩”来指“辨说”。如《荀子·修身》言:“夫‘坚白’‘同异’‘有厚无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辩,止之也。”《荀子·非相》言:“故君子之行仁也无厌。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言君子必辩。小辩不如见端。”《正名》篇里“说”“辨”有合成“辨说”一词的情况,也有分开使用的情况。“辨说”合用情况如:“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辨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期命也者,辨说之用也。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同上)“说”“辨”分开使用情况如:“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同上)从此引文并结合整个文本内容看,“说”有解说义,“辨”有论证义,二者都是“喻动静之道”(同上),即给出理由以论证思想观念的,所以合起来称“辨说”,是心对道的认知后的言说。至于“辨”与“辩”的差别,从《非相》分“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和《正名》分“圣人之辨说”“士君子之辨说”的内容看,《非相》之“辩”等同于《正名》之“辨说”。下引文即表明“圣人之辩者”同于“圣人之辨说”,“士君子之辩者”同于“士君子之辨说”:
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是圣人之辩者也。先虑之,早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辩者也。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夫是之谓奸人之雄。(《荀子·非相》)
有兼听之明而无奋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无伐德之色。说行则天下正,说不行则白道而冥穷,是圣人之辨说也……辞让之节得矣,长少之理顺矣,忌讳不称,袄辞不出,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治观者之耳目,不赂贵者之权埶,不利传辟者之辞,故能处道而不贰,吐而不夺,利而不流,贵公正而贱鄙争,是士君子之辨说也。(《正名》)
接着,据文本讨论荀子是如何讲“说”“辩”的。荀子讲“说”“辩”的目的是“用名”,并且是从“辨说者”来讨论辨说。《正名》里讲“圣人之辨说”和“士君子之辨说”之后,便是比较君子与愚者之言: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类,差差然而齐。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足以相通则舍之矣;苟之,奸也。故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则舍之矣……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啧然而不类,誻誻然而沸。彼诱其名,眩其辞,而无深于其志义者也。故穷藉而无极,甚劳而无功,贪而无名。故知者之言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则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恶焉。而愚者反是。
通过“君子之言”与“愚者之言”的比较,明确荀子所赞扬的“君子之言”是服务于言说的,这也是荀子思想的目的,即“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同上)。从引文可以引申出,荀子之“说”“辨”讨论的是“君子之言”,此“君子之言”就是荀子认为应该采取的“说”与“辨”,即无论是批评别人观点还是阐发自己的主张,都要给出理由,此理由必须是“正道”,即“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辩说譬谕,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荀子·非十二子》)。正如冯友兰所说:“心的认识跟‘道’相合(‘心合于道’)。所立的‘说’跟心的认识相合(‘说合于心’)。所有的命题跟主题相合,为主题服务(‘辞合于说’)。所用的名词都能正确地表示事物(‘正名而期’),能反映实际情况并且易于了解(‘质请(情)而喻’)。分析和类推都合乎规律(‘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取别人的话,能够吸取它的合理的一部分(‘听则合文’)。发表自己的主张,要把原因和根据都讲出来(‘辨则尽故’)。这是荀况对于一个正确的合乎逻辑的思考和辩论的总的要求。”(17)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8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08页。
最后,比较荀子“辨说”与墨家“说”“辩”的不同。《说文解字》对“说”与“辩”二词从多种意义来说明。在先秦逻辑里,“说”“辩”是两个核心概念。伍非百对二者有区分:“辩者,指正负两方而言。说者,指正负之一方而言。谓其立敌对诤者曰‘辩’,谓其各自立量者曰‘说’。”(18)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5页。此释是以《墨辩》文本内容为参照的,《墨辩》将“说”“辩”区分得十分清楚,“辩”有当下学科的意义,“说”归属于“辩”学科下的内容之一。关于“说”,我们将《墨经》六篇中与“说”相关的论说联系起来,便可确立其涵义。“说,所以明也。”(《经上》)“以说出故”(《小取》)“夫辞,以故生……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大取》)“故,所得而后成也。”(《经上》)“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无然,若见之成见也。”(《经说上》)用沈有鼎的话概括,“说”的含义是:“‘说’就是把一个‘辞’所以能成立的理由、论据阐述出来的论证……有时举例来说明一个一般性的规律或定义,也名为‘说’。”(19)沈有鼎:《沈有鼎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32页。“辩”,《小取》开篇就从“辩”的作用、方法、内容、规则等角度予以论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墨子·小取》)由此可见,墨家“说”“辩”不同而且范围更为广泛,它适用于任何内容的“说”“辩”,成就了中国逻辑学科;荀子的“说”“辨”意义相近且只适用荀子的“正道”论证。二者相同之处在于:其一,都有己是他非的说辩目的,庄子批评儒墨之辩就是基于此,“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庄子·齐物论》);其二,都是以“道理”阐发来展开论证的,如《中国思想通史》言“由于将‘类’与‘礼’及‘法’相结合,荀子使‘类’概念成了儒家君子立场上‘听断’的工具……是以‘隆礼’为‘明故’的前提……荀子是以逻辑从属于儒家道德的体系的”(20)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58—559页。。
三、结语:“正名-用名”论证类型与中国逻辑文献
笔者不主张将“荀子的正名逻辑”单独挑出来,写成接近西方逻辑部分内容的理论,忽略《正名》篇里的其它内容,如言“荀子名学之核心乃是名或概念之理论。荀子对于辞或命题之探讨较为简略,虽然,荀子对于命题作过分析,且亦有合于有效推论形式之论述之实例,然而,荀子并未能抽象地提出有效之推论形式。因之,根据逻辑学之定义,可知,荀子之名学并不等同于逻辑”(21)李哲贤:《荀子之名学析论》,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第224—225页。;不主张将先秦名学分为政治伦理的名学和逻辑学的名学,如温公颐、虞愚等;也不主张用因明立、破来讲“说”“辩”,如栾调甫用因明立、破来说“明是之说”与“争非之辩”,“明是之说。案《经上》云:‘说,所以明也,’即谓‘说’为用以说明其所立之‘故’。盖立者其‘故’必真,若其不真,则‘故’不立。不立之立,因明谓之似能立,能立之立,因明谓之真能立……争非之辩……即谓‘辩’为用以争正彼方所立之非,为因明之破”(22)任继愈、李广星主编:《墨子大全》第5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512—513页。。这三种逻辑传统差异甚大,其差异笔者已从多方面有所比较(23)参见曾昭式:《先秦逻辑新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这里仅说明“正名-用名”是中国传统逻辑的论证类型,其中“用名”表现于说辩中,说辩也呈现出一种论证结构,即从理由到主张的结构,并包括理由规则、从理由到主张的规则。这些规则的基础是已正之名,即理由一定是基于自己学派已正之名的述说,从理由到主张的规则不是形式规则,而是价值取向等(先秦大多派别认为生活常识不需要论证,也不屑于论证)。不像三段论讲的是形式规则,检验用三段论论证的结论正确与否是按照三段论规则进行的;也不似用因明展开的论证,因明论证也是从宗、因、喻三支定的规则展开的,批评别人论证有问题,是从违反因明的什么规则来讲的。中国传统逻辑则是从具体内容上说理,如儒、墨等学派都不接受“白马非马”论证,是因为公孙龙的论证违反了人们的具体认知,其《名实论》中的“正位”理论是“白马非马”不好言说的,所正“白马”“马”名在“用名”(“白马非马”论证)中内容变异。即便是《大取》所讲“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中的“故”“理”“类”也是由已正之名来确立的,所以我们用符号“-”表达“用名”与“正名”不可分。这里还有一个“说”“辩”的形式“推类”问题,此问题将另文讨论。
中国古代逻辑也是研究论证结构与规则之学。这里需要处理两组关系:一是哲学方法与逻辑关系,二是逻辑理论与逻辑应用。前者如经典解释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经典解释结构与规则为中国古代逻辑关注的对象;后者的中国古代逻辑理论与应用是两个方面,本文认为只有中国先哲提出了中国逻辑理论方称得上中国古代的逻辑。这种逻辑的素材选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中国古代经典的逻辑文献,如先秦经典中的《公孙龙子》《墨辩》等就是中国古代逻辑的文献,《公孙龙子》中的《名实论》《指物论》是讨论“正名”问题,是基于“位”下的“彼”“此”“彼此”名实关系问题;《白马论》《通变论》《坚白论》是讨论“用名”问题。《墨辩》中的《经》《说》讲“正名”,《大取》基于《经》《说》中的哲学、科学、政治学等已正之名,总结论证结构与规则,《小取》则在不同的“说”“辩”形式中讲如何“用名”的问题。第二类是中国古代哲学文献中的逻辑讨论,如《正名》篇的主题是“语治”,破三惑,正人心,使之合于“士君子辨说”而服务于君王治国之道。在“正人名”中讨论了名的由来、制名的原则、名的分类(如单名、兼名、大共名、大别名)、辞、说、辨等。对于这两类逻辑问题的研究,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从名称看,不同文化的逻辑都可以称为“逻辑”;从论证类型看,包括亚里士多德三段论论证、佛学论证、“正名-用名”论证等。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基于如上两种文献,在比较不同文献中逻辑问题差异的基础上,求得中国古代逻辑的一般性特点,然后开展逻辑史比较研究。此研究或许是崔清田的讨论问题的深化(24)崔清田:《“中国逻辑”名称困难的辨析:“唯一的逻辑”引发的困惑与质疑》,《逻辑学研究》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