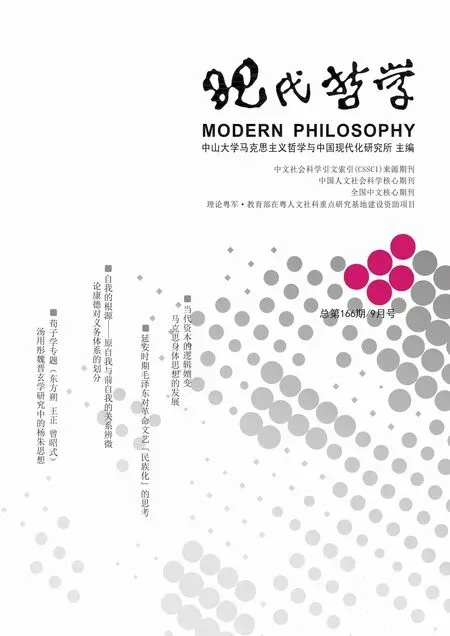荀子的政治正当性理论
——以权力来源为中心
东方朔
一
“政治正当性”是一个现代政治哲学的概念,以此概念为基础去探讨传统政治思想的得失,已然成为当今学者常常致力的工作。有关荀子的政治正当性理论,学者也多有研究,且主张各异,看法不一。本文无意对此作详细的检讨,但试图说明就此概念的现代含义而言,“政治正当性”所预认的观念前提在于自我意志的自由和自决,舍此,则任何权力的“正当”或“不正当”皆无从谈起。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本文的内容有三个方面:其一,尽管我们可以用“政治正当性”这一概念来说明荀子的相关主张,但在权力来源的问题上,荀子并不曾追问权力本身的正当性问题,也可以说荀子对权力之正当性问题有其特殊的关心和了解方式;其二,许多学者所论述的荀子的“权力正当性”,其实义乃是权力行使的合理性,换言之,荀子并不曾关注权力在“根据”上的正当性,而只在乎权力在“效果”上的合理性;最后,文章检讨了荀子何以只重权力在效果上的合理性的原因。
那么,政治正当性问题是在何种意义上关联到荀子的思想论述?依荀子的说法,“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荀子·礼论》)。在此,荀子已清楚表明,人类要实现自己的欲望和保证自身的生存,只有依靠先王(圣王)“制礼义以分之”;而圣王由于其优异的德能及其“尽伦”“尽制”(《荀子·解蔽》)的特点,可以获得人们的信赖,并带领人们摆脱“争乱穷”的状态,实现和平、安全和秩序。
不过,荀子所说的圣王是“尽伦尽制”的,在观念形态上类似于韦伯所谓的“理想型分析”(ideal type analysis),盖凡言“尽”者皆就理想说。但从政治哲学上看,“尽制”必指向现实的外王层面。例如,一个合宜的社会组织结构为什么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此“等”“差”“称”的标准由谁来制定?又凭什么来制定?在何种意义上我们有服从这些标准的道德义务?类似问题涉及到组织社会国家中的具体的权力结构安排,以及此权力结构中所不可避免的支配和服从关系,因而,着力呈现此种权力结构中的“支配-服从”关系中的逻辑并非是一项可有可无的工作。虽然依荀子的主张,我们似乎有足够的理由去承认圣王所建立的权力结构以及国家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相对于自然状态下人类“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荀子·性恶》)的结果而言,没有比圣王的组织和安排更好的。然而,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终止哲学层面的追问,我们需要给出一些坚实的理由来说明具体的现实层面上的权力统治如何能够获得道德的有效辩护,或者说,我们需要有一种同样坚实的论证来表明我们有一种服从政治权力统治的道德义务,否则,类似“凭什么支配、为什么服从”的疑问便始终会存在于人们的心灵之中。
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涉及到“政治的正当性”问题。“政治正当性”(political legitimacy)一词原本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概念,而对此概念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的理解则头绪繁多,颇为复杂(1)相关学者的研究,参见[美]马克斯·韦伯:《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康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周濂:《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加]大卫·戴岑豪斯:《合法性与正当性》,刘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美]约翰·西蒙斯:《正当性与合法性》,毛兴贵译,《世界哲学》2016年第2期,等等。。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正当性意谓着对于一个政治秩序所提出的被肯认为对的及公正的(right and just)这项要求实际上存在着好的论证;一个正当的秩序应是得到肯认(recognition)。正当性意谓着政治秩序之被肯认之值得性(worthiness to be recognized)”(2)[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84页。。对此,石元康指出,哈贝马斯有关正当性的定义有两个主要方面值得注意,一是把政治秩序问题看作是正当性的评价对象,亦即任何政治秩序的达成,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言,权力必须要有一个道德基础,以便“使得统治者可以统治得心安理得,而被统治者也认为统治者统治的权力是正当的”(3)石元康:《天命与正当性:从韦伯的分类看儒家的政道》,《开放时代》1999年第6期。;另一是正当性所涉及到的“肯认”和“值得性”,亦即在政治秩序“这个组织中的人必须认识并且接受这种权力及不平等的安排是有基础及公正的,因而值得人们给予他们的肯认”(4)同上。。不过,对于浸淫在当今中西比较气氛日益浓厚的学者而言,或许会很自然地追问,作为一种与西方不同类型的文明,中国“古代有没有正当性这个问题,最开始是如何关心这个问题的?又会在什么样的视野和概念框架中、以什么样的语言词汇提出这样的问题?”(5)许纪霖、刘擎:《政治正当性的古今中西对话》,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年,第8页。类似的追问把正当性问题放入到不同文化和传统的脉络中来理解,使得对正当性的具体含义及其理解变得更为复杂。无疑,正当性问题在中西不同的传统中可能有不同的探究方法和途径,但假如我们把正当性问题作为一个普遍问题来理解,那么,透过对正当性问题的不同的言说方式,中西之间虽会有差异,但此问题本身的理论有效性依然值得我们重视,盖任何权力的统治本身皆需要提供一套理由来证明其自身是对的,是可接受的。按周濂的说法,“在政治领域中,只要存在支配—服从关系就会有正当化的诉求。并且无论我们如何构想正当性的具体内容,正当性都是对支配关系所作的某种道德证成。这种道德证成并非可有可无,它可以通过使支配者拥有发布命令的权利、被支配者负有服从命令的义务,从而确保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性”(6)周濂:《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第5页。。
从西方政治哲学史的角度来看,正当性问题涉及许多复杂面相,我们不可能一一加以梳理和探究,故而本文所讨论的荀子的政治正当性理论主要指的是荀子有关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主张,而且于其中主要探讨荀子有关权力来源的正当性问题而不及其余,这是需要首先加以说明的(7)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在理论上涉及权力的来源、权力的更迭以及权力的制约等多方面的问题,此处只论及权力来源的正当性问题,至于权力更迭和权力制约的正当性问题,笔者已有另文处理。。
二
我们通常会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最早有关权力的来源及其正当性的文献在周初的《尚书》和战国中期的《孟子》中有较具代表性的说明。不过,在此问题上,荀子的主张既不同于《尚书》的天命观,也不同于孟子的命定论,而表现出其政治哲学的特色。
小邦周克大邦殷之后,需要有一套理论来说服旧有的殷商民众,并为其“夺权”行为进行正当性辩护。按照周公的说法,是上天改变了天下的元首,结束了大邦殷的国命(8)“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尚书·召诰》),不是我小邦周胆敢取大邦殷的命,而是上天不把天命给那些诬枉而又暴乱的人(9)“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尚书·多士》),我小邦周只是佑助天命,奉行上天的明威,执行王者的诛罚而已(10)“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尚书·多士》)。上天之所以改厥元子,并不是上天刻意要舍弃夏或舍弃殷,而是因为你们夏、殷的君王纵于淫佚,夸大天命,不敬上天保民爱民之德,故而上天降下亡国的大祸(11)“非天庸释有夏,非天庸释有殷。乃惟尔辟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乃惟有夏图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时丧,有邦间之。乃惟尔商后王逸厥逸,图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时丧。”《尚书·多方》。对此,周公总结道:“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可见,周人天命观的核心在于统治者权力来源的“正当性”是由上天所给予的,但“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天命不可依恃,统治者惟当终日乾乾,敬德保民,否则上天仍会“降丧”而收回成命,故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12)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确可以指出,周人的这种“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的天命观似乎在敬德与获得天命之间建立了某种因果关系,丧德者亡国,敬德者保有天命。倘若如此,则丧德者亡国可生发出一种正面的、积极的警励意识;而敬德者保有天命,则天命原有的最终决定权的意义便一转而系于统治者人为的主观方面的努力,而有可能使天命的绝对性得以架空。。可以说,“天命、敬德、保民”构成了周人“政治正当性”的基本内涵。
逮至“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13)[汉]刘向:《校战国策书录》,诸祖耿撰:《战国策集注汇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796页。的战国时代,孟子已清楚认识到“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故孟子力主统治者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注重民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以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的说法向为学者所称道,表现出民心向背的重要性(14)《孟子·梁惠王下》有一段记录可清楚看到这一点:“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不过,在权力的来源的正当性问题上,孟子的一套论说基本上承袭着周人的主张。孟子在回应万章问“舜有天下也,孰与之”的问题时,直接以“天与之”作答。《孟子·万章上》记云:“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在孟子看来,统治者(舜)君临天下的权力来源于上天,既不是尧给予的,也不是民众主观意志的赋予。当万章问孟子:“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同上)孟子明确地回答道:“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同上)但天不能言,其如何将权力与人?孟子认为,需要天子向天推荐而天接受他,向民推荐而民接受他。孟子此处似乎认为,统治者权力的来源是以天意和(民意)民众的福祉为基础的。不过,在最终意义上,天意不由民意来决定,天与之则与之,“非人之所能为也”(《孟子·万章上》),换言之,民众并没有决定统治者在位与否的最终权力,统治者丧德而沦为暴君,民众可以推翻他,即便如此,民众的行为也不是自己主观意志的表达,而只是“替天行道”的表现而已。因此,在统治者权力来源的问题上,孟子大体承袭着周人的主张,若必辩其异者,则孟子由周人的天命论反倒走向命定论或命运论(15)参见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5页。当然,孟子也发展出了一套“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孟子·尽心上》)的正命论。。
那么,荀子是如何说明统治者权力来源的正当性呢?在《荀子》一书中,与“权力”一词相近的概念是“势”,故云“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荀子·正论》)。又,依荀子“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荀子·性恶》)的逻辑,追求权力(势位)应是人性的内在要求,所以荀子认为“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荀子·荣辱》)。事实上,相比于孟子,荀子更清楚地认识到政治的本质是权力,同时也真切地看到权力在教化民众、实现秩序中的重要意义。“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乱世,得乱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乱得乱也。君子非得势以临之,则无由得开内焉。”(同上)然而,统治者毕竟如何“得势”以临之?我们曾经说过,面对“德”与“位(势)”的分离,荀子虽心生幽怨与无奈,同时也表现出对“德位合一”的理想形态的向往,但在此形态破裂以后,他依然坚持以德致位,鄙视“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者”(《荀子·非十二子》),期待“尽伦尽制”的圣王的再世(16)参见东方朔:《荀子的“圣王”概念》,《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因此,在统治者统治权力的来源上,荀子既否定了周人的天命论,也不同于孟子的命定论。在荀子看来,天只是自然之天,“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天不是一个人格神,并没有命人予权力的意志,而统治者的统治权力也不是“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孟子·万章上》)的上天或命运的安排。依荀子,统治者权力来源的“正当性”应当在权力的起源上得到恰当的说明,质言之,统治者之统治权力当因其优异的德(能)及其为民众带来实际的福祉而获得民众的认可。
不过,在具体论述荀子的主张之前,在理论上首先应当区分权力在“根据”上的正当性和在“效果”上的正当性(其实义当为合理性或证成性)这两个并不相同的概念。换言之,我们既不能只说明根据的正当性而无视效果的正当性,也不能以效果的正当性(合理性)来取代根据的正当性。之所以要提出这一区分,主要源于坊间有些学者在论及荀子有关权力来源的正当性问题上多以“效果”来代替“根据”,使得“正当性”问题滑转成为“证成性”问题,盖站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角度,在权力来源的问题上,所谓“根据”的正当性说的是统治者的统治权力获得被统治者的意志同意(谓自由自决);而所谓“效果”的正当性指的是统治者权力作用的结果在客观上符合被统治者的期许和利益要求。虽然此两者互有关联和重叠,但并不相同。即便统治者的统治权力获得被统治者的意志同意,但如果此权力作用的结果造成国家混乱、民众流离失所,那么,其正当性的辩护效力将会遭到极大的减杀;反之,我们也不能以效果的“正当性”(合理性或证成性)来取代根据的正当性,效果是权力运用给民众带来的实际利益和福祉,但权力来源的根据的正当性,关注的是统治者所获得的统治权力是否取得被统治者的意志同意——此一根本的道德基础,故而以效果或所获得的实际利益为权力来源的正当性证明并不完全合适和如理(17)有关正当性与证成性的关系并非本文所欲讨论的重点,周濂认为“一个政治权力哪怕拥有再多的证成性,也无法推出它就拥有正当性,但是一个原本具备正当性的政治权力,如果它缺乏足够的证成性,例如缺乏基本正义、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安,就一定会削弱它的正当性”。(参见周濂:《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第43页。)。周濂曾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此中关系,简洁而明晰:张三会定期将自己的车开到服务优良的某洗车厂清洗,但一天他因红绿灯将车停在某十字路口时,一小孩并未征得张三同意便开始擅自洗车,小孩的洗车技术和服务态度都好,也是张三所要的,但当小孩向张三要洗车费时,张三拒绝了。通过这一事件可得出的结论是:小孩的洗车行为并没有正当性,因为他没有征得张三的意志同意;但由于小孩的服务质量和态度良好,也是张三所希望的,故小孩的洗车行为有合理性(证成性)(18)参见许纪霖、刘擎:《政治正当性的古今中西对话》,第3—4页。。
三
假如我们基于上述有关“根据”的正当性和“效果”的正当性(合理性或证成性)之间的关系作为理论的判准,那么不难看到,在权力来源的正当性问题上,荀子和传统儒家大凡皆以“效果”的正当性(合理性或证成性)来取代和说明“根据”的正当性。我们暂且从《荀子·富国》篇开头的一段开始分析。荀子云:
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势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如是,则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则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则群众未县也;群众未县,则君臣未立也。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居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强胁弱也,知惧愚也,民下违上,少陵长,不以德为政:如是,则老弱有失养之忧,而壮者有分争之祸矣。事业所恶也,功利所好也,职业无分:如是,则人有树事之患,而有争功之祸矣。男女之合,夫妇之分,婚姻娉内,送逆无礼:如是,则人有失合之忧,而有争色之祸矣。故知者为之分也。
这段文字向来被学者认为是荀子思想中极为重要的文字,梁启超将之视为理解荀子政论的“出发点”之一(19)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1页。。依荀子,在前政治社会的群居生活中,原初人与人之间聚族而居,“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同上),并没有什么等级差别,人们原则上各凭自己的知能而各尽其力,各遂其生。在此时期,虽然人群地位相同,没有尊卑贵贱之别,但人与人之间由于知识不同而有智愚之分。然而,因为没有相应的政治制度和管理组织,导致智愚同势,智者没有机会行其治道、建其功业,结果人人纵欲行私而生天下之害,及其至也,则不免而有“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荀子·性恶》)的局面。为了逃离这种“强胁弱也,知惧愚也”(20)“惧”训“恐吓”,或“欺凌之使之恐惧”。张觉训“惧”为“害怕”,恐非是。(李涤生:《荀子集释》,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第198页;熊公哲注译:《荀子》上册,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182页;张觉:《荀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8页。)、天下悖乱相亡的状态,难道我们可以去过一种离群独居的生活吗?荀子显然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依荀子,人的生命在宇宙万物中其实显得十分的弱小,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但若要以“牛马为用”(《荀子·王制》),依靠单个人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并不可能,“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荀子·富国》),此正所谓一人之所需,百工之为筹,故云“人之生不能无群”(同上),人类必须合作结成团体,组成社会国家,非此则不能“胜物”以有度地满足人的欲望,确保人类的生存。然而,由于人的欲望贪得无厌(21)《荀子·荣辱》云:“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而满足欲望的物品又有限,故若“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荀子·荣辱》),而物不赡则争,争则乱;人情也是如此,劳苦之事皆为人所厌恶,而劳苦所得的成果又皆为人人所喜欢,长此以往,人人就会以树立自己的事业为苦,而有争夺他人之成果的祸患。至此,荀子认为,为了“救患除祸”(《荀子·富国》)、息争止乱,必须有优异的智者来领导群伦,明定尊卑贵贱之分,使众人和谐相处(22)荀子的这种观点或看法在来源上或受到《管子》的影响。如《管子·君臣下》云:“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黄宗羲《原君》谓:“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大体也与此相关。但黄宗羲认为,人主之所出乃“受命于天,原非得己”(《明夷待访录·奄宦下》),这一说法与周人和孟子的主张似乎没有多少差别。。
此处,不妨说荀子是以浓缩的方式描述了一幅“自然状态”的图像。为了摆脱这种“争乱穷”的困局,荀子以“知者为之分也”一语作结。此说法包含多重含义:首先,在荀子看来,摆脱前政治社会的争乱状态,进入政治社会的“支配-服从”关系,亦即在权力的最初起源上,是以“智者”获得其统治地位作为标志的,智者不出,人群便仍处于只考虑其自然本性的状态,仍服从于丛林法则;其次,“群而有分”是组成社会、达致和谐与秩序的最佳方案,惟待有“分”,方能凝定人群,区分职业等级,组成社会国家,进而有效地建立秩序,故云“有夫分义,则容天下而治;无分义,则一妻一妾而乱”(《荀子·大略》)(23)对于荀子言“分”所包含的含义,陈大齐有概括的说明。Eirik Lang Harris论荀子的政治哲学,专门有一节论“分”(allotments),认为“分”对于荀子的政治哲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是理解其组成社会概念的核心。但他不同意佐藤将之(Masayuki Sato)将“分”理解为规范性的概念,而认为是描述性的概念。在他看来,暴君(the tyrant)的分虽然使其国家和人们的生活遭受危险,然而,他的定分的事实表明他的分一点也不合理。不过,假如我们紧扣着荀子言“知者为之分”及其类似脉络来看,荀子在此意义上的“分”显然是一个富含价值意义的规范概念,这从荀子论君道的“四统”以及大量的相关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参见陈大齐:《荀子学说》,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56年,第147页;Eirik Lang Harris, “Xunzi’s Political Philosophy”, Dao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Xunzi, ed by Eric L.Hutton, Dordrecht: Springer: 2016, pp.98-99.)。然而,此处我们更关心的是能够明分、定分的智者指的是谁?智者凭什么或通过何种途径为人群明职定分?换言之,智者为人群定分的权力是如何获得的?
先说定分的智者。按荀子在《礼论》《荣辱》《王制》等篇的说法,是“先王制礼义以分之”,故而定分的原则是礼义,定分的主体是“先王”,但“先王”又常与“圣王”“圣人”“仁者”等说法相同或相似;而在《富国》篇中,荀子则说以“智者为之分”。如是,“智者”当与“先王”“圣王”等说法同义;且同在此篇中,荀子又认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所谓“管分之枢要”指的是掌管定分的关键或核心,如此看来,“智者”也可以指的是“人君”,而“人君”是社会国家中握有最高权力的统治者。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意义上的“智者”或“人君”是在合知虑和德能为一体的角度上说的(24)冯友兰在论及荀子有关社会国家之起源时,引上述《富国》篇的一段后,有一评论甚可注意。冯氏云:“盖人有聪明才知,知人无群之不能生存,又知人无道德制度之不能为群,故知者制为道德制度,而人亦受之。‘故知者为之分也’,‘知者’二字极可注意。盖人之为此,乃以其有知识之故,非以其性中本有道德之故也。”此处特别强调“知者”的本质在于其有“知识”而非本性中有“道德”。这一看法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就人类在尚未进入政治社会、在没有礼义文明的情况下,“知者”之“知”如何一开始就能“知道德”“制道德”?此处尚需从道德动机上加以说明,盖荀子主“圣人”(包括“知者”)与“途之人”在本性上相同;另一方面,从孟、荀之异的角度看,冯氏强调“知者”的知识面而非本性中的道德面显然有其合理性。但其中的疑惑在于,《荀子》一书在许多地方又常常把“为之分”的“知者”与既仁且知的圣人或王者看作同义,换言之,“知者”不仅仅只是“有知识”,而且有道德,所谓“道德纯备,智惠甚明”(《荀子·正论》)。为此,冯氏的说法或许可以启示我们一种可能的解释,即在由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社会的过程中,荀子的思想可能存在由“知者”到“圣王”的发展过程,在社会国家起源的最初阶段,“知者”的本质更多的表现为知识和见识,尔后经由在漫长的过程中逐渐演变积累,起伪而形成道德,而合德智为一体。为方便起见,本文将“知者”笼统地理解为仁智统一的王者或德能上如理的君主。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荀子所说的“智者”是一个应然意义的理念形态。(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2页;东方朔、徐凯:《荀子的道德动机论——由Bryan Van Norden与David B.Wong的论争说起》,《学术月刊》2018年第1期。)。
显然,去除不必要的辨析,我们关注的问题是“智者”或“人君”最初是依靠什么获得权力?综合《荀子》一书的相关论述,可以直接地指出,“智者”或“人君”之所以能取得其统治的权力,主要是由于其超卓优异的知虑和德能以及它们带给民众的实际效果(25)罗哲海也认为,在荀子那里,“君主的出现乃是为了人民的福祉,而非以谋求自身的利益为念。他们是基于受人信赖而掌管权力”。但他又认为,在荀子的学说中,“统治者的地位之所以获得认可,确实有某种契约的成分作为基础”。若此处所说的“契约”是以西方思想为参照,则罗氏的说法不免有过度诠释之嫌。其实罗氏自己对此说法也颇感犹豫,甚至不免前后扞格。(参见[德]罗哲海:《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陈咏明、瞿德瑜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87、90页。)。民众之所以拥立人君,给予他绝对的地位和权力,首先是因为人君的道德权威(知虑与德能)的身份使得其政治权力“正当化”,而不是民众的意志同意(26)参见东方朔:《权威与秩序的实现——荀子的“圣王”观念》,《周易研究》2019年第1期。。由民众意志达成一致的方式给人君权力,在荀子思想中是不可想象的。若紧扣着《富国》篇的脉络,则民众是在“欲多而物寡”前提下,为了除患避祸、止争息乱、赢得安全与和平,而拥立那些德能知虑最为优异的人为人君,赋予他最高的权力,明职定分,建立秩序,“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荀子·王制》)。换言之,荀子并不是在“根据”的正当性上,而是在“效果”的合理性上来论述和说明权力及权力的来源。
四
史华兹在论及此点时曾经指出:“与霍布斯不同,荀子并没有提出过圣人如何设法建立其权威的问题。”此处所说的权威,其恰切的含义应是近代意义上的政治权力的正当化。依史氏,在荀子的思想世界中,“先锋队精英的实际品质——不论这种品质是如何形成的——自始至终都是极为关键的”(27)[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6页。。史氏所言无疑端的。事实上,荀子所谓的“智者”或如理意义上的“人君”确因其优异的品格构造和卓越的才能而赢得民众的信赖而获得权力,荀子在《王霸》篇中使用“聪明君子”来代替“智者”,其实两者的意思并没有多大区别。荀子云:“羿、蜂门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驭者也。聪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势从之,人不服而势去之,故王者已于服人矣。”此处所谓“聪明君子者”即是“王者”或“智者”,可泛指有德有位的人君等;“服人”谓使人顺服;“势”一般可理解为“权势”“权力”。大意是说,聪明君子善于使众人顺服。众人顺服,权力便从之而来;众人不顺服,权力便随之而去,故王者之人止于使众人顺服而已。此处王者之人或人君之所以能使人顺服而有权力,并不是因为其统治的权力在来源上获得众人的意志同意,而是说众人之所以对人君顺服(而使其有权力),原因在于王者之人或人君卓越的德、能及其制定的制度设施所具有的带给众人的客观效果所致。荀子在“君子”之前特别加上“聪明”作为修饰词(28)此处“聪明”一词当在宽泛意义上来理解,揆诸《荀子》一书的相关文本,其含义大抵包括志意、德音、智虑的卓越等方面(《荣辱》《富国》),陈大齐将之突出地概括为“既仁且智”。(参见陈大齐:《荀子学说》,第178页。),并在“聪明君子”之前铺垫了“羿、蜂门”“王良、造父”,意在说明正是这些德能优异人群的特殊优越性(及其客观上带给众人的利益福祉)造成众人的顺服和权力的来源(29)在“是谁给了统治者统治权力”的问题上,传统儒家虽有“民本”之说,但从未在“经由民众意志同意赋予其权力”此一正当性的根源意义上用心思考;“民本”虽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其实质更多的是一种道德训诫意义上的应当“为民作主”,而不是在权力根源意义上的“由民作主”,它只是在发心动念上告诫统治者要懂得“民心”的重要。故而在特殊的理论格局和传统的制度结构中,“民本”之说会在很大程度上流为统治者的统治技巧的术语。。
此处我们应当注意到荀子的一种特殊说法,所谓“服人”与“人服”。民众之所以顺服,是因为“智者”善于“服人”;而“智者”所以“善服人”,则纯系于其优异的德(能)。此外,“人服”一说在含义上又关联到“认可”(consent),但“认可”一词在权力来源的正当性上既可以从“根据”的正当性上说,也可以从“效果”的合理性上说,而这两种说法在意思上并不相同(30)罗哲海认为,在荀子看来,“人民的认可即是权力的直接基础”。依此翻译,这种说法在含义上似乎并不明确,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不过,此句的英文原文为“the acceptance by the people directly becomes the mandate for power”,此处罗氏没有用“consent”而用“acceptance”,前者偏向于意志表达的同意,而后者明显具有对效果或结果的接纳。([德]罗哲海:《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第94页; Heiner Roetz, Confucian Ethics of the Axial Age: A Reconstruction under the Aspect of the Breakthrough toward Postconventional Thinking,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75.)。乍看起来,《荀子》一书许多地方都有与此相类似的说法,如云“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荀子·非十二子》),“从服”意含认可;又云“天下归之之谓王”(《荀子·王霸》),归者,依也,顺也,也已然有认可义。荀子最典型的说法是在《富国》篇,荀子云:“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者,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虑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则治,失之则乱。百姓诚赖其知也,故相率而为之劳苦以务佚之,以养其知也;诚美其厚也,故为之出死断亡以覆救之,以养其厚也;诚美其德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藩饰之,以养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无它故焉,其所是焉诚美,其所得焉诚大,其所利焉诚多。”此处“仁人”可指代智者或人君;“知虑”“仁厚”“德音”指其优异的德(能);“所得”“所利”谓因其优异的德能获得民众的信赖而赋予其权力、并藉此权力“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者”而给民众所带来的客观的利益和福祉。荀子的逻辑是:因为“仁人”的知虑、仁厚、德音足以能为社会去乱成治,为百姓带来最大的幸福和利益,故百姓“诚赖其知”“诚美其厚”“诚美其德”,乃至于“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贵之”“亲之”“为之出死断亡”的说法表达的是百姓对人君统治权力的心悦诚服的认可。只不过荀子所说的这种“认可”,是在“果地”而非在“因地”,或者说是在“效果”的合理性而非在“根据”的正当性来说明的,而这样的说明已然由正当性滑转成了证成性。
那么,在权力来源的正当性上,荀子何以只在效果的合理性而不在根据的正当性加以说明?此中的原因颇为复杂,但与儒家的重德尚贤理论或精英主义主张相关应是有根据的(31)对于儒家重德精神的得失,劳思光有精到的分析,此处不展开说明。此外,中国传统也向有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说法,孟子则浩浩然谓“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荀子也有“无君子,则天地不理”(《孟子·公孙丑下》)的观念,及至近人梁漱溟有“吾侪不出,如苍生何”的主张。当然,精英意识非独为儒家所有。(参见劳思光:《儒学精神与世界文化路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前引史华兹所谓“先锋队精英”的品质,表达的正是儒家的精英意识;日本学者渡边秀方认为,在荀子那里,“得贤以治国的思想,溢满了他的遗著”(32)[日]渡边秀方:《中国哲学史概论》,刘侃元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98页。;而罗哲海则干脆指陈,“荀子无疑是早期儒家中最极力鼓吹精英统治的人物,而这与他替道德寻出理性的基础有直接关联。如果道德态度只有通过理性的洞察力才能赢得,那么一般的‘愚众’必然要接受外来的管束,而知识界的精英们则可以追求自身的影响力和独立性”(33)[德]罗哲海:《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第290页。。罗氏从道德需要以理性为基础,指出精英对于一般“愚众”的必要性,自成一说。事实上,在权力来源的问题上,荀子之所以将“正当性”(其实质是合理性)置诸于那些具有优异德能的智者或人君身上,在他看来,一方面是因为只有这些德能优异之人才能为民众救患除祸,排忧解难,为政治社会带来良好的秩序;另一方面,在荀子的眼里,民众或百姓又多是一群愚陋无知且自私好利之人,可引之于大道,而不可与其共明事理(34)《正名》篇云:“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郝懿行谓:“夫民愚而难晓,故但可偕之大道,而不可与共明其所以然,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22页。)。因此,在盛赞贤明智者的另一面,荀子对大众的愚昧浅陋也多有描述。如荀子云:“彼众人者,愚而无说,陋而无度者也。”(《荀子·非相》)又云:“志不免于曲私,而冀人之以己为公也;行不免于污漫,而冀人之以己为修也;甚愚陋沟瞀,而冀人之以己为知也:是众人也。”(《荀子·儒效》)不仅如此,这些人还不学问,无正义,以货财为宝,以富利为隆。依荀子,在人欲无穷而物品有限的状态下,领导群伦、制定规则以摆脱困境的工作并不能寄望于这些愚陋的民众,而只能寄托于那些德能优异的智者(人君)。盖理论上,民众既昏蒙无识,自利偏私,则逻辑上他们也就没有能力仅仅依靠其自己选择出他们的有德能的统治者;相反,民众的愚陋闭塞只有等待智者的开示,所谓“告之、示之、靡之、儇之、鈆之、重之”,尔后才能使“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僩也,愚者俄且知也”(《荀子·荣辱》)。不仅如此,在荀子的思想世界中,民众的利益和福祉乃至一切人生事务都需要智者或人君为他们谋取和安排,圣君一出,则“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若使无君,则家不得治,国不得宁,人不得生(35)参见东方朔:《差等秩序与公道世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1页。。用现代政治哲学的语言来说,似乎一切的“主权”(sovereign)都归属于人君而非民众。故荀子云:“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势,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荀子·富国》)。意思是说,人君以德抚下,百姓以力事上,用力的要受有德者之役使;百姓的劳力要靠人君(之德化)而后有功,百姓的群体要靠人君而后和谐,百姓的财富要靠人君而后积聚,百姓的环境要靠人君而后安稳,百姓的生命要靠人君而后长寿。明乎此,则荀子所谓“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妇,是之谓至乱”(《荀子·王制》),其实义之所指当不待解而明。
如前所云,本文是站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讨论荀子有关权力来源的正当性问题,它意味着权力来源的正当性乃是预认了自我意志的自由和自决为观念前提。故而,与有些学者的看法不同,我们认为荀子并没有从“根据”的正当性,而只是从“效果”的合理性上来说明权力的来源。换言之,荀子真正关心的是权力行使的合理性,而不是权力来源的正当性。荀子重德,且极言“德必称位”(《荀子·富国》)。然而,在来源问题上,“德”之实现赖乎个人的修为;而“位”(权力)之取得归诸百姓之自决,此诚为正当性之究竟义,不可混淆。奈何荀子自始则视百姓为愚陋无知之人,但可教而化之,而无能自决其领导者,至是所谓正当性问题在儒家传统中总是晦而不明,暗而不彰,其故盖良有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