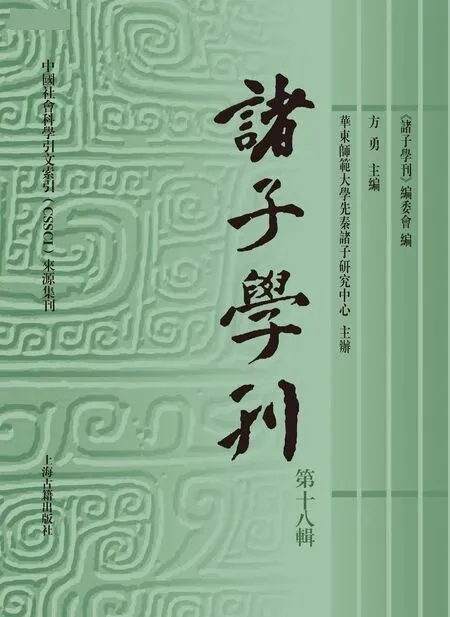從“道”與“藝”之維看“數”*
——以儒家“六藝”之“數”爲中心
王傳林
内容提要 先秦時期的人們對“數”的體認是極爲深刻的,他們不僅敏鋭地看到了“數”與“道”的關係,而且從“技”與“藝”之維看到了“數”以及深藴其中的技術性、藝術性與審美性。“數”作爲經驗呈現出從感性過渡到理性的路向,“數”作爲技藝呈現出人與物的互動,“數”作爲知識呈現出圖式化、程序化與邏輯化的進路。從“數”與“道”的邏輯關係來看,“數”、“道”之間,以是相藴;“數”藉於“道”,“道”以“數”顯。儒家“六藝”之“數”大抵藴含數度之道與理財之道。“六藝”之“數”作爲“六藝”之“一藝”具有“理念數”與“技藝數”的基本特徵,因此有其獨特性與藝術性,亦有其技術性與程序性,以及人與物的互動性。
關鍵詞 數 數哲學 六藝 技藝 經驗 知識
早在“軸心時代”(1)[德] 卡爾·雅斯貝斯著,魏楚雄等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頁。,中西方的人們對“數”的認知與運用就已經達到較高的程度。從儒家“六藝”之“數”與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數”來看,數度之道在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之間遊弋,他們殊途同歸地從“道”的層面來理解與詮釋“數”,並努力將其指向人自身。
一
先秦時期,先民們在占卜時,根據龜甲燒裂的自然成紋之象,觀“象”成“數”,取“象”分“類”,逐漸地從具體事物中抽繹出“數”並賦予其哲學意涵。這即是《左傳》僖公十五年所言:“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古人認爲“數”是天地萬物之所以然的本質所在,亦是事物與事物之關係的本質所在。“數”有道數、天數、命數、禮數、律數、曆數、度數、算數等多種意藴,“數”涵蓋了道理、規律、方略、策略、技藝、方術等諸多義項。大體上説,先秦時期的“數”有三種基本義項: 一是理念數(2)《廣雅》曰:“數,術也。”秦漢時期,人們基於《周易》“象數”發展出術數之學,此種“數”既有理念數之義,又有數學數之義。;二是數學數;三是技藝數。
根據《周禮·地官司徒》記載,“六藝”是指“禮、樂、射、御、書、數”。所以説先秦儒家“六藝”之“數”是技藝數,這種技藝數既有理念數之意藴,又有數學數之意藴。古人認爲,“數: 計也”(3)許慎《説文解字》(上),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47頁。,“算: 數也”(4)同上,第371頁。,故將數、計、算互訓而用。同時,他們認爲數、計、算貫通天道,即數學數與技藝數貫通理念數。他們聲稱:
夫算者,天地之經緯,群生之元首;五常之本末,陰陽之父母;星辰之建號,三光之表裏;五行之準平,四時之終始;萬物之祖宗,六藝之綱紀。(5)李淳風《孫子算經·序》,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頁。
由是觀之,“算”作爲方法、技藝與數度之道的呈現可謂是統攝天地萬物、人倫物用與政治綱常,甚至成爲人們生活的基本準則與價值標準。“數”作爲一切存在之“道”與“理”的呈現與人們經驗理性的湧現而存在,指導人們的日常生活、社會與政治的運行。
然則以往有學者將儒家“六藝”之“數”理解爲占卜之數或占卜之術、或以“術數”概之,其實是不妥切的。或曰,以“術數”解釋先秦儒家“六藝”之“數”,尤其是孔子所傳授的“六藝”之“數”是存在問題的。根據《論語》記載,孔子是不語怪力亂神的,更是罕言利與命的,因此將儒家“六藝”之“數”解讀爲命、卜、相之術並用來推測自然、社會與人事吉凶的方法或技藝,這與《論語》所記是不符的。我們認爲,應該將儒家的六藝之“數”理解爲數度之道與理財之道,類似於今天的算術、會計或計算之法,其主要内容應該是“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此九章之術是也”(6)鄭玄注,賈公彦疏《周禮注疏》(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71頁。。因爲孔子“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7)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909頁。,所以他精於此種技藝應該是有極大可能的。當然,“數”作爲具有哲學涵義的概念在先秦兵家、法家、墨家、道家以及其他先賢那裏也偶有涉及(8)《孫子兵法·兵勢》云“治亂,數也”,《管子·權修》云“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管子·重令》云“天道之數,至則反,盛則衰”;又如《韓非子·飾邪》云“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墨子·雜守》云“天下事備,强弱有數”;等等。,但是相較於儒家而言,其他諸家對“數”的關注多是數度之道,並没有將其技藝化、知識化。因此,儒家的“六藝”之“數”作爲技藝成爲區别於其他諸家的重要教育範式之一。
與先秦儒家將“數”技藝化不同,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學派認爲“數是萬物的本質”,“萬物皆數”,同時認爲“數”是“存在由之構成的原則”和“終極的原因”(9)[美] 弗蘭克·梯利著,葛力譯《西方哲學史》,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18頁、15~19頁。。他們有時將表達數學理性的純粹的數與宇宙萬物冥冥之中的神秘之數相混淆,同時又將數之内涵(本質、規則)和現實生活中的現象相比附,使得“數”看上去不僅貌似邏輯嚴謹而且很神秘。特别是他們將數與音樂、數與幾何圖形、數與天體運行相關聯,其中更是夾雜難以捉摸的神秘與不可言喻的臆測。在畢氏學派那裏,“數的恰當排列”被詮釋爲“宇宙的法則”,這種“恰當排列”湧現出一定的比例或者對稱,並被他們視爲審美理想——和諧。“他們這樣做時,完全沉溺在符號解釋之中”,“他們企圖承認萬物的守恒秩序可以用概念來理解,來表現;他們企圖在數學關係中找到這種秩序的最後根源”(10)[德] 文德爾班著,羅達仁譯《哲學史教程》(上),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69頁。。然而,隨着“不可公約數的發現”(11)[英] 羅素著,何兆武等譯《西方哲學史》(上卷),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43頁。,畢達哥拉斯學派的這種將哲學建構與神秘主義、數學理性相結合的做法導致了“畢達哥拉斯悖論”。值得指出的是,畢達哥拉斯學派認爲“一”是萬物之源,其他事物都是由“一”而生,並且賦予從“一”至“十”這十個數字各自不同的内涵。其中,“四”代表正義,“七”是智慧之神秘闡發,“愛情和友誼用數字‘八’來表示”(12)[美] 弗蘭克·梯利著,葛力譯《西方哲學史》,第18頁、15~19頁。,“十”不僅是一個完美的數字,而且包含了相同數目的質數和合數。同時,他們不僅發現了勾股弦定理(斜邊長度數值的平方等於直角邊長度數值平方的和),而且形成了獨特的數思想。當然,他們對“數”的理性理解是和對神的感性理解交織在一起的,以至於有學者批評他們的數學思辨“都是從宗教的靈感中引申出來的”(13)[法] 萊昂·羅斑著,陳修齋譯《希臘思想和科學精神的起源》,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83頁。。畢達哥拉斯學派將“數”與神秘相結合或者説數學與神學相結合對中世紀以後的哲學家影響頗深,如阿奎那、笛卡爾、斯賓諾莎和康德等人,他們思想深處大都或多或少地殘存一種宗教與推理密切交織的情結,“一種道德的追求與對於不具時間性的事物之邏輯的崇拜的密切交織”(14)[英] 羅素著,何兆武等譯《西方哲學史》(上卷),第46頁。。此外,畢達哥拉斯學派還將宇宙中“數”的規則與秩序引向現實社會與政治領域,並以此論證建立優良社會與道德規範的可能性。
較之,儘管軸心時代的中西方的哲人們不約而同地注意到“數”與“數字”,但是他們的哲學理路卻不盡相同。畢達哥拉斯學派大抵是沿着純粹理性挺進的,他們最終走向了數學、幾何學與哲學,而先秦儒家則是沿着實踐理性與倫理理性挺進的,他們最終走向了知識、技藝與倫理學。所以,深受畢達哥拉斯學派影響的古希臘的“四藝”(幾何、算術、天文和音樂)與儒家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雖有小異,實則大同;尤其是其價值向度都是指向塑造人與成就人的。
二
“六藝”是“大道”的呈現載體與範式,由“道”至“藝”,“道”的抽象性與形上性被“藝”的邏輯化與藝術化所取代,“人”作爲行爲主體“循乎道”、“遊於藝”。此時,“道”向“人”敞開,“藝”的呈現使得“道”與“人”同時在場,並以藝術化的形式呈現“道”與“人”的完美結合——“藝”之境界。
(一) “六藝”之“數”源於經驗
追根溯源,“六藝”之“數”源於生活與生産經驗,它是生活與生産經驗的理論凝結,是理論理性對感性經驗的抽象化與圖式化。“六藝”之“數”作爲經驗,其形成過程既可視爲一種理論自覺的過程,亦可視爲一種理論製作或理論抽象的過程。只不過,在“數”之經驗的形成過程中,製作者面對的並不只是某種具體的材質或事物,而是需要從生産與生活中的林林總總的事物中抽離出有關“數”的智識並使之經驗化、理論化。林林總總的事物有着不同的質地、紋理與規律,呈現出光華、幽暗或神秘的表象以及難以捉摸的性質,這些並不會輕易地爲人所把握。因此當製作者面對林林總總的事物時,則需從所面臨的事物的本質着眼去尋其特性,找其規律;唯有如此,才能够駕馭其特性,掌握其規律,進而形成洞見。這個過程是人與物交互的過程,猶如人馴化野生動物(例如馴化野馬或野牛等)一樣,在馴化過程中,野生動物爲人所馴服、所利用。與此同時,人自身也在這種馴化過程中完成自我塑造——成爲騎手或獵手等具有相應特殊技能的人,從而形成感性經驗並從中拓展自己的視野,提升理性智識。簡言之,人面對林林總總的事物既是探尋其特性與規律的過程,也是自我塑造與理論建構的過程;同理,“六藝”之“數”作爲經驗其形成過程亦可作如是觀。
儘管個體經驗是構築人類共同經驗的細胞,但是個體經驗自身卻有其獨特性,猶如演員與合唱隊的邏輯關係。當然,我們並不否認“數”的最初經驗是由個體感知而來的,個體情感從自我中流溢而出並形成具有共通性與共同性的集體經驗的交集部分。“數”作爲經驗對象向每個經驗者敞開與湧現——是其所是地敞開與湧現,其間,個體經驗如水滴融入大海呈現出經驗的共通性與客觀性。最初的感性經驗在不斷實踐中逐漸被圖式化、程式化與邏輯化,直至形成較爲固定的習慣或技藝。然而,日常經驗的粗糙性、豐富性與碎片化在某種程度上支離了“我”的整體性與“道”的整全性,凡此經常迫使“我”陷入日常經驗的困境,以至於造成對“道”的遮蔽。因此,日常經驗無法進入理性批判的細節,人只有駐足於純粹經驗與實踐理性才能擁有深邃的眼光,才能洞穿迷霧般的表象,才能抵達無遮蔽的真理之域。因爲事物之規律性與必然性只會在無遮蔽的狀態中敞開與湧現,並成長得生機盎然。在日常經驗的燭照所不能覆蓋的領域,理性之光是異常奪目的;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事物之“數”纖毫畢現。因此,人可以在日常經驗的基礎上借助理性之光探尋大道及其萬般景象與呈現範式。一言以蔽之,“經驗”言説“理性”,“數”言説“道”。
“六藝”之“數”作爲經驗,其尋繹與建構是個充滿張力的雙向過程,“人”作爲行爲主體一方面要順乎事物之性;另一方面又要有能力尋繹出其中的特性、形成規律——“數”。同時,在這個雙向過程中所形成的經驗既要能爲人的再次經驗所驗證,又要符合事物的本質性、規律性與必然性。在這個尋繹活動中,人作爲經驗理論化的主體要能够從自然紛繁的事物中尋繹出事物之共性與規律,並以理性統合完成這種抽離與演繹。這個過程本身之於紛繁的事物而言,是一種理性之光照亮事物之幽暗的過程,物自體之幽暗經由理性之光逐漸消退,其内在結構與紋理——其數,其本質性、規律性與必然性漸次被理性之光所照亮。换言之,人是“思”的主體,“數”是“思”的對象;人在思時通過數字符號面向存在。人之符號化能力的進展與物理實在之幽暗的退卻成反比,符號因其普遍性與有效性成爲打開自然界與人類世界的鑰匙(15)參見王傳林《董仲舒之“數”》,《光明日報》,2015年11月23日第16版。。
(二) “六藝”之“數”作爲技藝
當人們以“六藝”概稱“禮、樂、射、御、書、數”時,“數”作爲“技藝”的意藴便湧現出來了。“六藝”之“數”作爲一種技藝,正是在人與物打交道的過程中形成的;在人與物的互動過程中,人獲取了智識,形成了技藝。“六藝”之“數”作爲一種技藝不僅僅是對事物特性與規律的精準把握,而且也是對事物之共性與規律的知識化。這種知識化是通過特殊的形式與邏輯推理來實現的。當然,人與物打交道的過程在此並不是簡單的粗暴的互動過程,其間需要長期的觀察、推演與訓練,人作爲知識化過程中的主體需要持久地在這個互動過程中與特定的對象相親熟。可以説,任何一種技藝的形成都是經歷了漫長而艱辛的過程,因爲人需要理解特定對象的特性與規律,這是一個緩慢而艱苦的過程,其間所産生的諸般念頭不僅會稍縱即逝,而且往往缺乏理論理性的支撑。諸般念頭並非皆是源於理性的純然的知識,它們往往是非理性的靈光一閃。誠然,技藝的形成之於生命個體而言也是其生命成熟的過程與理性呈現的過程,這種過程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够獲得的,它容涵了諸多艱苦的探尋與嘗試。即便是聖人孔子也是經歷了漫長的時間之流才做到順乎自然之規律、識得諸事之道理的,誠如其所云“吾十五有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爲政》),“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論語·子罕》)。换言之,一個成熟的有理性的人一定是能够順乎自然規律、因循事物之理的人,也一定是恰當把握時機使自我生命達到圓融或圓滿境界的人。
技藝之所以稱之爲技藝,它體現出人、技、道的三者統一。遺憾的是,人在技術形成過程中其整全性卻被逐漸消解,同時,社會的分工也使得人的全面性逐漸隱退——成爲專門人才。西漢時期,人們常用通五經、明六藝作爲贊美之詞,大抵是稱贊某人學養與素質的出類拔萃,兼通諸技。比如在司馬遷眼中,“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孔子世家》)。大體上看,“六藝”之“數”作爲技藝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人作爲行爲主體與具體事物相互動,必須克服自身的固執與偏見,識得事物之規律,同時還要通過一系列的動作與程式來展示人與物互動的過程——技藝演示與訓練。第二層面,人作爲行爲主體必須有能力穿透事物紛繁而複雜的表象,理解自身並使之與具體之物達到相互的理解。簡言之,技藝演示與訓練的過程即是人理解物與人理解自身的過程。第三個層面,人作爲行爲主體要明白此種技藝是如何來塑造自我生命的;或曰,此種技藝是如何成爲生命的一部分的,又是如何形成一種極具個性化之風格的。
其實,“六藝”之“數”的教育也是一種技藝。“六藝”之“數”的教育作爲一種技藝,它是對“六藝”之“數”這種技藝進行傳授和啓迪的技藝,是開啓受教者的經驗理性、重塑其敏感度、提升其理解力與想像力的教化活動。在“六藝”之“數”的教育中,感性的經驗讓位於理性的計算與嚴密的推理,“數”的教育與詩、書、禮、樂的教化有明顯的區别,它似乎明顯地排除了感性在其過程中的作用,使受教者不僅學會與“人”打交道,更要學會與“物”打交道。同時,技術形成的過程也是受教者擺脱自身盲目性與任意性的必經之路,它爲生命的持續展開賦予新的價值向度,使生命不至於無謂地耗散在幽暗的混亂之中。因爲任何一種技藝的價值所在並不是俘虜人,而是給人帶來自由,開啓一個全新的世界,並讓人理解這個世界、暢遊於這個世界,從而切近本源、識得大道。誠然,每一種技藝都藴含着行爲主體對世界、事物與自身生命的理解與把握,因此我們認爲技藝作爲一種活生生的存在其本身便是生命的敞開與湧現,便是大道的敞開與湧現。
(三) “六藝”之“數”作爲知識
尋綜六藝,契闊馳思。儒者遊乎六藝之囿,騖乎仁義之塗,自覺地肩負起傳承大道、播撒知識的重任,將基於“六藝”的教化視爲塑造理想人格的首要任務,並以此去理順社會、政治與人倫之秩序,努力使其和諧運行、健康發展。
“六藝”之“數”作爲知識,它向我們呈現的是“數”的理論化的存在,具有可傳授性。其中,解釋與建構發揮重要作用,因爲“數”之知識的傳授要求教育者與受教者在知識本身達到某種高度的理解與契合,同時這種理解與契合還須符合“數”的本質規定性和人與物之間的規律性。儘管在此過程中,經驗會發生必要的作用,但是更多的還是需要借助理性的力量與邏輯的力量,因爲若要符合“數”之本質規定性就必須將後天經驗從中盡可能地排除,否則其結果就有可能是經不起檢驗的。“六藝”之“數”作爲知識若不跨越從後天經驗到先天理性的統合,從面對“物”躍向面對“思”,那麽這種知識便不是盡善盡美的,甚至可以説是缺少形而上學之根基的。
“六藝”之“數”作爲知識教育,它强調“數”這種技藝的形成過程與生命歷程的耦合。其中,訓練扮演了重要角色,這種訓練是全方位的,它包括心智的訓練與技能的訓練;尤其是技能的訓練,甚至需要手把手地指導。因爲“六藝”之“數”的教育是在教育者與受教者長期互動與艱苦訓練中完成的,其間師者不斷糾正受教者的各種謬誤與任性,使其朝着理性與邏輯挺進。在這種教育過程中,教育的主體與客體均發生變化,他們的生命與思想通過教化活動被重新定義,並被賦予新的價值。同時,這種教化活動通過對已知的熟稔去找尋通往未知的道路,並實現多方位的更新與提升: (1) “數”作爲知識其自身的更新與提升;(2) 教育者自身知識與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更新與提升;(3) 受教者自身知識與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更新與提升。在這個教化活動中,受教者被刻意塑造成符合某種特定標準的“人”(如會計、出納等),即符合“數”之技能的“人”。所以説,“六藝”之“數”作爲知識與“六藝”之“數”作爲知識教育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路,前者强調積累與實證,後者注重理解與把握;前者强調純思與抽象,後者注重整合與塑造。
當然,“六藝”之“數”作爲知識與“六藝”之“數”作爲技藝,此二者有聯繫,也有區别。在知識領域中,“數”被其自身的邏輯所限定,可以通過實證來檢驗;在技藝領域中,“數”自身所藴的“道”賦予了“技”之“妙”(靈性)。相較而言,前者頗具客觀化、規律化之特性,後者則頗具情境化、詩意化之韵味。“數”作爲知識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了行爲主體的主體性,是屬人的一般性的認識對象與學習對象;“數”作爲技藝則需要行爲主體的高度參與,並且要達到相當高超的境界——將“數”之技藝内化於自身。在知識領域中,理性出場,非理性退隱到幕後,甚至完全退出;在技藝領域中,非理性成了主角,理性退隱到幕後。“六藝”之“數”作爲知識是注重程式化與邏輯化的,甚至是僵硬而冰冷的;“六藝”之“數”作爲技藝則是充滿情境化的,富有靈性的,甚至是頗具神秘色彩的。原因在於,“六藝”之“數”作爲知識是可重複的,可檢驗的,而作爲技藝則似乎是不可完全重複的,技藝的展現不僅僅要求行爲主體“在場”,而且其展示過程要求其對技藝有很强的控制力、感悟力與呈現力,有時此過程可能是靈活多變的,充滿彈性的,並非東施效顰或邯鄲學步所能領悟的。
三
先秦時期的人們對“數”的體認是極爲深刻的,他們不僅敏鋭地看到了“數”與“道”的關係,而且從“技”與“藝”之維看到了“數”以及深藴其中的技術性、藝術性與審美性。
(一) “數”藉於“道”,“道”顯於“數”
從“六藝”之“數”的本質來看,“數”作爲“六藝”之“一藝”是藴含“道”之精神的。儘管“道”貫通於“技”,但是人作爲實踐“技”的主體則需在對技藝的不斷深化中來體認與把握“道”。顯然,一個不精通某種技藝的人是很難對此種技藝之道有深刻體會的,更不要説達到高妙的境界了。誠如孟子所言“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孟子·盡心下》),這裏的“規矩”與“巧”即如“數”與“道”。莊子筆下的“庖丁解牛”(《莊子·養生主》)與“輪扁斫輪”(《莊子·天道》)的寓言所闡釋的也是這個道理。
其實,所謂“道”顯於“數”,就是“道”以“技”顯。值得指出的是,“道”在“技”的靈活性、變化性、藝術性與個性化中得以敞開與湧現;相反,“道”則在“技”的知識化、邏輯化與固定化中被窒息與消解,即“道”本身所藴涵的諸般特性被知識化的過程所凝固與遮蔽,由此,“道”被帶入幽暗之所。這種情形猶如“紙上談兵”、“閉户學操舟”(16)明人王廷相在《石龍書院學辯》曰:“世有閉户而學操舟之術者,何以舵,何以招,何以艪,何以帆,何以引笮,乃罔不講而預也;乃夫出而試諸山溪之濫,大者風水奪其能,次者灘漩汩其智,其不緣而敗者幾希。何也?風水之險,必熟其幾者,然後能審而應之,虚講而臆度,不足以擅其工矣。夫山溪且爾,而況江河之澎洶,洋海之渺茫乎?彼徒泛講而無實歷者,何以異此?”參見王廷相《王廷相集》(二),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605頁。,前例説明“(趙)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故招敗亡;或曰,空談死道理,不知戰争作爲一種技術或藝術的變化性與靈活性,其敗局早定。後例説明“道”以“技”顯,千變萬化;空談誤事,唯有實踐出真知。
“六藝”之“數”是對“道”的具體化呈現,是一種技藝與技藝數。當然,傳授“六藝”之“數”也是一種技藝,一種教育或教化的技藝。儘管“六藝”之“數”與傳授“六藝”之“數”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技藝,但是它們均是對“道”的體認、把握與運用。所以説,“六藝”之“數”作爲一種技藝與技藝數是深藴“大道”的。脱離“道”來解讀“數”是膚淺的,脱離“數”來解讀“道”是空洞的;同樣,僅僅關注於“數”的形式與表象則是看不見“道”的精深與玄妙的;或曰,“技”只有在其運至“妙”時,“道”才會自然呈現。
(二) “技”以載“道”,“數”以“藝”顯
技以載道,道以技顯。倘若一門技藝没有鮮活的傳承,而是成爲固定的知識,死了的書面道理,其諸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便被消解了,其技之藝境則無從得見了。如若想讓“道”復活,就必須先讓“技”有所傳承與展現,“技”之“妙”的呈現即是“道”復活的標誌。
由“技”至“藝”,需要工夫、需要練習,只有道、技、藝三者貫通,才能達至“藝”、呈現“美”。這其中所表現出的不僅僅是行爲主體對自身的理解與控制,更重要的是對“物”的理解與控制,以及對“道”的理解與把握。正是在這個雙向理解與控制的過程中,行爲主體通過不斷地提升自己的感受力與理解力達到對物之性的洞悉與貫通,從而使“道”在“技”的展示過程中呈現出來;基此,“人”在趨於“道”的過程中形成技藝。不可否認,“道”是很難被直觀所洞見的,它必須借助“技”來敞開自身、呈現自身。當然,“道”作爲理念而存在並不是僵化的,“理念一方面通過思想而實現,一方面又通過行爲的媒介而實現”(17)[德] 黑格爾著,賀麟等譯《哲學史講演録》(第二卷),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第183頁。;如是,理念與客體,道與人、物才會實現統一。
誠然,“道”之境界是頗爲神秘的,也是難以把握的,而“技”之境界與呈現則是直觀的、情境化的。古人認爲,唯識得音律之數,才能習得琴技,領悟琴道。清儒顔元指出,“歌得其調,撫嫻其指”只能算是處於“學琴”階段,“手隨心,音隨手”才算是進入“習琴”階段,“心與手忘,手與弦忘”才是真正進入“能琴”階段(18)顔元著,王星賢、張芥塵、郭征點校《顔元集》(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78~79頁。。其實,“學琴”階段是“琴”控制“人”——事物以其固有特性征服人的主體性與能動性;“習琴”階段是“人”控制“琴”——“人”作爲操琴的主體首先馴化自己肢體的頑固與僵硬,逐漸進入嫺熟階段——“人”通過對“道”的體認與把握開始馴服事物固有的特性;“能琴”階段是“琴”與“人”合而爲一——事物固有特性與人的主體性、能動性與創造性實現統合,人與琴完美結合,“道”得以呈現、得以情境化與在場化。所以説,人在學琴、習琴與能琴的過程中,識得音律之數,不斷練習,終至“人”與“琴”爲一,即“人”與“道”爲一。
概言之,道之於技、道之於數,其猶如是技藝之上的技藝,只有在技藝呈現的高潮才會清晰呈現。儘管“道”始終貫穿於“技”中,但是只有當由數近道、由技進藝之時,才可能出現“庖丁解牛”過程中的“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莊子·養生主》)的妙境。
四
從教育角度看,儒家“六藝”中的“禮、樂、書”側重於德性教育,“射、御、數”則側重於技能教育。其實,“六藝”之間是彼此相資,以是相藴;或曰,六藝異科,而道皆同。推而言之,“數”“道”之間,以是相藴;“數”藉於“道”,“道”以“數”顯。“數”作爲經驗呈現出從感性過渡到理性的路向,“數”作爲技藝呈現出人與物的互動,“數”作爲知識呈現出圖式化、程序化與邏輯化的進路。
儒家“六藝”之“數”作爲“六藝”之“一藝”具有“理念數”與“技藝數”的基本特徵,因此有其獨特性與藝術性,亦有其技術性與程序性,以及人與物的互動性。所以説,儒家“六藝”之“數”作爲先秦數哲學的基本範式之一具有與衆不同的哲學意藴與價值向度,值得我們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