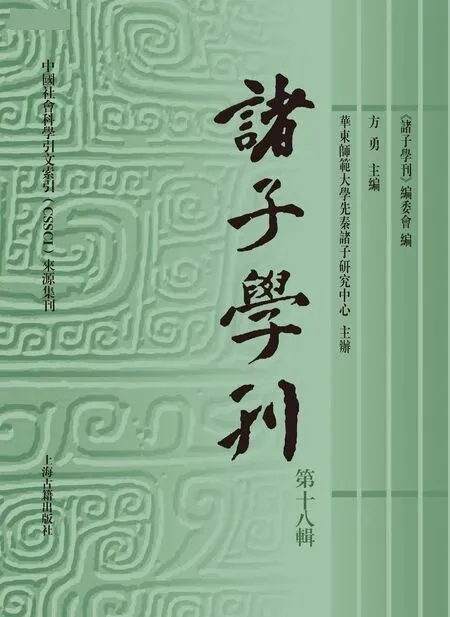親親相隱與差等之愛
——儒家倫理、政治及孝道擴展的結構
岳賢雷
内容提要 儒家認爲,“親親相隱”並不破壞(否定)政治正義(所謂“直”),後者正是存在於以前者爲中心的差等結構之中,所謂“直在其中矣”。第一,差等原則才是真正符合正義的原則;第二,無差别原則包含在差等結構之中。差等之愛的結構即孝道擴展的結構,“親親相隱”的本質即在於退出政治領域,以保護親情倫理,因此不可能導致政治上的腐敗,其典型體現在孟子稱舜“竊負而逃”的思想實驗中。這個故事尤其能説明政治以倫理爲基礎,但正義絶非不重要,而是要由脱離事件相關人倫理關係的政治身份人來維護。
關鍵詞 親親相隱 差等之愛 孝 大義滅親 竊負而逃 倫理 政治正義
學界對“親親相隱”争論了十多年,筆者認爲,争論的焦點集中在儒家以親情之愛爲核心的差等之愛——即其倫理政治結構——是否破壞社會與政治正義。對此争論的考察,必然會涉及對儒家整個倫理政治結構的理解。筆者認爲,這同時也是對孝道及其擴展結構的理解。本文即是以“親親相隱”及其争論爲綫索,對傳統儒家意義結構進行考察。
一、 對“直”與“隱”的解釋
“親親相隱”的直接文本是“父子相隱”,前者是後者的引申與發展,後者的直接文本即《論語·子路》所載: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關於“隱”,大概有四種解釋:
第一,對外不稱揚(隱含隱痛之意),不檢舉、不告發,即法律中的“親屬容隱”權(1)經俞榮根先生考證,古代法律確認的“隱”,包括對犯罪人通風報信以抗禦偵查和緝捕,及“相容隱”之人可免於作證和拷訊取證以抗禦刑訊和審判。見俞榮根《私權抗禦公權——“親親相隱”新論》,《孔子研究》,2015年第1期。、回避制,對内的“幾諫”和“微諫”。此説代表人物爲鄭玄(2)程樹德《論語集釋》,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925頁。,今人有郭齊勇、林桂榛、周桂鈿、丁爲祥等先生(3)見郭齊勇《“門内”的儒家倫理》,《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郭齊勇《“親親相隱”“容隱制”及其對當今法治建設的啓迪》,《社會科學論壇》,2007年第8期;郭齊勇、龔建平《“德治”語境中的“親親相隱”》,《哲學研究》,2004年第7期;郭齊勇《也談“子爲父隱”與孟子論舜》,《哲學研究》,2002年第10期。參見郭齊勇主編《儒家倫理争鳴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儒家倫理新批判〉之批判》,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林桂榛《“父子相爲隱”與親屬間舉證》,《現代哲學》,2010年第6期;林桂榛《“父子相隱”與告親的正義性問題》,《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8年第2期;周桂鈿《“子爲父隱”新議》,《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8年第4期;丁爲祥《孔子“父子互隱”與孟子論舜三個案例的再辨析》,《學海》,2007年第2期。。
第二,櫽括,引申爲矯正。代表人物有梁濤、顧家寧、廖名春、王弘治等先生(4)見梁濤、顧家寧《超越立場,回歸學理——再談“親親相隱”及相關問題》,《學術月刊》,2013年第8期;廖名春《〈論語〉“父子相隱”章新證》,《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王弘治《〈論語〉“親親相隱”章重讀》,《浙江學刊》,2007年第1期。。這種解釋出於緩解父子親情與法律正義之間的緊張,其合理性其實就是“幾諫”與“微諫”,但不如後者具體詳細,且有父子之間互相“責善”的意味(5)《孟子·離婁上》:“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離婁下》:“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第三,伏滅、伏絶,即“敬以直内,起敬於微眇,絶惡於未萌,義以方外”,以王興國先生爲代表(6)王興國《再論“親親相隱”——“直”與“隱”之辨》,《學術月刊》,2014年第8期。。此論折中了上面兩種觀點,析理入微,頗有新意。然既曰“絶惡於未萌”,就不適合已經犯下罪錯的情況。
第四,以權謀私、政治包庇和腐敗。以鄧曉芒、劉清平等學者爲代表(7)鄧曉芒《再議“親親相隱”的腐敗傾向》,《學海》,2007年第1期;《就“親親互隱”問題答四儒生》,《學術界》,2007年第4期;《就“親親相隱”問題再答四儒生》,《學術界》,2008年第3期、第4期。收入鄧曉芒《儒家倫理新批判》,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劉清平《美德還是腐敗?——析〈孟子〉中關於舜的兩個案例》,《哲學研究》,2002年第2期。。
筆者認同第一種對“隱”的解釋,對第四種理解的反駁,詳待下文。
關於“直”的解釋,大概有三種:
第一,自然情感的直率、真誠,持這種觀點的人比較多。王興國先生稱之爲“人情”論,以馮友蘭和李澤厚先生爲代表。其並指出以梁濤、顧家寧爲代表的“由情及理”派,對“父子相隱”這一章中的“直”的理解仍然是“情感”論的。另外,何善蒙、曾小五、陳壁生等學者也將此章之“直”理解爲情感的率直與真誠(8)見何善蒙、貢哲《率直與正直——〈論語〉中“直”及其内涵再探》,《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3期;曾小五《〈論語〉中的“直”與“仁”之辯——兼及近年來“親親相隱”的争論》,《原道》,2012年第1期;陳壁生《孔子“父子相隱”思想新解》,《中國哲學史》,2008年第1期。。
第二,正直、正義(9)黄勇先生認爲,此章之“直”應該理解爲“正曲爲直”之直,並認爲子爲父隱本身不是直,而是通過微諫的方式以實現直之手段。見黄勇《正曲爲直: 〈論語〉“親親相隱章”新解》,《南國學術》(澳門),2016年第3期。筆者認爲“正曲爲直”仍然屬於廣義“正直”的範疇,祇不過將其動詞化。孔子説“直在其中矣”,很明顯直不是最終目的,而父子相隱所體現親情才是。本文將闡明,子爲父隱不是實現直的手段,而是以自身爲目的之意義世界,直不過是其附帶效果。。
第三,人情人心之直,自然情感的本然之直。换句話説,即儒家思想中的“自然情感”,或曰“順理之直”、“天理人情之至”。以朱子爲代表(10)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46頁。,今人有郭齊勇、張志强等學者(11)張志强、郭齊勇《也談“親親相隱”與“而任”——與梁濤先生商榷》,《哲學研究》,2013年第4期。。
《論語》中的“直”大概有兩義,一爲道德上的正直、道義上的正義;一爲性格的率直、情感上的真誠。第一種義項甚多,如:“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爲政》);“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顔淵》);“以直報怨”(《憲問》);“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衛靈公》);“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微子》);“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孰謂微生高直?”(12)通常謂微生高爲不率直,筆者以爲此直爲差等之愛結構中的“正直”,與“直在其中”同義,解釋詳下。(《公冶長》);“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13)史魚堅守原則,雖然不及“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的君子蘧伯玉,但其“直”仍然是一種德性,而非單指性格上的率直。(《衛靈公》)等。第二種義項有:“質直而好義”(《顔淵》);“狂而不直”(《泰伯》);“友直”(《季氏》);“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惡訐以爲直者”(《陽貨》)等。第二種義項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稱爲德性,所以率直與正直有難以截然劃分的情況,比如“直而無禮則絞”(《泰伯》),“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陽貨》),與仁、知、信、勇、剛並言,皆爲德行之稱,“直”不可能單指性格上的率直而與德行毫無關係。一般情況下,率直之人若“堅持”其率直,可成就正直的德性。
這一章的“直”首先是葉公讚揚“直躬”的行爲所體現的無差别原則,因此肯定首先指正直與正義,而不是指情感上的率直與真誠。孔子説:“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直在其中矣。”看不出孔子所言“直”的字義與葉公有什麽不同,祇是對“直”的意藴、所關聯的“世界”有不同的理解。葉公認爲“直”就是無差别原則,孔子認爲“直”應該存在於差等之愛之中。因此,孔子並没有否認“直”的無差别的含義,祇是認爲這種無差别原則應該鑲嵌在差等之愛的結構中。换句話説,無差别原則在差等之愛結構的整體中,居於最外緣的位置。無差别原則是對待無差别之人(比如陌生人)的原則,而父子之親是差等之愛的核心,怎麽可以無差别對待呢?
“直躬”之“直”爲無差别原則,在《韓非子》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印證。韓非子説:
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奸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韓非子·五蠹》)
韓非子從維護君權的絶對性出發,明確反對儒家以父子關係爲核心的差等原則。在法家看來,君主之下的兆民都是無差别的,正是看到了“直躬證父”所體現的無差别原則和對儒家差等原則的破壞,韓非子才將之稱爲“君之直臣”與“父之暴子”。
但在《吕氏春秋》《莊子·盜跖》《淮南子》等諸子文獻中,“直躬”之“直”皆解讀爲“信”,這是怎麽回事呢?我們將文獻集中引録如下: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14)“載”通“再”,見陳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09頁。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吕氏春秋·當務》)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莊子·盜跖》)
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淮南子·氾論訓》)
《吕氏春秋》中的“直躬者”頗有巧言令色之嫌,他先通過無差别的“信約”破壞了差等之愛的原則,之後又想通過差等之愛的原則來取得“孝”名,前後矛盾。故曰“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這三則文獻中的信皆爲“守信”,不同的是“直躬者”之信是普通民衆與普遍規則(王法)之間的政治信約,尾生之信是普通人之間的臨時信約。二者的共同點即是無差别對待,不管面對的對象是父親,還是環境突變。對於後者,《盜跖》篇前文有交代:“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15)此典故使尾生在後世成爲守信的代表,感情色彩由貶至褒,李白《長干行》“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即是。或許是因爲與女子期約而死與愛情中生死相許的形象太接近了。用現在的話説,二者皆爲“教條主義”。
原來,無差别原則下的正直與守信,是一體之兩面,就其内在品質來講爲正直,就其符合别人的期許來講爲守信。
因此,“隱”指對外的不稱揚,不檢舉,不告發,和對内的“幾諫”和“微諫”。而“直”指正直、正義没有問題,關鍵是這種正直和正義是在差等之愛結構中的。葉公所讚揚“直躬”之直取消了這種結構,所以孔子説: 在差等之愛中,本來就存在着“直”;這是在以父子關係爲核心的差等結構中的直,與你們無差别的直是不同的。因此,也可以説,孔子贊成的直爲“天理人情之直”、“順理之直”。
二、 孝道的擴展: 差等之愛的結構
上引《莊子·盜跖》與《淮南子》中的“尾生”,有學者認爲即《論語》中的“微生高”(16)見程樹德《論語集釋》對“微生高”的考證,第347頁。: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公冶長》)
我让每个人拿出一张纸,把小马最近干的捣蛋事儿全写上,写完后当场宣读。那些受惊的女生义愤填膺,在纸上沙沙写着。这些女生平时个个伶牙俐齿,待会儿一定会批得小马体无完肤。小齐狠狠瞪了小马一眼,低头写了起来。小齐是班里的作文好手,他写的内容肯定尖锐猛烈,上去一朗读,还不把小马羞死?小马虽然是个调皮大王,但要叫他当众挨批也是受不了的。既能教化人,又锻炼了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我暗自为自己一举多得的教育智慧而高兴。
對微生高通常的理解是,微生高不率直、不真誠,沽名釣譽。以朱子爲代表,《集注》云:
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殉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17)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82頁。
其實,“乞諸其鄰而與之”不一定是把鄰居家的當作自己家的再借出去,完全可以在人來借醋的時候,坦言自己家没有,“不過你等會兒,我給你向鄰居借去!”這也是非常可能和非常真誠的。用今天的話説,這種人叫“熱心過度”。“熱心過度”恰恰是無差别原則。當别人來向自己求助時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説與别人有約定了。看來正直與約信是有關聯的,正直不過是按照公共約定的規則做事。所以微生高所有的“直”名很可能就是守信,而非率直或真誠。這可能也是《吕氏春秋》與《莊子·盜跖》皆以“信”稱直躬與尾生的緣故。
嚴格來説,“自然情感的真誠”與“順理之直”,在儒家的語境中並無差别。不過第一種觀點往往被誤解爲個體經驗情感之真誠的意思,這就不是儒家的本義了。王船山在對此《論語》“父子相隱”章的訓義中説:
凡一德之成,皆必順乎性之所安,而不任其情之所流,與氣之所激。唯中國爲禮義之邦,先王之風教陶鎔其氣質,而士君子以學術正其性情,故人咸有以喻其天性自然之理,……而五方風氣之變,未有禮義以調其情、平其氣,則雖有一德之長,而成乎詭異不經之行,且自旌異以爲人所不能及矣。楚俗尚氣,而任情之一往。(18)王夫之《四書訓義》,《船山全書》單行本之七,岳麓書社2010年版,第750頁。
因此,在個體經驗情感上,“直躬”很可能是非常真誠的,但這種真誠不是儒家的“天性自然”之誠,即不正。這裏所謂“自然”不是任何個體後天經驗意義上的自然而發,個體後天經驗上的差等情感基本上每個人都不一樣,很多人不是以父母爲中心,他或她最在乎的很可能是戀人、愛人,或者老師,或者領導,甚至國家或某種意識形態,各種可能都有。但儒家偏偏以父子或親子關係作爲差等結構的核心,其理由何在呢?
人們常説父子爲天倫,但情感不就是後天的嗎?存在先天的情感嗎?儒家認爲有的。孟子説:“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盡心上》)孩提之童對父母的愛就是先天的情感,因爲孩童尤其嬰兒必然需要“父母”,即使不是親生的父母。這種依賴在儒家看來就是最原本的愛,它與被這種需要所唤起的“父母”對“孩子”超出個體自我即忘我的付出,是愛的根本。儒家認爲這種情感應該被保持,在後天經驗中不斷被回溯、被唤醒,被實現爲新的形式。後面這些是在先天的基礎上成長出來的“正”的情感,儒家認爲這才是“自然”。而其他形式的情感如果僅僅是後天的,與先天的親子之愛没有關聯的,那麽在本體論——生命論上就是無根的。這也就是《孝經》提出要以孝爲德之本的緣故。後天的情感與親子之愛發生關聯,準確説即一切行爲以孝爲最終目的,爲實現孝行之一部分,所謂“泛孝論”與“孝之終始”即是(19)參見岳賢雷《逆向時間性與自然血脈上的人文精神——〈西銘〉孝論釋義》,《原道》總第35輯,2018年第 1輯。。《禮記·祭義》曰:
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這就是差等之愛的結構。孔子説,真正的“直”恰恰是差等之愛當中體現的直。第一,每個人都應該這樣;第二,那種無差别的“直”祇體現在它的差等結構的最外緣,是對於陌生人的直。後者就是我們現代人通常理解的正義,一視同仁,無差别原則。其實,無差别原則、一視同仁是講在同等條件下無差别,如果條件是不同的,卻得到同等對待,那恰恰是不公平。所以“直躬”對待鄉人和對待其父,其實是不平等的,因爲父親和鄉人——對於“直躬”這個人來講——是不一樣的。所以“直在其中矣”,可以從兩個方面去理解: 第一,這種表面上有差别的對待,其實才是真正符合正義原則的;第二,人們通常所理解的無差别的對待,其實是包含在這種等差結構裏面的。
三、 政治與倫理:“親親相隱”與腐敗問題
儒家講“親親相隱”,又講“大義滅親”,二者是否矛盾呢?後者的直接經典文本是《左傳》隱公四年:
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衛國州吁弑君作亂,老臣石碏之子石厚爲虎作倀,衛人殺州吁,石碏殺子,論者謂石碏爲“純臣”,且許之以“大義滅親”。其間接經典文本之一是《左傳》昭公十四年,叔向殺弟,孔子稱之爲“古之遺直”,“治國制刑,不隱於親……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殺親益榮,猶義也夫”!(20)張國鈞先生認爲“其是之謂乎”與“曰義也夫”、“猶義也夫”皆傳疑不傳信,孔子對石碏與叔向皆表示存疑,並非完全肯定(見張國鈞《大義滅親之疑和親屬容隱之立》,《政法論壇》,2016年第4期;《大義滅親首用之疑及其親屬容隱萌芽》,《船山學刊》,2016年第4期;《〈春秋〉懷疑大義滅親而發育親屬容隱》,《孔子研究》,2014年第2期)。筆者認爲其“發育容隱”的結論是成立的,但其論據值得商榷。從經典上下文與語法上,皆看不出孔子對二人有批評的意思。王引之謂“曰義”之“曰”當作“由”,楊伯峻認爲後“猶義”亦當讀爲“由義”,即“行義”(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367頁)。行義即爲直,未必如杜預、孔穎達認爲直低於義(見杜預注、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3頁)。再者就是《公羊傳》莊公三十二年,季友誅兄叔牙、慶父,《傳》稱“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又説飲而鴆之,不直誅,爲“隱而逃之,使托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在維護君臣大義的前提下,兼顧親親。
叔向、石碏、季友,這些人的共同特點是皆爲諸侯之世卿公族,而後二人更是處理弑君大罪,在可見的後世法律中,這種謀反大罪,也是不在容隱之例的,更何況這些人無法脱離其政治身份,不能像普通人那樣以倫理爲主,首重親親。另外,經査昌國先生出色之考證,在孔子之前,父子親情倫理還没有從宗法政治中獨立出來,而是被統攝於宗支友倫之中,後者的行爲標準即宗法(君臣)大義(21)査昌國《西周“孝”義試探》,《中國史研究》,1993年第2期;《論西周孝尊祖敬宗抑制父權》,《史學理論研究》,2001年第2期;《論春秋之“孝”非尊親》,《安慶師範學院學報》,1993年第4期;《論孔子孝觀念的革命性》,《北大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輯。收入査昌國《先秦“孝”、“友”觀念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因此,當孔子之後的儒家在評價這些“大義滅親”事件的時候,如果能够兼顧親親當然更好,如果不能,也不能苛責。不過,從“殺親益榮”的説法揣摩,孔子肯定認爲“殺親”本來是不該增加榮耀的。
是孔子將父子親情奠定爲君臣正義的基礎,而君臣也首先是有等差之倫理,其普遍性的規則祇是輔助性的。從政治身份的角度來看,要“不隱於親”,才是直,這没有問題。不過,祇要能够回避政治身份,就首先要照顧倫理身份。有學者認爲這是不同情境的問題,不是不同角色的問題(22)見金小燕《“親親互隱”是倫理原則嗎?》,《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筆者認爲,這不是不同情境的問題,無論偷羊還是殺人,從倫理身份角度講,都要隱(23)不過,謀反、謀叛、謀大逆在後世法律中是不許容隱的。另外,父母、祖父母對於子孫也没有嚴格的法律上容隱的義務(見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9頁;又見該書第一章第二節“父權”)。但道德上仍然有義務。。就其對每個人都有效來講,就是倫理原則。
在倫理身份中是要隱的,在政治身份中則不隱(24)《禮記·檀弓上》:“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對於儒家來講,政治根源於倫理,所以當兩種身份發生衝突的時候,在同等條件下,當然要棄政治,保倫理。在正相關的關係上倫理爲政治奠基,政治是倫理的實現,例如天子的政治身份就是天子倫理身份的實現,諸侯、卿大夫、士亦如之,庶人作爲人子或人父爲其倫理身份,作爲民爲其政治身份,政治身份可以上升下降變化,唯倫理身份爲人父爲人子不變。倫理爲體,政治爲用,體無不同而用各異,雖用各異而共在天子之大用中,即在以天子爲中心的政治共同體中。用不可害體,體毁則不復有用。
既然政治是倫理的實現,那麽是否可以利用政治的力量來保護倫理呢?筆者認爲在嚴格意義上,這是可以的。比如作法官的兒子利用自己的職權幫助自己父親逃跑(就像很多人對舜“竊負而逃”的理解一樣),這件事本身是否屬於腐敗行爲,筆者認爲要看這個兒子在這之後的行爲。如果他這麽做了之後仍然一如既往地享受他的政治權力,即他以倫理的標準破壞了政治的標準之後,仍然要從政治標準中獲得利益,那麽很明顯他是腐敗行爲,他有兩套標準;但如果他這麽做的同時認爲(知道)自己在犯法,並且和父親一起進行逃亡,那麽他對政治規則(在根本上)仍然是遵從的,祇是没有將之作爲成就自己的根本方式(那是倫理),即政治的標準是倫理標準的擴展,當不能擴展時捨棄政治保住倫理,仍然是唯一標準,這樣就不是腐敗行爲。
陳嘉映先生説,政治的目的應該是保障人的良好生活,後者屬於文教的範疇(25)陳嘉映《哲人不王》,《價值的理由》,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頁。。换作儒家的話説,政治的目的是爲了保障倫理生活。倫理亦屬於文教範疇。在儒家看來,政治是爲倫理服務的,如果一個人爲了保護倫理而退出政治,政治没有權力無限追責,這就是説,政治是有其邊限的。非不能也,不爲也(26)俞榮根先生在考察舜之所以能遵海濱而處,皋陶不追及之時説:“問題不在國家公權力之不能,而在於國家公權力之不爲。這‘不爲’並非官官相護之不爲,而是國家公權力對父子親情表示敬畏和尊重,其偵查權、緝捕權止步於父子親情之前。”見俞榮根《私權抗禦公權——“親親相隱”新論》,《孔子研究》,2015年第1期。。即使對於被殺人之子,儒家也不提倡無限追責。比如舜之遵海濱而處,樂而忘天下,這個天下不僅喻指天子之權力,也指政治文明的範圍。當一個人完全退出政治文明領域,此時再去“追責”,其實不能維護任何正義,不過就是仇殺、報復而已。當一個人的父親被殺,其父之生命便已經消亡,此時能够做的祇能在是文明範圍之内討回公道與正義,因爲一個人無端被殺是不正義的,但其生命是不可能恢復了(人死不能復生),這不受政治控制,而歸於天命所屬。
既然以體用來説倫理、政治,那麽有體而無用也是可能的,是否存在祇有倫理,没有政治的情況?筆者認爲是肯定的,並非人必須過政治的生活,而倫理的生活卻是必須的。《孟子·盡心上》講君子三樂(27)“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即可以不包括政治生活,而祇是倫理生活,而第一樂即是家庭天倫。亞里士多德説,人是(城邦)政治的動物,認爲政治是人性的完滿。在某種意義上儒家亦持此義,不過是在完成倫理、服務倫理的意義上,而絶不超越獨立爲外在自足之“形式”,而祇能是原有質地固有文理的彰顯,並不真的增加什麽。張祥龍先生認爲,對於儒家來講,親子關係(其中包含人之爲人最深長的時間意識)是人之爲人的本質(28)見張祥龍《孝意識的時間分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從人類學、社會學來講,最初人類並没有國家和政治,有的祇是家庭或家族及人與人之間的倫理情義關係(29)見[以色列] 尤瓦爾·赫拉利《人類簡史: 從動物到上帝》,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但以父子或親子關係爲中心來定義人的本質,不僅是從人類學經驗而來的結論,更是對人的自然生命性與人類特有的内時間意識的認知(30)見張祥龍《家與孝: 從中西間視野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版。。
四、 舜之“竊負而逃”: 差等之愛的典型説明
第一個被認作腐敗的案例,也是捨棄政治而保護倫理的案例,即孟子説的舜“竊負而逃”。當然,《孟子》中的這個“故事”祇是一個思想實驗,是假設,不是事實(31)參見劉偉《論政治生活的有限性——以孟子“竊負而逃”爲核心的考察》,《現代哲學》,2014年第5期。。《孟子·盡心上》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這裏,政治和倫理區分得很清楚,皋陶作爲法官,他的職責就是逮捕犯罪的人,舜對此絲毫不能干涉。“夫有所受之也”,有司法獨立的意思(32)朱熹注云:“言皋陶之法,有所傳授,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359頁。。對於舜來講,父親大於政治,正如楊澤波先生所言“父子親情比‘王天下’重要,道德比事業重要”(33)楊澤波《〈孟子〉的誤讀——與〈美德還是腐敗〉一文商榷》,《江海學刊》,2003年第2期。。舜放棄了天子之位來保護父子親情,既然已經放棄了權力,怎麽可能還利用權力來包庇父親呢(34)對此案存在幾個誤解: 1. 認爲舜先命皋陶逮捕父親,再從監獄中把父親偷出來,然後逃走。其實,皋陶逮捕瞽瞍不需要舜的命令,“執之”是皋陶執之,即使其兒子舜爲天子,“夫有所受之也”説得很清楚,舜没有權力干預。如果先已命令皋陶逮捕父親,桃應再問舜爲什麽不禁止他就是多餘的。2. 將“竊”理解爲“盜竊”。舜竊負而逃,是在瞽瞍被抓捕入獄之前,而且是先棄天子之位,然後逃跑。否則一旦抓捕入獄,舜在已經棄掉天子之位的情況下,再將瞽瞍盜竊而出的可能性已經非常小,不是不肯爲,而是不能爲。事實上,“竊負而逃”竊是副詞,指偷偷地、私下地,不是“盜竊”之義。3. 認爲瞽瞍已經抓捕入獄,舜利用自己的天子身份,將之盜出,然後棄位逃跑。認爲這是腐敗。筆者認爲,正如前文所説,這種情況雖然有所犯法,也是可以的。這裏,維護正義的責任不在於舜,由於他的父子親情——倫理之根本處於危險之中,他當然要保護親情倫理,而維護正義的責任在於此親情關係之外的其他政治身份人。?鄧曉芒先生對此有一個進一步的批評,他説:
該案的本質衝突並不在於親情和王位哪個更重要,而在於親情和正義哪個更重要,在於是維護家庭親情關係還是維護他人的生命權。(35)鄧曉芒《再議“親親相隱”的腐敗傾向——評郭齊勇主編的〈儒家倫理争鳴集〉》,《學海》,2007年第1期。
親情和王位哪個更重要,固然不是此案的本質衝突,但此問題對於儒家來講,絶非不重要。儒家講:
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孝經·聖治章》)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孟子·離婁上》)
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禮記·中庸》)
這是説政治身份是倫理身份的實現,身爲天子是孝道的最高表現。《孝經》説“孝無終始而患不及己者,未之有也”(《庶人章》)(36)唐明皇注本無“己”字。關於有“己”無“己”之差别,參見陳壁生《明皇改經與〈孝經〉學的轉折》,《中國哲學史》,2012年第2期。,當舜抛棄天子身份而與父逃亡,其實意味着孝道最大的虧損,這本身是一種最大的災難。但這不是不孝,恰恰相反,爲了守護孝道的根本,這是必須的,即政治身份服務於倫理身份——我參與政治領域,是爲了從中得到我需要的東西,比如俸禄(以養親)、榮譽(以顯親),宋以後那種爲天下而天下的至公主義不是先秦儒者所熟悉的(37)參見唐文明《朱子〈孝經刊誤〉析論》,《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但我不能否認這個領域的規則,所以政治有其獨立性。而政治以倫理爲基礎,不是如西方那樣以個體爲基礎,是中國思想的獨特之處,因爲相對於無差别原則,平等實現的關鍵恰恰在於對不同的情況不同應對,即他者意識。而親子關係首先就是超出自我,是有他的,而且這個“他”最爲獨特,不管是父母養育子女,還是子女孝敬父母,其行爲對象的獨特性需要耐心、細心體會。這裏不能一成不變,祇能唯變所適(38)《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孝子唯巧變。”《禮記·曲禮上》:“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大學》),這是對他者、對世界獨特性最充分的尊重。
對於第二個問題,儒家的回答也是與鄧先生不一樣的。親情比正義重要,正如我們前文所説,儒家的正義是在差等之愛之中的,後者的核心即親情,而正義作爲無差别原則祇是處於邊緣位置,爲對待陌生人的原則。核心當然比邊緣重要。對於每個人來講,父親的生命大於普通人的生命(39)據《三國志》記載,曹丕曾經試問群臣:“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當時邴原毫不遲疑地回答:“救父親!”君主的生命尚且大不過父親的生命,更何况陌生人。。這裏對等比較的是父親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不是諸如給父親買輛寶馬與他人的生命這種不對等的比較,所以“維護親情與維護他人生命權”的比較是不準確的。《禮記》講“父之仇弗與共戴天”(《曲禮上》),“居父母之仇,……不仕,弗與共天下也”(《檀弓上》)。舜之所以要逃到海濱,逃出政治文明架構之外,是針對被殺者之子而言的,於己於人,皆是出於孝道的考慮(40)“海濱”喻指天下、政治文明架構之外,參見劉偉《論政治生活的有限性——以孟子“竊負而逃”爲核心的考察》,《現代哲學》,2014年第5期。。
自己的生命大於陌生人的生命(41)惻隱之心不等於捨己救人,後者是現代集體主義推崇的價值觀,並非傳統(儒家)美德。不過惻隱之心有可能導致捨己救人,那是當事人始料未及的。而且惻隱之心是當下自發的,不是理性思考的産物,傳統儒家不可能認同爲了拯救一個陌生人而自覺自願搭上自己的性命。這就是爲什麽惻隱之心爲仁之端而孝悌爲仁之本、爲德之本。,父親大於普通人,筆者認爲這没有問題。這是人之常情,儒家正義正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而不對人有額外的强求,像要求愛路人與愛父母一樣,愛乞丐像愛自己一樣。鄧曉芒先生從無差别原則出發,説:
當一個人對於殺人者堅決不寬恕,哪怕這個殺人者是自己的父親或兄弟也不徇情時,這樣的人難道天下百姓還不能够信任他嗎?他不肯原諒自己的殺人的父親或兄弟,難道不正是出於對天下所有人的生命一視同仁的珍愛嗎?難道不正是秉公執法、“王子與庶民同罪”的堅決執行者嗎?(42)鄧曉芒《再議“親親相隱”的腐敗傾向——評郭齊勇主編的〈儒家倫理争鳴集〉》,《學海》,2007年第1期。
但鄧先生忘了,對於舜來講,取得天下人的信任,并非能讓他安心立命之根本,孟子説得很清楚: 天下之士悦之、富有天下、貴爲天子,皆不足以解憂,只有讓父母安心,看到父母喜歡自己,才足以解憂。(《孟子·萬章上》)儒家認爲,一個人不能爲了天下人的信任,乃至爲了對天下人的責任,而讓自己身心不安,畢竟前者是外在的,後者才是内在自足的。《詩》云: 有女如雲,匪我思存。鄧先生堅持的“大義”當然是偉大的,不過它要看由什麽人來堅持,如果牽涉的當事人與法官没有親情—倫理關係,法官當然要一視同仁。
但當當事人爲自己的親屬時,自己就要從這件事中退出,即使是朋友也要盡可能回避,但無論是沉默還是逃跑,都不是以倫理否定政治,而祇是放棄政治以保護倫理。就像放棄枝葉以保護根本的例子,枝葉不可能利用枝葉的力量來自我毁滅以保護根本,而祇能是根本放棄對枝葉的供養來自我保護,這裏不可能贊成政治(枝葉)上的自我腐敗。當一個人倫理—政治的通路已經斷絶之後,對於政治正義的維護自然要由其他道路通暢的人,即脱離事件相關人倫理關係的政治身份人來完成。
餘 論
吴增定教授在《現象學與“對世界的信任”》一文中認爲,胡塞爾和海德格爾都没能克服現代哲學中世界喪失的危機,重建對世界的信任。他引用黑尔德的話,指出二者推崇希臘思想,卻都忽略了它的一个關鍵維度,即政治。而這正是希臘人建立對世界樸素信任的原初方式——對城邦公共政治生活的參與。(43)吴增定《現象學與“對世界的信任”——以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爲例》,《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儒家並不否認政治參與的重要性,只是認爲更本源的方式是倫理參與,而政治是倫理的擴展。因此,儒家維持“對世界信任”的根本方式,就是通過以親子關係爲核心的倫理生活,及其擴展爲“立身行道,揚名顯親”的孝道—政治生活。
關於“親親相隱”及其“不正義性”,筆者認爲,壞人團夥之間的親密性與親子關係具有相同的超善惡的特徵。壞人團夥犯罪,但他們並不懷疑公共規則的有效性,反而他們更加切知其有效性。但如果親密關係人(如親人、好友)之間出賣了彼此,那麽他們對世界的信任就失去了,失去對世界的信任,必然是虚無主義(世界的崩潰),以致於無所不爲。因此文明建制的基礎就失去了,公共規則及正義也就不再可能。比如,“文革”强行規定廢除任何“私”心,鼓勵父子、夫妻之間互相舉報,所有親密關係都受到破壞——文明都崩潰了,談何公共規則!
因此“盜亦有道”在這個意義上,就不是一個諷刺性的問題,壞人之間也講義氣,也有非常真實的“仁義道德”。(44)《莊子·胠篋》講的“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云云,其實是將仁義道德作爲組織管理的工具,本文這裏乃是作爲對世界信任的情感及生存論基礎。莊子批評儒家的仁義建立在非道德的暴力基礎上,並且成爲暴力擁有者維護自己統治的工具,就是那句著名的“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莊子的批評無疑是深刻的,對於一切專制統治都是成立的。不過,儒家對竊國(比如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的態度之所以不是那麽强烈地反對(只要仁義的規則不變;丢棄仁義禮智,儒者視爲“亡天下”),也可以從其並不危及儒學親子之愛的核心來理解。當然,這並不能爲儒家面對專制時的軟弱態度而辯護。當然,也不能因爲後者而否認了親子之愛及一切親密情義關係,在建立對世界信任關係中的根本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