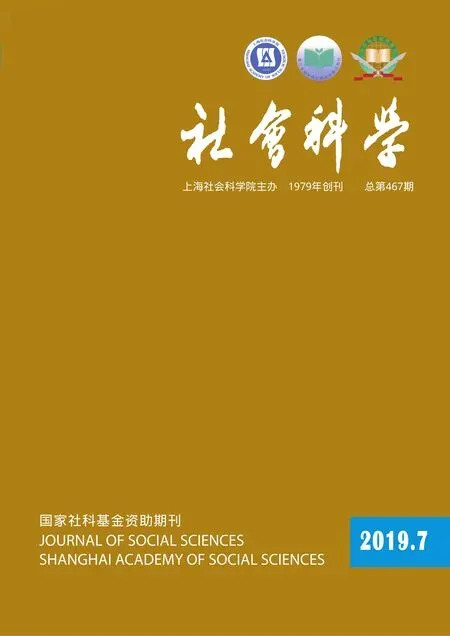何为善:儒家生生伦理学的解读*
杨泽波
人类发展如此之久,追求的极致目标无非是善、真、美而已。伦理学追求善,知识论追求真,美学追求美。自我从事儒学研究以来,即将与善相关的因素划分为智性、仁性、欲性三个部分,坚持三分法。近年来在建构儒家生生伦理学的过程中,又对这种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使之成为这门新学说的核心标志。有了这种新方法,便可以对何为善这个古老话题,做出自己的界定和说明了。
一、欲性之肯定
虽说求善是人的目的,但在此之前,人必须能够依靠物质条件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在儒家生生伦理学系统中,这方面的内容即为物质利欲,简称物欲,与物欲相关的因素叫做欲性。
儒家生生伦理学不否认物欲。“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说法虽出自《管子》,但儒家同样认同。孔子十分重视义利问题,首创义利之辨,但他对物欲并不持敌对态度,不走极端。孟子也一样,他不是苦行僧,有饭食不吃,有车辆不坐,有随从不要。义利问题的关键是看是否合道:合道,利再大亦不为过;不合道,利再小亦不能受。儒家不仅不否定物欲的作用,而且不将物欲等同为恶。恰如荀子所说,好色、好声、好味、欲食、欲暖、欲息,是人的自然欲望,本身并不为恶,只有顺其发展,争夺生而辞让亡,残贼生而忠信亡,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这个不好的结果才为恶。在先秦儒家义利之辨之中,不管是孔子,还是孟子、荀子,都不否定物欲。没有物质层面的生存,其他都说不上。[注]这并不是说人要是贫穷的,就可以不讲道德。贫穷没有一个绝对的值,即使物质条件十分贫乏,仍然不能放弃对于善的追求。民谚“屈死不告官,饿死不当贼”中的后半句,非常形象地表达了这个道理,体现了高超的生活智慧。这与以“替天行道”为口号的农民起义并不矛盾。农民起义主要是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而政治意义的农民起义,从根本上说,也离不开道德的诉求。
尽管儒家不否认物欲,但不以此为重,更加看重的是义,是道德,始终坚持道德的理想主义。既肯定利,又看重义,如何把握两者的关系,是一门大学问。先秦儒家是从人禽之分的角度来讨论这种义利关系的。人禽之分意义的义利之辨本质上属于价值选择关系。价值选择关系的要义有二:第一,在一般情况下,义与利并不矛盾,可以兼得,既可以要利,又可以要义,既可以要鱼,又可以要熊掌;第二,在特殊情况下,二者又会发生矛盾,不可兼得,这时必须选择价值更高的义,放弃价值较低的利,如果这样做了,就成就了善,做了好人,反之,就不能成就善,就沦为了小人。牢牢把握人禽之分义利之辨的价值选择关系,是准确理解儒家相关思想的关键。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有缺陷,将人禽之分义利之辨的价值选择关系理解为绝对对立关系,最终导致“存天理、灭人欲”等说法的出现,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大失误。
儒家历史上对于物欲的肯定,一般不超出上述范围。对今天而言,这个范围明显过窄了,除此之外,还应该关注法权问题。孟子与齐宣王对话时虽然讲过“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认识到有了固定的产业,百姓思想才能稳定,百姓思想稳定了,社会才能太平,但没有将其上升到法权的高度。这方面黑格尔的看法更有启发性。黑格尔非常重视法的问题,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权利。每个人都有权利将其意志变成物,受此影响,物不再是自在自为的,而是属于自己的,亦即自己对物有所有权。这一思想告诉我们,单纯讲物欲还不行,要成为政治主体,还必须将其上升到法权的高度。虽然这个话题严格说来属于政治哲学范畴,但在伦理学中也需要引起足够的关注。
二、仁性合于伦理是一种善
求善这个命题本身就意味着善有自己的准则,否则求善就没有了依据,成为了不可能。因此,人们往往认为,求善必须首先制定善的准则,善的行为即是行为者通过学习掌握这些准则,从而对这些准则的服从。
但现实生活并非如此。自孔子创立仁的学说后,仁便成为了道德的根据,能否成德成善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看能否按照仁的要求而行。后来,孟子进一步创立了性善论,提出了“四心”的说法,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并列,分别与仁义礼智相对,特别强调“四心”不是由外面取得来的,而是原本就有的,即所谓“我固有之”。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良心,都属于仁性的范畴。仁性的根本特点是内在。按照孟子所言,是非的标准不在外面,就在自己的心中,不需要他人告知,自己心知肚明,当恻隐时自知恻隐,当羞恶时自知羞恶,当恭敬时自知恭敬,当是非时自知是非。
人何以有仁性是一个重大学术问题。依据儒家生生伦理学,这当从两个方面分析。首先,人作为一个有生命的物来到这个世界,原本就带有一种生长倾向。这种倾向对人后来成德成善有着基础性的作用,不仅使人可以成为自己那个类中的一员而非其他,而且只要顺着这个倾向发展,遵循既有的行为规范,自己的那个类便可以得到有效的绵延。因此,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原本就有规则,虽然这些规则还只是自然性而非社会性的,严格说来还不能以善相称,但它毕竟为后来善的发展打下了根基。其次,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生存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因素,如社会风俗、文化传统等,都会对内心产生影响。我们不能想象一个人完全脱离社会而生存成长,也不能想象这种社会生活不会对内心产生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人的智性有了一定的发展之后,也要利用它来思考道德问题,这种思考同样会在内心留下一些痕迹。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对内心的这种双重影响,会使人的内心形成一种东西,这就是伦理心境。生长倾向和伦理心境不能截然两分,在实际生活中前者一定会发展成为后者,而后者也一定要以前者为基础。包含生长倾向的伦理心境是其广义,反之则是其狭义。
生长倾向和伦理心境是两个不同的来源。前者是人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个瞬间就具有的,后者则是人在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中逐渐形成的。生长倾向和伦理心境不仅来源不同,性质也不同。前者是先天的,即天生就有的,后者是后天的,即后天养成的。尽管有此区别,但它们又有一致性,都是先在的,具有先在性。了解生长倾向和伦理心境的先在性,是消除他人对我相关说法诸多质疑的关键环节。有人提出,我以伦理心境解说仁性,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做法,与儒家传统不合,因为儒家论道德从来都持先天的立场,认为道德根据是“我固有之”,是“天之所与我者”。要消除这种误解,必须明白狭义的伦理心境只是我诠释仁性的一个步骤,除此之外,我还讲一个生长倾向,生长倾向是天生的,对这个问题的证明不能诉诸于经验。当然,狭义的伦理心境是后天的,但应当了解后天也可以转变为先在。由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形成的伦理心境当然是后天的,但它在处理伦理道德问题之前早已存在了。这种“早已存在”,就是先在。而这种“先在”,根据我的理解,其实就相当于西方哲学讲的先验。人们对西方哲学这个概念的理解往往过于神秘化了,好像根本不能追问其来源似的。然而,如果上面的梳理没有根本性过失的话,我们不仅对先验有了与学界不同的理解,而且可以化解学界对我以伦理心境解说仁性的批评。[注]杨泽波:《经验抑或先验:儒家生生伦理学的一个自我辩护》,《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2期。
具有先在性的伦理心境平时处在隐默状态,这种情况就是学界现在常常讲的“隐默之知”。隐默之知是生活中常常可以见到的一种现象。为此我曾举过开车的例子:一个人用了很大的气力学会了开车,这种技能熟练到一定程度之后,便在自己身上隐藏了起来,在不开车的时候,甚至忘记了自己有这个本领。但隐默之知不会永远隐藏自己,一旦遇到相应的情况,就会显现自身。恰如一个人多年没开车了,当重新接触一辆车后,又可以很自然地启动上路,该转弯时转弯,该加速时加速,该刹车时刹车。伦理心境也是如此。平时没有遇到道德问题,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有伦理心境。可一旦遇到道德问题,它又会自己冒出来,告诉我们什么为是,什么为非,什么当做,什么不当做。熊十力以“当下呈现”讲良知之所以是一个了不起的命题,值得高度重视,原因就在这里。
儒家这一思想有着重要的哲学价值,它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具备一定思维能力的人,其成德成善的过程并不是从制定和学习新的准则开始的,而是始于发现和遵从自己内在的是非之心。[注]我提出这个说法,不是要否定学习对于成德的重要性。哪怕通过最简单的社会观察,也会明了,儿童遇事如何去做,总是要学习的,总是要大人教的。但对具有一定思维能力的成人而言,则不是这样。这些“成人”遇事时内心早已有了是非的标准,不需要“临阵磨枪”式的学习,只要发现并遵从内心的这些标准就可以了。但这里所说的“具备一定思维能力”很难给出一个年龄的标准。在这个问题过于较真,一定计较是多少岁,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人们在从事道德行为,做出道德选择之前,头脑并不是空的,不是一张白纸,上面早就有了东西。这种东西就是建立在生长倾向基础之上的伦理心境,就是仁性。伦理心境最奇妙之处在于,它虽然是后天的,但又具有先在性。这种先在性是实实在在的,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就一般情况而言,可以直接判定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善的生活不是从抽象原则,而是从自己的内心,从仁性出发的。孟子性善论最重要的价值或许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看得真切。
为了加深对仁性这一特点的理解,我们不妨将其与功利论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功利论是西方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代表人物是边沁。边沁把趋乐避苦作为其理论的基础。在他看来,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快乐有量的差异,如强度有大小,持续有长久,感受有远近,人们可以依此选择最大的快乐。如果一种行为带来的快乐占优势,它就是道德的、善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恶的。如果一种行为带来的完全是快乐而没有痛苦,它就是最大的幸福。大多数人都去争取这种最大的幸福,也就达到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理论后来为密尔所继承。密尔同样将快乐看做最重要的原则,但与边沁不同,他认为快乐不仅有量的差异,也有质的不同。人不能只是追求肉体享受,还必须追求更高级的精神快乐,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做一个满足的猪更有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密尔强调,功利论所追求的不仅是行为者自己的幸福,也包含一切与此相关人的幸福,甚至认为为别人而牺牲自己换取的幸福才是最高的幸福。由于密尔的努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成了功利论的最高准则。在功利论系统中,凡是符合这一准则的,就是善,反之,就不能称为善。儒家仁性学说完全不是这样,它并不关心建构新的准则,而是强调这个准则自己原本就有,就在自己的心里。一个将善的准则置于外部,一个将善的准则置于内心,依据前者善是一个外在的对象,求善必须遵从外在的准则,依据后者善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求善必须反求诸己,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路。
即使与德性论相比,孟子思想的特点也十分突出。近年来,德性论传统开始回归。德性论的重要特征是不以行为为中心,而以行为者为中心,关注的重点不是我应该怎么做,而是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特别强调不能将学说的重点和希望置于某些行为指南或道德规则的法典化,应该将其落实在人的德性上。但德性论并非完全不关注准则。赫斯特豪斯即将这一准则作过这样的表述:“一个行为是正确的,当且仅当,它是一个有美德的行为者在这种环境中将会采取的典型行为。”[注][新西兰]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美德伦理学》,李义天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54页。德性论关注的是行为者个人的德性,儒家仁性系统同样关心个人的德性,就此而言,二者有一定的相近性。但必须清楚看到,儒家仁性系统不仅讲德性,而且进一步强调这个德性不是空的,里面有丰富的内容,有具体的标准。这些内容和标准就是良心,就是本心,就是道德本体。求善必须从这个本体出发,否则一切都将沦为空谈。这些内容,德性论是不大关注的,至少不像儒家仁性系统这样重视。
综上所述,根据孔子仁的学说和孟子良心的学说,善的生活不是从制定和学习某些行为准则开始,而是从发现自己的内心开始的,通过内求找到自己的仁性是求善的第一步。仁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由仁性成就的善,本质上说即是对既有社会生活规则的服从。此前我曾撰文对伦理和道德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指出伦理偏重于人伦之理,指人际关系中既有的行为规范,道德则偏重于人与道的关系,指由道中所得的那个部分。[注]杨泽波:《三分法理论效应三则》,《复旦学报》2019年第5期。按照这种划分,这种遵从仁性而成的善即为伦理之善。
三、智性成就道德是另一种善
依据仁性行事,可以达成伦理之善,但这并不是善的全部。因为仁性是伦理心境,伦理心境来自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对内心的影响,所以由仁性而成的善只是对既有社会规范的服从,这一性质决定了其自身一定有其缺陷。
我在其他文章中对这个问题有过专门分析[注]杨泽波:《“存在先于本质”还是“本质先于存在”?——儒家生生伦理学对存在主义核心命题的批评》,《道德与文明》2018年第6期。,指出仁性隐含的缺陷首先表现为仁性失当。所谓仁性失当,是指仁性本身不够合理,其正确性有待讨论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主要是就狭义的伦理心境而言的。伦理心境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社会生活。如果社会生活没有问题,伦理心境一般而言也是健康的。但如果社会生活存在问题,作为其结晶物的伦理心境很可能也存在问题。仁性隐含的缺陷还表现为仁性保守。这里所说的保守首先是指社会习俗的保守,其次是指伦理心境的保守。伦理心境来自于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社会习俗。社会习俗尽管总体上与社会生活保持同步,但又有某种惰性的力量,一般又落后于社会生活。因为伦理心境要受到社会习俗的影响,而社会习俗本身有惰性的力量,所以伦理心境一般也跟不上社会生活的步伐。即使社会习俗完全可以与社会生活同步,作为其结晶物的伦理心境一经形成,同样具有一定的惰性,其变化发展一般又落后于社会习俗。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共同决定了,伦理心境从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包含了容易趋于保守的种子。除此之外,仁性隐含的缺陷更表现为仁性遮蔽。仁性遮蔽是我特别重视的一种现象,特指由于受到外部影响,仁性有所扭曲,产生变形,受到掩盖的一种情况。这种现象在当前情况下特别值得警惕。由于强大的国家机器可以运用舆论宣传自己的主张,受其影响,人们很容易被“洗脑”,使伦理心境发生变形,人像没有脑子一样,跟着别人做出错误的决定。如果社会环境恢复正常,仁性仍然可以发出光亮,但仁性遮蔽所造成的巨大危害,绝对不可小视。仁性失当、仁性保守、仁性遮蔽这些问题具体表现各有差异,但原因没有不同,都是对仁性缺乏真正的了解,这就是我说的“仁性无知”。仁性无知不是不能体验到仁性,而是指对仁性缺乏理论层面的真正了解。
由此可知,由仁性而成的伦理之善只是对既有社会行为规范的遵从,只是实然,还不是应然。如何从实然进至应然,是一个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既然仁性有这些不足,而其根源皆在仁性无知,依据三分法,要解决这些问题,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动用智性,对仁性来一个再认识。因此,求善不能只讲仁性,只满足于伦理,还必须再往前走一步,求助于智性。在儒家生生伦理学系统中,仁性与伦理相应,智性与道德相应,这种由智性决定的善即为道德之善。智性之所以可以成就道德,是因为它有认知的功能。智性既可以外识,了解社会发展和道德生活有关的道理,又可以内识,对伦理心境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外识和内识都不可缺,但内识更为重要。[注]杨泽波:《儒家生生伦理学中智性的双重功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这不仅是因为外识必须借道于内识,没有内识不可能有好的外识,更因为内识涉及对内心的观察,涉及对伦理心境的体悟,相对讲也更为困难和复杂。因此,智性在道德之善中担当的角色绝对不可或缺。换言之,以伦理心境为依据也可以成善,但它还不是人生的最终目的。要实现人生的最终目的,必须再上升一步,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启动智性对自己的道德根据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人为什么有仁性?仁性为什么会对人提出要求?这些要求是不是合理?一言以蔽之,我们不仅要知道仁性告知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更要知道仁性为什么要这样告知,其合理性在哪里。
这一思路通过康德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我们知道,康德建构其道德学说的进程较为特殊。康德注意到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种普通的伦理理性,这种伦理理性十分管用,即使不教给人们新东西,人们也知道如何去做。但非常可惜,这种普通伦理理性还有很多不足,容易出问题,特别是面对较为复杂的情况时容易不知所措,陷入“自然辩证法”,甚至将非道德的行为视为道德的。为此必须对其进行哲学反思,将其加以抽象提高,上升到哲学的层面,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将我们上面追求道德之善的思路,与康德从普通伦理理性中抉发道德法则的进程相比,不难看出,二者有一定的相似性:它们都尊重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的伦理理性,但又不满足于此,希望进一步将其抽象提升,使之上升到道德的层面,成为真正的哲学,真正的形上学。但儒家生生伦理学不是康德哲学的简单重复。康德的努力还较为含混,缺乏方法论的基础,以至于学界很长时间不大了解康德的致思路线,这种情况只是到了近些年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观[注]近年来,李明辉、邓安庆在这方面贡献尤多。详见李明辉:《康德伦理学与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4年版,第二章“道德思考中的隐默面向”,第四章“康德的道德思考”;邓安庆《启蒙伦理与现代社会的公序良俗——德国古典哲学的道德事业之重审》,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二章“康德哲学的实践哲学转向与启蒙伦理的义理阐明”。,儒家生生伦理学则直接将这一思路置于三分法的框架之内,分别与仁性和智性挂钩,不仅伦理和道德的划分有了更为扎实的根基,心学与理学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明朗起来,更易于理解和处理。
启动智性追求道德之善,需要有勇敢精神。在一般情况下,动用智性对仁性加以内识以达成道德之善后,伦理之善和道德之善,其表现形式可能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不随地吐痰还是不随地吐痰,不乱穿马路还是不乱马路,有序排队还是有序排队,但因为有了智性的加入,其性质已经有了本质性的变更,不再属于伦理,而是具有了道德的性质,成为了道德之善。但在特殊情况下,智性必须对仁性加以修正调整,此时需要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比如,“二战”时期,身处战争前线的日本侵略者,绝大多数受到战争宣传机器的影响,处于疯狂状态,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站出来,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思。这种人越多,战争对人类文明造成的损害就越小。但这种勇敢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些人很可能会因此牺牲自己的生命。又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大多数人跟着形势走,争当“造反派”,捍卫革命路线,做出疯狂举动,以为这样做就是革命行为的时候,同样需要有一些人站出来,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对这种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保持理智的头脑,甘当“保皇派”、“逍遥派”,甚至是“反动派”。这样的人越多,社会偏向错误方向的可能就越小。但这个时候能挺起脊梁的,只是极少数,也只有这极少数人才能成为民族的脊梁。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我们犯了那么多的错误,固然有政治方面的因素,但人们盲目崇拜,丢失自我,缺少独立思想与勇敢精神,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原因。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的力量远不如前,但它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信奉宗教的人,会按照自己宗教的教条行事。但信众很少能够对这些教条加以根本性的反思,只是因信称义,将其视为不可怀疑,不可动摇的真理。因为世界上有不同的宗教,这些宗教原本就存在着矛盾,有的还相当严重,一旦这些教条受到某些力量利用,必然发生冲突。这是文明冲突成为当今社会第一等问题的深层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有效的办法,便是动用智性对自己的宗教信仰来一个彻底的反思。一旦如此,我们就会明白,宗教只不过是一套极为精致诱人的说法而已。信众可以以信仰的方式相信它,但如果将其视为无可动摇,不能质疑的真理,就大错特错了。误将信仰当作真理,信仰与真理严重错位,是造成当今文明冲突的重要原因。要化解文明冲突,必须首先了解和接受这个道理,有英雄人物挺身站出来,对自己的信仰系统加以再认识,以至于对其进行变革,否则以宗教矛盾为中枢的文明冲突没有破解的任何希望。
启动智性追求道德之善,还需要谨慎态度。一方面,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十分复杂,常常会出现一些矛盾的局面,即使启动了智性,也很难一下子给出一个明确的、大家都认可的答案。伦理学界常常争议的一些两难选择,都属于这种情况。另一方面,更为复杂的是,如果动用智性发现仁性有缺陷从而必须对其加以调整的话,很可能会破坏原有的道德规范。这种调整是否合理,能否有好的社会效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简单启动智性就可以万事大吉的。如果考虑不周,随意而行,很可能给社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这时儒家经权智慧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在儒学历史上,成功运用经权的案例很多。《孟子》中的两则材料特别有代表性。一是“援之以手”: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注]《孟子·离娄上》第十七章。
按照礼的规定,男女相接,手不可相互接触。但如果嫂嫂掉到水里了,也可以伸手相救,否则便是豺狼之道。男女授受不亲为经,嫂嫂落水伸手相援是权。
二是“不告而娶”:
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万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则吾既得闻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注]《孟子·万章上》第二章。
按照礼的要求,娶妻必须禀告父母,但是舜的父母不好,如果禀告了,就不能娶妻,不娶妻则没有后代,废人之大伦,所以舜可以“不告而娶”。娶妻必告父母是经,舜不告而娶是权。
《孟子》中的这两则材料说明儒家对于行权有严格的要求,不仅要求必须出于好的动机,而且必须充分考虑到行动的后果。以这两个案例来说,“援之以手”不是出于邪恶之意,而是救人之命,“不告而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利欲,而是不废人之大伦。为了更好地学习儒家经权智慧,我认为需要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这就是“第二良心”。儒家生生伦理学将良心分为两种,即:“第一良心”和“第二良心”。前者是在孟子意义上使用的。孟子所说的良心是天生的,不学而能,不虑而知。后者不是天生的,特指行为者运用智性能力,做出选择时的善良意志,包含好的动机和充分考虑后果这两项具体内容。虽然“第二良心”与“第一良心”性质不同,但二者并非完全没有关系。“第二良心”来源于“第一良心”,因为人的行权之所以有好的动机并充分考虑其后果,是受“第一良心”影响的结果。没有“第一良心”,单靠智性无法做到这一点,智性本身是不能决定方向的。
儒家生生伦理学重提古老的经权智慧,强调“第二良心”的重要,意在告诉人们,在追求道德之善的过程中,不仅要有勇敢精神,同样要有谨慎态度。勇敢精神和谨慎态度是一物之两面。勇敢精神是说一旦发现仁性蕴含着不足,容易流向弊端,必须加以调整,这种做法在特殊情况下有很大的风险,必须有自我牺牲的精神。谨慎态度是说在启动智性的过程中,不能胆大妄为,要有一种敬畏的心态,战战兢兢,如覆薄冰,时刻想到智性选择也可能出问题,为社会带来不好的影响。我将二者区分开来,特别凸显后一个方面之重要,意在说明,这很可能是现代社会出现重重混乱的重要原因。充分看到智性的局限,懂得必须慎用智性,是一门必须补上的哲学必修课。
四、仁性之伦理与智性之道德的统一是完满之善
前面分别谈了伦理之善和道德之善,这种区分的根据全在仁性与智性的不同。伦理之善的基础是仁性。仁性是伦理心境,来自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和智性思维的内化。伦理心境一经形成便存于内心,处于隐默状态,遇事又会表现自己,告诉人们如何去做。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听从它的要求,就可以完成具体的善行。因此,伦理之善是遵从社会既有规范的善。儒家心学一系的意义全在于此。但仁性并不足够,因为仁性自身也有缺陷,如果对其缺乏真正的认识,很可能出现失当、保守,甚至遮蔽的问题,为各种弊端所困。因此,不能止步于伦理,还需要进一步将其发展为道德,追求道德之善。道德之善的基础是智性。智性虽然不能离开仁性,但不满足于此,要求对其加以再认识,检查其来源,考察其性质,分辨其特点,直至在特殊情况下对其加以调整改动。由此达成的即是道德之善。因此,道德之善是通过智性对仁性再认识后,运用自由意志自觉选择的善。伦理之善和道德之善不可能完全分开。善的生活,当始于伦理,止于道德。将伦理与道德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够成为完满之善。
将善划分为伦理之善和道德之善,有助于对海德格尔关于追求“本真”存在的思想做出新的说明。“本真”存在是海德格尔追求的目标,这本身没有问题,但他没有三分法,没有把伦理和道德区分开来,思想并不完备。儒家生生伦理学不同,在这个新的系统中,仁性属于伦理,本质上属于“常人”的范畴。“常人”虽然不是“本真”的存在,但自身也有价值,对此首先应该抱敬畏的态度。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很多问题,不是“常人”有失本真,而是“常人”没有做好,没有达到“常人”的高度。当然,“常人”毕竟不是人生最终的目的,还必须启用智性,对仁性进行再认识,乃至于必要时对其加以调整和改动,从“常人”态度中超脱出来,追求“本真”的存在,将伦理上升到道德。这一步工作并非一般想象的那般简单,只要善于筹划,勇于决断,就可以万事大吉了。由伦理上升到道德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必须十分慎重。如果智性不受任何限制,胆大妄为,随意而行,表面看是追求“本真”的存在,很可能是行一己之利,逞一时之快,实际得到的很可能是另一种形态的“假我”甚至“俗我”,给社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至此,我们便可以对何为善这个古老的话题做出我们的回答了。善的生活需要对物欲有一个基本的肯定。人要活得有意义,首先要保证能够在物质层面上生存。没有物质层面的生存,道德难免成为一句空话。在现实生活中,善起始于仁性。人自来到世间便具有一种生长倾向,更为重要的是,人作为在世的存在,一定会受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的影响,这就决定了社会生活一般的道德标准作为一种结晶物早就保留在了内心,这就是仁性。有了仁性就有了是非的标准,遵循这种标准,不受小体物欲的干扰,就达成了伦理之善。但这还只是“常人”之善,只是实然,还要进一步追求道德之善。道德之善的要点是运用智性对仁性加以再认识。通过这种再认识,不仅可以对仁性有充分的了解,不再陷入仁性无知之中,避免失当、保守、遮蔽等问题,更可以发现仁性本身的不合理之处,主动进行调整甚至改造,使其归为合理。总之,伦理归属于仁性;道德归属于智性。伦理是实然,是“常人”之善,是合于人伦之理的善;道德是应然,是“本真”的善,是得于道的善。心学属于伦理,经过诠释的理学属于道德。伦理是有缺陷的、未完成的道德;道德是没有缺陷的、完善的伦理。求善必须兼顾这两个方面,次第而行,以仁性之伦理之善为起点,不断前行,直至智性之道德之善而后止。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