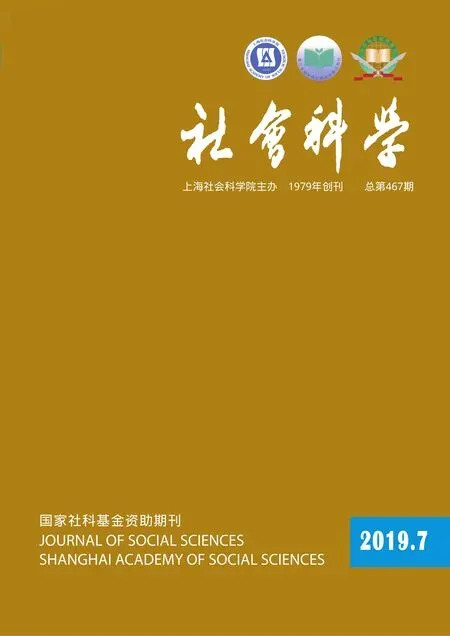农民、政府与环境资源的利用*
——明清时期下河地区的农民生计与淮扬水利工程的维护
肖启荣
一、洪泽湖水的分泄与下河地区的水环境景观
自明嘉靖以来,淮扬地区成为洪泽湖分泄入海的走廊,深刻影响着该地区水资源环境的变化,如何维持该地区农民的生计成为官民面对的问题。因国家水利工程的格局以及具体的地理环境与资源,官府通过政策的调整、民众通过对资源的利用,农民的生计格局得以形成。
自明嘉靖时始至万历初,山阳、宝应、高邮、江都四州县境内运河东堤上兴建了众多的减水闸坝,万历二十三年确定分黄导淮的方针之后,又有陆续的增建[注](明)胡应恩:《淮南水利考》卷下,载《中华山水志丛刊·水志》第24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544-545页。。康熙十六年,靳辅主持治河,集中于高邮城南分水,是为归海五坝[注]《行水金鉴》卷一三五《运河水》,“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总河靳辅题奏高宝兴盐等七州县”条,载《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第8册,第4573页。。这些闸坝下各有引河,分水东流入射阳湖荡区,调节湖水与运河水的水位,排泄洪水,灌溉田地,直至清末,基本的格局未有实质性的改变。
山阳、宝应运河东堤上减水坝下的次级河道总体而言,大多顺直,又因为射阳湖距离各州县运堤的距离以及水环境的差异,而有所差异。山阳县东南乡自北而南较大的河道有渔滨河、市河、涧河、南溪河、北溪河、泾河,射阳湖在县治东南七十里[注]同治《山阳县志》卷三《水利·东南乡水道》,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5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5-53页。,换言之,这些河道的大体长度约七十里。宝应县境内射阳湖距离县治六十里,但射阳湖以西有黄昏(县东七里)、火盆(县东三十五里)、獐狮(县东南四十里)、关车(县东四十里)、蚬虚(县东北四十五里)诸荡,运河东堤分下的河道先流入这些小荡,然后再流入射阳湖,河道被分成了两个部分,里程较短,约为山阳县境内河道里程的一半[注]康熙《宝应县志》卷一,“山川”,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高邮县境内运河东堤下分流河道的归宿,以县治为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部分:县治以北的河道流入洋马、时家、秦家荡,入盐城县大纵湖,县治以南的流入泰州蚌蜒河以及兴化县西车路河。洋马荡在州治东北十五里,时家、秦家二荡位于州治东北四十五里,此外尚有秦家、鱼池網、沙母、草荡,与之相连,换言之,州境东北十五至四十五里的范围内为荡区,故而治北运河东堤下的分流河道里程在十五至四十五里之间。治南的水系总体分为运盐河与澄子河两个水系,承受来自归海五坝分下的高邮湖涨水,流入兴化县境[注]嘉庆《高邮州志》卷二,“下河”,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4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125页。。
总之,山阳、宝应、高邮三县境内运堤以东射阳湖荡区以西的河道顺直,里程较短,相对而言治理较易。
荡区以东的河道格局与荡区以西截然不同。宝应、高邮运河东堤上的分水会潴于兴化县与盐城县西境,同时因为地势南高北低,南部江都县境内运盐河北部的分流河道、泰兴、泰州境内的水也流入兴化西部荡区,兴化西部形成广阔的湖荡,是为潴水之区。诸水在此经诸河道分流入海,出现了经、纬之别,“经河”自西向东,“纬河”自南而北,导水从两个方向分流,一通过盐城县境内的西塘河、东塘河,北向盐城县西北的喻口、东向盐城县城东南的石口,分流入海;一是经兴化县境,注入串场河入海[注]康熙《兴化县志》卷二《水利》,“来水”、“去水”,载《泰州文献》第一辑,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382-383页。。民国《兴化县志》卷一《舆地志》“兴化县境全图图说”论曰:
兴邑地势控扼西南,展伸东北,地平土沃,陆少水多,县城适当上河来源汇处,四面环水,经纬河道于此分流。计经河除蚌蜒、兴盐界河与东盐公共,外有梓辛、车路、白涂、海沟各河,纬河除海陵溪与高邮公共,外有南北官河、东西唐港、横泾、串场各河,其经河均注入串场河分下各闸,经由境内海港及邻境新洋、射阳各港归海[注]民国三十二年铅印本。。
自乾隆初年始,由于清口淤垫,洪泽湖水排入下河地区日益频繁,为防御坝水的需要,盐城、兴化、宝应、高邮境内湖荡区圩田迅速兴起[注]民国《宝应县志》卷四《食货志上·田赋》,第57页。,湖荡边的圩堤将圩田与湖荡区隔离开来,湖荡区成为相对独立的空间[注]四州县境内依然存在广大的湖荡区域,射阳湖荡区面积广阔的局面一直持续至建国后。参见罗健、张维新《宝应县湖泊湖荡保护管理工作的调查与思考》,《江苏水利》2012年第7期。。盐城县圩田始筑于康熙年间[注]雍正十年,政府在对盐城县的田地的清丈中,以庄名作圩名,将通县田地计折归圩,用以正疆界,征赋税,说明盐城县筑圩至少始于康熙年间。参见乾隆《盐城县志》卷三《城池·坊都》,乾隆十二年刻本。,乾隆八年在知县黄垣的主持下得以大力的修筑[注]乾隆《淮安府志》卷八《水利》“盐城县圩岸志叙”,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69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84页。。至清末,由于天妃正、越闸的修筑,淡水区域遂往北延伸至射阳河沿岸,县西湖荡始逐年淤淀,被开垦成稻田,但未修筑圩田,至民国初年,盐城县的圩田区域限于东塘河、西塘河以东区域[注]参阅光绪《盐城县志》卷首,“盐城县水道堤圩分图”,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5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2页。。兴化县圩田始筑于乾隆十八、九年间,位于东北的兴盐界河以南、唐港河以东、范公堤以西区域[注]关于兴化县筑圩情形见咸丰《兴化县志》卷二《河渠一》,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48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其分布可参阅民国《兴化县志》卷一《舆地志·兴化县全境图》。。宝应县圩田始筑于嘉庆年间,位于大纵湖沿岸[注]关于宝应县筑圩情形见民国《宝应县志》卷三《水利》,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4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民国《三续高邮州志》卷一,“圩岸”,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4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73、275、276页。。高邮州圩田亦始筑于嘉庆年间,自道光以迄光绪年间大力修筑,侵占湖荡[注]民国《三续高邮州志》卷一《河渠志·圩岸》,第270-277页。。因为湖荡区为受水之区,为防御坝水泛涨,滨临湖荡区的田地需修筑堤防,是为“荡圩”。乾隆八年,盐城知县黄垣维修盐城县圩岸,有河圩、里圩与荡圩三种,河圩防大河之水,裹圩,防支河别涧,荡圩则防大纵、九里、马鞍诸湖荡水,其中“荡圩长二万二千三百四十七丈二尺,计一百五十一里零”[注]乾隆《淮安府志》卷八《水利》“盐城县圩岸志叙”,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69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84页。。山阳县马家荡沿岸修筑了横堤,明显是为防御马家荡水的侵袭[注]同治《山阳县志》卷首,“图”,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5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宝应县“东乡地旷而卑,半邻湖荡,坝水泛涨,胥付波臣。”
综上所述,自明代至乾隆时期,淮扬地区的农业格局为运西湖区、运东湖荡以西区域以及湖荡区。嘉庆以来由于湖荡沿岸圩田普遍兴筑,湖荡区虽呈缩小的趋势,但是仍面积广阔,并成为一个独立的区域。因此淮扬地区农民的生计格局大体为:运西湖区渔业区、运河沿岸稻作区、湖荡混合农业区。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官府与农民是如何分别利用区域内的自然资源,维持行政运转与生计,从而揭示淮扬运河的维护与里下河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相互影响的一个侧面。
二、稻田区
运东运河堤沿岸是较优良的稻田区域。明人胡应恩即言淮扬运河“堤之东皆民腴田”[注]淮南水利考》卷下,“樊梁湖”条,第540页。,乾隆七年,漕运总督顾琮说到:“窃见淮安南北地之高下,本相等,乃田价悬绝,至有相去仅数十里,如淮南泾河上田,每亩值银十余两,淮北下地一顷,仅值银七八两者。考其所由,淮南河堤多建涵洞,灌注有资,故堤外之田悉成上腴。”[注]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一一一,顾琮《请广淮北水利疏》,乾隆七年,道光七年刻本。这里的“上腴”之田显然是稻田。高邮州农民以种植水稻为主业,水稻是主要的商品,水稻的种植规模从碾业为境内主要商业的状况可想见:“本地商业以碾坊为大宗,查乾隆时碾饷册名凡三千余户,殷盛实可想见。道光、咸丰以来下河多受水灾,湖西又遭兵燹,碾业逐渐衰歇,光绪中通计城乡碾坊不过一百数十户,碾米除土销外,但坐待外客来贩,遇大吏命办粮糙或军需,则喜出望外,终不能自行运米出售各埠,此销路之所以不广也。”[注]民国《三续高邮州志》卷一,“实业志·营业状况”,第302页。
之所以如此,是得益于运河的灌溉以及河道的自然状况。由于运堤以东湖荡以西区域河道里程较短,较易治理,加之地势较高,紧临运河,灌溉、防洪条件较之其余地区为佳。宝应县沿运庄镇田地因地势较高,无旱涝忧:“城北门曰松原、松岗,土城在焉,田兼高下平陂。又北曰龙首村,田膏腴无旱涝忧。东北曰殷家庄、黄塍沟,台墟庄附焉,地高壤沃,种松朱桃杏畅茂,岁旱虑水。又南曰槐楼,曰瓦甸,曰汜水,曰扛桥,至界首镇,沿堤之田无旱涝忧,如龙育村,罹水患时,田没于水者或十且八九,沿堤存小田一千余顷,又售于淮人者半[注]康熙《宝应县志》卷二《建置·庄镇》。。“山阳“水道原本闸洞,方运河畅流时,东南稻田数千顷咸资其利,号称膏腴”[注]同治《山阳县志》卷三《水利》,第59页。。高邮州境内运堤以东稻田的优劣则明显分为荡区以东、以西两个区域:“农产以稻为大宗,东乡地势低洼,止收早稻一熟,麦豆俱少。南乡土脉腴润,所产糯稻独多,麦及山药、萝葡亦颇发达。沿运河东堤一带产稻既佳,兼产慈菇、荸荠,获利尤厚。”[注]民国《三续高邮州志》卷一,“实业志·物产”,第298页。其关键在于荡区以东的稻田灌溉藉运河水,而荡区以东则藉荡水:“民田在运河东者曰一万七千余顷,以诸闸洞左近为上腴,其次距闸洞稍远而曲港支河递相灌输,最东则藉诸荡水反灌之,亦能有秋。大抵河东地分六总,一、五两总地面稍高,二、六两总次之,四、七两总最低,沟洫通利,惟遇开坝则一片汪洋,沉垫屡月,盖享水利大者受水害亦大也。”[注]民国《三续高邮州志》卷一,“实业志·营业状况”,第300页。
荡区以东的形势则有所差异。首先,田地地势不平,杂以旱作,水稻一熟制与二熟制杂存。光绪《淮安府志》卷二《疆域·物产》曰:“其物产则山阳东南乡与盐城、阜宁多稻田,兼莳豆麦。”阜宁县“东乡大半为稻作,一熟制,西南乡为两熟制”[注]民国《阜宁县新志》卷一二《农业志·农作》,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6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页。。兴化县“皆水田,止宜种稻,近场高旱始种麦、豆,不过十之一二”[注]咸丰《兴化县志》卷三《食货志·物产》,第109页。。从农民的角度来讲,水乡种植稻米的经济价值相对较高,稻田一熟制的收益又高于二熟制:“农家除支赋税工资整地施肥各费约计每亩所得,一熟制之稻田平均为六斛,纯收益二元余,两熟制之稻田平均为四斛,纯收益一元余,麦平均为三斛,纯收益一元余。大豆平均为五斛,纯收益二元余,蜀黍平均为四斛,纯收益不及一元,玉蜀黍平均为四斛,纯收益二元。余甘蔗平均为十余担,纯收益五元,花生平均为十六斛,纯收益三元,棉花连子平均为四十斤,纯收益二元余,此后逐渐改良,获益倍徙,可断言也。”[注]民国《阜宁县新志》卷一二《农业志·农作》,第233-234页。稻麦迭作,由于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与肥料,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收获打了折扣,也限制了种植面积:“低田艺稻,秋禾既登,渥水频耕,泥深没踝,力倍于粪。高田稻麦迭莳,一岁再获而劳倍,粪勤不能多种。”[注]民国《续修盐城县志》卷四《产殖志·农垦》,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5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08页。
其次,稻作以及旱作物的生产,受土质的影响,产量均不高。民国二十四年国民政府土地调查员何新铭赴盐城调查,认为盐城农民勤劳生产而不敷应用的主要原因是土质瘠薄:
细考此间农家颇为简朴而耐劳,其体力之强健,男女如一。但劳苦终年,而仍不敷应用者,实因土质瘠薄,生产不足。即如最好之质,每年只能种稻一次,及或麦一次,或棉或豆各一次,施肥虽多,产量亦少,又无山林果木蔬菜等副产以助之,而人烟又多,地不敷用,加以苛杂高利等之层层剥削,欲求倖逃,不可能也。[注]何新铭《盐城实习调查日记》,载萧铮主编《中国地政研究所丛刊·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01册,(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77年版,第53161-53162页。
又引用盐城人葛树滋所著《兴农芻献》,以合陇堤为例,分析了盐城农民的生产与生活状况:
编者身居盐邑第八区合陇堤,对于本区风土人情知之谂而言之易,无须舍近远求。择其优者如永和乡以言之。永和乡属在合陇堤之上游,水肥土腴,为全堤冠。居户四百七十五家,(在米併乡前)男女老幼一千八百三十五口,相率务农,绝少副业。有田五千一百亩,以人口支配,每人应有耕地三亩弱,平均每家约有田十亩。物产以稻为大宗,麦次之。产量每亩以二百五十斤计,共收一百二十七万五千斤。每百斤化米四斗,共有米五千一百五石。若以人生衣食日用之所需,从俭计算,极低限度,每人每日需米不能少于一升,统而计之,全年每人需米三石六斗,全乡需米六千六百余石,则超出此收获量一千五百余石。而赋税亩捐种种垭本,农具、庐舍以及冠婚丧祭,一切人事应酬等项,尚不在内。若再通盘合计,其不敷之数尤足惊人,当在三四万元之谱。[注]《盐城实习调查日记》,第53164-53165页。
总之,运堤以东、荡区以西区域是较优良的稻田区域,稻作占据绝对的地位。荡区以东的区域,也以稻作为主,同时种植豆、麦等旱作农作物,不如运堤以东沿岸区域单一,同时由于土质的影响,产量也不高。
三、湖荡区
湖荡区水体区域广大,陆地区域相对较少,生活在湖荡区的农民,依据资源的自然状态,来安排生计的方式,呈现出混合农业的景观。
兴化县境水域广阔,明嘉靖时期号称“三湖六十荡”,湖荡区湖田、藕池、渔业、草场交错共存[注]万历《兴化县新志》卷三《人事之纪·地亩》,载《泰州文献》第一辑,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152页。。宝应县獐狮荡、广洋湖、火盆荡诸荡中心区域采取稻、渔、藕混合的生业方式,其比重根据具体环境而定:
又东曰獐狮荡、朱斗庄、贾家林、陶家林、苗家林,扬舲沟附焉,罹水患时无高下,近远皆水,水涸,高者艺稻,下者莳藕,渔庄蟹舍相望。
又东接广洋湖,环湖而庄者曰乔垛,曰白鼠,曰东西决溪,曰南北鹤儿湾,曰兰亭,曰廖徐庄,形势与獐狮荡等。
又东折而北,曰蛤拖沟,曰火盆荡,曰沙子头,曰甄家庄,曰蚬虚,曰金吾庄,皆水田,岁旱不涸,民艺稻者什三,捕鱼者什七,夏藕花红数十里。
由界首折而东北曰相家荒,曰羊天庄,达于柘沟,郭家庄、赵家庄附焉,罹水患时,田没于水,今涸,高者耕种如旧。下者若小塘庄、逍遥港、鸭儿荡、邱家纲之属,荒草填咽,数十里无人烟。
又东曰潼沟寺,田渐辟,以邻荡水故,秋八月,野凫章鸡之属遮天动地以来,食稻殆尽。
又北门曰芦村胥家庄,蔡家庄、石家庄附焉,田高下如柘沟。[注]康熙《宝应县志》卷二《建置·庄镇》。
山阳县东南荡区与此类似:
东南汇为巨浸,沮洳弥望,有萑苇茭蒲之属,居民伐苇取鱼,待日而饱,或编苇作箔,织芦为藩,以食其业。[注]同治《山阳县志》卷一《疆域》,第23页。
盐城、阜宁县地势起伏甚大,作物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特征。湖荡以东较低区域多水田,濒临黄河故道以及串场河区域,地势较高,多沙田,除稻作、水产外,也有麦子以及适宜于沙田的花生、红薯,更为低洼之地则种植线麻、朽麻等农作物。盐城县 “东乡高燥,宜麦。西乡下泾,宜稻。高下适中,则稻麦皆宜。而农人大率以稻为重。……莲子、芡实之属不及南方者良,唯湖荡产蔆藕为多,利稍厚矣。……盐邑沙地种薯渐广,皮朱而味甘,汁多而筋少,较阜邑所产过之。……草之名不可枚举,唯蒲茭茅苇茂密于海滩湖荡之中,利或倍于树谷。……”[注]光绪《盐城县志》卷四《食货志·物产》,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5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阜宁知县安贞吉论述阜宁县低乡的种植结构曰:“黄浦四乡胶淤之地最低,而近水者植蒲芦,低而得水者插秧,不得水者种漫稻,种二麦、菜子。土沙两和之地,低洼者种麦,平坦者种杂禾是已。而线麻、朽麻宜洼地,水非漫顶,不致萎滥,植之而索绹,乘屋售绳铺,得善价利也。”[注]光绪《阜宁县志》卷一,“物产”,光绪十二年刻本,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数字方志。
湖荡区水资源丰富,农民从事捕鱼的环境支持度和资源便利程度较高,渔业在农村副业序列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有以之为主要生计的渔民。
兴化、盐城、阜宁海洋渔业与内河渔业共存,这里只讨论内河渔业。兴化县知县胡顺华曰:“本县之田除附郭坊厢二十里仅可种办外,其余东乡四十余里尽皆斥卤草场,维白手与人,莫敢承领,民以鱼虾为业,而生理之鲜少。”[注]万历《兴化县新志》卷三《人事之纪·地亩》,“兴化县知县胡顺华为恳乞轸念凋疲,府赐酌处加派军饷银两事”,第157页。至清初康熙年间进行赋役改革之前,兴化县河泊所存有四里,纳渔课钞七十二两余[注]万历《兴化县新志》卷三《人事之纪中·户口·所》,第178页。。渔民将鱼、虾、蟹进行干制、腌制处理后贩卖,规模较大,为此雍正年间,政府专门酌留盐斤,作腌制用:
国朝雍正十三年查淮南不销官引,州县酌留盐觔,兴化户口十二万七千零,连腌切每年酌留一百四十三万五千三百二十一觔,应于该县境之丁溪、小海等场酌留盐鱼、盐蛋。邑人腌鱼及鸭卵贩卖江南,络绎不绝。虾米、虾子,取其子就日曝干,经久不坏,味胜虾米。醉蟹,醉以酒,用瓶封固,经冬不变味。[注]咸丰《兴化县志》卷三《食货志·物产》,第109页。
盐城县“鳞介之属甚繁,而海错二日勝,大纵湖之蟹最为南人所重,春月水晶虾随甚美。……若鱼皮、鱼鳔、蛏干、虾米、腌卵、腌鱼、秫酒等物皆可贸迁远方”[注]光绪《盐城县志》卷四《食货志·物产》,第95页。。
阜宁县境的内河渔业,“由马家荡而下,直至射河尾闾,支流万派,水族繁滋,古所为鱼蟹之乡也,取鱼之器指不胜屈,渔人岁入亦无确实之统计。除射河流域外,南北两洋亦为产鱼地,邑人概称曰洋港。南洋即野潮洋,营渔业者按水面之大小岁纳鱼租(田主只收本息)。北洋流域(顺滩港、蛤蜊港、大財港、得胜港、大小双龙港、自然港均为渔区)属苇荡营官地,亦由居民岁纳水租,专营渔业。洋中之鱼均黑脊,味极肥美,业渔者以夏秋潦水为丰年之兆,冬季水涸取而腌之,畅销邻县”[注]民国《阜宁县新志》卷一二《农业志·畋渔》,第236-237页。。
湖荡区特有的植物也被利用开发,作为农民的副业。蒲茭茅苇的经济价值较高,“草之名不可枚举,唯蒲茭茅苇茂密于海滩湖荡之中,利或倍于树谷”[注]光绪《盐城县志》卷四《食货志·物产》,第94页。。蒲苇的使用在春、秋二季,春季可作蒲菜食用,秋后收割用以编制蒲包:“蒲苇丛生陂塘间,功省利溥。春初蒲菜堪饫宴飨,秋后取蒲茎编包,销路极广(盐场运盐多用之)。其賸遗琐碎则分别经纬,织缕待贾,鲜有弃材。”[注]民国《续纂山阳县志》卷一,“物产”,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5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14页。兴化县有编制蒲包、蒲席、芦席的特色庄镇:“蒲包,出中堡庄。蒲席,出城北篷垛。芦席,出西门外。”[注]咸丰《兴化县志》卷三《食货志·物产》,第109页。宝应县也产芦、茭、蒲,东乡荡田种植的南柴,可织折席[注]民国《宝应县志》卷一,《土产·草之属》,第18页。。阜宁县“羊寨镇北苏家庄居民业农之暇悉事蒲织,出品佳良,而尤以包为最,盛行扬属之十二圩等处,每年售数约达十余万,计价六七千元。其他产蒲之区,居民或织为席,或层而累之为蒲合,销途皆旺,达于丹徒、丹阳等县”[注]民国《阜宁县新志》卷一三《工业志·蒲织》,第238页。。而“沿射阳河两岸多柴尖、柴滩,产芦既广,故芦织品亦繁,篆河喻口姜家湾等处农户收藏以后,每织席折、芦花鞋、芦花毯之类,售数甚夥,而篆河多以女工织盐席,销售陈家港盐务公司,每年计数百万箝(六张为一箝),并南销兴化。樊川一带滨海之苇性绵而质厚,制为物,颇耐用,贫家妇女碾之为篾,作箩匾箕篮诸用具,货之于市,均农家副业也”[注]民国《阜宁县新志》卷一三《工业志·芦织》,第238页。。总之,蒲苇的利用在春、秋两季,具有季节性的特征,只能作为农民的副业。
生长于荡区的大蓝、小蓝,是制作染料靛青的材料,也是经济价值较高的植物,有专门的种植。兴化县境“靛,大蓝、小蓝,出城东各垛,浸汁为靛,虽不及建靛之佳,然远近数百里皆赴兴采买,其利甚溥”[注]咸丰《兴化县志》卷三《食货志·物产》,第109页。。盐城县“濒湖有靛,可以供染”。宝应县道光时期“货之属”即有大蓝、小蓝[注]道光《宝应县志》卷九,“土产”,载《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四○六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96页。,是重要的土产,民国年间仍旧如此:“大蓝、小蓝,二蓝俱产衡羡庄、观音寺镇,大蓝如菠,三刈始尽,色最娇。小蓝形如广三七,茎红叶圆,色较深,一刈即尽,均历久不变,他处仿种,弗若也。”[注]民国《宝应县志》卷一,“土产”,第18页。
如前所述,从农民的角度来说,稻米的种植价值较高,因而湖荡不断被开垦成稻田,进而在荡区形成村落。湖荡开垦成田地自明初已盛。嘉靖年间,兴化知县“尽将得胜等湖六十四荡湖心白水复行丈量,踏出湖田一百八十三顷九十六亩有奇”[注]万历《兴化县新志》卷三《人事之纪·地亩》,第152页。。康熙中前期以来,河工基本安澜,至乾隆年间,政府重视下河地区农田水利的维护[注]参见肖启荣《清代洪泽湖分泄与里下河平原防洪的实践过程研究(1644-1855)——黄运治理背后的国计民生》,《地方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荡区的开发速度加快,至嘉庆年间,由于清口淤淀,洪泽湖水下注频繁,荡区开垦的田地多以圩田的形式圈筑保护,湖荡区的圩田大规模兴起。
总之,稻作与渔业是湖荡区的两大主要耕作方式,同时,荡区特有的蒲苇、蓝草等植物资源,也被农民加以利用,成为主要的农村副业。稻、渔以及其余水产、蒲苇等水生植物的利用,大可维持农民的生计,如果整治下河水利的资金与人力以及随之而来缴纳的赋税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对农民来说是不划算的。康熙年间,河臣拟浚海口,以下河七州县田亩可以涸出耕种为由,请七州县以涸出田亩所征赋税为费用,即遭到七州县士绅的反对,理由是:“且夫役数十万之夫,糜二百七十八万之帑,弃民田庐坟墓无算,曰以救田也。然工未成,水中之田民田也,鱼可捕,菰蒲可采也,工既成,民之田河臣之田也。向之糜帑藏,弃庐墓,勤畚锸,以成万不可成之功者,今仍没其产而绝其食,民何利焉?”[注]潘耒:《翰林侍读乔君墓志》,载《皇朝经世文编》卷一一一。
四、运西湖区
运西湖区是广大、连绵的水域,宝应、高邮、甘泉渔业颇具规模,多职业渔民。宝应县明代渔民以渔船为单位缴纳麻胶、麻翎等项银,“每岁帮贴漕船之款”,由河泊所缴纳。清初河泊所裁,“改归民征民解,隶此籍者五百余家,谓之渔里户”。征解款项以户头一人主之。康熙后期至乾隆时期,弊端日征,改为官征官解,渔里户永不征银[注]民国《宝应县志》卷四《食货志上·田赋》,第64页。。民国时期渔业税收的情形如下:
河泊所出办麻胶银十九两五钱一厘,麻翎及水脚银一百一十五两一钱六分八厘,渔课钞银三十九两一钱七分一厘,共银一百七十三两八钱四分,随正加一耗羡银一十七两三钱八分四厘,遇閏加征银一十三两二钱四分二厘,随正加一耗羡银一两三钱二分四厘。[注]民国《宝应县志》卷四《食货志上·田赋》,第64页。
高邮州渔业上下河皆有,但以上河为主,“至若渔业,唯湖中植双帆操巨罟之纲船资本较厚,运堤以东业渔者不过田夫农隙藉以补助,或贫民讬破船以谋食,殊不足为轻重云”[注]民国《三续高邮州志》卷一,“实业志”,第300页。。关于具体之规模,民国《三续高邮州志》记之曰:“鱼行上下河皆有。查同治末年上河注册在官之行户凡五十余家,下河行户亦不少,但多半兼开他行,非专门名家耳。光绪以来湖水渐浅,出产逐渐减色,业亦稍衰延,至清末上河行户仅存二三十家而已。”[注]民国《三续高邮州志》卷一,“实业志·营业状况”,第302页。又曰:“民国八年渔业组织公会调查本县上下河渔行共九十二家,县署征收营业税,每行银币二元五角,共计二百三十元。大網船约百只,中網船约二百只,小钓船、鲜船约二千七百只,业户人口男女共计一万五千余名。地方另设局所编号,岁收旗照捐千余圆。”[注]民国《三续高邮州志》卷八,“实业”,第586页。
甘泉县境内北湖,“湖中人多业渔”,“各镇市设鱼肆,每晨诸渔以鱼集,牙侩平其价,贩者兑之,运于郡城及他所。其运鱼者行如飞,自湖至城远者六七十里,辰巳之时必至,谓之中鱼”[注]焦循《北湖小志》卷一,“叙渔第五”,载《中华山水志丛刊》第32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223、224页。。民国《甘泉县续志》曰:“北境内滨湖人习渔业,岁所产甚丰。”[注]民国《甘泉县续志》卷六《实业考·渔业》,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4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32页。从其捕鱼船只来看,应有较大的规模,与宝应、高邮大体相当:“其大者有三,一曰风兜,用大船蒲帆,双植大罟系船后,风浪大作时,鼓于湖心,往来如奔马,每度可得鱼数百斤。二曰泥网,亦用大船大罟,俟无风时围而猎焉,所得亦多。三曰羉,结绳为之,锐其末,沉水中,张口,当急流,每获亦可百余斤。”[注]《北湖小志》卷一,“叙渔第五”,第223-224页。焦循所列捕鱼之法大体十五,此三为最大者,应为前述高邮湖西渔业之“双帆操巨罟之纲船”,故而应为职业的渔民。
渔民以自然捕捞为主,并且互助合作。湖区渔民捕鱼船只大小不一,方式多样,除上列三种大船的捕捞方式外,尚有余下各种:
其次曰笼罩,一人以罟系植木五,置水中,一人以竹篙捣之,鱼惊而上窜,升其罟以受鱼,得鱼亚于羉。
曰旋网,一人立船头,两手敛而鱼包其中。
曰大索,以索布面,鱼之性,见索则不前,一人立船上,以罩沿索取之,每得大鱼。其下曰抹滩,两人持网端裸行水中,力牵而行其人,云水唯八月最寒,能于是月行水中,虽冰雪不畏也。
曰张卡,以线牵水面,用竹签锐其两端,屈曲环于线上,键以菱梗,诱以麦,鱼食麦,则口为签困,渔之巧者莫如此。所获多鲫,味最鲜。
曰张丫子,剖竹编如人字形,置浅水中,黄鳝、泥鳅入,无他鱼。或亦得蛇。
曰叉,以短竹置四刃矛于末,一人左右手各持一,沿湖滨或溪涧取之。
曰花篮,编竹如□状,梅雨时置围田中,诸鱼逆流而上,每旅入,不能出。
曰打避风,系一网于两船间,各用木系船作声,以迫鱼入。
曰跳白,用小船粉垩其板,月下行湖中,以诱鱼。曰张瓦,用两瓦合之,置柳根或茭草,中虎鲨以为巢,清晨举之,每瓦中可得双。
曰推板,湖浅时一人左手持长竿,竿端午以板推水中,右手持罩,鱼随板跃,以罩罩之。
曰哇船,养鸬鹚十余,以绳束其颈,放水中,得鱼不能咽,以手哇之,然臭恶,鱼味最下。[注]《北湖小志》卷一,“叙渔第五”,第224页。
上述捕鱼方式,应为湖区通行的捕鱼方式[注]民国《三续高邮州志》尽行抄录,第301-302页。。
湖滨之田地,大多种稻:
湖滨之田宜稻,居民多力农,其田自下下至上上,相去二三丈,为等六七。最下者为湖荡、草场,种菱,种茭草,或长龙古三稜,至旱之岁亦栽稻。次之为滩田,栽早色稻,拖犁归、四十子两种。再上为圩田,栽五十子。再上为高圩田,栽六十子及望江南。又上则为车田,又上为中车田,又上为高车田,俱栽大头栽秈。再上则岗田。岗田去水远,运水多费人力,每任其莱。车田者其水可随车而至也。[注]《北湖小志》卷一,“叙农第四”,第223页。
滨湖田地税收较轻,政府对于滨湖居民田地的维护也不甚着意,而是由民自行为之:“临湖滩地名为淌田,在前清时代虽值熟年,粮概免征,较高之区则分亦减,优加体恤,可为从宽。特明知其频遭水患,而视若罔闻,不为之设备筑圩,以保安全,是亦大失。”[注]《扬州水利图说》卷上,“近湖水利”,载《中华山水志丛刊·水志》第16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7页。因之,在水小的年份,即使稻子受淹无收,尚可倚赖小麦,而在水大之年,则只能“付之波臣”,民国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次大水,沿湖村庄“十不存一”[注]《扬州水利图说》卷上,“近湖水利”,第4页。。
五、地方税收及其对水利的影响
自明嘉靖时期始,政府开始征收湖荡税,同时清丈开垦的田地,予以升科征收赋税。嘉靖十七年,兴化知县傅佩丈量县境田地,将“三湖六十荡、草场、藕池、葑埂五千四百三十四顷五十三亩有奇,每亩岁纳银一分作为水面,以给师生俸廩”;嘉靖四十一年,知县程鸣伊“尽将得胜等湖六十四荡湖心白水复行丈量,踏出湖田一百八十三顷九十六亩有奇”[注]万历《兴化县新志》卷三《人事之纪·地亩》,第152页。。盐城县“前明原额田地八千三百五十二顷零,嘉靖间知县叶露新始将湖荡海滩丈量报部,增摊田额至三万五千七十二顷七十九亩一分三厘七毫。国初原额田地同此数”[注]光绪《盐城县志》卷四《食货·田赋》,第77页。。宝应县运堤东湖荡滩租称“新升河租”,“额征银一百三十六两九钱七分六厘,随正加一耗羡银一十三两六钱九分八厘”[注]民国《宝应县志》卷四《食货志上·田赋》,第63页。。
如前文所述,下河地区遭受水灾、田地大规模的被淹始自嘉靖年间,嘉靖年间的赋税田地数额应最高,清代的田地数额即以明代嘉靖年间为标准。康熙二十年以后,黄运大体得治,达到国家规定的税额明显是地方政府的行政责任之一。以地势最低洼之兴化、宝应、盐城为例。兴化县原额民灶田二万四千二百七十二顷[注]康熙《兴化县志》卷四,“田赋”,第421页。,康熙十一年,“止征熟涸田八百余顷”,康熙十二年最低,“止存涸田一百二顷”,“康熙十三年起积水未退,每岁止陆续开报涸出田地”,“康熙十六年涸田八百三十八顷零”,“康熙十七年涸田四千七百五十三顷零”,康熙十八年达到“四千八百八十顷”[注]康熙《兴化县志》卷四,“国朝蠲赈纪”,第435页。。宝应县原额官民田、牧马草场田、高邮卫归并屯田,通共折田二千四百五十二顷,“康熙七年至十九年间共九年大水,存熟田不抄过二百顷,二十年至二十四年间六百顷余,至二十八年始达一千七百余顷,占正赋的十分之八[注]康熙《宝应县志》卷五《土田》。。盐城县清初“田额三万五千七十二顷,十八年知县冯昱勘分盐邑无主永废田九千九百八十四顷有奇,并所屯田一百二十一顷有奇,田额废除约占阖县征收赋税田亩的1/3”,至康熙二十九年大旱,知县王赐璵混报全涸,致部议概令起征,民大困。知县武韟累详请豁。至三十二年巡抚宋荦、总督傅腊塔先后具题,仍格部议,旋奉特恩免征,民困始苏[注]光绪《盐城县志》卷四《食货·田赋》,第77-78页。。
从州县的层面来讲,稻田是稳定赋税的来源,这从地方志关于田地分布、赋税征收的记载得到证实。高邮州:“统计高邮田赋,丰年祗照额征得百分之八十八,其十二为湖西例灾,盖水利与水害俱轻,其农田在全境中不占重要位置也。”[注]民国《三续高邮州志》卷一,“实业志”,第300页。宝应“夙号水乡,地多低薄,大别有二,曰河东,曰河西。全县京田一千六百二十一顷有奇,河东八百八十四顷零,河西七百三十七顷零。河西居洪泽下游,环湖为田,叠罹水患,荒废者多。河东号称熟地,得全境十分之五而稍强。东乡地旷而卑,半邻湖荡,坝水泛涨,胥付波臣。河东二十四庄,只北乡三庄、南乡四庄田居上等,得东境十分之三而犹弱”[注]民国《宝应县志》卷四《食货志上·田赋》,第57页。。
稻田区的水利事业得到民间与地方官府的重视,运堤以东沿岸的稻田区域是着重关注的区域,从诸多方面表现出来。第一,是对运河堤岸上闸洞的修建与维护的重视。嘉庆《高邮州志》卷二,《增修·下河》论闸洞维护与河道疏浚的利害关系曰:“惟东北一路渐洼,而盐城海口迂远,宣洩不及,故邮邑向称釜底。然曩祗受运河小闸之水,无大汛滥,迨五坝既设,黄淮异涨入焉,而下河之害孔亟矣。抑从前运河未淤,涵洞以时启闭,下河尚通。近年运河浅狭,平时闭闸济运,下河已成叹地,一经开坝,黄水冲入,逐年淤垫,久不挑浚,则下河废,下河废,则蓄洩无资,农田奚望焉。”[注]嘉庆《高邮州志》卷二,“下河”,第116页。山阳县:“运河两岸各闸洞为各乡水道来源,而城内外河渠逼近,其通塞利害所系尤切。”[注]同治《山阳县志》卷三《水利》,第45页。闸洞对农田灌溉如此重要,遂为朝廷所利用,其维护全部交由民间。乾隆元年掌江南道事协理河南道监察御史臣常禄呈请运河两岸闸洞归官修,其论曰:
臣巡漕驻扎淮安,见运河两岸堤间有所谓涵洞者,询系民间设立,引河水以灌溉秧田,其洞直穿官堤,或木或石不等,共计十七座,向来听民修筑。小修每洞费银六七十两,大修每洞费银五六百两,皆民自己按田摊派,公举一人为洞头,具呈管河厅官协同胥吏估计监修,上有关于官堤,下有关于民田,所系甚重。迩年以来胥吏洞头勾通作弊,包揽承修,小修每洞勒银一百六七十两,大修每洞勒至一千余两,藉称有碍官堤,若不上下打点,决不能修。指派工料,强索使费,民不胜累。将来小民摊派维艰,一时虽修,不惟民田灌溉无资,且恐涵洞渐不坚好,官以为民所应修,民以为力不能修,其妨碍官堤正复不少。[注]《南河成案》卷三,《陈请淮安运河两岸闸洞归官修理部驳》,载《中华山水志丛刊·水志》第26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166页。
常禄巧妙的将闸洞的维护与运河堤防的维护联系起来,请求由国家负责运堤上闸洞的维护,但是朝廷驳回其建议,仍旧归民修理,只是让抚臣整治管理上的弊端[注]《南河成案》卷三,《陈请淮安运河两岸闸洞归官修理部驳》,第167页。。
第二,河道治理采取疏浚的方式,由官府组织,主要采取业食佃力的方式筹措资金。如山阳县市河与涧河。市河、涧河关系到淮安城的城市水利、交通与两岸田地的灌溉。自明中后期至康熙时期,漕督是河道维护中的主持者。康熙后期始,漕督淡出河道的管理,两河的治理由地方政府主持,经费开始来源于两岸的田业,一直持续至清末[注]肖启荣:《明清时期淮安城水道管理体制的变迁》,《历史地理》第3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8页。。其余河道的治理情形与此类似[注]同治《山阳县志》卷三《水利》“东南乡水道”,第45-54页。。高邮州田亩主要位于城北运盐河沿岸,也是高邮归海坝的排水河道,因此地方政府十分重视运盐河及其附属河道的维护,由知州负责挑浚事宜[注]乾隆《高邮州志》卷二,“下河”,乾隆刻本;嘉庆《高邮州志》卷二,《下河》,第123-124页。。
第三,在地方政府的鼓励下,清嘉庆年间圩田大规模修筑,使得湖荡区的开垦日趋达到高潮[注]各州县圩田的修筑情形见前文所述。。圩田修筑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生计,但是由于其对水域的侵占,对整体的农田水利也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尤以道光以来对高邮州的影响为最。圩田的修筑影响到洪水的排泄:“自来言高邮下河水利,专赖疏浚淤塞,而淤塞情形今昔不同。昔则水过沙停,积久渐窒,今则圩多河窄,无地可容,而支河僻港又多闭塞,甚有规占荡地,以为私田者。每遇启坝之年,昔时但惧不得达海,今后将忧不得达荡。且荡既成田,田复筑圩,是自受淤多而又添阻塞之病。”[注]道光《续增高邮州志》第二册《河渠志·下河》,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4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45页。圩田修筑与管理的缺失,也影响到圩田的收益:“光绪十四年臬使张富年亲勘下河,欲使无田不圩,遽兴大役,与水争地,绩用弗成,故邮境惟极东尚少圩岸,余则偏收之利,曲防之害,二者均不能免。”[注]民国《三续高邮州志》卷一《河渠志·圩岸》“支河修浚附”,第270页。但是赋税的征收显然排在了地方政府考量的首要位置,而且为节约行政成本,官府对于圩田修筑采取了放任与鼓励的态度,但是没有统一的规划与管理,高邮州志评论高邮州筑圩曰:“上河有堤,下河有圩,其用一也,然堤仅一面御水,圩宛在中央,则防守难。堤发官帑以修,圩敛民财以筑,则筹费难。且圩必有董官,择乡民充之,良懦或赔累以破家,桀黠又厚敛以肥己,则用人尤难,故圩小忧款项不足,圩大患心力不齐。或植基未固,或常年失修,一遇横流,沦胥以败。至若湖汊浅滩荡边荒垛频年垦熟,私筑小圩,官府但顾升科,并不禁其圈占。”[注]民国《三续高邮州志》卷一,“圩岸”,第277页。
第四,嘉庆以来,官府重视下河,轻视上河,开坝志椿水位偏向于以下河的安全为标准,运西湖区潴水不能及时排出,淹没村庄、尚未成熟的水稻,导致上下河的争端。据嘉庆《高邮州志》、光绪《高邮州志》关于归海五坝开放的记载统计,自嘉庆九年至道光六年,开坝时运河实际水位在1丈至1丈2尺之间,道光六年以后,实际水位约1丈5尺左右,咸丰以后涨至1丈5尺以上,光绪年间涨至1丈6尺以上,光绪后期达到1丈7尺左右[注]参见嘉庆《高邮州志》卷二《河渠》“运河五坝”,第138-139页;光绪《高邮州志》卷二《河渠志》“启坝定志·历年启坝附”,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4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1页;民国《续修兴化县志》卷二《河渠二·运堤闸座》,“附历年启坝尺寸表”,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48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49-450页。。又民国胡澍《扬州水利图说》论曰:
当年立有水志,水量达一丈六尺即开坝下洩,倘湖水不减,即继开二坝、三坝,上河庶可免患。乃自清同光以来,运堤逐渐增高,水位志椿亦逐渐增度,每高至一丈八九尺,坝仍不开,上河安能免患?盖下河近湖近荡之滩昔仅植菰蒲菱藕,较高之地则垦为田,此田惟栽早禾,秋前成熟收割,名为秋前五也。交秋开坝,禾已尽收,所谓淹田不淹稻,无损也。今则不然,早禾长养期短,收成较薄,晏稻长养期长,收成较厚,咸不栽早禾而栽晏稻,交秋不熟,坝若一开,则受淹。然不开坝,水少去路,湖西村庄多数陆沉。设风暴来,波涛震撼,不但庐舍不保,抑且生命难存,不得已请求开坝,官厅每以上河地面较少,下河地面较多,本此主意,明虽允开,仍迟延不启。[注]《扬州水利图说》卷一,“近湖水利”,第5页。
胡澍生长于江都,写作《扬州水利图说》时已经八十三岁,初稿成于民国三十三年[注]《扬州水利图说》卷上《序》、《目录》,第2页。,所述晚清扬州府之水利情形应较为真切。
总之,自明嘉靖年间始,政府开始征收湖荡以及开垦田地的赋税,各州县纳税田地的面积增长,清初采用了明嘉靖年间纳税田地的数额。地方政府采取维护河道、控制运堤减水坝的开启等措施,竭力维护稻田的面积,以获取稳定的税收来源。嘉庆时始,圩田大兴,侵占湖荡,对农田的排水与灌溉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运堤减水坝志椿标准的提高,使得运西湖区易受水灾,造成湖西与湖东的冲突与纷争。
余 论
佩里格林·霍登、尼古拉斯·珀塞尔在关于地中海区域个案的研究中指出:
历史学家必须按照分析环境资源如何满足人类需要的思路去审视各种地形构成的有机体系。……它需要密切关注各种限制生产活动的要素。……这样的限制因素——土壤、地形、气候、植被——为数众多,且难以克服。历史上人类对此作出的回应是极其巧妙和多样的,……生产者(要知道狭义的农业不过是多种地中海生产类型之一)用自己的“微观策略”去对付碎片化的环境。正是万花筒式的生产用地最终构成了编织世界表面的丝线;尽管自身由种种环境障碍多塑造,它却在区域划分——农田、泉水、小路、牧场、园地池塘或灌木丛——的专门性与精确性方面比地理环境本身更加细腻。[注][英]佩里格林·霍登、尼古拉斯·珀塞尔著:《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上),吕厚量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109页。
下河地区农民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以及地方政府在水利维护中表现出的对土地资源的态度,共同塑造了下河地区的农业与水利景观。
明中后期以来,在洪泽湖水分泄的影响下,下河地区的水利工程体系逐步形成,塑造出水资源景观的格局。下河地区的农民适应下河地区的环境与资源条件,形成了稻作、渔业与混合农业的生计方式。
运西湖区、运东稻田区、湖荡区农民的生计方式都呈现出多样与变动的特征,是农民为生存的需要,对环境适应的结果。农民依据具体的资源环境,选择生计方式,安排农事。诸如前文所述,高邮运东地区虽以稻米为主业,但是农民于闲暇之余也捕鱼,贫民甚至以之谋生。养殖业也是农民生计的补充:“河东水田便于养鸭,故每年输出者极多,唯产鸡不及湖西之肥大。阖境鸡鸭蛋甚多,为输出品之一。每年春夏本地炕坊炕出鸡鸭雏,运销江南各处。其蛋之双黄者尤为出产之特色。”[注]民国《三续高邮州志》卷一,“物产”,第298页。
农民的生计方式传统与地方行政也影响着环境的塑造。水乡低地稻作的便利与收益上的优势,使得运河湖荡区一直处于被开发成稻田的进程中,从而导致湖荡的萎缩。政府顺应了农民生计方式与环境的约束,将运东稻田的维护摆在水利维护的首要位置,以征收赋税,维持行政的运转。运堤的维护与下河腹里的水利工程均受其影响,影响着淮扬运河的景观与淮扬地区水利工程的维护。
——高邮博物馆精华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