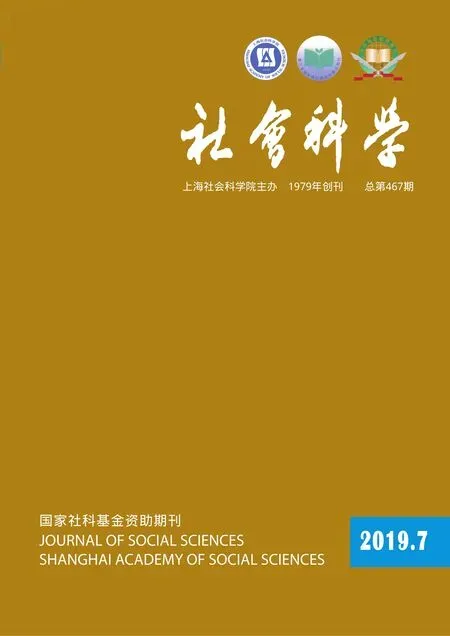“五四”文学研究的三个纬度*
——从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 (1917-1927)》部分导言说开去
王光东
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1917-1927)的文学理论和作品选集,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于1935年至1936年出版。全书共分十卷,由蔡元培作总序,编选人作每一卷的导言,胡适编《建设理论集》、郑振铎编《文学论争集》、茅盾编《小说一集》、鲁迅编《小说二集》、郑伯奇编《小说三集》、周作人编《散文一集》、郁达夫编《散文二集》、朱自清编《诗集》、洪深编《戏剧集》、阿英编《史料.索引》,这十位编选者都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直接参与者和推动者。本文重点分析的是胡适、周作人、茅盾、郑伯奇所写的导言,重读这些导言,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五四”与“西方”、“五四”与“传统”的关系以及“五四”文学的一些理论、观念对后来文学的影响等都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导言中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对今天文学研究的启示性价值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一 “文化传统”之于 “五四文学”
中国文化传统之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是复杂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反叛封建传统的过程中,对于传统文化又表现出热烈的肯定和创造性的转化,他们的这种双重态度,源于在传统文化的漫漫历史中,发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性力量。民族文化的发展一定是传承中的创造。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丰富的,先秦诸子、唐宋诗文、儒学经典、道家典籍……,丰富的文化传统在历史的进程中,沉淀为我们民族的精神和个性。“五四”作家在反对封建礼教法则对人性的压抑时,同时又在文化传统中寻找建构现代文化的资源,郭沫若对先秦文化中的孔子、老子给以热烈的赞美,周作人、胡适在新文学大系导言中,分别从传统文人创作和民间文学两个方面说明了新文化、新文学与传统的关系,为我们如何理解“传统”、发展传统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周作人在他撰写的“散文一集”导言中说:“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虽然在文学发达的程途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在理学与古文没有全盛的时候,抒情的散文也已得到相当的长发,不过在学士大夫眼中自然也不很看得起。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注]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版,第7页。显然周作人是把“五四”时期的现代散文看作是明清散文的一种复兴和转化,“现在的文学——现在只就散文说——与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注]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版,第8页。这种由古代转化而来的“新的传统”,同时又是传统的一部分,那么,是什么力量赋予传统新的因素呢?在周作人看来“即是西洋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注]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版,第10页。。由此看来,“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家在接受外来影响时,并不是否定传统,而是谋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郭沫若在他的《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论中德文化书》《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明阳》等文章中,也同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新文化建构的资源和力量。他认为不论是老子和孔子或他们之前的原始思想中,却能听到两种心音:“把一切的存在看做动的实在之表现!——把一切的事业由自我的完成出发!我们的这种传统精神——在万有皆神的想念之下,完成自己之净化与自己之充实以至于无限,伟大而慈爱如神,努力四海同胞与世界国家之实现的我们这种二而一的中国固有的传统精神,是要为我们将来的第二的时代之两片子叶的嫩苗而伸长起来的。”[注]郭沫若:《<文艺论集>汇校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郭沫若在传统中发现了自我实现和承担世界国家责任的现代精神,他对于传统文化的这种态度和周作人在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语中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意义,以谋求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那么,又该怎样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既肯定传统又反叛传统的双重态度呢?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社会历史发生转型和变化时,我们所面对“传统”往往呈现出它的“两面性”特征:一方面是不适应历史发展的滞后性;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与历史发展有意义的相关性。只有反叛这种“滞后性”,同时赋予相关性历史文化有意义的创造性力量,才能推动传统文化的更新,以适应新的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周作人等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人思想的发现,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具有了巨大的现代性价值。
胡适与此有所不同,它是在传统文化中“民间文化”这一纬度上寻找新文化、新文学的建设资源。“民间文化”与“文人文化”既相联系又有所区别,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中,曾把“文人的民间化”和“民间的文人化”看作是中国文学不断发展的两条路径,这两者有一个共同的指向——“民间”是文人创作的资源并赋予文学生命的力量。在他看来,文学变革的动力是与民间联系在一起的,依据这样的思路,新文学的产生也必然不能脱离与民间文化的联系,所以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认为:“中国白话文学的运动当然不完全是我们几个人闹出来的,……我们至少可以指出这些最重要的因子:第一是我们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作品,……第二是我们的老祖宗在两千年之中,渐渐的把一种大同小异的‘官话’推行到了全国的绝大部分……,第三是我们的海禁开了,和世界文化接触了,……使我们明了我们自己的国语文学的历史,使我们放胆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革命。”[注]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版,第15-16页。这个文学革命所延续的就是一千多年来白话文学,也就是民间的俗文学,胡适在“民间俗文学”的传统中找到了新文学发展的道路。刘半农与胡适持有相同的文学观念,刘半农认为:“中国内地的歌谣中,美的分子,在情意方面或在词句方面都还很丰富。”[注]刘半农:《刘半农书话》,陈子善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他不仅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把自己的诗学主张与民间文学相关联,而且还依赖江阴民歌创作了新诗《瓦釜集》。周作人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中说得更为明确:“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有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当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注]周作人:《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由上论述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早期的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的民间文化寄予了高度的热情。任何时代的文化都存在着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的区别,与下层民众密切关联并与他们的生活方式融为一起的民间文化,虽然浸透着主流文化的影响、体现着某个时代的价值观,但是这一民间文化传统由于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血肉相连,往往具有鲜活、生动、率真的生命活力,譬如民歌、民谣都是来自于下层民众真实的声音,它的艺术内容及其表达形式与已成规范的文人诗词相比较,具有更为强烈的创造性,这也正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创造新文学的过程中,极力张扬民间文学的重要原因。由此反思一下当下的文学创作,当代许多作家所缺少的正是向民间寻找资源的自觉意识。
我们面对的传统是复杂而又丰富的,传统文学的存在形态也是多元和多层次的,怎样发现“传统”并激活它使之成为新的文化形态的组成部分,是从“五四”直至今天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 “混合性”与异域文学的接受
“五四”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是“五四”文学研究中的又一个重要问题。一个民族和国家对异域文化的接受往往是与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相关的,自身的文化传统往往制约着接受外来文化的路径和内容。郑伯奇在《小说三集》导言中,用美国的心理学家史丹莱·霍尔的发生心理学理论,来解释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发生,认为“五四”文学在接受西方文学影响时具有“混合性”的特点,一个作家的创作可能同时受到多种西方文学思潮因素的影响,这一特点导致了“五四”文学构成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复杂性(这种“混合性”在“五四”文学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不同阶段都有所表现),这一特点也说明了中国文化传统具有包容性的胸怀和气魄以及吸纳外来文化的能力。重视这一特点,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一直与外国文学有着紧密的关联,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重视中国作家创作区别于其他国别作家的独特性;而且要充分的意识到“本土”文化传统如何制约异域文化的接受等问题。
霍尔认为:人类的进化是将以前已经通过了的进化过程反复一遍而后前进的,郑伯奇说:“若把这个臆说大胆的应用在文化史上面,我们也可以说,人类文化的进步,是将以前已经通过了的进化过程反复一番而后前进的,在文化落后的国家或民族,这种现象更为显著。”[注]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版,第1页。由此郑伯奇在回顾“五四”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时认为:“中国文学的进展,我们可以看出西欧二百年中的历史在这里很快地反复了一番。这不是说中国的新文学已经成长到和西欧各国同一的水准,落后的国家虽然急起直追也断不能一跃而跻于先进之列。尤其是文学艺术方面,精神遗产的微薄常常使后进国暴露出它的弱点。我们只想指出这短短十年中间,西欧两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地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来。”[注]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版,第2页。这一论述说明了西方文化、文学对于“五四”文学的影响不是单一的,而是混杂的,西方意义上的文学思潮和作品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正如茅盾在《小说一集》导言中说:“我们回顾第一个‘十年’的成果,也许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的‘新文学运动’的初期跟外国的有点不同?在我们这里,好像没有开过浪漫主义的花,也没有结写实主义的实。”[注]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版,第12页。这种现象的产生,当然与我们的文学传统、“五四”时期的历史现实、作家的审美理想等等问题有关,但与这种“混杂的影响”也是有关系的,郑伯奇在《小说三集》导言中认为:“所谓‘人生派’实接近帝俄时代的写实派,而所谓‘艺术派’实则包含着浪漫主义以至表现派未来派的各种倾向。这种倾向的混合并不是同时凑成的,这里自然有个先来后到,但这些倾向有个共同的地方所以能够杂居,确是不容否认的事。但这些倾向中比较长远,而最有势力的当然是浪漫主义了。”[注]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版,第3页。郑伯奇虽然指出了“人生派”与“艺术派”主要特征,但也看到了作家作品中所具有的“混合性”的特点,在创作社的这批作家中,特别是郁达夫和郭沫若的小说创作中,日本“私小说”的因素也是比较明显的。“五四”新文学创作所呈现出的这种“混合性”特点,启示我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要重视如下几个问题:1.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中国文学面对着与西方文学不同的文化传统、社会现实,也就不可能沿袭着西方文学的发展轨迹向前发展,这也就要求我们研究中国“五四”文学时,要重视中西文学不同的发展路径,这虽然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我们仍旧对于这种“差异性”重视不够,直接把一些“西方理论”照搬挪用,这种现象在新时期以来表现得更为突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与“五四”文学的“异域文学接受”有着很大的相似性,“混合性”也是其明显特征,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文学因素,同时杂糅在中国作家的创作中,因此简单地套用某种文化理论来分析中国文学,就会带来作品分析的隔膜感。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新文学大系”的导言,从文学现实出发,在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过程中,说明作家写作意义的研究方法仍旧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一种研究方法,这也就带来了我们需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2.所谓“本土化”不是简单的拒绝外来理论,而是一种思维方法的转变,也就是从“中国问题”出发去展开研究。曹锦清在《如何研究中国》中认为:“西方的理论和概念必须按照中国的语境加以语义学上的改造,通俗来讲就是中国化。如果这个过程不完成,用输入的西方理论直接套裁中国是要误读中国的。另外,把西方理论掩藏着的价值观念作为一个普世的价值观念我们也会犯错误,价值观念从来不是普世的。价值观念的来源只能是本民族内在的需求和当下实践的需求。”[注]曹锦清:《如何研究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中,我们可以看到导言作者大多都是以“中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问题,对西方理论的理解是融入中国问题的分析中的,因此鲁迅在充分肯定西方文学对“五四”作家的影响时,又深刻的提出了中国作家在“中国语境”中的独特性;胡适在“进化论”影响下形成了“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其目的是为了推倒旧文学,建立白话为一切文学工具的新文学观念;郑伯奇则从中国作家的历史境遇出发,分析他们接受外来影响的必要性及其差异。这种从本土出发分析问题的思维方法,是“五四”一代作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资源,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找到真实的自己和艺术的力量。
三 “社会性”作为文学的批评原则
新文学大系导言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文献,而且是文学批评的经典性文本。导言作者评价文学作品的原则不尽一致,具有浓重的个性化色彩,但对后来的文学研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鲁迅那种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不仅影响着文学史的发展,而且影响着知识分子的精神和灵魂。茅盾在小说一集的导言中,以表现“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作为评价作品的基本原则,对于今天的文学批评而言仍旧是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
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导言中,对于“五四”文学前半期创作提出了批评,认为有两个重大缺点,“这两个缺点,第一是几乎看不到全般的社会现象而只有个人生活的小小的一角,第二是观念化。”[注]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版,第10页。“大多数创作家对农村和城市劳动者的生活很疏远,对于全般的社会现象不注意,他们最感兴味的还是恋爱,而且个人主义的享乐的倾向也很显然。”[注]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版,第9页。“‘人物都是一个面目的,那些人物的思想是一个样的,举动是一个样的,到何种地步说何等话,也是一个样的’。这些恋爱小说内的主角大抵不是作家自己就是他的最熟悉的伴侣,可是一搬上纸面尚不免观念化,无怪那极少数的描写农村生活和城市劳动者生活的作品更其观念化得厉害!”[注]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版,第10页。文学创作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茅盾认为是“生活的偏枯”造成的,显然茅盾是从“文学表现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的角度来分析和评价“五四”前期的小说创作的。批评家对小说作品的评价可以有多样化的角度,这一时期的恋爱小说虽然有观念化的倾向,但从人的个性发展,反抗封建伦理法则的角度分析也有其时代价值,但是茅盾要求文学反映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文学意义的。茅盾秉持的是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原则,重视文学的“真实性和丰富性”,这一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事物总是有其两面性,当我们把“真实”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并且“绝对化”,就会带来对文学形式、技巧以及人与生活之间多样化审美关系的忽视,新时期个人化的“先锋主义”写作,在回归“文学本体”的过程中,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这一文学写作原则的反拨,但是当文学的个人化写作发展到一个阶段,呈现出疏离广阔的社会生活,成为个人的“小世界”的表达,生活以及由生活产生的意识日益狭窄时,文学与人,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多样化、丰富性的审美关系就会再一次变得简单化、观念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特别重视茅盾在导言中提出的,“生活的偏枯”会带来“文学的偏枯”的观点,由此对今天的文学创作有所思考。
新世纪以来,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中国当代城乡关系的巨大变化所带来的社会现实的变化,已经深刻的影响并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观念。伴随着这种变化,出现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也以“史诗”性的品格与这个时代建立了深厚的审美关系,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当下小说创作中存在的“生活偏枯”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呈现在如下两类小说的创作中:一是网络小说写作,一是部分青年小说家的“纯文学”写作。网络小说与纸媒小说相比较而言,它有着不同于纸媒小说的生产方式,在文化资本的操纵下,市场化的影响以及对读者阅读消费的期待,使网络小说更关心阅读者的趣味和阅读量,因此可读性、通俗性成为其主要的特点,而支持这种可读性的是男欢女爱、类似于武侠小说的人的超能力的夸张叙述、或者是黑幕、猎奇的感官刺激……如此以来,我们很难在网络小说中看到对现实生活的严肃思考,社会关系中“人的情感与生活”的丰富性被所谓的虚拟想象简单化,生活或者说人们普遍“感知的社会生活”在网络小说中的呈现是不够的。这类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消遣,只要无害也自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从文学理应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来要求这些作品,这些缺乏鲜活、生动生活经验和社会深度的作品是难以有真正的艺术价值的。对于部分青年作家而言,“生活偏枯”也是当下值得重视的问题,特别是那些正在学校读书或者刚刚走出校门的青年作家,其作品题材的狭窄和处理题材的能力的贫弱,和茅盾批评“五四”前半期创作时提出的问题是一样的:“第一是几乎是看不到全般的社会现象而只有个人生活的小小的一角,第二是观念化。”[注]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版,第10页。“五四”前半期的小说创作存在的问题与当下部分青年作家存在的问题是如此的相似,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茅盾在导言中的一段话,对于今天的作家而言仍然是有意义的,茅盾说:“怎样克服这些缺点呢?许多人的见解并不一样。从当时的青年群内(包括了青年的作者和读者)发出来的最普遍的呼声只是很干脆的一句话:让他自由发展就好了!(《小说月报》十三卷各期的通讯栏内就记录着一部分这样的现象)。但是,空空洞洞的一句‘让他自由发展’显然不是当时实际所需要。十二卷七号的《小说月报》有特别的一栏——‘创作讨论’,企图把这问题更具体的研究一下。参加讨论的,共有九位,在现今看来,其中有一位署名说难的《我对于创作家的希望》最为切实了。(这位说难,记起来好像就是胡愈之)。他这篇文章指出了作家们除‘感情的锻炼修正和艺术力的涵养以外,实际社会是不能不投身观察的。文学(广义)中之文法语法方面,是不能不分心研究的。旧来之语体小说,是不能不参考的。新闻纸第三面的纪事,是不能不多看的。而且街谈巷议和许多外行人的议论,也是不能不虚心听受的’。可是当时青年的创作家或有志于创作的青年却不耐烦下那样的水磨功夫。”[注]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版,第10-11页。茅盾这段对“五四”前半期青年创作家的评价和分析,同样应该引起今天的青年作家的深思。
四 结 语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十个导言所包含的理论思想、研究方法以及理解文学史的观念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影响是深远的,大部分导言体现出的文学史观是“进化的历史文学观”,他们对于新文学的理解和认识都与这一文学史观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一文学史观在今天应该怎样理解呢? 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中,蔡元培写的总序,郑伯奇胡适等人写的序导言中,都谈到了文学的进化问题,胡适在《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对“历史进化的文学观”表述的尤为清楚 :“文学革命的作战方略,简单说来,只有‘用白话作文作诗’一条是最基本的。这一条中心理论,有两个方面:一面要推倒旧文学,一面要建立白话为一切文学的工具。在那破坏的方面,我们当时采用的作战方法是‘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就是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故不能工也。……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注]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版,第19页。胡适等人所持有的这一“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揭示了不同时代的文学之间的差异性以及时代精神对文学发展的重要影响,是“五四”新文学建立过程中的重要理论与思想,这一理论使现代知识分子找到了反抗旧文学的必要性和建立新文学的合理性,在实践层面上以无畏的勇气构建新的文学世界,创造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五四”文学,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容以及艺术表达形式。这种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确认了文学与时代同步发展的内在联系,推动了中国文学的转变和发展,其历史意义和文学意义都是不容否定的,但是文学创作与文学史研究不同,文学史研究应重视文学史发展过程中,文学存在形态的多样性,不然就会忽略审美习惯、趣味的继承性和文学发展的联系性,对文学存在形态的丰富性进行“简化”处理。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作为“五四”时期的“作战方法”其历史意义是巨大的,但是作为今天我们研究文学史的原则是需要反思的,在强调文学的进化、发展时,不要忽略文学的继承性以及与文化传统的关联性,并由此为基础开拓文学史的研究视野和空间。
——《西泠印社社藏名家大系·李叔同卷:印藏》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