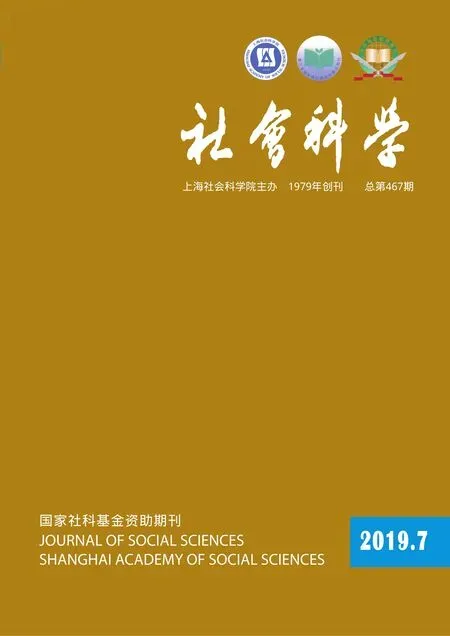论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中善意相对人的认定*
袁碧华
基于提高交易效率、保护交易安全的考量,我国确立了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以下简称“越权代表”)对善意相对人有效的制度。《合同法》第50条规定,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所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民法总则》第61条也作出类似规定:法人章程或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对善意相对人无效。可见,无论是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还是2017年颁布的《民法总则》,相关制度并无不同,都认定越权代表的效力取决于交易相对人是否善意。虽然善意相对人的认定对确定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的效力如此重要,然而,何为善意相对人,在立法和司法上却并不明晰,其认定标准需要明确。
一、越权代表中善意相对人认定的混乱
(一)学界的分歧
一般认为,知道或应当知道属于“恶意”,而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则属于“善意”。“知道”(actual knowledge),意指相对人明确了解或认识到了,是一种事实判断。“应当知道”(constructive knowledge),则是一种法律推定,是指根据某种客观事实推定行为人能知道,或者按照一般人的普遍认知能力可以推断出行为人已经知道。
学界存在多种关于善意认定的观点:一是单纯善意说。此说将“善意”解释为“非明知”,认为第三人对于外观的信赖只要出于善意就足够了,不必考虑是否存在过失[注]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42-243页;朱庆育《民法总论》(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0-361页;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3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15-217页。。这种观点明显有利于相对人,对相对人没有课以注意义务。二是无过失说。这种观点将善意解释为“不知且非因过失而不知”[注]参加崔建远主编《民法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马新彦《民法总则代理立法研究》,《法学家》2016年第5期;汪渊智《代理法论》,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23-424页。。如果相对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却因为过失而不知,则相对人亦负有一定责任,法律也没有必要对其进行保护。此种观点对相对人的注意义务提出了一定要求,即不能存在过失,该过失包括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轻微过失则可以豁免。例如,王利明先生就认为,相对人不能因其自身的疏忽大意或懈息而对行为人没有代理权的事实不知道[注]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75-676页。。三是无重大过失说。即只有“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才可被认定为善意[注]参见陈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下册),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9页(执笔人为方新军教授);王利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详解》(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773页(执笔人为朱虎教授);迟颖《〈民法总则〉无权代理法律责任体系研究》,《清华法学》2017年第3期。。较之第二种观点,这种观点减轻了相对人的注意义务,也就是说,相对人的轻微过失和一般过失都在所不论。例如,陈甦先生赞成重大过失说,他认为,我国立法对什么是善意并没有明确界定,应该采纳《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2款“取得人知道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该物不属于让与人的,非为善意”的规定,只要相对人不具主观上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即为善意,而如果仅存一般过失,不影响对其善意的认定[注]陈甦:《民法总则评注》(下册),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208页。。
在商事领域,以越权担保为典型的越权代表行为层出不穷,而善意相对人对其效力的影响问题也引起商法学者的高度关注。这是因为,公司可能通过章程或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对法定代表人的职权予以限制。例如,《公司法》第16条就对外担保事项作出规定,一般担保事项,公司可以依据公司章程而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公司章程可以对担保总额、单项数额进行限制;特别担保事项,主要指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则必须经由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才可。在法定代表人存在职权限制的情形下,相对人是否需要审查法定代表人是否越权,尤其是该等事项已经公司内部章程或董事会、股东会决议予以限制,相对人如果没有审查该些章程或决议,是否属于相对人的过失而无法适用善意相对人的保护制度,学者对此争议较大,莫衷一是。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区分公司内外关系而认定公司内部限权的效力不能及于外部相对人。这种观点认为,《公司法》第16条调整的是公司内部关系,对法定代表人权限的限制是公司内部的管理性规定,因而仅对内部有效,对外无效。因此,该第16条不能作为公司对外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依据。进言之,公司内部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权限限制,是公司内部的事情,相对人对此没有审查义务,一般推定为善意,越权担保行为一般有效[注]钱玉林:《寻求公司担保的裁判规范》,《法学》2013 年第3 期。。
第二,区分限权规定是管理性强制规范还是效力性强制规范来判断越权担保的效力。一些学者主张,应从《公司法》第16条的性质即该条规定是管理性强制规范还是效力性强制规范来判断越权担保的效力。管理性强制规范不能否定越权担保的效力,只有效力性的才能否定效力[注]参见高圣平《公司担保相关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甘培忠《公司法适用中若干疑难问题争点条款的忖度与把握》,《法律适用》2011年第8期;赵旭东《新公司法条文解释》,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李金泽《<公司法>有关公司对外担保新规定的质疑》,《现代法学》2017年第1期。。因此,判断越权代表的效力时,也无需考虑相对人是否善意。
第三,从交易事项是否重大来判断相对人是否构成善意。有学者认为,越权担保是否有效,须依据交易相对人是否善意来判断。而交易相对人的善意与否应根据交易事项是否重大来判断。对于那些动摇公司基础的非常规交易,如公司投资或担保行为(其性质与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等行为相似),属于重大交易事项,其决定权应交给股东会或股东大会通过特别决议来决定。换言之,在重大交易事项下,相对人应当负有一定的审查义务:相对人有义务要求法定代表人提供公司章程、有关机关的决议,否则无法构成善意,公司则可以拒绝承担责任[注]张舫:《法定代表人越权签约对公司的拘束力——对<《公司法》>相关条文的分析》,《法学论坛》2011年第3期。。
(二)实务部门的分歧
对于越权代表效力的这种认识分歧同样反映在司法实践中。关于越权代表善意相对人的司法裁判,也存在较大分歧,甚至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
有学者统计了我国458份司法裁判案例样本发现,目前公司越权担保合同通常情况下被认定为有效(87.77%),只有少部分情况下才会被认定为无效(11.57%)。其中,是否要求相对人承担审查义务,绝大部分法官(91.05%)认为,交易相对人无需承担审查义务,而认为交易相对人需要承担审查义务的法官仅占9%左右[注]李游:《公司担保中交易相对人合理的审查义务——基于458 份裁判文书的分析》,《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5期。。可见,目前司法界的主流观点是,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属于公司对内的程序性规定,是公司内部事务,作为公司外部关系的相对人,没有突破公司内部关系而审查其内部限权文件的义务,进而一般推定其为善意第三人。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周亚与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案的判决中,法院认为,虽然《公司法》第16条规定了公司可以通过章程或股东会、董事会对担保事项作出限制,但是该规定属于公司内部决策的程序性规定,应严格区分公司的对内关系与对外关系: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是否经公司内部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不影响其对外签订的合同的效力,否则会损害交易安全。因此,法院最后主张第三人对法定代表人权限不负有任何审查义务,相对人一般推定为善意[注]最高人民法院:《周亚与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网站,http://www.court.gov.cn/wenshu/xiangqing-9932.html,2015-10-14。。
然而,这种对相对人过于倾斜保护的审判思路被诟病较多。在一些案件中,法院也试图做某些修正或调整,即对法定代表人的职权是否获得授权,要求相对人承担一定的审查义务。如果应当审查而未审查,应认定相对人为恶意。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吴文俊与泰州市天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周文英等民间借贷纠纷案的判决中,法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第16条第二款的规定,作为天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戴其进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而以公司名义为其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是违反公司法规定的。至于相对人吴文俊,其明知戴其进为天利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应当知道天利公司为戴其进的债务提供担保应经天利公司股东会决议,但其并未要求戴其进出具天利公司的相关股东会决议,显然具有过错,不能被认定为善意相对人。当然,在这个判例中,法院主要基于《公司法》第16条对公司对外担保尤其是对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决策机构和议事程序作了明确规定,法律的明确规定已经突破了公司内部关系,推定社会公众皆已知晓且必须遵守,因此,任何人包括相对人不得主张不知道法律规定而免责[注]最高人民法院:《吴文俊与泰州市天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扬州东煜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周文英的民间借贷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中国裁判文书网站,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564399d4-519a-40df-9e33-9025b34b7bb9,2014-12-24。。
司法实务机关的这种修正甚至走向了另一极端。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5稿)》。其中第一条即规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按《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司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公司依照合同法第五十条等规定,主张担保合同对其不发生效力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文件虽为征求意见稿,但反映了审判机关的最新态度。如果该征求意见稿得以通过,将彻底颠覆之前所确立的倾斜保护交易相对人的制度,而走上另一个极端:即对公司利益的偏重保护,只要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无论相对人是否有能力知悉,都一概认定相对人为恶意。由此可见,这种审判思路校正幅度之大,正是对越权代表中善意相对人的认知混乱所致。
二、越权代表中善意相对人认定混乱的反思
如前所述,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要么认定相对人无需对公司内部限权事项承担审查义务,要么要求相对人承担较重的审查义务或一概认定越权代表中相对人皆为恶意,反映了立法上对相对人利益保护与法人利益保护的矛盾态度,也反映了制度设计中效率、安全、公平等不同价值追求的冲突。实际上,公平是任何法律的基石,商法及其规则的制定也不例外。当然,对公平的过度追求,可能会阻碍对交易安全和效率的追求。时至今日,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已然成为现代商法重要的价值追求,“由意思倾向于信赖,由内心倾向于外形,由主观倾向于客观,由表意人本位倾向于相对人或第三人本位……”[注]蔡章麟:《私法上诚实信用原则及其适用》,载郑玉波主编《民法债编论文选辑》上卷,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843-844页。,正是这种价值追求的体现。然而,矫枉不可过正,对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的追求,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公平。制度中的不同价值追求需要衡平,对不同主体的利益保护也应当综合考量,偏重任何一方都可能造成实质的不公平。
(一)偏重保护相对人的弊端
第一,偏重保护相对人导致另一交易方利益得不到保障。交易安全绝非仅保护交易一方的安全,而应保护交易双方的安全。公司也是交易一方,其自身的交易安全也是交易安全保护的应有之义,因而保护交易安全需要对相对人与公司均衡保护。司法实务部门偏重交易效率、追求司法便利的做法,虽然保护了交易相对人,但强化了市场主体的滥权和机会主义心理,对公司明显不利[注]罗培新:《公司担保法律规则的价值冲突与司法考量》,《中外法学》2012年第6期。。实践中,不少法定代表人违反章程规定,未经公司相关机关决议,擅自对外提供担保以及实施其他重大交易活动,尤其是一些上市公司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罔顾公司和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擅自以公司为自己或自己的关联企业提供担保,使公司承担较大风险,甚至将本来正常经营的公司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种保证了相对人交易安全但却置公司的财产安全于不管不顾,由其被法定代表人任意侵蚀的做法,并不符合实质公平的原则。
第二,偏重保护相对人导致相对人的“懒惰”。其实,公司法律制度不断发展,公司内部治理规则早已上升为法律规定,并为社会公众所知晓。公司作为一个组织体,是资本和人力的联合,其意思形成需要公司的决策机关集体决议,任何一个自然人,包括法定代表人,都不可能为所欲为,都不可能代表公司决定一切,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如果仍旧将公司这个法人看成一个“黑箱”,而不管如何,只认可法定代表人拥有代表公司一切事务的权利,只依据法定代表人的外观行为来判断公司的意志,这是否太罔顾现实?实践中,相对人明明有条件知道法定代表人的权限受到限制,但由于法律对其过度保护,相对人宁愿做一个懒惰的人,反正责任都在对方。在相对人具备一定能力的情况下,仍然保护其“懒惰”,于公司而言,是不公平的。
第三,偏重保护相对人导致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受损。法定代表人往往是由公司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担任,若大股东通过法定代表人滥用权力,小股东基本没有决定的余地,却要其承担大股东滥用权力的全部后果,对其也不公平。例如,上市公司万家乐A多次为大股东违规担保,使其背负巨额担保债务,严重侵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注]王晓易:《万家乐陷担保循环圈:大股东担保和为大股东担保》,http://tech.163.com/06/0327/03/2D6K7RFK00091KT0.html,网易科技网,2006-03-27。。可见,保护相对人的交易安全必须有一个度,还必须顾及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偏重保护公司的弊端
第一,公司内部风险向相对人转移并不公平。众所周知,与自然人不同,作为一种成员多元组织(一人公司例外),公司的意思形成和意思表示相分离是一种常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仅为在公司意思形成后,在公司意思的对外表示环节代表公司进行意思表示的主体。意思形成与意思表示的分离,对公司而言本身蕴含着一定风险,公司的“命脉”悬于法定代表人一个人身上,如果法定代表人不按照公司意志谨慎行事,就将置公司于危险的境地。因而需要对公司利益恰当保护,设置越权代表仅对善意相对人有效的制度。但是,如果过于保护公司利益,将善意相对人的认定标准设置过高,要求相对人的审查义务较重,就可能将这种公司内部机制产生的风险转嫁给相对人。那种一概认定相对人负有审查义务,或者一概认定相对人为恶意,就是一种转嫁风险的做法,对某些相对人来讲明显不公平。
第二,一体对待差异较大的相对人并不公平。无论是否定相对人有审查义务的观点,还是认可相对人有审查义务的观点,或者认为公司对法定代表人的限权本就是法律的规定,应推定全体相对人都已知悉;或者认为公司限权的内部文件,尤其是章程,本就是对外公示的,亦应推定全体相对人皆已知悉。实际上,这些观点都没有注意到相对人的主体身份存在较大差异,也没有认识到这种差异可能对善意相对人的判定存在较大影响。不同的相对人,其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是不一样的,其获取公司的章程等材料并作出正确的形式审查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对公司利益实施保护时,如果不加区分,一体对待所有的相对人,势必对某些相对人不公平。
第三,要求相对人完全知悉公司内部的意志形成机制并不公平。外观上,根据《民法总则》第61条、第62条规定可知,法定代表人具有广泛的代表权,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皆由法人承受。诚如学者所言,“由于法人只能经由代表机关实施交易,所以在法人的外部关系上,代表权或代理权原则上是一种概括的、不受限制的权限。”[注]朱广新:《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中外法学》2012年第3期。然而,实际上法定代表人代表权并不是无所不包的。不但公司法对法定代表人的职权有明确限定,而且也允许公司内部通过章程或有权机构对法定代表人的职权进行限制。因此,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极具复杂性,公司对法定代表人的限权渊源也是多种多样。要求相对人都去审查,不仅不可能办到,也将极大增加交易成本,势将影响交易效率。例如,在股东会决议限制法定代表人职权的情形下,一个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众多,且并不公开,具有偶发性、不确定性和不易获得性,别说是普通的民事主体,就是特殊的商事主体,也是很难知悉的,或者很难完全知悉。要求相对人对这些文件统统予以审查,将对相对人非常不公平。
第四,要求相对人不分事项负有同等义务并不公平。法定代表人所越职权的事项也可分为一般事项和重大事项。基于重大事项对公司及股东利益的重要影响,法律都会明确规定重大事项的决定主体。例如,对于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变更公司形式、公司章程修改等,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由股东(大)会决定。又如,德国《股份法》、《变更法》等法律也规定,修改公司章程、筹资和减资措施、资产转移、公司合并、公司的分立、企业的转型、公司的加入、公司的解散等引起公司基本结构发生变化的事项,股东大会有决定权[注][德]托马斯·莱赛尔、[德]吕迪格·法伊尔:《德国资合公司法》(第3版),高旭军、单晓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页。。而一般事项大都属于日常经营事项,法律并不明确规定决定主体。对于法律明确的重大事项,相对人的注意义务显然需要重些,而对于一般事项,相对人的注意义务就应轻些,不能要求相对人对不同事项负有同等的注意义务。
三、越权代表中善意相对人认定标准的构建
(一)区分主体身份下善意相对人的认定
与公司从事交易活动的相对人各不相同。抽象来看,主要可以分为特殊的商事主体和除此之外的其他民事主体。商事主体即商人,其特殊的商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由商事法律直接确认的。许多国家或地区均以商法典或单行法的方式对商事主体资格的取得与丧失、权利与义务、主体的名称及类别、行为的范围及效果等作出规定[注]赵旭东主编:《商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版,第61页.。例如,《法国商法典》第1条规定:“凡从事商活动,并以其作为经常性职业者为商人。”[注]金邦贵译:《法国商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德国商法典》第1条规定:“本法典所称商人是指经营营业的人。营业指任何营利事业,但企业依种类或范围不要求以商人方式进行经营的,不在此限。”[注]杜景林、卢谵译:《德国商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日本商法典》第4条规定:“本法所称商人,指以自己名义,以实施商行为为业者。依店铺或者其他类似设施,以出卖物品为业者,或经营矿业者,虽不以实施商行为为业,也视为商人。”[注]王书江、殷建平译:《日本商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104条规定:“商人是指经营实物货物买卖的人;或者在其他方面因职业而对交易实践或货物具有特殊知识或技能的人;或者那些由于雇用代理人、经纪人或居间人——这些人因其职业是具有这种特殊知识或技能的——而可以得到这种特殊知识或技能的人。”[注]石云山等译:《美国统一商法典》,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3页。我国立法虽然没有明确界定“商事主体”概念,但规定在《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外商投资法》《个体工商户条例》等中的营利性法人、营利性非法人、营利性自然人等都属于商事主体的范畴[注]由于本文研究的是营利性法人越权代表问题,即研究对象是公司法人,公司是特殊商事组织,商事组织与自然人是两种不同的商事主体,组织的决策程序与商自然人不同,出于对等原则和公平原则考虑,本文的商人相对人也缩小为公司法人,不包含商自然人,也不包含决策机制不同的其他营利组织(如合伙)。。
与普通的民事主体相比,商事主体的能力并不相同,因而需要对商事主体与一般民事主体区别对待。这种区别对待早已体现在各国商事立法中。无论是实行主观主义商法的德国,还是实行客观主义商法的法国,抑或实行折衷主义商法的日本,都是如此。这是因为:首先,商人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或个人,具备相关专业知识,比一般民事主体更为精明。“相比于传统或狭义民事关系而言,商事关系更多的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强调盈利性和营业性,具有强烈的竞争性,且凡是从事商事活动的主体都假定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注]江必新:《关于裁判思维的三个维度》,《建筑时报》2019年3月25日。尤其是一些专业机构,不仅对交易流程熟悉,自身还拥有强大的风险防控能力,其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自然就需要对其提出更高的标准,要求其承担更重的义务,司法机关在认定时也会更加严格[注]徐海燕:《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签署的担保合同的效力》,《法学》2007年第9期。。其次,商人熟悉公司内部相关决策机制。如果相对人为商人,尤其是商法人,其自身就是公司治理结构,也熟悉公司内部可能通过章程或决议对法定代表人的职权作出限制,也了然公司内部存在权力分工,明白没有任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拥有无所不包的权力,因此,商人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权限并不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也知道影响公司或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要么是应由股东会来决定,要么是应由董事会来决定,法定代表人仅为决议的具体执行者。当然,如果相对人是除商人之外的普通民事主体,可能其对公司内部复杂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机制并不熟悉,根据其自身能力,无法判断公司是否需要限制法定代表人的职权,是否存在限权的内部文件,以及是否需要审查公司限权的内部文件,当属“无过失”的善意。
因此,在认定相对人是否善意时,应当区分相对人的主体身份。相对人主体身份不同,其认知能力和注意义务也应是不同的。商人的注意义务较重,应该采纳一般过失说,而一般民事主体的注意义务可以低一些,应该采纳重大过失说。例如,若相对人为商人,没有要求对方提供章程以查阅公司内部对法定代表人权限的限制,构成相对人的重大过失,不能推定其为善意;而对一般民事主体而言,可能并不了解公司复杂的决策机制和章程的作用,无需负担如此高的注意义务,客观上也没有这个能力,因而一般推定为善意。
(二)区分限权渊源下善意相对人的认定
1.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法定限制
为了约束法定代表人这种广泛的代表权限,法律直接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进行了限制,此即法定限制。公司是一个组织体,内部有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关,各机关各司其职,分权与制衡,这是公司治理的基本逻辑。根据我国《公司法》第13条的规定,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董事长、执行董事、经理,都是属于公司的具体执行机关。股东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通常决定关系股东权益或公司自身的重大事项。至于监事会,是由股东会选举产生,监督董事会和经理等经营层的监督机关,其不能兼任董事会成员或经理。按照公司内部机关的职责分工,显然,那些属于股东会和监事会的职权,法定代表人是不能享有的。例如,《公司法》第37条、第46条、第99条、第108条等规定的事项,这些都是公司股东会的法定职权,《公司法》第43条、第103条、第121条等还对股东会部分职权行使的表决比例作出专门规定。例如,《公司法》第43条第二款就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有学者认为,法定代表人违反法定限制的情形,虽然也属于越权代表行为,但不属于《民法总则》第61条中规定的越权代表,没有适用《合同法》第50条与《民法总则》第61条善意相对人制度的空间,可以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应自始无效[注]张舫:《法定代表人越权签约对公司的拘束力——对<公司法>相关条文的分析》,《法学论坛》2011年第3期。。实际上,这些强制性规定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尚存争议。任何违反法定限制的越权代表行为,都直接依此认定无效,对相对人并不公平。笔者认为,这些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仍然应当适用善意相对人制度。而且,需要从相对人的主体身份来作区分,进而判断其是否善意。如为商人,应推定其知悉;如为非商人,则应推定其不知悉。
2.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意定限制
除了法定限制,《民法总则》第61条第三款也规定,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可以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进行限制。无论是章程还是权力机构的决议,都体现了公司的意志,遵循公司自治的结果。因而在公司内部,由公司章程或其指定的权力机构限制法定代表人之代表权,是公司内部的意定限制。根据限权渊源,可将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意定限制分为章程限制与权力机构限制。
首先,章程限制下善意相对人的认定。公司章程登记于工商部门并向社会公示,具有对外的公示效力。章程的这种对外公开,使其具有一定的公示公信力,并为社会公众,尤其是与其交易相对人,提供一种了解公司情况以作参考的渠道。既然社会公众可以获得已经公示的章程,也就可以了解章程内容。如果章程对法定代表人予以限权,应推定相对人知悉,相对人也就无法构成善意。然而,非商人并不以从事营利活动为业,并不了解公司的运作机制,要求其注意到法人章程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超越了其判断能力。因此,对于非商人而言,章程对法定代表人的限制,应推定其不知;而对于商人而言,则推定其知悉。
其次,权力机构限制下善意相对人的认定。在公司内部,有权对法定代表人职权进行限制的机构主要有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可以按照法定或章定的议事规则和表决程序作出限权决议。但是,不同于章程的公开性、稳定性,这些内部机构的决议具有非公开性、偶发性的特点,相对人很难通过公开途径去查阅,且这些决议可能较多,彼此还存在一定冲突,相对人即便能够获得,也难以作出准确判断。无论是商人还是非商人,要求他们了解公司内部机构作出的决议限制,不仅非常困难,成本也会很高,严重影响交易效率。因此,公司内部机构决议对法定代表人的限权,一般都推定相对人不知道。当然,对于公认的重大事项,则另当别论。
(三)区分限权事项下善意相对人的认定
越权代表所越权限,可以分为一般事项与重大事项。不同的事项对公司影响程度不同,其公开的程度也不一样,对相对人善意的认定亦有不同的影响。
1.重大事项下善意相对人的认定
涉及越权代表的重大事项,主要可以归为两类:一类为对公司基本组织结构产生较大影响的事项。例如,有关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形式变更以及破产等;二类为对公司影响较大的对外交易事项,例如,对外担保、借贷、投资、重大资产转让等。
对于影响公司主体变更的事项,因其对股东关系重大,公司法一般都作出明确规定,将其规定为股东(大)会的职权。如果法定代表人超越股东会的职权而擅自行为,这些越权代表是否有效,有学者认为,由于这些重大事项已由法律明定,相对人理应知晓,故不存在善意问题[注]张舫:《法定代表人越权签约对公司的拘束力——对<公司法>相关条文的分析》,《法学论坛》2011年第3期。。前文已述,这种情况下一概认定不适用善意相对人制度并不妥当。应当按照相对人的认知能力来判断,推定商人知道这些法律规定,而推定非商人不知道。
对于特殊的对外交易事项,法律一般也明确规定了决定主体。例如,我国《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如需对除股东之外的其他人提供担保,可由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确定。对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由股东会决议是否同意。我国《公司法》第148条就借贷作出规定,公司对外借贷需要依据公司章程而定,由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相关主体决议确定。针对重大资产转让,我国《公司法》第121条规定,超过公司资产总额一定比例(30%)的购买或出售重大资产行为,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才可。实际上,许多国家的公司法都有类似规定,一般将重大交易决定权交由股东(大)会。譬如,多数国家将公司重大交易的决定权交给了股东会。例如德国《公司变更法》也规定,企业重要组成部分之出让行为,须征得股东大会同意才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判例中也认为:“企业虽然可以将其重要组成部分转移给子公司,但这一种涉及公司结构变化的基本问题,母公司的董事会不得撇开股东大会而擅自作出转让的决定,因为这样就有可能彻底改变股份有限公司中现有的制约和平衡机制。”[注][德]托马斯·莱赛尔、[德]吕迪格·法伊尔:《德国资合公司法》(第3版),高旭军、单晓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页。根据日本《公司法》第467条的规定,如果股份公司转让其全部事业或部分重要事业,必须获得股东大会的决议认可[注]《最新日本公司法》,王保树主编,于敏、杨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页。;美国修订后的《示范商业公司法》第12 条也规定,对于非常规商业经营过程中的资产出售,董事会必须提交股东会讨论通过[注]参见《美国公司法规精选》,虞政平编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09页。。这主要是因为,涉及公司重大资产的交易行为,对公司基本组织结构的影响也可能与公司合并、分立一样,因而对股东也有较大影响,股东对这些交易拥有决定权,并有权决定是否需要退出公司)。当然,也可能按照章程规定或股东(大)会的授权,由董事会决定。法定代表人对于这些特殊交易事项的越权,应当要求商人承担更重的注意义务,适用无过失原则,推定有一般过失就不构成善意。若相对人为非商人,由于其无法判断公司内部决策权限配置及复杂的决策机制,其注意义务较低,适用重大过失原则,一般情况下推定其不知道,构成善意。
2.一般事项下善意相对人的认定
重大事项之外皆为一般事项。随着公司自治程度的提高,对于一般事项,一般情况下都由公司自行决定,公司可以依据公司章程或者依据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而自行作出决定。如果法定代表人所越事项为一般事项的话,则视限权渊源而定:若为章程限制,应推定商人知道,非商人推定不知道;若为公司权力机构限制,无论是商人还是非商人,都因相对人难以获悉公司内部权力机构的临时性、非公开性的决议,而推定一般情况下皆不知道,都构成善意。
结 语
在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中,善意相对人的科学认定绝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权利均衡配置问题,涉及到法人、法人股东、法人相对人以及法定代表人的权利平衡配置。那种任何不考虑相对人商人与非商人身份、法定代表人权利限制的渊源、权利限制事项性质的简单认定都有失偏颇,都是对社会主体及其行为复杂性认识不够所导致,必然不能实现法律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精准调整,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平和正义。因此,在认定相对人是否善意时,应结合相关因素,综合认定。首先应当区分相对人的主体身份。相对人主体身份不同,其认知能力和注意义务也不同。商人的注意义务较重,应该采纳一般过失说,而一般民事主体的注意义务应低一些,应该采纳重大过失说。在此基础上,再区分法定代表人限权渊源来区分认定善意相对人,譬如法定限制与意定限制区分,意定限制中的章程限制与权力机构限制区分。不同的权利限制渊源具有不同程度的效力、公示性及可获得性,必然对善意相对人的认定产生不同的影响,需分别确立不同的认定标准。最后,还应区分越权代表所越权限事项的性质来认定,可分为一般事项与重大事项,不同的事项对公司影响程度不同,其公开的程度也不一样,对相对人善意的认定亦有不同的影响。综上,综合考量相对人的商人与非商人身份、法定代表人权力限制的渊源、限权事项的性质,确立善意相对人的认定标准: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事项,若为章程所限,推定商人知道而非商人不知道;若为权力机构所限,则推定相对人不知道。如其越权事项为公司重大事项,无论是章程所限或权力机构所限,均推定商人知道而非商人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