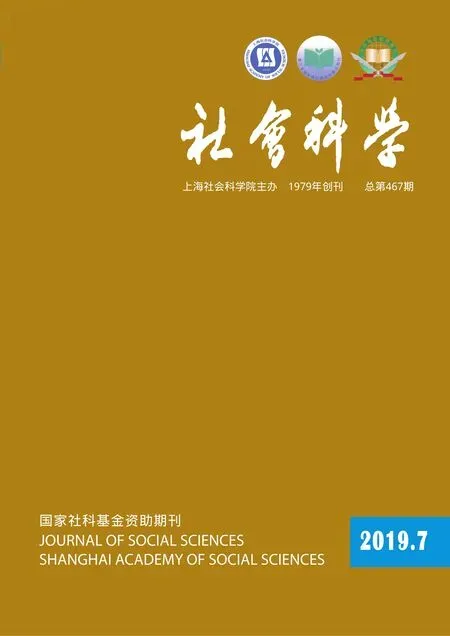守义与知命
——《论语》中君子人格的两个基本规定及其意义
郭美华
大多认为,在孔子那里,“君子”的概念有一个从位向德的转变。从德的角度来理解“君子”,是一个基本进路。不过,纯粹从德来理解,蕴含着导向错谬的可能,即将生命引向逼仄,将世界引向局促。实质上,作为仁、礼(或仁义)之德与政所规定的人,只是人自身丰富而多样生命存在的局部,而非全部,甚至根本不是人的最为本质之处。超越狭隘之“德”,从人自身的存在来看,君子作为人格存在,并非要指向一种跨越时间限制与空间限制的“唯一之人”,而是要指向所有人与每个人,是开启当下与未来每一个降生临世之人走向其自身的可能通道。简言之,君子就是一个“中介”,君子的中介意义,即在命与义之间敞开对于一切人之存在样式的容纳可能性。
因此,在孔子哲学中,君子人格的生存论意义,最为基本的规定性就是守义和知命。知命是“知其不可奈何”,守义是“为之”[注]晨门讥笑子路,认为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其意是显露孔子在智与仁之间的矛盾。隐者之意在于指出:现实不可为而孔子力图有所作为,不知不可为,是无智;知不可为而为,是不仁。换个视角,孔子所彰显的价值具有某种中介性质,以至于在隐者的批评之外,世俗之人也对孔子有批评。比如《阳货》第一章中,阳货认为孔子在仁与智之间进退失据,自以为怀有治国之能,却让其国与民迷失,是不仁;有出仕的机会却不能抓住,是不智:“(阳货)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隐者和阳货的批评,恰好彰显了孔子之教的困厄,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君子生存的困厄。,用孟子的话来说,亦即知命是“无为其所不为”[注]《孟子·尽心上》。,相应地,守义是“为其所为”。按照孟子的界定,所谓命,就是“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注]《孟子·万章上》。孟子是将天与命连在一起言说的,他认为天是“莫之为而为者天也”,命是“莫之致而至者”。通常认为二者的意义是一致的,比如朱熹说:“盖以理言之谓之天,自人言之谓之命,其实则一而已。”(《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09页)朱熹的理解,当然与孟子本意不一致。在孟子,天命是政治哲学的含义,即在政治领域,本应该是人自身的自觉行为所造成,但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偶然或必然之势。朱熹将天和命在理本体论上统一起来,一方面忽略了天命本身的偶然性与无常性,一方面将天的实体义与命的过程义混淆了。从而,朱熹模糊了人为与力行之间的界限。尽管孔子在天命与人能之间也有一些界限模糊之处,“将人的理性或主观能动性绝对化为天命”(参见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5-96页),但主要倾向上,孔子还是将天命视为人(尤其君子)之行的界限概念。。无论是类还是个体,人类自身的整体存在中,无疑有着隐、显或明、暗两个不同的侧面。人自身的整体性存在中,有无数的构成性因素,但并非每一种因素都是人之存在的本质性因素。孔子所肇始的儒学,一个重要之处就在于突出了基于主体能动性的道德生存,以之为人类自身存在的本质之处。从人自身的能动性道德生存而言,这是操之在我的“守义”。但守义的道德生存,并不穷尽人的生命的全部,更不穷尽世界自身的全部。因此,在守义的道德生存展开过程中,如何经由领悟天命而持守界限,以释放人自身乃至天地世界自身的“无穷未知性”,就成为“知命”的本质内容。在此意义上,君子的守义标志着人之存在的有限积极性一面,而君子之知命,则标志着君子存在的无限消极性一面。就道德生存论而言,前者就是道德生存的界域,后者则是自然(或天地世界)的界域。守义是君子的重要道德规定性,知命则是更高的道德规定性,即知命是守义得以可能,以及超越守义得以可能的规定性。守义可以说是经由人的道德活动而成就自身、成就世界;知命则是超越人的道德生存而敞开自身、敞开世界。进而言之,义的持守,命的领悟,以及守义与知命两者之间的界限持守,就是君子人格的基本规定性。[注]关于道德生存展开的过程性与天命呈现的划界意义,参见郭美华《古典儒学的生存论阐释》第三章“过程与划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5-67页。如此规定性,其根本的意义在于昭示出:一方面守义是对人自身的道德挺立,凸显人的道德价值与存在尊严;另一方面知命是对人自身生命存在之幽深的敞开,凸显人之现实存在的卑微与谦卑,展露世界的无穷广袤与他者的无限差异性。
因此,对君子人格的理解,必须警惕经由道德性内圣,再以神秘的方式,将天命自为化与自觉化,以狭隘的自我弥漫整个世界,吞噬他者在其自身的可能性与差异存在的界域。捍卫天命的自在性,让渡他者的差异性,是真正的君子人格中更为深邃的责任,而这往往被许多君子人格的诠释者所忽视了。
一 、《论语》中君子守义的几层内蕴
属人的存在有着自明的起点,就是“学而时习”,即觉悟与生命存在活动的源初浑融一体之绽现。[注]参见郭美华《论“学而时习”对孔子哲学的奠基意义》,《现代哲学》2009年第6期。觉悟是人自身生命存在的本质。存在的自我启明或自我启明的生存,其觉悟之明有程度的大小深浅之不同。达到特定程度觉悟之明的人,就是君子。对《论语》或《论语》中的孔子而言,君子具有核心意义,因为它既以“君子”开篇,也以“君子”终篇。
《论语》开篇: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君子,刘宝楠引《白虎通》《礼记》说:“称君子者,道德之称也”,“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注]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页。君子有某种“道德”。君子有三点醒目之处:一是其道德基于自明而有之学;二是相与讲学讨论是进德的阶梯;三是这种道德觉悟是内在之明,区别于外在认知。此所谓君子,不单单是“不知而不愠”,而是与“学而时习”之“悦”及“朋自远来”之“乐”统为一体的。将自身觉悟与外在认知区别开来,并将君子之生命存在内容排除在外在认知范围之外,这是君子人格的基础性方面。[注]将君子或人的真实存在排斥在认知界限之外,这是《论语》中孔子关于人之道德存在的一个基本倾向,比如,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子曰:“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里仁》)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卫灵公》)生命的真实而具体之在,都是不可以外在而普遍之知来加以把握的,在此意义上,《宪问》中孔子感叹“莫我知也夫”的真实意义,就不单单是感叹没有人“理解他”,而是感叹没有人理解“真实存在逸出认知之域”的道理及其自身切己的生命存在之实。
认知眼光与功利目的具有内在一致性。不以外在之知为存在的目的,也就意味着君子人格拒斥被工具化。因此,孔子说:“君子不器。”[注]《论语·为政》。君子是有教养和德性的人。而器是因其对于自身之外的需求而有用处的存在物,是一种工具或手段之物。因此,君子经由学思而成就其德,不能以自身之外的他物为目的,而是自为目的。君子成德,不同于物之成器。器总是有特定作用之物,其用体现为人的需要。因此,器之用以人之需要为体,其体用是分离的。君子学以成德,就是要在自身成就内在德性以为体,而有其体必有其用——有德以为体,则有德以为用,也就是说德之体为性,德之用为行——德性与德行是统一的,而与一般器具之体用、性行相分不同(实质上,一切器物都有用无体、有行无性)。器具之物总是适用于某种用途,有所偏;但成德之君子,其目标是“成人”,是智仁勇礼乐等全方面、丰富性的造就自身。物有偏,君子成德则无所偏。器有其形,有形则有名。一个器物的价值,往往“声名在外”,任何一个器具之物,往往就是一个“普遍之名”的例示而已。君子学以成德,孔子谆谆教导不可以名或为人所知为目的,德是默识心通、敏行讷言。学思修德,重在觉悟默识,重在践履,重在成就自身为一内外充盈的完满者,不是一个“普遍概念”的例子。
不陷于工具化的君子,其自为目的而存在,就是内在德性的成就。如此内在德性的生成,固然有自然情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但最为核心的则是君子之存在于天下,只以“义”为自身的生存内容或生命原则。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適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注]《论语·里仁》。
適、莫,有两种不同解释:一说適同“敵”,即抵牾、对峙、排斥之意;莫同慕,即贪慕、亲近之意;一说適、莫是“厚”“薄”之意。[注]刘宝楠:《论语正义》,第147页。比,也是亲近之意,但与適、莫相对举,“与比”,用以突出“有原则的自觉选择”之意。所谓“天下”,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事。我们结合起来看,所谓天下,不过就是人之行事与行事之人。君子作为读书明理之人,他自身行事和与人交接,既不以特定之人或物为敌对排斥的对象,也不以特定之人或物为贪慕亲近的对象;既不厚此而亲,也不薄彼而疏;而是以义与非义为衡断的基准,义则行之、交接之,厚之;不义则不行之、疏远之,薄之。而对于“何以为义”或“义何在”,有不同的理解。义作为行事之“宜”或行事的应当,或内在于人心,或内在于事情,或为某种超越的普遍规范。这在后世心学与理学的分歧中得到折射。理学突出义是超越的理,所以强调行事符合理-义;心学突出内在之理,所以强调外在之事或物,相对心而言,无可无不可,只要心依自身之理即可。不过,从君子重在学思修行而言,超越之理,与内在之心,应该统一到切己行事之中。而所谓切己行事,就是教学相长、友朋切磋、思修成德的具体行事中有一个“规则之义”统摄在其中。
义作为君子人格的生命内容,本质上基于自觉的选择和自主的行动,并且,君子自觉地以义作为自身的本质规定性: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注]《论语·卫灵公》。君子以义为自身之本质,这里蕴含着义作为君子生命存在的更为深刻的理解,即义是自身觉悟之君子自觉选择的必然,即自由存在的君子,一旦自觉而自由地选择,就必然选择“义”作为自身的行动原则。[注]这可以从两方面进一步说明:一是孔子自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一是颜渊问仁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前者是个体性体验性内容,后者是个体性理性抉择而成普遍原则。尤其是,后者显然可以在康德普遍立法原理上来理解,具有极为深刻的意蕴。原则、体验与行动的浑融统一,就是一种作为本质性生命内容的义,即“喻于义”;“喻于义”以“作为规则或原则的义”为生命自身的本质内容,使君子显著地与小人区别开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注]《论语·里仁》。传统上认为君子、小人在这里是指“位”而言(刘宝楠:《论语正义》,第154页)。孔子这句话的主要意思是让处于治国者位置的“君子”,明白一个简单道理:即治国应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一方面,民众作为无位之“小人”,本身就是求利谋生,治国者之治国,必须使得民能得其利而遂其生,不能反过来让民众放弃求利,而追求某种缥缈的“理念”或“原则”;另一方面,治国者作为君子,必须守义,严格限制自身,不能与民争利。孔子张教化,其基础是富之而教以趋善;孟子所谓仁政,也是先实现养生丧死无憾而再行教化。政治治理的最腐败的病症,就是让民众去守义,而掌权者却中饱私囊、贱民自肥。通过让自身与他者有所区别地实现出来,由此区别关乎相互区别双方的本质,则区别的内在含义,就与区别开的双方,尤其自觉而能动的区别者(即君子)的本质相一致。在此意义上,当君子以将自身与小人相区别的方式而彰显义作为自身之本质时,其中蕴含着一个更为深刻的道德生存论理解,即自觉地使自身与共在的他者相区别,是君子人格的根本之处——他既不以所有人的共性为自身的追求目的,也不以自身之求作为普遍共性强加给他者为其生存的目的。[注]从生存论上的自觉区别意识出发来理解《论语》中君子与小人的对举,较之从价值上的是非、对错、好坏、高低角度来理解,是一个更为合于君子之为君子的本质的理解方式。《论语》中其他君子与小人对比的陈述,比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颜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卫灵公》),“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等,尽管包涵着很强的价值区别之意,但这仅仅是一种“概念上的区别”,而非“生存论上的区别”。孔子对于行的强调以及对于多言的否定表明,概念上的区别低于生存论上的区别,比如孔子对“行先言后”、“敏于行讷于言”、“耻于言过其行”等的强调,就表明了这一点。
义作为君子的生命存在之本质,一方面以求别成异为本质指向,意味着真正的个体性之生成;另一方面,它作为普遍的原则,又是使得个体性得以可能的前提。在孔子看来,当君子(无论有位无位)与他者相互关联而共在之际,其存在必须以合于义的方式来展开。比如孔子评价子产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注]《论语·公冶长》。“使民以义”,既是以义为普遍原则来范导行动,也是以民之自成其自身为普遍原则指向的目标。
就君子个体而言,义作为自身明觉而行动的原则,与思具有密切关系,相应地义就成为思的根本内容之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注]《论语·季氏》。子路以为君子重要的是“勇于行”,但孔子明确强调,君子之勇,在于勇于行义,实质上就是以义行勇而义在勇上。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注]《论语·阳货》。孔子对于君子与义之间的如此规定,在存在的普遍性与个体性、同与异之间,给出了一个基本方向,即君子在于经由普遍性的自我立法而走向独特的自我生成,即“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注]《论语·宪问》。,这是君子人格的基本内涵,也是“君子守义”的基本内涵。
二、《论语》中君子知命的界限意义
《论语》中命的含义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就其与君子人格相联系而言,知命意味着相互关联却又内在辨证的理解,即知命有两个层次的要义:一是自身认知有限性的确认;一是对于命不可知的领悟。天命自身的显现,基于人自身作为有限性存在而展开为过程。孔子自述自身的生命存在之展开历程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注]《论语·为政》。在此过程中,引人注目的是:天命之为天命的出现。《朱子语类》有一条有趣的记载:“辛问:‘“五十而知天命”,何谓天命?’先生不答。又问。先生厉辞曰:‘某未到知天命处,如何知得天命!’”[注]《朱子语类》第二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553页。朱子此话真意难揣,但其自认“未至知天命处”而不敢说“知得天命”,大端不外乎意识到“天命之为天命”不可骤语。这个问答其实触及到了《论语》中天命的复杂性——知命之知的辩证性内蕴,即以不可知为知的知命。
简单说,天命在《论语》中基本指向一种虽然渗透、穿越人之存在、却不为人之主体性所支配的力量(以偶然和必然为表现的力量)。如此力量与主体性力量相区别,可以理解为“外在性或异在性限制力量”。但如此异在性限制力量,却可能体现为两个表面上完全相反的理解。一方面,就个体生命的偶然降生而言,似乎“命定为人”具有某种形而上学的“内在必然性”。比如孔子自述“文在兹”与“德在予”之论:“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起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注]《论语·子罕》。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注]《论语·述而》。
文教与德性,本来是主体性的方面,但如果形上地追问人何以有文教和德性,只有诉诸于一个不能无穷后退的最后实体或力量。一般的理解,就是将天从异在性限制力量,转化为内在主体性的本体论依据。这个理解其实是不妥的。正如孟子所谓良知良能之“良”就是不能再做理智的进一步追问一样,在生存论上,文教与德性的根源就是人类的现实生存本身,而不能脱离历史与现实去虚构其超越性根据。“天生”的意思就是认知或理智运用的界限,不能再作穿凿之论,从而停止对于人生的妄思而切己地践行。
在此意义上,天命的另一方面意义就完全体现为异在性限制力量。如此力量既是理智思考的界限,也是生存自身的界限,主体只能发出悲叹:“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注]《论语·八佾》。“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注]《论语·先进》。“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也乎!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注]《论语·雍也》。“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注]《论语·宪问》。“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注]《论语·季氏》。
悲叹之所针对,表面上体现为德性生存与天命之间的背离。人的主体性生存不可避免地遭遇异在性限制力量,这种力量不但给予我们生命,而且戕害我们的生命,乃至剥夺我们的生命。尽管随着近代以来的主体性力量之拓展,这种异在性限制力量似乎也缩小着其领域,但从哲学上看,异在性限制力量随着主体性力量的拓展,依然显现自身为无边无际的幽暗深渊。因此,君子作为主体性生存,只能以“畏”的情态来因应作为幽暗深渊的“天命”。畏意味着敬而远之,意味着人打开自身领悟了的内在精神情态,向着未知之物开放自身。“畏天命”之所以是君子的生存情态,与君子的自觉区别性意识相关,正如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一样,孔子也反对占卜、算命:“不占而已矣。”[注]《论语·子路》。占卜算命很显然意味着一种生存的懦弱与悖谬,它力图认知不可认知之物及其力量,并以之来规定自身可自知自觉的生命展开。畏是一种直面异在性限制力量,却将之与主体性生存相分界的生存情态,如此畏的情态,一方面持守着自身之义,一方面又不以义捆缚自身而使自身向幽暗渊深开放自身。
因此,作为君子的畏之生存情态意义下的知天命,此知就不是消解天命的幽暗渊深,不是消解天命的广袤无垠,而是将天命的深邃与广袤接纳进入我们的生命深处,并揭明我们每个人自身内在的幽深与广袤。当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注]《论语·尧曰》。之际,不单单是一个认知的诚实之德,即“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注]《论语·子路》。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注]《论语·为政》。,对于自身无知的领会与承认,这是一种认识论上的诚实德性;而且更进一步意味着一种生存论上的德性,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论语·颜渊》、《论语·卫灵公》。、“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注]《论语·宪问》。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注]《论语·子罕》。,不让自己有限的认知和自觉领悟,弥漫、遮蔽无边无际的世界,这是生存论上的德性。认知的德性与生存的德性之统一,在颜回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他“为仁由己”而“克己复礼”[注]《论语·颜渊》。,且“不迁怒不贰过”而“三月不违仁”[注]《论语·雍也》。。颜回的人生显现了高超智慧与高超德性,“严谨自我限制而不陷世俗之为”的存在状态,孔子多次赞其“贤”,孔子在将子贡与颜回比较时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注]《论语·先进》。在将颜回与自己相比较时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注]《论语·述而》。如此言说昭示了一种生存的进境,对于世界的拓展,将政治的世界与仁礼的世界相分离,并拓展至与隐者世界的关联,以及由隐逸世界而牵引出无边广袤无限深渊之境。
在此意义上,君子之知命,就是一种在人的共存之中,对于他者和世界自在性的让与。如此让与,世界不是进入逼仄,而是进入宽阔。这就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注]《论语·述而》。。所谓“坦荡荡”与“长戚戚”的涵义,似乎有些隐晦。传统注疏中,有的认为“坦荡荡”是无忧无惧,“长戚戚”是忧患、忧惧之意。君子志于仁而博学守义,内心一依于理,故坦荡无碍;小人无仁无义一心逐利,得失之间忧患怕惧不安。这个理解恐怕太过局限于字面了。有解释认为,坦荡荡是一种“宽广”之貌,长戚戚则是一种“局促缩迫”之状。这个解释可以深入一点来理解。
《孟子》中有几个说法,可以深化这一章的理解:“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注]《孟子·滕文公下》。“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注]《孟子·离娄上》。“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注]《孟子·公孙丑上》。“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注]《孟子·尽心上》。
由此而言,仁作为人之所居,义作为人行走之所由,就是“君子坦荡荡”的要义。它并不是一个心灵境界的问题,而是一个人自身所处的生存论境遇。按照孟子的说法,仁义礼智等,并非某种抽象的概念规定性,而是活生生的生存论状态:“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注]《孟子·离娄上》。仁是事亲之活动;义是从兄之活动;智是仁义活动中的觉悟;礼是仁义之生存活动的节文;乐就是仁义礼智融为一体的生存论情态。这种生存之乐,其基本的规定性,也就是孔子的“仁智统一”之行。当孟子突出强恕而行、反身而诚,从而“万物皆备于我”之时,他所说的,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论意义的抽象把握万物之理(如理学所说),而是一种“取之左右逢源”的相融共生之生存论“广阔之境”。在具体的道德生存活动中,我、他人、万物一体共在,整体中的每一个具体个体,都充盈着情感相融、秩序明觉与意志自主自得。这是君子成就自身的必然指向。因此,君子就生活在自身宽阔胸襟之境与广阔世界之境的双重“广阔博大”之中。
小人与此相反:将自己从与他人、万物的一体中孤立出来,只有自己,罔顾他人他物;只顾一己私欲,毫不尊重秩序;他为个人的利欲而驱动自身与他人和万物对峙,最后自己也成为自身欲望的奴隶——他没有一个让自身融身其间的世界,他甚至没有自己,如此他活在“缩迫局碍”之中。
概而言之,君子知命的生存论德性,就是君子让世界保持其幽深与广袤、让他者、让自己能自行跃入无边无际的生存深渊。
三、孔子圣化与君子世界的窄化
理解命和义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是人类生存的重要方面:“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注]《庄子·人间世》。命和义交织,划定界限,由此界限,给出了自由生存的可能。对于君子在守义与知命二者之间的界限及其对于自由生存可能的开启,孔子有一个感叹,表明他的学生们根本没有领会这个界限:“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注]《论语·阳货》。因为孔子承认自己并非圣人甚至亦非仁人:“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注]《论语·述而》。同时,孔子也说不得见圣人,而见到君子已足够了:“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注]《论语·述而》。因此,一定意义上,“天何言哉”之语,就是作为君子的孔子自见之语。作为君子,其存在展开的界域,就是在“天无言而四时行百物生”的间隙与裂缝中,自明而自行。天行与人能之间,并没有一个本质一贯的无缝贯穿。换言之,守义的道德生存,并不僭越自身为天之言。从而,天自身的无常与自在,就使得作为他者的学生,可以自行在天行与人能交织而豁显的裂缝里自得其走向自身的可能性通道。子贡作为学生,没有自寻自身存在的通道,没有置身天人之间的“界域”,而是以孔子作为自己的高墙之围;“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注]《论语·子张》。乃至于将孔子视为不可企及的日月:“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注]《论语·子张》。最后直接将孔子视为“天”:“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注]《论语·子张》。子贡对于孔子的神化与圣化,为后世所继承,造成了一个极大的恶果,即虚构孔子,从而遮蔽了孔子作为君子在“守义”与“知命”之间的中介与开放,进而遮蔽了广袤的世界与无穷的他者。
在子路对隐者的批评中,如此遮蔽更为深刻地体现出来: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莜。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注]《论语·微子》。
以“义”批评隐者,这是鲁莽灭裂的子路才能做的事。在《论语》中,孔子对于隐者的赞许与敬佩,显露得极为自然真切。在《论语》中,隐者也有夫妻、父子、朋友等伦常关系,他们在现实生存中也面对“君臣父子”关系:“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注]《庄子·人间世》。庄子这里将父子关系视为“命”,具有不同的意蕴。究其基本的倾向而言,他将君臣之义与父子之命视为生命存在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但他并不以之为生命存在的全部内容,甚至并不以之为本质的内容。逍遥与养生,作为生命自由存在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不断自我解放,不断祛除束缚的追求历程。子路无视于隐者对于现实伦常的非政治实现样式,直接以政治支配下的人伦关系为唯一的人伦关系,不但阻碍人伦以及基于人伦的修德与教化的独立性可能,更阻碍了超越政治之域而走向隐逸生存的可能通道。
简言之,在子贡与子路的理解里,孔子的思想世界趋于狭隘,而且经由后学所虚构与圣化的孔子,古典时代的思想与生活世界也变得局促与狭窄,一个充盈差异性与丰富性的世界、一个清澈透明与幽深隐秘交织的世界、一个自我成就与让渡他者的世界,演化为了只有圣人主宰的单面世界。由此,君子人格,徒具其名而未得其实。在当今之世,如果君子人格依然被引向狭隘政治之域及对其准则的顺服,君子人格依然导向对幽深而广袤世界的肤浅化与逼仄化的唯一显现之途,那就意味着孔子再次被虚构与扭曲地“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