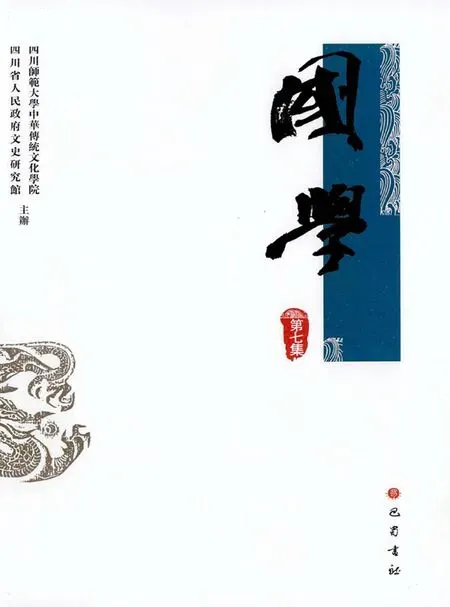宋齊丘與南唐朋黨
楊偉立
南唐朋黨之争,歷李昪、李璟兩朝,相當數量的官吏捲入了鬥争的漩渦,對南唐的前途産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關於這場鬥争,當事者互相擊搏,有心者記其見聞,著述者發為史乘,留下一些材料,為後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據。但是,這些材料零星分散,比較深層次的問題未予標明。近人夏承燾先生很重視這個問題,他在《馮正中年譜》裏多次提到,並指出問題重要。由於題目所限,他對南唐朋黨問題施墨甚少,故南唐朋黨問題尚須進一步研究。
一、宋齊丘首樹朋黨
朋黨,黨争,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屢見不鮮。“南唐之士,亦各有黨。”①馬令:《南唐書》卷二十《黨與傳·序》。南唐朋黨之争,始作俑者是宋齊丘。他率先集結以自己為首的政治集團。
宋齊丘結黨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 各書説法不一,《江南野史》的作者龍衮認為在保大元年(943),黜宋齊丘為鎮海節度使之後②龍衮:《江南野史》卷二《嗣主》:“……黜宋齊丘為潤州節度使。(鎮海軍節度使駐潤州——筆者) 既行,朝廷有位者咸竊排毁,言:與親信陳覺等樹朋黨,嫌隙自此始矣。”。《釣磯立談》的作者史叟認為在南唐建立之後。至於年份,又含糊不清①史叟:《釣磯立談》第8 條:“宋子嵩以布衣干烈祖,言聽計售,遂開五十三州之業,宗祀嚴配,不改唐舊,可謂南國之宗臣矣。及世事移改,新用事者,爪距銛鋭,方曹起而朋儕之……”又第27 條:“宋子嵩晚年惑於陳覺、馮延巳等……新進用事之人,聲勢氣燄,炙手可熱。”“及馮、陳、宋、查之黨成,齊丘也在嫌,不得已,遜於九峰之谷。”。夏承燾定在升元末年②《馮正中年譜》“保大元年十二月”:“按:南唐黨争,醖釀於升元之末。”《唐宋詞人年譜》第49 頁。。看來他們的論斷都不够準確。
宋齊丘結黨,早在南唐建立之前。馬令《南唐書·宋齊丘傳》説:
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入輔政,委齊丘左右之。齊丘於是益樹朋黨,潜自封殖③文瑩略同。《玉壺清話》卷十《江南遺事》:“…… (徐) 温卒,方用(宋齊丘) 為同平章事。遂樹朋黨,陰自封殖,狡險貪愎,古今無之。”。
烈祖(徐知誥,吴國權臣徐温養子,南唐的創立者,歸宗後,更名李昪,廟號烈祖。此下除引文外,一律寫成李昪) 出鎮金陵的時間在吴楊溥太和三年(931)④《舊五代史》卷一三四《潜僞·楊溥傳》:“天成四年,僞吴改太和元年,是歲,李昪出鎮金陵……”非是。應從《通鑑》、馬令《南唐書》。,名義為鎮海。寧國節度使,權力範圍是總録朝政。同時,用他的長子李景通(後改名李璟) 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廣陵輔政(吴國京城在廣陵,今江蘇揚州市),又派王令謀、宋齊丘輔佐李璟。這樣的人事安排,當然是李昪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作出的,表達了他的政治意圖:(1) 牢牢地把持吴國權柄,為“傳禪”之漸。(2) 嚮外界宣示,李璟是他的繼承人。李昪處理如此重大問題的關鍵時刻,用宋齊丘輔助李璟,可算是十分信賴了,卻就在這個時候,宋齊丘開始結黨。
李昪“歸老金陵”,意謂他完全控制了楊氏吴國政權,取代的形勢已經造成。李昪於太和三年十二月扺達金陵,便積極推動“傳禪”的上演。
(1) 擴建金陵城垣。李昪進入金陵,便擴建城垣,次年八月告成,周圍二十里。封建時代的城池,都是政治統治中心。金陵,龍盤虎踞,既是政治中心,又是軍事重鎮。李昪在作升州刺史的時候,曾經擴建過一次城垣,現在更加擴大,把它建成大而固的政治、軍事堡壘,與吴國京城——廣陵隔江對峙,造成一種勢態,威脅吴主楊溥,迫使楊溥讓位。
太和五年(933) 五月,宋齊丘勸李昪徙吴主都金陵。李昪不得不在金陵營建宫城,自己住入私第,“虚府金以待吴主”,宋齊丘這一着,使李昪陷於被動,幾乎掀翻李昪的老窩。
(2) 宋齊丘公開阻止“傳禪”,拖延歲月。《通鑑》説:“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吴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悦,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為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色髭,嘆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 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吴主,且告齊丘。齊丘以宗先己,心疾之,遣使馳詣金陵,手書切諫,以為天時人事未可,知誥愕然。後數日,齊丘至,請斬宗以謝吴主,乃黜宗為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勲、行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為都押牙。”①《通鑑》卷二七九“後唐潞王清泰元年二月”,第9103—9104 頁。
(3) 宋齊丘説景通的壞話,威稱景遷之美。馬令《南唐書·宗室·楚王》説:“宋齊丘參決時政(在廣陵輔佐景通——筆者),多為不法,輙歸過於元宗(即李景通——筆者),而盛稱景遷之美。”“烈祖於是召元宗至全陵,授鎮海節度副使,即以景遷為太保、平章事,代秉國政,有奪嫡之漸。”
(4) 宋齊丘薦陳覺為景遷教授,以賈聲價。“宋齊丘每忌元宗,欲自結景遷,乃薦陳覺為景遷教授,以賈其聲聞。”②馬令:《南唐書》卷七《宗室·楚王景遷》。
宋齊丘自從進入李昪幕府,便一心慫恿,支持李昪取代楊吴;現在,李昪在實現禪代之際,宋齊丘一反往昔,起來阻撓反對,而且要更换李昪安排的接班人。
宋齊丘此舉的目的十分明白:第一步控制幼君;第二步侵權、專權,步徐温、李昪後塵,最後取而代之。這時,李昪的朝廷還没有建立,宋齊丘就在打算奪取李昪的“國家”了。
宋齊丘推薦陳覺為景遷教授,出自個人野心,抱有政治目的,所以文瑩、馬令説他的行為是“樹朋黨”。後來,陳覺真的成了宋齊丘的黨羽,其地位僅次於宋齊丘。故宋齊丘舉薦陳覺為景遷的教授的行為便是宋齊丘結黨的開始。
南唐宋齊丘結朋黨與前代和後世情況都不同:無論漢、唐或宋、明的朋黨,都是人們在政治上發生了分歧之後,相同政見的人逐步集結起來,形成對立的政治派别,展開鬥争。而宋齊丘則先有個人野心,單方面集合黨與,樹立朋黨,運用它去實現既定的政治目的。所以馬令説:“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入輔政,委齊丘左右之,齊丘於是益樹朋黨,潜自封殖。”③馬令:《南唐書》卷二十《宋齊丘傳》。
二、南唐朋黨的組織——小人有黨,君子未嘗有黨
南唐朋黨的存在,赫然如陣雲。“凡文武不同,皆布朋黨。”④同上。骨幹分子“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⑤陸游:《南唐書·江文蔚傳》載“對仗彈奏”。炙手可熱。另外一批官僚則把他們視為寇仇,形同水火。兩派尖鋭地對立着。南唐政界的這兩種人,馬令把他們劃分為小人黨與君子黨。既然有兩個黨存在,每個黨總得有個頭。誰是頭? 按照馬令的意見,宋齊丘是小人黨(下文簡稱宋黨) 的頭,孫晟是君子黨(下文簡稱“孫黨”) 的頭。
《通鑑》説:“宋齊丘待陳覺素厚,唐主亦以覺為有才,遂委任之。馮延巳、延魯、魏岑,雖齊邸舊僚,皆附依(陳) 覺,與休寧查文徽更相汲引,侵蠹政事,唐人謂覺等為五鬼。”①《通鑑》卷二八三“後晋齊王天福八年三月”。馬令《南唐書·馮延巳傳》也説:“ (延巳) 與陳覺友善,自結於宋齊丘以固恩寵。”陳覺、馮延巳、延魯兄弟、魏芩、查文徽、李徵古等,後來都是南唐的高級官員,他們一致拱衛宋齊丘,所以,宋齊丘為宋黨的頭,可以作為定論。
宋齊丘是一個特殊人物,在南唐政權中佔有特殊地位,宋黨人士把他稱作“造國手”,在南唐官僚中有很大的號召力,“順風一呼,而肩摩踵接,唯恐其不容”,“望風塵而投欵者,至不可數計”②《釣磯立談》第17 條。。經過幾年的活動,宋黨便形成了。李昪建立南唐之初,侍御史張義方提出:“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③陸游:《南唐書·張義方傳》。這不是無的放矢。張義方鋭敏地觀察到南唐朋黨的存在及其危害,因之提出侍御史應該加以糾彈。到升元末年,“宋喬丘廣樹黨羽,以張聲勢”④馬令:《南唐書》卷二十一《李徵古傳》。。宋黨又有很大發展,成為一個擁有人數可觀的政治團體了。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宋齊丘領尚書省用人一事得到印證。馬令《南唐書·宋齊丘傳》説:
……中外繁劇之務皆在尚書省。(宋) 乃求知尚書省事,(李昪) 亦許之。於是悉取朝廷附己者分掌六司,下及胥吏,皆用所親吏。
宋齊丘作尚書省長官,整個尚書省上從尚書令,下至亭長,掌故之類胥吏全是宋齊丘的黨羽。按《新唐書·百官志》所載尚書省官員胥吏共1274 人,這是全國性中央行政機構。割據江淮地區的南唐小朝廷當然不能與之相比,就算南唐尚書省官員胥吏總數衹有唐代的八分之一吧,也該有159 人。試想,要在很短時間内從全部黨羽中挑選出159 個適合尚書省各種職位的人,其間必有大量的組織工作。首先,要掌握全部黨羽的名單、情況;其次,要做好上述工作,必須有一批人做管理工作;第三,招之即來,有一定的組織性。因此,可以看出:宋黨不僅人數不少,而且是一個有相當組織性的政治團體。
另一派的頭是誰? 馬令認為是孫晟。孫晟,高密(治今山東高密) 人,後唐宣武節度使朱守殷的判官①此本《通鑑》與兩《五代史》,馬令《南唐書·孫晟傳》、龍衮《江南野史·孫忌》同,陸游《南唐書·孫忌傳》謂孫晟(又名忌) 事秦王李重榮,與諸書異。。朱守殷叛變失敗,孫晟南奔,投吴國權臣李昪。李昪“喜其文詞,使出教令”②陸游:《南唐書·孫晟傳》。,深得信任,參與禪代密計。南唐建,官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元宗朝,為右僕射。孫晟算得上資深官僚,有資格做孫黨的頭。但是,孫晟為人“孤剌”,“獨介自守,不接見賓客,生平所不喜者,惡之不能忘。其與宋齊丘、馮延巳輩,幾如不同天之仇”③《釣磯立談》第23 條。。“鐵石心腸,落落以忠赤自許。至其論人材,則門下蓋如掃焉。”④《釣磯立談》第29 條史叟語。像這樣的人是不能做政治集團的領導人的。升元七年(943) 二月,烈祖李昪死,孫晟恐怕馮延巳等人用事,孫晟“欲稱遺詔令太后臨朝稱制”⑤《通鑑》卷二八三“後晋齊王天福八年二月”,第9245 頁。。在封建時代,這是一樁政治大事,身為中書侍郎的孫晟當然知道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更重要的是:這一舉動是針對馮延巳等人的,也可以説是針對整個宗黨的。而孫晟竟單槍匹馬,一個人出戰;在所有材料中看不見孫晟與其同黨商量痕迹,更説不上組織同黨一齊下手。要是孫晟是“孫黨”的頭,對於這類重大事件,内部應當商量,組織力量,共同去完成,纔是正道。從這個事例可以看出孫晟不能做孫黨的頭,也不是孫黨的頭。
孫黨中,其他如常夢錫、江文蔚、韓熙載、蕭儼等,都是激進分子,抨擊宋黨相當猛烈,又都是資深官僚,有資格充當孫黨的頭。但是,從他們的表現看來,都不是。常夢錫很有人望,而“剛褊少恕,每以直言忤物”。“每公卿集會,輙喑嗚大咤,驚其坐人,以故不為時所親附。”⑥陸游:《南唐書·常夢錫傳》。江文蔚“秉心貞亮。不容阿附”。當其對仗彈奏,在上疏之前,“先具小舟,載老母,以待左遷”⑦陸游:《南唐書·江文蔚傳》。。韓熙載“雖才識優贍,而質性疏散,凡在位者,道不復同。於是深居移病,罕與朝謁”⑧徐鉉:《徐公文集》卷十六《唐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旨昌黎韓公墓志銘》。。蕭儼“無文而辭繁碎”⑨馬令:《南唐書》卷二十《宋齊丘傳》。。他們這些人個性狂狷,與孫晟同屬一個類型。像這樣的人是難以充當政治團體的領袖的,特别是在現存材料中没有反映他們任何一位曾經組織領導與宋黨進行鬥争的痕迹。所以,孫黨没有頭,衹是站在宋黨對立面的一些反對派官僚,如同一盤散沙,説不上政治集團。(為了行文方便,下文仍將反對宋黨的官僚稱為“孫黨”。)
雖然,從組織的角度看孫黨,它並不存在,但是,畢竟有批人,“群臣敢言者:常夢錫、蕭儼、江文蔚、韓熙載等十數人”⑩同上。與宋黨長期堅持不懈地進行鬥争。實際上和他們站在一起的還有徐鉉。他對宋黨的鬥争,不屈不撓,自比漢代的朱雲①《徐公文集》卷三《陳覺放還,至泰州,以新詩見寄,作此答之》有云:“朱雲曾為漢家憂,不怕交親作世仇。”以至“滿朝權貴皆曾忤”②同上書:《貶泰州,出城作》。,還有張易“面斥奸臣,不畏强禦。傾邪者見之而屏息,黨錮者聞之而銷聲”③《全唐文》卷八七五。陳致雍:《諫議張易謚議》。。再如喬匡舜“除奸深係念,致主迥忘身。諫疏縱横上,危言果敢陳”④《全唐詩》卷七四八。李中:《獻喬侍郎》。。還有嚴續、趙宣輔都可能是“孫黨”的成員與支持者。他們以道義相許,有是非觀、正義感,政治立場相同。因為没有明確的組織,不能有計劃、有目的進行活動,所以在鬥争中,不能集中力量,旁人看起來好像一些人在瞎起哄。如龍衮所説:“當齊丘秉政蒞任,皆斥腐儒鯫生,聲洿行穢,故不大用。及位已崇峻,由於哆於頰,背憎面贊,群誣黨議,十舌百喙。”⑤《江南野史·宋齊丘》。這便是龍衮眼裏的孫黨在南唐朋黨鬥争中的情景。
宋黨則相反。他們上下齊心,内外結合,對“孫黨”的打擊頗有力度。江文蔚説:
……與酷吏司馬正彝同惡相濟,迫脅忠臣……枉法竄逐。群兇勢可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南唐軍隊在福州城下慘敗) 周行之中,有敢議論,則馮、魏毁之於前,正彝持之於外,搆成罪狀,死而後已⑥陸游:《南唐書·江文蔚傳》。。
馬令説:
凡文武百司,皆佈朋黨,每國家有善政,其黨輙但言宋公之為也;事有不合群望者,則曰不用宋公之言也。每舉一事,必知物議不可,則群黨競以巧詞先為之地,及有論議者,皆以墮其計中⑦馬令:《南唐書》卷二十《宋齊丘傳》。。
宋黨的黨與遍佈南唐境内,又能上下齊心,内外結合,便足以説明其規模與力量了。所以張易説:“群小構扇,其禍不細。”⑧馬令:《南唐書》卷七《宗室·景達傳》。“孫黨”面對這樣的政敵,總是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直道未能勝社鼠!”⑨《徐公文集》卷二《寄蘄中高郎中》。徐鉉無可奈何地發出這樣的嘆息。故馬令説:“世衰道喪,小人阿附以消君子,而君子小人反類不合,故自小人觀之,因謂之黨羽,而君子未嘗有黨也。”⑩馬令:《南唐書》卷二十《黨與傳·序》。為行文方便,下文仍將宋黨的反對派稱為“孫黨”。
三、南唐朋黨鬥争的實質
南唐朋黨兩個派别與意見分歧,在烈祖李昪升元末年已經明朗化,鬥争也就開始了。“孫黨”對宋黨的鬥争,總是理直氣壯、點名道姓地斥責宋黨人士為小人險夫,其行為將為國家大害。宋黨並不示弱,報以重拳。雙方尖鋭對立,不共戴天。那麽,他們的分歧是什麽? 鬥争的目的安在?
升元末年的一天,中書侍郎孫晟登門拜訪宋黨的頭頭宋齊丘。孫對宋説:
君侯以管樂之才,當阿衡之地,好惡舉動,不可不審。且人主所與共心者,近則法從數君子,遠則七人之列與三院御史,皆繩愆糾謬之任;又勸講金華,所以開發上聽;羽儀儲宫,所以隆國本:皆須搜擇碩德,其性方整,重質有守,而不回邪之人。此日所除,群聽尚且不愜,將復何所冀邪!①《釣磯立談》第27 條。馬令《南唐書》卷十五《陳陶傳》:“陳陶,世居嶺表,以儒業名家……升元中,至南昌,將詣建康,聞宋齊丘秉政,凡所進擢,不愜士論,自料與齊丘不合,乃築室於西山……會宋齊丘出鎮南昌,陶志不屈,而齊丘亦不為之薦辟。”
孫晟認為,宋齊丘所使用的人都屬於回邪一類。回邪,乖戾邪辟。“回邪之人”就是不正派的人。宋齊丘任用回邪之人,佈在朝廷上下,特别是在皇帝、太子周圍造成特異的政治氛圍,猶如設置了一個染缸。凡是被投入染缸的,顔色都要變,染於蒼則蒼,染於黄則黄。孫晟用墨翟的話説,舜、禹、商湯、周武的輔佐都是賢人,“所以染當,故王天下”。夏桀、殷紂、周厲王、周幽王重用壞人,“所染不當,故為天下僇”。孫晟進一步指出:南唐皇帝、太子左右是一些“小人險夫”,“政當有敷受之垢,或可以移乾剛之斷”。要是把南唐弄到那個地步,你宋齊丘“方將挈其契領,無所及矣”②《釣磯立談》第27 條。。
孫晟察覺宋黨花很大工夫嚮皇帝、太子施加影響。皇帝李昪深沉寬裕,天資明察,宋黨方面的影響起不了多大作用。對太子李璟,則甚為擔憂。歷代的統治者都認為太子是國家的根本,把太子培養成什麽樣的人,關係着某姓王朝是否能够維持與昌盛。自從李昪控制吴國大權,賡即着手選擇培養自己的繼承人。李昪和宋黨從不同角度看重這個問題。宋齊丘推薦陳覺為景遷教授於前,幾有奪嫡之漸;李昪使馮延巳與李璟游處於後,潜移默化。孫黨人士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
馮延巳少有文雅的美譽,李昪用他為校書郎,使他與李璟游處。李璟為元帥,又任馮延巳為元帥府掌書記。馮延巳利用游處之便,嚮李璟灌輸聲色犬馬一類享樂腐化思想、生活方式,潜移默化,消磨他的上進意志。宋黨人士用心多麽深刻! 孫晟當面嚮馮延巳指出:你的這種做法:“適為國家之禍!”①《通鑑》卷二八三“後晋齊王天福八年二月”,第9245 頁。點出了馮延巳的邪惡本性與用心,“延巳失色,不對而起”②《釣磯立談》第11 條。。對此,史叟議論道:“ (馮) 所養不厚,急於功名,持頤竪頰,先意希旨,有如脂膩。其入人肌理也,習久而不自覺,卒使烈祖之業委靡而不立。夫然後知孫丞相(孫晟——筆者) 有先知之明。世之議者,乃指以為由忮心而發,豈其然邪?”③同上。
宋黨人士的政治品質低劣,用心不正,可能李昪没有察覺,“孫黨”則認為非常嚴重。周詳慎密的常夢錫在升元末年,“歷言宋、陳、馮、魏(岑) 輩奸佞險詐,不宜置左右”④《玉壺清話》卷十《江南遺事》。,司門郎中判大理寺蕭儼表稱“陳覺奸回亂政”⑤《通鑑》卷二八三“後晋齊王天福八年二月”,第9245 頁。。
孫晟、常夢錫、蕭儼都是李昪器重的士人。他們看見宋黨勢力坐大,上層人士身居高位,把皇帝、太子包圍起來,把皇帝、太子不知不覺地投進染缸,被宋齊丘等人拖上邪路,最終“為天下僇”。他們公忠體國之情,溢於言表。常夢錫、蕭儼的進言,李昪深以為是,準備有所舉措,可是,李昪旋即發病,來不及清理宋齊丘等人的過錯,便與世長辭了。
元宗襲位,南唐朋黨鬥争立即升温。保大十多年間,兩派鬥争連綿不斷,貫穿元宗整個執政年代。滋舉幾件大事,以觀雙方的思想、立場。
(1) “孫黨”先發制人。《通鑑》説:
(烈祖李昪殂) 中書侍郎孫忌(即孫晟) 恐馮延巳等用事,欲稱遺詔令太后臨朝稱制⑥同上。。
孫晟的鬥争鋒芒直指李璟即位前的東宫舊僚——宋黨如馮延巳、延魯、魏舉,還有陳覺、李徵古都是李璟做太子時的舊僚。按照中國封建社會的慣例,潜邸舊僚在故主襲位之後都會得到重用,故孫晟想利用宋太后(李璟的生母) 臨朝稱制,牽制新君,阻遏馮延巳等人挾新君命令朝臣,防止南唐君權旁落於宋黨之手。此説一出,馬上遭到翰林學士李夷鄴的堅決反對,宋太后本人也不贊成,於是太后臨朝稱制便告擱淺。孫晟的發難戛然而止。
(2) 宋黨搶權,排斥“孫黨”。元宗登位,立即以“鎮南節度使宋齊丘為太保兼中書令,奉化節度使周宗為侍中”①《通鑑》卷二八三“後晋齊王天福八年二月”,第9246 頁。。宋齊丘回到金陵,黨羽們麕集在他的周圍,積極投入鬥争。他們的鬥争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方面,宋黨骨幹分子從元宗那裏攫取高官要職。在保大元年(943) 之内,馮延巳從元帥府掌書記升至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馮延魯從禮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勤政殿學士,陳覺為光政殿副使、太僕卿,魏岑、查文徽為樞密副使。第二個方面,打擊反對派官僚。常夢錫本是元宗要重用的人,也是元宗即位後第一個被召見的大臣,元宗許諾用他做翰林學士,“齊丘黨疾之,坐封駮制書,貶池州判官②《通鑑》卷二八三“後晋齊王天福八年三月”,第9248 頁。《徐公文集》卷二十《常夢錫行狀》説得更明白:“今上(元宗) 嗣位,恩禮甚優。公以發號之初,四海瞻望,幾微所慎,宜在斯時,盡規極言,如恐不及。於是大忤權貴,貶佐池州。”。元宗即位後一個月,就罷宰相李建勲為撫州節度使,由於“東宫官屬稍稍侵權”③馬令:《南唐書》卷十《李建勲傳》。,周宗與宋齊丘同時入相,“中書令宋齊丘廣樹朋黨,百計傾之”④《通鑑》卷二八三“後晋齊王天福八年十二月”,第9257 頁。。可見宋黨勢力之大,竭力排斥孫黨。次年正月,侍中周宗被黜為鎮南節度使。與周宗同時罷黜的還有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居詠。這是保大二年及三年初的情況。保大四年,因南唐對閩國戰争的勝利,宋黨的查文徽被任為撫州刺史;馮延魯被任為永安節度使監軍;“歸隱”九華山的宋齊丘,經陳覺等的活動,又被召回金陵,任為太傅兼中書令,封衛國公;馮延巳為中節待郎平章事。
(3) 隔絶中外,架空元宗。宋黨利用李璟在繼承帝位中的矛盾心理—— “緣烈祖意”,要將帝位傳給景遂——包圍元宗,架空元宗,造成宋黨少數頭目專權的形勢。
(保大二年正月) 唐主決欲傳位於燕(景達),齊(景遂) 二王。翰林學士馮延巳等因之欲隔絶中外擅權。辛巳,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僚唯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國人大駭⑤《通鑑》卷二八三“後晋齊王開運元年正月”,第9261—9262 頁。龍衮《江南野史》卷四《宋齊丘》載宋齊丘上書反對“敕諭”不可信。。
馮延巳等東宫舊僚用事,孫晟曾經擔心,一年不到,問題果然出現了。這道敕書的出臺,顯然是宋黨幕後活動的結果。後來,御史中丞江文蔚指出:常夢錫被貶,“奸臣得計,欲擅威權,於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勅公卿庶,僚不得進見。履霜堅冰,言者恟恟”⑥陸游:《南唐書·江文蔚傳》載對仗彈奏。。事關重大,“孫黨”的“蕭儼上書極論曰:元帥開府,人猶驚駭,況委之大政,而群臣不得時見,臣恐中外隔絶,奸人得志,非陛下之利也”⑦馬令:《南唐書》卷二《嗣主書》。。書奏不報。侍衛軍虞候賈崇叩閣求見,重申危害,元宗收回成命①馬令:《南唐書》卷二《嗣主書》云:“侍衛軍都虞候賈崇詣閣求見,曰:‘臣事先朝二十餘年,每見延接疏遠,未嘗壅隔,群下之情,罔有不達。今陛下即位,所委任者何人,而頓與群臣謝絶,深居邃處,而欲聞民瘼,猶惡陰而入乎隧道也。臣老矣,長不復奉顔色。’”,馮延巳等人的陰謀纔未能得逞。
(4) 罷宣政院。宋黨的行為,可能引起了元宗思考。“天子(元宗) 以典司誥命,最宜親密,乃别置宣政院於内庭。”②《徐公文集》卷二十《常夢錫行狀》。將貶在池州的常夢錫召回金陵,充翰林學士,專掌宣政院。這樣做,雖然是遏制宋黨,“而魏岑已為樞密副使,善迎合,外結馮延巳等相表裏。夢錫終日論争,不能勝,罷宣政院”③陸游:《南唐書》卷二十一《魏岑傳》。,宋黨又勝利了。
(5) 逼迫元宗交權。
保大十三年(955) 十一月,後周的討伐大軍突然臨於淮上。南唐軍隊屢屢敗北,至後周顯德五年(958) 五月,割長江以北十四州與後周成平,用顯德年號,淪為後周附庸。“嗣主……神情躁撓,慌悸不安。”④《江南野史》卷四《宋齊丘》。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灾。’ 唐主乃曰:‘禍亂方殷,吾欲釋去萬機,棲心冲寂,誰可以托國者?’”李徵古接着説:
宋公,造國手也,陛下如厭萬機,何不舉國授之!
陳覺從而附和:
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等時入侍,談釋、老而已⑤《通鑑》卷二九四“後周世宗顯德五年十一月”,第9589 頁。。
李璟臨於危難境地,宋黨認為奪權的時機已到,乾脆伸手摘下李璟頭上的皇冠。中書舍人陳喬排閤而入,對李璟説:
臣聞社稷之重,焉可假之他人,今且授之,則百官朝請,皆歸齊丘,一民尺土,非陛下所有,尚能制齊丘而再有之乎? 臣見淖齒、李兑復作,而讓皇幽囚於丹陽,亦
陛下之所親見,一日垂涕,求為田舍翁,不可得矣①馬令:《南唐書》卷十七《陳喬傳》。淖(nào) 齒,戰國時楚國人,入齊。《戰國策·楚策》:“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李兑,戰國時趙國人。趙武靈王立小兒子為王(是為惠文王),用李兑為相。四年後,大兒公子章作亂,李兑起兵拒之,公子章死,李兑等遂圍趙武靈王於沙丘宫。“主父(即武靈王) 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雀) 彀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宫。”(《史記》卷四十三《趙世家》) 讓皇,吴睿帝楊溥。天祚三年(937) 八月禪位給齊王徐知誥(李昪),李昪册他為讓皇帝。升元二年(938) 四月,李昪遷楊溥及其子孫於海陵,嚴兵守之,絶不通人。。
宋齊丘等打的這個主意,確實包藏禍心,陳喬鑿穿他們的詭計。交泰元年(顯德五年,958) 十二月,元宗纔決心處理宋齊丘及宋黨骨幹分子:科宋齊丘以“賣國”罪名②《江表志》中。,允許歸九華舊隱,最後,幽死;陳覺、李徵古賜死;所有宋齊丘黨羽一律不問。
從朋黨鬥争的歷程看來,鬥争的實質是體國與窺竊。所謂體國,即保護南唐李氏的統治,“孫黨”努力所為。所謂窺竊,就是從李璟手中把統治權逐步奪過去,據為少數宋黨骨幹所有,最後取而代之。南唐的朋黨之争,對李氏統治産生了巨大的負面作用。吴任臣論道:“陳覺等六人,皆宋齊丘黨也。蟠據中外,遞相柄任,率與正人為仇,兵連禍接。故唐時牛、李兩黨動摇國是,區區江南,不務遠略,而仍尋往轍,國隨以亡。嗚呼,豈不悲哉!”③《十國春秋》卷二十六陳覺等六人傳論。論者以為南唐朋黨之争,是南方與北方兩派政治勢力的地區利益的矛省所致,顯然與事實不符。
南唐淪為後周附庸,疆土迫促,國勢日危,從南方强國一蹶而為弱小之邦。宋齊丘與一些骨幹分子的死亡,專權、篡權的可能也不復存在,大規模的朋黨之争也就基本結束了。
四、元宗袒宋
宋黨敢於那麽猖獗,抱着控制新君、侵權當權、最後奪權的目的,一次又一次地掀起黨争,事實證明宋黨的行為是錯誤的。其中詳情,元宗當然情楚,應該認識到宋黨對南唐的危害。但是,元宗對他們很信任,在朋黨鬥争中,總是袒護他們。元宗處理福州之役的肇事者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福州之役是陳覺背着元宗擅自發動的,動員兵力是南唐開國以來最大的一次,結果南唐軍隊大敗於福州城下。由於陳覺、馮延魯僨事,元宗大怒,派人去軍中就地處決,旋又命令將二人鎖歸金陵,聽候處置。御史中丞江文蔚指責他們的罪行説:
馮延巳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聰,斂怨歸上。……作威作福,專任愛憎,咫尺天威,敢行欺罔。……傷風敗俗,蠹政害人……
天生魏岑,道合延巳,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逋逃歸國,鼠姦狐媚,讒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巳,遂當樞要。……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
岑與覺、延魯更相違戾,互肆威權,號令並行,理在無赦①陸游:《南唐書·江文蔚傳》。。
江文蔚對仗彈奏在陳覺、馮延魯鎖歸金陵聽候處理的時候。他以為陳覺、馮延魯必遭誅戮,又歷數馮延巳、魏岑罪過,要求元宗“軫慮殷憂,誅鋤虺蜮”。所謂“虺域”,就是两兇——陳覺、馮延魯。
宰相馮延巳、太傅兼中書令宋齊丘從中緩頰,元宗免了陳覺、馮延魯的死罪,改為貶官流放。員外郎韓熙載切諫:
臣觀覺等,罪不容誅,但齊丘、延巳因為陳請,所以得全。且擅興者無罪,則疆場生事,喪師者獲存,則行陳解體,請行誅戮,以重軍威②馬令:《南唐書》卷二《嗣主書》。。
這些指責和要求是完全正確和正當的。元宗不僅不傾聽反對派的讜論,反而替陳、馮曲為辯解,親筆批答説:“陳覺之行,實太傅之舉矣。及師敗之後,事下有司,太傅無救拔之詞,有自訟之表,得不再思。何者! 先朝舊臣,國家元老,不唯舉人偶失,可得興言,直是謀之不臧,亦未有加罪之理……彼二子(陳、馮),孤若懷憤悱之意,戮之久矣。此際長流遠郡,斥為庶人,五木被身,一家狼藉,永從流放,與死何殊! 卿等憂國情深,除姦意切,諸所徵引,批譽未殫。”③《徐公文集》附録:《宋故金紫光禄大夫左散騎常侍上柱國東海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責授静難軍節度行軍司馬徐公七十六行狀》。
相反,元宗對“孫黨”又是另一種態度:貶江文蔚為江州司士參軍;“韓(熙載) 之至言,當自為體國而發”④《釣磯立談》第12 條,史叟語。,被宋齊丘誣為“酒狂”,貶和州司士參軍。
又如處理白水塘事件的特使徐鉉。南唐為了給養軍隊,大興屯田,“吏緣為姦,强奪民田以為屯田,江淮騷然”⑤陸游:《南唐書·元宗紀》。。元宗命徐鉉前往察訪,“一如親行,可興可廢,悉以便宜從事後奏”。徐鉉先到楚州,將“楚州應非理遷入屯田”之産業,盡還本户。百姓讙譁感泣,如釋狴犴。再到常州,也照此處置。“協比衆惡之徒,構以擅作威福。”元宗立即召回徐鉉,待罪私第,“蒼蠅貝錦,膠固組織,詰難問狀,不容自理,鍛煉深刻,將置大辟”。最後,元宗“特屈彝章,長流舒州”①《徐公文集》附録:《宋故金紫光禄大夫左散騎常侍上柱國東海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責授静難軍節度行軍司馬徐公七十六行狀》。。
又如派遣堅決反宋黨的張易出使契丹,希望他在航海中淹死。“易當使海東,王(李景遂——筆者) 驚,促入白上,以為:‘朝臣如張易者不可多得。奈何遠使,使之冒犯風濤也。’ 上曰:‘無憂也,如易之為人,海神豈敢侮之耶。’”②《釣磯立談》第25 條。務欲置之死地。
又如淮甸之役,兩軍交戰之中,元宗派遣出使後周的官員都是“孫黨”或反宋的人。保大十四年(956) 正月,劉彦貞敗於正陽。二月,南唐軍敗於清流關下,滁州失守,接着揚州、泰州又被攻下,形勢十分危急。三月,元宗以右僕射孫晟為司空,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去見周世宗。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時馮延巳為尚書左僕射,位在孫晟上,故孫稱馮為左相——筆者) 晟若辭之,則負先帝。”③《通鑑》卷二九三“後周世宗顯德三年三月”,第9545—9546 頁。孫晟竟被殺戮。
在遣孫晟之前,元宗已派翰林學士、户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鍾、李屬於反宋官員——筆者) 奉表稱臣、求和。“唐主復使李德明、孫晟言於上(周世宗——筆者),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 (世宗欲盡得江北之地) 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威,願寬臣五日之殊,得歸白唐主,盡獻江北之地。上許之。’”李德明回到金陵,勸元宗盡割江北之地。元宗不悦,“宋齊丘以割地無益……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惡德明與孫晟,使王崇質異其言,因譖德明於唐主曰:‘德明賣國求利。’ 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④同上,第9544 頁。。元宗、陳覺、李徵古等堅決反對割江北十四州。至保大十五年(957),後周軍攻下壽州城,繼續進攻,不斷取得勝利。交泰元年(958) 三月(壬午朔) 辛卯,周世宗入迎鑾鎮(在長江北,屬揚州)。“唐主……乃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翼,使聽命於中國。……丙申,覺至迎鑾。見周兵盛,白上,請遣人渡江取表,獻四州之地(時淮南之地,後周已克十州,唯廬,舒、蘄、黄四州還屬南唐佔有,現在陳覺擅作主張) 劃江為界,以求息兵,辭指甚哀。”世宗允許了,陳覺“請遣其屬閤門承旨劉承遇如金陵”取表。“唐主復遣劉承遇奉表……請獻江北四州(江北十四州全歸後周),歲輸貢物十萬。”⑤《通鑑》第二九四“後周世宗顯德五年三月”,第9580—9581 頁。
從這些事件中,可以看到元宗對朋黨兩方的不同態度,是何等鮮明。
元宗袒宋,壓制“孫黨”,助長了宋黨的囂張氣燄,到淮南喪失,纔感到自身的弱小與後周的威脅。“建康與敵境隔江而已,又在下游,敵兵若至,閉門自守,藉使外諸侯能救國難,即為劉裕,陳霸先耳”①馬令:《南唐書》卷四《嗣主書》“顯德六年”條。,於北宋建隆二年(961) 遷都南昌,憂愁而死。
元宗袒宋,自食惡果,至死也没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常夢錫“嘗與元宗苦論齊丘輩,元宗辯博,曲為解釋,夢錫詞窮,乃頓首曰:‘大奸似忠,陛下若終不覺悟,家國為墟矣!’”②陸游:《南唐書·常夢錫傳》。
元宗性格“柔和”,或者説“仁懦”,喜歡臣下阿諛。當其襲位之初,宰相李建勲説過這樣的話:“主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習性未定,苟旁無正人,但恐終不守先帝之業。”③《通鑑》卷二八三“後晋齊王天福八年三月”,第9248 頁。李璟襲位,已經二十八歲,“春秋鼎盛,留心内寵,宴私擊鞠,略無虚日”④《南唐近事》。。這就是“習性未定”的具體表現。東宫舊臣馮延巳之流以聲色犬馬引誘,宋齊丘、馮延巳、馮延魯、魏岑之輩以拓境蠱惑,李璟愛之好之,自然不知其非。范祖禹説:“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異,故其去小人也難,遠君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忤旨,則終身擯斥。盧杞、裴延齡之徒,至死而念之不衰,迫於死亡,不得已然後去之,君子則於其不可去而逐之矣。夫賢之與佞,正之與邪,聽其所言,觀其所行,亦足以知之矣。德宗反而易之,豈惡治而欲亂哉? 蓋其性與小人合也。”⑤《通鑑·德宗(中)》。這段話用來評議李璟也是合適的。
五、鄙哉,斯人也
宋齊丘之於南唐,一方面是宗臣,另一方面又是賣國賊。為什麽宋齊丘由南唐的宗臣變成了南唐的罪人?
雖然宋齊丘曾經真心實意擁護過李昪,可是宋是有政治野心的人,隨着地位的變化,私心的驅動,思想也就變了。
宋齊丘從南唐宗臣變為南唐的賣國賊,也不是偶然的,自有其思想根源與現實基礎。當時有兩個關於宋齊丘的傳説與他的思想轉變有密切關係:(1) 宋齊丘年輕時夢乘龍上天⑥《玉壺清話》卷十《南唐遺事》:“傳云齊丘少乘龍上天,至垂老猶抱狂妄,及國家發難,尚欲因其釁以窺覬,時年七十三矣。”馬令《南唐書·宋齊丘傳》:“相傳言齊丘少時嘗夢乘龍上天。……及國家之難,因欲遂其窺竊之計。”;(2) 宋在微時,相士説他有“貴不可説”的相貌⑦《南唐近事》:“宋齊丘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説’……”。這兩個傳説對具有檏素唯物思想的人來説都會嗤之以鼻的。但是,對某些人説,卻有特殊的、神秘的意藴。
龍是中國古代人們想象中的神物,屬於四靈之一,是神靈之精,後來人們把皇帝比作龍。三國吴人孫休“夢乘龍上天”,果然當了皇帝①分别見《後漢書》卷十七《馮异傳》及《三國志》卷四十八《吴書·三嗣主傳》。。“貴不可説”乃是勦襲蒯通遊説韓信“貴不可言”的陳詞。“貴不可言”,即是大貴,要成為最高統治者。
夢乘龍上天,有貴不可言的相貌,深深埋在宋齊丘的思想裏。作為一個普通人想當皇帝,簡直是狂妄。宋齊丘當其投狀姚洞天,“誠懇萬端,衹為飢寒二字”②《五代史補》卷二“宋齊丘投姚洞天”條。的時候,絶無這種非分之想。一旦政治地位發生變化,而且他親眼看見徐温、李昪奪權、掌權,他又是李昪奪權、掌權的得力幫手,洞知其中細節,自然想步徐温、李昪的後塵,認為下一輪權力的轉移,論天命就該輪到宋齊丘了,窺竊非望的思想便從此産生。“宋子嵩用意一變”的根源就在這裏。記載關於宋齊丘傳説的三個人都把傳説與保大十五年“宋公監國”聯繫在一起。審查他首樹朋黨的動機與窺竊非望的野心和行動,完全吻合。宋齊丘為了私利,不顧南唐的前途,不斷掀起鬥争,把富强一時、有希望統一中國的南唐,推入灾難的深淵。鄙哉,斯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