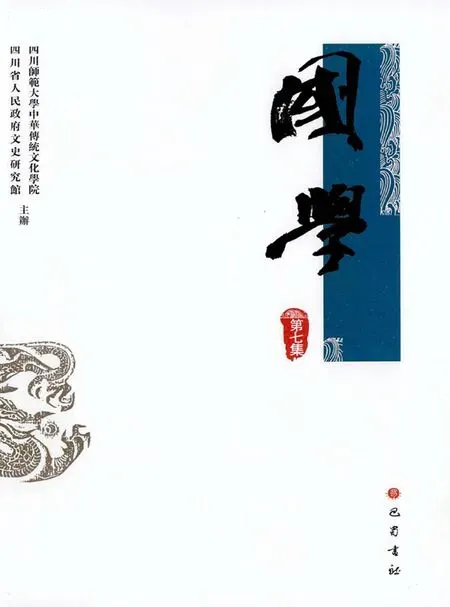先秦時期的重常史觀
王 燦
“常”和“變”,不僅在整個中國古代文化中常見,而且更是中國傳統歷史觀念中很常見的一組重要概念,因為這組概念是非常具有歷史意藴的。但是,對歷史中“常”與“變”的認識和理解,是先秦史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關於這方面,嚮來缺少專門研究。目前,僅僅有寥寥數篇涉及這方面的内容,而且範圍較為狹窄,僅僅關注了法家及其代表人物韓非的“常”“變”思想①參見王效峰:《常變之間:“聖王今王化”到“今王聖王化”——法家歷史觀再認識》,《理論月刊》2012年第7 期,第30—32 頁;邢靖懿:《韓非“常”“變”思想管窺》,《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5年第2 期,第68—71 頁。,更重要的是,它們也不是對先秦史學生活中“常”與“變”的專門研究。
一、《逸周書》的重常史觀
重視“常”,是先秦時期歷史觀的主流和重點。先秦時期的“重常”觀念非常豐富,有的直接體現在語詞上,有的則間接表現在思想内涵中。
先秦時期對“常”和“變”及其關係多有表述。首先,在先秦古籍中,有很多地方都提出要重視“常”,比較突出的就是《逸周書》。《逸周書》是先秦重要史學典籍。晁福林先生認為,《逸周書》“主綫是記載周文王、武王、成王時代的周王朝的開國史,並且是以問題述史的最早的史學著作,它開啓了先秦時代述事明理的一代史學著作風尚。《逸周書》的研究可以使人們窺見中國早期史學著作風貌的一個側面,對於研究先秦史官職守提供了寶貴的史料”①晁福林:《論〈逸周書〉 的史家主體意識》,《史學史研究》2009年第1 期,第36—41 頁。。《逸周書·史記解》的成書時代,一般認為是在春秋後期或者戰國初期②黄懷信先生從“ 《序》篇文字而考求”“其時代,大約在晉平公卒後的周景王之世”(黄懷信:《逸周書源流考辨》,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89 頁)。唐元發先生推斷《逸周書》的成書年代宜在戰國初期(唐元發:《〈逸周書〉 成書於戰國初期》,《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6年第6 期)。其他學者雖略有小異,但是其觀點仍基本認同《逸周書》大部分仍是春秋或者戰國時期成書。當然,成書時未必會改動原文,但是,《國語》成書也非一時所為,其記載的事迹及其用語亦未必是成書時語詞,但是,對成書時代不可確考的古籍,目前衹能如此大致劃定其範圍,因此,至少其成書和寫作年代可以作為一種參照。,其内容反映了先秦時期的各種生活和觀念,這是確定無疑的。這段話非常明確地表達了對“常”的重視:
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陽氏以亡。(《逸周書·史記第六十一》)
從上述引文可見,雖然《逸周書》指出“陽氏之君”因為“好變故易常”而亡(具體體現在他“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 其中心意思是從政治成敗的角度而言,但是,這裏的政治觀與歷史觀緊密相連(這也是中國古代尤其是先秦時期歷史意識强大的重要體現)。此處所謂“故”,應該就是指“延續已久的原來的做法或者習慣、職位”等等,而這裏毫無疑問表現出對過去(及“歷史”) 的尊重,這就是一種重視“常”的歷史觀。《逸周書》接着從具體事務上舉例指出無“常”的嚴重後果:
宫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宫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飢饉無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逸周書·史記第六十一》)
其實,《逸周書》的這種“重常”史觀,是建立在其對於整個人生和世界的認識基礎之上的。它指出:“天生民而成大命,命司德,正之以禍福,立明王以順之,曰:大命有常,小命日成,成則敬,有常則廣,廣以敬命,則度至於極。夫司德司義而賜之福禄,福禄在人,能無懲乎? 若懲而悔過,則度至於極。夫或司不義而降之禍,在人,能無懲乎?若懲而悔過,則度至於極。”(《逸周書·命訓第二》)
在這裏,“大命有常”的意思是因為“天”賦予了人類固有的“命”,這種“命”由於其“天賦”而具有了“常”的性質,因為“天”是“常”的。這種思想,與西方的《聖經》中人應該永遠與“造物主”保持一致、不背叛“造物主”所賦予的天性這一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逸周書》還進一步闡述説:“天有常性,人有常順,順在可變,性在不改,不改可因,因在好惡,好惡生變,變習生常,常則生醜,醜命生德。明王於是立政以正之,民生而有習有常,以習為常,以常為慎,民若生於中,夫習之為常,自氣血始。明王自血氣耳目之習以明之醜,醜明乃樂義,樂義乃至上,上賢而不窮,哀樂不淫,民知其至,而至於子孫,民乃有古,古者因民以順民。夫民群居而無選,為政以始之,始之以古,終之以古,行古志今,政之至也。政維今,法維古。頑貪以疑,疑意以兩,平兩以參,參伍以權,權數以多,多難以允,允德以慎,慎微以始而敬終,終乃不困。”(《逸周書·常訓第三》) 這一段的《逸周書》用非常嚴密的邏輯,從“天”之“性”到“人”“性”,順理成章地引出了對於“常”的看法。關於“常”,《逸周書》的這一段又分為兩個層次。一是人性論的層面:“人”由於“天”賦予的“常順”之“性”具有“不改”的特徵,所以要“因”;而人在生活中由於有“好惡”導致“生變”,故需有“明王”“立政以正之”“自血氣耳目之習以明之醜”,使民能“醜明乃樂義,樂義乃至上,上賢而不窮,哀樂不淫”。二是由人性論推演到歷史觀的層面:“民知其至,而至於子孫,民乃有古,古者因民以順民。夫民群居而無選,為政以始之,始之以古,終之以古,行古志今,政之至也。政維今,法維古。頑貪以疑,疑意以兩,平兩以參,參伍以權,權數以多,多難以允,允德以慎,慎微以始而敬終,終乃不困。”
至於上升到“國家”層面,同樣也應該是遵循“常”“度”:“故天之生也固有度,國家之患,離之以故;地之生也固有植,國家之患,離之以謀。故時之還也無私貌,日之出也無私照,時之行也順無逆。為天下者用大略,火之燀也固定上;為天下者用牧,水之流也固走下。不善故有桴,故福之起也惡别之? 禍之起也惡别之? 故平國若之何? 頃國、覆國、事國、孤國、屠國皆若之何? 故日之中也仄,月之望也食,威之失也陰食陽,善為國者使之有行。是彼萬物必有常,國君而無道以微亡。”(《逸周書·周祝第六十七》) 上文中對“度”與“故”和“常”的論述,都在强調要遵循已有的,為人民所習見、習知並習從的合理制度之意,而一旦不再遵循這些“常”“度”和“故”,就必然會造成社會和政治的大震蕩,所以,到最後的結論就是“萬物必有常,國君而無道以微亡”。
另一處的論述引用文王的話,對此做了大致相同的表述:“文王曰:‘吾聞之,無變古,無易常,無陰謀,無擅制,無更創,為此則不祥。’ 大公曰:‘夫天下,非常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國,非常一人之國也。莫常有之,唯有道者取之。古之王者,未使民民化,未賞民民勸,不知怒,不知喜,愉愉然其如赤子,此古善為政也。’”《逸周書·逸文十一》所謂“無變古,無易常”“無更創”,其實都是從立政角度指出應該尊重古代的成制,不要改變“古”和“常”,不要立意“更創”,這在史觀上就是典型的崇古和“重常”史觀。但是,在過去,二者經常被不加區分而混為一談。其實,從上引《逸周書》原文可見,二者雖聯繫緊密,卻並非一事。“古”强調的是“古代”,重在説明時間維度;而“常”强調的是“已經習為習見”,重在説明“為人們所習慣”之維度。至於“無更創”,更是强調要慎重考慮改變已有的、已經被人們所習見習知的古代制度,這似乎有“保守”之嫌,最易被從“進步論”的角度予以詬病,其實,我們更應該知道,並且人類的歷史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對制度尤其不要輕易改變,因為新制度建立往往會帶來更多的弊端,最怕的就是陷入當代學者用錢先生名字命名的這個“錢穆制度陷阱”①陳蔚:《不要陷入“錢穆制度陷阱”》,《社會科學報》2008年2月28日第3 版。。而人類歷史上發展最為穩健並至今對整個世界發揮最重大影響的英美文化,恰恰是一直遵循着經驗理性主義,慎言“更創”而穩步前進並取得了最為引人矚目的成就。而中國歷史上“更創”最為大膽的,恰是以“復古”為名而導致身敗名裂的王莽改革。因為,王莽改革名為“復古”,實際上,他是以一己之見强行改變當時人們已經習見習知的制度和習慣,所以導致民怨沸騰、官員棄職而去。因此,真正的“無變古”“無易常”,其實不是盲目“復古”,而是重在“無更創”。
“常”是對客觀形勢的應然判斷,所以它就因此具有了合理性:“大國不失其威,小國不失其卑,敵國不失其權……百姓咸服,偃兵興德,夷厥險阻,以毀其武,四方畏服,奄有天下,武之定也。”(《逸周書·武稱第六》)
正是因為“常”是符合客觀形勢的、有道理的、對“民”和“國”是有益的,所以,“常”應該被遵循,不能被違背:“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王乃召塚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於大庭,問罷病之故,政事之失,刑罰之戾,哀樂之尤,賓客之盛,用度之費,及關市之徵,山林之匱,田宅之荒,溝渠之害,怠墯之過,驕頑之虐,水旱之菑。……有不用命,有常,不違。”(《逸周書·大匡第十一》)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古”之事都可以成為“常”,“常”必須合乎“道”,這點,從《逸周書》的創作宗旨可以見到:“昔在文王,商紂並立,困於虐政,將弘道以弼無道,作度訓。殷人作教,民不知極,將明道極,以移其俗,作命訓。紂作淫亂,民散無性冒常,文王惠和化服之,作常訓。……成王既即政,因嘗麥以語群臣而求助,作嘗麥。周公為太師,告成王以五則,作本典。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徵以觀察之,作官人。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職來獻,欲垂法厥世,作王會。周公云殁,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謀守位,作祭公。穆王思保位惟難,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芮伯稽古作訓,納王於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晉侯尚力侵我王略,叔嚮聞儲幼而果賢,□復王位,作太子晉。王者德以飾躬,用為所佩,作王佩。夏多罪,湯將放之,徵前事以戒後王也,作殷祝。”(《逸周書·器服第七十》)
可見,如果在上者無道,就會由於在上者的榜樣作用,很容易使得“民”跟着陷入“無道”之“習”中,也就是説,“民散冒性無常”,因此文王纔會“將弘道以弼無道,作度訓”“文王惠和化服之,作常訓”。接着,《逸周書》還在同一篇章裏,同樣從消極角度談到了“常”的形成,那就是“積習成常”,所以纔“不可不慎,作銓法”:“民非后罔乂,后非民罔與為邦,慎政在微,作周祝。武以靖亂,非直不克,作武紀。積習生常,不可不慎,作銓法。車服制度,明不苟逾,作器服。周道於焉大備。”(《逸周書·器服第七十》)從上面的引文可見,“常”既然要符合“道”,也就具備了合“理”性和合“法”(此“法”是指對絶大多數人有益的法則) 性,因此纔不能隨意變更,而是要尊重。因為“常”的合理性,所以,能够達到“常”,是一種被追求的理想境界:“維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時候天視可監,時不失以知吉凶。”王拜曰:“允哉! 余聞在昔訓典中規,非時罔有恪言,日正餘不足。”(《逸周書·小開武第二十八》)
《逸周書》對於“常”的重視,還體現在對於歷史中“人”的修養上:“父子之間觀其孝慈……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酒以觀其恭,從之色以觀其常,遠之以觀其不二,昵之以觀其不狎,復徵其言以觀其精,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此之謂觀誠。……飲食以親,貨賄以交,接利以合,故得望譽徵利而依隱於物,曰貪鄙者也。質不斷,辭不至,少其所不足,謀而不已,曰偽詐者也。言行亟變,從容克易,好惡無常,行身不篤,曰無誠者也。少知而不大決,少能而不大成,規小物而不知大倫,曰華誕者也。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竊名者也。故曰事阻者不夷,時□者不回,面譽者不忠,飾貌者不静,假節者不平,多私者不義,揚言者寡信,此之謂揆德。”(《逸周書·官人第五十八》) 這些雖然是從“識人”的角度而言的,但是,如果從歷史的角度考察,實際上也是歷史人物評價中的“重常”觀。下面的言論也是强調對人有“常”德的重視:“下邑小國,克有耇老,據屏位,建沈人,罔不用明刑。維其開告予於嘉德之説,命我辟王,小至於大。我聞在昔有國誓王之不綏於卹,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罔不茂揚肅德,訖亦有孚,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於王所,自其善臣以至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獻言在於王所。人斯是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王用有監明憲,朕命用克和有成……命用迷亂,獄用無成,小民率穡,保用無用,壽亡以嗣,天用弗保,媚夫先受殄罰,國亦不寧。嗚呼! 敬哉! 監於兹,朕維其及,朕藎臣,大明爾德,以助予一人憂,無維乃身之暴皆卹。爾假予德憲,資告予元,譬若衆畋,常扶予險,乃而予於濟,汝無作。”(《逸周書·皇門第四十九》) 所謂“苟克有常”,在這裏是明確用“常”作為標準來對一個人的“德行”進行衡量的。從歷史的角度而言,就是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標準。
當然,對“常”的重視,還體現在《逸周書》的很多方面,政事即為其一,但是,這些政治規則的得出,其實就是對歷史經驗的總結。比如:“宗揜大正,昔天之初,誕作二后,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於少昊,以臨四方,司□□上天未成之慶。蚩尤乃逐帝,争於涿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説於黄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以甲兵釋怒,用大正,順天思序,紀於大帝,用名之曰絶轡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天用大成,至於今不亂。其在啓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今予小子,聞有古遺訓,予亦述朕文考之言,不易。……君乃命天御豐穡享祠為施,大夫以為資箴,太史乃藏之盟府,以為歲典。”(《逸周書·嘗麥第五十六》) 以上强調“昔天之初,誕作二後,乃設建典”“今予小子,聞有古遺訓,予亦述朕文考之言,不易。予用皇威,不忘祗天之明典,令□我大治”,其實都是從總結歷史經驗和遵循前人遺則的角度强調了遵守“常”的重要性。再如:“ ‘……何循何慎? 王其敬天命,無易天不虞。在昔文考,躬修五典,勉兹九功,敬人畏天,教以六則四守,五示三極,祗應八方,立忠協義乃作。……六則:一和衆,二發鬱,三明怨,四轉怒,五懼疑,六因欲。九功:一賓好在笥,二淫巧破制,三好危破事,四任利敗功,五神巫動衆,六盡哀民匱,七荒樂無别,八無制破教,九任謀生詐。五典:一言父典祭,祭祀昭天,百姓若敬;二顯父登德,德降為則,則信民寧;三正父登過,過慎於武,設備無盈;四譏父登失,脩政戒官,官無不敬;五□□□□,制哀節用,政治民懷。五典有常,政乃重開,内則順意,外則順敬,内外不爽,是曰明王。’ 王拜曰:‘允哉! 維予聞曰:何鄉非懷? 懷人惟思,思若不及,禍格無日。式皇敬哉! 余小子思繼厥常,以昭文祖之守定武考之烈。嗚呼! 余夙夜不寧。’”(《逸周書·成開第四十七》) 周公所言之“何循何慎”的“循”和“慎”的内容,他自己做了回答,就是“王其敬天命,無易天不虞”,而“無易”者,“守常”也。
但是,在《逸周書》裏,唯一認為“無常”的是“天命”:維王不豫於五日,召周公旦曰:“嗚呼! 敬之哉! 昔天初降命於周,維在文考克致天之命,汝惟敬哉! 先后小子,勤在維政之失,政有三機五權,汝敬格之哉! 克中無苗,以保小子於位。三機:一疑家,二疑德,三質士。疑家無授衆,疑德無舉士,質士無遠齊,籲敬之哉! 天命無常,敬在三機。”(《逸周書·五權第四十六》) 這並不矛盾,因為,天命唯德是依,而“德”就是以民為本。從“敬在三機”的内容來看,其實就是指的要以民為本的方法,其中,又重申了“常”的重要性:“刑以權常”,即通過“刑”這種“反常”(“權”) 之法達到能够促使民人回復“常”(“常道”) 的目的①筆者認為把“刑以權常”解釋為“刑法用以調控賞賜”是不妥當的,因為這種解釋既背離了原文的主旨,其解釋方法也是對假借的濫用,同時又不符合上下文的語境。。當周武王討伐商紂的時候,其理由除了我們所熟知的背棄天命之外,其實還指責他背棄“常道”(“棄成湯之典”):“……今在商紂,昏憂天下,弗顯上帝,昏虐百姓,棄天之命。上帝弗顯,乃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紂。肆予小子發弗敢忘,天命朕考,胥翕稷政,肆上帝曰:必伐之。予惟甲子,克致天之大罰,□帝之來,革紂之□,予亦無敢違大命。……天王其有命爾,百姓獻民其有綴艿。夫自敬其有斯天命,不令爾百姓無告。西土疾勤,其斯有何重。天維用重勤,興起我罪勤,我無克乃一心。爾多子,其人自敬,助天永休於我西土,爾百姓其亦有安處在彼,宜在天命,弗反側興亂,予保奭其介有斯勿用天命。若朕言在周,曰:商百姓無罪。朕命在周,其乃先作我肆罪疾,予惟以先王之道御復正爾。百姓越則,非朕負亂,惟爾在我。……古商先誓王成湯,克辟上帝,保生商民,克用三德,疑商民弗懷,用辟厥辟。今紂棄成湯之典,肆上帝命我小國曰:革商國。”(《逸周書·商誓第四十三》) 理所當然,昏虐統治者之所以失去天命而應該被推翻,其原因也在於他背棄“常道”,他的百姓也因此而隨之背棄常道,所以,新的有德聖王,就應該恢復“常道”推翻暴君和昏君,同時用“常道”來端正混亂之國的臣民。而同樣,周國之所以能够興起並滅商,也正是因為周能够善守常道。當武王滅殷之後,周公轉述周文王的治國要道給武王,其中講到諸多的措施,但是其目的都是一個,即使得“民乃知常”:“維武王勝殷,撫國綏民,乃觀於殷政,告周公旦曰:‘嗚呼! 殷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虚,和此如何?’ 周公曰:‘聞之文考,來遠賓,廉近者,道别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營邑制,命之曰大聚。……此謂仁德。旦聞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且以並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時,以成萬財。萬財既成,放以為人,天下利之而勿德,是謂大仁。淵深而魚鱉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稱賢使能,官有材而士歸之,關市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之,水性歸下,民性歸利。王若欲來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此謂歸德。五德既明,民乃知常。’”(《逸周書·大聚第四十》) 其實,周公所列舉的種種達到“大聚”的條目,都是從民生的各個角度談的。
二、其他先秦古籍中的“重常”史觀
不僅是《逸周書》如此,在其他先秦古籍中,也是有相當多的地方提到了“常”的重要性。
在《周易》中,多有談到“常”者,比如: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 子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周易·乾·乾文言》)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静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周易·乾·乾文言》)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静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周易·繫辭上》)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周易·坤·象傳》)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周易·上經》)
《象》曰:“需於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周易·上經》)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周易·上經》)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周易·上經》)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周易·下經》)
以上所列舉的《周易》中的文段,都提出了對“常”的重視和對反“常”的否定。
作為中國最早典籍之一的《尚書》,更是非常明確地對“常”的重要性做了肯定,指出能做到“常”是“吉”的:“寬而栗,柔而立,願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强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常哉!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同寅協恭和衷哉!”(《尚書·虞書·皋陶謨》)
下面的引文實際上也指出了“常”的重要性:“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於厥邑。胤後承王命徂征,告於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征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後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尚書·夏書·胤征第四》) 所謂“謨訓”“天戒”,其實都與“常憲”基本是同一含義。
《尚書》指出,歷史上的聖王都是要重視“常”的:“盤庚學於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尚書·商書·盤庚上第九》) 盤庚開導臣民,並專門教導在位的大臣遵守舊制、正視法度,也是體現了對於“常”的重視。在《尚書》的另一篇裏,也同樣體現了對於“常”的重視:“嗚呼! 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於天,結怨於民。斫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尚書·周書·泰誓下》) 可見,商紂的罪狀之一就是“狎侮五常”。而相對的,商朝的開國聖王商湯就是因為能遵守“典常”而得國:“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於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於上公,尹兹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 往哉惟休,無替朕命。”(《尚書·周書·微子之命》)
下面的文段其意思基本相同,都是强調了遵守“典常”的重要性:
嗚呼! 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尚書·周書·周官》)
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於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兹東郊,敬哉!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兹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於汝政,弗化於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於奸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於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尚書·周書·君陳》)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詩經·國風·唐風·鴇羽》)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經·小雅·節南山之什》)
爾受命長矣,禄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詩經·大雅·生民之什》)
先秦時期的一些官職名稱,都與重視“常”有關,比如“太常”,後世就成為重要的禮官,其實也源自先秦時期: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周禮·春官宗伯第三》)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旗,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周禮·春官宗伯第三》)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旗,車吏載旗,師都載旃,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是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搜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周禮·夏官司馬第四》)
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氐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考而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周禮·夏官司馬第四》)
而政事的主要目的就是使得百姓知“常”、守“常”: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别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禮記·禮運第九》)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渭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禮記·禮運第九》)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别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記·樂記第十九》)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禮記·樂記第十九》)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奸,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禮記·樂記第十九》)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禮記·緇衣第三十三》)
《康誥》曰:“惟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禮記·大學第四十二》)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 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禮記·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對於一些反“常”的行為和現象,先秦時期的人們主張要高度警惕:
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春秋左傳·莊公八年》)
初,内蛇與外蛇鬥于鄭南門中,内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于申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焰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春秋左傳·莊公十四年》)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春秋左傳·莊公二十五年》)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春秋左傳·莊公二十五年》)
顓頊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捨之則囂,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春秋左傳·文公十八年》)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 其不失國也,宜哉! 《夏書》) 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又曰:‘允出兹在兹。’ 由己率常可矣。”(《春秋左傳·哀公六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狩者何? 四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 譏。何譏爾? 遠也。諸侯曷為必田狩? 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春秋公羊傳·桓公(元年至十八年)》)
也不僅是在文字上如此,在思想上表露出“重常”史觀的更多,還不僅是從文字上可以看出。這些從《尚書》重點所記録的多為正常之事、制度、常態和常道可以看出來。關於這些,我們可以略舉一二例,比如《尚書》開首之篇《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鷸毛。帝曰:“咨! 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 囂訟可乎?”
帝曰:“疇咨若予采?”歡兜曰:“都! 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 静言庸違,象恭滔天。”
帝曰:“咨! 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 鯀哉。”帝曰:“吁! 咈哉,方命圮族。”嶽曰:“異哉! 試可乃已。”
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帝曰:“咨! 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嶽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 予聞,如何?”嶽曰:“瞽子,父頑,母囂,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試哉!女於時,觀厥刑於二女。”釐降二女於媯汭,嬪於虞。帝曰:“欽哉!”(《尚書·堯典》)
這一篇文字裏,除了最後一段提到的舜的家庭生活有些非“常”外,其他都是“常”態:制度、常事、常態、正面之事。
再以《春秋》的第一公魯隱公時期的歷史為例,這其中記載了不少的事情: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夏五月,莒人入嚮。無駭帥師入極。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鄭人伐衛。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君氏卒。秋,武氏子來求賻。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葬宋穆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邾人、鄭人伐宋。螟。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宋人伐鄭,圍長葛。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冬,宋人取長葛。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滕侯卒。夏,城中丘。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入盟於浮來。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子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挾卒。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春秋·隱公》)
從上文可見,《春秋》這一部分,雖然也有一些非常之事,如戰争、弑君,但是,更多的是正面的盟會、婚喪嫁娶等事情。而且,即使是記載的非正常的事情,但其目的卻在於批評而不是宣揚。也就是説,表面上是記録的非常之事,實際上是為了説明正常之事的可貴。
近代以來,由於對進化史觀的無條件接受和推崇,在事實上形成了史觀判斷上的誤區,那就是,衹要是主張尊重過往的觀點,都被視為是“保守”甚至是“倒退”的。我們可以從錢穆先生對於袁樞《紀事本末》的批評上窺其一斑。
三、結 論
我們要對“常”有正確的理解:“常”是“常道”(而非“常事”) 之意,實際上是對以往典章制度和成功經驗的總結。重“常”不是頑固或者倒退,而是出於對已有人類理性和經驗的尊重。作為理性早啓的“理性之國”,先秦古人們缺乏西方那樣的超越性宗教信仰來替他們做判斷,他們更多的是靠前人在生活中積累下來的經驗和知識,通過理性來達到其生活的幸福。但是,在另一方面,先秦古人對於如何正確理解歷史中的“變”也有自己的獨特的看法,那就是“常事不書”。這兩者共同構成了先秦“常變”歷史意識的兩個方面。
這點與先秦時期的諸多已被發掘出的各種歷史意識和觀念(比如“法先王”思想、“殷鑒”觀念等等) 都有關聯,但是又有不同。
還要説明的一點是,《公羊傳》中還有所謂“常事不書”的話:“春正月,公狩于郎。狩者何? 四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 譏。何譏爾? 遠也。諸侯曷為必田狩? 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春秋公羊傳·桓公四年》)①[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215 頁。那麽,這怎麽理解呢? 錢先生的“重常”史觀,豈不與之正好相反? 其實,二者並不矛盾。《公羊傳》的原話是“常事不書”,指的是“事”,是慣常所必行的、没有突出意義的、非根本性的大事,就如前文錢先生所打的比方,如同一個人生活中的“早上起來晚上睡覺,照常每天三頓飯,這有什麽可記。這是日常生活,等於無事”,所以不必記;而“常”卻是“制度”,或是正面的、有突出意義的“大事”。因而,這與錢先生看似矛盾,其實卻是兩事,實際上是因為袁樞對“常事不書”的理解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