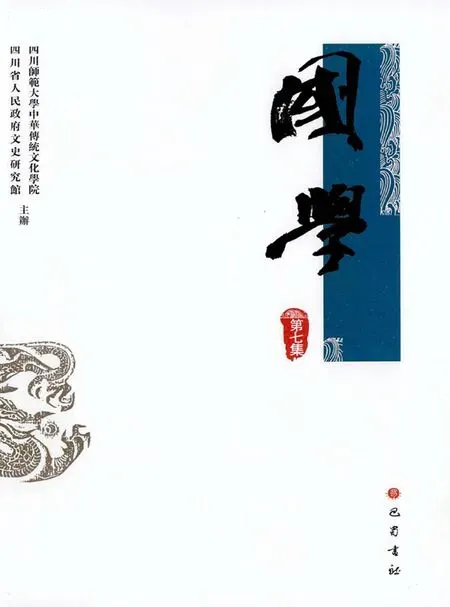粟特佛典寫本學與粟特佛教概述
張文玲
一、粟特文寫本簡介
(一) 德國吐魯番收藏及其研究成果
絲路北道所發現的寫本主要分藏於以下四處:巴黎國家圖書館、聖彼得堡東方科學研究院、柏林吐魯番收藏部(分貯於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以及所有權屬柏林布蘭登堡研究院而收藏於柏林國家圖書館東方部門) 以及大英圖書館東方及印度收藏部。其中收藏數量最豐者,為德國1902—1914年間,由當時柏林民族學博物館(Museum für Völkerkunde) 所主導的普魯士吐魯番考察團四次考察所帶回柏林的寫本共計約四萬件寫本殘片,其中保留了二十多種語言和文字。
德國普魯士吐魯番考察所帶回柏林的寫本,主要是以梵文、漢文、吐火羅文和古突厥文所書寫。此外,尚有約四千五百件以多種中古伊朗語所書寫的寫本殘片,這些寫本殘片大多出自摩尼教、佛教和基督教的經典,故其内容大多與宗教有關。用以書寫這些寫本殘片的語言有中古波斯語、安息語和粟特語,而這些語言是以以下不同的文字所書寫:(1)book=143,ebook=148所謂的摩尼文字、粟特文字、敘利亞文字(祆教文字) 或白匈奴文字(一種書寫大夏語言的希臘斜體字)。這些中亞古文字和語言與宗教經典之間存在一些複雜的關係,經過百年來學者的研究,已厘清了一些不易厘清理解的關係。例如:摩尼文字衹用來書寫摩尼教經典,而摩尼教經典有以中古波斯語、安息語和粟特語甚至大夏語書寫的。粟特文字可用來書寫以粟特語、中古波斯語和安息語書寫的摩尼教經典,也可用來書寫粟特文佛典以及基督教經典。此外,粟特文字還可用來書寫與醫藥、幻術有關的文書,還有書信。這些以各種中古伊朗語所書寫的手稿殘片,其定年衹能粗略定在公元8—11世紀之間。而手稿的内容,特别是以安息語和中古波斯語所書寫的文本,可能創作編輯於公元3—4世紀之間,在此之後,傳抄於吐魯番地區①本章節以上之所有内容參考自Reck Ch.,“The middle iranian manuscripts from the Berl in Turfan Collection:diversity,origin and reused”:in Eurasian Studies Vol.XⅡ/1—2,2014,pp.541—542.。
由於柏林吐魯番部所藏的中亞寫本幾乎全為殘片,因此,首要之整理研究工作便是辨識殘片的内容,找尋原屬同一件寫本的小殘片,將之拼湊成一個完整開本或一篇完整的文章。接着便是確認殘片的經文内容是屬於哪一教派或部派的經典。此外,復原整理寫本的工作,還包括與現存相關的各種語言文本進行比對,同時還需與四散於其他收藏中的寫本進行校勘比對②Sander L.,“Early Pakrit and Sanskrit Manuscripts from Xinjiang (second to fifth/sixth centuries CE):Paleography,Literary evidence,and their relation to Buddhist schools”,in Buddhism Across Boundaries:Sino-Platonic Papers,222 (March,2012),p.26.。
德國東方寫本編目計劃對一片寫本的編目,其著録的内容包括:
1.對寫本出土歷史方面的記録:寫本發掘處的編號縮寫;
2.對寫本的行政管理記録:寫本所在處的編號;
3.對寫本的制式描述記録;
4.寫本内容分類編排;
5.相關出版品及研究註記③Reck Ch.,“Kurz oder lang,hoch oder quer- Über die Buchformate der Sogder”,Juni 2009,online-Publikation,URL:http:/ /orient.ruf.uni-freiburg.de/dotpub/reck.pdf,ISSN 1866—2943.。
柏林所藏所有以中古伊朗語書寫的寫本殘片都已數位化,其影像皆可見於吐魯番研究數位網站④Reck Ch.2014,pp.541—542.柏林吐魯番研究數位網站:http:/ /www.bbaw.de/bbaw/Forschung/Forschungsprojekte/turfanforschung/de/DigitalesTurfanArchiv。
新疆古代寫本為多國所收藏,然而對這些寫本數十年來投注最多心力,且有系統地研究、辨識、編目、出版,成果最為豐碩者,應屬德國吐魯番研究⑤上述之觀點,為印度古文字學專家同時也是參與吐魯番收藏寫本編輯出版的Lore Sander 女士在2013—2014年間的一次會面中,對筆者所言。。
book=144,ebook=149
(二) 粟特寫本相關之文化背景
現存粟特文寫本的使用者——粟特人,其家鄉Sogdiana 地處中亞兩大河流 (Amu-Darya,Syr-Darya) 之間,粟特是由許多位於Zarafshan 和Kashka-Darya 河沿岸的緑洲國所組成的,其中最負盛名者為康國(位於今烏兹别克境内Samarkand 一帶) 和安國(位於今烏兹别克境内Bukhara 一帶),即所謂的昭武九姓中的康與安二姓。隋唐之際,粟特人在連接中國到西方的絲路國際貿易上居領導地位,粟特語言應流通於當時的絲路道上。致使在此期間,許多粟特人移居至中国新疆及内地。由於阿拉伯勢力進入中亞,約在10世紀末粟特滅亡,操持粟特語者移居至新波斯及後來的烏兹别克①吉豐田(Yutaka Yoshida),“A handlist of Buddhist Sogdian texts”in “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第54 號,2015a,p.167.。
粟特文字是一種發展自敘利亞—阿拉米語(Syrisch-aramäisch) 的文字。現存最早的物證,見於出自敦煌附近長城烽燧遺址公元4世紀的古代書信,從中可見古代粟特文與阿拉米語文字的相似性,及其横嚮書寫的書寫方式。現今出自撒馬爾干附近Mug 山公元8世紀初的粟特文信件是出自粟特本地的古代粟特文的物證,同樣是以横嚮的書寫方式書寫。但直嚮書寫的書寫方式,在7世紀時也同時出現在粟特地區。玄奘《大唐西域記》卷第一對粟特文有如下的記載:
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地名窣利,人亦謂焉。文字語言,即隨稱矣。字源簡略,本二十餘言,轉而相生,其流浸廣,粗有書記,竪讀其文,遞相傳授,師資無替。
其中的“竪讀其文”便是指出現在粟特本地的直嚮書寫方式。除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記》記載粟特文的直嚮書寫外,直接的物證見於公元8世紀出自撒馬爾干附近Afrasiab 的一件壁畫上的題銘,以及10世紀Ladakh 的一段銘文。
用以書寫粟特文以及古突厥文的文字,基本上是一樣的,粟特文的文字比古突厥文的書寫文字要古老些。現存古代粟特文的物證大部分出自敦煌藏經洞與吐魯番地區約公元8至10世紀的文書以及出自Bugut 和Karabalgasun 寫在石頭上的文字。古代維吾爾人承襲了粟特文字,加上一些特殊符號而將粟特文字進行了一些修改,並對書寫方法作了進一步的發展。之後,蒙古人沿用了這樣的文字,並直嚮書寫。現在的伊朗人一直是横嚮閲讀,而出自今塔吉克斯坦的Penjikent 的一件銘文被證明是直嚮書寫的。因此,粟特文手稿是直書、横書兩種書寫方式都存在。因此,基本上,如果一件粟特文殘件,其原本是書寫在歐洲式book=145,ebook=150的書籍(Kodex) 裝訂形式上,那就應該是横嚮書寫與横嚮被閲讀;但如果殘片原先是書寫在手卷或梵筴裝形式上,那就應該是直嚮書寫與直嚮被閲讀①本章節有關粟特文字之内容,參考自2017年12月21日Reck 女士以郵件回覆筆者所提有關粟特文字書寫及發展之相關問題的答覆。此外,亦參考自Reck Ch.,2009,online-Publikation,URL:http:/ /orient.ruf.uni-freiburg.de/dotpub/reck.pdf,ISSN 1866—2943.。
二、粟特文佛經寫本學概述②本章節之内容,主要參考依據如下資料來源:(1) 德國粟特文寫本專家Dr.Christiane Reck 女士於2017年在《伊朗語言文化研究手册》(Handbuch der Iranistik) 第二册第七章“寫本學”中所發表的一篇《佛教粟特寫本學》(Buddhistisch-sogdische Manuskriptologie) 專論。文中她綜合了近百年來歐美及日本學者對粟特文佛經寫本的研究成果,並提出此領域最新的研究方嚮。(2) Reck 女士提供給筆者的當今最新的粟特文佛經寫本研究資料。(3) 近一年來,筆者通過書信往返請教Reck 女士有關粟特文、粟特寫本的收藏與研究所得的知識。另外,本文有關柏林吐魯番所藏粟特文佛典的數量與内容及相關之圖片,皆承蒙Reck 女士慷慨提供,在此表達由衷之謝意。
(一) 寫本的出土、收藏與數量
現存的粟特文佛經寫本,大多發現自敦煌藏經洞與吐魯番緑洲地區。出自吐魯番緑洲地區的粟特文佛經寫本,主要出自高昌古城;有些文本殘卷出土於吐魯番附近地區,如吐峪溝、交河(Yarchoto) 以及碩爾楚克(Šorcˇuq) (位於焉耆(Karašahr) 附近);其餘的寫本殘卷則出土地不詳,或没有著録。這些寫本在20世紀初被帶到歐洲及日本,主要分藏於以下五處:巴黎國家圖書館、大英圖書館、柏林吐魯番收藏部(分貯於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以及柏林國家圖書館東方部門)、蘇俄聖彼得堡科學院Vostocˇnych Rukopisej 研究所,以及日本京都的龍谷大學。新近的發現則收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等其他中國境内的博物館及圖書館。發現自敦煌藏經洞的佛經寫本,在質量與研究編輯上,都優於出自吐魯番緑洲地區的寫本,因為後者大多為斷簡殘編,使得文本内容在研究推斷上大受限制,也因此衹有部分的粟特文佛經寫本出版③Reck Ch.,2017,p.385.。
柏林吐魯番收藏的粟特文寫本,其現状大多為斷簡殘編,其數量與内容大致可歸納如下:
1.約五百件以摩尼教文字書寫的摩尼教寫本殘片④有關柏林所藏約五百件以摩尼教文字書寫的摩尼教寫本殘片的研究請詳Enrico Morano,“A Working Catalogue of the Berlin Sogdian Fragments in Manichaean Script”,in M.Macuch,M.Maggi and W.Sundermann (eds),“Iranian Languages and Texts from Iran and Turan”:Ronald E.Emmerick Memorial Volume,Wiesbaden,2007,pp.239—271.,以及約五百件以粟特文字書寫的book=146,ebook=151摩尼教寫本殘片①有關柏林所藏約五百件以粟特文字書寫的摩尼教寫本殘片的編目研究請詳Reck Ch., 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德國所藏東方寫本目録册》):Band XⅧ,1 (第18 册,第1 部分)。,亦即共計約一千件的摩尼教寫本殘片;
2.約五百件以粟特文字書寫的佛教寫本殘片②同上,第2 部分。;
3.約五百件以敘利亞文字書寫的基督教寫本殘片③同上,第4 部分。,以及約五百件以粟特文字書寫的基督教寫本殘片④同上,第3 部分。,亦即共計約一千件的基督教寫本殘片;
4.除此之外,還有約一百件不明其出處的寫本殘片,以及約五十件以婆羅迷(Brāhmī) 文書寫的很小的寫本殘片。
以數量而言,柏林吐魯番所藏粟特文佛典的數量冠於全球;而巴黎與倫敦所藏文書,雖然數量上較少,但在内容上卻豐富許多⑤上述有關柏林吐魯番所藏粟特文佛典的數量與内容相關資料,為德國粟特文專家Reck Ch.女士所整理與提供,謹此由衷感謝她對筆者的熱忱協助。。
(二) 粟特文佛經寫本的定年及其文本依據
幾件敦煌出土的粟特文寫本,根據其紙張特徵以及末頁提署(版本記録),可定年為公元7世紀後半葉以及公元8世紀前半葉⑥Yoshida,“Buddhist literature in Sogdian”,in The Literature of Pre-Islamic Iran,edited by Ronald E.Emmerick ,Maria Macuch,2009a,p.288;MacKenzie,D.N.,“The Buddhist Sogdian Texts of the British Library”,Acta Iranica 10,Téhéran/Liège,1976,p.10f;Reck,2017,p.385.。這樣的定年,符合對部分的吐魯番殘卷特别是手卷殘件的定年。然而,大部分的粟特文寫本很可能是在9 或10世紀間完成的⑦Henning W.B.,Mitteliranisch,in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1.Abt.,4.Bd.:Iranistik,1.Abschnitt:Linguistik,Leiden;Köln,1958,p.55.。在有些粟特文寫本中,來自維吾爾佛經書寫者的影響是有證可循的。在定年為10—11世紀的粟特文寫本中,可見古突厥書寫者的名字及其語言影響⑧Sundermann W.,“A Fragment of the Buddhist Kāñcanasāra Legend in Sogdian and its Manuscript”,in Ancient & Middle Iranian Studies I,2006,p.717.。
粟特文佛典的遺存證明了以下兩點有關古代粟特人的佛教信仰狀況:
1.中國境内的粟特人,自公元7世紀開始,便有信奉佛教者,而其使用的重要佛經早先是譯自漢文佛典,但也有些是譯自梵文及吐火羅語文本⑨Reck Ch.,2017,S.385.;
2.在粟特本地,佛教並未紮根⑩Yoshida,2009a,pp.288—292.,也因此粟特佛教徒未能從其母國獲得任何的贊助,book=147,ebook=152而使得粟特文佛典和印度、古突厥文和漢譯經典比起來相對較少,但也因而顯得更加珍貴。
(三) 粟特佛經寫本研究回顧概述
粟特文佛經寫本的研究,在寫本被發現之後便立即展開,出自敦煌的寫本很快地便被辨識、出版及評論。這些出版品的内容主要關注點在粟特文寫本的内容闡明以及與之相對應的漢譯佛典的比對上;而與文本相關的語言學以及佛學的分析研究,自始至今都還持續着。然而有系統地對敦煌手稿寫本的研究,至今尚未開始。柏林吐魯番部所藏粟特文寫本的出版,是從内容豐富、可快速辨識的殘片開始出版。德國學者Sundermann 與日本學者Yoshida 在其出版品中貢獻了他們對寫本學(Manuskriptologie) 與時俱進的觀點,然而至今尚無全面性地對粟特文佛典寫本學的研究①Macuch M.,“Iranische Literaturen in vorislamischer Zeit”,in HdI,2013,pp.294—296.Reck,2017,p.386.。
Henning W.B.對粟特文及其書寫方嚮做了基礎性的研究,而關於粟特文、書寫方嚮以及書籍開本的繼續討論,則見於其他論著的相關段落中②例如Reck Ch.於2007年九月的第三届德國東方學家日(XXX.Deutscher Orientalistentag) 所發表的一篇有關粟特文的書寫方嚮及其書籍形式的研究(Kurz oder lang,hoch oder quer- Über die Buchformate der Sogder)。。有關中亞佛教文學基本特點的研究,可從A.V.Gabains 女士於1964年所發表的著作③Gabain,A.v.,Alttürkische Schreibkultur und Druckerei “ 刊載於Philologiaae Turcicae Fundamenta,Teil 2,hg.p.N.Boratav et al.,Wiesbaden,1064,pp.171—191.中對於古突厥的書寫文化和印刷術的討論探其梗概。
(四) 寫本的紙張
粟特文佛經是寫在紙張上的。出自敦煌藏經洞中的粟特文寫本手卷,其高品質的書寫紙張,被認為是中國所製,其製作年代應在藏族進入敦煌(公元786 / 787年) 之前。其尺寸大小高約26 厘米,寬約46—50 厘米。而部分出自吐魯番的粟特文佛經手卷殘片紙張,也應屬於這個時期所製的同類紙張。在此時期之後,所製造的紙張品質較差,尺寸也較大④Kudara K&Sundermann W.,Fragmente einer soghdischen Handschrift des Vis'e acinti-brahma-parip cchā-sūtra,1991,p.249;Yoshida 2009a,p.291.。
20世紀初以來,在研究中亞出土的寫本上,特别是對以中文及古突厥文書寫的手稿,通常使用日益精準細緻的自然科學研究方法來探討⑤Colditz,I.,“Die Manuskriptologie der iranisch-manichäischen Turfantexte”.HdI,2013,p.353.。1980年代西歐地區的學者提出“寫本的物質性”探討研究,使用自然科學的材料分析方法對古代寫本進行材料分析研究,進book=148,ebook=153而出現所謂的“新文字學”(New philology) 以及“物質文字學”(Material philology)。古代寫本的材料分析研究,主要是指對紙張纖維和書寫的黑色及其他顔色墨水的分析①D.Durkin-Meisterernst et al.,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17 (2016) 7—13,Berlin,pp.7—8.。德國柏林布蘭登堡研究院吐魯番研究部,在一項和德國聯邦材料研究局(Bundesamt für Materialforschung) 共同合作的研究計劃中,便針對幾件從敦煌和吐魯番寫本中挑選出的紙張進行研究②Rischel A.G.,“Old Turkish Fragmen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Paper analysis of 62 manuscripts and block prints”,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8:Buddhica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Teil 1:Das apokryphe Sutra Säkiz yükmäk yaruk,beschr.v.S.-Ch.Raschmann,Stuttgart 2012,pp.265—311.。由於這些古代紙張當時生産時,使用了差異性很大的製造原料,亦即不同的植物纖維以及再度回收使用的織品纖維,以至於這些古代紙張在分析的結果上,出現了非常不同的結構組織。這種現象也可能出現在製作於10—11世紀的粟特文佛經寫本殘片之中③Reck,Ch.,2017,pp.386—387.。
而在墨水的材料分析上,柏林布蘭登堡研究院吐魯番研究部、漢堡大學寫本研究中心、德國材料研究測試研究院以及哥廷恩科學研究院共同合作,針對十件以粟特文書寫的伊朗文寫本上的墨水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黑色墨水的成分有銅和鉛,而紅色墨水主要是以硃砂為顔料(有些紅色墨水以純硃砂為顔料;有些則為硃砂和鉛相混合,或硃砂和紅鉛相混合;有些則為硃砂和鉛與鐵相混合)。紅色墨水中所加的紅鉛導致寫本上的紅色墨水褪色或變色,而墨水中的砷則有抑制顔料的腐蝕及變色的作用④D.Durkin-Meisterernst et al.,2016,p.11.。通過寫本材料研究發現:這些粟特文寫本有着不同的紙張與不同成分的墨水。據此可知,這些粟特文寫本可能使用了不同的技術和材料來製作,因此,很可能是出自不同的生産地區。寫本的材料分析為研究寫本的專家提供了哪兩張或多張的斷簡殘編寫本原先可能同出於一本書的可能性⑤D.Durkin-Meisterernst et al.,2016,pp.12—13.。
出自吐魯番的粟特文手卷寫本,原先是單面書寫,後來被裁切成許多段而用以書寫古突厥文不同性質的文本,爾後這些殘片有些又被用作其他用途。這種紙張再利用的情形亦見於敦煌寫本上,例如伯希和從敦煌帶回的寫本(編號:Pelliot chinois 2020,Pelliot chinois 2021,Pelliot chinois 3515),其背面便用以書寫次要的漢文文稿⑥Reck,Ch.,2017,p.391.。
幾件出自吐魯番的印度形式書籍(Pustakabuch) 殘片,在紙張的表層出現了一層白色的石膏層,文字便書寫在此石膏層之上。這種現象主要出現在内容為講述故事的寫本殘片上,其用意是否為藉以提高寫本的價值並用以保存文本,或是有其他未知的作用,對此,尚未能確定。像這樣在紙張的表層塗上一層白色的石膏層的現象,同樣見於其他語言例如book=149,ebook=154梵文寫本殘片上①Reck Ch.,Mitteliranische Handschriften,Teil 2:Berliner Turfanfragmente buddhistischen Inhalts in soghdischerSchrift,beschrieben von Ch.Reck.Stuttgart 2016.(VOHD XⅧ,2),p.453.。
(五) 現存寫本原先呈現的書籍形式
出自吐魯番與敦煌的粟特文寫本,其書籍形式大致上可分為兩種:一種為仿效中國的手卷形式,另一種為仿效印度所謂的Pot·hī 或Pustaka,亦即類似一般熟悉的貝葉裝或梵筴裝。
在敦煌所藏寫本中的手卷,有一部分是模仿中國手卷形式製作而成。在伯希和收藏中,有一個保存完整的手卷,寬25.5 厘米,長770.5 厘米,内容為《因果業報經》。在卷首及卷尾皆書有經名,以及《三歸依文》。在手卷背面開端書有經名,此外,在經文末端書有經名,並且在捲雲狀花紋邊框裝飾下,以中文書寫了所有者之名(曹景泰?),根據其姓氏(曹),可知此手卷應為一位粟特人所有②Gauthiot R.,Le Sûtra des Causes et des Effets du bien et du mal.Paris 1926,v;Reck,2017,387.。
柏林吐魯番部收藏的寫本殘片,絶大多數為非常小的殘片,這些殘片有些顯示出黑色或灰色的邊綫以及行綫,一如中國式文書常見的情形。粟特文寫本中的每一行文字並不填寫於既定的欄内,而是每行之間僅留存很小的間距。
在吐魯番廣為流傳的書籍形式為仿效印度的梵筴裝,通常在書頁的三分之一處,會有一個供穿繩用的圓孔,但有些書頁則無,而是衹留一個呈圓形或四方形的空白處。粟特文寫本在梵筴裝的文字書寫上,有短行與長行之分。在短行寫本中,每一行是平行於書頁較短的一邊;在長行寫本中,每一行是平行於書頁較長的一邊。短行的梵筴裝寫本有不同的大小尺寸,如有14.7 ×48.5 厘米,最小的尺寸至少也有12.5 ×40 厘米。大尺寸短行的粟特文梵筴裝寫本,如柏林所藏的大乘《大涅槃經》,其修復還原後的尺寸為27 ×59 厘米③Sundermann W.,“A Sogdian MahaM-ya-namaha-parinirva--asu-tra manuscript”,“The Way of Buddha”2003: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Otani Mission and the 50th of the Research Society for Central Asian Cultures,hg.T.Irisawa,Kyoto 2010,p.76f.。長行寫本的尺寸大多較小,約20—30 ×10 厘米,例如30.9 ×8.3 厘米或28.0 ×10.0 厘米。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在吐魯番地區廣為流行的梵筴裝形式,在敦煌衹出現一例④Reck Ch.,2017,p.388.。
(六) 寫本的頁碼與標題
手卷形式的粟特文寫本並没有頁碼,衹有梵筴裝的寫本纔有編碼的需要。粟特文寫本book=150,ebook=155的頁碼有時單獨出現,有時則為書頁標題的一部分。梵筴裝的標題並没有醒目的裝飾紋飾,其作用在於協助内容的閲讀。所謂的頁碼標題,在短行寫本中,其所放置的位置是標示於經文之前;而在長行寫本中,則横置於經文上方。標題通常都以小寫書寫,其内容大多包括一部作品、書或是章節的簡要名稱以及頁數標示(數字+頁)。粟特文寫本上的頁碼標題通常出現在寫本的正面,這種情形與大多數的古突厥語以及其他的梵筴裝寫本是相反的①Sundermann W.,2006,717;Sundermann,2010,p.77.。然而部分粟特文寫本上的頁碼標題也有出現在寫本反面的,例如一件粟特文長行書寫的梵筴裝《金剛般若論》(Vajraprajñā-s'āstra) 寫本②Sundermann W.,Rez.V.D.N.MacKenzie (Hg.),“The Buddhist Sogdian texts of the British Library”,BSOAS 40,1977,pp.634—635.。
(七) 版本記録或末頁題署
(八) 寫本上的插畫
有關華麗的手稿插圖,最重要的一個例子為粟特文本《阿離念彌長者本生》(Aran·emijātaka) 的梵筴裝插畫④Sundermann W.,“Eine soghdische Version der Ara·nemi-Legende”.De Dunhuang à Istanbul:Hommage à James Russell Hamilton,hg.M.Bazin,p.Zieme,Turnhout 2001,pp.339—348,Taf.XXⅣ—XXXⅡ.;Ebert,J.“Sogdische Bildfragmente der Ara·nemi-Legende aus Qocǒ in Turfan”.De Dunhuang à Istanbul∶ Hommage à James Russell Hamilton,hg.M.Bazin,p.Zieme,Turnhout 2001,pp.25—41,Taf.I—XⅨ.。其經頁的正面為經文,背面整頁是與經文内容相對應的插畫。基於經文是以垂直方嚮書寫的長行梵筴裝形式,推測此手稿可能為直立式的書籍形式(Vertikales Buchformat)。在吐魯番文書中,還有其他的插圖碎片,其插圖没有佔滿一整頁,這book=151,ebook=156些插圖碎片至今尚未辨識,也未找到與之相對應的經文①Reck Ch.,2017,p.389.。
(九) 書寫的文字及書寫方式
粟特文佛經寫本是以粟特當地的文字書寫。粟特文字是一種發展自敘利亞—阿拉米語(Syrisch-aramäisch) 的文字,其常見的書寫方式是以斜體字書寫,其中許多字母之間很難區分,甚至無法區别。許多粟特文佛經寫本,特别是以手卷形式書寫的佛經,是以較標準的字體書寫;雖然也是以斜體字書寫,且每個字之間相連在一起,但每個字母之間的區别都標示得很清楚。過去將這樣的書寫文字稱為“經書文字”(Sūtra-Schrift)②Henning W.B.,Mitteliranisch,Leiden;Köln,1958,p.55.,後來Sims-Williams 於1976年將之改為“正式形式文字”(Fformale Schrift),因為這樣的書寫文字並非衹出現在佛經的書寫上③Sims-Williams,N.“The Sogdian Fragments of the British Libery”,in :Indo-Iranian Journal,1974,p.44.。許多出自吐魯番的粟特文寫本殘片是以不同方式的斜體字來書寫的。對於粟特文字,特别是考量到其與維吾爾文之間的關聯性,與之相關的詳細古文字學,目前尚無研究出現。
在柏林所藏吐魯番寫本中,有幾件粟特文寫本殘片是以婆羅謎文書寫的,這類殘片的内容大都與醫學有關④Reck Ch.,2017,p.389.。有一件寫本殘片被確定是以梵文與粟特文雙語書寫的,其内容為《天譬喻》(Divyāvadāna) 中的一句偈頌。粟特文手卷及梵筴裝寫本上,由左嚮右閲讀的文字書寫方式,被證明於公元5世紀下半葉時,便已出現在粟特本土以及印度河上游地區的銘文上了⑤Yoshida Y.,“When Did Sogdians Begin to Write Vertically?”.Tokyo University Linguistic Papers 33,2013,pp.375—394.。粟特文梵筴裝寫本應該就是普遍依據這樣的傳統書寫形式而書寫。
(十) 内容更正的標記與雙語書寫
若抄寫之文句有遺漏而需增補之時,將欲增補之字,以小一點的字體寫在要加入之行的旁邊;而在增補之字插入之處,在此行的另一邊,標示以一個小“十”字。有一個增補之例,是將遺漏之文句寫在一張紙條上,並黏貼於手稿上。而當已經書寫上之文句需删除時,則在欲删除的文句下方,點示其邊綫。
除了上述有一部粟特文佛經寫本是以古突厥文書寫其版權題署,以及書寫者的姓名是古突厥文書寫外,粟特文佛經寫本並没有明顯的以粟特文與古突厥文同時雙語併行書寫的book=152,ebook=157情形①Reck Ch.,2017,pp.390-391.。
(十一) 寫經學派與書寫工具
關於出自敦煌與吐魯番的粟特文以及古突厥文寫本的共通性和特徵的研究,至今尚未啓動。基於上述古突厥寫本上出現的書寫者之名,以及其他與粟特文寫本所共通的特徵,今人推測當時從事兩種文字寫本的書寫者,可能存在於共同的書寫學校及書寫工作坊。可能有些粟特文的書寫者已經突厥化到可以書寫兩種字體,而古突厥文的書寫者也能製作粟特文手稿②Yoshida Y.,“Die buddhistischen sogdischen Texte in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und die Herkunft des buddhistischen sogdischen Wortes für Bodhisattva:Zum Gedenken an Prof.Ko--gi Kudaras Arbeiten an den sogdischen Texten “.Übers.V.Y.,Kasai in Zusammenarbeit mit Ch.Reck,AOH 61,2008b,pp.340-344.;Yoshida,2009a,pp.288—329.。
一般而言,寫本都是用黑色墨汁以及分叉的管狀羽毛所書寫,但是少數的佛教經典可能是用毛筆寫的。衹有極少數的粟特文佛經手稿,其部分章節是以紅墨書寫③Reck Ch.,2017,p.390.。
小 結
由於出自敦煌與吐魯番的粟特文與古突厥文寫本在時空上有非常緊密的共通性,因此,未來對於粟特文佛經寫本的繼續研究,應該不僅止於將粟特文佛經寫本與漢譯以及其他語言佛典進行比對研究,同時也應朝着探討粟特文與古突厥文寫本的共通性與相異性方面去深入瞭解。
三、粟特文佛經概述
由於玄奘在公元630年左右到達粟特地區時,並没有記載當地的粟特人有信仰佛教,且由於很少的佛教遺迹在粟特地區被發現,因此學界認為:佛教並未傳入粟特地區④Compareti M.,Traces of Buddhist Art,Sino-Platonic Papers,2008,p.181.。由於粟特佛典大多發現自敦煌與吐魯番緑洲地區以及碩爾楚克(Šorcˇuq),且根據幾件留存下來的粟特佛典上的版權頁或題署,可知這些粟特佛典是翻譯於敦煌、洛陽和長安,因此學界認為:粟特人由於經商而來到中國新疆與内地,在移居到這些佛教興盛之地後,受到影響book=153,ebook=158而皈依佛教,並翻譯製作佛典。大多數粟特佛典的定年在7世紀下半葉和8世紀上半葉,且大多數粟特佛典是譯自漢譯佛典,小部分可能譯自梵文或吐火羅文。有一件出自吐魯番的粟特佛典殘片寫道:此經譯自庫車語,亦即吐火羅語B。而一件出自敦煌的粟特佛典版權頁記載:一位住在洛陽名為Chatfārātsrān 的粟特人,出資請粟特僧人Jñānacinta 將一件印度佛經翻譯成粟特文。但由於相關的梵文或吐火羅文原典已不存在,因此無法比對證明其出處①Tremblay,X.,“ The spread of Buddhism in Serindia:Buddhism among Iranians,Tocharians and Turks before the 13 Century”,in A.Heirman and S.p.Bumbacher (eds.), The Spread of Buddhism,Leiden/Boston,2007,pp.75—129.上述有關粟特佛教背景筆者主要參考自:吉豐田 (Yutaka Yoshida),2015a,168 以及Yutaka Yoshida (吉豐田),2009a,pp.288—290.。
强化实践团队概念,进行团队内资源优化整合是导师的重要工作内容。导师可以通过拓展训练、实战模拟等途径训练自己所指导的团队,以使低年级学生在训练中达到相互了解、默契配合的效果,进而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早在一百年前,在伯希和從敦煌帶回保存完好的粟特文佛典回到巴黎不久,R.Gauthiot比對漢文與粟特文佛經,而開始了粟特文佛典的解讀。百年來,在法、英、德、日等國學者的努力下,現今已有五十多部粟特文佛經被確認與研究,有些已出版,有些尚未出版。日本粟特文學者吉田豐將之分為以下四類②吉豐田(Yutaka Yoshida),2015a,pp.169—176.:
1.從漢譯佛典中,可找到相對應經句的粟特文佛典。由漢譯佛典翻譯而成的粟特文佛典,在現存的五十多部粟特文佛典中佔多數,有38 部之多;
2.雖不明其直接來源出處,但其中部分經文内容已被辨識的佛典;
3.混雜的經文;
4.以粟特文字轉寫漢譯經文而成的佛經。由於這類經文基本上與漢語、維吾爾語經文相同,因此可視為維吾爾佛教的經文,例如《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
(一) 從現存粟特文佛經内容管窺粟特人的佛教信仰
雖然現存的粟特文佛典衹是原先的一小部分,但或許還是可據此管窺當時粟特人的佛教信仰内容。根據現存五十多部粟特文佛經,筆者對粟特佛教做了如下的分析與探討。
1.主要信奉之神:觀世音菩薩與藥師琉璃光佛
現存的五十多部粟特文佛經中,包括直至今日還廣為流通的幾部大乘經典,如《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大方廣佛華嚴經》《佛説無量壽經》《大般涅槃經》《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維摩詰所説經》以及《大悲咒》(全稱《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大悲神咒》) 等。此外,尚有多部密教經典,如《佛説灌頂七萬二千神王護比丘咒經》《佛説大輪金剛總持陀羅尼經》《地藏菩薩陀羅尼經》《觀世音菩薩秘密藏如意輪陀羅尼神咒經》《觀自在菩薩如意輪念誦儀軌》《不空羂索咒經》,book=154,ebook=159從中可見密教觀世音菩薩信仰的盛行。
上述粟特文手稿佛典,之所以被認定是依據漢譯佛典翻譯而成,在於比對粟特文與漢譯佛典後,找到了相對應的經句。例如在E.Benveniste 於1940年出版的《粟特語文本編輯、翻譯和評論》(Textes sogdiens,édités,traduits et commentés) 一書中第14 號文本第26—35 行的内容:
結此手印於心……必須清晰思慮如來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現於眼前,必須真誠唸誦此咒語:七遍。由於結此手印及持咒語,所有如來當留意到你,他們將守護你並放光於你。任何你所犯的重罪及不該有的行為將全數消失殆盡①上述經文内容為筆者根據Yutaka Yoshida (吉豐田),2009a,p.296 中的英譯翻譯而成。。
特别是後半段的内容:“由於結此手印及持咒語,所有如來當留意到你,他們將守護你並放光於你。任何你所犯的重罪及不該有的行為將全數消失殆盡。”其與以下之漢譯相近似:《觀自在菩薩如意輪念誦儀軌》:“由結此印及誦真言故。即警覺一切如來,悉當護念加持行者,以光明照觸。所有罪障皆得消滅。”
除了觀世音菩薩外,藥師琉璃光佛在粟特佛教徒中,也是很受歡迎的一位。因為四件不同的粟特文寫本,其内容皆與《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有關,一件出自敦煌,另外三件出自吐魯番。這四件之中,除了一件出自吐魯番的寫本外,其他三件是譯自玄奘的譯本《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現存粟特文寫本中,有一段描述若要去除病痛,應禮拜藥師琉璃光如來的方法,如:念誦此經四十九遍,憶念於心,造藥師琉璃光如來佛像七尊,並點燈四十九盞,放生四十九個衆生等②相關經句文本請詳Benveniste E., Textes sogdiens, édités,traduits et commentés (《粟特語文本編輯、翻譯和評論》)1940年出版的第6 號文本第125—43 行。另詳Yutaka Yoshida (吉豐田),2009a,p.293.。
由於許多粟特文佛典製作於唐代都城長安與洛陽,或唐代西域督護府勢力範圍内的敦煌和吐魯番,所以現存粟特文佛典的内容,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唐代佛教的内容,或可説是反映了唐帝國之内外族的佛教信仰。
2.經、律、論三藏具足
雖然現存粟特文佛典以經為大宗,有關律與論内容的粟特文佛典為數不多,僅見《四分律》《四分律删繁補闕行事鈔》《四分僧戒本》以及《阿毗達磨俱舍論》,但據此可説粟特佛典内容是經、律、論三藏具足。上述一件出自敦煌的粟特佛典,記載了一位住在洛陽名為Chatfārātsrān 的粟特人,出資請粟特僧人Jñānacinta 將一件印度佛經翻譯成粟特文。這book=155,ebook=160顯示在洛陽有粟特僧人,因此也可推論:在洛陽地區很可能曾經存有粟特人所建之佛寺。在有僧有寺的情況下,律藏的存在便屬必要,因此現存寫本中有《四分律》《四分律删繁補闕行事鈔》《四分僧戒本》等粟特文律藏的遺存。前後有五部律自印度傳至中土,何以粟特文的律書目前衹見《四分律》殘片的遺存? 這應與《四分律》在唐代的興起有關。《四分律》(Dharmagupta-vinaya) 原為印度上座部系統法藏部(Dharmagupta) 所傳之戒律,是自印度傳來的五部律之中,在中土最為發揚光大並傳佈於後的一部律藏。《四分律》於唐代初年興起,這與中國律宗長安終南山南山宗的創立者道宣(596—667) 不無關係。他著作等身,其中號稱為“南山三大部”中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便有粟特本傳世,可見粟特佛教與唐代佛教的密切關聯性。
3.在家衆的信仰内容
從現存的粟特文佛典可以推測,在粟特佛教徒之間所流傳的佛教信仰,有强調因果關係與不應食肉等内容。講述因果關係的相關經典有《佛為首迦長者説業報差别經》《佛説善惡因果經》以及《佛説灌頂七萬二千神王護比丘咒經》。例如,粟特文殘件編號SCE 6—12、60—67、67—70、82—83、90—91、217—218、252—255、496—500 的内容與《佛説善惡因果經》有關,其中編號SCE6—12、60—67 的内容為阿難嚮佛請問善惡因果的關係,最後佛告阿難:“你所問的問題,全部與前世所行有關。由於過去世中,每位衆生之心行不同且互不相等,所以其報應也就有千萬種不相同的類别。”①這些粟特文殘件的内容請詳MacKenzie D.N.“The Sūtra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Actions”in Sogdian,London,1970,pp.2—5、4—7、12—15、28—29,以及Yutaka Yoshida (吉豐田),2009a,pp.301—302.對於因果報應果真不爽的懷疑,見於一件出土於吐魯番的粟特文殘件,其内容如下:“我父母受苦如是,且一直忍受着地獄(般) 的折磨,雖然他們行善無數,他們依舊生活艱困。我真不知何以至此。所以,我問佛陀(緣由何在)。”②Yutaka Yoshida (吉豐田),2009a,p.302.很可惜,粟特文本中有關佛陀對此一問題回答的部分已佚失了。
而禁止喝酒吃肉也是粟特佛教所强調的内容。有一部尚未辨識其出處的粟特佛典D:BSTBL∶ 7—11,其版權頁指出,此經翻譯自印度原典③吉豐田(Yutaka Yoshida),2015a,p.175.。此經列舉飲酒的禍害如下:
酒醉令原先亮麗的身體變得卑劣,令統治者失去權力,令智者失去智慧,令有名望者因而變得默默無聞,令富人變窮,並且為衆生所厭惡。因此之故,不應喝醉人之飲。
book=156,ebook=161此經的結尾寫道:“飲酒的禍害與罪過罄竹難書,在此謹簡述一二。”①寫本編號Or.8212.191,第7—11 行,相關經文翻譯請詳MacKenzie D.N.,1976,pp.8—11;Yutaka Yoshida(吉豐田),2009a,p.297.
在現存佛典中,篇幅最長者為《須達拏本生》(請詳後述),其次便為一部内容講述不應食肉之經,經中用了1200 行告知衆生不應食肉的道理。這部經衹有前段22 張經頁不存,其餘皆完整保存。其中最主要講述不應食肉的理由如下:
不殺與不吃肉者,不受(所有) 許多的疾病之苦。任何祈願不再世世輪迴受疾病之苦的人,就必須絶對節制而不吃肉。那是因為一顆佛(性) 種子存在於(所有的)五種衆生以及四大(構成萬物的四大元素) 之中,且因為每個衆生皆當成佛②此經文文本請詳E.Benveniste, Textes sogdiens, édités, traduits et commentés (《粟特語文本編輯、翻譯和評論》)1940年出版的第2 號文本中的第39—46 行。另詳Yutaka Yoshida (吉豐田) Buddist literature in Sogdian,2009,p.297.。
此經有一段佛陀對阿難講説不應食肉的道理如下:
諦聽! 不論我過去世以任何生命形式出現,我一直都是慈悲而不殺生……由於我不吃肉喝酒,因此我得正覺……深思以下事實真相:肉不生長於樹上,也非從草叢中所生出。肉並不由大地所生,肉的取得,僅來自於殺生,將頭砍下,把身體剁成塊③此經文文本請詳E.Benveniste, Textes sogdiens, édités, traduits et commentés (《粟特語文本編輯、翻譯和評論》)1940年出版的第2 號文本中的第1198—1213 行。另詳Yutaka Yoshida (吉豐田) 2009,p.298.。
在柏林的吐魯番收藏中,有三件粟特文小殘片與此經有關,但分屬不同的翻譯經典④Yoshida,Y.(tr.Bz Y.Kasai and Ch.Reck) “Die buddistischen sogdischen Texte in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und die Herkunft des buddhistischen sogdischen Wortes für Bodhisattva”,Acta Orientalia Hungarica 61/3,2008,pp.335—337.。可見有關不食肉的經典在吐魯番地區的粟特佛教徒中,應是相當流行的。
(二) 粟特文佛經故事
1.粟特文佛經故事集的來源
自早期印度佛教以來,講授佛經故事是傳達佛教義理的一種善巧方便。早在佛教教義仍以口誦方式流傳,尚未被刻寫下來之時,幾則屬於公元前3世紀或公元前2世紀所流傳的佛本生故事,便已被刻成浮雕,裝飾在印度巴爾户(Bhārhut) 和桑奇(Sanchi) 佛塔的石欄上了。由此可見,最遲在公元前2世紀後半葉時,許多本生故事在印度已廣為流傳,book=157,ebook=162且被視為是神聖重要的,故被用來裝飾圍繞於埋葬佛骨舍利或象徵佛陀的佛塔四周①Rhys Davids,Buddhist Birth-stories,London,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pp.liv-lv.。這個傳統隨着“説一切有部”傳到新疆絲路一帶,有部譬喻師以譬喻手法傳授佛經義理,使得本生與譬喻成為絲路緑洲洞窟寺院壁畫上很受歡迎的主題。
在佛教經典為數不多的故事譬喻集當中,《天譬喻》(Divyāvadana) 與“根本説一切有部”關係密切。學界一致的看法是:《天譬喻》是由“根本説一切有部”在大約公元200—350年間所完成的②Rotman,Andy, Divine Stories.Divyāvadāna-Part 1,Boston,2008,p.6.。有一件粟特文殘件被D.Maue 辨識出與《天譬喻》有關,且其中有一句梵文偈頌旁邊有以婆羅謎文書寫的粟特語翻譯③Sims-Williams,N.„ The Sogdian in Brāhmī script”,in :R.E.Emmerick et al.(eds.),Turfan,Khotan und Dunhuang,Berlin,1996,p.307;吉豐田(Yutaka Yoshida),2015a,p.174.。雖然研究證實:現存的粟特文佛教經典與漢譯佛典有密切關係,但這件粟特文《天譬喻》殘件,應作如是理解:來自中亞的粟特人,在其從家鄉經絲路來到中國内地的過程中,應有很多機會接觸到北印度、犍陀羅及中亞絲路所流通的佛教經典。因此,雖然《天譬喻》(Divyāvadana) 不見有漢譯本,但這件粟特文《天譬喻》殘件證明了《天譬喻》已流通於粟特佛教徒之間了。
佛經故事的流傳有一大部分是以中亞語言書寫的,然而由於大部分中亞佛經故事寫本的保存狀況不佳,大多為斷簡殘編,衹有非常少數的故事結集,其内容不足以提供故事的原典出處、編輯完成的時間或其流傳過程的訊息。漢譯《賢愚經》算是一個例外。除此之外,回鶻文《十業道譬喻鬘》(Das'akarmapathāvadānamālā) 雖為殘卷,但也算是難得傳留至今的一部中亞佛經譬喻集④Ehlers,G.," Kurzfassungen buddhistischer Legenden im Alttürkischen ",in: Buddhistische Erzählliteratur und Hagiographie in türkischer Überlierung,ed.J.p.Laut,K.Röhrborn,Woesbaden 1990,p.3.。《十業道譬喻鬘》已被證實有多種中亞語言文本:吐火羅文A (焉耆語)、吐火羅文B (庫車語)、粟特文與回鶻文,其中衹有回鶻文的《十業道譬喻鬘》保存情況較佳,其餘吐火羅文A、吐火羅文B 及粟特文的《十業道譬喻鬘》都衹是殘卷⑤Peyrot,M.;Wilkens,J.,“Two Tocharian B Fragments Parallel to the Haris'candra-Avadāna of the Old Uyghur Das'akarmapathāvadānamālā”,i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 Volume 67 (3).319—335 (2014),p.319.。
根據回鶻文《十業道譬喻鬘》的版權頁,回鶻文本是翻譯自吐火羅文A (焉耆語),而此焉耆語文本又是翻譯自吐火羅文B (庫車語)⑥Jens Wilkens-Georges-Jran Pinault-Michaël Peyrot,A Tocharian B parallel tot he legend of Kalmāsapāda and Sutasoma of the old Uyghur Das'akarmapathāvadānamālā,i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 Volume 67 (1),1—18 (2014).S.1.。而以現存粟特文《十業道譬喻鬘》的殘片與回鶻文本相比對,德國粟特文學者Sundermann 認為粟特文的《十業道譬喻鬘》很可能同樣翻譯自吐火羅文文本⑦Sundermann W.,2006,p.719.。現已辨識的粟特文《十業道譬喻鬘》中的故事為《虔闍尼婆梨王本生》(Kāñcanasāra-Jātaka)。
book=158,ebook=163目前已辨識的粟特文佛經故事有:《須大拏太子本生》(相當於巴利語《本生經》編號第547 的Vessantara-Jātaka)、《虔闍尼婆梨王本生》(Kāñcanasāra-Jātaka)、《阿離念彌長者本生》(Araemi-Jātaka),另有一則故事相當於《賢愚經》卷九的《善事太子入海品》或《大方便佛報恩經》卷四的《惡友品》,其中保存内容最多的是《須大拏太子本生》。
2.粟特文《須大拏太子本生》研究概述
《須大拏太子本生》可説是印度佛教故事中傳播的時間最久遠、地域也最廣闊的一個故事,很可能是粟特文佛典中最古老的佛典之一。其現存粟特文《須大拏太子本生》寫本的年代可能為公元649年。經中故事主角名為Suδāšn (Sudāšan),這很可能是由梵文su (意指好,善) 和伊朗文δāšn (dāšan) (意指:禮物)①Sims-Williams N.,Indian Elements in Parthian and Sogdian,K.Röhrborn and W.Veenker (eds.),Sprachen des Buddhismus in Zentralasien.Wiesbaden,p.139;Yutaka Yoshida (吉豐田),2009a,p.307.構成的。有趣的是,漢譯本中故事主角名為須大拏,似乎與粟特文《須大拏太子本生》中故事主角之名Suδāšn 較為接近,而比起梵文文本中的Vis'vantara 以及巴利文本中的Vessantara 就差更多了。
粟特文寫本《須大拏太子本生》的研究早在20世紀初期便已開始。第一位研究者為R.Gauthiot,為了找出粟特文《須大拏太子本生》經文是根據哪一部經翻譯而成,他曾比對巴利文、藏文與漢譯文本②須大拏太子本生的巴利文見《本生經》第547 號本生,藏譯本,例如:菩薩蔓(丹珠爾,卷一二九)、《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甘珠爾,卷四十一)、《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甘珠爾,卷四十二)、翻譯自漢文《太子須大拏經》的藏譯本……等。漢譯文本,例如:《六度集經》卷二、《菩薩本緣經》卷三、《太子須大拏經》、《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十四、《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十六等。請詳Yutaka Yoshida,What has happened to Suδāšn's Legs? ~Comparison of Sogdian,Uigur and Mongolian versions of the Vessantara Jātaka,in :Commentationes Iranicae,2013,pp.399,401—403;Yutaka Yoshida (吉豐田),2009,p.304.。接着,英、法、德、日各國學者也分别比對其他語言的《須大拏太子本生》文本,例如犍陀羅文本、梵文文本③,以及古代中亞語言文本,其中有和闐文本Jātakastava 《佛本生贊》中第45 個本生(141—143 句贊頌)、吐火羅語A 及吐火羅語B (各有一個殘片被辨識是依據Jātakamālā《本生鬘》)、維吾爾語及蒙語本④。
在比對粟特文與其他語言的《須大拏太子本生》文本後發現,粟特文《須大拏太子本生》文本不是譯本,因為上述各種語言的《須大拏太子本生》故事的内容没有任何一個文本和粟特文本完全相同,粟特文本中没有借自漢譯的用語,而也没有證據證明是譯自梵本⑤,因此認為粟特文《須大拏太子本生》的劇情内容應是自創的文學作品。粟特文本中有些故事情節是特有的,例如有關須大拏太子出生前,皇后夢中所見之瑞相,不見於巴利
相關梵文文本例如:出自吉爾吉特(Gilgit) 的Mūlasarvāstivāda-Vinay(《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ĀryaS'ūra,Jātakamālā(聖勇《本生鬘》) 以及Kemendra,Bodhisattvāvadānakalpalatā中的須大拏太子本生
④ 有關須大拏太子本生各種語文文本以及粟特文本與維吾爾、蒙文本的比對請詳:Yoshida,Y.,2013,pp.401—412.
⑤Durkin-Meisterernst,D.The Literary Form of the Vessantarajātaka in Sogdian.With an Appendix by E.Provasi / / Ch.Reck,and D.Weber (eds.),Literarische Stoffe und ihre Gestaltung in mitteliranischer Yeit.Wiesbaden,2009,pp.65—89.book=159,ebook=164文、藏文與漢譯文本中,其内容為:“陛下,我感覺到似乎七顆摩尼如意寶珠從太陽神那邊出發,而進入到我右脇。”(粟特文須大拏太子本生VJ6—8) 另外,粟特文《須大拏太子本生》中出現了很多粟特人本土宗教所信奉的神名,例如Azrua 和Weshparkar①Yoshida Y.,(吉豐田),2009a,pp.304—305.。
雖然整篇粟特文《須大拏太子本生》故事没有和任何其他文本完全相同,但在某些故事情節上又分别和其他不同語言文本有相同之處。例如:衹有漢譯本西秦沙門聖堅所譯《太子須大拏經》卷一有如下之情節:“至滿十月便生太子。宫中二萬夫人聞太子生,悉皆歡喜踊躍,乳湩自然而出。”其内容與粟特文《須大拏太子本生》寫本a4—7 行的内容相近:“當太子出生那天,乳從六萬婦女胸部流出。”②Yoshida Y.,2013,p.403.差異衹在於漢譯本中為“二萬”,粟特文本是“六萬”。
比對粟特文《須大拏太子本生》故事,與年代上比之要早一些的文本(梵文、巴利文以及漢譯經典),則粟特文《須大拏太子本生》故事迥異於其他文本的是:故事情節增加了一段很戲劇性的内容,亦即太子一家在到達指定的放逐地點之前所經歷的磨難。對此,漢譯《太子須大拏經》卷一僅僅輕描淡寫地寫道:“檀特山,去葉波國六千餘里,去國遂遠,行在澤中,大苦飢渴。”而粟特文本則增加了須大拏太子在飢渴中,捨身割自己腿上之肉煮給妻兒吃,並繼續前進的故事情節。粟特文《須大拏太子本生》寫本中,第20—23 張寫本内容為描述太子一家在到達指定的放逐地點(檀特山) 之前所遇到的困境,其中的第21—22 張寫本已佚失。第20 張寫本描述太子一家遇到一條大河,難以前進。第23 張寫本描述太子妃Mandrīy 痛不欲生,並寫了一段須大拏太子對太子妃所説的話,其中有一句是:“皇后! 你是否願意看一下我的腳變成什麽樣子?”在這之後,文本上寫道:“當太子妃Mandrīy 看到須大拏太子腳上的肉都不見了,而以骨頭步行時,她自身的疼痛停止了。”此外,這張寫本也描述了太子妃當時絶望的心情,她説道:“今日,我對宗教功德、善行(的善報) 以及所有神明已絶望,因為今日我們將因飢渴而在沙漠中死去。”③Yoshida Y.,2013,p.408.
須大拏太子腳上的肉為何不見了? 這段情節内容的描述很可能出現在已佚失了的第22張寫本上,比對與粟特文佛教寫本關係密切的維吾爾文以及蒙文文本可知,粟特文佛教第22 張寫本的内容應為:須大拏太子割自己大腿上的肉,在一塊平坦的石頭上煮了後,拿給妻兒吃④Yoshida Y.,2013,pp.409—410.。
“本生”,梵文jātaka,意指(佛陀) 過去世之事。本生雖屬佛所説教法的九大類(九分教⑤部派佛教時代,大衆部將佛所説教法的類型,分出九大類,稱九分教。) 之一,但比起戒律以及其他講述義理的經文,在傳譯流傳過程中,應屬較可自由闡book=160,ebook=165述發揮的一種佛教文學。因為,其目的是以譬喻講故事的方式,因時因地,隨衆應化,將佛教的義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講説給信衆聽。因此,不同時代、不同地區所流傳的同一則本生故事,在局部情節的描述上,難免産生因時因地制宜的增減删補,也正因如此,各地所傳的本生故事内容,常能將一時一地的民情與特色表露出來。粟特文本異於梵文、巴利文以及漢譯經典,而增加了須大拏太子捨身割肉喂食妻兒的戲劇性的情節,以及加入家鄉地區所信奉的神祇之名等故事内容,從中或可管窺粟特佛經故事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