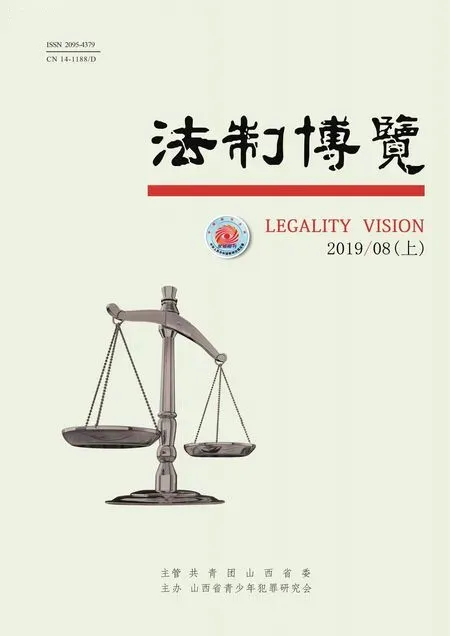土地经营权之法律性质辨析
阚 雪
大连海事法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当前“三权分置”政策正在逐步推行,法学界为了积极响应这一变革,试图从法律层面为其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但现阶段,法学界对于“三权分置”的相关理论分析以及制度架构并未形成共识,尤其是三权中的土地经营权的法律性质,至今众说纷纭,且法律法规并未对其作出明确的界定。需明确的是,这些理论上的分歧不仅会产生法律法规乃至政策的争议,更会进一步影响“三权分置”改革的推进以及改革成果的稳定性。鉴于此本文将针对土地经营权法律性质这一争议点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对该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一、土地经营权概述
(一)土地经营权的政策含义
土地经营权这一名称早在《物权法》与《土地承包法》颁布之前就出现在各地方规范性文件之中用于指导农地流转。但其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并以此确定其含义则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
2013年12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从国家层面首次提出土地经营权这一称呼,并要求“放活土地经营权”;2016年10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赋予经营主体更有保障的土地经营权,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关键。土地经营权人对流转土地依法享有一定期限内占有、耕作并取得相应收益的权利。”
通过对上述政策文件的总结,可以看出2016年的《意见》对土地经营权的定义更加明确清晰,此也可作为土地经营权政策含义的代表。
(二)土地经营权的概念
在土地经营权政策含义的基础上,以《意见》中对土地经营权含义的表达为参考,其对土地经营权的定义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其将农户排除在土地经营权的主体之外,这一构造值得商议,笔者认为将农户排除在土地经营权的主体范围之外会使得土地经营权这一新设立的权能不具有普遍性从而使其与“放活土地经营权”这一政策目的相背离;其次,其将土地经营权的客体定义为“流转土地”而将“承包土地”排除在外,这一构造笔者也对其存在异议,除上述理由之外,笔者认为其不符合“土地经营权”的全局意义。
综上,笔者认为应将土地经营权定义为土地经营权人对其依承包合同或者土地转让合同取得的耕地享有的在一定期限内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二、土地经营权法律性质之理论争议
(一)物权化债权说及其争议
物权化债权说,该说认为应将土地经营权的法律性质定性为债权,但同时给予其与物权相似的保护,赋予其登记能力。[1]持有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首先从法的体系来解读,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包括转包、出租、互换以及转让,而这些转让方式明显具有债权性质;其次,将土地经营权的法律性质定性为债权具有正当性。根据三权分置的政策含义,土地经营权是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的,而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由土地所有权中所分离出的用益物权,若将土地经营权定性为债权则符合“所有权—用益物权—债权”这一权利结构;再次,将土地经营权定性为债权会使得土地经营权的流转难度降低,符合三权分置的政策目标。同时,由于赋予土地经营权登记能力,也就使得土地经营权人的利益不会因债权的隐蔽性而受到损害。
但笔者认为,并不应将土地经营权定性为债权,原因如下:首先,土地经营权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物权化债权说仅将因流转获得的土地经营权定性为债权,而将因土地承包获得的土地经营权排除在外,这就使得同是“三权分置”产生的土地经营权有的是物权有的是债权。[2]从而造成了不必要的区分与混乱;其次,土地经营权的主体定位不明确,如上所述,该学说仅将流转取得的土地经营权定性为债权,并未提到承包农户是否拥有土地经营权进一步说明其拥有的土地经营权是债权抑或是物权。
(二)权利用益物权说及其争议
权利用益物权说,顾名思义认为土地经营权为权利性质的用益物权。作为该学说的理论支撑主要包括:首先,支持该说的学者认为,土地经营权的是建立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上的且后者为前者的客体,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在设定土地经营权后依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设定土地经营权只不过是为了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所包含的各项权利。[3]该种构建属于“所有权—用益物权—用益物权”的构建方法,根据我国《物权法》第136条具有现行法依据。其次,将土地经营权定性为权利用益物权可使得土地经营权更具有稳定性,使得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安全得到保障;再次,会扩大土地经营权主体范围,有利于推进三权分置政策的实施并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效用。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持一定的怀疑态度。首先其理论依据支撑不足,上文中提到认为土地经营为权利有益物权是基于《物权法》136条之规定即用益物权之上可再设用益物权。但依据该条规定仅能得出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在地面、地下或者地上分别设立,而不能得出用益物权之上再设立用益物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4]因此笔者认为以该条作为理论支撑依据明显不足;其次,将土地经营权认定为权利用益物权虽会保护土地经营权主体的利益,但不可否认的是存在过度保护的问题。由于物权不具备债权所具有的灵活性以及不能完全按照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制定合同,使得许多希望对土地经营权进行流转的主体望而却步,这也就不符合放活土地经营权这一政策导向;再次,将土地经营权定性为权利用益物权会使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用益物权虚化,原因是按照上述观点,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土地经营权同为用益物权且权利内容十分类似,久而久之就会有虚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风险。综上所述,笔者并不认同将其定性为权利用益物权的观点。
三、土地经营权法律性质之界定
(一)不动产用益物权
通过前文对物权化债权说以及权利用益物权说的剖析可得出上述两种学说不能很好的对土地经营权进行定性。笔者结合土地经营权的政策目的以及当前的法律体系认为土地经营权的性质应为不动产用益物权,该用益物权是以农地为其客体而非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客体的权利。
(二)定位之理论基础
结合上述笔者对土地经营权的定位,土地经营权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农户基于承包合同获得的土地经营权,可称为原始土地经营权;另一类是受让方通过土地转让合同间接获得的土地经营权,可称为继受土地经营权。[5]将原始土地经营权定性为不动产用益物权该理论依据源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性质由于其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根同源将其定性为不动产用益物权也就不存在法理上的不通。
关于继受土地经营权又可以因其流转方式的不同分为两个分支对其理论基础进行解读,分别是物权性质的流转与债权性质的流转,对于因物权性质的流转所产生的土地经营权结合上述原始土地经营权进行论证,仍可将其定性为不动产用益物权且不超出当今法理法体系框架。对于因债权性质的流转所产生继受土地经营权则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现行法体系,对于该部分定性笔者认为正是政策改革的体现,进行创新性尝试未尝不可。
(三)定位之政策现实意义
将土地经营权定性为不动产用益物权符合政策规定,该种定性可使得土地经营权的主体范围更加广泛且流转更便捷安全符合“放活土地经营权”的政策要求。再者将具有债权性质流转的土地经营权定性为用益物权会进一步保障土地经营权主体的利益且在一点程度上减少纠纷的产生。总之,对土地经营权进行定性除应考虑体系法逻辑以外还应与政策以及现今司法实践相结合,使其性质的定位推动实践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