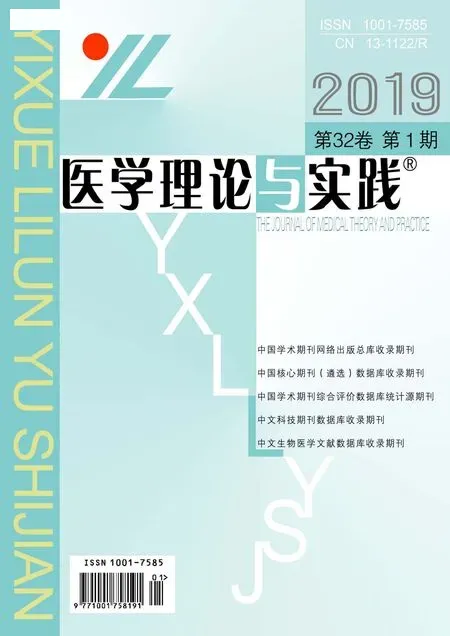维生素K拮抗剂Ⅱ诱导蛋白在肝细胞癌中的应用进展
胡 迪 武文娟 王凤超
1 蚌埠医学院,安徽省蚌埠市 233000; 2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
在中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在上升,这使得癌症成为2010年以来死亡的主要原因。原发性肝癌是原发于肝脏的上皮性恶性肿瘤,是全球第二大常见的癌症死亡原因,肝细胞癌(HCC)占原发性肝癌的90%以上。目前肝癌的早期筛查主要依靠肝脏超声和AFP。但是多数HCC患者一经确诊,已属晚期,易错过最佳治疗时期。异常凝血酶原或维生素K缺乏或拮抗剂Ⅱ诱导蛋白具有早期诊断HCC敏感性、特异性高等特点,本文通过对PIVKA-Ⅱ的生物学概况及临床应用两方面进行综述。
1 生物学概况
1.1 PIVKA-Ⅱ的发现 在20世纪30年代,维生素K因参与止血作用被发现。直到1974年,维生素K对止血作用的机制才被证实[1]。凝血酶原在维生素K的存在下,其1个或数个谷氨酸(Glu)残基羧化为γ-羧基谷氨酸(Gla),成为有活性的正常凝血酶原。因为Gla的存在使正常的凝血酶原可以与钙离子结合,参与凝血过程[2]。Stenflo等人的观察性研究表明,维生素K拮抗剂诱导的异常凝血酶原缺乏这种羧化的残基,不能与钙离子结合,不能参与凝血过程[1]。所以,异常凝血酶原被称为脱γ-羧基谷氨酸(Des-gamma-carboxyprothrombin,DCP),也被称为维生素K缺乏或拮抗剂Ⅱ诱导蛋白(Protein induced by vitamin K absence or antagonist-Ⅱ,PIVKA-Ⅱ)
1.2 PIVKA-Ⅱ在肝细胞癌中的合成 1984年Liebman等人的研究发现,约90%的经活检确诊的肝细胞癌患者血清中可检测到PIVKA-Ⅱ,且平均水平在900ng/ml,在正常对照组中未检出,2例手术和1例化疗后患者血清PIVKA-Ⅱ水平显著下降,而在疾病复发时又升高[3]。Liebman的发现,让人们对肝细胞癌血清肿瘤标志物有了新的认识,对肝细胞癌的早期诊断提供了帮助。但是,PIVKA-Ⅱ在肝细胞中产生的具体机制仍不明确。早在1985年的一项关于大鼠肝微粒体中维生素K代谢的研究指出,凝血酶分子在其N端有一个所谓的Gla域,其中包括10个γ羧化谷氨酸残基。这些γ羧化谷氨酸残基来自于凝血酶前体蛋白中的谷氨酸,是在肝细胞中通过维生素K依赖的羧化酶系统合成[4]。随着时间的推移,仍有很多学者在继续研究PIVKA-Ⅱ在肝细胞癌中的产生机制。2017年,Taniguchi等人的实验中通过培养不同的肝细胞癌细胞系,包括Huh-1、Huh-7、HepG2、Hep3B、PLC/PRF/5、HLF和HLE细胞系,用实时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凝血酶原mRNA的水平,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定量检测DCP[5]。他们的研究表明肝细胞癌细胞系Huh-1、Huh-7、HepG2、Hep3B和PLC/PRF/5都是PIVKA-Ⅱ生成细胞系,而HLF和HLE细胞系不能产生DCP。而且,凝血酶原mRNA仅在DCP生成细胞中表达。他们得出,DCP的生成和凝血酶原mRNA的水平有密切的相关性。最终数据表明聚腺苷酸二磷酸核糖转移酶-1[Poly-(ADP-Ribose) Polymerase-1,PARP-1]激活了凝血酶基因的转录,而过量的凝血酶基因转录诱导了肝细胞癌细胞系生成DCP。此项实验也说明PARP-1抑制剂可能可以非常有效地治疗肝细胞癌。
1.3 PIVKA-Ⅱ在肝细胞癌中的生物学功能 虽然PIVKA-Ⅱ在肝细胞癌中的生物学功能还不明确,已有很多学者从多角度出发,探讨PIVKA-Ⅱ在肝细胞癌增殖、血管生成等方面的影响。Suzuki M等人对PIVKA-Ⅱ作为肝细胞癌的一个潜在自体生长因子做了相关实验,通过培养肝细胞癌细胞株,定量检测、纯化PIVKA-Ⅱ,采用细胞增殖培养、免疫印迹分析法、荧光素酶基因报告分析等方法对PIVKA-Ⅱ的生物学机制进行研究,他们指出,PIVKA-Ⅱ可与肝细胞生长因子(HGF)受体蛋氨酸(Met)结合,而Met表达于肝癌细胞株Hep3B、SK-Hep-1和HT-29中,并使Met络氨酸残基磷酸化,激活Met-JAK1-STAT3信号通路,从而促进HCC的增殖,而PIVKA-Ⅱ并不会影响Raf-Mek erk-MAPK信号通路[6]。2014年的一篇综述中提到PIVKA-Ⅱ可能通过PIVKA-Ⅱ-KDR-PLC-γ-MAPK信号通路促进肝细胞癌血管生成[7]。
2 临床应用
2.1 PIVKA-Ⅱ在HCC诊断中的作用 自1984年Liebman在HCC中发现PIVKA-Ⅱ开始,便有很多学者对其做了大量的研究。2015年,Poté N等人研究表明,在肝细胞癌早期诊断上,肿瘤标志物PIVKA-Ⅱ明显优于传统标志物AFP,并且有对肝细胞癌微血管侵犯(MVI)的预测作用[8]。而且,Yu R等人对10 738例HCC高风险患者进行定量检测PIVKA-Ⅱ,最终有1 016例PIVKA-Ⅱ阳性(截断值:40mAU/ml)患者(至少有2种影像学检查或活检病理结果)确诊为HCC,占所有PIVKA-Ⅱ阳性患者的49.1%。而且,在已经确诊的HCC患者中,有241例PIVKA-Ⅱ阳性,早期影像学检查却是阴性。结果表明,PIVKA-Ⅱ在HCC与非HCC的鉴别诊断上,PIVKA-Ⅱ的受试者曲线下面积可以达到0.8,明显优于AFP[9]。张毅敏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肝癌组织中PIVKA-Ⅱ呈高表达,而且VitK2能够降低肝癌细胞中的PIVKA-Ⅱ水平、抑制肝癌细胞生长、降低肝癌细胞侵袭能力[10]。在亚太肝细胞癌管理临床实践指南中提到,不推荐血清AFP作为小肝癌的诊断方法,肿瘤标志物的联合检测可提高其诊断HCC的敏感性,且其特异性并不会变的更低[11]。
2.2 PIVKA-Ⅱ动态监测在肝细胞癌肝切除术中的应用 目前对肝细胞癌患者的治疗方法中外科治疗仍是肝细胞癌患者能够获得长期生存的最有效手段[12]。经手术切除术的BCLC分期B/C、B和C的患者5年生存率明显高于经TACE治疗的患者(OR分别为:2.71、2.77、3.03;P<0.000 1)[13]。但是肝细胞癌患者术后的监测仍然很重要。Meguro M等人的研究中将2004年1月—2012年5月期间接受过肝切除术的205例患者(105例HBV感染、100例HCV感染)纳入研究,进行回顾性分析,HBV和HCV感染者依据血清AFP和PIVKA-Ⅱ水平都被分为三组(两者都高组HH、一高一低组HL、两者都低组LL),进行组间肝功能指标、术后无复发生存率、总生存率等的对比[14]。Meguro M等人的结果得出,HBV感染组中LL组、HL组、HH组平均无病生存时间:64.81±7.47 VS 36.63±7.62 VS 8.98±6.17(P=0.001),平均总生存时间:85.30±6.55 VS 59.44±7.87 VS 46.57±11.20(P=0.018);HCV感染组平均无病生存时间:50.09±5.90 VS 31.01±7.21 VS 14.81±3.08(P<0.001),平均总生存时间:79.45±8.30 VS 58.82±7.56 VS 32.87±6.31(P<0.001)。很明显,无论是HBV或HCV相关的HCC手术患者,高水平的AFP和PIVKA-Ⅱ预后都很差,AFP和PIVKA-Ⅱ是独立的危险因素,与肿瘤的复发有关。 Feng X等人的研究指出PIVKA-Ⅱ对直径>3.0cm的肿瘤具有较高的敏感性,而且,无论肿瘤大小如何,在HCC的诊断上,PIVKA-Ⅱ都较AFP是更好的选择[15]。
2.3 PIVKA-Ⅱ动态监测在肝细胞癌肝动脉化疗栓塞术中的应用 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是目前被公认的肝细胞癌非手术治疗最常用方法之一。TACE治疗后肿瘤标志物的监测对HCC患者的预后也是至关重要的。Arai T等人采用回顾性研究的方法,以肿瘤标志物的变化趋势为基础,对经TACE治疗后复发肝癌患者进行疗效评估,研究得出PIVKA-Ⅱ变化趋势可能有助于评估复发肝癌患者TACE术后的治疗效果[16]。此研究将484例经原发性肝癌切除术患者进行门诊常规随访,每3个月做1次超声检查、检测血清AFP和PIVKA-Ⅱ,每6个月查增强CT扫描,最终以出现HCC典型的影像学特征的新病灶诊断复发,其中162例复发后行TACE治疗,最终142例患者纳入研究。这142例患者每3~4个月进行1次CT或MRI的检查,然后将TACE术前4周内和术后1个月内的动态增强CT进行对比,根据修订版实体肿瘤疗效评价标准(mRECIST)将术后疗效评估为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疾病稳定(SD)、疾病进展(PD),总缓解率为CR+PR、疾病控制率为CR+PR+SD。同时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对比TACE术前和术后1个月后第一次门诊随访时血清AFP和PIVKA-Ⅱ,分为低水平组(术前和术后肿瘤标记物水平均低于其截断值(AFP:100ng/ml和PIVKA-Ⅱ:100mAU/ml)、升高组(术后肿瘤标志物水平高于术前)、降低组(术后肿瘤标志物水平低于术前)。用Kaplan-Meier法计算TACE的总生存期(OS),并用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单变量数据分析得出PIVKA-Ⅱ和AFP变化与OS之间存在相关性P<0.000 1,PIVKA-Ⅱ或AFP升高组,OS中间值越小。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发现PIVKA-Ⅱ变化趋势与总缓解率相关(P=0.009)和疾病控制率相关(P=0.004),同时PIVKA-Ⅱ(高水平组 VS 低水平组:危险比8.47,95%可信区间4.54~15.84,P<0.000 1)可以作为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在HCC治疗的临床过程中,经常出现复发,而对于复发后的治疗经常采用TACE术。2015年,Hiraoka A等人通过检测肿瘤标志物AFP、AFP-L3和PIVKA-Ⅱ,将阳性肿瘤标志物(AFP≥100ng/ml;AFP-L3≥10%;PIVKA-Ⅱ≥100mAU/ml)数量作为TACE术后的预后评分,其中采用日本肝癌研究小组(LCSGJ)中提到的:TACE术后肿瘤标志物的持续升高作为TACE治疗失败的标志,研究结果指出肿瘤标记物阳性数量(≥2)是一个预测TACE术后反应的简单方法,更加详细的评估TACE治疗无效HCC患者[17]。Ichikawa等人分别用化学发光酶免疫分析法和电化学发光法检测TACE术前和术后1个月时的血清AFP和PIVKA-Ⅱ水平,联合mRECIST对未行手术切除而行初步TACE术的HCC患者的生存时间进行早期预测[18]。其研究中设定术前AFP或PIVKA-Ⅱ基线水平为AFP≥200ng/ml或PIVKA-Ⅱ≥60ng/ml,积极的反应为术后1个月时较基线水平下降50%,最终分析结果得出AFP基线水平<200ng/ml的患者平均总生存时间(Overall survial,OS)明显高于AFP≥200ng/ml的患者(29.4个月VS 6.1个月,P<0.000 1),而在AFP≥200ng/ml的患者中,治疗后AFP水平有无积极反应,对平均OS并无显著影响(11.5个月VS 11.5个月,P=0.620)。比较PIVKA-Ⅱ基线水平发现,PIVKA-Ⅱ<60ng/ml与PIVKA-Ⅱ≥60ng/ml的患者,平均OS并无明显差异(20.9个月VS 20.6个月,P=0.765),而治疗后PIVKA-Ⅱ有反应与较长的生存期显著相关(67.0个月VS 19.8个月,P=0.020)。这些研究结果都能得出,TACE术后定期监测血清PIVKA-Ⅱ可以有效预测预后。
2.4 PIVKA-Ⅱ动态监测在射频消融术中的应用虽然外科手术治疗是HCC患者能够获得长期生存的最有效手段,但是对于多数肝癌晚期患者,已错过最佳手术时期,近年局部射频消融术成为HCC非手术治疗常用的手段。2017年,Nitta H等人的研究表明射频消融(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治疗前阳性肿瘤标志物的数量可预测预后[19]。其研究中采用在RFA治疗前2周内检测AFP、AFP-L3和PIVKA-Ⅱ,这些肿瘤标志物的上限分别为20ng/ml、10%和40mAU/ml,超过上限被称为阳性肿瘤标志物。将纳入研究的患者分为阴性组、单阳性、双阳性和三阳性组,最后随访观察确定是否复发。经统计分析得出3年无复发生存率和总生存期为阴性、单阳性、双阳性、三阳性组分别为30%、19%、16%、11%(P=0.02)和94%、88%、66%、37%(P<0.001),多变量分析表明双阳或三阳组与肿瘤局部复发(HR 5.48,95%CI 2.44~12.33,P<0.001) 和总生存期(HR 4.21,95%CI 1.89~9.37,P<0.001)相关。以上数据表明,在RFA治疗前可通过联合检测PIVKA-Ⅱ、AFP及AFP-L3评估患者是否适用此治疗方式。另外,在HCC患者射频消融术后,PIVKA-Ⅱ是血管浸润最有效的预测因子,相比PIVKA-Ⅱ水平≤100mAU/ml,当PIVKA-Ⅱ为101~200mAU/ml时,危险比为1.95;PIVKA-Ⅱ水平>200mAU/ml时,危险比为3.22,较AFP及AFP-L3敏感性高[20]。Lee S等人的一项回顾性研究结果表明,RFA术后PIVKA-Ⅱ是一个独立的预后因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患者总生存期和无复发生存率的危险比分别为(HR 3.438,95%CI 1.33~8.877,P=0.011;HR 4.934,95%CI 2.761~8.816,P<0.001),而AFP只与无复发生存率相关(HR 1.995,95%CI 1.476~2.697,P<0.001),与总生存期无关[21]。
3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目前的很多研究都指出PIVKA-Ⅱ在肝细胞癌的诊断、预后监测、预测复发等多方面具有良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并且在与其他肿瘤标志物AFP、AFP-L3联合检测可提高其作用,但是仍需要大量临床研究以使其可能的临床价值最大化。另外,目前对PIVKA-Ⅱ在肝细胞癌中合成的机制中证实了PIVKA-Ⅱ是一个致癌因子,在HCC的发展中介导了促进HCC的增殖、侵袭和转移的信号通路的激活,因此,在未来有可能通过靶向抑制信号通路的方式治疗HCC。所有这些研究中,采取的临界值都没有统一标准,后续的还需要大量的实验,希望可以有确切的标准为HCC的早期诊断及预后监测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