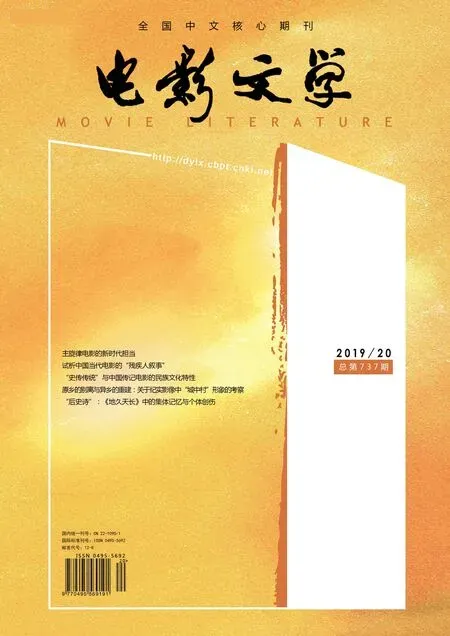形胜神穷:武侠影视剧中的数字奇观再商榷
叶绵耀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上海 200241)
数字技术的创新使电影与生俱来的照相美学与数字技术的虚拟美学相结合,把电影艺术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被誉为“现代科幻电影技术里程碑”的《2001太空漫游》(1968)通过计算机技术把科学想象中的“宇宙景象”具象化让人惊叹不已;乔治·卢卡斯在筹备拍摄《星球大战》(1977)时成立的“ILM”(工业光魔公司),开启了特效电影的时代。1990年之后,好莱坞电影运用数字技术制造视听奇观已是蔚然成风。《终结者2:审判日》(1991)中令人肾上腺素陡升的殊死搏斗、《侏罗纪公园》(1993)中远古的恐龙世界以及表现跨越阶级、超越生死爱情的《泰坦尼克号》(1997)都离不开对数字特效的倚重。
与好莱坞相比,数字特效在中国起步较晚,新世纪之后的《极地营救》(2002)、《惊涛骇浪》(2003)等电影在表现灾难场面时有所尝试,但是由于技术上的不成熟并未给观众带来震撼的视觉享受。数字特效对中国电影的美学观念真正造成冲击是从武侠类型片伊始。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开启了国产古装大片的特效化之路,《十面埋伏》(2004)、《无极》(2005)紧跟而上。2010年之后,古装大片趋于平静,取而代之的是古装魔幻大片,《白蛇传说》(2011)、《画壁》(2011)、《倩女幽魂》(2011)以及徐克的“狄仁杰系列”利用数字技术创造出亦幻亦真的空间环境,再到《妖猫传》(2017)中的大唐气象,这些影片中恢宏磅礴的场景取悦了观众的感官体验。
数字技术的触角同样也延伸至武侠电视剧,但带来了同质化的泛滥之象。玄幻缥缈的空间背景、洁白无瑕的磨皮滤镜、轻盈至极的武打动作,使这些作品更像是批量生产的流水线作业。数字技术通过后期制作从成本和人力上解决了武侠影视剧在实景拍摄中飞天遁地的难题,创作者们对数字技术的自信不言而喻,然而把数字技术仅当成营造视听快感的手段,游离于叙事之外的特效注定不能让观众从低层次的生理快感走向审美的高峰体验,引起他们对人生、历史和宇宙的思辨,因而大部分武侠影视剧都是有“形”无“神”,即形式上美轮美奂而内核上空洞单薄。
“形”与“神”是中国古典美学中一对重要的范畴,早在先秦两汉时就有相关论述。例如春秋战国时的《论语·雍也》论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强调了“质”和“文”的统一对形成君子人格的重要性,后世把其内涵外延至文学创作中对内容和形式的要求。西汉《淮南子》的《诠言训》中有言:“神贵于形也。故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穷。”在《说山训》中又说:“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两者都强调了“神”对“形”的主宰,只追求“形”必然达不到“传神”之境,后世的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亦延续了这一准则。例如绘画强调“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诗歌创作有“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唐·皎然《诗式》)的主张,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评价杜甫诗:“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由此观之,对“神”的重视,不仅是艺术创作与批评的法则,同时也是古典美学的接受原则。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当下武侠影视剧对数字特效的过度崇拜,只注重技术本身最终带来的不过是“形胜神穷”的奇观而已。
一、“子弹时间”消解了武打快感
武侠影视剧的武打快感主要取决于武打动作的设计与蒙太奇剪辑。“勇猛激烈的对打动作与快速密集的剪辑会形成一种连续不断的视觉影像的激流,会给观众造成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也就是说,影片尽量缩小镜头与镜头之间的时间距离与空间距离,使得本来单个的、间断的电影形成了一种快速的、完整的、连续的影像叙事链。”[1]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导演张彻的“新派武侠”即是通过学习西方动作片的剪辑方式来创造激烈勇猛的武打节奏,一反粤语片中舞台戏曲程式化的打法。“那时华语片通常三百左右镜头,我们才知道西片镜头是上千的!奇怪的是大陆和台湾的导演,有的似至今未知,所以节奏很慢”。[2]在香港“新浪潮”电影导演谭家明的《名剑》(1980)中,结尾李慕然与连环的决斗片段时长为186秒,143个镜头,平均每个镜头不到0.77秒,这种快速的剪辑方式使两人空中翻、前翻、后翻、鲤鱼打挺等各种武术动作令人眼花缭乱、瞠目结舌,生死胜负在电光石火的交锋之间,武打动作一气呵成,毫无拖泥带水之感。摇晃的镜头、移动摄影以及两人刺伤彼此之后的短暂对峙,动静有致,最后连环像火箭一样弹向李慕然被劈成两半石破天惊。香港影评人石琪认为此段落“堪称香港片最佳剑斗”[3],武打设计可谓臻至化境。
然而这种被学者贾磊磊称为“疾风暴雨式的剪辑”在当下已难觅踪迹,取而代之的是“子弹时间”式武打,这是当下武侠影视剧的数字奇观之一。“子弹时间”(Bullet time)也称为“时间的特写”,是一种常在电影、电视广告或电脑游戏中使用摄影技术模拟的变速特效,例如强化的慢镜头,其效果是凸显时间的静止和展示物体运动过程的美感。“子弹时间”因在好莱坞电影《黑客帝国》(1999)中男主角Neo后仰躲避子弹的慢动作而声名大噪。它最初在武侠电影中往往被用于诗意效果的营造,例如《英雄》(2002)中无名与长空在雨中对打,晶莹剔透的雨滴落在剑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但如若过度使用反而丧失了原来拳拳到肉的武打快感。
以1977年楚原导演的“邵氏”电影《三少爷的剑》与2016年尔冬升导演的版本为例,1977版影片时长为90分23秒,即5423秒,其中武打片段总时长为863秒,占比是15.92%。2016版影片时长99分50秒,即 5990秒,武打片段为1467秒,占比为25.45%。从理论上来说,后者的武打快感应比前者更强,但事实并非如此。1977版的武打段落极少持续1分钟以上,干净利落的武打风格使影片的节奏十分紧促。而在2016版中,“子弹时间”的滥用造成每个武打段落动辄两三分钟的时长。例如开篇燕十三与高通的决斗,大量的慢镜头把武打动作过程展露无遗,两人之间的互攻、躲避以及灯笼在空中的飘落都有短暂的定格。这种现象在网络剧《倚天屠龙记》(2019)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例如第四集中灭绝师太与杨逍在酒楼打斗时,杨逍运起内力把酒瓶、古琴攻向对方,酒瓶与古琴飞向灭绝师太的运动时间大大延长,丝毫没有表现出高手对决时的风驰电掣,双方甚至没有肢体接触就完成了一场打斗。这不仅影响了武打快感的呈现,并且时常中断叙事节奏。武侠影视剧中的慢镜头应该注意使用时的语境,例如第三集中纪晓芙在后山练剑时,“子弹时间”放慢了树叶落地的时间,漫天飞舞的树叶与女子轻盈的动作在慢镜头下相得益彰,给人“武舞”之美感。但是在攸关生死的对决之时,受众的注意力不在动作的“美感”,而在“快感”。
从伊莱休·卡茨的“使用与满足理论”来看,在武打场面中运用“子弹时间”造成暴力快感消逝的主要原因是它与受众对武侠的审美期待产生落差。卡茨将媒介接触行为概括为一个“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触—需求满足”的因果连锁过程,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会形成受众对某种媒介的期待,然后影响他们对媒介的接触,接触的结果可能会满足或不满足自身的需求,但无论结果如何都会影响到他们之后的媒介选择行为。观众之所以为武侠影视剧所吸引主要是基于古今文学对“江湖”“侠客”的渲染。武侠是“成人童话”,是“英雄梦”的投射,侠客的行动空间被放置于江湖中。虽然从唐传奇到宋话本再到明清的武侠小说乃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金庸古龙,对“江湖”的描述一直在变化,但不变的是,“江湖”是“一个带有象征色彩的文学世界,活动着一个个替天行道的布衣大侠,表演出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救世绝活”。[4]侠客应如唐代诗人李白在《侠客行》中所描述的那样:“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基于此类文学作品中对江湖与侠客的描绘所感染而沉淀的文化心理,刀光剑影、快意恩仇、以暴制暴、不理会官府的“江湖”自然而然就成为受众的集体想象,“暴力”也就成为武侠作品的叙事主题之一。
在社会因素层面,香港武侠影视剧对观众的“武侠观”有重要影响。武侠电影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武侠电影在内地与新社会格格不入被迫中断,直到80年代的娱乐片浪潮中才重回大众视野,武侠电影在香港反而得到延续和创新,可以说香港武侠电影是大多数受众的武侠观的启蒙者。“(香港)大众电影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激发与引导情感……旨在令观众看得过瘾。打斗或追逐都带有独特与生动的情感内容,如残暴、恐怖、怕事、谨慎等,又或这些情绪的混合”。[5]273-274这种特征影响了受众对武侠电影的审美期待。从武侠电影史来看,从张彻的“新派武侠”到走向国际的李小龙、成龙,都足以证明观众沉溺于那种一气呵成的武打所带来的酣畅淋漓之感。而当下武侠影视作品使用过多的“子弹时间”和慢镜头动作,本质上与受众的审美期待视野相抵牾。虽然它们通过放慢物体的正常运动速度和延长运动时间能制出梦幻和诗意的认知效果,但“暴力”的快感也消解于其中。这些武侠影视剧中的武打慢镜头大多数时候既不是苏珊·朗格的“情感符号”,也没能成为克莱夫·贝尔所言的“有意味的形式”,仅仅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空洞的展示。这也是当下武侠影视剧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武侠身体”的文化意味丧失
“身体”是“武”的载体,是武侠电影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符号,它的内涵始终区别于其他类型电影中的“躯体”。“在某种程度上,功夫电影可以被看作是史蒂文·夏米洛和琳达·威廉斯所称之为的‘身体类型片’,如同色情片、恐怖片和感伤剧一样提供‘一种越轨的感官刺激’……功夫片是关于身体的类型片,这种身体是如此特别、富有表现力、壮观甚而奇异”。[6]3在武侠电影史上,武侠身体的文化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早期实验电影中,对‘飞越’的身体经验进行电影化表达是关键性的一步,而这种奇观日后则成为武侠电影的一种类型传统”。[7]25320世纪20年代是武侠片/神怪武侠片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身体”在电影中不仅是吸引观众的噱头,例如在《红侠》(1929)中有女性裸露的画面,在《女侠白玫瑰》(1929)中展示了女性在操练时的腿部特写,更重要的是,邬丽珠、吴素馨、范雪朋等人在神怪武侠片中所饰演的“女侠”——她们灵活而健美的身体区别于当时家庭伦理剧中的孤苦瘦弱的女性形象。这些女侠被赋予了锄强扶弱的使命,在银幕上腾云驾雾救人于危难之中,呈现出反封建的现代启蒙意识。然而她们又没有完全挣脱父权的束缚,因为她们在行侠仗义时必须以易装的方式进入世俗社会,最后又必须牺牲婚姻和爱情,独自遁世。因此此时的女侠/女侠片“这一类型同时也制造(或者说视觉呈现)了一个独特的白话社会空间——一种模糊了前现代风俗和现代渴望、通俗趣味和先锋实践的乌托邦民间文化”。[7]258女侠实际上折射出彼时中国社会从前现代过渡到现代时的矛盾心态。
1967年张彻的《独臂刀》开辟了“新派武侠”,“身体”在电影中被风格化表现为“阳刚美学”。为了扭转此前香港影坛中的脂粉气,张彻起用了王羽、狄龙、陈观泰等一批肌肉强健的男演员,他们在决斗时故意脱掉上衣,袒胸露乳上演盘肠大战,并以断臂、刺伤、血如泉涌等方式对身体进行凌虐。而从李小龙开始,“‘功夫’已经永久性地成为跨国想象的一部分”。[6]2他在打斗时的怪叫与怒喝以及富于节奏感的重击与挥舞把中国功夫推向世界,也把中国电影推向好莱坞,以至于在昆汀·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2003)中处处有李小龙的影子。成龙跻身于国际巨星行列以及他长寿的明星地位也是因为把身体机能无限放大,超出常人身体机能的极限。“他不惜一切讨好观众,用血肉之躯炮制亡命的特技场面,又在片尾字幕给观众重温剪去受伤的片段。这些片子令人肾上腺素上升的部分原因,在于摄影机记录的险情,都是真实的”。[5]262杨紫琼、章子怡同样也是带着“打女”的标签闯入好莱坞的。因而,无论是作为白话现代主义中的视觉景观,还是美学风格的物化表现,或是成为“东方/中国”的意指,表演性的“武侠身体”始终是迥异于其他类型电影的视觉符号。
然而数字技术大大降低了导演与演员进入武侠世界的门槛,因为武打动作可以通过后期技术合成,这就导致了演员的身体机能不再被重视。早期的“侠女”邬丽珠、吴素馨以身体健美著称,王羽、狄龙、陈观泰都有武术功底,李小龙和成龙就更不用说,刘家良和程小东更是从武术指导走向导演创作。在表层上,功夫明星与武侠类型片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在深层上,功夫明星因为自己的身体机能而在武侠电影中承担着特定的文化意味。反观当下的武侠影视剧,“功夫明星”与“类型片”的对应关系模糊导致“身体”的这种文化指涉功能泯然于众声喧哗的影视剧市场中,陈晓(2014版《神雕侠侣》中杨过的扮演者)、杨旭文(2017版《射雕英雄传》中郭靖的扮演者)、曾舜晞(2019版《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的扮演者)、秦俊杰(2019网络剧《听雪楼》中萧忆情的扮演者)等这一批武侠电视剧的主演与其他新生代偶像共同构建了当下的“小鲜肉”景观。换言之,如果说当下武侠影视剧中的“身体”还有文化指涉意义的话,那么仅仅是作为物欲消费的符号表征而已,然而这并不具有独特性,因为身体的这种指涉意义同样存在于玄幻、爱情、校园等其他类型和题材的影视剧中。这是由于在消费语境下,功用性身体指数价值由“美丽”与“色情”两个主题主导[8]124。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绣春刀》系列中为什么起用演技平平的刘诗诗与杨幂,没有谢晓峰的风流倜傥与文韬武略的林更新依然能出演《三少爷的剑》(2016)。
在早期的武侠电影中,由于演员具有一定的武术功底而减少对特技的依赖,表演性的身体也获得较高的观赏性。当下武侠影视剧为了赢得收视率与票房而起用具有庞大粉丝群体的偶像明星,数字特效为他们打开了方便之门,因为只要通过后期合成,人人都能成为飞天遁地的武林高手,但是诸如在空中定格再加上三百六十度的旋转不仅令人审美疲劳,同时也失去了承担特定文化意味的可能,“武侠身体”也就变成了拒绝被灵魂覆盖的“皮囊”,正如波德里亚所言:“如果说以往是‘灵魂包裹着身体’,今天则是皮囊包裹着它,但皮囊并非那作为裸体(因而欲望)之泛滥的皮肤:皮囊就像是魅力的服装和别墅,就像是符号,像是对模式的参照(因此可以被裙子取代而不发生意义上的改变,正如我们今天在剧院及其他地方发现对裸体不择手段地利用那样,在那里尽管挑起了伪性欲,但仍作为时装例词中的一个多余词条而出现)。”[8]122
三、“场景失真”造成表意减弱
由数字合成的场景“失真”在当下的武侠影视剧中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在后期制作时技术上的不成熟造成场景“布景化”,观众能明显感受到背景与人物的脱离。例如在电视剧《神雕侠侣》(2014)第一集中,林朝英身着喜服在漫天大雪中起舞而全身却片雪不沾,这种弊病同样存在于电影《三少爷的剑》(2016)的开场。在第六集中,郭靖、黄蓉等人带着杨过乘船返回桃花岛,荧幕上的船与大海没有融为一体,能明显地看出是通过把船放置于绿幕前拍摄,后期“抠”掉绿色背景换上大海背景,“抠图”的制作方式使整个场景看起来十分虚假。
二是通过数字技术制作出来的场景与观众的现实生活经验错位而造成了虚幻。悬崖山洞、江河湖海是武侠作品中常出现的场景,然而数字合成取代实景拍摄之后,众多影视剧作品中的“悬崖”无一不是云雾缭绕,仿佛悬浮于云端之上的蓬莱仙境,例如《三少爷的剑》(2016)中谢晓峰与燕十三最后决斗的场景,群山漂浮于云海之中,苍穹触手可及,影像风格与网络游戏中的场景设计一般无二,这也是此影片最大的败笔。燕十三乘船去神剑山庄、神剑山庄外的森林石梯以及慕容秋荻带人攻打神剑山庄无一不透露着浓浓的“网游”趣味。其实,数字技术不应该受责备,但只有“出于艺术的要求,以及拍摄的成本和拍摄可能性的考虑,用来拍摄那些难以拍成或者不便拍摄的镜头,或者是对镜头细节进行加工和修改,而且,这样做的依据和目标都是现实感和真实感”[9]的技术处理,观众才不至于出戏。毕竟,武侠中的“江湖”虽是与庙堂对立,但人物的生存空间依然是基于世俗的现实,“武侠”不是“仙侠”。
数字合成的场景对叙事造成最糟糕的后果之一就是背景环境独立于叙事与表意。中国古典美学十分强调环境和景物的表意作用,明代文学家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有言:“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浑然成,其浩无涯矣。”情中有景、景中含情的诗才能有“气”,这是古典审美中的最高范畴。这一审美趣味在胡金铨的《侠女》(1971)中得到极致体现。东厂高手最后一次追杀杨慧贞等人时,慧圆大师带着弟子伫立在岩石上,脚点树叶施展轻功降落在敌人面前。这一过程采用逆光仰拍,并插入缥缈的烟雾、波光粼粼的水面以及阳光点点的树叶等镜头,这与当下用数字技术做出来的假花、假树、假天空相比,环境的真实质感更加强烈,并且在人物与画面的天人合一中营造出禅宗的空灵之意。而网络剧《听雪楼》(2019)虽复制了《卧虎藏龙》(2000)中的竹林对决、《英雄》(2002)中的胡杨林之战与《十面埋伏》(2004)中的花海等美轮美奂的场景,但视觉特效与叙事的脱节注定对提升作品的意蕴毫无帮助,想象中的赞扬之声并没有随之而来,也没有掀起收视热潮,在平淡无奇中寂寞落幕。
电视剧《新甘十九妹》(2015)为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较好的探索。此剧是一部传统武侠的复古之作,在武打方面,全部采用吊威亚的近身肉搏实打的拍摄手法,为数不多的用数字特效制作的场景成为全剧的亮点。例如第十二集中甘十九妹在荷花池大战尹剑平,两人足尖轻点荷叶,四围悬浮着被剑气掀起的荷叶,使得刚猛的武打中又不乏柔美韵味。数字技术在此剧中没有成为一味追求展示奇观的手段,而是用于解决在实拍中无法完成的场景。更关键在于此剧全部采用磅礴大气的实景拍摄,环境成为表情达意的媒介。
在第十四集中,甘十九妹在巢湖渡口识破尹剑平的真实身份后,由于两人身份的对立发生一段武打情节,值得注意的是此段落中有四个“潮水袭岸”的镜头(如图1~图4)。从麦茨的理论来看,它们是独立镜头中的非陈述性插入镜头,虽然不属于故事情节的范围之内,但在叙事和表意层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个镜头在甘十九妹与尹剑平执剑对峙时,其作用是使情绪从悠扬过渡到急促,颇具“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唐·许浑《咸阳城东楼》)的意味,属于“起”。第二个镜头惊涛击石,犹如敲响的战鼓,两人开始短兵相接,是“承”。第三个镜头潮水急且浑,暗示着叙述的转折。甘十九妹的武功在尹剑平之上,但对他颇有惺惺相惜之意,未尽全力而稍落下风,此镜头后反守为攻,形势急转。第四个镜头在胜负之后,潮水恢复清明,正是“横风吹雨入楼斜,壮观应须好句夸。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宋·苏轼《望海楼晚景五绝之二》),即为“合”。

图1

图2

图3

图4
《新甘十九妹》(2015)采用大量极淡极雅的天青色调,具有古典意味,此段落也同样如此。“渡口”“潮水”等意象在古典诗词中有哀愁伤情之意,例如“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唐·张祜《题金陵渡》),“渚寒烟淡,棹移人远,飘渺行舟如叶”(宋·姜夔《八归·湘中送胡德华》);粤曲南音《客途秋恨》中的缪莲仙亦是在“孤舟沉寂晚景凉天”时独倚蓬窗忆多情歌女;在武侠小说里最广为人知的渡口是《神雕侠侣》中杨过与郭襄初遇的风陵渡口,从此误终身。因此,在此片段中的“渡口”已不仅是叙事空间,还是独特的审美意象。上一代的家仇和师仇延续到甘十九妹与尹剑平身上,惺惺相惜的两人终究要站在敌对面,起起落落的“潮水”是矛盾纠结的内心外化。“渡口”在剧中出现多次,全剧也是在黄昏日落时的渡口中落幕:身中剧毒的甘十九妹与尹剑平相偎在渡桥上,遥望着日落,等待奇迹的出现。“渡”亦是佛家的“渡”,是重生。“君看渡口淘沙处,渡却人间多少人。”(唐·刘禹锡《浪淘沙》),可唯独“渡”不了这一对有情人。“宿命”是武侠作家笔下无解的难题,古龙如此,萧逸亦如此。实景拍摄为还原武侠小说中的基调提供了良好的媒介,“寓情于景”是古诗词常用的手法,王国维亦强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但是当下的武侠影视剧创作运用数字技术有偷闲省事之嫌:在摄影棚中布置三两道具,再配上一块绿布,众人便在这个狭小的空间中进行表演。虽然后期通过技术把背景处理得逼真非常,但它们始终是“现实的影子”,和“真”隔着一层。例如通过对比2003版与2017版《射雕英雄传》中郭靖、洪七公与老顽童被黄药师驱逐离开桃花岛后,在海中航行船沉的情节可以发现,2003版采用的是实景拍摄,气势宏阔,大船急速行驶时劈开的波浪以及下沉时海水涌进船舱都渲染了形势危急。而2017版是在棚内拍摄,后期再用数字技术处理。大船下沉时海面波澜不兴,除了摇晃摄影机制造船往下沉的假象之外,环境因素丝毫没有作用于情绪渲染。
四、结 语
技术没有“原罪”,相反,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2D、3D到4D足以说明影视创作的每一次提升都离不开技术的创新,数字技术“拓展了影像时空的表现力,所创造的虚拟现实、超现实、沉浸感以及游戏感为电影观众提供了更加丰富和逼真的观影体验”。[10]但是,于武侠影视剧而言,专注于数字影像奇观的制造,导致武打快感弱化、“身体”沦为消费欲望对象以及环境表意功能丧失也是必须反思的问题。对形式的过度强调必然会忽视内容建设,极度追求视听生理快感也会导致精神痛感,表面的浮华始终弥补不了内涵的苍白。技术仅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本体,不能代表一切,更不能成为技术的奴隶。归根结底,影视作品是艺术作品,是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它们不仅要冲击观众的视听感官,更要冲击观众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