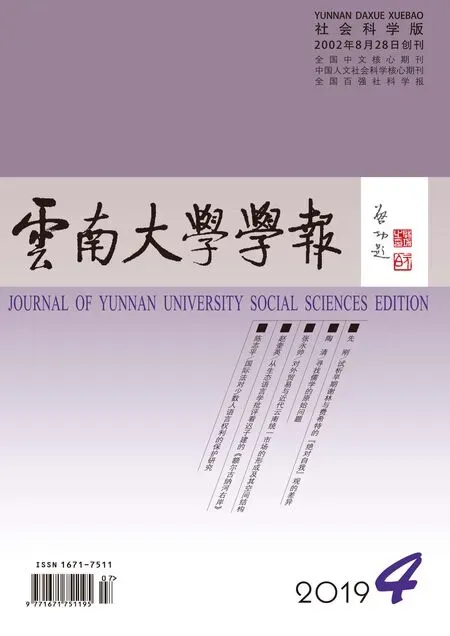从生态语言学批评看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
赵奎英
[南京大学,南京 210093]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迟子建是具有比较突出的生态精神和生态语言意识的作家。其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该小说以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女酋长的口吻,讲述了我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鄂温克族近百年的沧桑历史和生存现状。从生态批评角度对《额尔古纳河右岸》进行研究的不少,但从生态语言学批评角度对其进行专门考察的不多。“生态语言学批评”是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两大基本范式之一。它是从生态语言学角度对“语言系统”和“语言运用”进行批评分析,指出其中的“生态”或“非生态”因素,以促进语言结构和语言运用的生态化,从而达到促进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或改善的目的。以往的生态语言学批评多以普通语言系统和非文学性话语文本为批评对象,但由于生态语言学研究与批评的“跨学科”甚至“超学科”性质,使其完全可以运用到对文学文本的批评分析之中。因此我们这里试从生态命名、生态句法、生态叙事等方面对《额尔古纳河右岸》进行生态语言学批评,以期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的生态语言和生态精神。
一、迟子建作品中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语言
《额尔古纳河右岸》于2008年获得茅盾文学奖。迟子建在颁奖大会上发表获奖感言时说:“这个时刻,这个夜晚会留在我的记忆当中。因为我觉得跟我一起来到这个颁奖台的不仅仅是我,还有我的故乡,有森林、河流、清风、明月,是那一片土地给我的文学世界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注]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71f3bc0101soq7.html。在谈论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时又说:“没有大自然的滋养,没有我的故乡,也就不会有我的文学。” “有了故土,如同树有了根;而有了大自然,这树就会发芽了。只要你用心耕耘,生机一定会出现在眼前。如果没有对大自然深深的依恋,我也就不会对行将退出山林的鄂温克这支部落有特别的同情,也不可能写出《额尔古纳河右岸》。对我而言,故乡和大自然是我文学世界的太阳和月亮,它们照亮和温暖了我的写作和生活。”[注]迟子建、胡殷红:《人类文明进程的尴尬、悲哀与无奈——迟子建谈长篇新作〈额尔古纳河右岸〉》,《艺术广角》2006年第2期。由此可以看出,故乡、土地、大自然对于迟子建创作的意义,亦可以看出迟子建作品所具有的人与自然亲密相依的关系。
但作者之所以能够创出作《额尔古纳河右岸》,不仅因为她对大自然的依恋,更不是因为现实世界中人与自然亲密和谐的关系,而且出于作者对大自然被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被破坏的忧愤和不满。迟子建在谈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创作历程时说:“那片被世人称为‘绿色宝库’的土地在没有被开发前,森林是茂密的,动物是繁多的。”但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大规模、持续不断的“开发和某些不负责任的挥霍行径,使那片原始森林出现了苍老、退化的迹象。沙尘暴像幽灵一样闪现在新世纪的曙光中。稀疏的林木和锐减的动物,终于使我们觉醒了:我们对大自然索取得太多了!”但作者也并非一味地反对工业文明,反对开发。她说:“其实开发是没有过错的,上帝把人抛在凡尘,不就是让他们从大自然中寻找生存的答案吗?问题是,上帝让我们寻求的是和谐生存,而不是攫取式的破坏性的生存。”[注]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264页。以下关于该小说内容的引文均出自此版本。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对当今由于人类过度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危机是有清醒认识的,她的创作是具有一种自觉的生态保护意识的。
迟子建作品不仅具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其作品的语言也具有突出的生态特征,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生态语言”。对于什么是“生态语言”,我们可以从生态语言学的角度做一下大致的界定。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生态语言是人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基础上生成地体现了一种全息性关系[注]根据钱冠连的解释,“语言全息论(the theory of language holography)是以生物全息律、宇宙全息律与系统论来解释语言内全息状态与语言外全息状态的语言理论”(钱冠连:《语言全息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0页)。我们这里用“全息性”来表达语言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心理环境以及宇宙整体之间或天地万物之间的一种全方位的息息相关的关系。和生态意识、生态观念,或有利于表现或促进人的生态意识、生态观念的语言。
那么,什么样的意识、观念才称得上是生态意识、生态观念呢?我们知道, “生态学 (ecology)的前缀eco-是从古希腊词‘oikos’(家或栖居之地)发展而来的”,“生态学”的原义是“房屋,栖居地,住所”。[注]Jonathan Bate,The Song of the Earth. London: Picador, 2001, p.75.对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学”, 海克尔则把它界定为“关于自然的经济的知识”,“是研究生命有机体与有机环境和无机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的科学”。[注]Quoted in Robert P. Mclntosh,The Background of Ecology: Concept and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s, 1985, pp. 7-8.综合生态学在古希腊语中的原义和海克尔对生态学的界定,可以说“生态”这一概念包含三个关键义项:那就是“家园”“生命”与“相互关系”。并且人们在强调生态的“关系”含义时,总是把它与反对主客二分、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相联系。在这三个关键义项中,如果说“生命”是生态概念的灵魂,“家园”是生态概念的基底,“相互关系”则可以看作使生态概念各义素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的血脉,三者相互依存、共同构成生态概念的意义整体。如果说一个人是具有生态观念、生态意识的,就意味着他是关心栖居家园的,关心生命存在的,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而反对主客分离、人类中心主义的。[注]详见赵奎英:《论自然生态审美的三大观念转变》,《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根据这一界定,所谓生态语言,也可以说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基础上生成的、关心生命存在、关心栖居家园,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而反对主客分离、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全息性”语言。如果我们按以上标准来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具有生态意识,一部作品的语言是不是生态语言,我们通过考察可以肯定地说,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具有自觉的生态意识的,这部作品的语言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生态语言”。而要想更深入地理解这部作品语言的生态性,还需要从生态语言学批评角度进行一些具体分析才行。
二、生态命名: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
《额尔古纳河右岸》语言的生态性首先表现在大量使用体现出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自然词汇上。大量的自然词汇的使用标志着该作品的语言是从自然中生长出来的有根的语言,它体现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程度。迟子建在谈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创作过程时曾经说:一部作品的诞生,就像一棵树的生长一样。《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棵“树”就是在“那片春天时会因解冻而变得泥泞、夏天时绿树成荫、秋天时堆积着缤纷落叶、冬天时白雪茫茫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从山峦到海洋》)迟子建把《额尔古纳河右岸》比喻成一棵“树”,把故乡、土地、大自然比喻成树的“根”,清楚地表明《额尔古纳河右岸》就是在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生长起来的。
我们知道,文学作品不能凭空存在,文学作品是存在于它的语言之中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生长起来的,这也决定了它的语言也是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生长起来的有根的语言。这种有根语言的直接表现就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描写动物植物、风雨雷电、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的自然词汇,这些自然词汇汇聚起来讲述的不只是鄂温克族“人”的历史,也是鄂温克族“栖居地”的历史,在这里活动的不只是鄂温克族的人,还有在这片土地上生成变幻的各种自然风物,如驯鹿、黑熊、灰鼠、山鹰、猎犬、狗鱼、明月、清风、河流、星星、山脉、森林等等。这里的一切自然物(以及人造物)都是像人一样具有生命的,在这里人和自然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用作品中的话说:“如果把我们生活着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比喻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的话,那么,那些大大小小的河流就是巨人身上纵横交织的血管,而它的骨骼,就是由众多的山峦构成的。”“山上的树,在我眼中就是一团连着一团的血肉。”(《额尔古纳河右岸·黄昏》)由此可以看出,在这里,自然万物都是有生命的,人与自然是血肉相连的。只是迟子建这里的语言仍然具有一些“拟人化”特征,是以一种“拟人论”的思维来思考人与自然的连续性的。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大量使用自然词汇,一方面表现在作品语言中的词汇大量指涉自然事物上,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作品经常以自然现象给人物进行命名上。如作品中的人物妮浩为自己的女儿取名为“交库托坎”,“交库托坎”的意思为“百合花”;为自己的小儿子取名为“耶尔尼斯涅”,意为“黑桦树”。百合花美丽、纯洁,黑桦树结实、健壮,可惜这些寄寓了美好寓意的名字,并没有给这些孩子带来美好的命运,两个孩子接连夭折。所以当作品的主人公,也是故事的讲述者“我”给孙子起名字时,“一想到妮浩给孩子所起的与花草树木有关的名字是那么的脆弱”,便“索性给他起名叫九月, 因为他是九月生的”。想着“神灵能够轻易收走花草树木,但它却是收不走月份的”。但无论是以花草树木来命名,还是以季节月份来命名,很显然都是以自然现象来给人物命名的。
迟子建不仅善于给作品中的人物用自然现象、自然事物命名,而且也喜欢给没有名字的自然事物以名字。如作品中写道:“山峦跟河流不一样,它们多数是没有名字的,但我们还是命名了一些山。比如我们把高耸的山叫阿拉齐山,把裸露着白色石头的山叫作开拉气山,将雅格河与鲁吉刁分水岭上那片长满了马尾松的山叫作央格气。将大兴安岭北坡的那座曾发现过一具牛头的山称作奥科里堆山。”(《额尔古纳河右岸·黄昏》)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存在着大量类似的给没有名字的自然事物尤其是山川、河流这些自然地理命名的现象。不管这种命名,对于迟子建来说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但这种命名从生态语言学批评的角度看,是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的。这种“命名”的生态价值当我们联系语言中的“无名”“抹除”现象时可以看得更清楚。根据吉布斯对英语中的物种名称的调查,那些更易发现或被认为对人类非常重要的物种,往往会获得多个命名,当有些物种不易发现,或被认为对人类来说不重要的时候,它往往无法获得命名,出现“词语空缺”现象。[注]朱长河:《认知语言学与生态语言学的结合——以词汇系统为例的可行性分析》,《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 2期。很显然,当一种植物由于对人类无用无法获得自身的命名而只能归入“杂草”之类时,它们自身的价值是不会得到承认的,人们也是很难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对它们加以保护的,生态系统的退化也就在所难免了。因此对“自然现象的命名”是德国生态语言学家穆尔豪斯勒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他的课题讨论了“通过重新命名小型有袋动物或重新引入古老的土著名称来拯救数量不断减少的小型有袋动物”的尝试。[注]Alwin Fill and Peter Mühlhäusler eds.,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1, p.50.
斯提布在《生态语言学》中曾经专门谈到语言的“抹除”现象。根据他对“抹除”的界定,如果一种自然事物没有名字,也就意味着它在语言中被“抹除”了,这种事物当然也是不受重视的。斯提布明确地将“抹除”界定为“人们心智中对那些不重要或者不值得考虑的生活领域的一种叙事”。[注]Arran Stibbe,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160.因此,如果对一种事物,知道它是存在的,但不给它一个名称,这是人们对这种事物不够重视、不够尊重的结果,就像在人际交往中,不称呼别人的名字或称谓,用“喂”的方式与人打招呼,或用“那个女人”“那个男人”谈论一个人那样,都是不够尊重对方的表现。当自然事物没有自己独特的名字时,它也就没有自己的独特存在。无名字是对自然事物独特存在的抹除,无法表达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友好关系,当然也不利于人们对这种自然事物的保护。这也是容易让自然事物自生自灭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说:“那时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森林,不仅有遮天蔽日的大树,而且河流遍布。所以很多小河是没有名字的。如今这些小河就像滑过天际的流星一样,大部分已经消失。”(《额尔古纳河右岸·清晨》)这段话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正印证了这种情形。
当然,有名字的河流也可能会消失,但它的消逝是在“光亮”中的消失,容易引起人们的警醒和注意。但那些没有名字的存在则是处于“冥暗”或遮蔽之中的,它的消失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郭象在《庄子·齐物论》注中说:“夫名谓生于不明者也。”意思是说,“名”是从冥暗“不明”中产生的,它因此具有使“不明”者进入光亮的“明”的作用,具有使不存在者存在的“显迹赋形”的作用。而海德格尔一再强调语言的光照性、澄明性,认为“命名”是一种“让显现”,“让到场”,也正与此相通。海德格尔说:“唯语言才使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进入敞开领域之中。在没有语言的地方,便没有存在者的任何敞开性。”“由于语言首度命名存在者,这种命名才把存在者带向词语而显现出来。”[注][德]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294页。海德格尔又说,“语言的使命是在作品中揭示和保存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诗的本质是一种创建性“命名”。[注][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0页,第44-45页。在海德格尔那里,并非分行排列的语言作品才是诗,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当然小说本质上也是诗,它也是对存在的创建性命名。而命名对于自然的存在具有本质性的意义,它可以使自然存在者的存在得到“显现”和“保存”。
而斯提布的生态语言学批评也正从“凸现”的角度谈到“命名”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一般化的表达”可以通过结构化实现对表达对象的“同质化”,而“反对一般化的极致就是命名——通过名字表现个别化。”通过个性化的命名,“个体被表达为独一无二且不可替换的,同质化则与之相反,个体只是更大组织或群体的不可区分的一部分”。[注]Arran Stibbe,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p.180.斯提布的这种思想受到查尔斯 ·爱森斯坦关于“同质化”与“个性化”问题看法的影响。爱森斯坦认为,除非我们开始看到物体和生命体的独特性和价值,我们不会关心他们,并会最终摧毁他们,并提出应用“神圣”一词来描述“独特事情”的价值。在他看来,“神圣的物体或存在是特别的、独特的。因此是无价的,不可替换的”。斯提布由此认为:增加个体的人、动物、植物、森林或河流凸显性的语言,有助于抵抗同质化的倾向。用爱森斯坦的话说,其可以构建一种“神圣性”的感觉。[注]Arran Stibbe,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p.181.而命名正是这样一种抵抗同质化、增强事物个体性和独特性也是增强其神圣性的手段。而迟子建的作品中的那些个性化命名,同样使命名的事物最大程度地凸现,并使人与自然获得了一种深层次的交融。如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作品中的“我”,也是故事的讲述者为自家的爱犬取名“伊兰”,作品中的人物达西为捉来的山鹰取名为“奥木列”,拉吉米为刚出生的雪白的驯鹿仔取名为“木库莲”都发挥了这种个别化、独特化和神圣化的功能。由此来看,《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自然命名,是具有重要的生态文化价值的。
但这里一个有趣且发人深思的现象是,《额尔古纳河右岸》故事的讲述者“我”,命名了许多没有名字的山川河流,也提到了书中出现的其他所有人的名字,但却唯独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她说:“我讲了一天的故事,累了。我没有告诉你们我的名字,因为我不想留下名字了。我已经嘱咐了安草儿,阿帖走的时候,一定不要埋在土里,要葬在树上,葬在风中。只是如今选择四棵相对着的大树不那么容易了。”“阿帖”的意思就是汉语中的“奶奶”。一个热衷命名自然事物的人却成了“无名者”,让自己留在没有名字的领域,这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呢?如果说命名是个别化,是一种照亮和突显,那叙述者对自我的无名化,是不是也正代表了作者对自我的一种有意识地“抹除”?这种有意识地抹除,是不是正标明了一种人类自我有意后退的立场呢?如果这样来看,《额尔古纳河右岸》讲述者的“无名化”也是具有深刻意味的,它可以让人更好地退回到或保留在自然之中,达到人与自然的更深层次的一体交融。
三、生态语法:人与自然的连续性
迟子建作品语言的生态性,不仅表现在大量运用自然词汇、自然命名上,而且也体现在使用生态语法中。应该说,生态语法的类型是不固定的,它在不同作品中有不同的表现。但生态语法从精神内涵上来说,又是具有某种共同的标准的。大致说来,生态语法应该是那种体现了生态观念,或有利于表现生态观念、生态世界整体或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的语法,而不是那种把人与自然割裂开来的二元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语法。反之,则应该被视作“非生态语法”。关于英语中的非生态语法,生态语言学批评的开创者韩礼德有过富有启发性的批评分析。根据韩礼德的观点:英语语法的非生态性主要表现在它对人类与其他非人类存在者加以区分、打破人与自然之间的连续性上。首先一个区分就是人类施事者与非人类施事者之间的区分。
韩礼德指出,在这种语法中,人类处在施事极的主动的顶峰,而其他没有生命的物体则被放置在另一端。这些事物只能被施加行为而不能施为,并且他们一直待在那里直到被打扰。只有在灾难性的语境中,没有生命的事物才被比喻性地界定为施事格,它们才有可能变成某个摧毁性的物质过程作为“亚类”的行为者。例如,地震摧毁了城市,大火损坏了屋顶,一个树枝倒在了车上等等。英语语法不把没有生命的物体呈现为行为者,当然也不把它呈现为进行中的构成性或保存性的过程。因此,这种语言环境中的人们会认为“各种事情正是森林做的”之类的表达是有问题的。因为“在英语中,当我谈到一种无生命的事物时我说‘它在干什么?’意味着‘它为什么在那里?——把它拿开。’因此‘森林正在干什么?’意味着把它清除掉。而不是期待这样的回答:它在贮存水分,它在净化或湿润空气,它在防止洪水”等等。“这种语言使我们很难具有严肃的把无生命的自然看成是事件的主动参与者的观点。”[注]Michael Halliday, “New Ways of Meaning”,Alwin Fill and Peter Mühlhäusler eds.,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p.194.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根本原因正是对人类与非人类存在者在语法中进行尖锐的二元区分。这种区分不仅表现在对施事者与非施事者之间,也表现在对有意识的与无意识的、能感知的与不能感知的、能理解的与不能理解的等等存在者之间进行区分。韩礼德指出,“这种对现象进行二分的理论在历史的某个阶段上对于我们的生存是明显重要的,但它现在正走向尽头。因为它在‘我们’与其余生物之间强加了一种严格的非连续性”。[注]Michael Halliday, “New Ways of Meaning”, Alwin Fill and Peter Mühlhäusler eds.,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p.195.
但韩礼德所说的这种英语普通语法中的种种二元区分,其实在文学语言中是经常会被打破的。在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我们更会发现打破这种区分的诸多例证。如果说这种区分的语法是一种“非生态语法”的话,那么《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打破这种区分的语法,则可以说是一种“生态语法”了。因为在这里,万物都是有灵的,一切事物似乎都具有与人同等的主体性、主动性,都具有感受力、理解力,它们可以听懂人类的语言,也是完全可以作为施事者发起活动的。如小说中写道:“如果雨和火这对冤家听厌了我上午的唠叨,就让安草儿拿进希楞柱的桦皮篓里的东西来听吧,我想它们被遗落下来,一定有什么事情要做的。那么就让狍皮袜子、花手帕、小酒壶、鹿骨项链和鹿铃来接着听这个故事吧!”(《额尔古纳河右岸·清晨》)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非人格事物是可以像人一样做施事者的,“雨雪”可以把人看老,“镜子”也是可以看山、看树、看云、看人的。不仅“雨和火”那些自然现象可以听懂人的故事,那各种人造的物件,也都能够听懂人的故事,并且它们还“一定有什么事情要做”的。在通常的语法中,非人类存在者,尤其是无生命的存在者,是不具有施为能力的。但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不仅风雨雷电等自然力量、自然事物可以作为施事者,连“狍皮袜子、花手帕”这些看起来没有生命的存在物也是可以做施事者的。让非人类存在者、非意识、非生命存在者担当施事者的角色,不仅可以打破语法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区分,而且这种主动化的施事者的角色,还可以增强对非人类存在者本身的凸显。
斯提布在《生态语言学》中说:在个性化和个别化之外,通过对从句中的参与者的“前景化”也可以增强存在者的凸显,并且根据Van Leeuwen的描述,说明了“人们(或者其他物种的成员)是如何通过主动化而在语言中前景化的”。Van Leeuwen认为,在活动中,当社会角色被表示为主动的、动态的力量时,就是主动化;而当他们被表示为“承受”某个活动或者“居于接受终端”时,则是被动化。主动化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被实现:如在及物性结构中,社会角色被编码为物质过程中的行动者,行为过程中的行为者,精神过程中的感知者,语言过程中的讲话者,或者是关联过程中的指派者等等。而当一种社会角色被主动化后,他也就被最清晰地前景化了。[注]Arran Stibbe, Ecolinguistics: Discours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182.实际上,不仅人类社会中的角色可以通过在活动中的主动化而被前景化、被突显,其他物种角色也是如此。“当参与者被表示为做、思考、感触或说某些事,而不是被做的时候,其就被主动化了”。[注]Arran Stibbe,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182, pp.183-184.而迟子建小说中描写到的各种自然事物、自然现象,甚至人造物件,都往往通过这种主动化而被前景化、被突显出来了。这种“主动化”因此也是一种“生态语法”,具有重要的生态文化意义,它凸现了自然的主体地位,加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连续性,创造了一种人与自然连续一体、和谐共生的“生态共同体”话语。
四、生态叙事: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对话
我们知道,生态文化的核心目标就是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要想重建这种关系,就要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话、交流与联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不首先面对一系列的语言问题:诸如自然具有与人交流的能力吗?或者说其他动物或人类之外的自然有语言吗?如果语言只是人类的语言,语言与自然、环境或世界之间又是什么关系,人类能够通过语言指称或达到自然世界吗?等等。这些问题是生态文学、生态文化研究面对的问题,也是具有生态语言意识的作家要面对的问题。而迟子建也正是这样一位具有自觉的生态语言意识的作家,她通过自己的作品思考并回答了这一问题,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独白语言观,并用一种对话体的生态叙事具体展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她说:
我相信动物与植物之间也有语言的交流,只不过人类生就的 “智慧” 与这种充满灵性的语言有着天然的隔膜,因而无法破译。鱼也会弹琴,它们把水底的卵石作为琴键,用尾巴轻轻地敲击着,水面泛开的涟漪就是那乐声的折射。我想它们也有记录自己语言的方式,也许鸟儿将它们的话语印在了树皮上,不然那上面何至于有斑斑驳驳的沧桑的印痕? 也许岩石上的苔藓就是鹿刻在上面的语言,而被海浪冲刷到岸边的五彩贝壳是鱼希望能到岸上来的语言表达方式。[注]迟子建:《假如鱼也生有翅膀》,《知识之窗》2013年第10期。
但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听懂自然的语言。所以迟子建又说:“对于这样一些隐秘的、生动的、遥远的、亲切而又陌生、糊涂而又清晰、苍凉而又青春的语言,我们究竟能感知多少呢? ”[注]迟子建:《假如鱼也生有翅膀》,《知识之窗》2013年第10期。但无论如何,迟子建强调自然也是有语言的,并且自然也是能够听懂人类的语言的。即自然有语言,并能听懂人的语言,迟子建才主张人与自然要进行对话交流的。她说:人类把语言最终变成纸张上的文字,本身就是一个冒险的不负责任的举动,因为纸会衰朽,它承受不了风雨雷电的袭击。如果人类有一天真的消亡了,这样的文字又怎会流传下去呢? 所以,我们应该更多地与大自然亲近,与它对话和交流,它们也许会在我们已不在的时候, 把我们心底的话永存下来。[注]迟子建:《假如鱼也生有翅膀》,《知识之窗》2013年第10期。
迟子建这里的目的并不是要真的否定文字,否则小说中就不会有后面“西班造字”那样的内容安排了,而是强调“我们应该更多地与大自然亲近,与它对话和交流”。作品中的“我”说:“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如果午夜梦醒时我望见的是漆黑的屋顶,我的眼睛会瞎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清晨》)“我郁闷了,就去风中站上一刻,它会吹散我心底的愁云;我心烦了,就到河畔去听听流水的声音,它们会立刻给我带来安宁的心境。我这一生能健康地活到九十岁,证明我没有选错医生,我的医生就是清风流水,日月星辰。”(《额尔古纳河右岸·黄昏》)在作者看来,大自然既是人类栖居的家园,是人类的对话交流者,也是治疗人类精神疾病和身体疾病的医生。这里的一切自然现象、自然事物(甚至人造物)都是有生命、有灵性的,会说话的,并且也是能听懂人说话的。只是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说话方式,人不一定都能听懂自然的语言,或者压根就不相信自然有语言,因此也不会去倾听自然的语言。但在作者的心目中,自然是有语言的。
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自然的语言是一种“道示”的语言,是“寂静之音”。按照儒家的观点,自然的语言也是一种“行与示”,它既需要“倾听”,也需要“观看”。艾布拉姆在《感官的魔咒》中也指出,人类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暗示性踪迹,从蜿蜒穿过大地的河流,到被雷电劈断和烧成树桩的黑色的老榆木,这些都作为自然的“书写”,曾为古老的预言者所研究,远古人类也正是靠对这些自然符号的解读才存活下来的。最初的文字也正是在与这些自然符号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注]David Abram, The Spell of Sensuous:Perception and Language in a More-Than-Human World, New York: Vintage, 1997, p.95.而人类的先民,之所以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下来,靠的就是对各种自然符号、自然语言的观察和解读能力。《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鄂温克族人也是把那各种各样的“迹象”作为“自然的语言”来看待的。如他们通过观看灰鼠挂在树枝上的蘑菇,就可以知道将面临着怎样一个冬天。那灰鼠挂在树枝的“蘑菇”,就是“自然的语言”。
这种把各种各样的“迹象”,各种各样的自然符号都视作语言的生态语言观,使得《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小说虽以“我”的口吻讲述,但它不是“独语体”,而是“对话体”小说。并且它的对话者主要不是人而是自然。小说开头就说:“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对于讲述者来说,与她永恒相伴的是自然,倾听她说话的也是自然。作品中说:“我是个不擅长说故事的女人,但在这个时刻,听着刷刷的雨声,看着跳动的火光,我特别想跟谁说说话。达吉亚娜走了,西班走了,柳莎和玛克辛姆也走了, 我的故事说给谁听呢?安草儿自己不爱说话,也不爱听别人说话。那么就让雨和火来听我的故事吧,我知道这对冤家跟人一样,也长着耳朵呢。”由此可以看出,这部小说,其实是在“人与自然”之间展开的一场对话。但这里的对话者还不仅仅止于自然现象,因为在这里“万物有灵”,那些人造物也是可以倾听人类的语言,可以与人进行对话的。“狍皮袜子、花手帕、小酒壶、鹿骨项链和鹿铃”都是可以听“我”讲这个故事的。因此,这部小说不是独语体而是对话体小说。“我”尽管没有固定的对话者,可是“我”说的话都有听众,大量自然物都是“我”心灵的对话者,都能听懂“我”的话,“我”也能听懂他们的话。而且,随处都是对话者:一块石头、一片云彩,都是对话者。只是对话是无声地进行的。[注]张丽军等:《温厚·悲凉·清澈——〈额尔古纳河右岸〉三人谈》,《艺术广角》2009年第3期。
而这种对话体的叙述方式,实际上也正是一种“生态叙述”方式。当代美国生态批评家威廉·麦克杜威尔希望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分析自然文学文本中的各种声音,为生态文学批评、为自然文学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因为在他看来,“对话体”最能体现一种生态精神。麦克杜威尔提出,根据巴赫金的看法,再现现实(自然)的最理想形式是对话的形式,在这种对话形式中,多种声音或观点可以相互作用。与之相反,那种独白的形式,则鼓励单一的言说主体去压制任何与他或她的意识形态不符的观点。以这种观点为出发点,麦克杜威尔认为,存在于伟大的自然之网中的所有实体,都应该得到承认并拥有自己的声音,一种生态的文学批评就可能探讨作者是怎样再现人类世界的声音与自然中非人类世界声音的相互作用。由此,麦克杜威尔将巴赫金的这种“对话理论”作为探索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对话”关系的理论基础,并以此来分析自然写作、景观文学或具有生态取向的文本。麦克杜威尔还指出,在把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运用于景观文学分析时,也会遇到一些问题。一个最明显的问题是,至少从字面上看,树木、石头、河流是不会讲话的,更谈不上书写、发表对我们谈论他们的许多事情的反应了。文学的每一个试图倾听自然的声音或阅读自然之书的努力,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特征。尽管存在着这些问题,在景观文学中运用对话模式,却可以敞开一个文本,使得在景观的所有构成要素(包括人)中,进行生态关系的分析成为可能。[注]Michael J. McDowell, “the Bakhtinian Road to Ecological Insight”, in 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 eds., The Ecocit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 and London: Georg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72, p.374.透过麦克杜威尔的这种生态对话理论来看《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对话体叙事,可以更深入理解其中所包含的生态意识。在这里,各种自然事物都是与人平等的对话者、言说者,也正体现出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