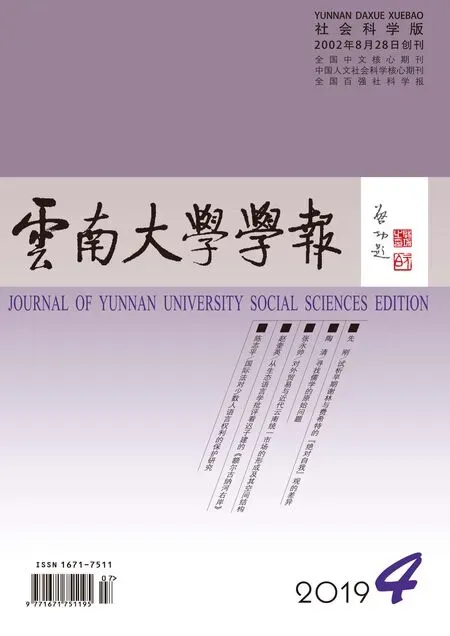国际制裁的目的、条件、方式及其对中国参与国际制裁的启示
罗圣荣,刘明明
[1.云南大学,昆明 650091;2.浙江大学,杭州 310058]
国际制裁,是指通过实施强制压力(如采取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强制措施)以表达本国立场和改变对象国行为,从而达到特定目的的对外政策工具。[注]E. A. Rose, “ From a Punitive to a Bargaining Model of Sanctions: Lessons from Iraq”,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9, no.3,(September 2005), pp.459-480.一战后,“国际制裁”一词频繁见诸于政界与学界。从一战后国际社会对战败国德国的经济和军事的双重规制,到今天联合国因核问题对朝鲜进行全方位制裁,表明国际制裁一直是国际社会惯用的政策性工具。对于国际制裁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研究。在理论层面,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一是研究实施不同制裁方式所需要的条件;[注]如丽莎·马丁(Lisa L. Martin)认为公信力在多边制裁的合作中起着关键作用(Lisa Martin, “Credibility, Costs, and Institutions: Cooperation on Economic Sanctions”, World Politics, vol.45, no.3(April 1993), p.407);丹尼尔·德莱兹勒(Daniel W. Drezner)指出在制裁的谈判阶段和实施阶段,多边制裁在合作中面临的利益协调和背叛等问题(Daniel W. Drezner, “ Bargaining, Enforcement and Multilateral Sanc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no.1(Winter 2000), pp.73-102)。二是对影响制裁有效性的因素的分析;[注]艾拉(Ella )和 杰弗里(Jeffrey)从制裁后果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有针对性的制裁能够减少人道主义危机,提高制裁的有效性(Ella Shagabutdinova and Jeffrey Berejikian, “Deploying Sanctions while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Are Humanitarian ‘Smart’ Sanction Effective?”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vol.6, no.1(February 2007),pp.59-74);罗伯特·哈特(Jr. Robert A. Hart)从民主化程度的角度分析了政体类型在制裁中的作用,认为民主国家在经济制裁的运用上更为成功(Jr. Robert A. Hart, “Democracy and the Successful Use of Economic Sanction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53, no.2(June 2000), pp.267-284);罗伯特·佩普(Robert A. Pape)认为现代国家的民族主义及其寻求替代能力的提高,降低了目标国在面对制裁时的脆弱性(Robert A. Pape, “ Why Economic Sanctions Do Not Wor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2(Fall 1997), pp.90-136)。三是对制裁目标的研究;[注]如詹姆斯·琳赛(James M. Lindsay)提出了贸易制裁的五类目标,分别是服从、颠覆、威慑、国际象征和国内象征,并通过不同案例分析了不同目标的实现程度(James M. Lindsay, “Trade Sanctions As Policy Instruments: A Re-Examin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0, no.2(June 1986), pp.153-173)。四是对制裁可持续性的研究。[注]如菲奥娜(Fiona )和艾伦(Allan)分析了影响制裁持续性的因素,认为政权类型会影响制裁时间的长短(Fiona Mcgillivray and Allan C. Stam, “Political Institutions, Coercive Diplomacy, and the Duration of Economic Sanction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8, no.2(April 2004), pp.154-172)。在实践层面,对国际制裁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以联合国、美国或欧盟为实施主体的制裁案例。[注]如约翰·加尔顿(Johan Galtung)研究了联合国对罗德西亚(即今津巴布韦)的经济制裁,认为制裁收效甚微(Johan Galtung, “On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 With Examples from the Case of Rhodesia”, World Politics, vol.19, no.3(April 1967), pp.378-416);欧几里得·罗斯(Euclid A. Rose)研究了联合国对伊朗的多边制裁,其通过“讨价还价”模型,分析了制裁期间的谈判进程以及双方做出的让步( Euclid A. Rose, “From a Punitive to a Bargaining Model of Sanctions: Lessons from Iraq ”,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9, no.3(September 2005), pp.459-479);李晨阳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缅甸的长期经济制裁进行了研究,认为双方经济交往规模小、缺乏其他国家有效合作等是影响制裁成效的原因(李晨阳:《西方国家制裁缅甸的目的及其效用评析》,《国际安全研究》2009年第2期,第30-37页);阮建平从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了二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实施手段和方式等(阮建平:《国际经济制裁:演化、效率及新特点》,《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4期,第30-36页);柳剑平、刘威通过分析美国经济制裁实践中的政策目标与功效,探讨了美国经济制裁政策的政治化(柳剑平,刘威:《美国对外经济制裁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克拉拉·波特拉(Clara Portela)结合欧盟的主要制裁活动,分析了欧盟对外制裁的政策和法律框架,对制裁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估(Clara Portela, “European Union Sanc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When and Why Do They Work ? ”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vol.11, no.3(July 2010), pp.408-409)。此外,张曙光通过研究西方对华制裁案例及中国的对外制裁实践,分析了经济制裁的动机与绩效因素及理论假设(张曙光:《经济制裁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概言之,现有的国际制裁研究,在理论层面多集中于对制裁方式和制裁成效的探讨,尤其是针对经济制裁的分析比较丰富;实践层面则更倾向以西方国家为制裁主体的研究。尽管上述研究成绩斐然,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现有的研究无论是从理论层面抑或实践层面,多从国际法、世界经济、制裁效果等某个角度对国际制裁进行研究,分析视角较为单一。由于实施国际制裁是一项极为复杂的行为,现有的研究普遍缺乏对实施国际制裁的目的、条件、方式等进行一个较好的综合分析。其次,研究案例主要以西方或联合国发起的制裁案例为主,对非西方国家的国际制裁研究尤为欠缺。
由于国家实力等因素的限制,中国在以往的外交实践中,较少运用国际制裁这一工具。随着中国国力逐步殷实,国际社会期待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因此,中国开始逐步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制裁,以维护国际正义和国家利益。不过,迄今中国参与的国际制裁行动并不多见,国际制裁的经验稍显不足。在新的历史时期,只有充分认识国际制裁的目的,了解国际制裁的实施条件,合理选择制裁方式,才能使国际制裁真正为我所用。
一、实施国际制裁的目的
在无政府状态下,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始终是国际政治的主题。摩根索认为,“国家利益包括了三个重要方面,即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文化完整,在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中起着关键作用。”[注]汉斯·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15页。由于不同制裁主体的制裁能力及政策需求不同,其政策目标也不同,制裁目标的设定以国家利益为基础,通常包含着复杂的动机。
(一)惩罚目标国行为
尽管经常有官方免责声明, 但几乎所有制裁都有惩罚性意图,[注]Margaret P. Doxey, “Sanctions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the Spectrum of Goals and Achievem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55, no.2(Spring 2000), p.216.事实上惩罚可能是主要目标。[注]Kim Richard Nossal,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as international punishmen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3, no.2(Spring 1989), pp.301-22.当目标国的政策或行为不被制裁国认可或接受时,一方面,在目标国的政策实施前,可以通过对目标国进行制裁威慑,迫使其放弃既定政策,转变行为以顺从制裁国的偏好。[注]J. M. Lindsay: “Trade Sanctions as Policy Instruments: A Re-examin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0, no.2(June 1986), pp.153-173.在威慑阶段,目标国可能会选择顺从。然而,一旦制裁政策到位, 目标国可能不会轻易“屈服于外部压力”。[注]Margaret P. Doxey, “Sanctions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the Spectrum of Goals and Achievem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55, no.2(Spring 2000), p.216.因此,另一方面是对目标国行为的事后制裁,使目标国因自身的过激或者不当行为承受一定的痛苦与损失,同时对其未来的政策行为施加压力。2017年9月份,联合国安理会第九次通过新的对朝制裁决议,新决议继续对朝鲜进行谴责和实施综合性制裁手段,旨在促使朝鲜暂停核导活动,推进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国际社会也一致支持继续收紧对朝制裁。[注]胡欣:《兵锋直指朝鲜:美国的牌想怎么打》,《世界知识》2017年第19期,第30-32页。目的即通过制裁对朝鲜进行惩罚,迫使其放弃拥核计划。
(二)削弱目标国实力
在政治层面,制裁可以改变目标国在国际或国内层面的政治决策,实现破坏目标国政府稳定、改变其国内政治现状、加剧目标国国内政治分裂的目的。在政治透明度较高的国家,制裁可能导致目标国国内的大规模政治行动,增强公众采取反政府行动的意志。而在政治自由有限的专制国家,制裁很少能够为当地反对派提供制衡其领导人的动力。虽然制裁可能导致政治活动的增加,但目标国政府也会设法消减其影响。[注]Susan Hannah Allen,“The Domestic Political Costs of Economic Sanction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2, no.6(December 2008), p.939.因此,要使目标国政治发生剧变,甚至颠覆其政府,需要更为严厉且长期的制裁措施。例如,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对海地军政府的制裁,改变了其国内政治生态,使海地恢复了民主。[注]赵延龙:《冷战后联合国制裁的有效性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外交学院,2007年,第31页。
在经济层面,制裁主要体现在制裁国通过贸易或金融制裁等,对目标国进行进出口的扼制和封锁。但制裁对目标国经济造成损失的同时,制裁国经济也极可能蒙受损失。2013年美欧等西方国家由于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但由于欧洲对俄罗斯油气资源的严重依赖,制裁在对俄罗斯造成巨大国际压力和带来严重经济损失的同时,欧盟自身经济也受到直接影响,欧盟内部开始出现反对声音。[注]白联磊:《西方对俄制裁的影响》,《改革与开放》2015年第16期,第21-22页。
以军事为目的的制裁,通常是为了遏制军事冲突,通过制裁削弱目标国的国力,防止目标国的政策进一步扩大为军事行动或阻止战争规模升级。在外交上,针对不涉及目标国核心利益的对外政策,制裁国可以通过没有政治敌意的制裁来迫使对方放弃或改变其政策。如欧盟对外制裁的原因包括了恐怖主义、国内冲突以及外交争端等,而其针对邻国的制裁主要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
(三)宣传自身价值观
一些国际制裁的目的在于向目标国及外部世界宣传本国的价值观。制裁国并不总是公开表达其实施制裁的全部动机和目标,而是强调以及推广民主和人权等为目的。在单边制裁中,许多国家也以“民主和人权”为口号,藉此占据道义的制高点。[注]邵亚楼:《国际经济制裁:历史演进与理论探析》,博士学位论文,上海社会科学院,2008年,第70-71页。但这些主张可能无法完全准确地反映制裁国的政策思想。[注]Margaret P. Doxey, “Sanctions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the Spectrum of Goals and Achievem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55, no.2(Spring 2000), p.214.例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以缅甸的民主、人权问题为由,对其军政府进行了长期的制裁,要求军人承认1990年大选结果,向在大选中获胜的民族民主同盟彻底交权。[注]李晨阳、祝湘辉:《西方国家对缅甸的制裁措施》,《国际研究参考》2010年第5期,第19-24页。
(四)表明本国立场
在预期制裁不能改变目标国行为的情况下,仍有许多国家将国际制裁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工具,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象征性制裁虽不能使目标国最终屈服,但其足以表明制裁国谴责目标国和支持国际准则的立场。[注]Margaret P. Doxey, “Sanctions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the Spectrum of Goals and Achievem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55, no.2(Spring 2000), p.220在某一国际事件面前,当一国决策者无意行动时,如果本国民众期待其政府有所作为,要求进行有效制裁的呼声日益高涨,那么,本国政府或采取一定措施,包括制裁,[注]刘建伟:《国际制裁与国内结构变迁——以南罗德西亚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2年,第35页。以向国内民众或目标国表明自身立场。制裁国通过事前发出制裁威慑或实施制裁的信号,表达对目标国某项政策或行为的不满,起到一种国内或国际层面的象征作用。[注]柳剑平、刘威:《美国对外经济制裁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页。同时,由于国际制裁的公开性,有助于制裁国政府向其国内民众和盟国,展示其对威胁和局势变化的反应。如在中菲南海争端中,中国完全可以通过经济方面的制裁,威慑或发出制裁信号,向国内民众表达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的立场,对菲方施压,促使其改变在南海争端中的非理性行为。[注]梅新育:《中菲经济战》,《南风窗》2012年第12期,第72-74页。
现实中,由于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国际制裁的目标很少单一,既有政治性目标也有经济性目标,其中既包括可见的、已知的目标,又包括隐蔽的、未知的目标,[注]Mahmoud Jameel Jdeed:《国际经济制裁及其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3年,第28页。目标的制定取决于不同制裁主体的能力和需求以及目标国的抵抗能力等。
二、国际制裁的实施条件
制裁的发起不仅需要明确的目标,还必须具备若干条件,如双方的相互依存度、力量对比、利益权衡和国内外支持等。在全球化背景下所形成的相互依存中,交流渠道更加多样,使各国对外政策更富敏感性。国际制裁作为大国外交工具,双方的力量对比,包括实力和承受能力,是影响制裁实施的重要因素。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安全、能源开发和利用、环境保护等众多领域内利益相融。[注]樊勇明:《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页。国际制裁在为制裁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会损害制裁国的利益。因此,相对收益的考量格外重要。此外,制裁的实施不仅是政府层面的决策,还受到国内政治和国际社会的影响。
(一)相互依存度
基欧汉与奈认为,“交往只有发展到中止该交往会产生代价时才是相互依存。按照这种代价的大小,相互依存可分为均等依存、绝对依存和非对称性依存。”[注]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10页。首先是均等依存,存在于某一领域具有同等资源的国家之间,如冷战期间美苏的核均势,双方的资源均势导致相互依赖的程度较低。在均等依存的行为主体间,制裁的成效并不明显,即双方敏感性较弱。在低度的相互依存下,两国都不会因对方的制裁而付出较大代价。发起制裁可能在耗费较高成本的同时,却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其次是绝对依存,存在于某一领域具有绝对不相称资源的国家之间,目标国与制裁国在某一领域处于高度依存甚至依附关系。这种情况多存在于盟国或大国与其依附国之间,目标国一般对制裁国存在经济或安全方面的依赖。例如,在贸易往来中,目标国与制裁国的贸易份额在本国发展中占有较大比重,或在安全关系中,目标国在安全领域接受制裁国的保护。在这种高度依存的关系中,制裁通常会对目标国产生较大影响,造成一定程度的经济伤害或安全威胁。只有当目标国严重依赖制裁国时,制裁国才能够忽视目标国可以获得的替代性机会。
最后是非对称性依存。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减少了各国在某一领域均等依存和绝对依存的情况,更多的是非对称性相互依存。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大幅提高,增加了一国被制裁时的敏感性。另一方面也使目标国在面对一国制裁时,更容易向其他国家寻求替代,即各国在遭受经济制裁时的脆弱性在下降。[注]邵亚楼:《国际经济制裁:历史演进与理论探析》,博士学位论文,上海社会科学院,2008年,第50页。由于在资源上处于优势地位,大国对小国的制裁更容易发生。在非对称性相互依存的情况下,制裁使双方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故制裁国发起制裁时要考虑到双方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强弱。由于受到双方非对称依存程度的影响,制裁使目标国受到损失的同时,发起国也会付出代价,并且在非对称相互依存中,目标国与发起国都需要及时从外部寻求替代,这也会影响到制裁的实施和效率。因此,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是制裁实施的条件,在双方相互依存度较低的情况下,会增大制裁的难度。例如,美国虽长期对朝鲜实施经济制裁,但并未对朝鲜造成实质性影响。这是由于朝美之间经济依赖程度低,美国的经济制裁很难对朝鲜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更多情况下只是一种象征性制裁。
(二)力量对比
双方的相对实力是影响制裁发起的重要条件,包括经济、政治和军事各领域的实力及综合实力,其中经济是支撑一国实力的重要基础,通常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指标。制裁发起国的经济规模,一般远在目标国之上,这也是保证制裁效果的重要前提。除了国民生产总值,一国经济的健康程度也是潜在的影响因素,经济衰弱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制裁的影响。在分析制裁政策时,根据经济的健康程度,可以将目标国划分为贫困国家,存在显著经济问题的国家和经济发展强劲的国家。[注]Hufbauer, Gary Clyde, Jeeffrey J. Schott and Kimberly Ann Elliott, “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 History and Current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2, no.2(March 1987), pp.264-265.相比制裁国,目标国的经济通常更为脆弱,政治也相对不稳定。如果目标国拥有较强的综合实力,制裁很难取得预期效果。在多数成功的制裁案例中,制裁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目标国的10倍,有些甚至超过了100倍。[注]Gary Hufbauer, etal., 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 Washington: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7, pp.89-90.以美国为主导、欧盟和其他美盟友国家为辅的对伊朗全面制裁体系,制裁方实力远超目标国,持续加大的国际制裁使伊朗经济遭受重创,威胁到其社会和政权的稳定,对伊朗核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客观上将伊朗推上了谈判桌。[注]陈乃心:《伊朗核问题中的国际制裁作用分析》,博士学位论文,外交学院,2015年,第4页。
双方的承载力也是影响制裁发起的重要条件。国际制裁通过一系列强制手段对目标国的政治或经济造成打击的同时,也会损害制裁国利益。如果制裁方没有足够的能力承受制裁带来的成本,那么,在制裁目标国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制裁”自身。[注]陈薇:《欧盟对外经济制裁评析》,硕士学位论文,外交学院,2010年,第10页。承载力一方面受到内因,即双方实力的影响。实力较强的制裁国,能够承受更高的制裁成本和维持更长的制裁时间。政治和经济实力较弱的目标国,承受制裁的能力较低,面对制裁信号时更容易妥协。另一方面,承载力也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即双方是否能及时获取第三方的替代资源或市场。随着全球市场的开放,目标国能够寻求的市场增加,但较为脆弱或不稳定的目标国,对国家的控制能力较弱,寻求替代国或替代产品的能力有限,承受制裁的能力较低。如果制裁国能够寻求到更多合作,那么,目标国的供应市场和需求市场将会进一步缩小。[注]A.Cooper Drury, “Revisiting 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5, no.4(July 1998), pp.497-509.如欧盟作为叙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2011年叙利亚爆发危机以来,欧盟对叙利亚的一系列制裁措施,使叙利亚失去了传统的出口市场,造成叙利亚国内经济恶化、物价不断攀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叙利亚政府的控制能力。[注]张金荣、詹家峰:《欧盟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及影响》,《当代世界》2013年第6期,第38-40页。
(三)利益权衡
在不能预期制裁代价与收益的情况下,制裁双方会通过互判进行利益权衡。博弈理论认为,在能够获取完全信息的博弈中,制裁永远不会发生,充足的信息使双方能够预判制裁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注]Dean Lacy and Emerson M. S. Niou, “ A Theory of Economic Sanctions and Issue Linkage: The Roles of Preferences, Information, and Threat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6, no.1(February 2004), p.27.但现实中双方很难获取完全信息,双方对结果有不同的偏好,且并不确定对方的偏好,假设在制裁的威慑和实施阶段,制裁国和目标国的选择分别是:
阶段一:制裁国(制裁威慑/不威慑)
目标国(服从/不服从)
阶段二:制裁国(实施制裁/不实施制裁)
目标国(对制裁投降/不投降)
而博弈的可能结果有五个:
1=(不威慑)
2=(威慑,服从)
3=(威慑,不服从,制裁,不投降)
4=(威慑,不服从,制裁,投降)
5=(威慑,不服从,不制裁)
其一是制裁国的利益权衡。制裁国在实施制裁前会通过权衡制裁的成本与收益,得出预期的相对收益,决定是否制裁。如果在制裁威慑阶段,目标国选择服从,那么,制裁国可能更倾向不制裁,以低成本换取高收益。反之,制裁国更倾向于选择制裁,承受制裁成本,以避免由于目标国拒绝服从却不受制裁的行为,而引发的在未来国际谈判中丧失可信度的后果。如果目标国在威慑阶段选择不服从,在制裁实施后选择投降,那么,制裁国的相对收益可能较少。若制裁实施后目标国仍不服从,随着制裁的持续,制裁成本会随之不断增加,包括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内部成本如制裁消耗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说服国内反对力量以实现有效制裁的协调成本等。外部成本包括制裁合作中的协调成本和背叛成本,寻求替代的成本和关系成本等,制裁可能会影响到与目标国未来的关系。现实中多数国家倾向于维持现状,即不发出制裁威慑,以避免制裁威慑后对目标国让步而造成的声誉和可信度损失。[注]Dean Lacy and Emerson M. S. Niou, “ A Theory of Economic Sanctions and Issue Linkage: The Roles of Preferences, Information, and Threat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6, no.1(February 2004), pp.25-42.
其二是目标国的利益权衡。对目标国来说,在服从与对抗之间的选择,某种程度上也是利益权衡的结果。目标国在应对制裁时,在不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情况下,会衡量不服从的代价与妥协的成本,从而作出决策。通常情况下,在威慑阶段选择服从的目标国,更倾向于在有争议的问题上选择让步,以免受到制裁。这种倾向表明接受制裁的代价远远超过不服从的好处。而适应性较强的目标国,倾向于接受制裁,即在争议问题上选择不服从。原因可能是经济上的,在争议问题上让步的代价超过了接受制裁的代价,也可能是非经济的因素,如做出让步后所带来的国内或国际政治代价。但制裁一般只能在非核心利益上使目标国屈服。[注]Robert A. Pape,“ Why Economic Sanctions Do Not Wor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2(Fall 1997), pp.90-136.同时,目标国还会衡量顺从获得的利益,当预期制裁会成功时,顺从的益处就超过了最初触发制裁的违规行为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 制裁成为一种讨价还价的工具, 而不是惩罚性的手段。[注]Susan Hannah Allen,“The Domestic Political Costs of Economic Sanction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2, no.6(December 2008), pp.916-944.但在当今民族国家的价值序列中,一旦制裁涉及目标国的主权和安全等核心利益时,目标国可能宁愿付出较高的代价,也不会让步。民族主义通常会使一个国家或社会选择接受制裁而非放弃国家利益,而民主化的发展也促使公民将个人利益与国家目标相结合。[注]Robert A. Pape, “ Why Economic Sanctions Do Not Wor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2(Fall 1997), pp.90-136.
(四)国内外支持
不论对制裁国还是目标国来说,国内政治都是影响制裁实施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制裁收益与代价在国内政治团体间的不均等分配,导致不同利益团体对决策者施加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专制政权中,领导者对民众支持率的依赖程度较低,民意对国家决策的影响不大,但领导人的更迭容易引发政策的变化。[注]Fiona McGillivray and Allan C. Stam, “Political Institutions, Coercive Diplomacy, and the Duration of Economic Sanction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8, no.2(April 2004), pp.154-172.相比专制政权的国家,民主国家的决策更易受到国内政治的干预。[注]Richard Haass, ed., Economic Sanction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8, p.203.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受选举制约,需要更多的国内支持者,因此,决策通常会代表占大多数的支持者的利益。政策通常不会因领导人的更迭而改变,但易受到利益集团的游说。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决策的变更会影响到国内民众的信任度,在决策公开的情况下,如果制裁国未兑现发起制裁的承诺或一国轻易选择让步,都会引起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应,甚至降低政府的可信度。民意导向在制裁的发起中起到很大作用,某些情况下国内观众的压力会迫使政府采取相应制裁措施,民族主义会使国内民众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发起自发的抵制行为。因此,国家在做出相应决策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国内政治干预。
国际合作也是影响制裁实施的重要因素。首先,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或国际组织的参与有助于制裁的实施。在制裁目的不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情况下,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制裁更容易对目标国形成强大压力,使其脆弱性更为明显,寻求替代产品和替代市场的难度加大。对制裁参与国而言,国际组织的参与可以提高制裁的可信度,从而降低参与国背叛的可能性。其次,当制裁国能够获得目标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合作时,制裁将更为有效。全球化提高了目标国面对制裁时的灵活性,使其可以转向货物和服务的替代供应商,并将其出口转移到其他市场。通过与目标国主要贸易国的合作,可以对其施加直接的外部压力。此外,对目标国的国际援助还可以来自不太重要的贸易伙伴,这些国家可以在制裁期间加强与目标国的经济联系,从而缓解其面对制裁的压力。如果无法获得这些国家的合作,即使是协调一致的制裁也可能会以失败而告终。[注]E. V. Mclean and T. Whang, “Friends or Foes? Major Trading Partners and the Success of Economic Sanc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4, no.2(June 2010), pp.427-447.在制裁的国际合作中,参与者会将参与制裁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如果相对收益不符合其原本的预期,制裁方内部难免会出现态度的变化,进而动摇制裁的多方合作基础。[注]陈薇:《欧盟对外经济制裁评析》,硕士学位论文,外交学院,2010年,第40页。因此,为保证制裁效果,多方合作中的利益协调对制裁功效的发挥也十分重要。
三、实施国际制裁的方式
早期的制裁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制裁形式比较单一,大多作为战争的辅助手段。随着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建立和国际争端的出现,制裁作为一种战争的替代手段,被频繁使用,主要是政治制裁和经济制裁。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国际制裁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化。根据制裁的实施主体可以分为单边制裁和多边制裁;根据制裁涉及的不同领域,可以分为复合制裁和单一制裁;根据制裁的对象,可以分为全面制裁和目标制裁。
(一)多边制裁与单边制裁
多边制裁是两个以上国际行为体为实施主体参与的制裁。单边制裁即以一个国际行为体为主要实施主体的制裁。在相互依存度上,相比多边制裁,单边制裁对相互依存度的要求更高,如果双方相互依存度较低,在单边制裁中目标国更易找到规避方法。在实力要求上,单边制裁对制裁国实力的要求更高,全球化背景下同种商品替代弹性的增加,使目标国在面临单边制裁时更易寻求替代商品和市场。除非制裁国在某一领域的资源或产品中占有全球过半的生产力,以致可以影响到目标国的替代贸易。[注]Gardner, Grant W. and Kent P. Kimbrough , “The Economics of County-specific Tariff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31, no.3(August 1990), pp.88-575.但拥有这种能力的国家非常少,并且只能在短期内起作用。在成本收益上,相比单边制裁,多边制裁的成本更高,风险更大。首先,在合作的谈判阶段,需要耗费较高成本来游说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其次,在制裁的实施阶段,合作中的临时同盟可能因实施阶段的背叛问题而存在脆弱性,使主要制裁国面临较高的风险成本。[注]Daniel W. Drezner, “ Bargaining , Enforcement and Multilateral Sanc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no.1(Winter 2000), pp.73-102.
伊朗核危机爆发后,2003年—2015年间,美国等西方国家与联合国对伊朗发起了多轮经济制裁,主要集中在能源和金融领域。危机的前三年,以美国的单边制裁为主,2006年—2010年间,联合国参与到对伊朗的制裁中,并连续通过四次制裁决议,使伊朗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注]Mohammad Reza Farzanegan ,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nd Energy Sanctions on Iran’s Informal Economy”,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3, no.1(Winter-Spring 2013), p.33.在内外多重因素作用和利益权衡下,伊朗选择作出让步,缓和了其谈判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制裁推动了伊核问题的和平解决。[注]邹志强:《联合国与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国际研究参考》2016年第8期,第1-6页。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强国,其实力与制裁承载力都远在其他国家之上。由于多边制裁需要承担与制裁参与国谈判时的成本以及制裁实施过程中的背叛风险,由此,单边制裁成为美国实现政治目的时的常用手段。但近年来美国也在逐渐调整其制裁政策,以寻求制裁能够在多边框架下进行。在得到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支持的情况下,说服多国联合实施制裁的效果往往大于一国单独制裁的效果。[注]Thea Lee, “A Speech before the Senate Task Force on Economic Sanctions”, Progressive Response, vol.2, no.32(September 1998), p.2.
(二)复合制裁与单一制裁
复合制裁是指在不同领域实施制裁的同时,辅以军事压力与外交斡旋。单一制裁则是针对某一领域的制裁,如单一的经济制裁、政治制裁或军事制裁。在相互依存度上,复合制裁需要制裁双方在各领域拥有较高的相互依存度,而单一制裁只需双方在某一领域的依存,针对性更强。由于单一制裁仅针对一国的某一领域,能够减轻对目标国宏观政治经济稳定的影响,以减少非故意性后果。在实力要求上,相比单一制裁,复合制裁一方面需要制裁国的政策与措施在多领域配合,另一方面对制裁国在多领域寻求替代的调整能力也要求较高。在成本收益上,复合制裁成本更高,制裁在对目标国产生损害的同时,也会对制裁国自身的各个领域造成伤害。而单一制裁可以利用制裁国自身优势有选择性地影响目标的行为,故不会对自身产生太大影响。[注]简基松、王宏鑫:《美国对俄罗斯经济制裁之国际法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法学评论》2014年第5期,第148-155页。
自2006年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以来,联合国安理会8次通过对朝鲜的制裁决议,从对朝鲜实施武器禁运、冻结金融资产等多项严厉制裁到全面禁止对朝鲜的武器出口,禁止人道主义目的以外的贷款,并实施针对个人、实体企业的目标制裁。[注]李圣华、朴银哲:《国际制裁对朝鲜经济的影响分析》,《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18-28页。除制裁外,国际社会还通过外交斡旋、六方会谈和军事威慑等途径对朝施压。面对国际社会不断升级的制裁压力,朝鲜曾试图做出让步,选择回到六方会谈。而朝鲜在2018年4月宣布停止核试验,国际社会的复合制裁也是推动因素之一。尽管经济制裁仍是多数制裁发起国的选择,但结合军事、政治和文化手段的复合制裁,更有助于制裁达致预期目标。[注]颜剑英、熊伟:《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制裁的发展趋势》,《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23页。
(三)全面制裁与目标制裁
全面制裁是制裁主体对目标国整个目标人群实施的制裁。目标制裁是针对利益核心的主要掌权者或目标国的决策精英实施的制裁,包括禁止目标代表参加国际集会、冻结资产和阻止高级政府文职人员和军事官员及其家属的金融交易等。[注]Susan Hannah Allen, “The Domestic Political Costs of Economic Sanction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2, no.6(December 2008), p.939.两种制裁方式的选择主要涉及到合法性及制裁后果的问题,在合法性上,由于涉及到的范围较广,以整个目标人群为制裁对象的全面制裁更易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可能会伤害到无辜的个人或实体而违背国际法原则,如联合国对海地和伊拉克的全面制裁。[注]Peter Andreas, “Criminalizing Consequences of Sanctions: Embargo Busting and Its Lega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9, no.2(June 2005),pp.335-360.而目标制裁涉及的群体较少,更有针对性,较少存在合法性问题。在制裁后果上,全面制裁不仅会殃及目标国中的无辜平民,而且会对遭受中断的第三国造成严重损害,影响制裁国与第三国正常的经济关系,并导致其它不良后果。[注]Margaret P. Doxey, “Sanctions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the Spectrum of Goals and Achievem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55, no.2(Spring 2000), pp.220-221.目标制裁能够减少或避免非故意性后果,但也可能存在引发目标精英不满的情况。
1991年海湾战争以后,美国及联合国对伊拉克进行了长期的全面制裁,对其国内经济和军事实力造成重创的同时,导致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和其他非故意性后果,加剧了伊拉克国内规避制裁的走私和腐败等犯罪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普遍的不满和反对。[注]Peter Andreas, “Criminalizing Consequences of Sanctions: Embargo Busting and Its Lega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9, no.2(June 2005), pp.353-360.1991年海地发生军事政变后,联合国对其军政府实施了短期的全面贸易制裁和针对个人和实体的金融制裁,为海地恢复了民主宪政。但制裁在短期内对海地经济造成重创,对平民附带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注]赵延龙:《冷战后联合国制裁的有效性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外交学院,2007年,第31页。在制裁合法性和避免人道主义危机方面,目标制裁作为有针对性的打击手段和解决争端问题的方式,正逐渐取代全面制裁。
四、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参与国际制裁的思考
对中国而言,国际制裁相较于政策宣示等其他对外政策行为要更加有力,其实施比战争在资源消耗、国内政治、双边和地区关系上的代价小。因此,国际制裁不仅能满足中国在改变、限制、惩罚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实体与个体的需要,又能避免付出过高代价。但中国作为国际制裁的长期受害者,反对单方面对他国发起制裁,在联合国框架下参与国际制裁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外交原则,避免落入西方“霸权主义”下单边制裁的窠臼。但中国的制裁经验相对欠缺,可在借鉴以往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制裁经验的同时,在制裁中需要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制裁执行模式。
(一)明确制裁目的,争取国际支持
根据争端问题的严重程度,中国在参与国际制裁时有不同的预期目标。在实施制裁之前,首先要明确制裁的目的是威慑、惩罚还是宣示立场或其他,以及期望目标实现的程度及不同目标的主次。这样才能在制裁执行的过程中,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在评估制裁成效时判断是否达到预期目的。例如, 中国的“首要”目标可能是支持国际规范, 或满足国内民众对目标国行为的某些反应或要求等。[注]Margaret P. Doxey, “Sanctions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the Spectrum of Goals and Achievem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55, no.2(Spring 2000), p.211.
在争取国际支持时,要尽量满足制裁的合法性要求,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中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无论是执行联合国的制裁还是其他多边制裁,落实到国内都需要与国内法相适应,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在参与国际组织实施的制裁时,要注意国内执行措施与国际组织的政策协同。预先评估可能产生的非故意性后果,以制定相应措施尽量避免人道主义危机。
(二)制定制裁标准,精选制裁方式
制裁不应被强加为惩罚目标国整个社会的钝器, 而应作为对具体决策团体施加压力的有效工具。中国外交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价值观,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因此,在参与制裁时,需要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制裁标准,包括制裁的强度及制裁时长,明确是实施大范围长时间的高强度制裁,还是针对相关团体或个人的短期低强度制裁。通过与目标国相关机构的接触,明确制裁的范围和对象及其潜在的脆弱性,同时确保制裁不会对弱势群体造成不利影响。[注]Larry Minear et al., “Toward a More Humane and Effective Sanctions Management System: Enhancing the Capacity of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A Report to the Department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and the 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 United Nations, 1997, p.54.
在制裁方式的选择上,作为全球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中国可以利用自身优势选择有针对性的单一经济制裁,与友好国家分享市场,对不友好国家考虑采取强硬态度。[注]何中顺:《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理论与实践》,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年,第294页。中国支持适当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制裁,以及维护国际正义和地区秩序的多边制裁合作。另外,在避免非故意性后果的问题上,相比全面制裁,目标制裁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在全球化背景下,制裁是柄双刃剑。中国应努力提升制裁实力和承载力,增强制裁后盾,在拥有足够实力的基础上,更好地参与国际制裁。
(三)跟踪制裁过程,评估制裁效果
中国在参与国际制裁时,首先要建立起系统的制裁执行模式,在明确制裁目的和精选制裁方式的基础上,设立相关的制裁执行与监督部门,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跟踪制裁过程,进行实时的跟踪与专业技术评估。[注]Larry Minear et al., “Toward a More Humane and Effective Sanctions Management System: Enhancing the Capacity of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A Report to the Department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and the 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 United Nations, 1997, p.54.其次,制定相应的评估标准和建立有效的评估机制,完善配套的法律后盾及协调措施,使制裁更富有成效,以便对抗和平时期的威胁以及减少制裁带来的副作用。[注]Peter Wallensteen, Carina Staibano and Mikael Eriksson, eds. Making Targeted Sanctions Effective: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 Policy Options, 2003,pp.1-15.
评估国际制裁的功效,通常要看制裁对目标国产生了多大影响,以及制裁的最终结果是否符合中国的预期目标。[注]陈薇:《欧盟对外经济制裁评析》,硕士学位论文,外交学院,2010年,第14页。
同时应重视制裁措施对于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的评估,包括目标国的国内经济状况、公共健康、食品安全与营养、医疗、饮用水健康环境、教育、社会福利运作等诸多层面的副作用。制裁可能成功地迫使目标国改变政策, 但其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所支付的代价可能是永久性的。 因此,在实施制裁的同时,可能导致的消极人道主义影响也不容忽视。
结 语
国际制裁作为一种对外政策工具,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手段,中国一向主张国家间的问题和冲突应通过谈判、协调等方式解决,但当“胡萝卜”政策失效后,以制裁为主要方式的“大棒”政策有其成功的一面。随着中国的强大,在特定条件下,适当参与符合国际法、伦理道德标准和中国现实利益的国际制裁,或许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佳选择。中国在参与国际制裁时,首先要判断实施制裁要达到的目标,就中国当前外交工作的需要来说,更倾向于改变对方的对外政策和对外释放外交信号两个方面,不过也不排除其他目标在未来的可能性。其次是判断是否具备参与制裁的条件,应以本国与目标国的实力、承受能力对比为基础,尽量全面的掌握该国的有关信息,对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因素进行综合评估,通过利益权衡做出决策。再次,在制裁方式的选择上,对那些内部政治不稳定、经济不发达、在贸易与投资方面严重依赖中国的小国家,采取单一制裁就可以达到预期目标;而对于社会开放程度较高、经济比较发达、在贸易投资等方面对中国依赖程度不高的其他国家,采取多边制裁或复合制裁才有成功的可能。[注]颜剑英、熊伟:《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制裁的发展趋势》,《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22-23页。相对全面制裁,目标制裁更符合人道主义原则。中国在参与制裁时,在制裁的发起阶段,就应满足目标的合法性,在制裁的执行阶段,措施的设计要能够对决策者与实施者进行区分,从而对实施者做出约束,避免因伤及无辜使制裁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此外,在参与制裁的发起时,还要考虑到国内与国际社会的支持,在国内要完善相关体制和增强法律适用能力,促进制定适用于各种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示范立法。[注]George A. Lopez and David Cortright, “ Financial Sanctions: The Key to a ‘Smart’ Sanctions Strategy”, Die Friedens-Warte, vol.72, no.4, 1997, p.334.同时在国际层面,遵守国际法原则和标准。维护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誉,在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中提升制裁的可信度。最后,为保证制裁的有效实施,在制裁能力欠缺和制裁经验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应在制裁模式的建立和完善方面,为制裁的参与提供制度保障,让外交真正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