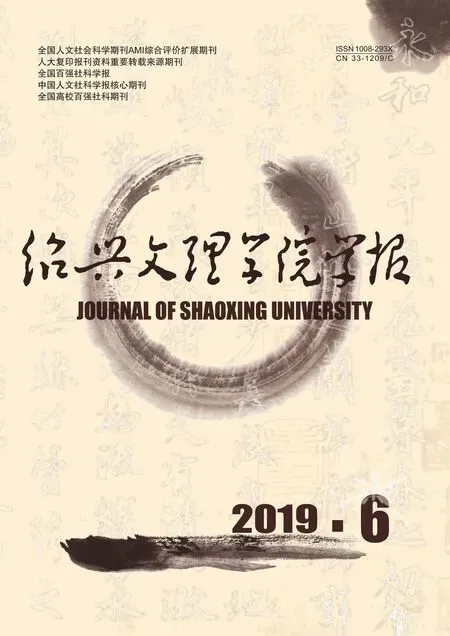性还是心:理学视域中的好恶定性
蔡 杰
(清华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084)
一、从《礼记·缁衣》的“好恶”主旨谈起
好恶问题是《礼记·缁衣》通篇义理思想的基点,历代注家一般都点明《缁衣》的宗旨在于好贤、好善,如郑玄指出“名曰‘缁衣’者,善其好贤者厚也”[1]1750,朱熹也认为“《缁衣》兼恶恶,独以‘缁衣’名篇者,以见圣人有心于劝善,无心于惩恶也”[2]卷一百四十。作为古代唯一一部单篇别行的《缁衣》诠释著作,《缁衣集传》对《缁衣》主旨思想的概括大致不出以往诠释家的基调(1)《缁衣集传》是晚明大儒黄道周的经学著作。黄道周(1585—1646),福建漳浦人,字幼玄,号石斋,是明末大儒,著名的理学家、经学家和书法家。乾隆四十一年(1776)谕文以品行称他为“一代完人”;道光五年(1825)清廷将黄道周请入孔庙从祀。明朝中后期阳明后学蛊惑天下,黄道周痛心疾首,主张以六经救世,上疏以六经授太子,并“在长安中,闭门深于幽谷,今复作小书生,再翻传注”,亲撰《洪范明义》《月令明义》《儒行集传》等经学著作,此中即包括《缁衣集传》。。《缁衣集传》开篇也指出“《缁衣》言好善也”(2)黄道周《缁衣集传·不烦章》,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文凡引《缁衣集传》原文,均以夹注的形式注明具体章目,不再另行出注。除特殊说明之外,《缁衣集传》引文均据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一点可以说是继承以往的阐释,但以往注家并无深入探讨人的“好恶”根源,那么人的“好恶”是属于人性,抑或情感,抑或发动于心,抑或是西方哲学中的理性或自由意志?是先天固有,还是后天所得?
关于《缁衣》中“好恶”属性的问题,在黄道周《缁衣集传》中已有较为完满的解释。这是以往对《礼记·缁衣篇》的注解本无法比拟的,也是《缁衣集传》作为单篇别行的独立诠释著作的应有之义。黄道周认为人的“好恶”是一种先天的人性本能。“好善恶恶,民之性也”(《缁衣集传·不烦章》),他将人的“好恶”安置于人性,实际上是为“好恶”找到了根源。那么,人的“好恶”问题就可以直接转化为人性问题来讨论。
将“好恶”安置于人性,那么“好恶”就有了人性的一切特点,即人的好恶本能是先天的,是纯善的。《缁衣集传》说“人性本善,理义悦心,见贤者而好之,见不肖而恶之,虽奸宄盗贼,其性一也”(《缁衣集传·恒德章》),意思是说人性是至善的,那么见到贤人便出于本能地喜好,见到恶人便出于本能地厌恶,不仅仁人君子如此,连奸人盗贼也有好恶的本能。
在这里,“好”(喜好)和“恶”(厌恶)可能是一种情感,但是“好善恶恶”却是人的一种本能,是人的一种特质,它属于人性而不是情感。或者说,“好”(喜好)和“恶”(厌恶)本身是说不上至善的,因为可能所好所恶的对象是善或恶,那么其善恶的价值判断就被所好者、所恶者所规定;而“好善恶恶”这种本能却是至善的,即人的本性开显,不仅在于其所好者是善、所恶者是恶所以是善的,更在于此好恶的道德价值判断是正当的,与天理相合,是天的意志的呈现,所以是至善的。那么整本《缁衣集传》所讨论的“好恶”,实际上是“好善恶恶”的本能,而不是“好”(喜好)或“恶”(厌恶)本身,因为只有“好善恶恶”这种本能才有至善性可言。
所以像宋明理学家追溯人性至善的来由一样,《缁衣集传》也讨论了人之“好恶”至善的来由。其论证过程不仅是:“好恶”根源于人性,人性是至善的,所以“好恶”是至善的;《缁衣集传》更是将“好恶”直接放置于根源之天的层面进行演绎。《缁衣集传》说“好繇天作,恶繇地奋。天动而好善,故因善以饰乐;地静而流恶,故因恶以立礼”(《缁衣集传·不烦章》),意思是说人的“好恶”产生于天地的动静。但是人的“好恶”如何产生于天地的动静?《缁衣集传》借助《周易·大有卦》的大象辞更进一步阐释道: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何谓也?曰:是法日之谓也。曰“虞帝之不法日”,何谓也?曰:隐恶扬善,天地之道也。然且举元除凶,不俟逾载,则是以日为道也。故陟明黜幽,鬼神所以从令也;喜阳恶阴,万物所以著性也。(《缁衣集传·示厚章》)
大有卦火在天上,这是日象,是太阳普照万物。那么,如何理解大有卦“遏恶扬善”?黄道周在《易象正》中说得更详细,“大有之遏扬,譬之临照,是天道也”[3]180,意思是说在太阳照射之下,一切贤人、不肖都十分明朗,无法隐匿,所以说“大明方中,邪慝不作”[3]181。那么由日所照万物,由天所命万物,万物的本性就与天相仿,所以鬼神从令、万物著性实际上是从日(天)之令、着日(天)之性。于是万物就有了日(天)的特点,也就是说陟明黜幽和喜阳恶阴都是万物所禀受于天的本性,而人的本性自然是包括于其中。
可见,人性的“好善恶恶”来由, 就是天性的陟明黜幽和喜阳恶阴。 善是阳, 恶是阴, 这是传统的中国哲学思想中的普遍认识。 事实上, 《缁衣集传》就是用人们的普遍认识, 即对善恶的阴阳定性, 来论证先天人性中的“好善恶恶”。
在论证人的“好善恶恶”的至善性之后,我们反过来也应该看到:人的道德价值判断有正误之分,所好者是善、所恶者是恶就属于正确,就是善的;所好者是恶、所恶者是善就属于谬误,就是恶的。人世间的道德判断出现正确与谬误的现象,亦即人的好恶行为具有善与恶的现象,那么我们就得讨论其根源所在。这个问题就是:人的“好恶”之所以存在恶的现象,其原因是什么?
从《缁衣集传》的诠释者黄道周的思想来看,他的人性论认为恶的来由是人性在后天被习气所破坏,在《缁衣集传》中对人的“好恶”之所以存在恶的现象其解释路数也与此相仿(3)关于黄道周的人性论思想,可参见拙作《黄道周对孟子性善论的坚守与诠释》(《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2期)。。《缁衣集传》说:“惟在堂陛之间,人人饰貌,则衡鉴难明;入于纷华之域,事事荡心,则爱憎易变。以易变之爱憎,投难明之衡鉴,故上听不清,下言愈乱,而《缁衣》《巷伯》之诗颠倒互诵也。”(《缁衣集传·恒德章》)这里出现的“爱憎”可以归入情感范畴,而“衡鉴”是衡器和镜子,就是鉴别的意思,主要体现为理性判断力。因此可以说,在黄道周看来爱憎情感与理性判断力,都是属于人的后天机能,都是来源于人的先天的好恶本能;或者说,人的后天的情感与理性都是统一与发端于先天的人性。
但是出于至善的人性中的好恶本能,为何却出现易变与难明的情况,也就是除了“好善恶恶”之外,还存在“好恶恶善”的恶的现象?人的理性判断力之所以难明,是因为在朝廷之上,人人都在伪装自己,所以理性判断受到遮蔽;人的爱憎情感易变,也就是可能出现恶的情况,是因为在纷华的世间,人被世事所左右迁移,所以“好恶一迁而情伪千出矣”(《缁衣集传·咸服章》)。也就是说在现实当中,人的“好恶”之所以存在恶的现象,是人处于朝廷之上、俗世之间受到的污染。因而将《缁衣》与《巷伯》之诗颠倒互诵,《缁衣》言善,《巷伯》言恶,人的本性受到后天的污染破坏之后,就会变成“好恶恶善”,就与“好善恶恶”完全颠倒了。这实际上是为人世间的“恶”安排一个合理的来由。
二、宋明理学中“好恶”归于性的一派
好恶问题虽然是《礼记·缁衣》篇的主旨性问题,如将好恶问题放置在整个宋明理学视野中,又会有怎样的阐发呢?宋明理学当中的心性论常有情、性二分或者心、性、情三分的习惯。《缁衣集传》将人之“好恶”归于性,其实只是其中一种,历史上也有一些思想家将“好恶”归于情,也有一些归于心。
将人之“好恶”归于性,最早可以追溯到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4]136,由于《性自命出》总体所展现的人性思想并非性善论,所以不曾将人之“好恶”收束为至善的“好善恶恶”,也就是说不仅好善恶恶,连好恶恶善也是属于人性的。这里“好恶”的范畴就包括了好善恶恶与好恶恶善,不特指好善恶恶,这一点与《缁衣》的好恶说有一定出入。有意思的是《性自命出》并非在区分性和情,而是区分性与物,亦即在讨论有关好恶问题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好恶是归于主体自身的一种属性(性),而主体的好恶所发则指向一定的客体对象(物),即所好者、所恶者。《性自命出》可以说是代表了早期儒家关于好恶问题的探讨。
朱熹则明确提出“好恶是情,好善恶恶是性”[5]396,好善恶恶更接近于一种超验的人性本能,而好恶则是从经验角度去观察定义的情感。也就是说朱熹的“好恶”一样是包括了具有好善恶恶与好恶恶善两种可能性,能发动产生此两种可能性的原因就是好恶这种情感;而其中的好善恶恶,虽然也是属于好恶情感的一种可能性,但是只有好善恶恶这种可能性符合先天的人性本能,或者说本身就是属于人性本能。
朱熹这一观点在他批评胡宏的时候,论述得更为详致。他说:“郭子和性论与五峰相类,其言曰‘目视耳听,性也’,此语非也。视明而听聪,乃性也。箕子分明说‘视曰明,听曰聪’,若以视听为性,与僧家作用是性何异?五峰曰‘好恶,性也。君子好恶以道,小人好恶以欲,君子小人者,天理人欲而已矣’,亦不是,盖好善恶恶乃性也。”[5]3385这里其实还有一些孟告之辨的意思。郭立之(子和)将人的生理机能(视听)视为性,胡宏也将属于人的生理机能的好恶视为性,这实际上是自然之性,就像告子的“食色,性也”。但是朱熹跟孟子一样,反对以自然论性。他认为眼睛具有看的功能不是性,眼睛应当能看明才是性;耳朵具有能听的功能不是性,耳朵应当能听清才是性。同样的道理,人具有好恶的功能不是性,人应当能够好善恶恶才是性,这实际上是应然之性。这一点是直接继承了孟子的论证方式。
所以胡宏对“好恶”的定性,以朱熹的理论看来就不是性,而是属于情。那么在朱熹的理论当中,人之“好恶”存在恶的现象,其来由是什么?关于这一点,其实朱熹是很容易就能为恶的现象找到来由的,因为既然认为人的“好恶是情”,那么恶就可以来自于情。不过朱熹用的是心的概念,他说“好善恶恶,人之性然也,而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党媢疾,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恶戾于常性”[2]卷一百五十三,意思是说后天环境对心产生干扰,从而导致了心对性的干扰。
可以通过比较黄道周与朱熹关于好恶问题的说法,发现二者的不同。朱熹认为好善恶恶是性,那么应该看到好善恶恶本身可以说是善的,好善恶恶就类似于朱熹预设的人性中的“天地之性”,是至善的。而朱熹在人性中除了“天地之性”外,还预设了“气质之性”,那么在好恶问题中“气质之性”将无处安放。因为好恶包括好善恶恶与好恶恶善两种,一种是善的,一种是恶的。如果好善恶恶属于“天地之性”,是至善的;而包括好善恶恶与好恶恶善的好恶属于“气质之性”,是有善有恶的,那么就讲得通。但是朱熹又说好恶是情,并不是性,也不是“气质之性”。于是朱熹对好恶问题的解释,在其心性论内部就产生了矛盾。
性与情已是二分,而性中“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又是二分,难免过于支离,这也是黄道周坚决反对“气质之性”这一说法的原因。相形之下,黄道周对好恶问题的解释可能会显得完善一些。他将人的好恶视为性,是至善的,是掺杂不得一丝气质的。这里的“好恶”其实单就先天本能而言,即好善恶恶,因为出现好恶恶善的现象是后天行为。黄道周将后天出现的好善恶恶与好恶恶善两种现象称为人的爱憎,也就是视为情,即属于气质的层面。我们用简单模型画出,如下:

可以看出,朱熹对“好恶”的定性,出现了“情”与“气质之性”的矛盾。所以,同样在将“好恶(好善恶恶)”视为性的一派当中,黄道周对好恶问题的解释是相对完善的。当然,从总体框架上看,二者均属于将“好恶”归于性的一派。
三、理学视域中“好恶”归于心的一派
对人之“好恶”的定性,在宋明理学史上,还有一派归属于心。这一说法也一样可以追溯到孟子,也一样借助了孟子的论证方法。他们利用了孟子的“四心说”,黄榦说道:“孟子曰‘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诚能自其好善恶恶之本心,广而充之,则骎骎乎君子之途矣。”[6]卷二十四黄榦虽出自朱子门下,但在心性的说法上其实与朱子稍微有一点差别。黄榦一方面也说“性即理也”[6]卷二十五,但是他同时又突出强调了“盖心者,万化之根本”[6]卷二十四,比之朱子是提高了心的地位,所以黄榦甚至认为“心便是性,性便是心”[6]卷十一。这一说法恐怕是朱子所不肯赞同的。那么反过来看,这里出现的好善恶恶的“本心”,实际上与朱熹的好善恶恶之“性”指的是一个东西,只是在黄榦的思想中,此本心与性没有十分严格的分别了,或者说他更愿意照着孟子的原话讲。关于这一点,牟宗三也做过一些说明,他讲道:“在孟子这个地方,‘性’是个虚位字,它的具体意义都从‘心’这里见。心不是抽象的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就是心。这个‘心’就是纯粹是理性的。没有一点感性的夹杂,所以它才能建立道德。”[7]
可以看出,其实无论是黄榦还是牟宗三,都在努力调和孟子思想中的“性”和“心”,而王阳明则在“心”这一条路上走得更远。王阳明也承认“心之本体则性也”[8],但他对“性”并没有多少探索的欲望,其学说的用力点全在于这个“心”上。所以他将人之“好恶”归于心,他借助孟子的概念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9]136,这里的良知、是非之心、好恶之心都是处于同一个层面的。
良知至善,那么是非之心、好恶之心自然也无不善,但是作为本体的“心”是需要不断做工夫才能达到的,而同时作为身之主宰的“心”,又如何指导道德主体做工夫去达到本体之“心”呢?这里就陷入一个困境,即“心”指导道德主体的行为达到“心”。于是王阳明不得不另外发掘出一个可以代替前者“心”的“意”,从而保持后者“心”的本体至善性。他说“为学工夫有浅深,初时若不着实用意去好善恶恶,如何能为善去恶”[9]53,用意即在于以“意”指导道德主体的行为达到良知之“心”。
王阳明这句话又分明将“好善恶恶”当成手段,将“为善去恶”当成目的。按理说,应是着意去“为善去恶”(手段)而达到“好善恶恶”之本心(目的);亦即在阳明四句教中,“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通过格物的手段达到良知的目的。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设置,即在其工夫论中目的与手段的混乱。所以在阳明的理论框架内,如果将“好善恶恶”归于心,可能是会出现矛盾的。
于是王阳明通过将“意”与“心”的融合,以及将“好善恶恶”排除于心之外,来修补自身理论可能出现的漏洞。他说“不知心之本体原无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恶恶,便又多了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书》所谓‘无有作好、作恶’方是本体,所以说有所忿懥好乐则不得其正”[9]53,这里则提出本体之心没有好恶,就将人之“好善恶恶”排除在心之外了。
既然“好善恶恶”不属于心,那么是属于意么?即陆澄问:“‘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安得非意?”王阳明回答说:“却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愤好乐则不得其正,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9]48在这里,王阳明既说人之好恶是诚意,又说亦着不得一分意,也就是说既是意,又不是意;而当能廓然大公时,好像又是本体之心。这样的说法比较模糊,始终无法安置“好善恶恶”的属性。
心学一脉传至刘宗周,对好恶问题有了相对完善的解释。在刘宗周的思想中,“意”是居于本体地位的,这一点在上世纪已有不少人讨论过(4)相关研究如:杨国荣《晚明王学演变的一个环节——论刘宗周对“意”的考察》(《浙江学刊》1988年第4期),张学智《论刘宗周的“意”》(《哲学研究》1993年第9期)。。所以刘宗周对人之“好恶”的定性,不再是在“心”与“意”间摇摆不定,而是认为“好善恶恶者,意之动。此《诚意》章本文语也。如以善恶属意,则好之恶之者谁乎?如云心去好之,心去恶之,则又与无善无恶之旨相戾。今据本文,好恶是意,则意以所发言,而不专属所存,明矣”[10]卷八,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好恶属于意而不属于心,否则就与“无善无恶心之体”相违背,因为无善无恶的心体自然不会好善恶恶。
将人之“好恶”归于意,大体仍可算是心学一派,只是刘宗周沿着王阳明的“心”的路子越走越远。尽管刘宗周与黄道周是同时代并称“二周”的大儒,并且刘宗周也能够对好恶问题作出相对圆融的解释,但他偏离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概念可能比较远,而黄道周则始终坚守着孟子的性善论。
对人之“好恶”的定性,除了主流的性与心之外,还有少数人认为归于情,并且多少与阳明学说有些关系。譬如明代沈佳胤认为“好善恶恶,情也;去善从恶,习气也;改恶迁善,工夫也”[11]卷六,用的是阳明的概念,却与阳明的学说大不相同了。再如清代罗泽南认为:“好恶,情也;好善恶恶,情之正也。《大学》‘诚意’而后,又有‘正心’一段。工夫者,盖人过得诚意一关,所好所恶已皆准之天理,特恐忿、好乐、恐惧、忧患之情一有之而不察,事前将迎,事后凝滞,此心不能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意虽已诚,心犹不可谓之正。诚意,诚此好恶也;正心,即正此好恶也。岂有诚意遂着意好善恶恶,正心遂不着意好善恶恶乎?”[12]卷二这里体现了对阳明学说的反驳。今天学者一般将好恶当作是人的一种情感,但实际上古人较少持这种观念。
四、传统西方哲学对好恶问题的多维解释
宋明理学如此解释人之“好恶”,西方哲学又是如何看待好恶问题呢?在西方哲学中,没有性、情二分或心、性、情三分,主要是区分理性和感性。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方哲学就十分推崇理性,理性可以说是整个西方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人的好善恶恶、辨别是非的能力来源于理性,这是整个西方哲学的基调。其实人之“好恶”总有理性的成分,也包含着感性的因素,但西方哲学一向拒斥感性,宁愿将“好恶”视为一种理性能力。这里的“好恶”是指好善恶恶的道德判断,就像王阳明讲的“是非只是个好恶”。所以本文并非旨在探讨西方哲学应将“好恶”归于理性还是归于感性,而是期望借助西方哲学,以其理性智慧对好恶问题的多维解释,更好地把握中国哲学对人之“好恶”的看法。
理性作为人的一种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当理性与道德主体的行为相结合时也就成为德性。所以人的理性中的好善恶恶的彰显,就需要从德性的层面去考量。但是理性是人作为人所固有的特质,德性却不是先天本有的,而是后天所得的。亚里士多德说道:“德性既不是以自然的方式,也不是以违反自然的方式移植在我们之中。我们自然地倾向于获得德性,但却通过习惯培养起德性。”[13]23这里突出强调了德性不是向外在获取而后移植到人心之中,也就是说德性是具有内在可能性的。但虽然是内在的,却只是一种可能性,或者说只是一种潜在的倾向而已。如果我们在后天对这一可能性置之不理,它并不会自然生长,也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没有一种伦理德性是自然生成的,因为没有一种自然存在的东西能够改变习性。……我们的德性既非出于本性而生成,也非反乎本性而生成,而是自然地接受了它们,通过习惯而达到完满”[13]25,这里的“习性”可以理解为先天本性,类似于告子说的“食色,性也”的自然之性。而德性却是“先以潜能的形式把它随身携带,然后以现实活动的方式把它展示出来”[13]26,我们实在不好拿这里的所谓“潜能的形式”与孟子的“善端”作比较,因为亚里士多德并不看重这一“潜能的形式”,他所反复强调的是现实活动的重要性。基于这一点,如果从先天与后天的角度上进行区分,我们宁愿将德性认为是后天的,因为它的一切意义都在于后天。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对待德性的得到时,相比于“获得”,更喜欢用“培养”这一词的原因。
那么好善恶恶、辨别是非的能力,自然也需要在后天培养。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先天的东西没有地位或者说地位明显不足。这是与宋明理学家对人的先天之性的看重所十分不同的地方。相比而言,中国传统的思想家对人抱有更大的信心,从而对民性、人民、政治是充满理想主义的希望的。
文艺复兴以来,康德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对好恶问题的讨论并非重要内容,不过也有了新的解释。人的好善恶恶、辨别是非的能力是一种合乎理性的、普遍的、无条件的绝对命令,这一绝对命令来自于善良意志的自律。这里出现的“意志”并不是意志主义者像叔本华、尼采讲的那种作为世界本体和万物根源的、主观精神性的意志,而是“一个只有准则的单纯立法形式能够用作共同法则的意志”[14]29,所以这种自由意志显然是理性的。因为康德实际上是十分拒斥感性的,认为这种自由可以独立于感性之外,他认为“在实践的理解中的自由就是任意性对于由感性冲动而来的强迫的独立性。……人的任意虽然是一种感性的任意,但不是动物性的,而是自由的,因为感性并不能使人的行动成为必然的,相反,人身上具有一种独立于感性冲动的强迫而自行规定自己的能力”[15]434,也就是说道德实践包括好善恶恶的行为发动于自由意志,而且是必然的行为。这是一种普遍的道德律,是理性为自身立法。
那么,这种好善恶恶所发端的自由意志就是先天的,是“一种不须一切经验的动因、一种完全由先天原则来决定,被称之为纯粹意志的意志”[16]5。但是在康德的学说里,这种由先天原则决定的自由意志,却是我们无法像在中国哲学中追溯人性的来源那样,去探讨自由意志的来源或性质。而且康德也说了这一点,关于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通过理性去知道它,“当我们意识到某物即使没有如经验中那样对我们出现,我们也是有可能知道它的,这时我们就通过理性而认识了某物,因而理性的知识和先天的知识是同样的”[14]31;但是我们却无法思辨、推导、论证它,也就是康德说的“不要跳过自然的原因和放弃经验可能教给我们的东西,而去把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从完全超出我们的一切知识之上的东西中推导出来”[15]608。理性之外的东西无法把握,近似于超验,那么只能给这一些全善、全知、全能的上帝以及灵魂、信仰腾出位置,于是等于就恢复了宗教。这是与中国哲学最大的不同所在。
宋明理学家所认为的好善恶恶是先天的人性本能,与康德对自由意志的设置有一定的相似性,因为二者都是先天的自发的能动力量,都是纯粹至善的。但是康德将自由意志的来由交给了上帝,而中国的思想家对人性的来由一般都认为“天命之谓性”或“性自命出,命由天降”,也就是来源于天。在这样的思维与论证方式下,传统儒家才没有发展出关于像上帝的人格神的宗教,而是走向了讲求天人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