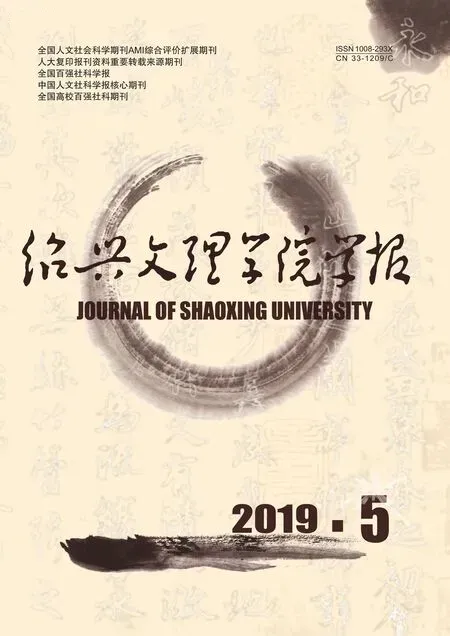超越历史 对话当下
——鲁迅翻译理论研究路线
彭勇穗
(广东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引言
据《鲁迅译文全集》(2008)统计,鲁迅一生译作达300多万字,涉及15个国家、77位作家的225部作品,成果丰硕,是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史的一座丰碑。鲁迅还撰写了大量译论(含译者附记、序言,以及专论翻译的文章,尤其是1920—1930年期间),被视为“现代翻译理论的发端”[1]195-223,是“中国现代翻译理论的建设者”[2]143。
鲁迅译论虽含理论要素,但形式零散,很难直接称为“鲁迅翻译理论”。不过,从1909年的《〈域外小说集〉序言》到1935年的《“题未定”草》,鲁迅的翻译思想高度连贯,涵盖翻译目的、翻译选材、翻译原则、翻译方法、译文效果、翻译伦理等方方面面。由此而言,鲁迅虽无明确的翻译理论体系,却有着系统、深刻的思考,至今读来仍有普遍意义和参考价值,因而,挖掘和重建鲁迅翻译理论既可行也有价值。
这种重建也十分必要。迄今为止,大多数鲁迅翻译思想研究史学倾向显著,大都侧重概括鲁迅翻译思想的主要面向,如解读“信”“直译”“硬译”“易解”“丰姿”或“不顺”等的历史含义。这些研究虽然把握了鲁迅翻译思想的若干要点,却未能充分反映鲁迅翻译思想的深层核心、内在逻辑和具有普遍价值的译学要素,因而,有必要讨论相关研究方法。而且,国内译学开始重视中国本土译论的现代转化,讨论“鲁迅翻译理论”的研究方法和路线对这些研究也有参考价值。
一、“鲁迅翻译理论研究”在“鲁迅翻译研究”中的位置
涉及鲁迅译论和译作的研究统称为“鲁迅翻译研究”,如《鲁迅翻译研究论文集》[3]。这些研究根据目标不同分为“涉及鲁迅翻译的研究”(Studies relative to Lu Xun’s Translation/s)和“关于鲁迅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 on Lu Xun)。前者范围较广,各人文学科带着本学科议题都可以讨论鲁迅的译论和译文。“关于鲁迅的翻译研究”主要围绕翻译关系(源文—译文关系)核心议题,探讨翻译行为的策略、方法、原则、目标、伦理等要素。
“关于鲁迅的翻译研究”根据主要研究对象不同又分为译论研究和译作研究。鲁迅译论是鲁迅在翻译实践基础上,批判吸收古今中外相关(翻译)思想的结晶,在翻译思想史的(跨)文化经纬和历史脉络中占据重要位置,具有独立研究价值。鲁迅译作研究又可分为两种路径,如卜立德[4]重译本对比批评,王友贵[5]侧重结合文化语境描述译本。译论研究与译作研究相互影响,译论研究有助研究者深入解读译作。译作研究可为译论研究提供经验基础,有助准确把握鲁迅译论关键词的具体含义。
译论研究和译作研究交叉于翻译思想研究。翻译思想研究分历时和共时两种路径:前者旨在分析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具体思想,定性和定量可结合使用;后者旨在归纳核心思想,揭示普遍要素,主要是定性研究。历时思想研究和共时理论研究代表了思想的两种形态:一种是具体、特殊的理性认识,直接指向特定翻译实践;一种是抽象、普遍的理性认识,相对独立于特定翻译实践,指向同类实践。“在对汉、德、日几种语言文本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论证鲁迅的翻译思想和艺术上的独创性”[3]2,其实只代表第一类研究,属历时路径下的鲁迅翻译思想研究。
翻译理论研究是共时翻译思想研究的高级阶段。翻译理论研究以扎实的历时翻译思想研究成果为基础进行理论化提升,从中揭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译学理论概念和原则。一般而言,理论化过程表现为:将具体事物转化为抽象概念,将特殊性判读转化为普遍形式逻辑,将悖论思考转化为辩证论述。理论的普遍性程度与理论化程度相关,取决于研究者的概念化、逻辑化程度。因此,理论虽表现为严密的形式逻辑关系,本质上却带有研究者的视角,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抽象思辨对话(详见本文最后一节)。
高玉曾提出,“鲁迅翻译理论研究虽不属于鲁迅文学翻译研究,但与之有密切关系”[6]。此言虽有洞见,但可进一步提炼。鲁迅翻译理论分“鲁迅文学翻译理论”和“鲁迅非文学翻译理论”,前者对应“鲁迅文学翻译”,后者对应“鲁迅非文学翻译”。“鲁迅文学翻译理论”是“鲁迅翻译理论”的一部分,与“鲁迅文学翻译研究”关系密切而又相互独立,是在后者基础上,特别考察文学译作生产背后与文学有关的译学理论要素。文学观影响了鲁迅的翻译方法心态和意图,如,鲁迅在《艺术论》和《小约翰》中都用了直译, 但心态完全不一样:前一种情况下,他承认译本“诘屈枯涩”, 希望“潜心研究者, 解散原来句法, 并将术语改浅,意译为近于解释”[7]44;后一种情况下,他认为直译“倘一解散,精神和力量就不同”[8]72。又如,即便不同作品都用了意译,他的目的也不同:《艺术论》中的意译是为了“解释”,而《小约翰》之人物名意译却为了保存“象征”。

“鲁迅翻译研究”系谱图
二、鲁迅翻译思想的研究资料范围
明确的研究范围是研究的必要基础。在鲁迅翻译思想研究中,学界常把1909年的《〈域外小说集〉序言》视为鲁迅自觉翻译思想的发端[5]28-32。王友贵还提出,从1907年起,鲁迅“更多的用心渐渐移至文学艺术与文化的一面,如重要的文章《文化偏至论》(1907)、《摩罗诗力说》(1907)等,后者在中国文学界的影响,起初并不明显,可后来愈来愈大”[5]14,不过,他并未深入讨论这些文章蕴含哪些潜在翻译思想。
其实,鲁迅的翻译思想转变与其文学思想转变相勾连,而1907—1909年间这些被称为“元鲁迅”[9]的文章正是鲁迅自觉翻译思想的根源,鲁迅思想研究界对此有普遍认知。例如,李欧梵就指出,“约在1907年他(鲁迅)已经离开了梁启超的以文学为政治教育工具的功利观点,而把文学看做一个民族精神本质的集中体现,它最能检验‘国民性’”[10]22。李泽厚则进一步把转变定在《科学史教篇》,指出该文前半属科学救国,后半属思想启蒙[11]452。在此基础上,郜元宝进一步提出,《科学史教篇》表面讨论科学,“实际上是要从西方科学发展所提供的经验教训中看到科学之下所隐藏的西方各民族精神发达的轨迹”,重心在“民族精神”[12]5。陋见以为,《人之历史》把焦点转到人身上,《科学史教篇》揭示“神思”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性,《文化偏至论》继而批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和政治文明,《摩罗诗力说》形成对真诚心声的向往,《破恶声论》展现对“去伪存真”的追求。这一系列文章形成鲁迅文学立人思想的同时,也兆示了他的翻译思想纲领——包括宗旨、路径、选择原则、方法、伦理等,《〈域外小说集〉序言》是这些思想的表达。
因此,鲁迅自觉翻译思想根源可追溯至1907年,并一直坚持到最后,1935年的《“题未定”草》与1907年保持着高度的质的一致性,只在部分思想上有所细化深化。1907年后的翻译生涯构成了鲁迅翻译思想研究的主要范围(1)曾有研究者根据鲁迅译作主题或翻译技巧来进行时期划分。据译作主题划分1903—1918、1919—1927、1928—1936三阶段,根据译文语言是文言文和白话划分了1903—1918、1919—1936两个阶段,翻译策略探索期1903—1909、直译期1909—1928、直译+硬译1928—1936。这些划分虽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要对鲁迅翻译思想发展演变进行阶段划分,不宜直接套用主题或翻译策略的阶段划分。,不过,1903—1906年也不能完全忽略。这个时期,鲁迅处自发翻译阶段,思想驳杂,译法兼具直译和编译。1903年的《哀尘》《斯巴达之魂》《月界旅行》已出现人名地名等专名音译,是“值得注意的变化”[5]10。
自发期和自觉期既相互独立,又有一定联系。如,1903年他翻译《月界旅行》的目标是“导中国人群以进行”,这与他1909年翻译《域外小说集》时追求“性解思维”的目标相近,都属目的语倾向(target-oriented)。但是,自发期的目的语倾向主要是时代潮流所致,受梁启超新小说思想影响颇大,与他1907年后的文学启蒙思想有本质区别。
根据鲁迅译论中关键表述的发展和变化,鲁迅翻译思想可分为五个阶段:
摸索期(1903—1906):此时期鲁迅尚未形成自己自觉的翻译思想,实践和译论明显受晚清主要学者影响,受梁启超新小说思想和晚清意译风尚影响显著,主要编译科学小说。
觉醒期(1907—1917):此时期鲁迅开始萌发自己独立自觉的翻译理论意识,但是,在关键译论表述上受严复影响较大,一方面仍沿用“诚”“信”“达”等字眼(刘少勤提出鲁迅的翻译伦理是诚[15]172-173,但未展开深入讨论),另一方面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立主张,如用“弗失文情”和“循字移译”来反对林纾式误译,用“词致朴纳”反对严复桐城雅文;翻译选材明确转向现代主义文学,文字上采用文言文进行翻译。
发展期(1918—1927):此时期鲁迅受新文化运动中刘半农等人影响,译论在“逐字译”基础上扩大到“逐字译”和“直译”并用,小说翻译实践丰富,受陈独秀、胡适主张的文学革命影响较大,翻译目的明确,即从外国借来“火把”和“药”,译文采用白话。
个性期(1928—1933):此时期鲁迅除继续小说翻译、继续用“直译”“逐字译”外,一个鲜明特点是着手苏联文艺理论翻译并与梁实秋等展开论辩,提出极具个性的“硬译”和“宁信而不顺”——“硬译”主要针对文艺理论翻译,不能用来指代鲁迅翻译思想全部。这个时期鲁迅有关翻译取材、目标读者、语言革新目标等思想受瞿秋白影响。
总结期(1934—1936):此时期鲁迅陆续回顾和总结自己的翻译思想,论及复译、重译等话题,并从语言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洋化”“异国情调”)。此时期许多提法也呼应他此前不同阶段的一些翻译思想。
总体上,鲁迅译作多,论述也不少,研究资料可谓汗牛充栋。对鲁迅翻译理论研究来说,相关研究资料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包括译论和译序,是研究的主要基础资料。罗新璋收录了一些代表性文章,但不能反映鲁迅翻译思想全貌。《译文序跋集》(2006)和《鲁迅全集(编年版)》(2014)提供了这方面的研究便利。至于鲁迅专门论翻译的文章,王友贵认为“比较重要的有三十篇”[5]155,不过,王先生实际引用了46篇。此外,鲁迅关于跨文化思考的杂文也有参考价值。
第二类是鲁迅的译文及相关研究成果,如《鲁迅译文全集》[13],以及伦德堡格(Lundburg)[14]、刘少勤[15]、王友贵[5]、顾钧[16]、黄乔生[3]等学者的相关论著。
第三类是鲁迅思想研究成果,如(但不限于):郜元宝的鲁迅文学研究[12]、李欧梵的鲁迅生平研究[10]、钱理群的鲁迅思想研究[17]等。
三、解读范畴和术语
鲁迅译论研究容易陷入孤立化和表面化倾向,即抽取某个流传较广的论断(如“宁信而不顺”“异国情调”“丰姿”“硬译”等),从字面解释其含义,或引用当代批评理论、翻译理论加以阐述,这种做法易脱离鲁迅翻译思想的内在关联,也易脱离历史语境。不过,鲁迅翻译思想研究又难免要用特定范畴和术语进行解读和概括,具体范畴和术语的选择取决于研究范式。传统译学范式下,“忠实”“对等”“准确”“可达性”等构成常用范畴,相应的,“直译”多被用来概括鲁迅翻译思想。许多聚焦“易解”“丰姿”“信”的研究就属这类。后结构主义译学范式下,鲁迅翻译的“历史”“目的”“文化意义”等受到特别关注,用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式的“异化翻译”来解读“硬译”“不顺”的文化意义的研究属于这类。
陋见以为,“直译”和“异化”这两个现行范畴并不十分切当。陈福康指出,鲁迅“直译”其实“包括正确的意译在内的‘正译’”[18]292,它与学界通常使用的“直译”有一定区别,那么,直接套用“直译”会令人错失鲁迅翻译思想特质。另一方面,王东风[19]曾揭示鲁迅和韦努蒂两人的“异化”有较大区别。那么,未加说明地直接套用“异化”也易产生误读。此外,“硬译”仅在苏联文艺理论论争期间使用较多,特指学术翻译(而非文学翻译),用这个概念指代鲁迅翻译思想易陷入以偏概全的误区。实际上,鲁迅主张的翻译策略——如果暂时搁置用什么概念描述的话——兼具“异化”的传统和后现代用法,同时包含充分性翻译和目的性两大原则,若照搬现有术语恐有削足适履之虞。
搁置现有术语、专注鲁迅译论话语本身,从他自身语汇中挖掘相关思想要素进行概念化和理论化,这或是鲁迅翻译理论研究的可行路径。笔者有些初步体会,就此抛砖引玉。
鲁迅译论处于传统与现代之交和中西之汇,研究他的翻译思想离不开这个总的(跨)文化经纬。其中,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周作人、歌德(及其背后的德国浪漫主义翻译思潮)、刘半农、瞿秋白等人先后在某种程度上发挥正面、直接影响,此外,林纾、梁实秋等人也从反面给了鲁迅灵感。鲁迅翻译思想的解读和把握需要结合上述思想背景和对话对象。
鲁迅翻译思想来源驳杂,潜藏四个主要思想要素:古、异、新、当下,是这四个思想要素互动的产物。如,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宣告他的跨文化借鉴总纲领:“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其因即动于怀古”[20]82。他的“古”指仍未被封建正统文化禁锢,仍能“抱诚守真”之古,或“摩罗诗人”的“抱诚守真”之古。他的“异”重在与目的语本土相对比后呈现的“新”——所以哪怕原作者意见是“古典底、避世底,但也极有确切中肯的处所,比中国的自以为新的学者们要新得多”[21]370,鲁迅也会选译。他的“求”彰显了实践性、主体性、当下性、本土性。异中求新,复古以鉴今,这是鲁迅总的翻译思想纲领。
目前,鲁迅翻译思想研究对“古”的要素和“今”的讨论均不够深入。对于古,学界基本观念要么是《域外小说集》语言的“古奥”,要么就是严复乃至佛经翻译思想对鲁迅的影响,而对“古”中其他潜藏要素未深入挖掘。至于“今”,现研究多聚焦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至于鲁迅通过什么方式驾驭域外和本土、古和今,以实现尊重原作者和译者自身目的的对立统一,这些问题仍有较大探讨空间。因此,今后的研究方向或是,通过研究鲁迅对“古”的怀念和追求,从深层次理解鲁迅翻译理论中的异质性、本土性、新颖性、当下性四要素如何实现统一。
退一步讲,即便移植现有术语进行研究并非全无用处,也要特别注意研究方式。孙艺风指出,“翻译学术语的移植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的、文化的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属性。在移植过程中,不同语言和文化系统发生关系,势必产生巨大张力。然而,从潜在意义上看,张力既是对话的产物,也是活力的开始”[22]33。确实,理论及其术语在不同本土语境中浸染不同的思想基础和研究诉求,术语移植会给研究带来张力。研究者若能敏锐捕捉张力并深入探讨,有助暴露原有(外来)翻译理论和术语的本土局限性,反过来提升其普遍性。因而,鲁迅翻译理论研究若采取这种双向批判——既批判阅读鲁迅翻译思想,也批判对待现有译学范畴和术语,有助于揭示术语背后的理论假定及其本土性,转而把现有术语当作待完善的假定,以探寻这些术语之“鲁迅义”,真正深入解读和理论化鲁迅翻译思想,丰富现有术语含义,推进译学理论建设。
四、超越历史,对话当下
鲁迅翻译理论研究以鲁迅翻译思想历时研究为基础,不过,历时研究后并不直接进入理论研究,需经共时研究初级阶段作为过渡。这个阶段旨在从总体上概括鲁迅翻译思想,归纳其宗旨、选材、目标、方法、伦理等。这个阶段虽也参考鲁迅译作研究成果,但以鲁迅的译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不过,鲁迅译论零散,时间跨度大,多基于当时中国历史语境,针对特定话题或作品而发,有时前后矛盾,如何处理好历时差异和共性一致性的关系是一个巨大挑战。共时研究初级阶段之后便进入理论研究,后者主要表现为将思想概念化和逻辑化。概念化指提炼思想要素关键词并进行抽象化定义;逻辑化指通过分析、演绎和思辨,重建概念间的逻辑关系。概念化和逻辑化之后,联系当代相关翻译理论原则及概念进行比较,有助于揭示有鲁迅特色的普遍译学要素。
首先,鲁迅翻译思想富含许多翻译思想要素,这些要素需进行概念化处理,以便从中提炼有鲁迅特色的理论术语。不过,鲁迅翻译思想有的用传统译学词汇表达,有的用日常词汇,散布于译论中,这些译作体裁、题材多样。研究者需要做出总体性判断和把握,提取具有跨时期连贯性和跨体裁、题材一致性的译论关键词,将其用作潜在概念加以解读、论证、定义,这个概念化过程用钱理群的话说是:“将鲁迅思想命题中的普遍内容与形式,从具体的历史纠葛中剥离出来”,将隐含的“抽象的逻辑范畴”从“具体的、生动的、形象的现象形态”中剥离出来[17]64-65。概念化是抽象化和去本土化,旨在揭示普遍性的译学概念,因而分析范畴就不是“中国”“外国”等本土指称,而是“目的语文化”“源语文化”等中性表述。
其次,概念化之后需进行逻辑化处理,即根据鲁迅的翻译行为逻辑(包括动机和目的等)重建各概念间的逻辑。这就要同时参考鲁迅自己的表述和(译)学界研究成果。需要指出的是,重建起来的逻辑关系虽超越具体历史事物,却不是非历史的(a-historical)。这些逻辑关系本质上不是客观因果关系,而是以文化价值观念为基础的社会因果关系,是文化逻辑。所以,尽管理论化过程剥离了历史内容,但这是相对剥离而非绝对剥离,是概念内容层面的剥离,而不是形式逻辑层面的剥离。鲁迅思想具有浓厚的人文思辨色彩,“总是在肯定的同时提出质疑”,“又在质疑的同时作出肯定”,表现出“双重肯定与双重否定”[17]93,这就要求概念逻辑重建过程也体现辩证性。
再者,概念化逻辑化后,理论比较和抽象归纳有助于提炼普遍译学要素。通过揭示鲁迅翻译理论与其他相近理论的共性和差异,一方面可彰显鲁迅在某些译学普遍议题上的独特视角,另一方面也检视各理论在相近概念、逻辑上的本土局限性,以便互为补充互为借鉴,获得更具普遍性的概念、更严密和辩证的逻辑,为译学注入新的思考。
尽管鲁迅翻译理论研究表现为概念化和逻辑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论是稳定、封闭的逻辑概念体系。理论研究包含探寻“深层结构”、进行“公共对话”[22]26-27两大要素,甚至可以说是在“深层结构”上的“公共对话”。其中,深层结构是公共对话的前提,研究只有超越表象和特殊性,提炼出一定抽象性、普遍性的概念和逻辑,研究内容才有公共对话的品质。公共对话是揭示深层结构的目标所在。如果鲁迅翻译思想研究不能从历时走向共时,从共时提炼抽象的概念、逻辑,它的价值就会受到限制,只构成思想史研究成果,不构成译学理论研究课题。如果研究最终不具有对话当下现实的潜力,理论研究也失去了其当代活力。
理论的对话潜力取决于理论的基本构成要素——概念。概念是符号,概念符号的抽象性决定了其指涉的开放性和普适性,这是理论概念指向新的历史、新的实践的潜力所在,而研究者和使用者带着实践关切和本土当下视域,为概念注入新的历史内涵。新的历史境域蕴含新的实践关系,这些关系反过来激活概念在概念化前、在过往历史实践中被遮蔽、未被展开的潜在关系。因此,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或者说,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从特殊到普遍再到特殊,从历史到形式再到新的历史,这个过程见证了思想的升华、深化和发展,从形式上看是概念的否定运动,从经验层面看是历史与历史、主体与主体间的对话。
对话有其时空状语。研究需特别注意重新检视鲁迅译学主张哪些要素、多大程度上、何种条件下,对当下跨文化实践有何启示意义。具体而言,研究者总是基于特定时代语境展开理论研究,“寻找对于当代有着深刻启示意义的鲁迅”[23]45。这既要结合译学的发展对鲁迅翻译思想进行扬弃(如“重译”思想),也要结合当下历史语境挖掘其潜力。过去二三十年,西方翻译理论的大量引进冲击和刺激了本土传统译论研究,译学界开始对本土传统译论进行现代阐释,这类研究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召唤中被进一步激发,本土译学理论生产和输出成为新的时代使命。同时,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之际,重新阐释鲁迅翻译思想已成为反思全球化中本土和异域关系、传统和现代关系的一种方式,是全球秩序重建的一个重要方式。这种背景下,研究者从鲁迅译论思想中挖掘有传统文化根源的理论要素,是对时代的回应、对当代实践的回应、对全球化的再定义。
理论对话也具有主体性。关于译学理论研究方法,陈福康说,研究者如果不拘泥于时间先后,照自己的剪接和理论设计,将有关材料重新组合,以论带史,优点是易先出理论性和体系性,缺点是写得浮,容易只见林不见树木[18]6。“以论带史”是研究者采用特定范畴阐释译学思想的结果,背后离不开主体性的发挥,以便对有关材料进行“剪接和重新组合”,这种思路下,“见林不见木”未必是缺点,理论研究的目的本就是剥离个别的、经验的现象以获取抽象的、普遍的要素。
对话还包含主体间性维度。“翻译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验事实,而非自然事实,这种事实必定包含有观察者的价值因素。”[24]由于不同研究者的实践诉求和价值关切可能不同,所选阐释范畴也就随之不同,所用“剪接和重新组合”方式也因之不同,最终眼中所见的“林”自然不同。这种不同使研究者之间的对话显得更有必要。研究就成为各研究者之间以及研究者与鲁迅之间对翻译选材和方法的价值协商和再定位。
因而,理论研究者对历史翻译思想的阐释是历史地阐释,研究者从自身历史语境出发,与过往翻译思想和其他研究者进行抽象思辨对话。研究者或揭示鲁迅译学概念的当代价值,或使当代理论概念在鲁迅案例中展现新的生命力,最终不断丰富现有翻译理论、指向当下跨文化实践。因此,“鲁迅翻译理论”一词与其说指向本体,旨在获得“放之四海皆准”的知识、原理,获得稳定、封闭的结构体系,不如说指向认识过程,指向不断对话和(再)建构的过程,旨在不断重建过往历史经验与当下的相关性。
五、结语
理论是思想的高级形态。理论研究旨在超越历史现象和具体经验,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或形成具有一定认识论意义的认知方式。普遍性意味着理论知识向着新的历史和实践开放,因而,理论研究不是封闭、稳定的概念体系,而是通过抽象化,尽可能消除知识的本土性和特殊性,以更好地解释或指导新的实践。换言之,理论只是中间物,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不在理论,而是通过认识过去启发当下,是历史与当下的对话。鲁迅翻译理论研究便旨在从鲁迅的翻译思想中提炼出对当下跨文化实践、译学理论建设有价值的思想要素,回应时代使命,回应当下跨文化交流的主要关切。
——黄忠廉教授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