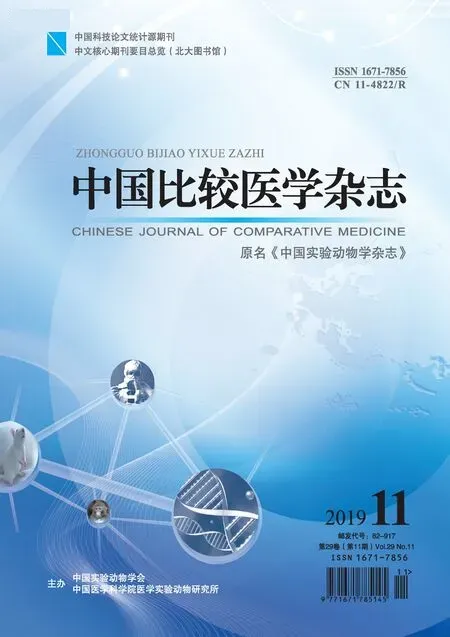免疫系统人源化小鼠模型的构建及其在肿瘤治疗研究中的应用
郭文文,乔天运,张彩勤,赵菊梅,师长宏*
(1.延安大学医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2.空军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西安 710032)
肿瘤免疫治疗是继手术、放疗、化疗与分子靶向治疗后,又一种新的能够改善肿瘤患者生存期的治疗方法。自2011年FDA批准首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pilimumab应用于黑色素瘤治疗后,免疫制剂在临床上已用于非小细胞肺癌、肾癌、头颈鳞癌、霍奇金淋巴瘤、恶性黑色素瘤等的治疗,并显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1-3]。肿瘤免疫治疗的进一步研究需要建立人体肿瘤与人体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动物模型。通常肿瘤模型是利用免疫缺陷动物移植入人体肿瘤细胞或组织,而该类动物由于缺乏完整的免疫系统,无法用于免疫治疗研究。人们尝试在免疫缺陷小鼠体内移植入人造血干细胞或功能性的淋巴细胞,使其具有人的免疫功能,这样的小鼠称为免疫系统人源化小鼠。该模型可模拟人体肿瘤细胞与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肿瘤免疫治疗药物的研发与临床前评估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本文重点综述免疫系统人源化小鼠模型的类型、构建方法以及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应用。
1 免疫系统人源化小鼠模型的构建
重度联合免疫缺陷动物由于T、B、NK免疫细胞的缺乏,广泛应用于人源化小鼠模型的构建,常用品系主要有NSG(NOD.Cg-PrkdcscidIl-2rgtmlWjl/SzJ)[4]、NOG(NOD.Cg-PrkdcscidIl-2rgtmlSug/JicTac)[5]、NRG(C.Cg-Rag1tm1MomIl-2rgtmlWjl/SzJ)[6]等。除此之外,用于人源化的NSG-SGM3(NOD.Cg-PrkdcscidIl-2rgtm1WjlTg(CMV IL-3,CSF2,KITLG)1Eav/MloySzJ)小鼠表达人IL-3、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GM-CSF)和干细胞因子,允许人造血干细胞(hematopoietic stem cell,HSC)的稳定植入[7];另有MISTRG(MC-SF, IL3, Sirpa, TPO, Rag2-/-IL2Rgc-/-)小鼠可支持较高水平的髓细胞发育,促进人单核细胞、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和巨噬细胞的分化,并促进NK细胞的发育[8]。由于上述动物体内仍然存在有少量鼠源性免疫细胞,通常在移植人源性细胞之前均需进行辐照,以达到清髓的效果[9]。而NBSGW(NOD,B6.SCIDIl2rγ-/-KitW41/W41)小鼠由于携带c-Kit基因突变,可支持无辐照小鼠造血干细胞的移植[9-10]。
依据人免疫系统重建的方法,将免疫系统人源化小鼠模型分为三大类:Hu-BLT(humanized-bone marrow,liver,thymus)小鼠模型、Hu-HSCs(humanized-hematopoietic stem cells)和Hu-PBL(humanized-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小鼠模型(表1)。
1.1 Hu-BLT小鼠模型
该模型是将免疫缺陷小鼠经亚致死剂量辐照处理后,肾包膜下合并移植人胎胸腺和胎肝组织,同时再经尾静脉注射分离自同一个体的胎肝或骨髓来源的造血干细胞[11]。Hu-BLT小鼠体内能检测到完整的T细胞、B细胞、NK细胞、单核细胞、DC、巨噬细胞等多种人免疫细胞,并可产生人源性的适应性免疫应答,是人源免疫系统重建最完善的小鼠模型[12]。经流式细胞术检测,Hu-BLT模型中可表达稳定的人CD45+细胞,其在外周血细胞的比例约为30% ~ 80%。而CD45+细胞比例超过25%标志着Hu-BLT模型构建成功[13]。

表1 不同免疫系统人源化小鼠模型的特点
该模型的重要特征是能产生人类粘膜免疫系统,因此可以应用于HIV[14]、EDV[15]等粘膜感染机制模型、造血系统及肿瘤免疫治疗的研究。但其供体样本难以获得,而且由于人胸腺组织中的T细胞对小鼠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仍然有高的亲和力,因此Hu-BLT模型可能在植入20周后出现移植物抗宿主反应(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GVHD)。而有研究报道将C57BL/6小鼠的Rag2、IL-2Yc和CD47基因三重敲除后的TKO-BLT模型在植入人的免疫细胞后45周未发生GVHD迹象,且保持人免疫细胞的高度重建,显著优于现有的BLT模型[16]。
1.2 Hu-HSCs小鼠模型
Hu-HSCs模型是将新生或成年免疫缺陷小鼠经亚致死剂量辐照处理后,破坏小鼠自体骨髓造血功能,再将新鲜的人CD34+HSC(可来源于人的G-CSF动员的血液、骨髓、脐带血或胎儿肝等)在24 h内经尾静脉或者骨髓腔注射入免疫缺陷小鼠体内,使多系Hu-HSC发育成包括T细胞、B细胞、NK细胞、骨髓来源的抑制性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s)和其他谱系阴性细胞在内的免疫细胞[17]。通常在植入后第4周hCD45+T细胞可达25%~60%,外周血中人CD45+T细胞超过25%,标志Hu-HSC模型构建成功[18]。
该模型的优势在于其造血系统及免疫细胞是HSC在小鼠体内重新发育而来的,对小鼠宿主具有免疫耐受,通常不会发生GVHD,模型稳定期可长达10~12周[19],可应用于HIV[20]、EBV[21]等感染模型及造血系统发育的长期研究,在肿瘤免疫治疗研究中显示出巨大的应用前景。然而,在该模型中影响免疫细胞分化成熟的因素较多。如成年NSG小鼠体内植入HSC后,12周才能够在外周血中检测出人T细胞,且T细胞的数量相对较少,活性不高[22-24]。相反,将HSC植入新生NSG小鼠后,很容易产生人T细胞。另有研究证明,雌性NSG小鼠比雄性NSG小鼠更支持人HSC的植入[25-26]。
1.3 Hu-PBL小鼠模型
该模型是将免疫缺陷小鼠经亚致死剂量辐照处理后,将5×106~ 20×106个新鲜的人PBMCs经尾静脉或腹腔移植入小鼠体内,以实现血液和脾中50% ~ 80%的CD45+细胞的植入,通常第一周就可获得人CD3+T细胞,第四周可检测到人CD3+CD45+T细胞超过25%[22, 27]。
Hu-PBL小鼠是目前最简单、经济的人源化小鼠模型,以重建人的T细胞为主并保持其免疫功能。与CD34+HSC衍生T细胞相比,当免疫缺陷小鼠移植PBMC时,人T细胞增殖速度更快,可重建更高水平的人T细胞,是研究成熟效应T细胞的理想模型[22]。同时该模型中还可检测到少量的B细胞、髓系细胞或其他免疫细胞。但该模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由于人T细胞和小鼠免疫细胞之间的MHC不匹配而出现的致死性GVHD反应[28-29]。通常会在人PBMC注射后4~6周出现明显的GVHD症状,治疗观察窗口期短,使用受限[8, 27]。但此实验窗口期可以通过改造NSG(NDG、NPG等)小鼠,使其缺失MHC-I或II基因而得到延长[30]。此外,降低PBMCs中CD4+T细胞的比例也可显著减缓GVHD反应[31]。然而,CD4+T辅助细胞亚群比例的降低会损害细胞免疫,这可能会降低该类小鼠模型的适用性。
2 Hu-PDX模型
基于临床肿瘤标本建立的PDX(patient-derived xenograft)模型较好的保持了原发瘤的特征,但由于其缺乏人体免疫系统,无法针对特定患者的肿瘤细胞或组织开展免疫治疗研究。在免疫系统人源化小鼠体内移植入特定患者的肿瘤组织而建立的模型称为Hu-PDX(humanized patient-derived xenograft)模型,因其可模拟人体中肿瘤细胞与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抗肿瘤免疫治疗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Hu-PDX模型的构建与肿瘤移植的时间和人源化的方法密切相关。如Hu-PBL小鼠模型免疫重建维持时间较短,因此Hu-PBL-PDX模型的构建通常是先移植患者的肿瘤组织,待肿瘤体积达到约120~180 mm3时,对小鼠进行亚致死性辐照后,再经尾静脉注射人PBMC;Hu-HSC小鼠模型由于GVHD反应较弱,免疫重建维持时间约为10~12周,所以Hu-HSC-PDX模型通常是先将人CD34+HSC移植入经亚致死性辐照处理的免疫缺陷小鼠体内,当小鼠体内人CD3+CD45+比例超过15%(通常为移植后12周),再移植入患者肿瘤组织[22]。该模型构建成功的标志是在肿瘤组织中能够检测到人的免疫细胞和细胞因子等。
目前,Hu-PDX模型已应用于多种类型的肿瘤研究中,如非小细胞肺癌、结直肠癌、肾癌、肝癌、三阴性乳腺癌、黑色素瘤等[22, 31-34]。这些模型给肿瘤细胞提供与人体更相似的生长微环境,可以从组织病理学、基因表达、基因突变、炎症和治疗反应等方面真实准确的反映了临床肿瘤患者的表现,在肿瘤的发生、发展和转移机制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尤其在肿瘤免疫治疗研究方面,是理想的肿瘤模型。
3 人源化小鼠模型在肿瘤免疫治疗研究中的应用
肿瘤免疫治疗是通过激活机体抗肿瘤免疫反应或阻断肿瘤免疫逃逸,以控制和杀伤肿瘤。主要包括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s,CAR-T)、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以及与其他免疫疗法相结合的综合疗法等,而人源化小鼠模型是开展上述免疫治疗研究的理想的临床前模型。表2是目前已报道的部分人源化小鼠模型在不同类型肿瘤免疫治疗研究中的应用。
3.1 CAR-T治疗中的应用
CAR-T细胞免疫疗法原理在于经嵌合抗原受体修饰的T细胞,可以特异性地识别肿瘤相关抗原,使效应T细胞的靶向性和杀伤活性均较常规的免疫细胞高,从而发挥抗癌作用。目前CAR-T疗法临床上主要应用于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等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治疗[35-36],而在实体肿瘤的治疗中应用较少。人源化小鼠模型目前已应用于各种CAR设计的抗肿瘤疗效评估。Abate-Daga等[37]利用胰腺癌Hu-PBMC-PDX模型,开发了一种针对前列腺干细胞抗原(PSCA)的CAR,为将PSCA作为基于CAR的胰腺癌免疫治疗的靶抗原提供了证据;另有研究报道证明在卵巢癌Hu-PBMC-PDX模型上,CD27能够共刺激CAR-T细胞以获得更高的持久性和抗肿瘤活性[38]。显然,Hu-PDX模型为评估CAR-T疗法在实体肿瘤中的有效性提供了新的方法。
3.2 肿瘤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研究中的应用
肿瘤细胞可以通过多种途径逃避免疫系统的识别及杀伤。通过激活肿瘤微环境中特定的抑制性信号通路是肿瘤逃避免疫监视的途径之一,这些抑制信号被称为免疫检查点。目前发现的免疫检查点包括: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ytoxic T 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4,CTLA-4)、程序性死亡受体-1/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1/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 PD-1/PD-L1)、T细胞免疫球蛋白-3(T cell immunoglobulin-3, TIM-3)、T细胞免疫球蛋白ITIM结构域(T cell immunoglobulin and ITIM domains, TIGIT)、淋巴细胞活化基因-3(lymphocyte activation gene-3, LAG-3)及唾液酸结合免疫球蛋白样凝集素-15(sialic acid-binding Ig-like lectin-15, Siglec-15)等。其中CTLA-4与PD-1/PD-L1信号通路的研究获得了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目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临床研究,但由于缺乏大量的动物模型进行筛选和验证,所以相关结果并不理想。许多研究已证实人源化小鼠模型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研究中的独特优势。例如,Kenneth等[39]应用EBV相关淋巴瘤的Hu-PBL-SCID小鼠模型来筛选一组抗人CTLA-4单克隆抗体(MAb),结果显示不同单抗在小鼠模型中活化人T细胞的效能具有显著的差异。Lin等[22]构建了Hu-PBL-NSI和Hu-HSPCs-NSI(humanized-hematopoietic stem and progenitor cells-NSI)两种人源化小鼠的非小细胞肺癌PDX模型,并评估了针对PD-L1/PD-1免疫检查点靶向治疗的效果。研究发现与Hu-HSPCs-NSI小鼠相比,Hu-PBL-NSI人源化小鼠模型在免疫靶向治疗中显示出更高的抗肿瘤效果。此外,Roberto等[33]成功构建了三阴性乳腺癌的Hu-CD34-HSC-PDX模型,并评估了抗PD-1抗体治疗的有效性。研究结果显示,抗PD-1抗体治疗可显著抑制肿瘤的生长并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尽管部分人源化小鼠模型在免疫治疗中取得了成功,但在一项针对非小细胞肺癌Hu-PDX模型的研究中发现,不同来源的CD34+HSPC供体重建的人源化小鼠针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反应不尽相同,这与临床上患者对抗PD-1治疗的不同反应率是一致的。并且在人源化小鼠模型中反应性的差异可能与供体的T细胞谱系有关[18]。因此,人源化小鼠模型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应用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改进。
3.3 免疫综合治疗中的应用
逆转T细胞抑制信号的药物(例如PD-1/PD-L1疗法)的成功应用使人们对癌症免疫疗法充满了信心,但单药治疗效果有限,联合免疫治疗可能具有良好的抗肿瘤效能。2019年3 月美国FDA批准了PD-L1抑制剂Atezolizumab联合依托泊苷、卡铂用于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一线治疗,这标志着免疫治疗进入联合治疗为主的2.0时代。人源化小鼠模型用于评价CAR-T细胞与抗体靶向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PD-L1和CTLA-4)联合治疗的效果[40]。Suarez等[41]在转移性透明细胞肾细胞癌的人源化小鼠模型中使用CAR-T细胞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进行联合治疗。这些靶向人抗碳酸酐酶的CAR-T细胞还可分泌人抗PD-L1抗体,以克服PD-1和PD-L1相互作用介导的检查点抑制。与仅使用CAR-T细胞处理组相比,联合免疫检查点阻断方法可有效增强抗肿瘤效力。Leonid等[42]使用胸膜间皮瘤的原位小鼠模型研究PD-1介导的T细胞衰竭与间皮素靶向的CAR-T细胞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通过阻断PD-1/PD-L1可以增强CAR-T细胞的疗效。另有研究报道,在EBV相关淋巴瘤的Hu-HSC-NSG模型中,PD-1和CTLA-4阻断抗体的联合治疗可显著抑制EBV诱导的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的生长,并且两种抗体联合用药的抗肿瘤效果优于单药治疗[43]。此外,在人结肠癌组织植入Hu-PBL-BRG小鼠模型中,利用抗人CD137和抗PD-1单抗联合作用具有显著抑制肿瘤生长的效果;研究者在利用人胃癌组织和自体PBMC构建的Hu-PDX模型中获得了相同的结果[31]。

表2 人源化小鼠模型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应用
4 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癌症免疫治疗的新时代,人源化小鼠模型是评估新疗法、研究组合疗法以及指导个性化免疫治疗的有效工具。但该模型的构建目前仍存在诸多缺陷,如免疫细胞与移植瘤之间的组织相容性问题、小鼠残留的先天免疫系统影响人免疫细胞的植入、缺乏物种特异性的生长因子促进某些免疫亚群的成熟等,这些因素导致人源化小鼠模型不能完全满足肿瘤—免疫研究的需求。为此,正在研发的下一代人源化小鼠,包括MHC基因人源化的小鼠[44]、抑制鼠源免疫细胞的人信号调节蛋白α(signal regulatory protein alpha, SIRPα)转基因小鼠[45-46]以及转入人源细胞因子如IL-2、IL-3、GM-CSF、SCF等的小鼠[47-48],有望通过解决这些问题以实现更高水平及更全亚群的人免疫细胞的植入。
人源化小鼠模型在肿瘤免疫治疗研究中的进一步应用有望解决临床治疗中存在的问题。如寻找明确的生物标志物以解决临床反应率低的问题、探索肿瘤免疫治疗与传统治疗方法相结合的联合疗法以解决免疫相关不良反应问题等。总之,人源化小鼠模型的不断优化以及其在肿瘤免疫治疗领域应用的扩大,必将为癌症免疫学和个性化医学提供前所未有的研究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