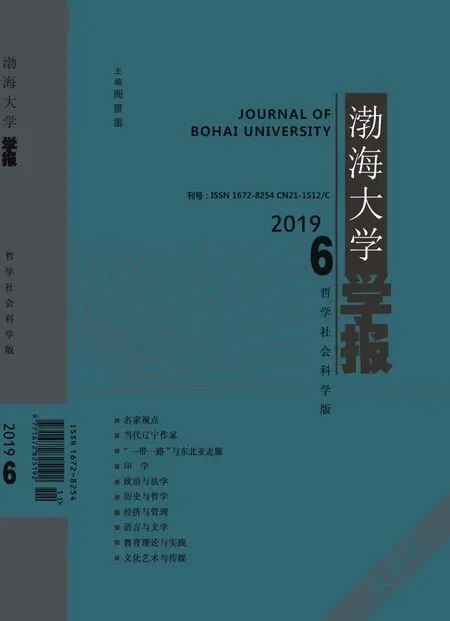仁礼合一视域下的孔子生死观
姚海涛(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山东青岛266106)
生存与死亡是人始终要面对的永恒命题,而要正确看待这一命题无疑需要审慎的理性、缜密的思维与旷达的智慧。古圣先贤对于这一命题多有深刻的洞见与卓识。先秦儒家的三位大师孔子、孟子、荀子均为高寿之人,各享73岁、84 岁、90 余岁高龄。他们对于生命有深刻体悟,且多有精彩论说。孔子将仁礼合一理论贯彻到其思想的方方面面,以此理论去观照其生死观,若合符节。仁礼合一既反映了孔子打通内(仁)外(礼),贯通人我,将人性根据与制度理据、自律与他律合一的道德理想,也表现了其圆融无碍的生命境界与人文关怀。孟子继承了孔子一体之仁,发展为仁政之说;荀子则继承了孔子礼的面向,发展为隆礼之说。在生死命题上亦当如是观,孟子注重“成仁”之生死,而荀子强调“隆礼”以养生送死,故先秦儒家生死观也只有回到孔子才能得到更恰当的理解,因为孔子生死之说奠定了儒家生死观的基本面向,对于传统社会生死观的形成具有奠基性作用。
一、对生命尊严与价值的肯认:生生之谓仁
尊崇好生之德或曰生生之德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古老传统。如《尚书·大禹谟》:“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1]《周易》有云:“生生之谓易”[2]“天地之大德曰生”[2](246)。梁漱溟先生也曾指出:“这个‘生’字是最重要的观念,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孔子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的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3]将生与生命、生意、生机、生育等多重意蕴联结起来共同构成了孔子生生之谓仁的思理内涵。透过孔子一生轨迹可见其对生活意义的探寻——以斯文自任,刚健有为、积极用世、自强不息、知行合一、内圣与外王并重。从孔子的言行中,我们无疑可以清晰地看到孔子将仁与生的汇通、联系、互动,其特别重视仁对生的架构、范导、平衡作用。天虽有创生万物(包括人在内)的生成作用,但要谈到护持生命,使其畅达无碍,达成各是其所的价值,就需要仁的全体大用。
人类是如何产生的,是生死观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一定意义上,这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人类学问题,更是一个涉及终极关怀的哲学问题。孔子认为,“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4]人禀受天地之精华,是天地基本品质的体现,是阴阳交合、塑造的产物,是鬼神精灵之荟萃。他进一步说,“故人者,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端,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4](374)人是天地的核心,是天地万物之统领,依赖美味的食物、和谐的音乐、华彩的衣物而生存。正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4](373)关于生死,他说:“象形而发,谓之生;化穷数尽,谓之死。”[4](308)通过阴阳之妙化,根据形体而产生的就是生;而穷尽造化与天数,则称之为死。这些关于人产生的各种界说,实质上肯定了人存在所需要的基本物质条件与延续繁衍方面的基本需求。
孔子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在此基础上力图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殊性、紧要处,透显、超拔出来以提振人超乎万物的地位,挺立起人的主体人格,由是构建起人效法天地的超越根据,充分彰显出了儒家天人合一的基本观念①。
此外,孔子将生命区分为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围绕个体生命,他从天人关系的自然视角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视角两个层面展开。他看到,个体与群体构成了一对互相需要的矛盾关系,个体的生存无疑要建立在群体的基础之上。而如何协调、组织好人群社会就成为摆在统治者面前的重要问题。孔子认为,统治者应当效法古圣先王之施政,让广大人民受到恩泽。所以他说:“舜之为君也,其政好生而恶杀,其任授贤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静虚,化若四时而变物,是以四海承风,畅于异类,凤翔麟至,鸟兽驯德,无他也,好生故也。”[4](109)古圣贤舜帝为政时爱惜生灵,选能任贤,德行如天地运转一样虚静无求,教化人民如同四时交替一样自然无迹。所以舜的教化能够通达于四方异族,德化顺从者实现了由人而物的全面覆盖。人的终极化存在关乎个体与群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角色伦理定位、制度平衡与人文协调等诸多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仁之于人生存的重要性得到最充分的彰显——正所谓“生生之谓仁”。
《论语》中记载的孔子遭遇“厩焚”这一突发事件的举动,如果以仁礼合一生死观的观察框架去确立理解视野,重现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无疑对于深刻理解孔子及其生死观大有裨益。事情是这样的:“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5]②《家语》中云:“孔子为大司寇,国厩焚。子退朝而之火所,乡人有自为火来者,则拜之,士一,大夫再。”[4](514)两处记载的“厩焚”事件,当为一事。不过,其所体现的孔子思想可能因记录者的不同而各有侧重。这一事件涉及孔子对人与马之死的价值权衡,也涉及对慰问者的礼仪化对待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仁与礼之两面。
《论语》中凸显的是“问人不问马”知仁的方面,所提点的是孔子仁学之下贯于人,体现孔子对人的生命价值之独特性、共同性与崇高性的肯认。仁之一字,从字形就可以看到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含义。如孔子还提到过“仁者乐山”“仁者静”“仁者寿”等大量以“仁”护持生命的道理。《家语》中凸显的则是孔子“拜之,士一,大夫再”知礼的方面,对那些自发赶到“厩焚”现场救火者根据不同的社会地位以合宜之礼拜之。这是孔子礼之学说的下贯,体现孔子对个体尊严价值之阶层性、差异性与特殊性的肯认、保持与平衡。“厩焚”事件在《论语》与《家语》中的不同记录,将其合并观之,不难看出其各自体现了仁礼合一思想之一面,共同诠释了孔子仁礼合一的思想主张。
二、对死亡的超越:朝闻夕死、事人事鬼与大哉乎死
生与死构成一对矛盾,有生必有死。如何面对死亡,也成为孔子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孔子那里,死亡不仅仅是一个事实或事件,更重要的是其彰显出一种存在意义。死可以被视作个体生存价值评判的盖棺论定事件,也可以视为让个体生存走向群体、融入群体,并在群体中彰显价值与意义的事件。基于此,人获得了进入历史之维的契机。
(一)面对死亡:朝闻夕死
自古皆有死。孔子见到的死亡可谓多矣,其中有普通的百姓,也有高高在上的君王,更有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生死寓价值,《论语·子张》中子贡对孔子“其生也荣,其死也哀”[5](500)的评价更是表达了孔子之不可及处,也表达出了孔子对于生死的体悟。
儒家最重视血缘关系,注重亲子关系,而孔子晚年却遭遇了亲人去世的接连打击——独子孔鲤去世,最喜爱的弟子颜回早夭以及子路惨死③。
生死有大道。生与死之间体现的是儒者领悟的“道”之大境界。孔子曾言:“朝闻道,夕死可矣。”[5](91)此语通常理解为孔子对“道”追求之迫切心情。但还可以理解为,道虽至大、至高,但其实即在朝夕之间,不离日用伦常。一朝一夕之间,即是道之所在。在孔子看来,人生就是一场对道的追求之旅;领悟之后,即使死去也会别无他求,更无挂碍。生与死本如一条河流之上游与下游一贯而下,只有将上游与下游合观,才能见到整条河流之样貌。也就是说,生与死只有在对立中才能把握其真意。例如张祥龙先生认为,儒家是以生存的极致来进入死亡、领会死亡,儒家的超越性体现在代际间家族存亡的时间性里面。所表达的是现行的时间序列只是提供给我们一个实际交往的工具框架,而与生活的意义无关。而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时间让人有了一个从本质上比其他生命更深广可塑、可回旋出新的联系样式的意义生成结构[6]。孔子的“朝闻夕死”的讲法一下子进入了意义机制的中心,领会到它的运作方式,人生意义尽在其中,即使死也了无遗憾。
《礼记》《家语》《史记·孔子世家》中共同记载的孔子临死前的诗化述怀是悲怆感的莅临,让死亡有了“时机化”的韵味,更有命运感的凸显以及悲剧感的蕴具。孔子之死,是一个文化史的大事件。他临终之前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4](461)其所传达的并不是个人对死亡的恐惧与忧虑,而是对春秋末年礼崩乐坏混乱时局以及儒家道统学脉的忧虑,以及对“明王不兴,莫能宗余”[4](463)的无奈与悲怆。孔子之死已经超越了个人的死亡,进入了意义回旋的空间,已然成为一个时代结束的象征,成为儒家学派分裂的开始,成为一个标志性文化符号的确立。
(二)事人与事鬼:仁爱与丧祭之礼的合一
死亡之事,人所不可免。但死后是否有另一超验的彼岸世界?孔子似不喜言。如《论语·先进》中的“季路问事鬼神”事。孔子的回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5](285)子路又问死,孔子的回答则是“未知生,焉知死。”[5](285)有学者认为,鬼神及死后事难明,语之无益。或认为孔子只论人生而不谈死后鬼神事,这是儒家对生的重视及对死的存而不论式回避。但为什么儒家所论之礼大部分为丧礼与祭祀之礼呢?这至少说明儒家非常重视死亡所带来的一系列事件之意义。钱穆先生的解释是:“死生本属一体,蚩蚩而生,则必昧昧而死。生而茫然,则必死而惘然。生能俯仰无愧,死则浩然天壤。今日浩然天壤之鬼神,皆即往日俯仰无愧之生人。苟能知生人之理,推以及于死后之鬼神,则由于死生人鬼之一体,而可推见天人之一体矣。孔子之教,能近取譬”[5](285-286)。
在《家语》中宰我问孔子鬼神之事,孔子答道:“人生有气有魄。气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归土,此谓鬼;魂气归天,此谓神,合鬼神而享之,教之至也。”[4](216)他将人分为“气”与“魄”两种存在形式,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气”与魂“魄”,二者分别是生与死、人与鬼充盈的外在表现形式。人生死本为一体,相互依存与对待,所以不知生就不知死。当然也可以说,知道了生也就明了死。人生之时,立于社会人群之中,死后归入土中,叫作鬼。鬼者,归也。魂气归于天上叫作神。将鬼神合起来祭祀,体现的是教化之极致。
在孔子那里,丧祭之礼蕴示着仁爱精神,同时与孝密切相联。他说:“不孝者,生于不仁。不仁者,生于丧祭之无礼也。明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4](346)孔子将仁爱与孝相联系,彰明丧祭之礼是为了教化百姓懂仁爱精神。修明丧祭之礼,百姓自然就懂得孝了。将生前之孝与死后丧祭之礼打通为一体,也就是将仁与礼合而为一了。
如果将《孟子》中曾称引“始作俑者,其无后乎”[7]的孔子愤激骂詈之语合并观之,孔子仁礼合一的生死观就更加显明。与“始作俑者”相联系的是,《家语·曲礼公西赤问》中子游与孔子也有一段相关对话:“子游问于孔子曰:‘葬者涂车刍灵,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是无益于丧。’孔子曰:‘为刍灵者善矣,为偶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4](573)子游在这里请教孔子随葬的泥做的车,草扎的马,自古就有了,然而如今有人制作土、木偶像来陪葬,这样做对丧事没有什么好处。孔子认为,为刍灵者与为偶者的区别在于仁与不仁。扎草人、草马的人“善”(仁),而制作土偶、木偶的人却“不仁”,属于动机不纯、居心不良。用制作如此惟妙惟肖的偶像陪葬,这不是接近于用真人来陪葬吗?将这两次论述放在孔子仁礼合一的视域中就能得到更适切的诠释。以俑殉葬尚且不可,更何况对人进行戕害式殉葬则更不可。其共同凸显的是孔子对暴殄天物的愤慨与对生命尊严和价值的肯认,更是其仁爱精神的体现。
再如樊迟问知之时,孔子的回答是“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5](157)此句若联系到《家语》中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就能更透彻地理解。孔子对死存而不论、悬置搁空的始末缘由是什么?子贡问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将无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将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无知,将恐不孝之子弃其亲而不葬。赐不欲知死者有知与无知,非今之急,后自知之。”[4](92)孔子对鬼神之事的难言并非其不能言,其不言自有不言之道理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言与不言的悖论:如果认定死之有知,孝子顺孙会伤害自己的生命以葬送死者;如果死之无知,又担心不孝顺的子孙遗弃亲人而不埋葬。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悬置,让其处于知与无知之间,这是某种意义上能够维系世道人心的“中庸之道”。正因如此,故有“修身以俟死”之说。
所以,我们看到现存的由儒家后学编撰的《仪礼》一书共十七篇,而其中关于丧祭之礼者多达七篇。对丧祭的重视影响到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也可见诸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时至今日,传统节日中与丧祭相关者也比较多,如清明节、端午节等。此外,孔子“三畏之说”中有“畏天命”,让敬畏感、神秘感的终极体验成为丧祭之礼的内在保证。
可见,孔子的生死观绝没有标准答案,绝不世俗化也并非远离人间烟火。在世间而又离世间的时机化情境构成人类生活的真实场域。于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就变得可以理解了,“杀身成仁”也就有了注脚。只有真正的智者才能“知幽明之故,达生死存亡之说”[4](275)。
(三)大哉乎死:息与休、君子与小人
孔子从来不“方人”,有“夫我则不暇”[5](377)的说辞。孔子曾经批评过子贡“方人”,同时对人的评价持守着“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的审慎而理性的客观态度。他也不会轻易许人以“仁”。《家语·困誓》中记载了子贡这名优等生的“厌学”情绪。 当子贡“倦于学,困于道”之时,希望能够“息于事君”。孔子引《诗》对其进行思想开导。对事君、事亲、息于妻子、息于朋友、息于耕这样五类事情之难,进行了系统的解说,人只要活着就必须不断地学习。于是子贡喟然叹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4](263)这一事件在《荀子·大略》中也有记录,但不如《家语》所载详尽。王先谦解释说,言人不可苟生,亦不可徒死也。这样就让死这一人生最后的事件有了价值理性意义与历史评价意义。
关于小人、君子之论,孔子多有探讨。如《论语》中的“喻于义”与“喻于利”之分,“周而不比”与“比而不周”之别,但这些探讨都是基于君子与小人生的意义层面,而对于其死却未涉及。而在《礼记·檀弓》中则提出,“君子曰终,小人曰死”[8]。可见,小人与君子之死亦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与他们的“生”一样也产生了等级、位阶之别。死亡成为“盖棺论定”式意义评价所在。
于是孔子所说的“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5](30)成为了生死一以贯之礼。礼彻生彻死,生死存亡之事以礼贯之。君子与小人之生不同,死亦有异。无疑,君子之“死”自具有更高的意义和价值。而这种更高价值体现的是君子之“仁”贯穿于作为超越的一体之“生死”之中。其生何以不同?因为仁也。君子以求仁为自己的追求目标,故其生也仁。君子之日常便是仁礼合一的具体而微之呈现。其死何以不同?体现于礼也。君子死后的丧葬与祭祀之礼自然与小人不同。
生死之间既是间断的,也是连续的,是间断性与连续性的统一。死作为礼之重要载体性事件,也与死者之“仁”密切结合在一处。丧葬之礼、祭祀之礼,既是血缘人伦关系的凸显,同时也与死者生前之“仁”否联系在一起。此外,在行丧祭之礼之时,也会使参与者通过复杂之礼“见到”生与死一体无隔之意义。此之于生者,对于消除心灵恐惧、获得灵魂安宁、得到心灵慰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孔子在经历过众亲死亡之后仍能保持生的韧性,其生命意义得到澄澈。所以孔子对生极为重视的同时,对死后的丧祭也同样重视。他有“祭如在”的说法,也有“生事尽力,死事尽思”[4](87)的说法,极为重视父母亲人的丧礼及祭祀之礼。但他又指出,“不以死伤生,丧不过三年”[4](314),指出丧祭的必然性限度。“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4](381)大顺是要奉养生者,丧葬死者,作为祭祀鬼神的原则,而不遗漏。“明于顺,然后乃能守危。”[4](381)死后之丧祭规格与个人生前的道德功业、社会地位有直接对应的关系。人于死后进入历史的契机到来,君子与小人的不同由生而死均得以朗显。
综上所述,孔子以仁礼合一的理论视域对“死生亦大”这一重大而严肃的人生主题的观照,既体现出了其圆融的境界与大儒的气象,也体现出了其对中华文化深层结构及其稳定态进行塑造的高度文化自觉。孔子一方面以“生生之谓仁”彰显出对生命尊严与价值的显性评价;另一方面他又以杀身成仁、丧葬以礼保留了对死亡的敬畏与超越,透显出对生命价值的隐性揭示。以上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孔子对人的终极人文关怀与理论旨归。这对于正确理解孔子的仁与礼具有理论意义,同时对于每一个生命个体正确理解生与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①值得注意的是,孔门文学科的优秀弟子子夏关于人之生的致思取向与孔子完全不同。他已经将生物进行了羽虫、毛虫、甲虫、鳞虫、倮虫这样细致的分类,并隐约意识到了生物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路径,模糊地触摸到了人真正的生物学来源。他说:“倮虫三百有六十,而人为之长。此乾坤之美也,殊形异类之数。”他指出,人类的出现是天地精妙之所在,变化的背后隐含着不易之数理。子夏常言此类知识,孔子未曾反驳,反抱以包容甚至赞赏的态度,认为这是“各其所能”。
②“厩焚”一事,钱穆先生在解释“厩”时指出,养马之处。或说国厩,或说是孔子家私厩。到底是国厩还是私厩,如果结合《家语》中关于此事件的记录就一目了然。
③如颜渊之死,子哭之恸。如果对照师徒二人在“子畏于匡,颜渊后”中一语成谶式的精彩对话,这种悲怆感就愈加强烈。就让历史定格在这一刻,方能见出孔子师徒间的情分,也方能见到孔子晚年的绝望与真实。子曰:“吾以女(汝)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好学的颜渊从某种意义上也已经领会到了孔子以道自任的博大胸怀,所以他与老师开了一个“玩笑”。“何敢死”体现的是颜渊对孔子之道传承责任的认知,可见二人之间对于“斯文”传承的心灵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