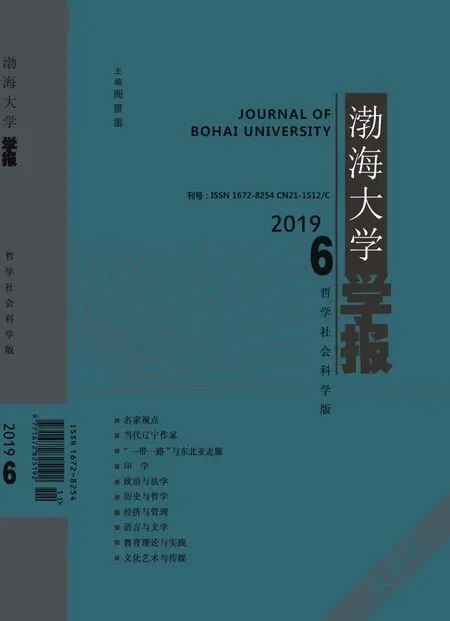小说创作是建构一个“寻找自我”的路径
——与作家苏兰朵的对话
林 喦 苏兰朵(.渤海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辽宁 锦州03;.辽宁省作家协会,辽宁沈阳004)
如果说,作家是生活的探秘者,那么文学评论家就是作家的探秘者。当然,这个探秘者与娱乐记者中“狗仔队”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评论家作为作家的探秘者更应该关注作家的作品。如果想要比较全面地掌握作家的作品,对作家创作的了解应该是很重要的内容。全面了解作家、了解作家的创作,对深入了解作品是有益处的,这才是真正的“大文本”观。从这个意义上讲,评论家也就有了探秘者的意味了。同样,对于作家而言,作家也是生活的探秘者。作家探秘生活,基于两个要素:一是作家要深入生活之中,对于这个观点,很多人有质疑,作家本身不就是生活在生活之中吗?为何还要深入生活呢?这里需要解释的,我们强调的深入生活是有一定语境意义的深入生活,是作为“作家”身份的“作家/艺术家”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去,深入到农村、工人等火热的基层现实生活中。当然,这个“深入”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延伸到每一个生活领域,即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体验着生活真实。二是要熟悉生活,不能是闭门造车来思考的生活探秘者。
林 喦:从某种意义上讲,你的每一篇小说好像都没有社会大背景,但社会大背景又无处不在。大多数小说的社会背景大都隐含在了小说人物日常周而复始的琐碎生活之中,在所谓“油腻”生活中寻找“人”存在的意义。探寻着“人”生存的意义以及在快节奏的现实生活中不断探寻人们精神迷惘与内心空虚的内因与外因,进而形成了属于“苏兰朵式”的“寻找主题”。如果说,此方面是现代都市生活存在的一个“问题”的话,那么,苏兰朵既属于该“问题”的发现者,也属于其自身面对生活的“迷惘者”。当然,我相信,作为作家的苏兰朵始终是比较清楚的思考者。你把你所发现的“社会问题”诉诸笔端。所以,我把你的大部分作品,尤其是小说集《寻找艾薇儿》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当作“社会问题小说”来归类的。
苏兰朵:第一次有人这样概括我的作品。如果和女性作家相比,我对社会问题关注的可能相对多一些。有的评论家说,从我的小说里看不出来作者的性别,可能也和这个原因有关吧。不过从我自己创作的角度讲,构思一个作品一般都不是从事件或社会问题入手的,而是从人物出发的。一个放不下的人物是我开始构思一个小说、展开叙事的起点。我比较愿意把我的人物放在一个困局中。破除困局的过程,就是小说衍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性得以释放,自然,社会问题也会得以展现。
林 喦:简单的一句话说出了你创作思维、方法和技巧了。我觉得你的小说基于了“社会问题”,如你所说的把人物设计在“困局”中,有了“困局”就要想方设法“破局”,无形之中就有了一个“寻找”的味道。“寻找”在世界文学史中也是具有“母题性”的。换句话说,“寻找”也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探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在你的小说中,有些问题是很难寻求到一种很“清晰”的答案,或者说清晰的方向感。比如短篇小说《阳台》、长篇小说《声色》,甚至有一些“灰”,是这样吗?
苏兰朵:我其实是个悲观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我的内在气质是偏抑郁型的。你在我的很多小说里可以看到我和这种抑郁在博弈。写作本身可能就是我和抑郁博弈的方式。迄今为止,是唯一有效的方式。我不否认我的很多作品有些“灰”,这种底色是掩饰不住的。但在这种底色之上,我觉得我的多数作品还是很有力量的,因为我必须战胜那些灰的东西,才能活下去。这么多年来,我喜欢的思想者始终只有三个人:弗洛伊德、叔本华和加缪。叔本华印证了我对世界的看法,弗洛伊德解释了“我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是的,我从童年来,并且一生都走不出去。而加缪给了我绝望之后的力量。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无意义的,然而西绪福斯还是不停地将滚落的巨石推到山顶,而获取另一种尊严和意义。我想,写作这件事就是我对抗无聊人生的那块石头。
林 喦:在西方世界,西绪福斯的故事由来久矣,他一直被当作勇气和毅力的象征。他有毅力、有勇气,还有一份极难得的清醒,他知道苦难没有尽头,但他不气馁,也不悲观,更不怨天尤人。西绪福斯是悲剧的英雄,成为与命运抗击的人类的象征。这个神话故事是颇有韵味的。简单地讲,我们每一天周而复始地“活着”,在某一个角度讲可能都是在做着西绪福斯推石头上山的事情。(笑)
你的小说结尾、结局总是那样迅速有力、回味绵长,正所谓: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比如在《寻找艾薇儿》《初恋》《白裙子》等小说中,你是想刻意保持这种风格,还是小说的情节逻辑发展的必然?
苏兰朵:谢谢你注意到这一点,小说的结尾确实是我很在意的一部分。对于我来说,在构思阶段,如果没有想好结尾的明确方向,我是不会动手写的。比如《寻找艾薇儿》,其实是先有结尾的。是这个结尾迷住了我,我是从这个结尾入手,倒推出这个故事来的。《初恋》也是一样,小鹏给秀儿打电话,想上楼来给她服务;秀儿辨别出他的声音,然后惊恐,接着思绪万千。这是在我构思阶段就想好的结局。我明确地知道这个结局是最有力量的,没有别的可以代替。所以,动笔之后,没有丝毫犹豫。我确实是在构思阶段想得比较细致的写作者,我会从头到尾把人物按照逻辑想通透,否则是不敢下笔的。边想边写的时候也有,但往往作品完成之后,都存在着很随意的问题,缺乏力量感,有的干脆就偏离既定轨道,写废了。
林 喦:你好像很在意小说的力量感,这是你追求的小说风格吗?
苏兰朵:也没有刻意的追求,作为阅读者,我比较喜欢有力量感的作品,所以可能我的审美倾向如此。我喜欢有内在张力,复杂、厚重的小说。可能长篇小说在堆积和铺垫这种力量感上会做得更好,短篇小说因为容量小,处理不好有时候会显得刻意。
林 喦:好,说到长篇和短篇的问题了。世界文学家中以短篇小说竖置文坛的比比皆是,比如创作《变色龙》《套中人》《苦恼》《万卡》《第六病室》的契诃夫;创作《羊脂球》《项链》的莫泊桑;创作《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的欧·亨利,中国的鲁迅也是短篇小说家,《三言二拍》《聊斋志异》也是短篇小说集。当然,你的短篇小说也形成了属于你的文学气象。但是,在大多数人的眼里,短篇小说的价值和意义远远不如长篇,这种“文学现象”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你怎么看?
苏兰朵:如果仅就文学现象来说,我认为两者的意义和价值不分伯仲。经典的短篇小说和长篇一样,都可以对人类产生不灭的影响。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叉的花园》、卡夫卡的《变形记》,还有你提到的契诃夫的《万卡》《套中人》,等等。如果从我个人的创作角度来讲,我是觉得我并不很擅长写短篇,我觉得短篇很难写。迄今为止,我最满意的短篇是《暗痕》。我正在往长写我的小说,我觉得长篇小说能够更多地实现我的文学理想。我对小说的理解,我的审美和价值观,可能需要长篇的容量来实现。不过到目前为止,我只写过一个长篇,我想会有下一部,下两部的……
林 喦:我倒觉得你还是比较钟情于短篇的,就像你把长篇小说《声色》中比较有特点的部分裁成短篇一样。从技巧上讲,这也是创作的一种智慧吧?(笑)
苏兰朵:哈哈,被你看出来了。这一篇其实是偷懒的表现。有一段时间约稿特别多,实在忙不过来,这是其一;其二是《声色》写好之后没有在杂志发表过,直接进入了出版环节,面向了图书市场的读者,杂志的读者没有读过这部小说让我觉得有点遗憾,于是就选取了其中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发在了杂志上,也算对杂志这部分读者的一个抛砖引玉吧,还是有私心的。(笑)
林 喦:你的小说,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现实感,少有过去的影子的留存,也没有对未来期待的介入,感觉就是现在发生的事、身边发生的事。作品中,没有明显的对过去的眷念和对未来的期待。为什么要写得这样克制?或者说是如何实现这种克制的,比如在《初恋》《白裙子》等作品中?
苏兰朵:《初恋》和《白裙子》里其实是有过去的。我自己认为,我的小说里都有过去,过去的经历对当下产生影响,这是发生在我很多小说人物身上的事。比如《初恋》中的秀儿,正是因为对少女时代没有实现的初恋的留恋,才会在现实中选择了小鹏成为初恋对象的替代,这是对过去的一种补偿。再比如《白裙子》,这个小说名字就是对过去的缅怀。另外像《寻找艾薇儿》中,艾小姐和张三最高兴的交谈,就是谈论小时候。寻找艾薇儿,其实就是寻找曾经的纯真。而在《白马银枪》和《歌唱家》中,过去都是作为小说的主体存在的。我是弗洛伊德的信徒,所以是不会舍弃人物的过去的,因为过去是因,现在是果。现在面对的困境,都和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没有未来这一点你说对了。也不是想克制,就是我没有看到他们的未来。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我的人物从过去走到现在都很疲惫,人生一地鸡毛,乏善可陈。未来也没什么可期许的,无非是用生命自身的力量去战胜这些,坚强地活下去罢了。
林 喦:抛开你的人物,说说你自己,你觉得你的未来怎么样?(笑)
苏兰朵:你从我处理人物的方式,就能看到我对未来的态度。其实你说的“没有明显的对过去的眷念和对未来的期待”这句话用在我身上倒是很合适的。我是那种经常否定过去的人,所以也不太留恋过去。我很注重当下,觉得无论喜和忧,还是成功和失败,都属于昨天,今天总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明天总是不确定的。但是今天必须有吃苦耐劳的努力,否则就没有明天了。年轻的时候可能还对未来有很多期待,现在觉得越往前走,失去的越多。除了家人和自己会写小说这点本事之外,我觉得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不敢有什么期待了。写作也是一样,只在意当下正在创作的这个作品,至于结果如何,不再去想了。
林 喦:对了,你大学毕业后是在电台工作,因为我在大学里从事新闻专业的教学,培养的学生大多数都从事了媒体工作,所以从我工作的性质角度讲,我还是比较熟悉媒体工作环境和新闻从业人员的。当然,因为你在新闻业工作过,比我更身临其境,更熟悉那里的一切。这一点,从你的长篇小说《声色》中是可以看出来的。电台里的某一个小频道,其实也是一个简单而复杂的“小社会”。透过这个“小社会”又能连接“大社会”,也是社会人生百态的一个缩影和真实的写照。尤其体现出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的那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你觉得芸芸众生都是为“利”而生,为“利”而往吗?
苏兰朵: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圈子”的地方就有鄙视链。一群人聚在一起,无论初衷多么美好,最后都会变成争夺资源、话语权及优越感的利益同盟和竞争关系。你说“利”其实说少了,还应该加上“名”,是名与利。有些人是主动出击,像《声色》中的常翠珊,从婚姻到事业,非常入世,像个斗士一样去厮杀,眼里和心里只有自己的利益。她先是毫不犹豫地抢了别人的老公,当上了官太太;又在得知丈夫有了外遇之后,以此和丈夫谈交易,通过走上层路线,顺利地当上了电台的副总监。当然,她也有自己的痛苦,但是她并不需要同情,因为同情什么用处都没有。痛苦只会让她变得更加自私和狠毒。这样的人,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遇到那么一些,身上像打了鸡血一样,永远那么生机勃勃。我是那种生性特别被动的人,从前特别讨厌这种人。他们就像安宁生活中的飓风,以破坏道德和公平来进展着一切,然后让另一些人“顿悟”,从此步他们的后尘。我有过多次被这种人击败的经历,曾经不止一次问自己,要不要“顿悟”,而使自己的努力得到应有的回报?结果是有很多关口我过不去。我之所以在写作的路上越走越远,是因为我没有力气在人群中厮杀。我是人群中的失败者、落荒而逃者。我特别喜欢萨特的那句话,“他人即地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写作对我也是一种拯救,它让我成为作家,让我远离人群也有能力生存。当我接受了这种生活,我的心态变得很好,生活一下子简单了。现在我也没那么讨厌那种人了,像邓文迪那样的女人,有时候我还会心生一点佩服。神赋予了每种人一种生存的本领,只要你努力,都会有回报。只是诗和远方,依然是值得追求的。我会在自己的这部分人生里和作品中坚持这种价值观。
林 喦:《声色》属于第三者叙事,作者一定是站在一个全知视角的维度,但这里面的几个“电台频道”中的人物,哪一个是你,或者有你的影子呢,如同你曾经说过“文学只是我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当然,可以没有,作家创作作品,塑造人物可以不是自己。
苏兰朵:和那些愿意把自身经历写成小说的作家相比,我算是对自我暴露得比较少的。可能我在诗歌、散文这两种文体中的自我展示更加真实一些。《声色》中的每个人物我都非常熟悉,毕竟在电台工作了20 多年。这本书出版后,我当时电台的朋友和同事都看了,他们一致认为,每个人物都是很多人的融合体,常常是在一个人物身上,能看到很多真实的人的影子。如果只谈影子的话,可能安娜的身上有我的一点影子。
林 喦:如果说《寻找艾薇儿》和《声色》写的是市井人群中人的生活状态的话,那么小说《白熊》中几个短篇开始转向到了“科幻”。这个转换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在科技发展到了“智能化”时代。这个转化基于你怎样的思考?
苏兰朵:除了几篇科幻作品,我的小说几乎都是现实主义作品,特别贴近当下的生活。写多了,想有点变化。之所以尝试科幻,是因为在这样一种故事设置的基础上,写起来更加自由,能用比较简洁的篇幅表现我想表达的东西。同写实比起来,它更加抽象。对于一个写过诗歌的人来说,有时候特别不喜欢把优美的语言、饱满的情感和犀利的观点都淹没在烦琐的细节和写实里,那无异于一种漫长的消耗。好比将一次火箭旅行变成了徒步跋涉。当然徒步也有徒步的风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更像是跋山涉水、爬雪山过草地的徒步行走。我在另一些作品里也深爱着这种行走。只是偶尔,我想做一次飞翔的旅行。可能科幻题材的几篇小说就是在这些念头下写成的,像枯燥的写作生活中的一次度假和对自己的奖赏。无论别人如何评价它们,它们确实给了我快乐。其实我的几篇尝试,充其量也就是个软科幻。我自己更愿意把它们当成心理小说。
林 喦:在你的小说里描写众多人物关系时,脱离不了的一个话题——男女关系问题,这其中你也探讨着关于“爱情”和“情爱”的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中,应该有比较清晰的界限的,但你的作品中似乎模糊了?对于这两个问题,你是怎么看待的?
苏兰朵: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说的“爱情”精神成分多一些,“情爱”则性爱成分多一些。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我的小说中几乎没有写过爱情。我其实并不相信爱情,或者说,我更愿意把两性关系中彼此在岁月中积累下的深厚情感和依恋称作爱情,而不是刹那、短暂的火花。在我的小说《白马银枪》中,白玉堂和安福喜夫妇之间的情感比较符合我的爱情观。我写“情爱”的那些小说,男女之间都不圆满,不是自欺欺人,就是互相否定。其实问题都出在自己的身上,他们误以为“情爱”可以使自身得到拯救,结果只是对自己伤害得更深。《暗痕》《阳台》想要表达的都是这个。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反思自我成长的人,尤其是心灵的成长,追问自己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自己,促使我学习了心理学。我的小说写作几乎没有为了爱情写爱情的篇目,我笔下的爱情或情爱都关乎成长。
林 喦:当然,作为女性作家,对爱情和情爱的表达是有着天然的性别认知的。读你的小说,有一个很强的感受,那就是冷静而不冷漠。没有对人性美化的冲动,也没有放弃对人性良善的坚守。你既有冷静和理性的一面,又有温情、细腻和不露痕迹的悲悯。你是怎样看在小说创作中的性别视角的?怎样理解女性视角的独特性这一问题?
苏兰朵:这个问题很大,我不确定是否能准确表达出我的看法。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在我的小说中,如果简单设置一个强弱对比的话,女性人物多半是强的那一方,男性人物反而是弱的一方。我笔下的女性无论表面的生活有多么不堪,内心总是有一种向往美好的力量的。《白马银枪》中的宋银珍、《女丑》中的碧丽珠、《诗经》中的袁红丽、《雪凤图》中的喻小凤,甚至《设计师彼得》中的春草,都是这样。她们周围的男人,无论是成功人士,还是屌丝,都无一例外更多呈现出男人的弱点来。在她们眼中,男人是令人失望的。如果这可以算作女性视角的话,我其实不知道在男性读者的眼中,我塑造的男性人物是否真实。因为在我读到的很多同时代的男作家的作品中,看到了太多他们以男性视角一厢情愿塑造出来的女性角色,那种本质上和欣赏三寸金莲没什么区别的对女性肤浅虚假的同情,总是令我很不舒服。女人的弱,在很多男作家眼里是一种美,可以催情。
我本能地对我笔下的女性人物倾注了更多的同情和悲悯,她们越坚强,在我眼里就越充满悲剧感。我曾经思考过,我究竟算不算个女性主义者,想到最后,还是被“悲观主义者”这个本质给终结了。我觉得“男女平权”是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实现的,男人天然的比女性充满外在的力量,因而会获取更多的权力和自由。女人的力量更多的来自于内在,因为稍微有点觉悟的女人首先要做的是,为了自我发展,先要能够承受这一切。
林 喦:显然,写作不是你的职业,而是你职业的附属品。现在你是一位成熟的作家,喜欢写作的初衷是什么?你一开始是写诗的,而且很成功,后来又转到了写小说,也很成功。一般来说,诗歌和小说是创作差异比较大的两种文学形式,说说你是如何驾驭这两种形式的?或者说是如何在这两种创作思维模式中自由转换的?
苏兰朵:成为一名作家,是我小时候的梦想。我小时候有两个梦想,另一个梦想是成为一名歌手。直到现在,阅读和听音乐依然是我主要的业余生活。我最近追的一个综艺节目是《乐队的夏天》,每集差不多都看了两遍以上,车里现在放的也都是里面的歌曲。我在电台工作的时候,做得最长的一个节目类型是音乐节目,1995年的时候还组织过一次全国性的流行歌曲颁奖晚会。那个时候如果我去了北京,可能最后会成为一名歌手经纪人。2015年我出版了一本音乐随笔集《听歌的人最无情》,至此,这个梦想才算彻底放下。我的严格意义上的处女作是发表在大学时代,是一首诗。大学时也在晚报上发表过随笔,还参加过《女友》杂志的征文大赛,是一篇两万多字的小说,得了个优秀奖。20世纪80-9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我在中学和大学时期,几乎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当代作品。写作,成为一名作家,这个梦想一直在延续,从来没有放下过。包括考大学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报考中文系,可能跟潜意识中的作家梦也有关。不过到了2005年,我才真正沉下心来认真写作。说起来成为一个诗人才让我自己感到意外,因为就我个人的阅读来说,小说的阅读量远远超过诗歌。或早或晚,我都会写小说的。不过我到现在仍然喜欢诗歌的表达方式,直接,更加透明,而且可以止于语言,止于美。小说相对来说技术性更强一些。如果把诗歌和小说做比较,我觉得诗歌是内在的那个自我,小说更像是我的面具。当我戴上面具的时候,读者看到的是各种人物在演绎着他们的故事,但其实声音、形体和处理问题的方式还是我。好的小说在气质上都是接近诗歌的,但是它们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文体表达方式,我做不到自由切换,自从开始全身心创作小说以来,我写诗的冲动和灵感越来越少了。
林 喦:当下的大众文化消费,影视作品、短视频、电子游戏占据了重头戏。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文学的空间会被无限的挤压吗?文学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在哪里?
苏兰朵:和我们这代人年轻的时候相比,文学的空间确实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挤压了。从前文学绝对是主角。即使是被改编成电影,原著的影响也丝毫不逊色。像《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芙蓉镇》《活着》。现在,文学在大众文化中已经变成了配角。人们通过电影、电视剧的热播,才能注意到原著小说。而且在影视剧改编这一环节上,原著的被尊重程度也严重被削弱,会更多考虑市场,更加重视戏剧效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读严肃文学中的长篇小说了,网络短文和冗长的网络类型小说占据了年轻人的主要阅读时间。我曾经和我儿子谈论过这个话题。我告诉他,你应该读到最好的东西,然后你才能分辨出什么是不好的,不值得你浪费时间。每年的寒暑假,我都会推荐小说让他读。他现在读高中二年级,今年寒假我推荐的是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三部曲》,暑假推荐的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当然他自己也有选择,初中的时候他喜欢东野圭吾,上高中之后开始读村上春树。文学确实越来越边缘化了,但是文学依然在那,不能被替代。就我自己而言,我内在心灵的成长和成熟,价值观的确立,逻辑思维的建立,有一半要归功于文学性阅读。即便成为了一个作家,阅读也是我主要的生活乐趣。我想这至少是文学的价值之一。
林 喦:我一直有一个预判性期待,未来,在大街上有拿着一部文学作品阅读的人,一定是那个时期的新贵。(笑),同时,也期待和你、我一样有着文学情结的人在文学的世界里寻找到价值,亦期待你的下一部作品。这次我们就聊到这里,有机会再聊,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