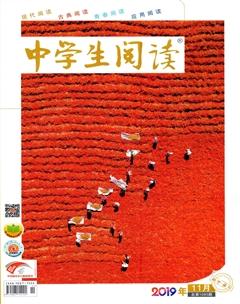在彼之邻
项丽敏

沿着浦溪河散步,见路边灌木上挂着一个“鸟巢”。“什么鸟筑的巢这么好看?”我惊叹着,脚步自然地移过去,还没走两步就被朋友一把拽回。“别过去,是马蜂窝。”
站定了再看,确实是马蜂窝。
马蜂窝并不像鸟窝那样随处可见,这么多年在野外行走,也只见到过两三回,且在很高的落尽了叶子的树梢上。土黃色的球形,硕大,孤独,如同废弃的城堡。这灌木上的马蜂窝和之前看见的不一样。形状像柚子,色泽又像刚出土的彩陶。我决定接下来的几天继续观察这个马蜂窝。
第二天,我提着相机出门。从居所走到浦园大道只需七八分钟。目光在昨晚见到马蜂窝的位置搜寻,很快就找到了目标——饱满的柚子形,棕褐与乳白相间的旋涡纹,拙朴中藏精巧,且与周围的环境色相融。我不由得惊叹那些马蜂,没有经过任何专业学院的进修,仅凭本能就懂得住宅美学,将居所修筑得可以与建筑设计师的作品媲美。
法布尔在《昆虫记》中,曾赞叹马蜂在住宅选址、材料采集、工程实施上具有的高强本领。马蜂选择的场地或在人们常走的山间小路上,或在附近的马路上,或在不会晃动的岩石上。这些地方要坚硬、干燥。它把收集到的粉尘用唾液浸湿,拌成灰泥浆。
除了粉尘。马蜂也会将枯死的树皮咬下,混入唾液,搅拌成黏稠的“混凝土”,有时也会采集废弃的纸壳,咬碎成泥糊状。用这些材料建筑的巢轻巧又坚固,且有较好的防水效果。建筑的初始阶段通常只有蜂王独自劳作,蜂王边筑巢边产卵,同时还要捕猎其他的昆虫,储存在巢里——那是给幼虫宝宝预备的食物。
马蜂是完全变态发育的昆虫,有卵、幼虫、蛹、成虫四个生命阶段。在幼虫期。由工蜂负责喂食。在蛹期,则会在六边形的穴口封上一层薄茧,停止进食,闭关自守。直到羽化为成虫才破茧而出。之后就迅速投身到捕猎、喂养幼虫和筑巢的事业中。
我在浦园大道看见的马蜂窝已经是竣工的“成品房”。站在距离马蜂窝两米远的地方,拉开相机长焦镜头,发现它的进出口在左侧,中部偏下的位置。这个位置比较避风,雨水也不会淋进去。进出口的圆孔很小。当镜头的焦距对准圆孔内部时,赫然看见一只马蜂的头脸,正“蜂视眈眈”地盯着我。
马蜂是有攻击性的,当它们感觉到来者不善时,就会群起而攻之,用尾部的蜂针刺蜇入侵者,注入毒液。“绕道走”当然是避免被马蜂攻击的上策,但我此时是作为观察者来到马蜂窝跟前,必须让自己以尽可能近的距离观看它们。
马蜂的攻击不过是自我防卫。以我多年来山野行走的经验,遇到蜂类,只要保持静止状态,就不会招来袭击。有几次,在山间野地,甚至有马蜂落在肩上、头发上。极具威慑力的振翅声在耳边轰鸣,尽管身上的汗毛都耸立着,但我仍旧闭着眼睛,在心里对自己催眠:放松,不要动,我是一根树桩。
第三次拜访马蜂窝是在两天后的下午。准确地说是去探望,怀着“不知道马蜂窝怎么样了”的担心,因为之前突然刮起狂风。降下一场雷暴雨。那些树木——香樟、玉兰、鹅掌楸和红叶李树,在风里仰伏摇摆的样子,像剧烈的挣扎,也像狂喜的舞蹈。忽然想起浦园大道的马蜂窝,待雨停歇之后,我抓一顶帽子盖在头上。拿起相机出门。
很快就走到浦园大道,马路上有很深的积水。绕过积水,走了一个来回,没有看到那个马蜂窝。怎么回事,是我记错位置了吗?或者是马蜂窝已被人清除?我从第一次看见这马蜂窝就有种担心,觉得它很可能会被除去。尽管它的位置在绿化带的灌木上,却还是不够隐蔽。
放慢脚步。我又走了一个来回,总算看见了那个马蜂窝,原来它就在路面有积水的地方,先前被我绕开了。马蜂窝外壳果然有多处破损,像在地上摔过,开裂了。好在它仍旧悬挂在灌木上,没有坠地。这要归功于它的建设者,在筑巢时,有意容纳进几根灌木细枝,钢筋一样撑住它。有七八只马蜂在马蜂窝破损的外壳上爬行,有时相互碰碰头,仿佛彼此安慰。或在商量着什么。从马蜂窝进出口的位置。不时有马蜂爬出,嗖地飞向远处。
马蜂修复破损的巢用了两天时间。两天之后,马蜂窝完好如初,丝毫看不出破损的痕迹。不知道马蜂是否有惊慌失措的时刻——当暴雨从天而降。箭矢一样射向马蜂窝时。躲在里面的马蜂是否感到恐惧?
万物都需要有各自的居所。
早晨有雾。走在路上,蓦然感觉到一丝秋意。知了也感觉到季节微妙的迁移,晨唱的时间推迟了一个小时,韵律也有了改变,加入有节奏感的唱词,“乌吉耀丝。乌吉耀丝”。电线上停着珠颈斑鸠,咕咕地叫着。斑鸠的叫声很奇妙,明明就在近处,聽着却觉得悠远,仿佛那声音来自一片幽秘森林。
走到马蜂窝的位置,拿相机拍了一张,转身走开。这几天,早晚散步时会来打一转,看看它在不在。看到它在就行了,就不再紧盯着看了。长久的窥探,对马蜂的安静生活也是一种打扰。
马蜂十月底会离巢,整个冬天都见不到它们的身影,是去了更为隐蔽的地方,在干燥避风的墙缝或树洞里,抱成一团,不吃不喝,减少生命的消耗以度过寒冷的冬天。
离马蜂弃巢而去的冬日还有一个季节。夏日曲终,秋日歌始,在浦溪河边,我和马蜂还拥有一个季节。做彼此秘密的互不干扰的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