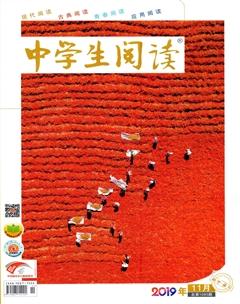木瓜河的向日葵
路明

一条小河从菜溪中学流过,隔开了初中部和高中部。河的名字有点奇怪,叫木瓜河。小镇盛产黄瓜、冬瓜、丝瓜……,就是不产木瓜。木瓜是遥远的南方的物产。我在作文里写,掉进河里的人,会扑通一声。变成一只木瓜。
“老木头”在黑板前唾沫横飞,我看着窗外的河流发呆。这节课本来就不是“老木头”的,教美术的金老头请了长病假,美术课被几门主课瓜分。作为我们的班主任,“老木头”理直气壮地霸占了其中的大部分。
我发了一会儿呆,翻出一本卷边的《圣斗士星矢》,放在课桌里偷偷看。我因参加数学竞赛,提前自学了初中数学,看闲书并不太耽误成绩。换作别的老师,也许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老木头”却不能忍。他每没收一次我的书。我就拿一道竞赛题去请教他。题目我事先研究过。是省决赛级别的题。他拿着题,抓耳挠腮,一筹莫展。我说:“穆老师您慢慢想,我先去上课了。”两节课后。我再去办公室找“老木头”,可怜的他还在伏案解题。我装作灵机一动,大声说:“穆老师,您看,这里添一根辅助线行不行?”我抢过题。刷刷刷写出解题步骤,然后歪着头问他:“穆老师,您看这样解答对不对呢?”他只好说:“对,对。”别的老师都朝这边看过来。几次以后,他就不管我了。
这天,“老木头”走进教室,身后跟着一个年轻的女老师。他介绍说:“这是霍老师,美院高才生,以后教你们画画。”他警告我们。不许欺负人家。我们都笑起来。稀稀落落的掌声中。霍老师走上讲台,鞠一躬,捋了捋头发。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是什么高才生。就是喜欢画画,很高兴认识大家。”说完又鞠了一躬。霍老师个子不高,短头发,有点害羞的样子。有点像当时的体操运动员霍尔金娜,总的感觉是跟别的女老师不大一样。后来我们知道,“霍尔金娜”当时还没毕业,是来我们中学实习的。
从前的美术课,金老头上来讲几句,黑板上做个示范。就由着我们各自瞎画。他拉过一把藤椅,喝茶看报纸,耗到下课铃响,拉倒。“霍尔金娜”不一样,她讲古希腊和文艺复兴,讲古典派与印象派之争。讲藏经洞和敦煌壁画。尽管我们都听不太懂。我们的纪律也不大好。有时“霍尔金娜”忍不住训斥几句,自己先脸红了。她喜欢凡,高,曾用一整节课的时间,给我们讲《星夜》《向日葵》等。她引用凡。高的话:“爱是一种积极的东西,它如此地强烈,如此地纯真,以至于要使一个人收回他的那种感情,正好像要他杀死自己一样是不可能的。”“霍尔金娜”定在那里,嘴唇颤动,说不出话来。许久,她用哽咽的声音说:“可能的。”
“霍尔金娜”上课时,我就趴在桌上画圣斗士和七龙珠。我刚画完贝吉塔变身超级赛亚人,抬头一看,她站在课桌前。周围一片吃吃的笑。我有点尴尬,假装无所谓地咳嗽一声。她拿起我的稿纸,看了看说:“画得不错,构图准确,线条也有力气。”停顿了一下,又说:“就是阴影没打好,立体感不够。”她把画还给我,微笑着说:“请继续画下去吧。”
车匪杵我一肘,说:“不会吧,你的脸红了。”我说:“滚。”
即使是车匪也没办法否认,“霍尔金娜”很好看。也许不仅仅是好看,还带着某种陌生的来自大学草坪的气息。慢慢地,她的课堂纪律好起来。村里囡和街上囡,一起仰头听讲,眼睛里有罗纳河上的星光。“霍尔金娜”说。素描有黑白灰三种颜色,黑色是阴影,白色是阳光,灰色是过渡。我想,一个小孩子,决不会平白无故变成大人,他也需要过渡。他会经过一条河,或者一道沟,走过去,就成了大人。过不去的,就扑通一声,或者吧唧一声。变成了木瓜。“霍尔金娜”是一座桥吗,还是一条船?也许有一天,我会像她那样,活成一个不那么令人讨厌的成年人。
“霍尔金娜”说。等三个月实习期满。如果校方满意,她就可以留下来,成为我们的正式老师。我们都觉得,霍老師课上得那么好,又没有竞争对手,留下是铁板钉钉的事情。所以当那一天,“霍尔金娜”告诉我们,这将是她给我们上的最后一堂美术课时,我们都蒙了。“霍尔金娜”红着眼眶,几乎讲不下去。一个女生哇的一声哭了。
第二天,学校橱窗外贴出一幅素描。是仿的凡。高的《向日葵》。线条粗犷,对比强烈,倔强干枯的花朵,在黑白灰的世界里无声地燃烧。花瓶下有一行字——霍××老师留下!再往下,是我们全班的签名。
中午再去看。画已被撕下。我去找“老木头”交作业,正好碰见“霍尔金娜”从办公室出来。她把我拉到一边。轻声问:“是不是你画的?”
我咬住嘴唇,不说话。她无奈又温柔地看着我,说:“请不要这样啊。”我低头看脚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不想让老师走。”
她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叹口气,说:“你这样,让老师很为难……”
有校领导叫她:“小霍,来,我们再谈一谈。”她拍拍我的肩。转身走了。
初中毕业后。我回学校看“老木头”,不知怎么说起了“霍尔金娜”。我发牢骚说,学校为啥把这么受欢迎的老师赶走,想不明白。
“老木头”说:“这你就冤枉学校了,是霍老师自己要走的。”
我说:“骗人。”
“老木头”笑了。说:“骗你干吗?学校确实想留霍老师,都准备签工作合同了。但霍老师后来又有机会到县一中了。你想嘛,能去县城,谁会不去?人往高处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