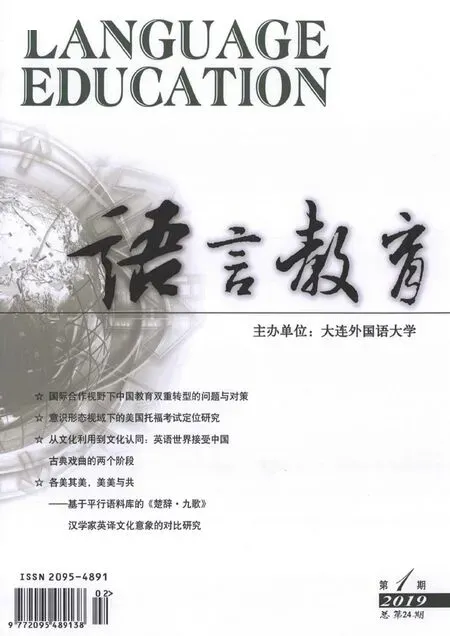“意义之音”的来龙去脉及功能价值研究
——弗罗斯特诗歌创作理论“意义之音”解读
焦鹏帅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
1. 引言
关于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提出的“Sound of Sense”,国内学者刘瑞英(2008)探讨了“意义之音”对于弗氏诗学的重要性、思想根源及内涵,并通过解读弗氏诗歌对“意义之音”进行了解读。韩丹(2008)从弗氏的艺术主张、创作实践和艺术创新三个方面结合实例对其“意义之音”诗歌理论进行了分析。两位学者对弗氏的“意义之音”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并未呈现详细文献给读者,也未就其具体内涵、功能与价值进行深入探讨。本文旨在通过文献考据的方式,循着语迹,进入语境,历时共时相结合地呈现这个理论的发展及各位学者对这一理论的不同视角的阐释,最后阐释该理论的内涵、功能与价值,希望对弗诗理解及中诗创作有参考之用。
2.“意义之音”的由来及在弗罗斯特传中的体现
据现有可查文献,弗罗斯特首次提到意义之音(Sound of Sense)①其实这一理论并非弗氏独创,而是英语文学的一个传统,他的贡献在于将其强化,形成了一种现代诗歌理论与实践。参见Potter L James. Robert Frost Handbook[M].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University Park and London,1982:156 原文是:(Sound of sense), this was not original with him, but his emphasis on it wa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modern poetic theory and practice.——他的这一核心诗歌理论,是1913年7月在致约翰·T·巴特利特的信中,针对19世纪诗歌的音乐性谐音而说的,他说:
我一直有意地使自己从我也许会称为“意义之音”的那种东西中去获取音乐性。……要得到这种抽象的意义之音,最好是从一扇隔断单词的门后的声音之中。(曹明伦译,2002:869-870)
这里弗氏指出当时一些诗人对于英诗过时的传统因循守旧:即音乐性是使元音辅音的和谐,用一个生动的例子来阐释他的“意义之音”,就是从门后去听一段话的意思。其实这就是话语的情景、语境和语域问题,每个人由于语音、语调,自然会赋予其独特的个体话语特征,这就是弗罗斯特所说的“声调”,或语气。即使你听不很清楚每一个词,但是总能依靠语境,准确辨别出话语的意义、情感以及戏剧互动。那么这个意义之音到底是什么呢?弗罗斯特接着写道:
它是我们语言的抽象的生命力。它是纯粹的声调——纯粹的形式。……意义之音也不仅仅是音韵。它是意义和音韵二者之结合。有价值的格律只有两三种。为使其有所变化,我们依靠的就是意义之音中重音的无限变化。情感表达之可能性几乎全在于意义之音和单词重音的自然融合。(同上:870-871)
弗罗斯特在这里指出意义之音的重点在声调,并且将其适用领域由诗歌延伸至散文,指出一个诗人应该“必须学会熟练地打破其无规则的重音与格律中有规则的节奏相交错的意义之音,从而获得语言的自然韵律”。同时他又将好诗与打油诗(doggerel)区别开来。进一步指出“意义之音”应该是意义和音韵的完美结合。如果这里讲的还比较抽象,那么弗罗斯特在后面与锡德尼·考克斯的通信中继续阐释他对音调的理解:
一首诗中有活力的部分是以某种方式同语言风格和文句意义缠在一起的音调。这种音调只有在以前的谈话中一直听到它的人才能感觉。我们在古希腊诗或拉丁诗中就感觉不到音调,因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说话的音调从来没传进过我们的耳朵。音调是诗中最富于变化的部分,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没有音调语言便会失去活力,诗也会失去生命。重音、扬音和停顿与音调并存,它们不是元音和音节的内在体,它们总是自由地伴随着意义的变化而变化,元音有其重读,这点不可否认。但意义重音占先于其它任何重音,它可将后者压倒甚至抹去。(同上:875)
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弗罗斯特眼中的声调应该是包括重音、扬音与音调的结合,其特征就是富于变化性:随着意义的变化而变化,为了说明声调问题,弗罗斯特再次以“oh”为例来说明语调的不同带来的语气的多样性和表达效果:
美国诗人实际上只使用了“Oh”的一种语气,即表示庄严壮丽:“啊灵魂!”、“啊大山!”、“啊一切!”这就是他们的用法。想想“Oh”是多么富于表现力:可以表示轻蔑,表示快乐,表示惊讶,表示怀疑——等等。(Lathem,1966:13)
这种语气的变化,不单体现在一个词中,也可以体现在一首诗中。弗罗斯特随后在《会想象的耳朵》(曹明伦译,2002:892-893)一文中以他的《牧场》一诗做了解读:
我要出去清理牧场的泉源,(轻松的、告知的声凋)
我只是想耙去水中的枯叶,(“只是”声调——保留)
我要出去牵回那头小牛,“对我来说挺不错”——
它站在母牛身旁,那么幼小,(同前,第二节中有悠)
短短的一首诗中竟然包含如此众多不同的声调、语气,这种声调语气的解读和实现完全依赖于读者对原语声调的熟悉与把握,也体现在诗人对这种声调的期待和解释。这种双重不确定性增加了弗罗斯特诗歌的多重阅读内涵,丰富了他的诗歌的内在情绪和意旨。在1914年2月致巴特利特的一封信中,弗罗斯特为句子下了个定义:
句子本质上是一种可把其它叫做词的声调串起来的声调。
……
句子声调被耳朵领会。它们由耳朵从本国语中搜集然后进入书中。书中的许多句子声调已为我们所熟悉。我想并不是作家创造了它们。最有独创性的作家也只是从谈话中活生生地捕捉到它们,它们总会在谈话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同上:879)
弗罗斯特在这里将声调的概念由词延伸到了句子,更重要的是在他眼里句子就是“词串起来的声调”。文学评论家丹尼斯·多诺霍(Denis Donoghue,1928-)认为“从句音出发,其实可以建立一套音步与韵律、造句法与日常语言之间的互相冲击的理论。音步是一个抽象的格式,活化它的是韵律,而语意上的层次变化和词的作用也在这过程中显现出来。格式是理想化了的,或概念化了的,但足以在心灵之耳中参与造化。同样地,语法和造句法的规律并不屈从日常语,但必须对它和韵律做出让步”(欧凡,2010:243)。
而在欧凡看来,“弗罗斯特关于句音的说法颇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西方诗歌的音乐性。看来句音相当于乐曲中的一个小节,而字词相当于个别的音符。中国古代的诗歌同样和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诗经、楚辞到诗、词、曲都可以配乐颂唱或吟诵。可是到了白话诗,音乐性就失去容身之地了。光靠一个尾韵,似乎很难承担赋予全篇音乐性的担子——不是流于单调,就是看着它拖家带眷似的,牵着一串长长的句子,不但不能予人音乐上的美感,反而使人可怜它,担心它时刻可能筋疲力尽,倒地不起”(同上:245)。
那么弗罗斯特所说的声调到底是什么呢?他曾说:
我所关心的只是捕捉那些尚未被写进书中的句子声调。请注意,我没说创造它们,只是说捕捉它们。没人能创造或增加句子声调。它们从来都存在——存在于人们的口中。……这一点除了写自由诗的谁都知道。它是传统的东西。它虽没被写进教科书但人人都知道。(曹明伦译,2002:895)
在这里,弗罗斯特坦率地表达了自己通过诗歌来表达人们日常生活言谈话语声调的意图,也指出了他所说的句子声调其实就是人们的日常口语,也指出了诗人与声调不是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而是一种捕捉、还原的描写关系。如果追根溯源,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声调与意义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的诗《声音与意义》(Sound and Sense):诗句不仅要避免刺耳难听,音响应该就像是意义的回声。①该译文参见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8500248.html,笔者略作改动。请读者仔细体会第5、6、7、8、9、10、11、12行音义结合的阅读效果:由元辅音的不同性质与节奏之快慢而反映出的溪水潺潺,波涛汹涌,动作吃力,飞行轻快之义。可以看出传统英诗讲究通过音响再现意义,达到音义的完美结合。那么这种音义结合是如何体现的呢?
3.“意义之音”的音意关系传统的实践
西方对声音与意义关系的探究有着古老的传统。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塞诺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二者的关系有着不同的见解。毕达哥拉斯强调二者的物理属性,认为和谐的音高关系之下隐含一种数学秩序;而亚里士多塞诺斯则强调了认知与音乐体验(Barker,1984;Polotti和Rocchesso,2008:16)。柏拉图则强调画面视觉效果,主要由于他认为音乐有着强大力量,声音与意义之间有着一种强烈的效果。而亚里士多德则从拟态理论(mimesis theory)来理解声音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他根据拟态理论,认为节奏与乐曲包含了很多类似于人类各种真正品性的情绪,诸如愤怒、温和、勇气、亲切及其它的相反情绪。通过在音乐中对这些人类品性的模仿,我们的灵魂以一种相似的方式被感动。因此,当我们听到一首乐曲时,我们会对我们所经历过的情绪反应产生共鸣。
17世纪的法国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认为声音与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在他的著作《音乐概要》(Musicae Compendium,1618)中阐述了二者的关系。他先将音乐分成三个基本部分:(1)数学物理方面(毕达哥拉斯);(2)感知方面(亚里士多塞诺斯);(3)音乐认知对个体听众心智的终极影响(亚里士多德)。对于笛卡尔来说,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声音的感知应作为科学研究的内容(Polotti &Rocchesso,2008:17)。
人类的所有音乐活动中,声音和意义紧密相关。声音来自物理环境和移动的物体,而感知的意义则产生于个体感受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意义。声音能够通过乐器和机器等客观的方式来描述,而感知的意义是一种主观的经验,它要求个人的解释以便清晰的表达这种体验(ibid,16)。在一篇有关弗罗斯特及其意义之音的访谈之中,这样写道:
一首诗终究必须要照顾的三样东西:眼睛、耳朵和我们所说的心灵。最重要的就是要深入读者的内心。当然要想深入其心须要通过其耳。而一首诗的视觉意象同样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将措词、排列成一种序列,以便更好地来控制读者声音的声调和停顿。诗人通过这种排列与字词的选择,就可以获得幽默、悲怅、歇斯底里、愤怒等各种效果(Newdick,1937:298)。在弗罗斯特眼里,“声音的特征就是使读者的阅读变得抑扬顿挫”(同上)。
具体地说,英语词汇中由于字母不同组合而形成的发音声响会让听者自然地生发意义联想,也就是说,字音总是被赋予了一定的相关意义。坡林(1985)对英语单词的构造与意义进行了研究,指出:
除了一定的拟声词(如hiss:咝咝声,snap:噼啪作响,bang:啪啪声)外还有其它的字母组合同样也能带给人相应的联想意义。“如“fl”的声音时常带有光在移动的意思,如flame(闪光),flare(闪耀),flash(一闪),……。字头“gl”也常有光的意思,可能是不动的光。如glare(耀眼),gleam(微光),glint(闪光),glisten(闪耀)。字头“sl”常有“滑溜”的意思, 如slippery(滑溜),slick(光滑),slide(滑冰),slushy(融解中)(坡林,1985:162-163)。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不同的声音并非一成不变地与它们所暗示的意思保持一致,比如短音“i”既出现在thin(薄)中,也出现在thick(厚)中。
除了这种拟声词和特定字母组合所产生的音响意义外,英语里的元辅音本身具有不同的音质属性。诗人可通过元辅音的搭配达到或和谐悦耳,或尖锐刺耳的效果。
一般而言,元音由于其发声时口腔无阻碍,因此其具有乐音属性。……一行诗里,如果元音所占比率较大于辅音,就会显得很和谐悦耳,反之就呈现不和谐的音响效果,从而使读者产生不同的联想感觉意义。(同上,164)
声音对于意义的影响关系还体现在声音的速度与进程上。诗人可通过选用某种形式的格律,通过排列元辅音的数量以及安排语气停顿以取得速度的控制。一般而言,“非重读音节要比重读音节发音快,因此,三个音节的格律要比两个音节的格律快。但是诗人可以通过替换音步的方法来改变任何格律的速度,从而达到诗人想到达到的意义、情感效果。只要两个或更多的轻读音节遇在一起,其效果是加大诗行的速度,反之重读音节遇在一起,则是降低诗行的阅读速度。同时诗行的速度也会因元音的长度或字音是否连读而受到影响,这些都会影响到诗歌所附带的意义”(同上,165-166)。另外,是否重读、弱读还在于诗人所要考虑强调的词语意义上。如弗氏的诗歌The Span of Life
The old dog barks backward without getting up,
I can remember when he was a pup.
那条老狗只狂吠而不起身逞强,
我还记得它是条小狗时的模样。(曹明伦译,2002: 390)
就诗行音节轻重安排来看,这首诗采用的是轻轻重格,每行四音步,双行押尾韵。诗的内容描写一条老狗衰老与年幼时的活跃相对比。那么,这里的声音安排如何体现意义呢?
首先,诗人选用的三个章节的格律是快速的格律,但在第一行诗里,他以很不一般的方式阻碍格律的速度:他用一种我们叫不出名字的音步来代替这种轻轻重格。这可以叫做重重重三音节的音步,即重音连续落在三个音节上。这种音步跟随着前一个音步的重音节就造成四个重音节排在一起的局面。另外,所有重音节都以一个强劲的辅音或连续辅音开始或结尾,这就使各字连读感到困难。口型在发出下一音节时必须改变:The old dog barks backward,其结果是这行诗不得不十分缓慢地前进,甚至于丢失了节奏,有些佶屈聱牙,不很上口,可是当我们读到第二行时,其节奏则是轻快的,每个音节都落在元音或流音的辅音上。这两行诗的进程与声音显然是跟字句所含的视觉意象相吻合的:即作者通过两诗行前后分别为滞纳、轻快的阅读效果来匹配老狗年老体衰行动迟缓与幼年时的敏捷活跃的意义。另外第一行里的“back”与前面的拟声词“bark”相呼应,形成一种回声一样的感觉,起到加强听觉意象的效果。(坡林,1985:170)
弗罗斯特诗中的这种“意义之音”的例子还很多,再比如其名篇《雪夜林边驻马》(“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全诗的韵式为“aaba,bbcb,ccdc,dddd”最后一节使用dddd来替代dded,给读者留下一种重复终止渐隐的感觉。诗中频繁出现的包含s音的词,如snow,see, horse, must, stop, farmhouse, harness, ask, some,sound, sweep, sleep等使读者仿佛听到雪落林间的“咝咝”声,再加上整体的连环韵和行间的头韵和半韵,烘托了雪夜林边的宁静气氛,也给读者带来了仿如置身其境的听觉意象。
从弗罗斯特有关“意义之音”或“句音”的论述,可以看出“除了词本身的符号外延所指,意义寓居于我们言语中的一切。而内涵意义则是由音高、重音、各种停顿以及其它不怎么有形的音调所展示出来”(Potter,1982:161)。这种“意义”显然是一种较抽象的意义,不太好定义,它一方面借助于诗人对自己遣词用语的暗示,另一方面通过句法、断句以及字词的位置以及停顿显现出来。而问题是书面语难以再现如此众多的语音诸方面情感。如果诗人不在场,自然就赋予读者更多的识别那些“句音”的责任。这就是弗罗斯特所说的“诗人的职责就是捕捉那些不能自我表现的人们说话时的音调、感情的变化。诗人的艺术魅力在于他必须将文字建构成一种传达媒介,将精确的语声传递到读者的耳朵”(Ven,1973:249-250)。弗罗斯特认为文字,特别是诗歌的文字,应该尽量接近自然话语,而读者可以凭借其所听到的不同话语方式的知识来再创造出那种“意义之音”。这种不同话语知识是由我们所处的文化所决定的,同时也反映出个体思维方式的不同。这也就使得弗罗斯特的诗歌的解读与认知呈现多样化的态势。
弗罗斯特有关意义之音及句音的理论似乎赋予诗歌某种音乐性。但又与阿尔杰农·查尔斯·史文朋①阿尔杰农·查尔斯·史文朋 (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位著名诗人。因其诗歌用词华丽,字斟字酌,只为韵式,而不是为意义而倍受诗界诟病。(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以及爱伦·坡所说的纯音乐不同。①爱伦·坡曾在《诗歌原理》(曹明伦译)一文中说:“我历来都确信以下事实:在节拍、节奏和韵律形式上都富于变化的音乐对诗歌来说非常重要,所以绝不可骄横地把它摈弃;音乐是诗歌至关紧要的助手,只有白痴才会拒绝它的帮助。鉴于此,我现在仍然坚持它确切无疑的重要性。也许正是由于音乐,心灵被诗情启迪时才会最大限度地接近那个它努力要实现的伟大目标—创造超凡之美。”(参见:曹明伦.爱伦·坡精品集[Z].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684 )我们可以看出,他所强调的音乐是为诗歌的“美”服务的。而弗罗斯特所说的音调、声调是为意义服务的。在弗罗斯特看来,诗歌的语言不仅仅要美,更应该体现诗人对人生本身意义与强度的洞见与思考,措词用语应不怪异,而应该尽量朴实,如日常口语谈话一样朴实无华。从根本上讲,就是“句音”是以意义为导向的,戏剧化的。正如弗罗斯特所说:“语言变成了行为”(Words that became deeds)。昭示着人类本性的最基本的情感能量。“为了避免进一步损害人类的语言……诗人必须回归一种前语言交际方式,通过语调的展现来传递有生命力的交际意义”(Potter,1982:162)。
4.“意义之音”在罗斯特诗中的功能
意义之音在弗罗斯特的诗歌里主要有如下功能:
1. 有助于通过其与规则韵律的多变关系,打破韵律的规则节拍中的重音的不规则性来激发节奏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在其叙事诗《家庭墓地》中可见一斑:通过节奏的多变来再现口语的特色。这种张力的和解巧妙地处理了诗歌术语中的混乱与形式之间的关系。
2. 起着人物性格刻画的作用。例如在《家庭墓地》中的诗行:
他在回过神来之前已说了两遍:
“难道男人就不能提他夭折的孩子?”
“你不能!哦,我的帽子在哪里?唉,我用不着它!
我得出去透透空气。
我真不知道男人能不能提这种事。”
“艾米!这时候别上邻居家去。
你听我说。我不会下这楼梯。”
他坐了下来,用双拳托住下巴。(曹明伦译,2002:67)
在这几句诗行中,意义之音起到了烘托感情的作用:丈夫谨慎、克制的话语与妻子冲动、语无伦次的话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3. 意义之音的主要作用还是其戏剧性的烘托,其中涉及感情渲染、人物刻画以及节奏变化等。弗罗斯特曾说:“戏剧性是句子本质中必不可少的东西。若句子没有戏剧性,其差异就不足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无论其结构变化多精妙也不管用;能拯救句子的只有以某种方式缠住字词进入书页,让想象的耳朵去倾听的语音语调。只有语音语调才能使诗歌免于单调的节奏,使散文体作品免于平铺直叙。”(同上,917)
4. 关于“意义之音”,赵毅衡教授在接受笔者访谈时,就其实质与汉诗以及现代诗的关系,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这个“意义之音”是现代诗的最基本的节奏特点。现代诗的节奏是意群。弗氏这里其实谈的是“节奏”(rhythm),而不是“韵”(rhyme),也与字数无关。现代诗的节奏其实与意义有关。所以我们说是sense group(意群)。现代诗不讲meter(音步),也不讲平仄。现代诗也不像法语诗一样讲究音节。比如上世纪三十年代写“豆腐干”的,如五言、七言等,这就对他们不起作用。甚至中国新诗也不是靠顿形成的。顿是机械的,而意群则是活的。就意群而言,散文的意群与诗歌的意群还不同,因为它不需要行行间的相应(correspondence),不需要形成一种节奏感。而诗则不同,它需要行行间地相应。关于新诗的节奏问题,中国目前始终没有搞清楚。而弗氏的诗讲究“韵”,是一种返旧。他的韵式安排呢,比较散、灵活,不同于严格的英语律诗。这是他对英诗的继承与创新之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他是个现代诗人,但不是个现代派诗人的缘由。(焦鹏帅,2011:65)
在弗罗斯特眼里,“声调变成了伟大的艺术催化剂,它的作用具有一种神秘的认知论。”②Frost as a critical theorist[OL].http://www.frostfriends.org/FFL/Frost%20on%20writing% 20-%20Barry/barryessay2.pdf. 原文是:For him sound was the great artistic catalyst, and its function was mysteriously epistemological.同时我们也看到他对诗歌的这种声音与意义之间的联系明显带着笛卡尔的二元主义色彩。
关于Sound of Sense的中文译文,笔者以为,sense这个词固然有“意义”之义,但它更强调的是一种个体通过特定的音调及声音感知出来的意义;而sound在此也不单指“声音”,而指人们话语里的音调、语气和口音。它既强调了听者的主观感受,同时又赋予被感知的声音的意义以多样性。从可译性的角度来说,这种声调也是最难在另一种语言中再现的。庞德将其称为“melopoeia”,即词被赋予指向意义生成的音乐属性。这种音乐属性只能由具有敏感耳朵的外国人所欣赏,而不能翻译,除了“上帝赐予的偶然或偶尔的只言片语”(Bussnett & Lefevere,2001:64)。著名现代诗人、诗评家西渡则从诗歌创新角度阐明了弗氏“意义之音”的意义:“弗罗斯特对声音和意义之关系的发现,改变了英语诗歌过分依赖单词重音和有限的格律模式的倾向,为诗歌的音乐性注入了新的活力。诗歌的声音对弗罗斯特而言不是对那些格律模式的机械重复,而是以某种方式和语言风格、文句意义纠结在一起的有着丰富可能性的声调,它本质上是一种说话方式。是我们说话的方式决定了一个词、一个句子应该怎么发声,而不是单词重音或诗歌的格律模式:‘意义重音占先于其它任何重音,它可将后者压倒甚至抹去。’”(西渡,2009:297)笔者以为,该术语的汉译可因循已有“意义之音”的汉译,也可不译,让其保持开放的特点,让不同的读者和诗人从自己的体悟中得出自己的理解。
5. 结语
弗氏提出Sound of Sense这个诗歌概念本身含有复杂的内涵,而非单一的一种解释,正如他的诗歌一样,貌似简单,其实深邃。这个概念的内涵不仅仅是音义对应的关系,也不仅仅是音调对于意义再现的意义,它既包含了重音变化对于节奏的影响,也包含了话者说话的情绪和语气,还包括了基于说者与听者共有的语言背景,听者对于话者的主观经验认知,它是一个复义性概念,是现代诗的基本节奏特点。
尽管各位学者对其有不同的阐释与理解,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诗歌创作中可以利用音调,利用语词的音响来表达诗歌所要阐释的意义,使诗歌的音意相互映照,达到一种完美的和谐:既美于义,又悦于耳,悟于心,还能凸显人物性格,烘托语篇气氛。明白“意义之音”的来龙去脉,弄清这个术语的内涵所指和功能,对于我们理解弗诗的创作原理及现代诗的创作都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