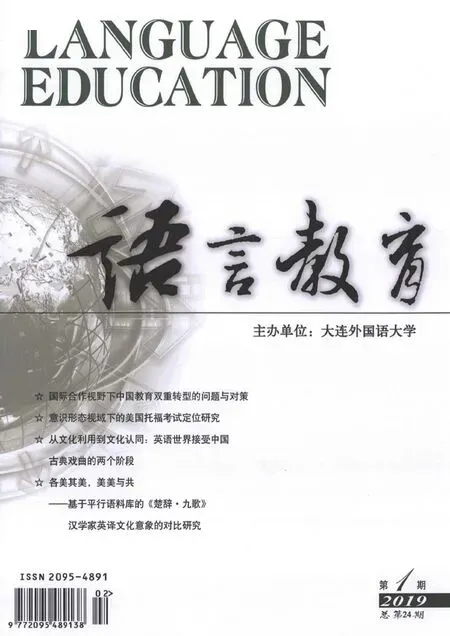从文化利用到文化认同:英语世界接受中国古典戏曲的两个阶段
吕世生 袁 芳
(南开大学,天津)
英语世界接受中国古典戏曲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并呈现了两种特征:第一阶段接受的特征是文化利用。这一阶段英语世界仅仅接受了中国戏曲的思想价值,却排斥了美学价值,文化误读十分明显;第二阶段接受的特征是对中国古典戏曲的文化认同。这一阶段,英语世界转向多元文化立场解读中国戏曲,关注中国戏曲的美学价值,通过翻译、改写、研究、演出等多种形式表达对中国戏曲的认同。
英语世界对中国古典戏曲的接受肇始于十八世纪中期我国元杂剧《赵氏孤儿》在伦敦的演出。《赵氏孤儿》是译为西方文字的第一个中国古典戏曲,译者为来华传教士马若瑟(Joseph M.de Premare)。后由法国启蒙思想家、剧作家伏尔泰改编,1755年搬上舞台,大获成功。受法国成功演出的影响,英国剧作家、演员墨菲(Arthur Murphy)将其改译为英文,于1759年4月以《中国孤儿》(The Orphan of China)为剧名在伦敦的Drury Lane Theatre剧院演出。此时伦敦戏剧的“演出季”已近尾声,观众去剧院的兴趣已开始消退,但是该剧的上演却激发了观众的热情,以至该剧连续演出九场,而且随后在伦敦年年上演,连续十年。当时的剧评家哥尔德斯密(Goldsmith)在《评论杂志》(Journal of Review)上描述了伦敦观众对《中国孤儿》的喜爱:“那天晚上的首场演出,全场观众好像感到满意极了,他们是有理由感到满意的……。强烈的情绪,耀眼的背景和绝妙的导演在我看来是他们满意的所在”(转引严建强,2002: 146)。《赵氏孤儿》在英国的成功演出成为英语世界接受中国戏曲的标志。然而,此间演出的这部元杂剧却是由法语转译而来,仅仅有选择地保留了部分文本主题,而艺术特色、美学价值经翻译后却难觅踪影。这种情形与其时译者的西方自我中心文化立场难脱干系。其时英国盛行古典主义戏剧美学,他们据此裁断中国戏曲,无可避免地产生了诸多不屑。他们接受《赵氏孤儿》仅限于其中的思想价值,是民族大义、忠诚信义等观念。简言之,这一时期英语世界接受的是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思想观念,而非其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而对后者的接受,则要推迟到20世纪前期,大约200年之后了。然而200年之后,英语世界对中国戏曲艺术的接受却转换了场地,转到了大洋彼岸的英语新世界。这就是以梅兰芳剧团访美巡回演出为标志的中国古典戏曲的再度“西传”。梅剧团成行美国的历史背景是中西文化接触的深入发展,英语世界对待中国古典戏曲的认知发生了变化,文化立场发生了变化。中国古典戏曲的艺术魅力在这片英语世界的新天地里开始绽放,普通民众、艺人、译者受到了感染,文化立场由一元转向了多元。这一历史过程中,英语世界接受中国古典戏曲是如何发生的,有何种特征,与其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之于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价值,笔者不揣浅陋尝试逐一探讨。
1. 英语世界接受的第一个阶段
十八世纪前期英语世界接触的英译本《赵氏孤儿》确切地说应为编译本,或者改写本也不为过。这个英译本是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文化立场的产物。《赵氏孤儿》是中国戏剧史第一个辉煌时期元杂剧时期的众多曲目之一。这一时期的中国戏曲,主要是北方地区的戏曲,在中国文化史上又称为“元曲”,此称谓源自这种戏曲的“曲白相生”艺术特色(“曲”指演唱,“白”指“道白”,又称“宾白”。此指舞台演出中演员既有演唱也有道白)。剧情发展到高潮时,人物感情澎湃时,演员都要演唱。然而,元杂剧在中国文化中得以立足的这一艺术特色,却难为英国的古典主义戏剧美学所容。英译本《中国孤儿》原文本中演员的演唱部分被全部删除,保留下来的仅仅是原文本的“宾白”部分,显然英语读者/观众所见的是“毁容”之后的中国戏曲。
这部戏曲进入英语文化后改变了艺术面相最直接的原因是英译本依据的法语本已远非原来面貌的中文原本。原文的演唱部分——其在中国戏剧史上得以立足的艺术特色——已被悉数删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时西方世界秉持自我中心的文化立场。法语本的编辑杜赫德(Du Halde)对原文本的评价是这种立场的具体体现。他认为:“中国戏剧不遵守三一律,也不遵守当时欧洲戏曲的其他惯例,因此不可能跟当时欧洲戏剧比拟”(Du Halde, 1735: 342) 。另一位批评家阿尔更斯 (D’Argens) 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赵氏孤儿》的作者没有遵守那从前使希腊人那么高明,而不久前又使法兰西人跟希腊人媲美的种种规律”(D’Argens, 1741: 161) 。①原文为法语,作者阿尔更斯假托两个中国人的私人通信,以中国人的口吻表达了其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看法。本文的引文译自英语译文Chinese Letters,译者匿名:In our comedies,Dear Yu Che Chan, we don’t observe any of those rules which formerly made the Greeks so perfect, and which for an age past, have made the French as perfect as the Greeks. I own to these that I could heartily with, that tho’ we don’t care to subject ourselves to the rules which the Europeans call the three unities, we should at least preserve a little more of the probable in our plays.毫无疑问,这些批评的依据是其时盛行于欧洲的古典主义戏剧美学,这种欧洲中心的文化立场扭曲了元杂剧的艺术品相。而即使译本保留的部分也是选择性的,这种选择性翻译归因于其文化利用的动机,对中国古典戏曲文本的文化利用成了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这是为欧洲十八世纪的社会历史发展困境所决定。
十八世纪是西方社会启蒙思潮高涨之际,启蒙主义者急需引入外部思想资源改变历史进程,值此时机中国的《赵氏孤儿》因其理性、道德价值为启蒙思想家看中。该剧首先被译为法语,随之被译为英语,英语世界接受中国古典戏曲的历史进程由此开始。十八世纪早期,欧洲传教士开始大量地进入中国,他们向欧洲传回了关于中国的种种文献,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包。这对于苦苦寻求外部思想资源以摆脱西方社会发展困境的启蒙思想家无异于旱季甘霖。就此而言,中国的古典戏曲登上十八世纪的西方舞台与其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密切相关,其中的价值观放射出的熠熠光辉启蒙了迷茫中的西方社会,在西方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彰显出中国古典戏曲的重要思想价值。然而随着启蒙主义的退潮,中国的价值观念对西方社会的思想价值随之减弱,中国戏曲与西方文化的接触陷入了长时间的中断。
这种情形持续到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西方文化的内在矛盾激化到了顶点,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利益集团,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西方社会秩序即将崩溃。这种情形促使西方反思自我文化,同时再度把目光转向了中国这个文化他者。一些智者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古典戏曲得以再度获得进入英语世界的历史机遇。与十八世纪相比,此时的西方开始出现了多元文化思潮,于是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中国古典戏曲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对其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的解读、翻译也都发生了变化。
2. 英语世界接受的第二阶段
二十世纪之初英语世界接受中国古典戏曲这一过程首先发生在美国,起因与第一阶段的文化利用不同。当时为修建贯通美州大陆的铁路,大量华工充当劳工来到美国,随之带去了中国古典戏曲。十八世纪的英语世界接受的是传教士翻译的中国戏曲,是被扭曲的文本形态的中国艺术,这样以舞台表演见长的中国戏曲就失去了向英语观众展示其艺术魅力的机会。而二十世纪美国社会接触的中国戏曲则是舞台形态的艺术,这应该是被其接受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戏曲起初在华人圈子中演出,但当地民众对这种独特的艺术却逐渐产生了兴趣。这种演出新奇、妙曼,美国民众甚为惊奇,当然也伴随诸多不解。但无论如何,这是令人着迷的艺术。如果说十八世纪西方的《赵氏孤儿》是一部中国戏曲,那只是就故事的中国元素而言,且主要意指戏曲的价值观及故事背景。而中国戏曲的舞台表演,在此之前,英语世界还从未有过直接体验。美国社会对中国戏曲的兴趣成就了1930年梅兰芳剧团访美巡回演出。这是英语世界再度接受中国古典戏曲的标志,标志着在沉寂百年之后中国戏曲再度激发了英语世界的兴趣。梅剧团在美巡回演出六周,成为一时轰动的文化交流盛事,连当时美国著名演员卓别林也观看了他们的演出。先前普通华人社团的演出使美国人初见舞台上的中国戏曲,而梅兰芳剧团的演出则使其领略了中国戏曲艺术的高度。梅兰芳因此被美国舆论称为中国的“文化大使”,而原本一次私人剧团的商业演出被美国戏剧界抬到了“国事访问”高度(Yel, 2014: 23)。
梅兰芳剧团的访美演出首先起于美国民众的兴趣,这一层面上,还难以看清文化立场这种思想层次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有待从学术或艺术界中去寻找。就在美国民众开心于中国戏曲的同时,学界对其的兴趣也开始提高。他们一方面对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进行比较研究,另一方面还积极地进行翻译改写。这一时期他们对中国戏曲的艺术价值开始有了客观认识,与第一阶段的完全否定截然不同。这意味着英语世界接受中国古典戏曲的立场悄然发生了变化,开始由自我文化中心立场转向多元文化立场。
2.1中国戏曲研究中的文化立场转变
多元文化主义的主旨是,任何文明都是历史的产物,是特定传统、地域、生存条件下的具体形态,都有内在理据,特定的价值体系。没有一种文明可以宣称比其他文明更为优越,也没有理由以主流文明自居,歧视、否定甚至取代其他文明(王希,2002: 49)。而“文化的多样性对于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生物平衡那样的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
多元文化思想萌芽于十九、二十世纪之初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内在矛盾激化的时期,是对西方自我中心思想的否定。虽然这一时期世界尚未形成完整的多元文化思想体系,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接触,却成了多元文化思想的催化剂。这也是中国古典戏曲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的别样体现。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英语世界陆续出现了关于中国古典戏曲的专著,但这些专著大都局限于中国戏曲知识入门级的介绍,如舞台形式、背景、道具、服装、化妆、行当、角色、表演程式等。这些介绍多是中国戏曲译文的伴随部分,甚至名称都无多大区别,如The Chinese Drama,The Chinese Theater等。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一部对中国戏曲较有深入研究的专著,《中国戏曲》(The Chinese Theatre),作者为祖克尔(A.E. Zucker)。该书讲述了中国古典戏曲的起源、发展过程,从唐朝的参军戏开始,到民国时期的京剧,还介绍了梅兰芳这位对中国戏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艺术家。关于中西戏剧的比较研究,作者专辟一章。这章是作者对中国古典戏曲所持文化立场的集中体现。
十八世纪《赵氏孤儿》进入西方世界时,其“曲白相生”的艺术特色,不为西方接受,视为“奇奇怪怪的混合在一起的东西”。而在20世纪的祖克尔看来,这种奇怪的混合物与西方起源时期的戏剧没有区别。他发现,古希腊的戏剧既有道白,也有歌唱。而且歌唱形式更为丰富,既有乐队合唱也有演员独唱。当剧情发展到高潮、演员感情迸发之时往往用歌唱形式表达 (Zucker,1925: 192) 。古希腊著名歌剧《阿伽门农》是这一艺术形式的典范。他进一步解释,古希腊戏剧中,抒情部分都通过歌唱来表达,而普通的对话多采用道白形式 (Zucker, 1925: 193) 。该书从古希腊戏剧中发现了中国戏曲艺术与之的相同之处。反观十八世纪的西方人士他们眼中的是中国古典戏曲与西方戏剧的相异之处。求同或求异的差别,实质是背后的文化立场的差别。
西方戏剧有悲剧、喜剧之分。中国戏曲如此划分是否妥当,至今纷纭不断。该书作者虽然没有提出自己的看法,参与分类的讨论,但其从悲喜剧这两个概念的源头入手探求中西戏剧分类的共性这一点来看,其本心不难识别。
古希腊文化中,“tragedy”和“comedy”原指两种音乐。tragedy原意是“羊之歌”(a goat song),或指祭拜酒神迪奥尼索斯(Dionysus)仪式上所唱的歌,或指仪式上为羊这个祭品所唱的歌。不管何种所指,该词都是一个音乐名词。另一方面,comedy (comus)是指酒神祭拜仪式上所唱的生殖之歌。祖克尔发现,从戏剧源头上讲,古希腊戏剧是按音乐形式分类的,而中国戏曲也是按音乐形式分类的。中国戏曲共分为昆曲、皮黄和梆子三种(Zucker, 1925: 193) 。就戏剧分类的起源而言,中西戏剧是相同的。至于西方的“悲剧”、“喜剧”或中国的“文戏”、“武戏”的划分都是历史演化到后来的结果。
在祖克尔之前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古典戏曲在西方看来是“奇奇怪怪的混合物”,相比于西方戏剧,是一种原始、幻稚的娱乐形式。在这一背景下,祖克尔能够发现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的共性是他对中国戏曲认同的一种表现。如果说梅兰芳剧团访美反映了大众层面对中国戏曲的兴趣,那么祖克尔的认同一定程度上则是学界兴趣的反映,也标志着英语世界对中国戏曲的理解扩展到了更广的社会层面。
两种艺术形式都是各自文化的具体体现,根据多元文化主义都有相对的价值,无优劣之别。祖克尔这些关于中国古典戏曲艺术价值的看法很难说是英语世界的普遍看法,但至少表明英语世界中已经出现了基于多元文化思想评价中国戏曲的倾向。1930年梅兰芳剧团访美巡回演出可以视为这种倾向的先期反映。如果美国社会对中国戏曲没有普遍的新的认识,梅剧团访美的巡回演出是不可想象的。毕竟这是私人剧团的商业性演出,剧团生存的考虑肯定要重于国家间的文化交流。
中国戏曲音乐也是此前英语世界对之不屑的另一方面。祖克尔将中国戏曲音乐与英国伊丽莎白时期戏剧做了比较,发现中国古典戏曲音乐的嘈杂喧闹恰似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北京的外国人对中国的打斗戏(fighting plays)唯恐避之不及,音乐锣鼓过于嘈杂。但是如果同样这批观众在伊丽莎白时代,就会对这种吵闹、器乐打击、甚至金属敲击声,以及各种插诨、打科变得开心不已”(Zucker, 1925: 210)。现代外国观众最为讨厌的这种喧闹音乐不仅存在于中国戏剧,也同样存在于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中国戏剧难为西方观众接受的那些特征,祖克尔在西方戏剧中仿佛都找到了类似的情形。他这样做意在说明中国戏剧的“不雅”并非其独有,而是中西方戏剧的共性或者通病。这里他没有给出价值判断,而是表现出对这些通病的某种理解。这里合理的推论是,中国古典戏曲与西方戏剧具有同样的美学价值和相当的艺术水准,没有高下之分。
祖克尔不仅对中国戏曲的艺术价值做出了多元文化主义的评价,而且对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也与西方的进行了比较。这是他努力全方位地寻找中西戏剧的共性的另一表现。他发现中西观众的欣赏习惯也多有相似之处,这一发现即使当今的戏剧研究者也颇为好奇。中国戏曲观众,尤其北方的观众,通常将戏剧欣赏称为“听戏”,伊丽莎白的时代观众也有“听戏”这种说法(Zucker, 1925: 197)。诉诸听觉是两类观众的共性。他还认为,诉诸听觉也能解释两种戏曲舞台布景较现代西方剧场更为简陋的原因。
他还发现中国古典戏曲观众与演员互动的方式并非是独特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观众也是一样的。表演场面精彩时,观众会发出叫好声;糟糕时会发出嘘声。伊丽莎白时代的观众对糟糕的表演则不仅限于嘘声,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向演员投掷鸡蛋、苹果或者石块(Zucker, 1925: 205)。祖克尔的这种表达是有感而发。关于中国古典戏曲的欣赏习惯,西方普遍认为中国观众缺少应有的礼仪规矩,当然这与他们的文化立场有关。而他的意思是说,两相比较,西方观众的反应往往更为粗野。
祖克尔对中国传统戏剧的观察思考表明英语世界对中国戏曲的接受进入了一个明显不同于先前的阶段。这除了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中国戏曲与西方文化的深入接触等因素以外,更要归于他的文化立场,以及中国古典戏曲的美学价值和艺术魅力,而其在中国剧场的亲身体验更是其多元思想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都是先前英语世界观众/读者所不具备的,也是其对中国古典戏曲的认识的历史局限所在。
他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及特有的文化立场发出了关于中国古典戏曲美学的不同声音,他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他对中国戏曲的这种认识并非孤例,这一时期另外一些中国戏曲研究者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这进一步证明了英语世界对中国戏曲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
2.2文本翻译中文化立场的转变
与祖克尔同一时期的阿林顿(L.C.Arlington)和艾克敦(H. M. Acton)也是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者和翻译者。他们的英译本《戏剧之精华》(Famous Chinese Plays)中对原文的增删改写随处可见,大量的副文本包括了译者的评价、原文本人物与西方历史文化人物的比较。①《戏剧之精华》出版于1937年,1963年再版。再版者为位于纽约的Russell & Russell公司,上海字林报社印刷,北平法文图书馆发行。本文引文均引自再版本。
阿林顿是美国人,1879年来北京为中国政府工作。长期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使他对中国古典戏曲有了深刻的认识,期间出版了《中国戏曲》(The Chinese Dramas,From the earliest time until today, 1930)。艾克敦是一位年轻的英国诗人,1932年来北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与诗歌。阿、艾二氏合作翻译的中国戏曲结集称为《戏剧之精华》。 该书的译者前言声称,中国戏曲同西方戏剧一样都是人类的心灵律动,是人类寻找情感共鸣的艺术表现(Arlington, 1963: XII)。这一声言肯定了中国古典戏曲的美学价值。鉴于十八世纪以来将近两个世纪里西方普遍看轻中国戏曲这一社会文化语境,阿、艾二氏的这种认识的文化价值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关于中国戏曲的艺术特征,也即为十八世纪的西人所诟病之处,二人的认识也具有颠覆性意义。他们认为:西方的戏剧艺术,歌唱、表演、舞蹈各种艺术形式界限分明,艺术表现的可能性因此受限,而中国戏曲则将多种形式融为一体,相得益彰,给予了艺术表现的最大可能性,这是真正的戏剧艺术(Arlington,1963:XIII)。曲白相生的元杂剧在十八世纪西方批评家看来是他们难以接受的异类,而在阿、艾二氏看来正是这种形式使中国戏曲的艺术表现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二种思想认识的区别一目了然。
《戏剧之精华》的翻译,寻常翻译文本中的增删改写随处可见,因此,我们在此无意详述,而其中“比附”与“评价”等策略则是表达其多元文化思想的独到手段。
“比附”这一概念源自佛经翻译实践,《戏剧之精华》的“比附”策略与此不同。他们并非借助目标语相近概念进行翻译,而是将原文中的主要人物与西方历史文化人物进行比对。这一策略意在诉诸西方观众/读者的文化经验,将原文剧中人物与西方的人物相关联,以强化译文接受者对原文人物的亲近感,缩小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距离。在戏剧翻译史上,《戏剧之精华》首先将这一策略用于中国戏剧的翻译实践,为缩小文化差距提供了有效翻译策略。这一策略完全改变了先前“译文加注释”这种通常作法,成为匹配二人多元文化立场的个性化翻译策略。
京剧《击鼓骂曹》的翻译中,他们的这一策略得到充分展示。该剧的主角祢衡在《三国》的故事中尽人皆知,如果缺失有关他的历史文化知识,观众/读者对戏剧中其与曹操两人的冲突,以及祢衡这一角色体现的人性深度都难以理解。他们一改通常的文化背景注释这种作法,直接将祢衡比作莎翁名剧《雅典的泰门》中的阿帕曼托斯(Apemantus)。阿氏是位哲学家,思想深刻,但性情乖僻,为人尖酸刻薄,这是英语世界普遍的文化经验。将这一人物与祢衡相比,西方观众/读者理解陌生的祢衡就有了历史文化基础,对其性格特征的理解会更为透彻。
他们的译文中,河北梆子《金锁记》中的女主角窦娥被比作《尤利西斯》(Ulysses)一剧中的帕涅罗佩(Penelope)。帕涅罗佩是剧中人尤利西斯的妻子。尤里西斯漂泊在外时,帕涅罗佩面对众多诱惑,不为所动,始终不渝地等候丈夫归来,她是西方文化中女性忠贞的化身。通过这一比附,西方观众对帕涅罗佩的情感就在不觉中被转给了窦娥。这种“文化移情”手段有效地调动了西方观众/读者的文化经验,成为文化解读阐释的心理基础。
类似的策略在他们的译本中随处可见。如《九更天》中的女儿岳香被比作希腊神话迈锡尼国王阿加门农(Agamemnon)的妻子,依菲琴尼亚(Iphigenia),西方文化中另一个忠贞女性形象。《一捧雪》中的负心人汤勤被比作本·琼生名剧《狐狸》中卖身投靠的小人伏尔蓬涅(Volpone)(Arlington, 1963: 262)。
《戏剧之精华》中比附策略的运用,译者的思想基础是两种戏剧代表的文化是平等的存在,构成了多元互补,可比性由此生成。
阿、艾两位的比附策略体现的多元文化思想需借助分析才能分辨清楚,而他们译文中的“评价”则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们的这种思想特征。
京剧《牧羊圈》中主角朱春登战后归乡,初遇母亲、妻子时,双方互不相识。对此译者分析:西方人可能觉得这不合逻辑,但在中国人看来离家多年未归,初次相见就直接冲上去拥抱,也不可思议(Arlington, 1963: 317)。译者指出了两种生活经验的不同,因此行为模式的心理预期不同。这是不同生存环境,不同文化模式作用的结果。不同的行为模式对不同的生存环境或文化模式都是合理的,都有自身的价值。
京剧《翠屏山》的译文中,译者又一次对中国的文化行为模式进行了评价,其中的多元文化思想非常典型。该剧是对中国文化忠义价值观的艺术阐释。该故事取材于《水浒传》石秀杀嫂。剧中梁山好汉石秀发现义兄杨雄之妻与和尚通奸,怒而杀之。对此行为译者的评价是,“石秀、杨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我们西方文化不能赞同,特别是二人杀死那位女子后得意的神态,我们更无法开心。不过中国人依据的是自己的行为标准”(Arlington, 1963: 389)。这里译者指出了不同行为模式背后存在各自的价值标准。虽然他们并不赞同剧中人的行为,但他们并没对此给予价值判断,而仅仅对不同行为模式特征给予了第三者描述。毫无疑问,描述文化差异而不附加价值判断这是他们的多元文化立场的具体表现。
纵观英语世界接受中国古典戏曲的历史过程,二十世纪英语世界对中国古典戏曲的接受发生了变化,主要原因是其对待中国戏曲以及中国文化的立场发生了变化,由自我中心主义变到了多元文化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而祖克尔、阿林顿等人的翻译研究则是这一进步的具体体现。
3. 结论
十八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中期,英语世界接受中国古典戏曲经历了两个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英语世界出于自身文化发展的需要,以文化利用为目的,接受了中国古典戏曲的思想价值,但同时否定了艺术价值。接受与否定的思想基础是其时欧洲的自我文化中心主义, 由此产生了对中国文化的误读。随着中国戏曲与英语文化接触的深入,中国戏曲的内在文化价值逐渐彰显,以及伴随社会历史的发展,多元文化思想的形成,英语世界逐渐认同了中国戏曲的艺术形式之于中国文化的合理性,对中国戏曲艺术特征的文化认同开始出现。
中国古典戏曲为英语世界接受的两个阶段反映了文化交流的一般趋势。一种文化接受另一种文化始于文化利用,这一过程的文化误读也为必然。但随着两种文化交流的加深,和多元文化思想的影响,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认同将会产生,这又推进了多元文化思想的发展,文化自我中心主义将随之不断转向多元文化主义。
英语世界对中国古典戏曲的接受始于文化利用,成于文化认同,这一基本趋势对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启示。中国文化走出去伴随文化误读,这是文化利用引致的必经历史过程,同时也与中西文化权利关系格局不无干系。中西文化交流将伴随文化误读而不断发展,发展的趋势将是对他者文化的认同,因此正视文化误读的历史必然性,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改变当下中西文化权利关系造就的多元文化格局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