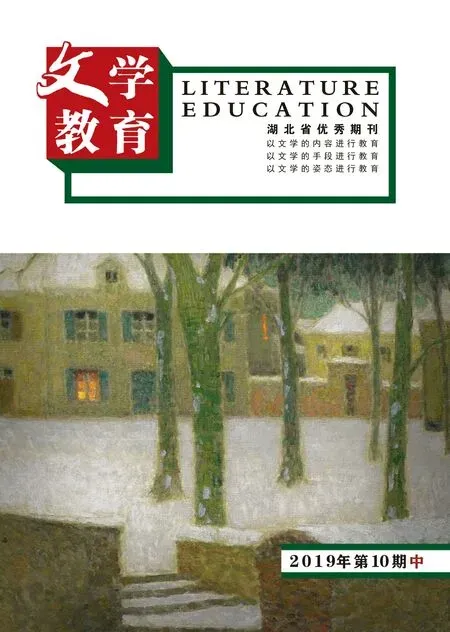战争与人性的伦理选择:《杀死父亲》评论
于 歌
普罗哈诺夫(Проха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ндреевич)1938年出生于第比利斯,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曾在尼加拉瓜、阿富汗、柬埔寨和安哥拉担任通讯员。在2004年凭政治惊悚小说《黑炸药先生》获得“全国畅销书”奖。现任《明日报》主编。普罗哈诺夫的作品原创风格明显,强调语言个性。在新闻和艺术创作中,他追随基督教,表现出对俄罗斯和所有俄罗斯人的同情。根据Юрия Поляков 的说法,从美学角度看,普罗哈诺夫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而从学派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他又是一位帝国作家,认为自身哲学是帝国士兵的哲学。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组合。
“战争”是俄罗斯民族文学中一个格外重要的题材。《杀死父亲》(Убить отца)是普罗哈诺夫于2005年发表在《火花》(огонёк)杂志上的一部战争题材的短篇小说。据介绍,本文为作者从部队战斗归来后写于汉卡尔—摩尔金斯基将军的部队在阿尔贡雪谷搜寻哈塔卜的地方。小说采用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讲述了俄罗斯第二次车臣战争中的一段战斗经历。
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方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聂珍钊14)本文拟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原理从三个方面分析这篇小说,反映作者在新时代对战争的新思考,阐释作品中战争与人性的伦理道德主题。
1.人物形象和战争伦理环境
普罗哈诺夫创作的多部作品都与真实的历史事件有关。根据作为战地记者的经历和对战争的思考,他写作了这部小说。小说讲述了俄军特种分队队长叶利扎罗夫大尉奉命追剿车臣头目曼苏尔。然而狡猾的曼苏尔有勇有谋,一再逃脱,并制造多起恐袭,击毙投向“联邦元首”的首领和毛拉(伊斯兰学者的尊称)。无奈之下,叶利扎罗夫根据联邦安全局的授意击毙了曼苏尔的父亲,在曼苏尔回家参加父亲葬礼的路上将其击毙。
人物形象和战争伦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就人物形象而言,文章主要刻画了两个人物形象——特种分队队长叶利扎罗夫和车臣匪首曼苏尔。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中,作者较为客观中立。没有大段苍白的文字去歌颂俄军大尉的英勇顽强和匪帮首领的残酷不仁,而是通过冷静、客观地叙述来表现大尉对军事任务的忠诚。叶利扎罗夫轻伤不下火线,连续三周追捕曼苏尔,愈挫愈勇;作战指挥灵活机动,在埋伏曼苏尔的过程中,对匪徒进行分组包抄,身先士卒;友爱和缅怀战友,“他从扎列伊科身上扯下银色圣母护身袋,命令将他的遗体放到指挥装甲运输车内。返回的路上,叶利扎罗夫一直紧握着扎列伊科沾满泥土和鲜血的手。”;爱戴自己的父亲,战争期间他对老父亲甚是想念。是父亲教会他如何埋伏,如何在雷道上行进,以致在射杀曼苏尔父亲过程中他表现出长久的抗拒和犹豫。叶利扎罗夫的人物性格是矛盾的。他温柔且哀伤,在追捕“幽灵”曼苏尔的持久战中筋疲力尽,渴望战争结束的那一天,“可以躺在温暖的帐篷里休息,有桑拿、电视、医疗点温柔的女护士,可以和挚友扎列伊科大尉见面。”而作为一名特战队员,他英勇顽强渴望战斗。尽管失败一次次袭来,他仍然聚精会神谋划每一次围剿,在与曼苏尔的决战中,他甚至迷信地希望曼苏尔不要现身,好像曼苏尔的命运已经和他连在一起。因为,当残忍又绝望的曼苏尔活着,他叶利扎罗夫就活着。
曼苏尔不仅与联邦军队作斗争,而且与自己的人民作斗争,对敌人和自己的人民都是残忍的。在刻画曼苏尔形象的过程中,作者也没有刻意诋毁车臣匪首,只是通过平直的叙述,表现出曼苏尔的凶残狡诈和人性柔情的一面,比如他将扎列伊科割喉时的冷血,将仇敌引入特战队员圈套的狡诈,将和平使者易卜拉欣暗杀时的无情以及强奸并杀害女俘虏的残忍;但同时在曼苏尔身上也保留了一丝人性,他在战争即将结束想要离开车臣后的第一件事,是回家乡卡尔山奇镇看望父母,并“将在战争中得到的厚厚一叠美元交给父亲”。故事的最后,曼苏尔父亲被杀。根据之前对曼苏尔的描写,以曼苏尔的智商,他完全有能力推测出这是一个圈套。但他依然奋不顾身地前往父亲的葬礼,想要看望父亲最后一眼,最终被联邦军队以狂轰滥炸的方式击毙。
文题中的“父亲”指的是曼苏尔的父亲。这位父亲向当局投降,劝儿子留下,向当局自首。因为他了解战争的不公正,想要拯救他的儿子。他曾是一名教师,希望有一个不同命运的儿子——“要不然你可以上学,去莫斯科,去大学深造。现在可能是律师、银行家或画家”,而不必“像狼一样在森林里面流窜,整日被直升机搜索”。他爱他的儿子,在临死之前,这位父亲“时不时停下向大山望去,仿佛希望能从夜峦中找到儿子发出的秘密信号”。这是一位伟大的父亲,这也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父亲。他没有罪之将死,却被当局秘密暗杀。这种悲剧性所产生的文学激情只有小说的审美空间才能容纳。
2.战争伦理与人性伦理的选择
伦理选择是人的道德选择,即通过选择达到道德的成熟和完善。(聂珍钊 2014;267)长久以来,伦理选择都伴随着精神或肉体蜕变的艰难过程。不同的伦理选择取决于所处的伦理身份。不论是曼苏尔的父亲,还是叶利扎罗夫的父亲,他们始终秉持善良的天性和慈爱的父性,他们用全部的热情和宽广的胸怀拥抱他们心中幼小无助的孩童。但叶利扎罗夫和曼苏尔却因具备不同的身份经历了一场痛苦而揪心的伦理选择。
叶利扎罗夫作为联邦军队的特战队员,他生命的意义是抓住曼苏尔并杀死他,为挚爱的战友报仇,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安定。他是一名军人,这是他的职业。面对狡猾的敌人,杀死敌人的父亲是结束曼苏尔的唯一途径。在联邦安全局中校给叶利扎罗夫下达任务时,文章将帐篷内茶杯和神像的前后状态作对比,反映了叶利扎罗夫内心的诧异和抗拒。在叶利扎罗夫刚刚进入帐篷时,中校茶杯中的茶叶翻滚,帐篷上还缝有神像;但当任务下达,叶利扎罗夫离开时,“茶叶在黑色的茶杯中继续翻滚;防雨布上,圣母像反射出微光。”茶杯变黑,圣象发光,都暗示着无情的任务——“击毙曼苏尔的父亲以吸引曼苏尔上钩”将是一次巨大的人性考验。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击毙曼苏尔的父亲无疑是违反人道的。俄军当局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击毙老人后,散布谣言称老人的死源于曼苏尔仇敌的复仇。尽管面对的是敌人的父亲,叶利扎罗夫看到的仿佛是自己的父亲。父子亲情对于他和曼苏尔来说一样重要。作为一个“儿子”,哪怕作为一个人,他都不忍心扣动扳机,“叶利扎罗夫想扔下枪,变为消失,化作一束光,从地面飞走。”但是从作战的角度来说,此举无疑是用最小代价达到最大的目的,即用曼苏尔父亲一人的死亡,挽救更多无辜的生命,从这个角度看,它又符合人道主义。极度的伦理困境和精神困顿折磨着叶利扎罗夫,他击毙的不仅是一个老人,一个父亲,还有自己人性中的善良。但同时,他成为了一名冷酷又合格的军人。这种矛盾产生的根源来自战争。战争本身就是恐怖和不公正的,战场上的敌对双方之间没有善恶,只有胜利,而毋庸置疑,叶利扎罗夫赢得了胜利。
叶利扎罗夫选择结束“父亲”的生命,狡猾残忍的曼苏尔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独立而又骄傲,“或藏作林中之狐,或隐为山中之羊,或化成斑斓野鸡,或游为水中鳟鱼,消失地无影无踪。”但是面对父亲的死,他愿意功亏一篑,飞蛾扑火折回故乡。他心中的父子亲情超越了战争本身,此刻他不再逃跑,无论输赢,择善弃恶,将仅存的人性付诸到这次自杀式的探望中。两者的不同选择揭示了普罗哈诺夫在小说中寄托的不同伦理立场和人性关怀。
3.战争、民族和宗教的历史悲悯
战争是一种无法理解和宽恕的暴行。战争造成的伦理灾难和参与者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伦理环境考验着每一个人。在战争中是没有善恶的,正如对敌人善良,就是对自己残忍;反之,敌人也应该恪守同样的法则。突然想起之前读过的一部抗日战争题材故事。在一次战斗中,八路军俘虏了数名日军,个别日军深受重伤。当时的军医坚持要给日军治疗,甚至用了对自己人都舍不得用的珍贵药品。然而在治疗的过程中,日军对医疗所偷袭,毫不留情的杀死了在场的军医。那作者又是如何看待战争的呢?
叙述者把自己批判性的同情融入客观的叙述中,我们一时难以捕捉作者的立场。我们只能在作者对战争、民族和宗教的错综关系中,找寻作者对人本身的历史悲悯和同情情怀。当扎列伊科第一次和叶利扎罗夫在战场上相遇,他说了一句话——“活下去”;当他被曼苏尔俘获,遭到侮辱和杀害时,最后一句话也是“活下去”。我们可以看到,以扎列伊科为代表的一部分俄罗斯军官是厌恶甚至恐惧战争的。他们并不像通过战争建功立业,只是想战争早日结束,自己能幸运的活下来。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战争本身的无情和可怕,任何人只要参加了战争,不管你是自愿还是被迫,是代表争议还是邪恶,都身不由己,随时可能被战争夺取生命。战争中的军人尚且如此,何况手无寸铁的平民。
战争结束了。叶利扎罗夫感觉“他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一千年,但参加过的战争微不足道,而新的战争像山一样一个接一个地袭击着他”。很可能他不会感到宽慰,他甚至更难,因为他“杀死了他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