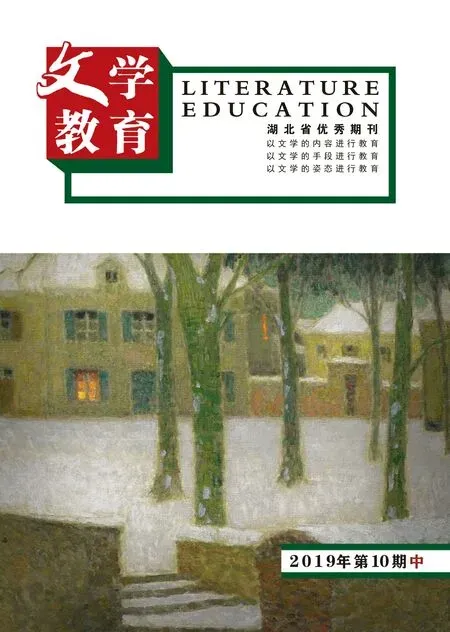批评的祛魅与逻辑的游戏:毕飞宇《小说课》与作家批评
丁苏晨
《小说课》是201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大家读大家”丛书系列中的一部,作品中大部分篇章都是毕飞宇2015年在《钟山》上的专栏,而这个专栏的文章,大多来自毕飞宇在南京大学开展讲座时候的讲稿。对毕飞宇《小说课》的研究,多集中于对这部作品在小说批评上做出的贡献,如刘艳认为,这种文学批评能够“回到文学本身”,是“有温度的”[1],张定浩认为,小说家批评的共同出发点,是“对着整个过去已有的、最好的文学见解在发言……他们在拓展文学的边界。”[2]段崇轩认为,穿越在理论与创作之间的毕飞宇把握了小说的深层规律和艺术真谛。[3]也有批评家指出作家批评与其自身创作的内在关联。如王彬彬则指出,作家在批评的过程中,会不经意间泄露出自身创作的秘密。每一个写作者都会建构起一种与经典作家的关系,而《小说课》,便是这种关系的反映。[4]如叶立文指出,作家批评体现了批评体式的解放与重写他者的自由,其中复述与重写则是他们常常使用的批评策略。[5]这其中交错的关系值得研究。
本文则着力于站在文学批评体式的立场上,探究这部作品广受好评的深层原因;通过深入文本内在逻辑,探究毕飞宇论证之方法,试图为当下的文学批评发展做出呼唤与努力。
这部作品在大众与专业角度上都可以说是广受好评,其销量高居不下,且被专业学者评价为“有温度和体贴的文学批评”[6]。究其原因,这与传统学院派文学批评与普通读者接受程度之间的间隙有关,亦与毕飞宇文学批评内在的逻辑追求有关。
一.批评的祛魅
“祛魅”一词,源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7],这一概念在当下有了更多的解读。文学的“祛魅”,即统治文学活动的那种统一的或高度霸权性质的权威和神圣性的解体。[8]这种解释,可以来自权威的文学观念与文学体制的压迫,具体而言可以是文学批评范式的限制。
“批评的失语与无力,是中国文坛始终存在的一个问题……从整体上来看,文学批评已经失去了对创作应有的指导和传播功能。”[9]论其原因,一是由于当下学院派批评家对西方文艺理论的理论崇拜,种种专业的、欧化的术语使得普通读者对学院派批评望而却步。而毕飞宇的小说批评,则以处处强调着“我”的存在的批评角度,“回到文学本身”的细读方法,缜密而自洽的逻辑结构,鲜活而富有激情的语言,为小说批评蒙上了一层“毛茸茸的”质感。普通读者不必熟读西方文论经典、不必研读枯燥的论述文章,亦能读懂文学批评,亦能从经典名著中读出反逻辑的罅隙,读出不易发现的内在纹理,这无疑能对“用自我施魅的方式去追求批评的合法性”的学院派批评家带来冲击。法国人阿尔贝·蒂伯代在本世纪初写的《六种文学批评》按照批评家的性质将批评分成三种类型:以报刊记者为主体的“自发的批评”,以大学教授为主体的“职业批评”和以公认的作家为主体的“大师的批评”。[10]这种批评理论应用于当下的中国可以说毫不过时。在八九十年代,汪晖、李陀、刘小枫等人的学术批评是一种带有个人感性经验的学术随笔,这类文章在阐释学理知识的同时不去刻意遵循严密的学术格式,这使得这些文章肆意而鲜活,有启迪之功效。新世纪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爆炸式”地传入中国,研习理论成为风气。而近十年来随着作家批评的兴起,“学术随笔”这种体式的文学批评似乎有重返文坛之势。
毕飞宇的《小说课》以其作家的审美能力与敏锐眼光,专注于“我”对文本的解读。说到关键处,他要强调一句“在我看来”;析到疑问处,他要说“我要提个问题”。这种个人化的解读,恰恰是一种为当下理论先行的批评风气祛魅的做法。这也体现在书中另一个典型特征,即毕飞宇对小说细部的观察与对“反逻辑”的揭示。他常常着眼于文本内部的细节,对小说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这种分析与理论无关,只关乎文本内部的逻辑结构。但是他并非力图达到文本内部的“真实”,而是在无限拓宽小说的阐释空间,他论小说,不关作者的事,可谓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例如在《“走”与“走”——小说内部的逻辑与反逻辑》这一章中,毕飞宇以《水浒传》中林冲“风雪山神庙”一节与《红楼梦》中王熙凤一节中的局部拿来分析,洋洋洒洒,细致入微。他通过林冲的“走”,来析出林冲是按照文本的内部逻辑,自己“走”到梁山上去的。
“由白虎堂、野猪林、牢城营、草料场、雪、风、石头、逃亡的失败、再到柴进指路,林冲一步一步地、按照小说的内部逻辑、自己‘走’到梁山上去了。这才叫‘莎士比亚化’。在‘莎士比亚化’的进程当中,作家有时候都说不上话。”[11]
这种类似于侦探小说般的逻辑推理,实在是引人入胜,令人叫绝。同时,毕飞宇分析了《红楼梦》中的“飞白”现象——他从文本的反逻辑之处,看出了人物关系的深密幽微,看出了作者的“不写之写”,看出了小说深层次的内在肌理。他根据王熙凤探视重病的秦可卿后的三句关于“走”的描写,来解析《红楼梦》小说描写的反逻辑。王熙凤刚刚离开秦可卿的病床,竟然“正自看院中的景致,一步步行来赞赏”。大多数读者也许只会有不适,但可能并不会多么深入地思考——而毕飞宇联系到王熙凤在决定收拾下流的色鬼贾瑞之后“方移步前来”的动作,联系到贾珍与秦可卿关系的特殊,尤氏对于这一切反常关系的态度等等细枝末节,将这些叙事的“线头”串联在一起,发现了表层文本遮盖之下一个更为巨大的、纷繁的世界。这些解读,或许会被认为是一种“过度解读”,可谁也不能否认,这些发现有其自身的美学肌理,有其激动人心的力量,能为读者带来一种阅读的惊喜体验,这些往往是学院派批评无法带来的。
《小说课》作为作家批评的代表作品,虽然做到了批评的祛魅,但是还是一种对技术层面上叙事方法、叙事角度、逻辑性的追求与考察,对于作品的深层精神内核、对于语言运用的美学特质、对于小说在其时代背景所具有的意义及地位都涉足较少。可以说,《小说课》将文本基本脱离于上述因素,从而对文本做出形式主义的分析,这类分析既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又有其不可逃离的缺点,即为逻辑而逻辑,陷入逻辑的圈套中无法走出。
二.逻辑的游戏
在《小说课》中,毕飞宇有抽丝剥茧的耐心与细致敏锐的洞察力,但是仔细分析,《小说课》中表面看起来自洽的逻辑,实际上有其裂痕与经不起推敲之处,作家毕飞宇在使用一种令人炫目的创作方法,与读者进行“逻辑的游戏”。
作家的文学批评,更大程度上应该被称为是一种“创作”,这种创作是一种基于作家阅读与写作经验的重写。这种“重写”在《两条项链——小说内部的制衡与反制衡》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在这篇文章中,毕飞宇对莫泊桑的《项链》做了一个有趣的“重写”:将原文中人物的名字、故事发生的背景改成符合“中国国情”的汉语版《项链》,但最终得出的版本却“面目全非,漏洞百出、幼稚、勉强、荒唐,诸多细节都无所依据”,从而得出了一个结论:文本的内部隐藏着真正的文学。这种“重写”在《小说课》中或隐或显地出现,它依靠的是毕飞宇对“反逻辑”的体察和对缜密逻辑的追求,是一种逻辑的游戏。毕飞宇,或者说《小说课》正是依仗着国人(或者全人类)对所谓“逻辑完整”中蕴含的安全性的本能依赖而进行文学批评。之所以称其为“游戏”,是因为毕飞宇在寻找逻辑的自洽与反逻辑的罅隙之时,自身的逻辑性亦值得推敲——换句话说,用《小说课》对其他文学作品的批评方式,亦可以用来批评《小说课》这一“文学作品”的逻辑与反逻辑。
以《两条项链——小说内部的制衡与反制衡》为例,毕飞宇在将人物姓名、故事发生背景置换后,寻找了十条(甚至可以更多)的“破绽”。摘取两条“破绽”如下:
第一,作为教育部公务员王宝强的太太,张小芳要参加部长家的派对,即使家里头没有钻石项链,张小芳也不可能去借。王宝强和他的太太都做不出那样的事情来;
第二,相反,哪怕王宝强的家里有钻石项链,他的太太张小芳平日里就戴着这条钻石项链,可他绝不会戴着这条项链到部长的家里去。在出发之前,她会取下来。他不想取下王宝强也会建议她取下;[12]
一般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会受到作家的牵引,尤其是这种看似“缜密”的逻辑推理式语言出现之时,出于一种急于获取答案的阅读心理,读者往往会一定程度上忽视推理的前提条件。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毕飞宇实际上运用了一种游戏般炫目的笔法,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至自己的思路,而这种思路并不能经受细致的逻辑推敲。在第一点中,张小芳为什么不可能去借项链?一般的中国读者,出于个人经验与对国情的体察,大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张小芳的确不可能如此:因为社会地位和面子使得借项链变成一件尴尬之事,任何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不可能这么做。然而再深入思考便可发现问题:为什么在莫泊桑《项链》的那个时代,马蒂尔德就可以坦然地向弗莱斯洁借项链了呢?毕飞宇显然是在预设了这部小说的极度合理与完美的前提条件下,为我们的读者进行一种置换,从而使得国人体验到一种“不可能”的经验,便以此证明他的观点——(《项链》)的内部隐藏着真正的文学。毕飞宇对《项链》的解读大致有三个层次:一是对《项链》的解读之解读,这一层次联系了国家的政治历史状态而对之提出了批判;第二层便是对《项链》的“置换式重写”;第三层便是对《项链》背后蕴藏的契约精神、忠诚精神进行的解读。这三个层面的解读新颖且有见地,其中提到的一个“小说是公器”的文学观念也能够支持其论证;且我们不可能否认《项链》的文学价值,因而毕飞宇的结论是无可置疑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论证过程钻了逻辑的空子——第二个层面上的置换,是缺少道理的。毕飞宇在置换背景的时候,对于这个游戏的“理性依据”只是几句模糊的书写:“今天的中国金钱至上,今天的中国资本垄断,今天的国人爱奢侈。换言之,今天的中国和1884年——也就是莫泊桑发表《项链》的那一年——的法国很类似。”我们并非生活在1884年的法国,对当时的国情处于一种“不在场”状态,至多只能通过政治经济条件去猜测当时的社会状况,然而这种猜测是否真的能够成为小说批评的理性依据?怎样确定在当时的法国这一借项链的事件就一定比“置换”后中国的事件更为合理?经验与常理在小说的解读中是否应该占据主导地位?毕飞宇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是一种“语焉不详”的状态,他用作家的创作手段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而绕过一些更为深层的逻辑问题。这也是毕飞宇在《小说课》中体现出来的“逻辑的游戏”。
三.结论
用《小说课》中的分析方式去分析《小说课》,会发现这本小说评论的逻辑疏漏之处,这正是《小说课》“创作化”的一个结果,也是其分析方式的一种弊端。中国当代作家批评往往同作家个人的创作经验紧密相连,如残雪建构起一套以卡夫卡为主要作家的“西方正典”,为自身创作寻找精神源流,“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余华通过其随笔批评,为自己的文学道路转向提供方向与依据;王安忆借用小说创作课堂,提出自己的创作原则并付诸实践等等。他们普遍因不满于文学批评所受的学术桎梏,在话语方式上具有一种反理论的写作倾向;对先验的批评方法的规避,对概念和体系的突破,以及对批评文本诗性本源的回归等等,均能体现出一种解放批评体式的努力。然而,在批评的过程中,如何不落窠臼,找到祛魅与逻辑的平衡点,找到个人经验与理性分析的平衡点,找到有温度与理性的平衡点,这是文学批评值得努力的方向。
注 释
[1]刘艳:《做有温度和体贴的文学批评》,《中国文学批评》,2018年第3期,第14页.
[2]张定浩:《文学的千分之一——读毕飞宇的〈小说课〉》,《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6期,第25页.
[3]段崇轩:《倾心营造小说的形而上世界——毕飞宇的小说理论与创作》,《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4期,第125页.
[4]王彬彬:《毕飞宇〈小说课〉评析》,《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6期,第20页.
[5]叶立文:《作家驻校制与作家批评的兴起》,《小说评论》,2018年第5期,第74页.
[6]刘艳:《做有温度和体贴的文学批评》,《中国文学批评》,2018年第3期,第14页.
[7]〔德国〕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9页.
[8]陶东风:《文学的祛魅》,《文艺争鸣》,2006 年第1期,第6页.
[9]叶立文.作家驻校制与作家批评的兴起[J].小说评论.2018(05):70.
[10]〔法国〕阿尔贝·蒂伯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页.
[11][12]毕飞宇:《小说课》,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