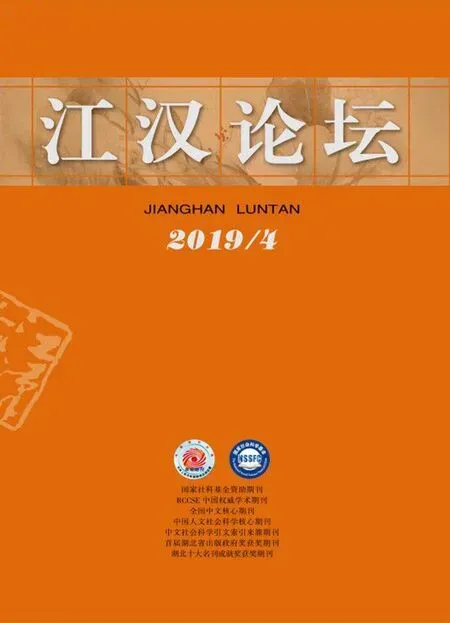南方春讯:广东改革文学论
李海燕
改革开放后广东迅速崛起的社会现实给作家带来强烈刺激,他们直接感受到改革开放的突出成就与剧烈变化,体会到广东变革的时代精神与文化传统,以紧跟时代步伐的态度绘制了一幅幅现代化与城市化的改革风云图,从而使广东改革题材创作在全国文坛独树一帜,成为广东文学突出的标识。从新时期初期陈国凯的工厂系列、吕雷的南海油田系列,到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章以武、黄锦鸿的《雅马哈鱼档》,再到新世纪陈国凯的《大风起兮》,吕雷的《大江沉重》,彭名燕、孙向学的《岭南烟云》等,我们可以感受到广东40年来在政治经济制度、价值观念、社会形态、生活形态等方面的巨大变革,广东在他们的笔下被赋予了强烈的时代气息和变革精神。
一、改革的先锋:从新旧之争到现代性质疑
众所周知,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以“现代化”为名的“宏大叙事”,作家们对改革题材热衷的实质是对民族现代化的渴望与梦想。广东作家孔捷生、陈国凯、吕雷、何卓琼等人以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高度的责任意识对正在行进和变化中的城市面貌和城市生活进行了多方位的展现:孔捷生、陈国凯致力于新时代工人生活状态和文化观念的转变,吕雷、何卓琼关注中国传统企业迈向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与困境,章以武、黄锦鸿的《雅马哈鱼档》引领了“个体户文学”创作潮流,钱石昌、欧伟雄的《商界》表现极具南国都市意味的商业改革大潮……新时期初期的广东作家们以满腔激情书写着南中国大地由传统到现代的变革之歌,给文坛带来了南方的改革春讯。
所谓“改革”,一般指革除旧观点旧力量,倡导新文化新思想新制度。《汉语大词典》将“改革”界定为“变革,更新。现常指改变旧制度、旧事物”①。《现代汉语词典》则认为“改革”是“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②。很明显,“改革”必然会涉及到新旧之争。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新旧之争更是尖锐剧烈。邓小平认为新时期改革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③新时期改革文学既敏锐感受到时代的改革诉求,又及时把握住改革大潮有关新旧之争的本质内涵,将改革进程中不同思想、观念与价值的较量争斗全面地呈现了出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首开“改革/反改革”的斗争模式,随后的改革文学也莫不沿着这一模式发展。在广东,吕雷的南海油田系列可谓权力斗争式改革小说的典型代表。他的《火红的云霞》 《炫目的海区》 《海响》等作品均形象再现了转型时期改革与保守两种对立势力的矛盾冲突。陈国凯、何卓琼等人亦惯于在小说中设置改革与反改革两大对立阵营,新旧之间的冲突与斗争被他们演绎得淋漓尽致。
改革开放的滔天巨浪将旧与新、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中国与西方等众多二元对立的话题带到人们面前,也同时带来惊奇、向往、惶恐、失望等各种现代性体验。诚如马歇尔·伯曼所说,现代性“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④但新时期之初改革文学的现代性话语却常常传达出一种坚定的理念:现代化改革势在必行,虽不可避免各种矛盾与斗争,但最终会走向现代化,实现国家与民众的现代化梦想。《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光朴使岌岌可危的电机厂焕发出新面貌,《新星》里李向南对顾荣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三千万》中丁猛始终保持着破旧立新的勇气与信心,《祸起萧墙》中傅连山坚持不懈的改革热情令对手叹服。广东新时期之初改革小说同样表现出一种线性历史发展观,改革者们大多对现代化怀着强烈渴望。他们认为现代性是民族国家的拯救工具,现代化改革则是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自己的改革行为必将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火红的云霞》中,梁霄成功打赢了“南化下马”狙击战,把“有限的资金花在‘四化’的刀刃上”;《炫目的海区》里,在罗文岳和陆烨的合力推动下,龙穴海区的中外合资有条不紊地进行;《总工程师的日常生活》中许融顶住人情压力,撤掉庸才厂长,重用技术专家,顺利完成电业公司的现代转换……但是,虽然改革在精英人物的引导下常有一个良好的结局或美好的展望,可改革者却往往陷于悲剧性处境:梁霄克服情感羁绊完成了工厂的顺利转型,但他本人却“落荒而逃”,被更上层权力部门打发到山区小县;罗文岳、陆烨等人均面临着家人的不满和权力身份的丧失。改革者悲剧情境的设置不仅使改革文学避免了简单的理想化和概念化色彩,使改革表现出凝重与艰难的一面,而且将传统与现代的各种羁绊展现在读者面前,加深了作品的道德忧患感和现代人文意识。
与天津、北京等地早期改革文学大多遵循斗争模式不同,广东的早期改革文本并不太注重工厂或企业改制中改革与反改革的矛盾纠葛,对流行于文坛的“现代化”领导权争夺话题亦无多大兴趣,他们更倾向通过日常世俗生活表现改革进程中时代的脉搏跳动与人们的心理情感变化。孔捷生的《普通女工》通过开钻床、数木盘、带孩子、忙家务等一系列日常生活琐事塑造了一个脚踏实地、勤劳朴实,努力追求自我与社会现代化的城市小市民何婵的形象。对何婵而言,她的生活由做工和带孩子两大部分组成。做工,她认真投入,力求零次品。带孩子,她希望儿子能有个快乐健康的成长环境,为孩子倾力付出。何婵认真踏实的生活态度赢得了大家的尊重、改变了居住环境、改善了家人关系,而她个人也在充实坚韧的日常生活中认识并提高了自我。孔捷生以日常题材写主旋律作品的手法在广东文坛颇为常见,陈国凯早期改革小说亦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工厂姑娘》中,阿香们在恶劣的日常工作环境下萌生起技术革命的强烈意愿。虽然他们的改革方案遭到官僚主义者们的反对与否定,但他们巧妙设计了一场由书记、厂长们亲身上石灰的劳动场面,最终如愿以偿地促使技革方案成功上马。
日常务实是岭南民众生存的主要形态,岭南文化也逐渐发展成以日常性为标志的软性文化。广东作家们以日常叙事展改革风云手法的普遍性应用使新时期初广东改革文学显现出与众不同的面貌,而现代性质疑的率先出现更昭示着广东改革与广东文学的先锋特征。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谓“现代性”是从社会学角度而言,它是社会全面现代化要达成的目标,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⑤,即“社会现代性”或“启蒙现代性”。而“现代性质疑”则指向文化(美学)领域内的现代化批判与反思,它是对启蒙现代性的断然拒绝与强烈否定,即我们常说的“审美现代性”。在广东改革文学中,陈国凯的工厂系列首开审美现代性批判之先河。当内地还纠结于新旧观念之争时,先行一步的广东已出现了欲望泛滥所致的各种现代性危机:厂领导为了出国玩乐而反对技术革新,宁愿花费一大笔外汇进口设备;香港混混用金钱开道顺利取得营业执照,堂而皇之地走私贩卖商品;广州马仔用不法手段谋取暴利;文艺青年借自由之名玩弄女性……陈国凯敏锐感受到广东改革开放进程中剧烈的社会变化、复杂的社会矛盾、不断出现的社会缺失,将这些问题融入到岭南民众的琐碎生活与情感纠结中,既超越了新时期改革小说的斗争模式,又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性反思倾向。
《雅马哈鱼档》 《商界》等作品的多元现代性表述同样突出。它们摆脱早期工业题材的局限,将目光投向商业领域,表现极具南国都市意味的商业改革大潮,反映市场经济发展对人们思想、生活、人际关系等领域的变化,探讨现代化变革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与个人问题,并力图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说,吕雷的宏大叙事主要着力于改革之争,陈国凯等人的日常生活叙事多关注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塑造,《雅马哈鱼档》 《商界》等商改作品则关注于经济理性在1980年代的初步显现。所谓“经济理性主义”,“是指以交换逻辑为基本存在逻辑,以经济行为为基本的存在形式,建立在货币哲学存在基础之上的以收益最大化为指归的经济思想体系。”⑥作为新时期最早表现城市个体经济、反映个体经营者生存状态的作品,《雅马哈鱼档》引领了“个体户文学”创作潮流,改编的同名电影于1984年上映后在全国引起轰动,并成为广东改革开放的第一张名片。当古老的帝都与昔日的“东方巴黎”仍沉浸在历史创伤记忆与迷惘彷徨之中时,南方的街边仔(女)们已打开鱼档,欢欣鼓舞地走向改革新天地。小说的先锋之处在于它首次着力于个人追求财富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传达了新时期初期人们对物质现代化的向往与渴求。但经济理性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个人物质富足、主体解放的同时,它还会诱使个人欲望无限膨胀而至个体“自我萎缩”。作者意识到经济理性的这一弊端,对阿龙、鱼仔们以不当手段获取不义之财的行为给予了批判和否定,并要求都市青年在“发财致富”的同时坚守正义和道德,以现代价值理性和道德观来规约极度张扬的经济理性,在“如何赚钱”的主题之外,又强调了“如何做人”这一话题,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两种话语在《雅马哈鱼档》中得到很好的融合。
二、时代进行曲:现实的记录与历史的反思
从文学思潮的角度来看,改革文学自1985年后因“寻根文学”“现代派小说”等文学潮流的影响而走向衰落,“文化因素的发掘,使创作的理性增强,也使作品的思想容量加大。而结果是,改革作为创作题材的重要性减弱,使得‘改革小说’作为一种创作潮流成为历史。”⑦但作为一种题材的创作,改革主题在1985年后仍然存在,改革开拓精神依然长存。1990年代以来,上海作家转向了集体怀旧,北京作家沉迷于欲望书写,广东作家却更关注正在行进中的社会现实。他们直面社会,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记录下改革的足迹,捕捉不断深化的改革给人们带来的持续变化,在时代精神的召唤下创作出一系列深受读者好评的改革小说。如《神仙·老虎·狗》(程贤章)、《世纪贵族》 (彭名燕)、《岭南烟云》 (彭名燕、孙向学)、《告别残冬》 (邹月照)、《虹霓》 (余松岩)、《大风起兮》 (陈国凯)、《大江沉重》 (吕雷、赵洪)、《蓝蓝的大亚湾》 (何卓琼)、《终结于2005》(展锋)、《那儿》 (曹征路) 等。这些作品或记录某一历史时段的改革现实,或全景式呈现恢弘的改革历程,生机蓬勃的南中国改革进程就这样呈现在读者面前。
“文章合为时而著”,变革的时代呼唤变革的文学,作为现代性书写重要组成部分的改革文学,其核心内涵是“改革开拓精神”,1990年代以来的广东改革文学一如既往地洋溢着改革激情,表达着人们对于现代化的集体渴望。《大风起兮》全景式地呈现了深圳工业区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改革历程,方辛们在变革激情的引领下将一个荒芜的海边小渔村发展成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大都市。《世纪贵族》绘制了一幅国有企业从苦创基业到挺进国际市场的改革画卷。原本平凡普通的于松涛、黎少荣们在时代感召下以一股生命激情成长为世纪贵族,追求着现代化新生之路。《神仙·老虎·狗》深刻地反映了粤北改革风云与客家生活场景,被时代大潮裹挟的牛皋以积极乐观的变革意识开启粤北山城的改革征程。《大江沉重》叙写了改革家邝建童、施之锐们以敢闯敢为的冒险精神带领山区小县走向城市化的变革征程。《红莲白莲》中拥有新观念新技术的马驰骋、杨燕芳等时代新人们凭靠充沛的青春激情将落后小镇建设成现代化大都市。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虽参照西方,但并不是西方模式的沿用和照搬,特殊的历史形态与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现代化改革根本没有多少经验可循。作为改革前沿阵地的广东,更是摸着石头过河,是激情与理想激励着他们在艰难险阻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从而在中国南方成功地打造出一个现代化大都市圈。广东作家们敏锐地把握住南中国这一时代精神与地方魅力,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充满激情的改革之域。
90年代的广东改革文学同样延续了80年代的日常叙事风格。虽然此时的改革文本多为宏大的主旋律作品,但浸染了岭南务实世俗之风的广东作家更倾向于以普通人的日常琐事、世俗纠纷来呈现剧烈变化的南中国。《大江沉重》将特区改革置于社会生活场景与世俗情感纠葛中加以呈现,既通过办酒会、穿衣服、吃饭、买卖楼花等城市日常生活琐事传达改革开放的宏大主题,又以夫妻、情人、同事等情感纠葛建构起特区改革的宏大框架:因不满妻子以肉体交易换取自己的政治前途,邝建童自愿到沧宁县担任书记;因钟情于县长施之锐,港商谢颖仪回乡投资;邝施二人的关系也不再是以往改革文学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携手并肩、惺惺相惜的互利互助。《世纪贵族》则是以错综复杂的爱情纠葛为主线展现特区企业的改革史,《告别残冬》以鲁家二子一女的家庭与情感生活来揭示1990年代都市改革众生相,《那儿》更突出工厂改制过程中工人的困窘生活,《终结于2005》以姬姓家族的日常生活变化反映农村的城市化……南中国改革书写在作家们日常世俗的生活叙事中变得生动多彩,南中国亦焕发出强烈的世俗风味和生活气息。
如果说1980年代的改革文学多注重当下与日常,宏大的历史意识与全球意识则是90年代改革文学的突出之处。1990年代以来,随着上海浦东的开发和国家经济重心北移政策的推行,长三角强劲崛起,急遽赶超珠三角,迅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引擎”。面对着长三角咄咄逼人的经济发展态势,再兼有素来的政治边缘、文化沙漠的身份焦虑,广东的失落感和危机感日益强烈,作家们纷纷以“重返”的姿态书写广东惊心动魄的改革发展史,搜寻改革之初各城市的魅力与激情,试图在历史、现实与未来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为社会与人们建构改革之城的身份认同,从而缓解广东人们的心理焦虑。《世纪贵族》 《大风起兮》分别从不同角度书写了深圳特区波澜起伏的改革历程,《大江沉重》 《红莲白莲》展示了珠三角小城镇20多年的工业化历史,《终结于2005》对珠三角乡村的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历史性观照,《告别残冬》对1990年代南国都市在改革大潮下呈现的各种复杂现象进行了广泛描写,《那儿》借小舅朱卫国的命运悲剧表现了南国都市的国企改革史……广东改革文学因全面呈现南国都市风云变幻的改革历程而表现出明显的凝重感与历史感。但广东改革史的建构并不同于对“老上海”神话的迷恋,而以“正在行进着的历史”将历史与现实连通起来,显现出改革身份认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全球化意识的增强可谓广东改革文学的另一特征。与1980年代改革文学多将目光局限在国内经济技术观念的破旧立新不同,90年代的改革文学更关注全球化进程中的城市变迁。《大风起兮》中,深圳的改革开放一开始便由粤港合力进行,第一个工业区的开创队伍主要由颇具国际眼光的驻港代表和港人组成,他们采用现代最新观念,冲破现行管理体制,在特区全面推行工程招标、干部聘任、住房商品化等改革方案,从而使特区在短短几年间实现了思想的解放与经济的腾飞。《大江沉重》中,珠三角小城沧宁的经济改革与毗邻的国际发达城市香港有着密切关联。作家一开始便对两地进行了鲜明对照,在强烈的反差刺激下,邝建童决意借鉴香港经验,从香港招徕建设资金:他一方面到香港招商引资,向谢氏集团敞开门户;另一方面大胆闯荡香港炒卖楼花。虽然邝的举措带有很大的冒险性,但他一系列大刀阔斧的行为最终使沧宁产生巨大改变。《世纪贵族》中,特区改革者在招商引资的同时更注重企业的国际化拓展,如建立与美国企业的贸易往来,鲸吞香港公司,加盟西方大型企业等,改革者的一系列行为莫不展示着中国现代企业已崛起于世界之林。《终结于2005》里永新村的城市化发展也离不开香港资本的大量渗透。《蓝蓝的大亚湾》更是典型的全球化叙事。作品主要讲述了大亚湾核电站的诞生史,展示了现代高科技企业创建过程中各国文化尤其是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冲突,而公司从最初的单纯引进西方技术到整体接纳西方管理系统及工作人员的行为更是传达了作者希望整合西方优势资源为“我”所用的全球化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作家们对现代化、全球化带来的衰颓景象亦怀有警醒,他们敏锐地发现广东在快速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日益陷入贫富分化、价值崩溃、精神迷失等破碎纷乱的后现代场景。《大风起兮》里方辛遗憾地看到新创立的工业区已涌动着一股钱欲与权欲的腐败暗流,《告别残冬》里充斥着感情冲突、官场倾轧、利益追逐等各种欲望纷争,《世纪贵族》中事业成功后的于松涛显露出独断专横与自私狭隘的一面,《终结于2005》中大伯们既欣喜于城市化带来的富裕,更忧心于现代化对传统文化、乡村精神和土地的破坏与遗弃。执着人文关怀的广东作家们对金钱唯上、权力寻租、文化同质等现代社会危机产生深深忧虑,道德回望与文化回归往往成为他们的救赎之途。他们或直接将改革者们塑造成大公无私、坚持正义、勇于献身的时代英雄;或表现出强烈的道德批判意识;或流露出鲜明的怀旧情绪与乡土情结。烦扰于现代困境的广东作家们终以关注现在、回望过去的姿态超越了纯粹的全球主义与地方主义,从而做到全球与本土的更好融合与平衡。
三、独特的历史景观:南方精神与时代弄潮儿
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至关重要,它既直接介入生活,又影响着文学创作主体的精神状态与思维方式,制约着他们的创作风格和审美追求。广东改革文学深植于岭南文化的土壤里,岭南独特的人文环境与地理精神品格塑造了广东改革文学与众不同的面孔。与其他地域相比,广东改革文学延续时间长、反映现实面广、表现问题深、创作队伍庞大,既能及时把握时代脉搏的跳动,又能全景式呈现改革开放历程,南方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契合更使广东改革文学呈现出独有的魅力。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创新求变、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无疑是广东先行一步取得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是南方精神的精髓所在。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曾评论岭南人,“言语异,风习异,性质异,故其颇有独立之思,有进取之志。”⑧李权时等人亦认为,岭南文化是一种“非正统、非规范性的世俗文化”⑨。岭南人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和冒险意识。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岭南形成了海洋文化与农业文化相结合的特点,它不仅承传了百越文化,也深受中原汉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岭南文化一开始便显示出与中原主流文化截然不同的面孔。中原文化以儒为本,讲究“中庸之道”,岭南文化则远儒近商,尊崇冒险与创新。其创新求变意识在岭南历史中随处可见,近代以来更是屡屡表现出引领潮流的先锋诉求,涌现了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等一大批叱咤风云的精英人物。岭南人的这种勇于创新、独领潮流的变革精神以历史积淀与文化记忆的方式传承并延续了下来,新时期广东再次以领头羊身份率先开始了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创新精神与时代意识重新焕发出炫目的光彩。深圳、珠海、广州等经济特区与开放城市在各个领域奏响改革开放的号角,以“超前的”观念与行为走在全国前列,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先锋城市。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新旧更迭的复杂场景给广东作家们造就了得天独厚的文学资源,他们秉承岭南文化的先锋传统,发扬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用手中之笔奏响了南中国改革的华丽乐章,塑造了一个个致力于改革创新的时代弄潮儿形象。
“卡里斯玛型”的社会精英一般身处企业、公司或工厂的管理阶层,具有普通人缺乏的特殊力量或品质。如《商界》中的廖祖泉、《告别残冬》中的司徒伯伦、《世纪贵族》中的于松涛等均为现代企业家,《大江沉重》《大风起兮》 《红莲白莲》中的邝建童、施之锐、方辛、马驰骋们则是地方行政官员。而无论哪一类,他们均有着实施改革措施的权力,也较普通民众更早感受到国家意志和时代要求。但他们并不是毫无目的地施行改革权威,相反他们均富有开拓创新精神,拥有现代经营理念和管理才能,在他们有条不紊又屡见奇招的改革中,城市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廖祖泉的中外合资大酒店奠基了,于松涛的集团公司组建了,邝建童的小县城百业兴旺,方辛的大龙湾工业区日渐繁荣……
但廖祖泉们与充分理想化的乔光朴、李向南们仍有较大的区别。为迎合时代要求,乔光朴等改革家多被打造成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他们不仅具有开拓创新意识,还拥有拯救苍生、匡扶社稷的能力,更满怀着为国为民的牺牲奉献精神,他们的改革创举无不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故刘少棠曾评价他们为“换了行头的高、大、全”⑩。广东改革文学中的时代英雄们则表现出不一样的面貌,他们的个人野心、私欲与爱国心、事业心往往纠缠在一起,显现出人性复杂多元的一面。如果说新时期初期的改革者还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乌托邦色彩,那么1985年后的广东改革文学则逐渐摆脱人物神化和政治化的痕迹,改革者的个体意识日益增强,改革者形象逐渐丰富立体。如《商界》中的廖祖泉精明能干,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和现代商业头脑。在商业改革大潮中,他及时抓住时机、运用自己的狡黠聪慧将小小的街道木器社拓展为区级的东营工商联合公司,并成功引进外资筹办联营性质的东湾酒店,收购惨淡经营的岭南家具厂。廖祖泉无疑是商业改革大潮的领路人,也是个人利益的追逐者,他努力寻求自我欲望与价值理性的平衡,从而达到社会与个人的共同现代化,这也正如他送别情人时所说,“我希望能在改变中国现状中同时改变自己”。其他如《世纪贵族》中的于松涛,《告别残冬》中的司徒伯伦、鲁建国,《虹霓》中的章凤君等改革者,无不集传统与现代、自私与崇高、热情与冷酷、专横与自信等矛盾特点于一身。这些半天使半魔鬼式的改革者形象正是急剧变革时代新旧冲突和斗争的产物,是社会矛盾与时代特征的真实反映,就如同创作主体对改革英雄们的悲剧性情境设置一样,它们不仅使改革者形象更为立体丰满,也更能凸显改革的艰难凝重。
改革前沿的特殊地位、创新求变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广东改革文学在捕捉时代脉搏、迅速反映改革开放、塑造时代英雄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广东改革文学的独特之处,并不仅仅体现在改革时代精神与岭南创新意识的契合,亦突出表现为浓厚的世俗风味与平民色彩。当北京、上海尚处于改革与否的争论观望状态时,南粤的街头小民已热火朝天投身到经济改革大潮中。创新求变的文化传统使南粤人敢闯敢为,富有冒险意识;重商求实的岭南文化风格则驱使南粤人迅速与世俗现代化浪潮一拍即合,以积极主动的改革姿态成为时代的参与者与见证人。《工厂姑娘》 《平常的一天》 《姐妹之间》 《两情若是长久时》等一系列工业改革题材均展示了普通工人为争取自己的生活权利而投身改革的不懈努力。《普通女工》以普通女工何蝉从文革“伤痕青年”成长为现代化建设能手的坎坷经历揭示时代变革给人们带来的新生与活力。《你不可改变我》则传达了高扬个体独立人格的现代性主题。
岭南文化的平民化和世俗化对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广东作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大多倾向平民文学的创作,以平民姿态书写普通市民的世态人情与悲欢离合,他们的文学创作流露出鲜明的平民意识。广东新时期之初改革文学的平民化倾向在1990年之后得到了长足发展,《大江沉重》 《大风起兮》等作品中的平民形象更是栩栩如生。1990年代以来,世俗消费文化逐渐取代大一统的政治文化成为中国大众社会的主导文化。在大众消费文化的驱使下,作家们纷纷从庙堂转向民间,有关时代、历史与社会的宏大叙事也多让位于反映日常生活体验的个人化写作,平民化创作成为世纪末文坛的一大突出现象。对于90年代以来的广东改革文学而言,平民意识的凸显不仅源于时代语境与都市经验,岭南文化的平民化更影响着他们平民话语体系的建构,地域文化与时代文化语境的契合使得其平民化和世俗化倾向尤为明显。陈国凯、吕雷、何卓琼等人虽因精英地位、革命情结及家国意识将主要精力投放在主旋律文学创作上,但小说却融入大量日常性和世俗性生活场景,时代英雄人物的人性化和日常化具体可感,市井小民的改革者形象更是鲜活生动:作家冰莹勇敢地冲破婚姻牢笼去追求一段新情感;打工妹阿霞以兢兢业业的工作参与到公司改制中;因弟弟重病不得已委身老板的打工女孩夏淼淼执着追求个人的尊严、价值和爱情;风流女工阿笑敢爱敢恨;美丽出众的刘水芹以务实精神、精明头脑为特区第一个工业区添砖加瓦……这些人虽普通平凡,甚至卑微渺小,可他们不仅执着于个体现代化的追求,而且为民族现代化献出了自己的微薄之力。受岭南平民风范影响的广东作家从平民立场出发,以普通市民的生活变迁与情感纠葛见证南中国的改革历程,广东改革文学凭借其平民特色最大限度地缩短了政治叙事与世俗化写作之间的距离。
改革开放是广东的魂灵,改革气质塑造着现代广东,它将广东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边陲省份转变为经济大省,它促使广东初步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使广东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样板。浸染岭南创新精神与平民意识的广东作家敏锐地把握住时代变革精神,及时书写南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超前展示变革中纷纭复杂的矛盾冲突和各种现代性体验,并巧妙地融入岭南地域风情与平民世俗色彩,从而构建出一道既独特又绚烂的南方改革景观。
注释:
①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5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0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16页。
③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
④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5页。
⑤ 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8页。
⑥ 杨新刚:《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都市小说论稿》,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⑦ 王泽龙、刘克宽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页。
⑧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合集》第10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0页。
⑨ 李权时等编:《岭南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
⑩ 刘绍棠:《破除模式投身改革》,《人民日报》1987年9月22日。